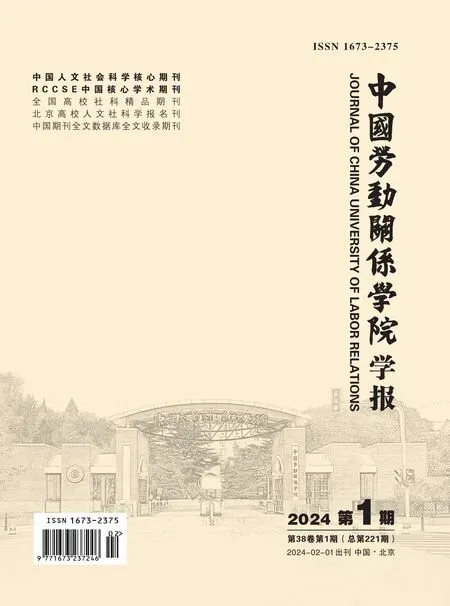倦怠社会劳动美的精神政治学审视*
2024-05-10宋丽丽
宋丽丽
( 1.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开放大学 发展规划与质量保障办公室,福建 厦门 361008;2.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将当下时代描述为功绩社会、积极社会、“兴奋剂社会”,相应地,当下时代的“人”沦为功绩主体(又译“KPI 主体”)、自我施暴者、加速主体。人工智能和数字社会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并没有让人获得更多休闲与安逸,反而让人陷入繁忙、沉重和日益倦怠之中。人们为了完成工作、为了完成业绩、为了所谓的更好生活,陷入了不断加速、不断自我施暴之中,在劳动与休闲、生存与生活、精神与肉体层面反复横跳和切换自我的精神状况,直至精疲力竭,成为倦怠主体。韩炳哲将这一倦怠主体描述为“倦怠的普罗米修斯”①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泰坦一族的神明之一,曾与雅典娜一起创造了人类,因将火种带给人类,惹怒宙斯,被用铁链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之上,其肝脏白天被鹫鹰啄食,夜晚又重新长出。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参见:韩炳哲. 倦怠社会[M]. 王一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前言.。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概念引发了数字时代和智能社会对劳动美的精神政治学审视,这一审视既包括劳动进化状况的时代之变,也包含智能劳动时代人的精神状况之变。梳理倦怠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典型特征、厘清倦怠社会的劳动美学之困、重塑人的劳动精神政治学,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倦怠社会之中人的精神状况的典型特征
(一)自我精神暴力疾病日益突出
福柯将18 世纪之后的现代社会称之为规训社会和“疾病分类政治学”(Noso-politics)的社会[1],将医院、精神病诊所、监狱、营房、工厂等空间和机构作为规训的场所和权力机构。规训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于暴力和规训是一种外在的驯化,主体是在特定空间被外在权力规训的“驯化主体”。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人的精神分裂、不断异化、逃逸,德勒兹将其揭示为“千高原”。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智能设备不断便捷化人们的工作,改善着劳动的效能。劳动的时间变得更加自由,人们在健身房、办公楼、咖啡馆、购物中心消遣娱乐时都可以处理闪烁于屏幕上的工作。这时,人们就从外在驯化主体走向了自我驯化的功绩主体。人们成了自己的雇主,规训的围墙不断从有形变为无形,从外界走向内在,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外在规训走向自我驯化,从权力的否定性惩治演变为自我绩效的肯定性加速。工作和劳动不再是外向型的硬性驱动而是内向型的自我驱动。自我加压和自我绩效导致自我精神状况的免疫系统受损,人们患上了注意力缺陷的疾病、患上了疲劳综合征。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加速使得人的身体似乎也丧失了器官的感受性能力,成为无器官的身体,自我成为一种欲望机器和效能机器的融合体。按照德勒兹的解释,“无器官的身体”可以理解为“疑病患者的身体、妄想狂的身体、精神分裂的身体、嗑药的身体、受虐狂的身体……”[2]。无器官的身体隐喻意在表明身体已经处于疾病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疾病的不断暴发。从主体角度而言,自我陷入肯定性的自我加速漩涡,只有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娱乐(购物、健身),才能抵消这种因绩效主义加速运动所带来的身心倦怠和由倦怠引发的焦虑。韩炳哲将其称为“肯定性暴力”,这种肯定性暴力是由于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数字信息过量导致的自我暴力。“由于过量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它们都是神经暴力引发的现象,由于它们不是由免疫学的他者所致,因此是非病毒性的。”[3]9-10自我精神暴力的疾病不是免疫类疾病,也不是病毒性疾病,它的攻击对象是自己、攻击源头也是自我精神。自我精神暴力疾病是自我系统内部的疾病,是一种加速社会之下的精神梗阻,它是面向无尽“操劳”状态的恐慌反映。自我精神暴力之眼不同于“美杜莎之眼”,美杜莎之眼是陌生美丽和恐怖直视的极端形式,自我精神暴力之眼是睁开双眼却反观自身的恐怖暴力。
自我精神暴力疾病不是敌我矛盾,而是自我矛盾。它产生于加速社会下的自我绩效、自我完善之中,甚至是在宽容平和的状态下显现。作为自我精神暴力疾病的患者经常用健身、喝咖啡来消磨时间焦虑和对抗倦怠,他们工作生活中一切正常。然而,其隐藏于正常生活之下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却很难被外界捕捉,也很难被外界拯救。自我精神暴力疾病以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疲劳综合征出现,在一个自我系统内部不断重复上演,直至燃尽自身、无比倦怠、精疲力竭。
(二)工作积极主义成为个人的精神政治学
超负荷工作、满载绩效和加速主义不一定带来倦怠,但自我加速和自我完善或将引发自我精神倦怠。自我加速和自我完善不一定完全指向生存论的劳动和工作,也指向虚假性的积极生活和消费主义的娱乐。当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阶段过渡到数字阶段,身体的剥削和时间的控制已经发生转变,表现为给予身体的自由和劳动时间上的自由。正如有学者所言,“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升级换代,速度代替数量的速度经济成为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物质杠杆。在平台化积累方式的推动下,时间和速度已然是当代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其在积累方式平台化发展中塑造了独特的资本主义时间景观”[4]。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时间景观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加速主义运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成为这一运动的技术利维坦。加速主义运动不仅体现为工作和劳动的效率至上,也体现在休闲娱乐和生活的积极主义行动之中。针对工作的自我监控和针对生活的自我监控一同进行,展现为工作中要做KPI 主体,生活中也要做KPI 主体。工作被一个个业绩主导,生活被一个个休闲娱乐的日程主导。韩炳哲指出,奢侈消费品、高档健身房、高档艺术品成为治愈倦怠、彰显积极生活、体现个人精神政治的有效形式。然而,娱乐和工作、生存和生活本就不能二分。事实上,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走向后福特主义、从鼹鼠游戏走向蛇游戏、从管制主义走向自由主义,已经将商品生产从物质领域推进到精神领域阶段,数据成为生产力要素,情绪成为商品,情感成为可交易的“物”,每一个功绩主体都可以自由地用积极工作和生活彰显自我的独特。然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且智慧的体系,它可以对‘自由’进行充分的利用,包括一切与‘自由’相关的实践、表达,比如情感、游戏、交流等”[5]4。积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生活化叙事,不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把“无限自我生产”作为一种积极叙事的逻辑去践行。
在工作中遭遇挫折和失败时,人们首先不去质疑公司、平台规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反而去反观自身是否哪里没有尽善尽美。自我施压和自我绩效促使自己向心中的完善自我迈进,然而,“在自我剥削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中,人们其实是向自己发起了侵略。自发侵略没有使被剥削者成为革命者,而是使他们意志消沉,无法振作”[5]9,进而通过积极生活来疏解工作中的倦怠。在数字时代,工作不只是坐在办公室、写字楼里的工作,它也可以在家中、地铁、咖啡馆中进行。但是,自由劳动的时间观念带来的不一定完全是便捷和高效,也有可能带来无法躲避的时刻处于劳作中的压力和焦虑。克里斯蒂安斯和杨雪指出:“人的‘数字化生存’业已从预言变成现实,人们既受益于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又受困于数字之网对生命的束缚和压制。平台经济持续不断地侵蚀着我们醒着的时间,使当代的数字劳工变成无休止工作的经济人,屈服于资本逻辑的操控,由此引发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问题。劳动者在数字工厂的高压环境中不得不疲于奔命,以至于精疲力竭,深陷倦怠之中。”[6]89这是由于资本的贪婪和不断革新的高效能数字新技术,这些技术从人那里获取的数据能量已经远超过了人的实际需要。大数据在让一切变得可视、可控、高效的同时,也导致数字平台和抽象软件(各类APP)与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大数据驱动、操控、管理工人,下达业绩、完成自动考核,人则沦为平台的利润机器和活的效能附属物。平台的算法速度、智能的革新速度、数据的完善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人自身的现有身体能力,使人在不断的加速中精疲力竭。因此,就有了“有限的现实之人与抽象算法无限增长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令人沮丧的顶点”[6]98。计算理性主义让有限变成无限,让现实变成虚拟,让“积极”成为必然性增长。
(三)积极消费、娱乐主义成为化解倦怠的至上之选
当下,“取悦自己”成为一种生活和娱乐的座右铭。然而,这种取悦不一定是自由自为的心境享受,而是虚假积极生活的例行公事。积极消费、娱乐主义成为化解倦怠的至上之选。在生活中,我们以消费主义取代本质主义,积极生活本身亦演变为一种带有符号性质的消费展示。鲍德里亚以消费物及其展示为切入点,揭示了在物的符号消费生存状态下人的抽象化和异化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就被定义为“景观社会”,这是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生活消费的景观。“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只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7]这也充分表明人沦为了卡西尔意义上的“符号的动物”,“这意味着在消费社会里,人们占有物的真实内涵不是蕴含在物的表面上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是追求体现在物中的符号意义”[8]。生活的符号主义崇拜、消费主义泛滥、形式主义程式,引发主体性的精神焦虑、空虚和无内涵性,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符号消费以即刻满足(购买的便捷化、物流的快捷化)为基础,在可见的社交平台(微博、微信朋友圈及其他社交平台)中获得即刻展示。数字化网络和可见社交平台为积极生活增添了即刻展示的翅膀,数字社交平台成为积极生活的见证者、开发者,但也让生活陷入符号消费主义色情展示的深渊。
我们在健身娱乐、游戏娱乐、社交娱乐、手办娱乐、饮食娱乐中穿梭,我们在数字化娱乐的氛围中陷入了对富有道德和至善意义的精神享受的疏远和冷漠。我们在娱乐中无比自律,我们将娱乐活动和娱乐获得感发展为一种个体的精神政治学。不好好娱乐就是未好好生活、未能愉快工作,娱乐变为有一种政治的强制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今天的娱乐现象的特点在于它远远超越了空闲时间的现象。例如,寓教于乐原本与空闲时间并无关系。娱乐的无处不在表现为娱乐的绝对化,这恰恰消除了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界限”[9]。当娱乐走向必然、娱乐和展示合流,娱乐就变得是政治性的而非自治性的,当娱乐成为疏解劳动倦怠的认知性态度,娱乐就会是至上主义的存在,娱乐至死与终身学习、工作一生成为同一话语。并且,积极娱乐的至上主义引发了沉思性生活和反思性批判能力的下降。娱乐将一切时间凝固为当下,数字社交、信息技术对人们的时间经验的威胁使自我时间生产机制受到阻碍,在对待过去时,人们不再接续传统、凝聚共识,逐渐遗忘;在对待未来时,人们不再渴望创造、建构理想,缺乏想象。“一切都将沦为娱乐:当我们既不严肃地沉思过去,也不忧虑地设想未来时,也就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娱乐化的时代,一个信息化导致娱乐至死的时代。而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时空加速和健忘流行。”[10]在积极娱乐至上主义的观念中,娱乐变得并非娱乐本身,娱乐变成唯一目的,但娱乐所引发的愉悦性感受却逐渐降低,用娱乐对抗倦怠的效果正在减弱。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每一个对闲散没有感觉的人因没有这感觉而显示出他还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那人性的’(det Humane)水准上。在这样一个人的生活里有一种不知疲倦的活动使得他被隔绝在精神的世界之外而将他置于动物的类别中……”[11]。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用各种琐碎、过量的数字化网络娱乐信息填补无聊的娱乐时间,实际上已经远离了“那人性的”水准,我们变成了网络视觉机器甚至是偷窥狂人。
二、倦怠社会的劳动美学之困
(一)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之困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2]。这种对劳动的定义是一种劳动创造论定义,抑或是“劳动创世论”定义,即谈论劳动时不是仅仅谈论劳动之于生存论的意义问题而是前生存论的意义问题,劳动亦是人类诞生、开启人类纪并取得创造性进步与发展的存在论问题。一般来说,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有的价值创造都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当我们谈论和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时,实际上是在从存在论的劳动美学视角谈论劳动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这里谈论的是“人类”这一存在物的整体状况。劳动“四最”观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体现了劳动与美好生活、劳动与劳动者、劳动与劳动精神的统一。但是,当马克思指出19 世纪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忍受恶劣工作环境和生存压力时,劳动的倦怠主要表现为精疲力竭的身体倦怠。当资本主义从机器大工业过渡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倦怠不再仅仅呈现为身体的倦怠,而是“身心倦怠”,尤其是心理倦怠。人被大数据的高效和算法的精准代码所捆绑,身体成为算法机器下的器官与附件,与马克思“局部工人”已经“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13]相比,今日的人已经沦为斯蒂格勒数字时代“一般器官学”[14]座架下的“整体器官”。在数字化的加速中,我们出现了知识短路、情感障碍、注意力缺陷等问题,在数字超工业社会的至效主义语境下,“超工业时代个体的扭曲和个体化的丧失”[15]已经延伸至具有普遍性的个体精神领域。由此而言,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之间显示出调和的困境与难以破除的张力,个体生存论的劳动倦怠发展出整体性的倦怠困局。当“关键的问题在于‘过劳’由被动性到自发性的根本性转变”[16]50时,作为整体性的倦怠社会就成为某种必然。这种“必然”既有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精神教化的奸险逻辑,即“功绩社会的主体倦怠感来自新自由主义精神下的‘成就自我’和‘效率崇拜’。自我和外界都产生命令,主体受到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主体将自己作为有待发展完善的功能主体,将自我剥削归为自我实现”[16]52,还有数字技术加速主义的无耻圈套,最重要的数字技术加速表现为平均的数字劳动速度的加速提升,即数字技术让数字社会进入持续性和整体化的加速阶段,并且“归根到底,数字加速是数字社会本身的加速,即数字变迁的速率本身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态度、数字价值、数字社会关系、数字生活习惯等皆随着不断提高的速率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改变”[17]56-57。由此产生了我们每一个“‘个性化’的数字劳动选择仅仅为数字系统化调控的结果,并非具有真正的自由,而是被迫在数字社会加速下持续生产‘剩余数据’。数字社会加速变成自驱式的内部循环系统。这一内部循环系统导致了数字时空异化、数字生活世界异化和数字自我异化三个紧密联系的数字异化层面”[17]55。“三重异化”使得作为整体存在论的劳动美学用之于作为个体生存论的劳动时举步维艰,倦怠只是一种结果和表现。
(二)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自我生成论的劳动观念之困
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价值作过这样的描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18]29,并且“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18]44。这些论述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表述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这些论述当然是科技进步论而非技术决定论,二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推崇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但人仍是主导力量而非技术,后者则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严格的技术决定论者还声称,追求效率和功用的内在驱动力是扎根于技术和使用技术的社会之中的,并认为技术变革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技术推动我们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获取我们的一切生存所需。然而,技术决定论“由此假设人民是技术的被动消费者,这从历史上讲是错误的”[19]。人民不只是技术的被动消费者,也是技术的创造者、开发者。人们不仅在消费技术及其创造物,也在通过使用技术和技术物创造美好生活,技术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谈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含义在于,一是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美(甚至是生活美、生存美),二是技术工具的进化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的简洁高效,进而实现人的休闲解放而非倦怠。马克思劳动美学的一个关键观点是超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的抽象定义与对现实劳动和具体劳动中的普通劳动者的贬低,达成对无产阶级基于劳动的解放的崇高美学建构。“马克思对劳动对象性内在特质的发掘,既完成了对劳动建构人本质的形而上学提升,又使劳动升华成对美的创造性活动、体验性过程和享有性感受。”[20]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科技进步论与劳动美学论的统一就不是单一的科技进步决定劳动美,而是人在劳动中蕴含美的创造活动、美的体验过程、美的享有性感受过程。这一观点并不排斥技术,而是显著表明劳动美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人本身。这种观点从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化过程、自我生命本真化过程、自我个性建构化过程来理解技术(亦包括由技术所创造的技术人工物、生产的商品等)。据此而言,技术进步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美的答案不言自明。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元宇宙、ChatGPT 等宣称如何提高劳动效率和创造无比美好的生活前景时,同样也带来了劳动加速主义运动和社会化的倦怠情绪。对于工作,我们庖丁解牛式的“工匠精神”变得匮乏;对于劳动,效率至上主义占据上风。韩炳哲通过阿伦特看到,“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积极生活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为劳作的层面”[3]28。诚然,现代社会不等于技术社会,但是将技术升级到决定论高度、将工具升级为目的本身,都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和劳动美学的社会。
如果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已经在由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元宇宙技术、ChatGPT 技术)所主导的平台、媒介、舆论上升为功绩主义劳动美学时,自我加速、自我剥削中的劳动倦怠似乎不可避免。人的劳动观念在倦怠社会和自我功绩主体观念合流挟持下,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劳动非美学的境地,就会“从活动生命走到倦怠劳动”,就会发生“功绩社会下的内卷与焦虑”,“所谓躺平便意味着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自身的消耗,自愿堕入不稳定性之中”[21]。从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技术工具的进化是否必然带来劳动的简洁高效,进而实现人的休闲解放而非倦怠——技术工具进化确实带来了劳动的简洁与高效,但并未实现人的休闲解放,反而引发了倦怠。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有一个著名的描述,“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165。这里描述的不仅是劳动也是社会分工,更是对何谓休闲的描述。从哲学视角分析,“休闲并未处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中,而是作为一种自我持留或纯粹的逗留。逗留的意义在于,当主体发觉自身静止不动或无所作为时,既没有急于摆脱‘令人不耐烦’的状态,也没有表现出某种无法自控和遭受苦痛的状态,而是回归到纯粹的逗留之中”[22]。虽然马克思所谈论的是针对劳动的描述,实际上也是在谈论休闲。休闲对应的是“逗留”,这种“逗留”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自持”,它不是急于摆脱繁忙,也不是无法控制或遭受痛苦的状态,甚至不是找个作为心安之处的时空,而是休闲带来了心安的时空。现代智能技术为人类的劳动、游戏、休闲创设了无比多样的工具和方式,但是,所有这些都依靠一种“网络依赖”的方式进行着,劳动是网络的,休闲也是,如果以自持的“逗留”观之,网络的游戏、休闲甚至不是休闲而就是“工作”,因为一方面这已经不是“逗留”而是“沉迷”,已经不是娱乐或休闲而是工作和劳动。这种沉迷不是没有代价的。从数字劳动的“免费性”观之,我们正在为大平台和大数据公司贡献我们的“眼球经济”,我们正在参与“受众劳动”并贡献“受众商品”,我们的“观看”行为成为互联网产销者劳动。正如福克斯所言,“脸书、推特和谷歌的用户永久地创建了被监控和商品化的内容及数据,致使在线行为实时总监视能够产生一个数据商品,从而依据用户兴趣和活动发送定向广告”[23]。这样一来,技术工具在带来劳动的高效便捷的同时,却也让人要么陷入持久工作、劳动的泥潭,要么陷入虚空网络的游戏休闲的深渊;要么被动成为互联网产销者,要么变成互联网商品的受众。
总之,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劳动美学与作为自我生成论的劳动观念,都在生发倦怠社会的精神政治学之困。如何认清和超越技术决定论,如何规避智能社会的劳动陷阱,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休闲观、生活观,是人们是否能够获得休闲自持与倦怠疏解的关键。
(三)神圣时间:一个倦怠社会的时间辩证法之困
马克思对工作时间有过这样的描述:“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18]407这个涉及无产者工作时间延长的问题直接点出了机器推广、分工细化等诱因。此刻,工作时间延长类似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作为产业军的“普通士兵”,“他们在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18]407下的被动延长。然而,当代数字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和自我加速的社会,工作时间的延长已经以弥散性质、“自由时间”形式融入数字化工作全过程,工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已经模糊,平台时代的劳动和价值创造已经出现“活劳动的社会性弥散,以及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性弥散”[24]。这样一来,似乎劳动越来越自由、劳动时间越来越自治,但这种“自由”劳动与“自治”时间带来的却是过劳症的精神折磨和自我精神世界的消解。自我实现(自我绩效)和自我毁灭(自我倦怠)合二为一。受制于数字资本和平台雇佣形式的限制,劳动者拼命加速,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零工从业者如同阿甘本所言的数字“神圣人”①“神圣人”是古罗马法中一种因罪而被排斥到政治共同体之外,可被任何人杀死的人物。参见:张凯. 神圣人[J].外国文学,2020(6): 89-97.,就连互联网的“大厂工人”也已经深陷畸形的加班企业文化之中,在加速化的“神圣时间”内不断过着无假日、无闲暇、无逗留的“神圣生活”。然而,“功绩主体幻想自己是自由人,拥有绝对主权,却处于效率的禁令之下,使自身成为神圣人”[3]86,承担着赤裸生命下的沉重。这种沉重似乎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人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是无产阶级,数字时代的互联网平台生产的是“无产阶级化”的拼命加班的“神圣人”和被数字平台排除在外的“神圣人”。拼命加班的“神圣人”将自己困在一种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Hamsterrad)之中[3]74,而被数字平台排除在外的“神圣人”成为人们常说的“无用之人”,前者在疯狂竞争和自我加速中失去时间自由,后者则被排斥在劳动时间之外。这样一种时间机制就是神圣时间,它构成了一个倦怠社会的时间辩证法。
在神圣人的神圣时间辩证法内,人们患上了过劳症、歇斯底里症,休闲时间被数据中介变为工作时间,经济生命大于一切其他形式的生命,数字虚体代替疲劳身体在数字界面和各类APP 中穿梭遨游,力图让现实身体恢复活力、抵消倦怠,实际的结果却是更加呆滞的眼神、更加僵硬的身体、更加迷离的精神的出现,人变成如同“僵尸”一般的怪物。既然数字化的常态是以虚体为中心构筑的僵尸学,那么,那些被数字化的生态圈剥夺了环世界从而沦为新时代的赤裸生命的个体就变成了怪物[25]。 在倦怠社会的神圣时间内,韩炳哲用“禁锢在没有节日的时代”来形容,这种判断是指人们由于繁忙、操劳无暇顾及节日和进行庆祝,人们无法在神圣时刻寻找内心的悠闲和与“神”联结。节日时间是另一种神圣时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如今由于工作、效率和生产变得绝对化,我们失去了一切节日和神圣时刻。工作时间变得极端化,它破坏了一切节日和庆典”[3]91。事实上,如今的人们忙于寻找各种过节的理由,试图放慢脚步、召唤曾经的自己。他们如下饺子般涌入旅游人潮、健身场馆、购物网站,“报复性”地旅游、健身、购物,试图通过这种“强硬”方式舒缓自己、瓦解倦怠。然而,事实上,由于倦怠围城未能拆除,加速主义、绩效主义未能消灭,短暂的休憩未能解决根本性的倦怠之困。悠闲生活和自我生命未能成为真正的叙事逻辑,社会个体依然遵循倦怠社会的逻辑重新起航。
三、何种精神政治学能够支撑起倦怠社会的劳动美?
已经是倦怠社会了,何谈劳动美学呢?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学把“自由”作为一种统治术,以精神自治和行为自由作为驱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的最佳模式。当经济系统中出现数字技术和算法模型作为驱动工作的典型时,人们对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感到不适[26],竞争性内卷也因此催生 ,劳动自然变得不是美学的而是焦虑和内卷的。从事实来看,数字技术支撑的经济模式和算法驱动的工作模式不会停歇,“量化经济”和“量化自我”会一同进行。数据主义和智能算法已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开启了新的数据启蒙主义运动。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都需要在新的数字化时代中重建自我的精神状态,以应对倦怠社会的冲击,回归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
(一)弱化自我加速和功绩主体定位,防止劳动畸形
马克思针对异化劳动问题曾这样描述:“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8]53这种批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资本对工人和劳动的剥削本质。劳动创造了美,但是,资本的贪婪却使得劳动畸形化、加速化,无论泰勒制还是福特制,都是一种绩效主义的表现。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泰勒主义也演化为对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无可比拟的信任,人被还原为比特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加速运动,启动了数字资本的“速度辩证法”。“数字资本主义主要呈现为‘数字泰勒主义盛行’与‘生活生产化’。前者表现为劳动工具统一化、劳动操作极简化和规训手段自动化,后者表现为生活空间工厂化和生活时间殖民化”[27]。生活空间的工厂化、生活时间殖民化实现了资本对每个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可能,一种绩效主义生活化的主张变得合情合理,反之,个体就会被排斥。自我加速和功绩主体成为自我定位的首选,这恰恰是劳动变得畸形、人变得异化的开端。因此,在对抗由资本、企业文化、社会系统生成的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作为劳动者的人不能陷入自我加速和功绩主体的定位之中,而是要回归劳动的本质状态,即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美,而非人沦为效率机器、异化成愚钝和痴呆状态。只有认清加速主义的本质危害、超越过劳的观念和行为限制,才能防止劳动畸形和人的异化。在实践中要注意防止两类“过劳症”,“一类是由于竞争压力等外在强制力被迫选择长时间超强、超时的工作,常用‘强制自发性’来刻画该类群体特征。而另一类群体则会表现出强烈的成功感、自我追求完美的内驱力所导致的主动选择过度劳动”[28]。要避免成为“焦虑社会”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要注意从观念认识层面、精神政治层面建构美好生活视域下的劳动精神,而非陷入倦怠精神状态下的劳动“异人”;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劳动本质的界定和美好生活的主张,将“被商品化全面渗透的生活并非美好生活,被货币所物化和赋魅的生活并非美好生活,被资本逻辑所宰制的生活并非美好生活”[29]的观念植入劳动精神塑造之中。
(二)主动建构抵消数字资本、技术平台牵制的生活模式,回归美好生活
当下倦怠社会的各种观念、互联网技术平台和自媒体传播机制深度融合,构造了一个强大的数字劳动观念网络,如同传染病一般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和工作劳动态度,积极主义和消极主义、加速主义和倦怠主义充斥于各类人群之中。不得不说,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在构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同时,也在打造新型的数字新教伦理和文化。因此,必须认清“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数字规则’所形成的隐秘规范力来进行社会调节与生产分配”[30]的阴谋,消除其对个人时空、生活工作观念进行数字裹挟的危害。依据阿伦特对劳动、工作、行动的定义,“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的人之条件”[31]。虽然阿伦特把劳动视为生命本身,将工作视为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适应的活动,有贬低人之条件的劳动价值和工作价值之嫌,但其所主张的积极生活需要以行动作为条件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这种积极生活既不是盲目、毫无节制地投入重复性的劳动或工作,也不是无思考、无批判地盲从跟随他人的观念行为。积极生活是一种沉思性的、选择性的实践生活,因为“人要展现自己的个性、呈现自己是‘谁’,就必须在人们之中与他人一起行动,即成为行动者”[32]。阿伦特所主张的积极生活或许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排除事或物的功利性目的“善政”和良知生活形式。这种主张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拷问是:“在结束生活之必需的阶段后,劳动将自身独立化和绝对化为目标本身”[33]是否合适?特别是当下数字时代,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在很多场合实现了对人类劳动替代的情况下,休闲至关重要。然而,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却在延长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对人的精神控制,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的占有与剥削。因此,数字社交平台把休闲变成一种展示活动,旅游打卡、美食分享都成了“积极生活”的写照。然而隐藏于这种“积极生活”的数字展示背后的可能也是一个过劳者和倦怠者,休闲是为下一步的出发服务,为再一次的加班提供润滑剂。这一问题的关键不是不要休闲,也不是不要展示,而是说要走出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构造的所谓“积极生活”幻象,以身体现实为根基、遵从劳动的本质规律性和美好生活的实际去工作、去生活,以沉思性的积极生活态度“反凝视”数字化的“凝视”。我们应对数字资本和技术平台构造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谨慎态度,通过反省自身和领悟美好生活真谛的前提,策划劳动活动与工作,而不能陷入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在世存在的无限操劳与操心状态,从而失去了某种可能的“诗意地栖居”的美好生活。
(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和劳动观,构建劳动美与生活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创造新世界、新生活的解放哲学,这一创造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自身,创造的方式是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劳动和实践,创造的结果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这样一来,无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还是人类社会解放,都与劳动和生活的美好目标紧密关联。“马克思哲学的生活立场体现在生活的主体性立场、批判性立场、历史性立场、实践性立场和创造性立场上。”[34]主体性立场表明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是美好生活的主体;批评性立场是对什么是真正美好生活的建构,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生活排除在外;历史性立场表明现实生活及其所依靠的历史实践的价值,实践性立场肯定了劳动实践创造美好生活的意蕴和价值;创造性立场表明美好生活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想象出来的观念。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蓝图构建劳动的实践场域,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采取劳动实践的方式,基于对美好生活的掌控化解倦怠社会的焦虑、内卷,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与劳动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倦怠社会的劳动美是否受到挑战,根源在于我们持有何种生活世界观和劳动观,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8]147。生活观影响劳动观,生活方式影响劳动方式,生命的方式由生活的活动和劳动的活动共同构筑。在日益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社会的劳动场域之中,在日益丰富化,甚至有些过度物质化的商品世界面前,在一个数字化表达和展示主导生活观念建构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挖掘马克思将人的劳动作为“生命活动”的定义价值,对劳动观、生活观、生命美学观进行重新审视,从而拯救日益倦怠的个体之精神政治学。巴迪欧曾对年轻人谈论何为真正生活时说,你们生活在一个危机的时代,这个危机不是缺乏自由的危机而是自由过度的危机,“这是一种消极的、消费主义的自由,它注定要在各种商品、各种时尚、各种意见之间不断变换。它没有为真正生活设定一个新的方向。……因为社会激进用虚假的竞争生活和物质性的胜利来反抗青年的自由,确定究竟什么才是创造性的和积极的自由,或许是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任务”[35]。虚假的竞争生活和短暂的物质性的胜利不能带来真正生活的答案,只会让人陷入加速倦怠和消费主义陷阱之中。
现在是我们真正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和劳动观、构建劳动美和生活美的时候了,只要我们对虚假自由说不,对物质性、商品化的物化积极生活保持必要距离,对何为真正生活保持本真性认识和切身性感受,对倦怠社会中的自身价值有清醒的了解,那么,应对倦怠社会劳动美困境的精神政治学,就藏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也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