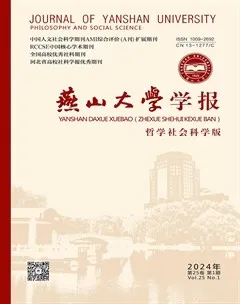良知的“自我审判”
——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2024-05-10王占彬
王占彬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良知见在”一词最初由王阳明提出,王龙溪也有阐发,其常常与“良知现成”相联系。郑泽绵认为将“良知见在”解释为“良知尚存”,蕴含一种盈科后进的动势。[1]但这还不能揭示良知在生活中的显在性。吴震认为“良知见在”和“良知现成”表述的内涵基本一致,都强调同一种良知观念。[2]71但两者意义其实是有区别的,“现成”有“现在完成”之义,“见在”有“当下自在”之义。彭国翔认为,“良知见在”指良知在本体层面上的先天完满性,“良知现成”指良知在经验层面的完成与完满状态。[3]然而,在王心斋那里,“良知见在”既指良知圆满具足又指良知在现实经验意识之中,但并不是说现实就是良知的完全展开。王心斋虽未提出“良知见在”一词,但其良知思想无不体现“见在”之义。比起“良知现成”,“良知见在”更能体现王心斋“日用即道”的思想,而较少引发争议。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王心斋的良知思想,探讨“良知见在”是否意味着“良知现成”,是否意味着不需要致良知。需要注意的是,王心斋也主张“良知致”,此“致”与“致良知”的“致”意义不同,前者为“发用”,后者为“扩充”。本文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良知致”是否意味着无须“致良知”?
一、致良知之善端:“良知见在”中的工夫论
关于“良知见在”,王阳明曾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4]21这是将“良知见在”作为存养心性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致良知以达到良知全体见在的目的。阳明又说:“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4]84“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4]96良知所见在的“几”即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苗头,致良知就是“知几”,将良知的苗头扩充到底。“见在”即“现在”,“良知见在”要求致良知必然显现于当下,而不在过去、将来。在工夫论层面,良知所呈现的不是良知的全体,而是良知的苗头,德性的善端,致良知是为了将良知全部开显。
如果“良知见在”意味着无须致良知的工夫,那现实中的私欲又如何处理?王心斋当然不会对私欲的问题视而不见,如他在《乐学歌》中说:“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5]63此“良知自觉”是“良知见在”的体现,良知能主动觉知到私欲的萌发,通过扩充善端来消除私欲。“良知见在”是否容纳致良知的关键在于,在“良知见在”的框架之下,私欲是否会产生?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日用酬酢是良知的发用,但心对各种事物不能必然做到恰如其分的处理,这就可能产生私欲,所以人要发挥主体性来彰显本有的德性。善端的扩充需要道德伦理规范,此规范是由包括圣人在内的百姓在生活中积累、提炼而成,良知时时处处见在于社会生活中。
良知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发用流行,此即“良知致”,故人可以随时随地致知。如王心斋说:“随大随小随我学,随时随处随人师。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罗天地真良知。”[5]54良知包罗万物并在万物之中,良知是一,一即一切,“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之外知。”[5]57“良知见在”不等于“良知现实”,过分的私欲是现实存在的,但它肯定不是良知的表现,私欲是良知被遮蔽的缘故,但不是良知本身的不足,善端的扩充就在于揭蔽。“良知见在”在经验层面表现为善端的时时显露,故人要随时随地致良知,以将潜藏的良知实现出来。读书、作文、学文学武、事亲事君都是依此良知而进行。由于良知是见在善端而非见在全体,故致良知就是要扩充此善端到最大化,扩充的动力又来源于自己的良知,故致良知即是人的“自致”,也就是“良知致”。
良知是本心,即道德主体,“本”就代表道德性,“心”就代表主体性。无本之心是可能陷入私欲的人心,无心之本是只存有不活动的状态,两者不是心学的主张。良知在日用中流行为见闻之知,人虽有主体性、主动性,但一旦不能顺应道德性,滞于见闻之知,使良知被遮蔽,就会产生私欲。比如,心是良知,心在眼睛所发用的视觉功能是良知的发用,因为眼睛时时刻刻在看即是良知时时刻刻在发用,良知能让眼睛看到“好色”,这可以说是一种善的功能,但心执着于“好色”就产生私欲。心之所以会执着是因为没有发挥自身的德性,陷入了“自欺”。扩充善端就在于使良知中的主体性与道德性相统一,以将善端扩充到极致。“良知见在”是先验层面的完全见在,是经验层面的端倪显现。良知本体不脱离经验但不完全就是经验,良知见在于经验表现为善端,善端不等于善的完全实现,故需要致良知。因此,“良知见在”是致良知的基础和起点,致良知是“良知见在”的落实和贯彻。如果将“良知见在”当作良知全体的见在,致良知工夫在此意义下就没有必要了,这显然不是心学的本义,但确实也会导致后世阳明学对“良知见在”的曲解,走向对道德规范的忽略。吴震说:“良知是一种先天存在,同时又是一种现实存在,这是一个良知本体论的问题。”[2]74因此,就本体角度讲,良知全体不脱离现实生活;就工夫角度讲,要使良知全体显现于现实,还须致良知。
二、良知即生活:“良知见在”之根据
王心斋说:“百姓日用即道。”[5]90“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5]62“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分定故也。”[5]62致良知就要回归人伦日用,回归生生之实理,否则就把良知看作悬空的佛性,修养就成了玩弄光景。“日用即道”的“即”有着“相即不离”之义,道不离日用,是日用的根源。穿衣吃饭、行住坐卧等日常行为都体现着良知,过分私欲不属于正常生活,致良知就是为了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即良知所流行的人伦日用。“良知见在”是说良知的体用相即,全体大用。良知时时处处见在,可以说是无方、无体。“良知见在”是强调良知寓于知觉,知觉不离良知,在这种情况下,知觉成为良知的知觉,良知成为知觉的良知。良知见在于见闻之知时会遇到私欲的遮蔽,私欲的产生源于主体没有将良知的道德性发挥出来,但被私欲遮蔽的良知依然在那里,不是说私欲所在的地方,良知就消失了。良知无处不在,凡是见闻存在的地方就是良知存在的地方。致良知就表现为扩充物来顺应的善端,消灭滞于外物的无知,以重现本有的良知。因为良知时时刻刻发用为见闻,故说“良知见在”;当良知流行于经验层面时,主体因为没有充分发挥善性而产生遮蔽良知的私欲,故需要致良知。私欲不是产生于外物,而是产生于己心,如阳明说:“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4]32非礼而视听言动就产生恶,此恶是由心之不正而起,所以要克服私欲就在于扩推内心的道德良知。
良知是不加思虑的先天存在,是内在的完满,人不必依托外物,只需明此简易的良知之学,就能自改、自化、自得其乐。良知的见在即是自我的见在,致良知就是找回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就在当下的现实中,故人只需在日常生活中顺应本性而行。王心斋说:“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可须臾离也。率此良知,乐与人同,便是充拓得开。”[5]49王心斋之“日用即道”继承了《中庸》中“道不可离”的思想,良知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离开生活的道不是真正的道,此即“良知见在”。人同此本心,心同此天理,故既可以致自我之良知,又可以致每个人的良知。良知表现为道德意识,每时每地都见在于意识。“良知见在”强调了良知的先天性和显在性,“指明人在本质上与圣人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本体论命题”[2]75。“良知见在”与孟子说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相一致,这既是说良知先天圆满具足,也可以说良知所外发的尧舜精神呈现于生活经验之中,但当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就等于圣人,“只是就本质上立论、本体上立言的一种立场预设”[2]75。现实的常人状态不能等于理想的圣人状态,现实社会的道德实践是通向圣人之境的必备条件。“良知见在”是强调拔本塞源的简易修养方式,但在现实发展中可能走向以自我为中心,将非礼行为当作良知,忽视礼义而走向狂禅,导致巨大的道德危机,这也是后世所批判的原因。但这种弊病并不是“良知见在”本身的弊病,其本义是没有问题的。“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落实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的所有行为当作良知。
王心斋强调了良知的具足性、自在性、显在性,良知当下即在,故后天行为就只是遵从良知,顺应本性。因为吾性自足,故不需要抛弃自家本来具有的“宝藏”而追求其他外在之物。良知见在说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周易》的“何思何虑”思想,将本心作为“同归”“一致”,“良知见在”在心学那里成为“不思不虑”的本体论依据。良知是活动着的存有,无时无刻不流行,致良知就是让良知流行顺畅,无私欲之阻碍。这可以让人们树立人人皆可成圣的信心,认识到良知即是吾心,良知即在生活,人只要在生活中做好当下事务,顺应天然之性,不必反复考虑、求索,满街的普通人就能成为圣人。故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是为了突出人伦日用实践的重要性,将重点放在了工夫论层面。“良知见在”具体而言是良知见在于人伦日用,突出了天理良知的平民化、大众化、日常化。王心斋以日用为良知见在的场所,突出民间化的百姓日用之学,“这几乎构成了心斋思想的一个标志性特点”[2]78。见闻之知构成日常生活,人伦日用体现天道,百姓顺其自然地去生活就是圣人行为的表现,如吴震所说:“良知与见闻,主要不是良知与知识的关系,而成了良知与生活的关系。而按照阳明的良知观念,良知不仅是亘古亘今的抽象存在,更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当下存在。”[2]81在王心斋那里,致良知之善端需要广泛学习圣贤经典、前言往行,明了经验性活动背后所体现的良知天理,“充其是非之心,则知不可胜用,而达诸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矣”[5]63。
三、万物一体之仁:“良知见在”之表现
“良知见在”是说良知见在于日常礼义,人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遵循礼义,此生活是礼义化、人文化的生活,即“仁”的生活。良知即是万物一体之仁,如王心斋说:“推本良知、躬行实践、明格物知本之要,充万物一体之仁。”[5]79人在发挥与生俱来的主体性时,若不合乎礼义就会受到私欲的束缚,私欲的生活不是“仁”的生活。私欲的遮蔽使人本身的良知不能开显,这就需要圣人良知的规范和约束,这种他律的方法本质上是自律,因为圣人之心与吾心并无不同,圣人的良知即是我的良知。良知不是抽象而超验的纯粹理念,而是在经验世界的具体存在之中,即先在于万物又遍在于万物。良知是道德之心,是主体的道德法则,不仅见在于人伦社会,也见在于自然世界。但吴震认为,如果良知见在于自然万物,就把主体之心作为宇宙存在本身,“其流之弊则有可能混淆主客、颠倒理欲、取消差等,带来诸多理论上的混乱,甚至陷入主观的‘独断主义’。”[6]但其实,因为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自然万物在人的道德之心的审视下,都被赋予了道德的价值和意义,万物皆统一于仁体。良知即仁之心,也是生生之理,万物的本质是生理,也是仁之体,在这种意义上,天地万物都成为良知本心的外发表现,万物的良知其实是我的良知,此即“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故致良知就是一种直觉、反观、内省的修养方式,而不是主体对外物的客观考察,对万物的把握即是一种自我把握。
“良知见在”有着双重含义:一是良知是先天的圆满,自然的具足;二是良知就在当下的现实中。王心斋之“满街都是圣人”的说法是将天理生活化、日常化,满街的百姓都各司其职,遵循正常生活的轨迹,即是遵循天理的表现。不是说满街都是现实的圣人,而是说满街遵循日常生活规律的人都是圣人,违背生活规律的就不是圣人,或者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圣人,良知见在于满街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良知见在”可以说是“良知即见在”,凡是良知都是见在的,但不能说凡是见在的都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致见在的事物,即现实的生活。“良知见在”要求致良知要顺应自然,不夹杂人为的安排和思虑,但这里的自然不是道家的自然,而是经过道德预设的“仁化”的自然。《中庸》中说:“率性之谓道。”天道就是率性而行,即顺应此天然的道德之心而行。
在心学中,“良知见在”显然不能说良知是完全既定的现实,因为还有致良知的工夫,它是特指良知是先天本来固有同时又是不断活动、发用于日用之中。良知在流行的过程中,一旦落实为见闻之知,就有可能受到私欲的遮蔽。因为人只能在经验范围内认识事物,故主体的致良知只能在形下层面进行,其表现为精研圣人经典,践行礼义,广泛学习前言往行等道德实践。显然,人人不能都是现成的圣人,当下所有经验也不能都是良知本体的直接呈现,否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就没有了意义,故只有合乎天理的经验才是良知的完全呈现。“良知见在”并不是说经验即良知,而是说良知不脱离经验,经验要合乎良知的要求。平民百姓在日用中做当下应该做的事即是圣人,这是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层层工夫统合为致良知的简易工夫,并不是取消了修养工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本”在心学那里就是“以致良知为本”,因为良知见在,人人都有仁心,人人都可以在身边的日常中去发挥良知,并不是非要做到“平天下”才成为圣人,良知是每个人的“天下”,致吾心之良知就是平自我之天下,以达万物一体之仁。一切的修养目标都在自己的心内,治理吾心以归返仁心,是一切的根本。
四、“自我审判”:“良知见在”与“致良知”之关系
王心斋说:“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真体不须防检。”[5]38人只要在根本上保持庄敬之心,持养良知天理,就不需要有意的防范、检查,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圆满自在、从心所欲。王心斋的“良知致”即是“良知见在”之义,它不意味着良知不需要“致”的工夫就可以自然呈现,而是说不需要形式上有意的防范,重在直指本心,就像治理污染的河流,要直接切断污染源,净化源头,而非只是“治标不治本”地净化支流。要真正在内心体认天理,确保毫无私意,视听言动就自然合礼。王心斋说:“予谓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此处亦好商量,不得放过。夫良知固无不知,然亦有蔽处。”[5]62这里的“良知有蔽处”应该指良知有被遮蔽的可能,故不必改成“人心有蔽处”[2]85。良知自身圆满,不会在被遮蔽时有所损失,“所谓明尽,只是认得良知,的确无遮蔽处耳”[5]156。体认吾心良知,就能彻底扫清私欲的遮蔽。甚至可以说,不需要“致良知”,因为良知始终虚灵不昧,不需要再被“致”,如王心斋说:“谓致知则可,谓致良知则不可。良知无时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无时而昏,不必加明也。”[5]146不过,良知是圣人之心,成圣还要个学的过程,学的目的即是安住此心。良知是自能辨别是非的真实无妄之心,但能辨别是非不等于成圣,还需要致良知之道,即“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多识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5]73,故王心斋也肯定格物、读书的重要性,“良知致”不代表人无须致知。
良知的道德性落实为现实中的仁义礼智等德目,良知的主体性落实为视听言动等实践活动。“良知见在”是说良知时时流行为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这需要道德性和主体性的共同作用,但若只发挥主体性而不发挥道德性,就可能产生恶,遮蔽良知,所以致良知就是要让主体性完全遵守道德性的要求,自觉与道德性合为一体。从工夫论层面讲,善端的扩充需要身体力行甚至百死千难的修养过程,故不能把当下的经验知觉完全等同于良知。成圣显然不是依靠空幻的参悟,而是切实的修行。如果把“良知见在”完全放在工夫论层面讲就失之偏颇,本体论中的“良知见在”不能否定工夫论中的致良知。良知圆满自足,不需要借助任何外物来完善自身,而经验之知有着不完善的可能性,但完善的本体依然寓于其中。既然良知是完善的,那为什么会造成不完善?因为良知的完善是本体论上的完善,工夫论上的致良知是为了复归本体上的至善,故一切工夫都是为了回到良知的大本大源,格致工夫只是手段。良知见在于经验,是良知自身圆满的必然呈现,就像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太一”自身圆满而流溢成万物,是万物的源头。良知感应外物而形成见闻,良知所在的主体执着于见闻就产生私欲,每时每地有见闻,故每时每地有良知。见闻之知虽然源自良知,但不等于良知。戒慎恐惧的格致工夫都是“良知见在”的表现,如王心斋说:“终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5]45致良知是良知完满具足而不断发用流行的表现。良知完满,见在于事事物物,包括致良知这件事,如果没有致良知,良知的见在就是不完满的。故致良知是良知见在的题中应有之义。
良知是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外在的礼仪规范也要经过良知的审视。道德行为的产生关键不在于言语、文字、礼仪,而在于此惟精惟一的道心,客观性的依据在内而不在外。良知具有判断能力,在一念发动时就能判定是非善恶而产生善端,“予谓良知者,真实无妄之谓也,自能辨是与非”[5]73。良知存在于道德意识,人心的发动即是道心的发动,一念的发动即是良知的发动,意识的发动与良知的发动同时发生。但吴震质疑说:
如果说人心良知是人心一念的审判官,那么岂不等于说人心之中存在着两种分裂的人格,就好像存在着一个罪犯、一个法官。法官固然是罪犯的审判者,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官审判罪犯的场所——法庭却是同一个心!更为荒谬的是,还必须是由同一个心来审判自己。用台湾学者王汎森的说法,此即“‘心’同时作为一个被控诉者和控诉者,殆如狂人自医其狂”。[2]83
其实,良知原本就是审判善恶的“法官”,其流行为见闻时,主体有可能陷入执着而使本体被私欲遮蔽,这就有了“罪犯”。“法官”是兼具道德性和主体性的良知、道心,“罪犯”是无道德性的滞留于见闻之知的人心,“法官”审判“罪犯”即是以道心审判人心,以良知主宰见闻,但人心的本来面目即是道心,见闻是良知的流行发用,故这种“审判”其实是人之心的“自我审判”。良知和意识不是两个分裂的人格,而是一个人格的体和用。“良知见在”也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体用一原之道,如王心斋说:“一者,良知之本也,简易之道也;贯者,良知之用也,体用一原也。”良知因其主体性而有人心,因其道德性和主体性的双重含义而有道心,人心因为在道德性上的不确定性,即“惟危”,需要道心的“审判”。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但这不是“狂人自医其狂”,而是“医能自医”,是良知在流行发用中的自我审判、自我省察、自我治愈。
五、结语
综上所述,“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活动性、活泼性,如王心斋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5]11这种“鸢飞鱼跃”的状态如同周公具备圣王之德,行动不会着意,合乎自然天则,不加人力安排。“良知见在”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本然呈现,表现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本来状态。良知是人之初的本来状态,其见在于见闻,但不滞留于见闻,一旦滞留就被私欲遮蔽,故致良知就是要摆脱当下的私欲以复其初。良知是天然自有之理,其所见在的状态是实实在在的,如王心斋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5]43圣人化育万物的根本原理就在于良知的见在性,良知能随时随地自然发用,无须人为安排其发用。圣人充分彰显了良知本体,完全合乎良知流行的变化规律。因为万物皆备于我,故化育自我即是化育万物。因此,“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双重意义:先在性与显在性。良知在本体论层面是先在的,与生俱来;在工夫论层面所显在的是善端,故须致良知。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显在于人伦和自然。心既是审判者又是被审判者,良知在体用一原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良知致”与“致良知”融合为“良知致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纠正“良知现成”在心学后期造成的流弊,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发展现代阳明后学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