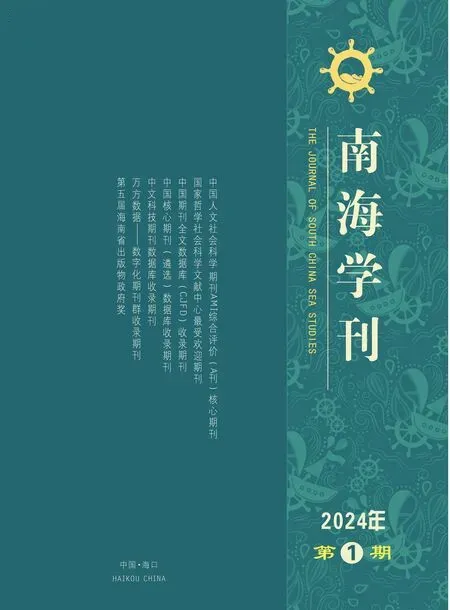丘濬“审几微”的哲学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2024-05-09李英华
李英华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菴,时人尊称他为琼台先生,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市)人。景泰五年(1454年)中进士。历任翰林编修、侍讲、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等职。弘治四年(1491年),加太子太保。不久,又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弘治八年(1495年),卒于任上。赠太傅,谥文庄。传世著作主要有《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重编琼台会稿》等。
丘濬是明代理学名臣,崇敬朱熹品格,宗奉朱子学术。他的《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就是从不同角度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大学衍义补》,从字面上看,这是对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补充,但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巨著,可称之为“治国理政百科全书”[1]。所以,丘濬是朱熹理学发展到明代时期的集大成者,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丘濬为何提出“审几微”?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理论原因。丘濬认为,真德秀《大学衍义》关于“诚意正心”的阐释不够精当,于是根据朱熹所谓“审其几”的命题,特意在《大学衍义补》中增补“审几微”一节。其二,实践原因。丘濬认为,如果不能及早发觉并处置事物刚发生时的不良倾向,待事物发展壮大再来设法应对就无济于事了,于是提出“审几微”,旨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丘濬解释了“审几微”的基本内涵,并从谨理欲、察事几、防奸萌、炳治乱等四个方面加以详细地阐释。而在《世史正纲》书中,则提供了关于“审几微”的大量的实践案例,涉及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这些实践案例大多是作为反面教材,对后世不无警示意义。
一、谨理欲:一念初萌之始,知其善恶之几
何谓“几”?丘濬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2]16这句话是从《周易》中引述的。丘濬接着解释说:
《大易》“几者,动之微”。一言乃万世训“几”字之始。盖事理之在人心有动有静,静则未形也,动则已形也。几则是动而未形,在乎有无之间,最微细而难见,故曰“动之微”,虽动而未离于静,微而未至于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吉凶先见之兆,先儒所谓万事根源、日用第一亲切工夫者此也。[2]16
所谓“动而未形”与“未离于静”,这是描述“几”介于有无、动静之间,故细微而难见。特别地,丘濬还指出,“几”是人心“理欲初分之处”,这是从理欲之辨角度剖析“几”的性质,表现为“吉凶先见之兆”。人心若符合天理,即为“吉兆”;反之,违背天理、放纵人欲,则为“凶兆”。因此,丘濬强调“谨理欲”,即谨慎省察内心的初始念头,善于辨析天理和人欲。
所谓“几”,有什么特征?丘濬说:
隐微,是人之所不睹不闻而我所独睹独闻之处也。……己所独睹独闻者岂非其几乎?几已动矣而人犹未之知,人虽未知而我已知之,则固已甚见而甚显矣,此正善恶之几也。[2]15
由此可知,一个人内心的理欲之“几”具有如下三点特征:第一,隐微;第二,人未知而我已知之;第三,它是事物的萌芽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丘濬同时使用“隐”与“显”两字来形容“几”。这表明“隐”与“显”具有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的。这涉及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即绝对与相对。但丘濬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
丘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内心产生某种念头,那么就意味着善恶、诚伪开始萌芽,他说:
是乃人心念虑初萌动之端,善恶、诚伪所由分之始,甚细微而幽隐也。学者必审察于斯,以实为善而去恶。譬如人之行路,于其分歧之处举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则,差毫厘而缪千里矣。[2]14
萌芽状态的念头尽管细微而幽隐,但必须高度重视,详加审察,明辨诚伪,存善去恶。如若不然,任其滋长,最终就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这就蕴含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也即反映了辩证法的质量互变的规律。正是基于量变的积累可能导致质变的思想认识,丘濬强调审察几微,防微杜渐,存善去恶,他说:
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惧乎其所初闻,方其欲动不动之间、已萌始萌之际,审而别之,去其恶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间、念虑之际,绝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则道不须臾离于我矣。[2]15
这里所谓的“人欲”,不是泛指一切人欲,而是特指不良欲望。丘濬之所以强调理欲之辨,旨在存天理而去人欲,亦即使人心符合天道。
丘濬不仅从理论上阐析“审几微”的理欲之辨,而且从工夫论角度阐明“审几微”的实践意义,他说:
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恶之几。知其为善也,善者吉之兆,断乎可为则为之必果;知其为恶也,恶者凶之兆,断乎不可为则去之不疑。则其所存、所行皆善而无恶,而推之天下国家,成事务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2]16
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果善欤,则推而大之;果恶欤,则遏而绝之。则善端于是而扩充,恶念于是乎消殄,逸欲无自而生,祸乱无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修、国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2]23
这两段话表明,若能切实践行“审几微”,从念头萌芽之际即断然存善去恶,并且持之以恒,使自己心性所存、身体所行,皆为善而无恶,那么就可以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境界。从理学角度分析,这两段话强调知行合一,即知之必行之;从辩证法角度看,这两段话蕴含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原因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不过,应该指出,这两段话所反映的丘濬的思维逻辑似乎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国家治理效果如何,并不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心性修养,而是涉及诸多方面的综合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丘濬认为:
世之人主,每于深宫之中有所施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胜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闻,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讽谏,申之以切戒,禁之以严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盖实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鹤鸣而声自闻也。[2]27
在丘濬看来,君主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未尝不知违背天理,但由于未能克制私欲,从而昧着良知放纵自己。为了掩人耳目,又严禁他人彰其丑行。但这种做法是徒劳的,结果是欲盖弥彰。在《世史正纲》中,丘濬对那些“背天理而纵人欲”的皇帝作了严厉批判。例如,对于秦始皇妄求“不死之药”,丘濬批判说:
天下岂有不死之人哉!岂有不死之药哉!始皇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寿耳,于是信方士之言,谓人有不死者;人之所以不死者,得不死之药而食之也;于是谴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访神仙,觅不死药。呜呼!天地间岂有此理哉![3]2531
再如,对于汉武帝妄图“长生不死”,丘濬批判指出:
为父母者,为之择配,使必相当焉,非偏爱之私,乃当然之理也。顾以一己之私,欲求长生之故,捐所爱,以予妖妄之人,乡里自好者有所不忍也,而堂堂天子乃忍为之哉!武帝为此,非独不君,且不父也。书之于册,遗笑千古。[3]2595
如果说秦始皇妄求“不死之药”与汉武帝妄图“长生不死”,其非理性与虚妄性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对于那些看似比较细微的失误,丘濬又持怎样的看法呢?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唐肃宗自立于灵武,改元至德,遥尊唐玄宗为上皇天帝。丘濬指出,唐肃宗太急于继承皇位了。如果他能够稍微等待一下,即待同年八月唐玄宗主动传位给他,然后即位,那么一切都将名正言顺。而唐肃宗之所以急不可耐,这是因为:“烛理不明,欲速而见小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呜呼!天理、人欲之间,几不容发,可不畏哉!”[3]2938—2939
需要注意的是,丘濬不仅严厉抨击帝王的“背天理而纵人欲”,而且对于士大夫的趋炎附势、丧失人格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东汉延熹二年(159)八月,梁冀伏诛,并夷三族。此外,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以阿附罪,免为庶人。对此,丘濬评论说:
士大夫平日所学何事?一旦乃甘心为权奸之腹心羽翼,所得几何?而遽遗恶于千万载,是皆起于患失之心,而图一时之幸;抑不思世无不死之人,恶无不败之理,吾何庸取一时之快,而为终身之玷,贻后世之讥哉![3]2695
进而又指出:
胡广辈在当时视李固、杜乔固若得志,然自后人观之,真不啻金玉之于粪壤也。呜呼!后之人附权奸以苟富贵者,尚鉴之哉![3]2695
丘濬希望后世士人能够以此为戒,在厉害关头千万不要“取一时之快,而为终身之玷”,而要保持良知理性,坚守独立人格。
二、察事几:审其几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务
所谓“事几”,即事物的初始萌芽。丘濬说:
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是之谓几。非但祸乱有其几也,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2]23
可见,所谓“察事几”之“几”与前文所谓“谨理欲”之“几”,二者有相同之处,即细微而难见;其区别在于,前者是指身外的客观存在,后者则是心中的主观意念。丘濬认为,从“事几”可以预见该事物发展的必然态势。这种判断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免过于简单。因为,有些事物在其萌芽与成长阶段,就有可能过早地夭折,也有可能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或影响,从而改变了最初的发展态势。
丘濬指出,“事几”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性,他说“盖事几之在天下无处无之”[2]19,又讲“天下之事,莫不有几”[2]21。“事几”的存在虽然具有普遍性,但要想及早发现并把握“事几”,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丘濬说:
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见。事已至而理之显然者,亦易见。惟事之方萌而动之微处,此最难见。噫,此知几者,所以惟神明不测者能之也欤![2]20
正因如此,丘濬特别强调要有先见之明,要做到“豫察”和“豫审”,他说:
几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方是之时,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朕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审其几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范之意;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2]24
在事物萌芽的初始阶段,如能豫察其朕兆、豫审其几微,就可以防微杜渐、不留后患。但在丘濬看来,“后世人主不知戒敕天命,故虽事几暴著,犹不知省,及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几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诚万世人君敕天命、保至治之枢要也。惟明主留意”[2]25。且不说昏君,就算是中主(即一般君主),往往也是欠缺先见之明,缺乏忧患意识,所以常常待到事态激变才慌忙被迫应对,但为时已晚,无可奈何了。所以,丘濬强调“几”之一字,就是“至治之枢要”。
那么,作为国家君主,应该如何做到“察事几”?丘濬指出:
谨微之道,在于能思。是以欲兴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于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于心,反复绎,至再至三,虑其有意外之变,恐其有必至之忧,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尽善,如何而处之则可以无弊,如何而处之则可以善后而久远,皆于念虑初萌之先,事几未著之始,思之必极其熟、处之必极其审,然后行之。[2]2605
丘濬强调,当君主欲兴一念、欲作一事之际,就必须谨慎思考、反复思虑,必至虑之极熟、处之极审,尽善无弊,然后行之。丘濬又说:
天下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可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为也;可为而不可言,则非可为者矣。人君于此,凡其一念之兴,几微方动,则必反思于心曰:吾之为此事,可以对人言否乎?可以与人言则为之,不可与人言则不为,则所为者无非可言之事。若然,则吾所为者,惟恐人传播之不远矣,尚何事于箝人口而罪人之议己也哉![2]27
前一段话,丘濬提出“思”之一字,强调君主于内心“精思熟虑”;后一段话,丘濬提出“反思”二字,强调君主所为必须“可与人言”——其实质意义就是,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亦即君主所作所为,必须至公无私、光明正大,这样才能利国利民、长治久安。
然而,丘濬在《世史正纲》中所记载、所评析的大多是反面例子。例如,丘濬批判指出:
汉自武帝以后,虽设丞相,徒建空名而已。然在人君威权己出之时,犹之可也;一旦弥留之际,受遗诏,辅少主,一切委之武臣,而平日所谓丞相者,曾不与闻。自是以后,大司马、大将军,遂执国柄,世世不易,以至于潜移国祚,其祸兆于此欤![3]2606
丘濬认为,君主与宰相应如元首与股肱,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他们亲密无间,相互信赖,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但是,自汉武帝开始,帝王不再信任宰相,设法分割甚至架空宰相权力,从而出现“潜移国祚,祸兆于此”的征兆。再如,西汉建始四年(前29),罢中书宦官,置尚书员五人。丘濬批评指出:
王凤欲专内外之政,始罢中书谒者,夺其所掌尚书之事,而增置尚书员,始以士人为之。……夫中书枢机之任,罢宦者,而用士人掌之,使政出于一,而权归于上,是固朝廷美事。然外戚假此而合内外之权,以专国政,遂驯至于移国祚,其事虽若可喜,而实可伤也。[3]2629
在丘濬看来,王凤罢中书谒者,而用士人掌之,这本是好事,但由此又导致西汉后期外戚专权、国祚潜移的问题。又如,东汉延熹九年(166),宦官使人指控司隶校尉李膺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导致李膺下狱,其党二百余人被逮捕,并策免太尉陈蕃。丘濬明确指出,“后世朋党之名,始见于此”[3]2698,进而又批判说:
朋党之祸,始于言语之微,而驯致于祸害之大,不徒祸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广,一世之善类,于是乎殄瘁;国家之元气,于是乎消蚀;遂使后世权奸,欲尽除善类以倾人天下国家者,往往假此以为名,是其为祸非独在于一时,而且及于千万世矣![3]2699
东汉时期,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及太学生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宦官集团以“朋党之名”指控士大夫,开启了后世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以“朋党之名”嫁祸于人的历史序幕。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以宦官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丘濬指出:
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权,盖近而易以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坚冰,而轻变太宗之制,崇宠宦者,增多其员,自是以后,浸干国政,末流之祸,盖基于此。[3]2919—2920
丘濬认为,唐玄宗于先天二年任命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这就诱发了唐中后期宦官专权的历史流弊。
综上所述,丘濬有鉴于“察事几”的重要意义以及惨痛的历史教训,他强调说:“是以君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2]34值得指出的是,所谓“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出自《道德经》第63章。其实,在《道德经》中也蕴含“察事几”的哲理,所谓“以观其徼”与“祸福倚伏”即是如此。大概是因为囿于朱子理学立场,丘濬没有说明老子哲学也是“审几微”的重要思想渊源。
三、防奸萌:阴长而渐盛,制之当其微
所谓“防奸萌”,指预防小人狼狈为奸。丘濬指出:
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辩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2]31
又说:
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见其有害,然其质本阴柔,用之之久,驯致之祸有不能免者。
人君知其为小人也,则于初进之际,窥见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见亲用,则未萌之祸消矣。夫然,又安有权奸窃柄之祸,佞幸蛊心之害哉![2]31
所谓“质本阴柔”,这是对小人之本质的深刻揭露与批判。这就涉及辩证法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即现象与本质。小人的额头并没有刻上“小人”两字,其外在表现可谓变化多端,但无不反映其“阴柔”本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小人往往与君子相提并论,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他们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丘濬引述程颐的话说:
《姤》,阴始生而将长之卦。一阴生则长而渐盛,阴长则阳消,小人道长也,制之当于其微而未盛之时。君子、小人异道,小人虽微弱之时未尝无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则无能为矣。[2]32
正如自然界的阴长则阳消,在社会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丘濬举例说:
如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君臣契合,莫能间之。近幸帖息畏伏,诚若无能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继嗣重事,卒定于其手,而德裕逐矣。几微之间,所当深察。[2]32
正是基于对小人“阴柔”本质的深刻认识,丘濬告诫说:“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2]34丘濬认为,对付小人,必须深刻预见阴长而渐盛的态势,因此必须制之当其微。
在《世史正纲》中,丘濬揭露、批判了小人为奸、左右政局乃至篡夺政权的历史事件。西汉元始元年(1),王莽自为太傅,号安汉公。又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丘濬批判指出:“平帝之世,政出于王莽,奸伪之徒,假尊儒之名,以收誉望文奸谋,圣人在天之灵,其不之受也必矣。”[3]2641东汉延康元年(220)十月,曹丕逼帝禅位,遂篡立国,国号“魏”。丘濬指出,这是后世权奸逼君“篡国之始”,并批判说:
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遂,而天殛之。丕袭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遂,故假禅代之名,以文饰其恶。……己实夺之,而谓之禅,将谁欺乎?非独欺人,盖欺天也!自丕为此,举世之权奸,遂假此以为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夺其国家者,按迹于天下。丕之父子,非独汉世之罪人,乃千万世名教之罪人也。[3]2720
由此可见,对于王莽“假尊儒之名”以收誉望、曹丕逼帝禅位的“篡国之始”,丘濬非常痛恨,认为是“千万世名教之罪人”。
值得注意的是,丘濬认为,要想有效地、彻底地防止奸萌,君主必须首先做到正心诚意,不能让私欲邪念潜伏心中。他强调指出:“臣愚以为,吾心私欲窃伏之几,尤甚于小人帖息求逞之几,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也。”[2]33所谓“先有以防乎已,然后可以防乎人”,这反映了辩证法中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如果君子自身不能正心诚意,就不仅不能防范小人,反而可能招引小人,使得奸伪之徒聚拢在自己的周围。例如,《宋史》记载宋理宗崇尚理学,故其崩后得谥为“理”。但丘濬批评指出,宋理宗之崇尚理学,只是表面喜好理学,并非真正由衷认同理学。所以宋理宗喜好理学,就如叶公好龙一样。丘濬批判说:“夷考其所存所行,其与理合也盖无几,史亦言其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呜呼!虚之一言,其理宗膏肓之病欤!”[4]3222因为宋理宗心术不正,虚伪地推崇理学,所以,他所任用的也是一群“作伪趋时”之人,正所谓:
一时任用者,多作伪趋时之人,同声附和,稍有议及之者,则以陈贾、胡纮目之,是以人才大坏,高谈有余,实用不足,权奸用事,知其无能为引以为助,一时居高位据要地者,多愦愦不事事之徒。[4]3222
一群虚伪之徒聚拢在宋理宗身边,其消极影响播及天下,正如丘濬所抨击:
人知帝之所好尚在此,往往慕而效之,处学校者,借濂洛之书以为课业;应科目者,剽濂洛之言以为程文。及其仕宦所至,立书院、祠堂以为崇儒,表遗书、语录以为示教,遂至天下从风而靡。[4]3222
更糟糕的是,宋理宗的虚伪还导致另一种后果,即所谓:“凡勤政事者,即目为俗吏;固边圉者,即目为粗才;甚至读书作文者,亦目之以玩物丧志焉。”[4]3222因此,丘濬尖锐地指出“宋亡于理宗”,并且告诫说:“后世人主,其尚以诚实为务,毋徇虚名以嫁祸于斯文,而贻世道之忧!”[4]3223
值得指出的是,丘濬所谓“防奸萌”,不仅是对君主的谏言,而且也是对士大夫、对君子的忠告。丘濬指出:
天下之理二,善与恶、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其在人,则君子、小人所由分焉,一于善则心存乎公,行合乎义,而为君子;一于恶则心存乎私,行依乎利,而为小人。[4]3123
这种君子、小人的区分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程颐、苏轼、刘挚等各自结党,互相攻击。丘濬为此批评说:
今观元祐诸臣,皆一时所谓贤人君子者也,一旦伸于久屈之余,不幸而当群奸误国之后,正当相与同心协力以异正拒邪,犹恐不足以胜之,胡乃以私忿小怨,自分党与,互相攻击。如此果善乎恶乎?公乎私乎?义乎利乎?盖其心介乎善恶之际,而出入乎公私、义利之间,比而不周,不能公天下以为心也。[4]3123—3124
这说明君子与小人之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辩证转化的可能性。丘濬对元祐党争的批判可谓极为公允,也极其深刻,反映了一种辩证眼光。丘濬批判说:
元祐诸贤,疾恶太甚,往往逆料他人未然之恶,而极力诋毁之,非但攻小人也,见君子少有纤芥之失,即已遽然攻之,不少假借,形于章奏者,不分轻重浅深,一概目以奸邪。[4]3121-3122
元祐党派之间互相把对方视为“奸邪”,这表明元祐君子的内心“介乎善恶之际”,并且“出入乎公私、义利之间”。若把丘濬的意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元祐君子近乎沦为小人而不自觉。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丘濬指出:“元祐所以变为绍圣者,岂但小人之罪哉,一时所谓贤人君子者,亦未尝无罪也!”[4]3124“小人欲空人之国,则肆为朋党之说。君子指小人为党,小人亦指君子为党,甚至君子亦自指君子以为党,而小人亦然;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4]3132质言之,北宋的衰亡,不仅是小人误国造成的,而且也与元祐党争有极大关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丘濬能够破除世人对于宦官的偏见与成见,认为对宦官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
人之生也,皆具天地之理,故其性莫不皆好善而恶恶,秉彝好德之良心,不以彼此而殊也。当桓帝之时,宦者虽曰专权恣肆,其中岂无明理达义之人,知其党类之非者。[3]2702
又说:
彼宦侍亦人也,同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其形体虽有不全,其心性初无少欠,论人者乌可因其所处之地,而遂疑其所存之心哉![3]2706
他举例说,东汉宦官吕强无比清忠奉公,即便是士大夫,亦鲜其比。丘濬由此推论说:“窃意古今宦臣如强比者固亦不少,但作史者因其类而并恶之,或至见遗,亦未可知也!”[3]2706丘濬进而指出:“后世秉史笔者,其存至公之心,片善不遗,寸长必录,使世之善人君子不幸而处此,咸有向上之心,而无自绝之念。”[3]2706这段话既反映了史家的公心,又体现了儒家的仁心,丘濬把它们融为一体,至为可贵!
四、炳治乱:乱常生于治,危常起于安
丘濬对“审几微”的理论阐析,以“炳治乱”殿后,表明其根本目的在于治国理政、在于长治久安。何谓“治”?何谓“乱”?在丘濬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丘濬没有对此作出特别的界定。但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总会出现治乱循环的现象。他说:
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2]35
国家有治有乱,这可谓是一个基本常识。丘濬思想观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认为治乱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鸿沟,并且非常睿智地指出“乱常生于治之时”。这反映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
丘濬指出:“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2]37丘濬认为,治乱循环反映了“物极则反”的道理,所以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必然是通过各种偶然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君主所应当致力的,就是尽量防止和消除各种可能诱发动乱的偶然因素。丘濬还指出:
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远,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2]35
诚然,所谓“常治而不乱”只是相对而言,而不可能是永恒的、绝对的“常治”。丘濬认为,只要统治者内心能够常以安危为念,审其几先,谋虑周远,应对有术,就可以实现常治不乱。
丘濬还特别指出,统治者应该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即:
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2]35
这里所谓“思”,表明了丘濬高度重视民情和民心,反映了丘濬的儒家民本思想立场。
丘濬通览中国古史,试图从中探索治乱循环的规律。他说: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乱之极矣,天必厌之而生治,治之将生,必有驱除之人,以扫其祸乱之余烈,以迓夫反正之君,俾其开一代之治端,基数百年之全威。历考前代,莫不皆然。周之衰也,分而为春秋战国,终而收拾之以秦,于是乎汉兴焉。汉之衰也,分而为三国南北朝,终而收拾之以隋,于是乎唐兴焉。……宋衰而女真分裂,蒙古乘其后,以夷混华,坏乱已极矣,我朝拨而反之正。噫!自唐虞之后,帝王之兴代,必以三者,三才之道也。[3]2525
这段话通论中国从上古到明代的治乱更迭历史,大体呈现出一种“治—乱—治”的变化发展态势,丘濬称之为“三才之道”。这种概括并不是丘濬个人的首倡,而是古已有之。但是,以“天地人之异统”(或“忠质文之迭尚”)[3]2525来说明“治—乱—治”的循环往复,未免给人一种拘泥或牵强之感觉。其实,丘濬所总结的“治—乱—治”的循环往复,接近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所谓“治乱循环”,并不是完全回复到原初状态,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发展。
当然,治乱之间的循环往复并不是指由“治”一下子转到“乱”,而是存在一个由微而著、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丘濬说:
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弊之地。……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预先有以防之也。[2]38
例如,东汉永平九年(66),始置中官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丘濬评论说:
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永平中,始置员数,则前此虽有中常侍之名,未有员数也;有员数始于此,然其数止十四人而已。后世有职名者乃至数千焉,呜呼!国政欲不紊,民力欲无困,得乎?[3]2666
再如,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罢免张九龄,而以李林甫兼中书令。丘濬指出:“唐室治乱之几分于此。”并引用崔融对唐宪宗的话说:“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贤相张九龄,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3]2928又如,唐贞元三年(787)秋八月,唐德宗欲废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进谏说:“愿陛下还宫勿露此意,左右闻之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丘濬指出:
李泌谏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谓此意之露,即是几微初动之处也。……小人非惟听吾言之所发,有所观望而生谗谮;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夺而窃权柄。是以人君于凡施为举动,如命官、讨罪之类,皆当谨之于几微之先,不可轻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窥测之。苟或一露其几,则将有贪天功以为己私,假上权以张己威,树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2]33
由此可见,由“治”转“乱”的关键因素,就是帝王存有私心、用人不当,或政制不良、包庇小人,而小人则伺机夺权专政,从而败坏国政。
北宋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始亲政。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不报。杨畏上疏,请绍述神宗,被哲宗采纳,于是诏复章惇、吕惠卿官职。同年四月,改元绍圣元年。丘濬评论说:“宣仁后崩,帝始亲政。祖禹之疏不报,杨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乱兴亡之几,于此乎判。”[4]3126这个例子再次说明帝王用人不当,就是由“治”转“乱”的关键因素。北宋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示意道士说:“朕乃上帝元子,为太宵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可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4]3138丘濬对此给予严厉批判,他说:
考封册之制,惟天子得行之,道士何人,敢以此而加之君上!……堂堂万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册,不为儒教之主,而主异端之教;不为万乘之君,而为道士之君。本欲以自尊自大,而不知适以自卑自小也![4]3138—3139
最后,丘濬特别指出,唐玄宗、唐德宗、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著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2]38在丘濬看来,唐玄宗、唐德宗和宋徽宗都在盛年执政,皆有“过人之才”,并且其治国理政一度实现“既济”,只可惜由于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豫防”,而最终导致“困苦流离”。丘濬对其遭遇深表同情与惋惜,故以他们的惨痛教训结尾,希望后人引以为戒,可谓用心良苦。
五、丘濬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丘濬的“审几微”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内涵,既蕴含了理欲之辨、义利之辩、公私之辩、知行合一等理学命题的思想精华,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涉及辩证法的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等基本范畴。要言之,丘濬的“审几微”论不仅蕴含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精华,而且富含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审几微”论是丘濬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它贯穿或渗透于丘濬哲学思想的各个要点。例如,丘濬的民本论、人才观、法制观、天人合一论等,无不蕴含了“审几微”的思想精髓。着眼新时代,丘濬哲学思想对于建设海南自贸港具有重要意义。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各种机遇、挑战与风险并存,我们要像丘濬那样修炼“审几微”能力,培养辩证思维与先见之明,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第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理念,建设人民满意的海南自贸港。丘濬哲学思想提出“以民心为己心”[2]391,主张“为民造福也”[2]354,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因此,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过程中,要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满足人民心愿,要使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泽海南百姓。
建设海南自贸港,要处理好义利关系问题。所谓“义利关系”,包含道义原则与物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义”指道义原则,以及群体利益或整体的、长远的根本利益,即公利与长利;“利”指物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或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即私利和小利。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时,应当把握好丘濬所主张的义利统一、义以生利的原则,不能因为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而损害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种较为严重的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现象。有些人甚至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他们在短期内也许能够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好处,但从长远看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一切徒劳。因此,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过程中,应该注重和遵循“见利思义”和“义然后取”的基本原则,要坚守“为民造福”的宗旨理念,这样才能建设好人民满意的海南自贸港。
第二,重视“用人和立法”,努力打造清廉自贸港。丘濬认为:“盖为政在人,人必与法而兼用也。”[5]1594因此,丘濬指出:“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则用之。至于左右辅弼大臣,又必于贤才之中,择其人以用之,非其人则不可用也。”[2]108同时,丘濬又强调说,“立天下之法”必须做到“法律”与“礼义”相辅相成,“用是以酌生民之情”[5]1597。要言之,在丘濬看来,立法必须“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5]1602。也就是说,必须遵循自贸港建设的固有规律,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必须符合民心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6]。因此,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过程中,应当选拔和重用那些正直无私、勇于担当的人才。如果提拔、用错了一个人,这并不只是用错一个人的问题,它会发生连锁反应,结成一种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从而腐蚀官场风气,进而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要建设好海南自贸港,就应当借鉴和吸取丘濬的用人之道。同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各项立法,应该遵循“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的基本原则,并且在文字表述上做到明晰具体、通俗易懂,正如丘濬所谓“显明其义,使人易晓”[5]1595,避免大量使用偏僻、晦涩的名词术语。总之,建设海南自贸港,必须做到用人得当和立法健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海南自贸港建设成为一个风清气正、和谐繁荣的自由贸易港。
第三,贯彻“天人合一”精神理念,把海南自贸港建设成为生态美好的“四季花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使海南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6]。这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这也是丘濬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理念。丘濬认为“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2]245,所以人类必须“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2]245,反映出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即把天地看成是一个大生命体,人类是其中有机的但又是最灵秀的部分。人类应当自觉参与大自然的造化过程,使自然生态变得更加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也使人性本身不断得到修炼和升华。
对于海南而言,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她拥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因此,应该把“天人合一”理念作为海南文化的核心、底色与特色。所以,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和贯彻“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也就是必须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重中之重。从1999年海南提出建设生态省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尚有许多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拓展和深化人们对生态文明,尤其是“天人合一”的内涵与意义的理解。只有深刻领悟“天人合一”的内涵与意义,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植根于一种深层次的人性自觉和文化自觉,而不流于一种短暂的功利性的权宜之计。要言之,在建设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必须坚持和贯彻“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这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树立文化自信,打造南海明珠。丘濬被明代学者誉为“当代通儒”和“中兴贤辅”[7]51。谈迁《国榷》说“丘文庄之明体达用,酌古准今,裒然为一代文宗也”[7]235。丘濬为什么能够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源于丘濬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文化自信精神。这种精神在丘濬《南溟奇甸赋》中也有鲜明的反映。该赋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不仅深情地描述、赞美了海南的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而且展示出丘濬本人的一种深厚而豪迈的文化自信,所谓“有一奇士,全钟其气。北学于中国,颉颃乎天下之士”[8]。今天,我们建设海南自贸港,应当传承和树立这种文化自信精神,并以这种文化自信精神为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和大力传播丘濬文化,使它成为新时代海南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
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要满怀信心地把海南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自由贸易港,而且要有雄心壮志把海南建设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开放包容、人文荟萃的文明新高地。一方面,我们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去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向世界传播包括丘濬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过程中把海南建设成为一颗南海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