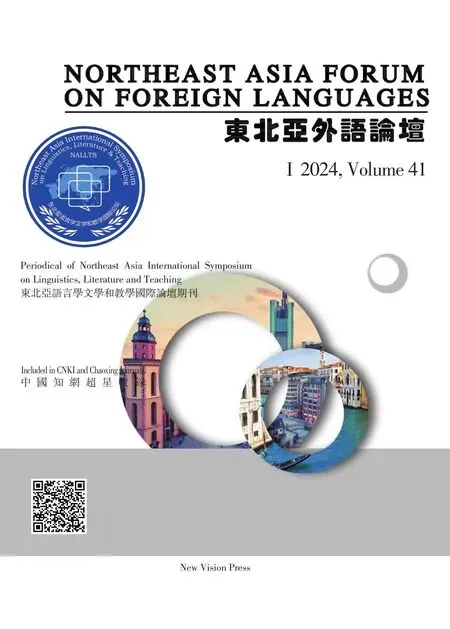孤独的人: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视域下《黑猫》中的异化研究
2024-05-09江心怡
江心怡 王 丹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引语
《黑猫》是19世纪美国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萧伯纳曾将爱伦·坡与马克·吐温相比肩。爱伦·坡在美国文坛的地位颇高,是美国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他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短篇小说领域的建树,享有“现代短篇小说之父”的盛誉。19世纪末,法国文坛先驱博德莱尔公开承认爱伦·坡对其创作的影响。在现代主义浪潮掀起时,爱伦·坡以不可遏之势成为现代主义各流派的鼻祖(朱振武,2008:21)。他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和影响力,目前学术界对其代表作《黑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恐怖效应、象征、死亡、哥特等主题上。然而笔者认为《黑猫》中主人公异化的特征十分突出。
“异化”的英文alienation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在神学中指的是“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郭海霞,2010:66)。在经济学中意为财产转归。政治上意为原始自由的消失,受异己力量支配。黑格尔首次在哲学范畴提出“异化”概念,马克思在提出劳动异化理论,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触及异化,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科技发展的消极影响叙述异化。马克思将异化理解为本属于人的物或活动,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获得独立性,并反过来制约人,统治人。弗洛姆在《孤独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中认为“异化”是现代人对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体验。伊恩·罗伯逊从社会学出发将“异化”理解为人在面对社会制度的压迫下所体验到的无力感、孤独与无意义感(赖干坚,1994:73)。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就是描述危机社会下异化的人(石昭贤,1981:4),现代文学中的异化包括人与社会、与自我、与物、与自然、与人关系的异化这五个方面(郭海霞,2010:66)。文本认为《黑猫》中主人公在与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以及与自身的关系这三方面发生了异化。
《黑猫》的主人公“我”因为遭受社会的嘲笑与虚情假意,从开始的善良变成残忍暴力的杀人变态,脱离社会群体后人物在孤立的生存困境下人格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人格的变化也随之导致人物与多方面关系发生异化。因此本文将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黑猫》。19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人格结构论。他认为完整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成分构成,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也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2018: 116)。本文旨在依托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理论分析《黑猫》主人公在与人、与物以及与自身的关系这三方面产生的异化,从而理解《黑猫》作者的写作意蕴。
一、“本我”的不满导致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异化
《黑猫》中,主人公由于社会群体造成的创伤与人的关系产生了异化,长期的孤独又使主人公与物的关系随之也发生了异化。
“本我”由本能、冲动及欲望构成,包含的许多部分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因此受到“自我”的压抑。“本我”是最难以被察觉的心理部分(弗洛伊德,2018:117)。主人公“本我”中爱的本能无法在社会群体中得到满足,导致与物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即“物质与精神的对立”(郭海霞,2010:70),也就是说人类本来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最后人类反倒被物质所掌控和主宰主宰,也就是物质制约了人。主人公“我”从小由于“心肠软”遭受旁人的嘲笑,因此逃避与人交往。长大后又领略了社会的虚情假意,于是便脱离社会集体,常年宅居在家不与人来往。然而独处导致极致的孤独,因此主人公将爱转移到宠物上,靠占有更多的宠物来获取快乐。“我”是黑猫的物质所有者,然而当“我”越是将快乐依托在宠物的亲昵上,就越意味着“我”对物质的依赖,假设当失去黑猫时,我也等于失去精神寄托。因此当发觉黑猫突然变得疏远自己时,“我”立马暴怒。从这个意义上,物质就主宰了“我”。“物质财富的拥有者沦为物质的奴隶”,坡告诫我们将快乐寄托在物质上是十分危险的,而通过占有物质获取满足感并不能消解孤独。
主人公逃避社会与人疏离,意味着“我”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疏远和分离,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残害(郭海霞,2010:67)。一方面主人公“我”常年蜗居在家,出入的固定场所“酒吧——家——回家的路”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走向,代表了他与社会集体之间疏远而孤立的状态。同时,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深入到了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之间,主人公和妻子丈夫同处一个屋檐,却对妻子拳打脚踢。夫妻关系之间,主人公对妻子具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妻子只是默默忍受毫无怨言,通篇缺少女性的声音,女性处在边缘位置,处在男性的控制之下。值得关注的是,我”是因“从小性情温顺”,以“富有爱心而闻名”而受人嘲笑。与人为善,遵从“至善原则”却并不能换来尊重和朋友的喜爱,只有对“我”软心肠的嘲笑以及薄情寡义,这也从侧面说明坡反映了整个社会下人与人之间同样处于冷漠无情的,相互对抗、竞争和疏远的异化状态。
《黑猫》中“我”没有姓名和任何身份信息,爱伦·坡企图以这种方式将其在读者心中放大为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当人们不再以“善良”为值得称赞的品质,嘲笑软心肠是性格怪癖时,这是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扭曲。作者爱伦·坡企图讽刺的是社会的冷漠与虚情假意以及对道德沦丧的批判。
事实上,主人公脱离社会群体的选择其实是对“本我”中爱的本能的坚守和对“恶”的抵制。“主人公”并没有因为遭受同伴嘲笑,就第一时间摒弃善良的品格,没有为了想融入集体而顺应形势变得与同伴一样冷漠和虚伪,逃避是主人公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困境的无奈以及对“本我”中善的维护,这一定程度上传达了的反异化思想。
综上所诉“本我”中渴望爱的部分使主人公脱离社会群体,将快乐依托于占有宠物,导致主人公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主人公与妻子,与社会集体的疏离反映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达爱伦·坡对社会道德价值观扭曲的批判,对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二、“超我”的削弱导致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
主人公“超我”削弱意味着主人公与自我的关系发生了异化。
“超我”遵循“至善原则”,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将社会道德与理想、价值观内化形成的部分。当“本我”违背“超我”时,通过良心惩罚使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产生罪恶感(弗洛伊德,2018:118)。
主人公的孤独使“超我”的作用被削弱,导致主人公与自我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主要指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人异化成非人,完全失去了自我而成为非我”(徐曙玉,2001:12)。“酒精”和“愤怒”激发了“本我”中恶的部分。弗洛伊德说过“人内心的潜伏着的无法察觉的思想、痛苦等感觉会在个体控制能力松懈的时候,比如醉酒或梦境,出现在意识层面让个体察觉”(弗洛伊德,2011:13)。主人公常年处于孤独封闭的状态,当“我”始终抗拒与人与集体接触,而无法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时,人与自我的关系在悄然异化。在爱伦·坡的《黑猫》中出现过对主人公这种异化的描述:
我的性情因过度饮酒变得极其恶劣,我一天比一天阴郁、暴躁,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对妻子我也开始口出恶言,最后甚至拳脚相向。我的宠物们自然也能感受到我性情的转变,我不仅忽略他们,还虐待他们。 (2018:301)
主人公“本我”中的邪恶的冲动借助酒精和愤怒得到了释放,当“我”残忍地剜去猫的眼后,我会感觉到朦胧的悔意。长期封闭的独处生活使“超我”道德规范的效力逐渐被削弱。虐待宠物,家暴妻子,无视别人的感情,这意味着“本我”中恶的部分在逐渐失控。主人公原本善良、性情温和。但由于“超我”的消弭,最终沦为一个暴力冷血又阴郁的“非人”。
主人公性格和道德的巨大颠覆意味着“我”与自我关系发生了异化。主人公“本我”中恶的欲望因为“超我”的消削弱而得不到压制,最终酿成惨祸,侧面表明了爱伦·坡告诫我们在处于独处的困境中时,重视“超我”道德自省对压制邪恶冲动的作用。
三、“自我”的毁灭促使人与自我关系的进一步异化
“自我”代表着理性,它在尽可能满足“本我”需求的情况下,又制止着“本我”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弗洛伊德,2011:38)。
主人公的“本我”存在恶的原始冲动。主人公的善良温与软心肠只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共同作用后的显现。文中提到妻子和“我”性情相似。但最后只有“我”变得暴力残忍,妻子即使经常要遭受家暴依旧为救猫挺身而出。这说明主人公“本我”中存在恶的本能且比较强烈。“自我”的毁灭意味着人与自我关系的进一步严重异化。
主人公的死亡恐惧感终究逼疯了他,“噩梦”充当打开潘多拉盒子的第三把钥匙,“自我”就此毁灭,“本我”中恶的部分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弗洛伊德说过“抑郁症中的出现的死亡恐惧,是因为自我放弃了自己,因为它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超我的爱,而是受到超我的迫害”(弗洛伊德,2018:124)。主人公因为被愤怒蒙蔽双眼在虐杀第一只黑猫后,始终饱受着“超我”的谴责和“我”对死亡的恐惧。在西方文化里黑猫的形象使女巫的化身,同时爱伦·坡又将黑猫命名为“Pluto”,“Pluto”在罗马文化中是掌管死亡与阴间的冥王,这也给黑猫这一形象增添了一丝恐怖和死亡的色彩。尤其是在主人公杀死第一只黑猫后,莫名出现了与死去黑猫极其相似的黑猫,而且最令其感到恐惧的这只黑猫的胸口上那酷似“绞刑台”的“死亡之图”。由此可见,主人公在杀猫后内心承受着由死亡恐惧带来的强烈恐惧感而备受折磨。“我”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
弗洛伊德认为当“自我”处在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消弭的危险之中时,“自我”就会放弃自己选择毁灭。于是主人公的“自我”便在持续性的死亡威胁下,选择了毁灭,当“自我”失效,不再发挥“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节者,这意味着“超我”的彻底失效。
“自我”的毁灭,意味着“本我”中恶的部分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彻底释放且失去控制。此时主人公与自我的关系进一步发生异化。“自我”听从“超我”道德规范的要求对“本我”进行压制,由于“自我”的毁灭,主人公的善良和理智被彻底泯灭了。这体现在结局主人公本想在地窖中虐杀第二只黑猫,但是妻子的阻拦使我更加被愤怒蒙蔽理智,最后残忍地虐杀了妻子。杀人过后,主人公完全没有任何后悔和恐惧,反而冷静地思考着如何处理尸体,因为主人公已经完全失去道德感,不再受良心、道德的约束和谴责,而是彻底被“恶”所掌控。后来,即使是在面对警察的盘问,也能做到坦然自若,甚至是将其视作一种挑战的游戏,挑衅着敲击妻子尸身所在的墙面提示警察死尸的所在。主人公肆无忌惮地宣泄着“本我”中恶的部分,道德沦丧,失去理智甚至变得麻木,“我”变为“非我”,人变为非人,原本善良温和的“我”早已不复存在,最终沦为残忍暴虐的杀人狂魔。
“自我”的毁灭,意味着“超我”道德规范的完全失效,这导致“本我”中恶的部分将不再受压抑,主人公丧失道德感和理智,此时主人公与自我的关系发生了进一步严重异化。
四、结语
在《黑猫》中,作者爱伦·坡展现了主人公为了逃避虚伪冷漠的人,脱离社会集体,在孤立状态下走向异化的过程。无名的主人公代表一个社会缩影,它体现的是作者所处的19世纪,当时正处工业化加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人变得疏离和重物质。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扭曲——对“善”的轻蔑态度其实是主人公走向孤独与异化的根源,爱伦·坡企图批判这种扭曲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唤醒人们与善的追求。同时表达了对现代人处在孤立状态下,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担忧。爱伦·坡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应当重视内心道德对邪恶冲动的压制作用。作者通过人物走向癫狂的过程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不仅让我们要警惕自我封闭的病态性格,鼓励处于孤立封闭的人们要勇于回归社会集体,在人群中获得快乐和归属感。而若将快乐寄托在物质上,必将失去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