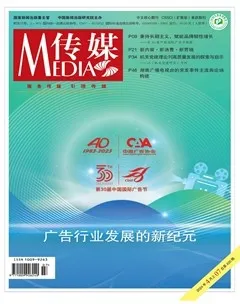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的叙事创新及其启示
2024-05-07倪莉
倪莉
当下为志、过去为史,现今的志即为未来之史。自古以来中国便有方志记载习惯。近几年,国家非常注重地方志的修编与传播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过多次强调:修史修志需要把书本与文物赋予生命,通过文学出版行业与文化传媒行业的相互配合,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更大范围地传播中国声音,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史志文化的一种创新传播方式,《中国影像方志》就是一系列蕴含浓厚地域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现代纪录片作品,是当今的影像志演绎,其对地方志的传播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中国影像方志》:现代影像版方志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从周朝伊始,我国便有编撰地方志的史官,在《史记》中也有小史掌管“邦国之志”、外史掌管“四方之志”的记录。这些经世致用的经典资源为后世研究地方历史提供了一手史料,是地方文献大宗。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中,创作者从地方文化出发,以现代化媒介技术呈现给观众各县域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为中国地方文化的表达打造了一部现代化的影像传记。
县域自古便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基础单位,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造就了如今各具特色的县。就县城地名而言,陕西韩城之名由来可在《诗经》总集中溯源;湖北监利之名起源于孙权“兼收鱼稻之利”典故;江苏句容之名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哲学理念契合;浙江安吉之名取义于汉灵帝“安且吉兮”的感叹等。如今很多县城都与周边乡村连接,这种连接纽带是推动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各个县城更迭的记录也是对整个中国日新月异发展的直观表现。该纪录片将影像视角投向县域,不拘泥于现有典章,通过箪食瓢饮小巷生活气息诠释了中国人朴素的生命哲学观。
历史上我国每隔几十年便会对地方志进行修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广泛成立了史志办部门,地方高度重视地方志的收藏与编纂,《中国影像方志》可谓通过现代影视技术传播地方志的开先河者。该片以省为一卷,以每省的各县为一集,计划摄制2300多集,截至2022年初,已经更新到876集,每集约40分钟左右。作为现代影像版中国方志,其谋篇布局采用的是传统的卷与篇进行模块化记录,特采用“引言”“地名记”“地理记”“人物记”“名胜记”“美食记”等板块详细记录各县情况。这些板块简洁明了,仅用3~6分钟就可以满足快时代、微记录的观看需求。
该片类似于以往的长纪录片,多方位、多视角地对国内各个县城的前世今生影像化呈现,通过展示各地风土人情、建筑风格和饮食文化等内容,见证了我国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感人之心,莫先乎情,该影像志中包含了很多情感寄托,让背井离乡的人有了更多思乡之情。每一集都设置了“后记”部分,创作者会言简意赅勾勒该县城风貌,表达创作初衷。
二、《中国影像方志》的叙事特点
作为方志史料,首先要忠于历史、保留历史史料的严肃性;而作为纪录片,又要求其兼具趣味性,与观众能产生情感共鸣。
1.融合多种叙事结构。该片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文献类方志史料,但从表现形式上又是纪录片。如果像以往那种历史纪录片的形式规划,既缺乏大量的影像資料也难以创新。但作为方志类纪录片,仍要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因而才有“取文字方志之精华,开影像方志之先河”的初衷。该纪录片融合了多种叙事结构,类似传统文字小说中使用的“念珠式结构”,又叫“团块式结构”或“串珠式结构”,主要用以讲述每个县城各个板块的历史。这些板块之间看似没有关系,但都属于县城人文景观中的一景,像串糖葫芦一般把一个县域的历史事件、文化特色、美食发展等串联起来,安排得十分合理自然。该纪录片还引用了电影剧作中常用的“戏剧式段落结构”,每个剧作由多个小故事来构成,并且每个小故事自身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还有戏剧性对比与冲突。该片在独立播出的每个县志内容中,由几个不同的小故事组成,这些小故事本身就具备故事性和冲突性,创作者在独立小故事之间的衔接上也花了心思,上一个故事的出场常常为下一个故事做铺垫。每个县志的阐述又都以时间发展为逻辑主线,这种兼具整体性和戏剧性段落的特点为观众翻开了一页页生动活泼的“地方历史书”。该片还使用“线性叙事结构”,除“引言”与“后记”外,微观层面的故事演绎正如散文一般娓娓道来,看似没有特定章法却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效果。
2.融入多种表现手法。方志文化不同于电视剧可以有多种艺术创作,它更强调历史的真实性。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既能保证历史真实的严肃性,又能尽可能地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就显得十分重要。过去的影像资料实在稀少,片中引用了一些县域的珍贵影像资料为辅助,但这种影像只有近代才会出现,而在历史上有很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故事并没有真实影像,因此创作团队引入了表演性质的情景再现,以影视化方式讲述过去的精彩故事,这种情景再现的方式仍以历史为蓝本,高度还原真实史实。此外,创作团队还引入了数字动画这种新媒体技术,如四川卷会理篇中,就使用数字动画描绘了状元杨慎从会川卫去永昌府的线路图,短短几十秒便使观众印象深刻。资料与技术的加持并非创作团队表现手法的全部,他们还花了大量时间采访当地文化传承者,保留了珍贵的当事人音视频资料,今天的记录在将来又会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抛开内容表现,创作团队在纪录片制作中也运用了多种技巧。例如,在展现历史战争激烈紧张时影像节奏偏快,而在表现人物生活气息的场景时节奏就慢;表现历史上的灾难场景时色彩暗淡,而在展现少数民族特色时颜色又变得鲜艳;展现生活场景时大多是近景镜头,而为烘托宏大场景时镜头就会拉得很远;表现局促与紧张时光线更为晦暗,而表现愉悦与轻松时光线更为明亮……
3.多角度阐述历史。从整个纪录片的呈现来看,创作团队采用了宏观到微观再回到宏观的叙事方式。“引言”开始,先让观众对具体某一县城有一个整体感知,大致勾勒该地区的前世今生,然后再进入具体“文化记”“手工记”“传承记”等各个板块,这些板块采用的是微观呈现,让观众从小处入手了解当地的生活文化,最后再回到宏观叙事的“后记”收尾。将这种叙事手法运用在方志文化的表达与传播上非常少见,它使令人望而却步的史料档案变成鲜活又有烟火气的“故事集”和“地方历史书”。其中,像“传承记”中对各地的非遗传承也有大量记录和描述。这些影像记录将会成为我国非遗的重要史料。
从表现视角来看,该纪录片一改以往引入“历史名人”的方式,而是从普通人的视角看待县城的变迁,以普通人为出发点去了解人们关心的历史和当下。该片中的“人物记”并非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而是选用更为贴近平民的人物与故事,如文化学者、当地商贾等。而在“民俗记”“传承记”和“手工记”中更是大量出现了普通的手艺人和表演者。这尽可能地消除了观众与历史的隔阂,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之间的距离,让人产生“历史离我们并不远”的参与感,大大弱化了以往方志给人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三、《中国影像方志》创新叙事的启示
地方志文化在資政、存史、教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融媒体时代,方志从文字形式进化到影视,使方志内容在呈现方式与传播范围上得到拓展,其肩负的文化传承使命也需要强有力的转型升级。
1.积极主动传播,普及方志文化。深入、系统地挖掘中华地域文化特色,以更加鲜活的方式推出名镇名村志纪录片或系列书籍,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努力将地方志文化作品纳入国家对外宣传的文化项目是重要路径。例如,乌镇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经当地各方努力出版的《乌镇志》就是国家的重点文化项目之一。还要扩大宣传地方志文化,比如,外文版本的地方志会成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旅游景点和地方文化的良好推介。通过投资洽谈的方式将方志进一步融入到各种商务活动中去,以背景材料的方式附带传播也是重要方式,例如,外文版本的《成都精选》就广泛出现在各种旅游景点窗口以及班列上。地方政府还可以与国内外权威学术机构合作,利用国际舞台进一步传扬方志文化,在宣传方志文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以更加容易被当地受众接受的方式与渠道进行异国宣传,实现“大部头”到“口袋书”的转变,建设中国各地区方志文化的“丝绸之路”。
2.文本向视频转化,强化方志传播看点。一直以来,即便是具备鲜明的地方韵味和极高的历史价值,方志文化仍会给人以晦涩难懂与刻板生硬的印象,所以这一不足便是现代社会方志文化传播的重要切入点。视频化是当下受众最喜闻乐见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画面彰显地域个性、用不同景别的镜头语言赋予地方文化全新视觉体验;利用不同地域的方言进行讲述能增强趣味性、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在方志文化的采访和记录中融入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凸显方志文化叙事个性化和平民化,将以往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气息的方志文化融入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中,再结合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增强地方志文化的亲和力和渗透力,让广大受众对方志文化产生兴趣、对地方人文产生兴趣。
3.讲好地方故事,增加方志文化趣味性。提到方志,多数人对其印象都停留在研究人员及相关学者为了查询资料或考证史料而去图书馆有目的性地查阅资料、学术研究,认为是与普通人毫无关系的档案资料,这也导致其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也比较大,很多小县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很多引人入胜的小故事。这些地方故事经过专业人士的编排和剪辑,引入戏剧叙述方式,以生动活泼的视频形式展现出来。正如禹州地区被列入国家非遗的“钧瓷”传承人任星航曾表示,方志既能让人们了解钧瓷的制造历程,也能让更多人感知禹州的社会现状。还有会宁的“洋芋”、安吉的“异物记”、沛县的“音律记”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史料延展,它们对各地风貌有极好的诠释。这种以讲故事来演说地方志的形式能够极大激发当地人的情感与文化共鸣。
4.应用多屏联展,创新方志文化传播模式。移动媒体的出现开启了传播的新时代,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共享全球各地的信息,实现了由“传播者”中心化向“受众”去中心化时代的升级。但《中国影像方志》在微博、抖音、公众号、自媒体等平台传播甚少,主要以“央视网”和“央视影音”等央视平台的科教频道传播为主,双向交流与反馈机制相对较弱,所以传播方式与渠道还需要丰富。在社会转型期,媒体与受众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分化与演变,人们对媒体内容的接触、消费日新月异,所以在思考方志文化的传播过程时,需要重视“两微一端”的开发建设,也需要转变传播图景,通过与短视频网站合作的方式对节目进行区别化播放,以更多的媒介渠道进行宣传与互动,尽可能放大方志文化的传播影响力。
四、结语
地方志,尤其县志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珍贵且重要的记录,记录了中国各时期各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图景。史志工作是具有文化底蕴和教化价值的事业,地方志工作不但要“修志”还要“续志”,做好地方志的普及与传播仍需创新。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
【编辑:王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