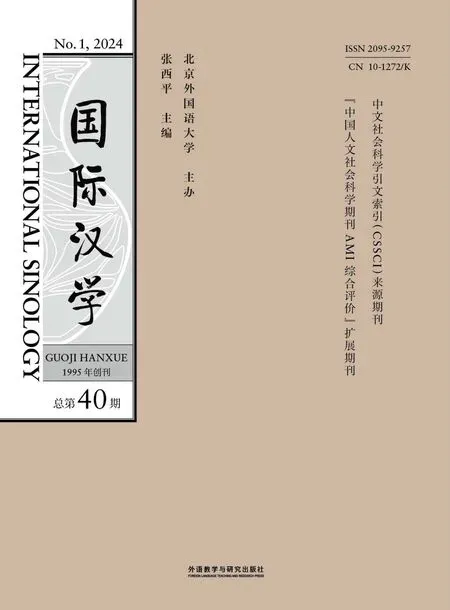评潘文国《中籍英译通论》*
2024-04-30蒋向艳
□ 蒋向艳
自20 世纪90 年代国内兴起“国学热”以来,传统文化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2004 年11 月,我国在海外设立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重视国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问题。从国家发展而言,一个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升之后,势必需要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文化形象,才能在国际上展示良好的综合形象。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传统文化亟需现代化,只有经过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那么,古代经典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在笔者看来,翻译无疑是使古籍“现代化”的最佳方法和途径,因为翻译即阐释①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490 页。。英译中籍,可以说就是以现代的方式阐释经典,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潘文国先生的最新论著《中籍英译通论》②潘文国:《中籍英译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以下简称《通论》)是一部应时而生的典籍英译论著。这部论著源起于作者2018 年年底应英国威尔士大学“英国汉学院”(British Academy of Sinology)的邀请,为文学院的硕士生讲授“汉学英语”(Chinese Classics in English Teхt)课程;作者在多年翻译理论探索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以准备这门课的讲义为契机,完成了这部论著。《通论》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理论篇,分六章阐述中国文化的体系与核心、中籍英译的新思路、中西方翻译理论简史及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下册为应用篇,以八章的篇幅分别展示翻译技巧、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古文今译、散文美译、哲言精译及诗歌翻译等翻译实践。两册书共近104 万字,可谓皇皇巨著。它不仅是一部全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课程教材,更是翻译学界的一项丰硕成果。
我对《通论》最大的感受,就是“新”。作者在论著中提出了不少中籍英译的新思想、新理论,发人深省。首先,第一章讨论中国文化的体系与核心,为中国文化体系下了四句话的断语,即“以‘六经’为源,以‘四部’为流,以《四库》为结,以‘治道’为本”③同上,第18 页。,简明扼要地抓住了中国文化体系的主脉。按照这条脉络去理解中国文化,则能把握其大矣。文中进而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治道”,即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讲“治理”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主题就是治国理政,追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④同上,第19 页。我们很容易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出发来理解这个观点: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始被确立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它确实是作为一整套治术用来辅助统治者巩固其对天下的管理的。中国延续两千年之久的科举制是使这套治术服务于政府管理的强大保证。“学而优则仕”,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必须熟读四部,尤其是经、史、子、集,只有对这些书籍谙熟于心、透彻理解并能举一反三加以运用才可能高中科举,进而加官晋爵,执掌国家行政管理之职。“四书”是继中国文化之源——“六经”之后最重要的经书,在科举考试中自元代开始取代“五经”成为试“士”的核心文本,这一做法延续至明清两代。元、明两代开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基础文本①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见《中国文化史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204—236 页。。晚明张居正为了给年幼的万历皇帝讲学甚至专门撰写了《四书直解》。官修史书的一大目的是“资治”,正如《资治通鉴》的书名所揭示的。经、史之外,子部的道家文本《道德经》被班固称为“君人南面之术”②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书,而探讨兵法的《孙子兵法》翻译到海外以后被解读为一部上乘的管理学著作,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包括商战在内的各个领域,③韩胜宝:《改革开放让〈孙子兵法〉红遍世界》,载《孙子研究》2018 年第5 期,第92—98 页。未始不与其突出的“治道”特征有关。即使是集部的文人文学创作,也莫不以家国情怀为这些作品根本的气质和精神。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核心,确实可以以“治道”两字来概括。潘先生对中国文化核心的剖析可谓深刻而透彻。
《通论》的第二个“新”,是潘先生在中籍英译上采用的新思路,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第二章。潘先生为“译出”辩护,以往中国人主要从事“译入”,“译出”主要由外国人来完成。但时移世易,“译出”的任务不能仅仅依靠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来完成,因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理解总比外国译者更全面、准确、深刻,“译出”往往承担着重塑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重担。如果译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甚至歪曲,势必导致中国文学文化形象的偏颇和扭曲。文中还从另一个角度为“译出”辩护:从语言发展的规律来看,多元化英语、复数英语(Englishes)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故“中式英语”并非十恶不赦,相反有其实行的必要性,尤其是中国典籍的英译,可以借助中国文学文化概念体系的英译来实现。此外,“文化的多元化则提出了‘译出’的另一个必要性”④潘文国:《中籍英译通论》,第61 页。。作者为中国人从事“译出”辩护,并非说以后译出事业不必由外国人来完成,仅仅由中国人来承担即可,而是以此鼓励更多的中国人运用好中英双语,为中籍英译事业出更多力。毕竟在实践中,中外合作翻译取得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如陶友白(Witter Bynner,1881—1968)、江亢虎合译唐诗集《群玉山头》,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1999)夫妇合作英译《红楼梦》,李治华、雅歌(Jacqueline Azélaïs,1919—2009)夫妇合作法译《红楼梦》,等等。
作者提出中籍英译的新思路,就是“三原一正”:“回到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架构”⑤同上,第69 页。,即“经史子集”的四部框架;厘清源流,即厘清中国文化之源——“六经”,以及围绕“六经”发展出的“四部”;精读原典;然后最重要的是“正名”,即“正校译名”,这是指中国文化体系里的术语翻译。作者认为,当前中籍英译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文化术语的翻译问题,这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文化形象在国际上的塑造。“在文化翻译中,术语是关键甚至是生命。‘西化之中国文化’的形成,除了学科架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术语。……因此具体做翻译,必须从‘正名’开始”⑥同上,第71 页。。这个问题是在典籍翻译所走过的独特历程中产生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首个热潮是明末清初以欧洲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西译运动,文中称之为“第一次出发”。在这个阶段,“从自己的语言文化出发去看别人的语言文化”⑦同上,第73 页。,即“格义”译法占据主导,从而导致中国学术话语西方化的主要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第二次出发”(始于2010 年)的历史性时期,潘文国认为一个当务之急是“以正名补救、升华和超越‘格义’”⑧同上。。这是因为第二次出发的时代条件已经远远不同于第一次出发时的明末清初,那种“格义”译法有很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新的时代呼唤新的译法和译本。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Roger T.Ames)、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1934—2017)以实践揭开了中籍外译中“正名”阶段的序幕。比如“孝”,晚明在华传教士译为“filial piety”,这是一个典型的格义译法,因为“piety”是一个宗教意味浓郁的词;而安乐哲给出的新译词是“family reverence”——“reverence”这个词显然更加贴近中国文化世俗性的特征。潘先生肯定安乐哲、罗思文这种哲学分析译法的尝试,同时认为中国翻译者应该在这场“正名”翻译运动中有所作为。潘先生身体力行,按“四部”框架对其中的名词进行译名的讨论,为构建中国文化术语的英文体系做了初步尝试。比如他提出需细化翻译不同层次的“经”:“六经”之经译为canon,一般的“经”译作classic,“传”译作transmission 或notes,“记”译作records。“诸子”译为schools of thoughts,“八 股 文”译 作four-couplet essay,“词”译作tune-poetry,“曲”译作melody-poetry。尽管具体的译词可以再讨论,但潘先生的翻译思路颇有启发性,值得今天的中国译者借鉴,并能鼓励他们加入对中国哲学术语翻译的创新尝试和探讨中来。
《通论》的第三个“新”见解,是明确指出中国和西方社会在语言使用上的主要差异造成中西方翻译研究的不同道路。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第一个提出西方译学的文化背景是双语乃至多语社会,甚至可以说,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就是一个“共同语+母语”的双语或准双语社会。①潘文国:《中籍英译通论》,第114—115 页。潘先生对照西方的用语传统,指出中国自古至清末一直是一个单语社会,直到20 世纪20 年代学外语的人增多以后,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才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双语社会”②同上,第324—325 页。潘文国先生在其《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一文首次特别提出“单语社会”和“双语社会”是中西两大译学传统形成的重要背景;详见《国际汉学》2020 年增刊,第5—36 页。。“单语社会”和“双语社会”之别是中西方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和历史背景,正是这一点决定和影响了东西方走上不同的翻译研究道路。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直译、意译之争和忠实、自由之争,正是基于“双语社会”的背景,因为只有在人们对译出语和译入语都懂的前提下才有探讨直译、意译,忠实、自由的可能;而在传统为“单语社会”的中国,当大部分读者只懂译出语、不懂译入语的时候,是无法探讨直译意译、忠实自由的。潘先生指出,对中国翻译研究有意义的是文质之争和译名研究。只有深刻掌握了汉英语言对比知识和中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才能立于两种语言、两种翻译研究传统之间,洞察到一般人难以明察的事实和真相。潘文国指出中西方翻译研究之别,也是为了说明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中国的翻译研究绝不应该盲目搬用西方的翻译研究理论和学术术语,而是必须建立适合自己的理论。③潘文国:《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国际汉学》2020 年增刊,第5—36 页。
由此,《通论》第六章系统阐述了中籍英译的新理论——文章翻译学。文章翻译学是潘文国先生近些年来致力探索的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一大理论成果。自2008 年以来,他力倡文章翻译学,先后在《典籍英译研究》第五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上海翻译》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专论,在学界介绍和推广这一理论及其应用。在《通论》中,潘文国系统梳理了他对文章翻译学的思考,从文章翻译学提出的背景、为什么是文章翻译学以及文章翻译学的道(信达雅)与器(义体气)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该翻译理论。他所倡导的文章翻译学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以做文章的态度去对待翻译,做翻译也就是做文章”④潘文国:《文章翻译学的名与实》,《上海翻译》2019 年第1 期,第3 页。,因为“文章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翻译成的文字当然也不能例外”⑤同上。。基于文章学的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涵盖了除口译之外所有书面语的翻译,要讨论中国的翻译学就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文章学,因为“离了文章学去谈中国译学传统,只能是隔靴搔痒;抛弃文章学去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也只能是无源之水”①潘文国:《文章翻译学的名与实》,《上海翻译》2019 年第1 期,第3 页。。“找到文章学,就找到了贯穿中国翻译研究两千年的一条主线,也为建设今天的翻译学找到了方向。”②潘文国:《中籍英译通论》,第341 页。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根植于文章学,即认为翻译既是翻译,同时也是写文章。文章翻译学的提出还为放弃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所有讲究辞藻的典籍都是“文章”,都是“美文”,也都是“文学”,都要运用“文学”的翻译方法。他将严复的“信达雅”视为译事之“道”,并构想出“义体气”作为具体翻译实践的要求,使文章翻译学既有形而上的理想境界可追求,又有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可循,从而使得该翻译理论日趋完善。总之,文章翻译学是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理论,可在我国译学界推广实践。笔者认为,文章翻译学是近年来潘文国先生对中国译学界最大的理论贡献,也是《通论》最大的理论亮点,书中尚有许多细节值得译界学者细品、揣摩,有心者也可以撰文加入关于文章翻译学的探讨中去,共同助力这一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除了上面对笔者启发最大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通论》内容宏博,第三章至五章简述中西方翻译理论简史,为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者提供必要的中西翻译理论参考。下册应用篇则以丰富的翻译实践现身说法,为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者提供借鉴。其翻译对象包括哲学文本如《老子》、诗赋、史书、古文、散文,其中第六章和第七章“哲言精译”部分,潘文国先生列出了五经四书和儒道法墨诸子散文的原文和多家英译文,并进行对比分析,资料弥足珍贵,分析鞭辟入里,对翻译教学和研究人员来说可谓“踏遍铁鞋无觅处”的宝库,颇具参考价值,也为译界人员提供了更多讨论的话题和空间。
总之,《中籍英译通论》展示了潘文国先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思考成果,是近年来中国翻译学界一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兼具的重要论著,是一部兼顾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典籍英译的通论性教材,对于中国翻译学以及中国典籍外译事业在新时代的发展均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