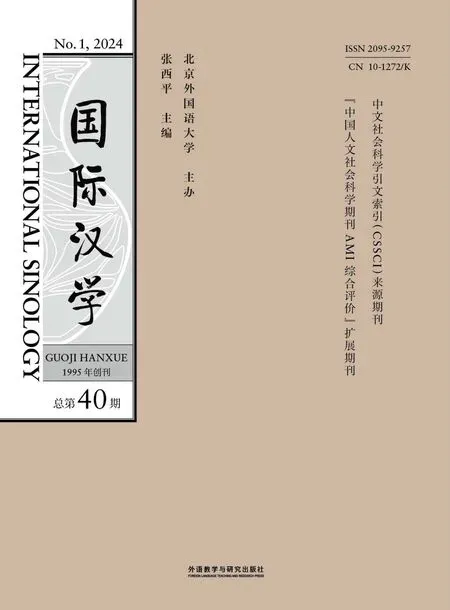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苏格兰的中国艺术品收藏
2024-04-30□谢琛
□ 谢 琛
一、引 言
英国北部苏格兰境内各类公私机构有数量可观的中国藏品,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所藏的甲骨文是东亚以外的第二大收藏①目前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内共藏有甲骨1784 片。这批甲骨主要由美国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Frank Chalfant,1862—1914)和英国驻山东青州的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共同购买、持有,后出售给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苏格兰皇家博物馆。郅晓娜:《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的资料来源》,载《甲骨文与殷商史》2015 年第1 期,第298—299 页。,仅格拉斯哥境内的伯勒尔博物馆(The Burrell Collection)一处就有1800 余件中国瓷器、玉器和青铜器等物品。与丰富的中国藏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系统性的对于苏格兰境内中国藏品的研究却极为有限。所幸,从2017 年开始,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与苏格兰境内的36 家机构合作,调查了整个区域内的中国、日本、朝鲜的藏品状况,该项目在2020 年初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公布了成果。②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Scottish Museums, https://www.nms.ac.uk/media/1161839/east-asiacollections-in-scotland.pdf,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该报告从方法论上借鉴了在1994 年出版的研究苏格兰域外收藏的作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苏格兰域外民族志收藏》(A Wider World: Collections of Foreign Ethnography in Scotland)和2004 年出版的对英国境内的日本艺术收藏进行统计的专著《英国日本艺术收藏手册》(A Guide to Japanese Art Collections in the UK),按照从东北到西南的地理位置顺序,以收藏机构为单位组织全书结构,另在各个机构的条目内按照国家和器物的类型进行分类。Barbara Woroncow, “Presenting Other Cultures,” A Wider World: Collections of Foreign Ethnography in Scotland. Broхburn: Alna Press Ltd, 1994; Gregory Irvine, A Guide to Japanese Art Collections in the UK.Amsterdam: Hotei Publishing, 2005。
15 世纪葡萄牙人开通了前往亚洲的新航路,其后荷兰和英国等国纷纷建立主营亚洲贸易的公司,自此中国的物品就开始源源不断被运往欧洲。但是由于苏格兰地处欧洲主要商路边缘,具有相对滞后性,目前可见的绝大多数苏格兰境内的域外藏品都是在1880 年至1920 年运往苏格兰境内的。③Woroncow, op.cit., p.55.笔者选取了这期间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苏格兰人收藏者,按照身份将之划分为四个类群:在亚洲任职的专业人士、与中国有涉的实业家、以亚洲艺术为灵感的艺术家、参加战争的军人。
这里的收藏者身份多元,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的数量非常少,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苏格兰人或因谋生求财,或受殖民利益驱动,或因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对他们来说,这一路收获的除了知识见闻以外,还有品目繁多的异域物品。与之对应的是,虽然此文涉及的“中国藏品”,即各机构内所藏的与中国有关的物品,现在的身份属性基本都是博物馆内以研究、教育和展示等公益目的而存在的“藏品”,但此研究的目标之一是还原物品在具体历史情境里从中国到苏格兰的迁转过程中,对于收藏者的功用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际互动中,这些“藏品”曾扮演劫掠品、礼物馈赠、工作成果、旅途纪念品等多重角色。重构这些“藏品”和“收藏者”在历史现场中的身份,对于揭示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中国和苏格兰这两个国家间的互动,探析中国物品在异域的接受史及其背后的动因,以及描绘对应时期苏格兰的历史图景都有重要意义。
二、来华任职专业人士的中国收藏
苏格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并不优越,超过三分之二的是岩石或土质贫瘠不宜耕种的土地,并远离中世纪以来围绕地中海发展的传统欧洲贸易和文化中心区域。与相对富庶的英格兰不同,苏格兰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外向移民频繁的地区,这种趋势在19 世纪后半期达到高潮。①Jeanette M.Brook, The Mobile Scot: A Study of Emigration and Migration 1861-1911.Edinburgh: John Donald, 1999, p.1.1901年的普查显示,苏格兰的人口总数约450 万,仅在1815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超过230 万人离开苏格兰前往海外。②T.M.Devine and Angela McCarthy,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in Asia, c. 1700 to the Present Settlers and Sojourner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对苏格兰人来说,出走海外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贸易和求职。③Dale Idiens, A Wider World: Collections of Foreign Ethnography in Scotland.Broхburn: Alna Press Ltd, 1994, p.3.苏格兰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前往北美、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还有少数前往亚洲。但是与其他目的地中以家庭为单位、以长期定居为目标的移民形态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前往亚洲的苏格兰人大多是年轻单身男性。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旅居者(Sojourners)而非定居者(Settlers),在完成财富积累后往往会选择回家乡。④T.M.Devine and Angela McCarthy,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in Asia, c. 1700 to the Present Settlers and Sojourner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3-4.
在亚洲旅居的经历使得在中国长期任职的苏格兰人的藏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具有优势,他们在与中国有涉的物品制作或收集上可以利用其在中国建立的社会关系,通过与中国人合作的形式获得第一手资源。
詹姆斯·霍尔丹·斯图尔特·骆克(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即骆克爵士,是一位热衷中国艺术的苏格兰收藏家,他旅居中国40 年,在英国对中国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时期曾担任要职,后又出任威海卫长官,退休后回到英国。除此之外,骆克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爱和修为都堪称学者级别。他能说流利的粤语和中文,曾出版过多部与中国有关的论著。
骆克的中国收藏包含门类很广,包括数量可观的古钱币、绘画和书法作品以及数千件拓片。目前他与中国有关的通信等文献材料存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器物类的收藏由他的女儿捐赠给骆克的母校——位于爱丁堡的乔治沃森学院(George Watsons’s College),现 由 学 院 以 借管形式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合作研究。在其特别擅长的中国钱币收藏领域,骆克有两本著作发表——《远东货币:从最古至今》(The Currency of the Farther East: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the Present Day)和《斯图尔特·骆克的中国铜钱收藏》(The 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pper Coins)。
骆克的中国收藏以较快速度扩充始于1910年,彼时的他在经济上较有保障,在威海卫的工作不繁忙,且明确得知自己升任港督无望,这为他购进和研究中国藏品提供了经济、时间和心态上的条件。⑤Shiona Airlie, Thistle and Bambo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 p.156.他初期的绘画藏品主要是从有洋行买办经历的中国香港人谢缵泰处购买。二人往来书信显示,谢缵泰曾向骆克以45 英镑的价格兜售18 幅宋元明时期知名画家的作品,在没有看到作品的情况下骆克就支付了这笔费用。①Shiona Airlie, Thistle and Bambo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 p.156.后来证明,这批作品中有不少是赝品。②Sonia Lightfoot, The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pp.40-41.但是,同样从谢缵泰处购得的价格非常低廉的一批19 世纪海派画家的作品却成为骆克绘画收藏中的亮点之一。③Airlie, op.cit., p.161.据席欧娜·艾尔利(Shiona Airlie)统计,从1910 年至1921 年,骆克从多方陆续购入约500 幅中国绘画作品。④Ibid., p.158.
骆克数量可观的中国收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其中除从买办处购得外,也不乏各界友人的馈赠,这些作品可以看作他在中国社会交往的缩影。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一幅黄公望落款的山水立轴,其上有跋语:“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常熟人。山水为元四大家之冠,画家奉为圭臬,光绪己亥二月大清国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王存善手题赠大英国辅政司骆任廷先生,时同任九龙勘界。”1899 年,时任广东补用道的王存善与当时任香港辅政司的骆克一同勘探新界,并与之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这件署名黄公望的作品应该是当时王存善送给骆克的礼物。⑤刘蜀永:《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2009 年,第35 页。另,在苏格兰国家画廊的收藏中有一幅由乔治沃森学院在2006 年捐赠的由艺术家蒋彝(1903—1977)为骆克爵士所作的肖像画,这幅作品是二人交往和友谊的见证。在蒋彝旅居伦敦的岁月里,骆克爵士曾与之交善,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曾在每周六的早上探讨中国经典。后来,蒋彝在骆克爵士的引荐下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职。⑥Da Zheng and 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ler from the East — A Cultural Biography.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7.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有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雷金纳德·法瑞尔(Reginald Farrer,1880—1920)和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等一批曾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植物猎人”的大量珍贵照片、手稿、地图和日记等档案材料。其中以苏格兰出生的乔治·福雷斯特对皇家植物园的捐赠品最具代表性。福雷斯特出生于苏格兰小镇福尔柯克(Falkirk)的布料商人家庭,完成基础教育后,曾在药店当学徒。他在得到一份遗产后,踏上了探索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旅程。1902 年,他成为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植物标本部门的一名助手。1904 年,他第一次来到云南,之后七次前往云南考察。在1932年最后一次考察中,福雷斯特死于心脏病,葬于腾冲。⑦Yvette Harvey, “Collecting with Lao Zhao [Zhao Chengzhang]: Decolonizing the Collecting Trips of George Forrest,” https://natsca.blog/2020/07/16/collecting-with-lao-chao-zhao-chengzhang-decolonising-the-collecting-trips-of-george-forrest/, 2021,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
笔者查阅档案目录,得知目前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中福雷斯特的藏品包括:10 盒福雷斯特在1903 年至1932 年的通信往来和日记等档案材料,内容涉及他前五次在云南的行程;分别以“建筑、寺庙、坟墓、城镇等”“福雷斯特、收藏家、人类等”“山、水、桥”“植物A-L”等命名的相片集;福雷斯特上课的笔记和图书等文献材料。近年来,越来越多与福雷斯特有关的研究指向他在云南时的纳西族助手“老赵”。“老赵”原名赵成章,他是福雷斯特在云南行程中的得力助手,甚至在福雷斯特居住在爱丁堡期间,赵成章也能独立带领由纳西族人组成的团队源源不断地向福雷斯特寄去各种新收集的样本和种子。在此期间数万件植物、鸟类、蝴蝶、蛇类和哺乳类动物的样本被送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埃里克·穆格勒(Erik Mueggler)在其一本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著作中,着力探讨了两位20 世纪初的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乔治·福雷斯特与云南村民在中国和缅甸边境收集植物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全书的引言部分以赵成章为主角,描绘了这位既识文断墨又对云南地理环境极为了解的纳西族人的日常工作,其中包括打包植物样本、绘制地图、与其招募来的其他村民从事为期数天或数月的远足探索、与赞助人“老福”(即福雷斯特)探讨新发现的样本等。
三、涉华实业家的中国收藏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欧美等国的铁路、钢铁、煤炭等行业得到飞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以实业起家掌握着大量资财的巨富资本家群体,他们的影响力已不只是局限于经济生产层面,而是渗透到政治、文化和公益事业领域,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下提及的两位实业家分别是出生于苏格兰、后移居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 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 和 在 格拉斯哥经营航运事业的威廉·布瑞尔(William Burrell,1861—1958)。他们除了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成绩斐然外,从其与中国有关的藏品中,我们还能看到他们所参与的国际事务和文化事业,也能看到中国艺术在当时国际环境中的接受情况。
苏格兰工业生产初期以靠近西海岸发展的棉纺织业为主,自1861 年起,受美国内战的影响,棉纺织业的原材料供应受阻,苏格兰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转向工程、船舶、机车制造、钢铁等重工业。①Olive and Sydney Checkland, Industry and Ethos: Scotland 1832-1914.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6.横穿格拉斯哥的克莱德河(River Clyde)沿岸建起了一批船舶制造厂,格拉斯哥顺理成章地成为苏格兰最主要的船舶制造和航运中心,并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帝国的第二城市”。威廉·布瑞尔是一位格拉斯哥的航运商人和慈善家。1944年,布瑞尔向格拉斯哥市政府捐赠了约8000 件其收藏的品目繁多的艺术品,其中约有1800 件中国藏品,②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Scottish Museums, https://www.nms.ac.uk/media/1161839/east-asiacollections-in-scotland.pdf, p.158,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包括184 件不同器型的从商代晚期到周的青铜器和汉代铜镜,超过1400 件陶瓷器,其中包括46 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唐代墓葬品、宋元明的青瓷,尤以洪武、嘉靖、永乐和康熙朝的官窑瓷器为精,仅康熙朝瓷器就达650 件之多。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17 世纪至19 世纪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③Ibid., p.187.布瑞尔的藏品可以说是在苏格兰境内国家博物馆外最具规模、最重要的中国收藏。
布瑞尔的中国收藏门类众多。根据尼克·皮尔斯(Nick Pearce)的研究,纵观布瑞尔一生,他的中国器物收藏生涯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早期收藏主要围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欧洲和美国范围内流行且符合大众审美的康熙瓷器展开。④Nick Pearce, “From Collector to Connoisseur: Sir William Burrell and Chinese Art 1911-57,” https://carp.arts.gla.ac.uk/essay1.php?enum=1097070125,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Nick Pearce, “A Group of Chinese Stoneware Buddhist Figures Reunite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58,1993-1994, pp.37-50.1911 年至20 世纪40 年代,中国境内铁路修建以后,大量墓葬发掘后,布瑞尔收藏品类开始扩大到更为专业和相对小众的早期瓷器、青铜器、汉唐冥器、玉器等。⑤Nick Pearce, “From Collector to Connoisseur: Sir William Burrell and Chinese Art 1911-57,” https://carp.arts.gla.ac.uk/essay1.php?enum=1097070125,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例如,他曾向在伦敦主营日本和中国艺术品的经销商约翰·斯帕克斯父子公司(John Sparks & Sons)处购得五件出土文物——长沙出土的玉腰带、青铜烙铁、河南出土的模型井、山西出土的谷仓模型以及龙门石窟的浮雕雕塑。⑥Ibid.
另一件改变布瑞尔购藏模式的重要事件发生在1943 年末,彼时82 岁的他表达了希望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格拉斯哥市的愿望。⑦Ibid.在此之后布瑞尔陆续购入超过2000 件新的藏品,其中包括一批形制比较大的适合在博物馆这样宽敞的公共空间中陈展的器物。如在1943 年12 月31 日,布瑞尔从艺术品经纪商约翰·斯帕克斯(John Sparks,1854—1914)处以350 英镑的价格购入一件真人尺寸的明代琉璃罗汉像。①据罗汉像基座左侧铭文可知,它于成化二十年(1484)仲秋,由工匠刘镇制造。铭文照片和相关研究,见Nick Pearce,“A Group of Chinese Stoneware Buddhist Figures Reunite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58, 1993-1994, p.42。
布瑞尔并未受到过专业、系统的有关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教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学者型收藏家和鉴赏家。他在15 岁时离开学校,加入由其祖父建立的家族航运生意。他所知的与中国有关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阅读及向几位亚洲艺术经销商咨询与其交流获得。布瑞尔本人从未到过中国,其中国藏品主要是在1911 年至1954 年向英国国内主营亚洲艺术品的经销商和拍卖行处购得。②Nick Pearce, “From Collector to Connoisseur: Sir William Burrell and Chinese Art 1911-57,” https://carp.arts.gla.ac.uk/essay1.php?enum=1097070125,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通过购藏,布瑞尔与S.M.弗兰克公司(S.M.Frank & Co)、约翰·斯帕克斯有限公司(John Sparks Ltd)、弗兰克·帕特里奇父子有限公司(Frank Patridge & Sons Ltd)等艺术品经销商长期保持着紧密关系。③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Scottish Museums, https://www.nms.ac.uk/media/1161839/east-asiacollections-in-scotland.pdf, p.185,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布瑞尔购藏的中国艺术品的质量和数量既是布瑞尔本人用功钻研的成果,也反映出当时英国国内中国艺术市场的成熟。
在美国发迹并被誉为钢铁大王的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小镇丹弗姆林(Dunfermline)一个贫困的纺织工人家庭,12 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在卡内基60 岁生日时,妻子将卡内基出生时所在的村舍买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现在的安德鲁·卡内基出生地博物馆(Andrew Carnegie Birthplace Museum)就是1928 年在卡内基出生的村舍旁边建的。在博物馆中有不少由卡内基本人捐赠的极具历史价值的物品,其中包括由康有为(1858—1927)及他女儿康同璧女士(1887—1969)赠送的两件真丝刺绣织品。康同璧女士所赠绣品图案为花卉、蝴蝶和蚂蚱。④Ibid., p.81.康有为所赠织品上有花鸟纹样,并绣有英文:This embroidery is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Peace Congress Hon Andrew Carnegie by His Eхcellency Kang Yuwe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Constitutional Association(该件绣品由中国国民党政会主席康有为阁下赠予美国国家仲裁与和平大会主席安德鲁·卡内基)。⑤Ibid.美国国家仲裁与和平大会于1907 年4 月14 至同月17 日在美国纽约的卡内基礼堂举行,安德鲁·卡内基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与来自全球的代表就国际和平和新旧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⑥W.T.Stead, “The 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Peace Congress in New York,” American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1907,pp.591-594.从这些馈赠的礼物可见卡内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及其国际影响力,亦可窥见他与中国有关人士的交往情况。
四、艺术家、收藏家的中国收藏
19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在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与东方艺术趣味紧密联系的艺术运动,如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将唯美主义运动重新定义为新英格兰艺术运动(New English Art Movement),并通过对1851 年至1878 年主要代表人物的演讲、出版物和设计,揭示亚洲艺术和文化对同时期英国艺术设计领域的重要影响。⑦Christopher Morley, “Reform and Eastern Art: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e New English Art, or Aesthetic Movement 1851 to 1878,” The Journal of the Decorative Arts Society 1850 - the Present, 2010, pp.112-136.中日两国艺术中的主题、线条和构图在“东方”审美复兴的背景下,成为很多欧美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为他们所借鉴,其后发展成为现代艺术设计风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詹姆斯·克罗默·瓦特(James Cromar Watt,1862—1940),出生于阿伯丁,建筑师、珠宝设计师,1879 年在阿伯丁文法学校毕业后任职于W&J Smith 建筑公司,并开始自己的建筑师生涯。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陆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等地游历。瓦特在希腊游学归来后,于1897 年发表了专著《希腊和庞贝装饰作品样例》(Examples of Greek and Pompeian Decorative Work)。①更多与瓦特有关的内容见Christine Rew, “James Cromar Watt: Aberdeen Architect and Designer,” Journal of the Scottish Society for Art History, 2000, Vol 5, pp.29-36。探访古迹,特别是对古代贵金属器物的研究,激发了瓦特的创作欲望。1896 年,他从建筑行业退出,开始专心于贵金属饰品的创作。他曾在1925 年前往锡金进行植物学考察,或在同一年游历了中国西藏和尼泊尔。②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Scottish Museums, https://www.nms.ac.uk/media/1161839/east-asiacollections-in-scotland.pdf, p.10,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瓦特并不十分富有,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中国和远东古陶瓷和金属器物藏家。他一生未婚,1940 年去世后,他的藏品被分别送往阿伯丁艺术画廊(Aberdeen Art Gallery)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Royal Scottish Museum)。在阿伯丁艺术画廊和博物馆中约有192 件漆器、珐琅彩、金属器等中国器物来自瓦特的捐赠。③Ibid., p.10.从中也不难看出瓦特作为一名精专于珐琅材质的珠宝设计师的个人趣味,比如其中就有一组中国19 世纪早期的女性饰品,银制底托上嵌有翠鸟羽毛制作的点翠头饰。④Ibid., p.15.此外还有数件明代以及清康熙、乾隆、嘉庆和光绪年款的珐琅器。⑤Ibid.
五、侵华军人的中国收藏
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出于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需要,快速对外扩张。英国将中国视为其亚洲部署的重要一环。从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至其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又对中国陆续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藏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苏格兰人,尤其是北部高地居民素来以体格健壮和勇敢善战著称,加之本地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和相对有限的就业机会,相较于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更愿意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参军,在历次侵华英军队伍中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有他们的身影,战争结束后相当数量的中国物品以纪念品、战利品或奖品的形式被军人带回故乡,成为苏格兰公私机构收藏中的一部分。
现在苏格兰境内的博物馆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收藏来自英国对华战争的劫掠品,但是并非所有物品的出处都有明确的记录可查,加之与它们有涉的苏格兰军人的生平鲜有文献可供参考,很多物品的来源尚有争议,但是部分战利品上的纪念性铭文可以清楚地揭示其身份。埃尔金博物馆有一个锡铁制的茶壶,其上刻有铭文“This teapot was taken at the capture of Woosung China”(此茶壶在攻陷吴淞时所获,中国),日期是1842 年6月16 日。由铭文可知,这是一件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吴淞会战的战利品。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内有一件晚清金制执壶,是由詹姆斯·奥普· 格 兰 特(James Hope Grant,1808—1875)的遗孀伊丽莎白·奥普·格兰特(Elizabeth Hope Grant,1816—1891)于1884 年捐赠给当时的爱丁堡科学和艺术博物馆(Edinburgh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其上刻有中英文铭文。中文是“重六十两,八成,咸丰二年”。两组英文铭文分别 是:“Taken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s Palace,Yuen Mien Yuen”(从中国皇帝的宫殿,圆明园获得)和“Presented to Lieut, General Sir Hope Grant G.C.B (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by the Officers of the Army in China, Pekin.October 1860”(由在中国的部队军官赠予上尉,将军爵士詹姆斯·奥普·格兰特‘巴斯勋章大十字骑士,北京,1860 年10 月’)。①Kevin McLoughlin, “Rose-water upon His Delicate Hands: Imperial and Imperialist Readings of the Hope Grant Ewer,” in Louise Tythacott edits, Collecting and Displaying China’s Summer Palace in the West: The Yuanmingyuan in Britain and France.London: Routledge, 2018, p.99.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格兰特将军在自传中提到这件金制执壶是奖品委员会(Prize Committee)送给他的礼物,并戏称它是中国皇帝用来在手上洒玫瑰水的器具。②Ibid., p.104.
苏格兰境内有数量颇丰的来自中国西藏的物品,在阿伯丁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Aberdeen Museums)中的435 件中国藏品中有147 件是西藏器物。③National Museums Scotl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Scottish Museums, https://www.nms.ac.uk/media/1161839/east-asiacollections-in-scotland.pdf, p.177,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3 月26 日。仅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一处可检索到的中国西藏物品就多达1332 件。苏格兰所获中国西藏藏品以1903 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以在印度的英国人通过与中国西藏人合作或者在当地购买的方式间接获得与中国西藏有关的物品。荣赫鹏(Fracis Younghusband,1863—1942)率领的英军侵略中国西藏战争开启了英国人直接从中国西藏获取器物的历史。以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为例,1903 年英国侵略中国西藏战争之前,该博物馆内的中国西藏物品主要从英国传教士手中购得,以与中国藏传佛教信仰有关的护身符、衣物、小的金属物品为主,旨在向英国民众显示在中国西藏传教的必要性和价值。在英国侵略中国西藏战争后,英军进入拉萨,西藏的物品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攫取,并源源不断地通过帝国网络运往英国本土。从1909 年至1910 年,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皇家苏格兰博物馆接收了来自埃里克·贝里(Eric Bailey)的120 件西藏物品。贝里家族几代人都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活动有关,弗雷德里克·贝里(Frederick Bailey)曾于19 世纪晚期在印度的林业部门任职,并与英国侵略中国西藏战争统帅荣赫鹏的家族关系亲密,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埃里克·贝里也曾参加此次战争,战争期间埃里克持续将在中国西藏所获的物品运往爱丁堡父母家中。其中明确已知的属于劫掠的物品包括他从中国西藏的奈尼寺庙(Naini Monastery)获得的1 件转经轮和8 件鎏金书封。虽然不排除英国人从中国西藏运往英国本土的物品中有一些确实来自当地僧侣和贵族对英高级军官的礼品馈赠,以及一些英国人出于对中国西藏文化的兴趣而出资购买的行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现有日记和通信等材料看,对大多数英国士兵来说“掠夺”所获是一种理所应当的能振奋人心的额外收益。战争劫掠文物的归还问题长期以来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归还文物是被掠夺国家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诉求,也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学界普遍认为将文物置于其所属的文化情境中,方能更好地解读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对于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最重要的参考文件是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 年公约”)。但是该公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如国际公约仅对缔约国有效,以及除归还文物需要更有效的国家间外交层面的接触和协商外,最重要的一环还在于藏品所属博物馆等机构对于物品入藏前流传信息的研究和公布。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以报告形式在2020 年公布的苏格兰境内中国收藏的调查颇具研究和讨论价值。
六、结 语
当私人收藏成为公共博物馆机构的一部分,除了个别围绕某一人物或某个特定收藏而设的博物馆外,藏品所涉的收藏史和私人藏家的主体性往往会在公共机构的发展和陈展过程中逐步消解,这时以“人”(收藏者)而非以“物”(藏品)作为切入点的考察往往能更有效地将“物”定位于其生命历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并能揭示“人”的特性。本文将苏格兰收藏者归纳为四个群体,虽无法对彼时与中国有涉的苏格兰人做到面面俱到的关照,但却能从中一窥彼时苏格兰的中国收藏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在华任职的专业人士在信息获取和社会关系上具有其他群体没有的优势,他们的中国收藏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性,通过与中国人合作和交往,他们获取藏品的主要方式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向艺术品经销商购买、委托中国艺术家制作、接受中国友人的礼物馈赠等。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现在苏格兰境内博物馆中的很多与中国有涉的藏品是旅华苏格兰人的工作成果或对在华工作生活的记录,这些苏格兰人除收藏艺术品外,还提供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珍贵史料。同样有在华直接经验的还包括参与侵华战争的苏格兰军人,作为战利品被他们带回到苏格兰的中国物品从出处(provenance)的正当性上讲无疑最有争议性,但也是英帝国扩张史的书写中最切题的注脚之一。这部分文物的追回和索要依然道阻且长,需要各方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并非所有中国物品的收藏者都曾亲身旅居中国,像布瑞尔这样财资雄厚的实业家积聚的规模庞大且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国收藏反映出来的是彼时英国乃至欧洲范围内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成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艺术特征之一是“东方”审美复兴,亚洲风格对欧洲艺术设计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也促使部分苏格兰艺术家走上购藏之路,从而兼有“收藏家”的身份。艺术家收藏群体的购藏往往与自身的艺术创作关联性密切,收藏视角的代入对研究艺术家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特定时期中国物品在海外被收藏、保存和迁移的情况往往极为复杂,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只与对应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物品的价值有关,还包括物品流入地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所涉具体人物的动因等,对这些因素的全面观察有待学界对域外包括苏格兰境内公私机构内的中国藏品进行个案化和更为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