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会带来“技术奇点”吗?
2024-04-25王永进
王永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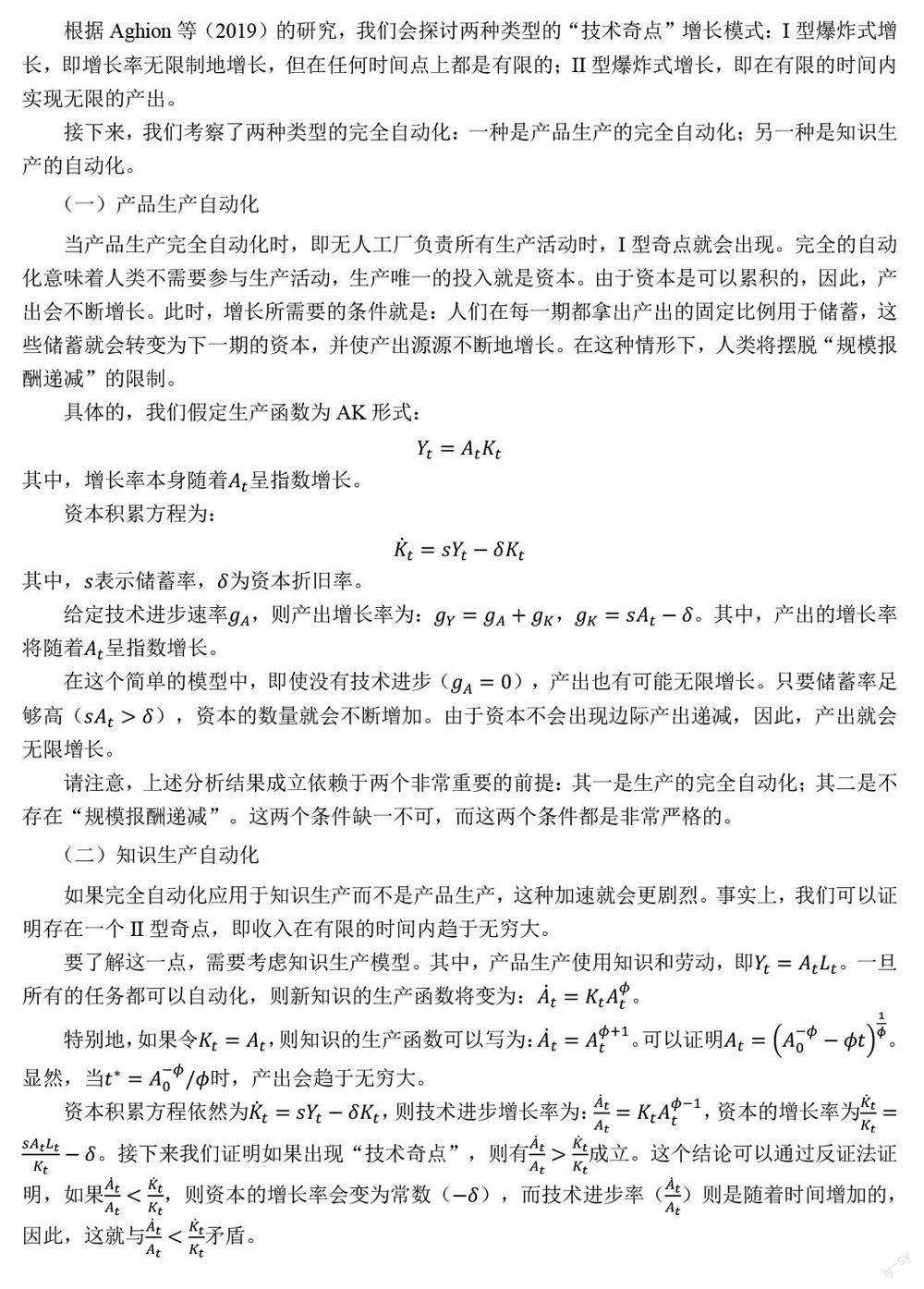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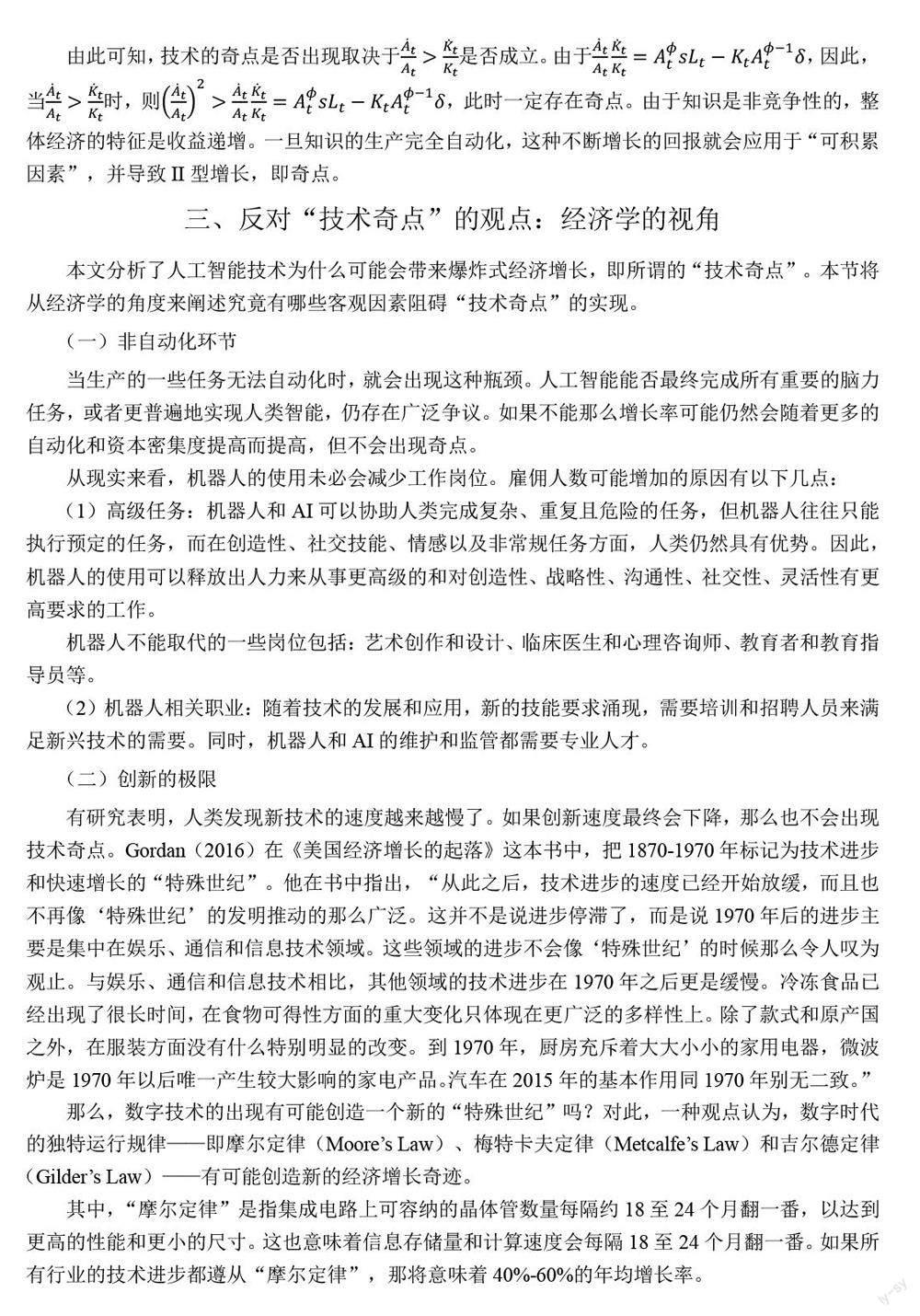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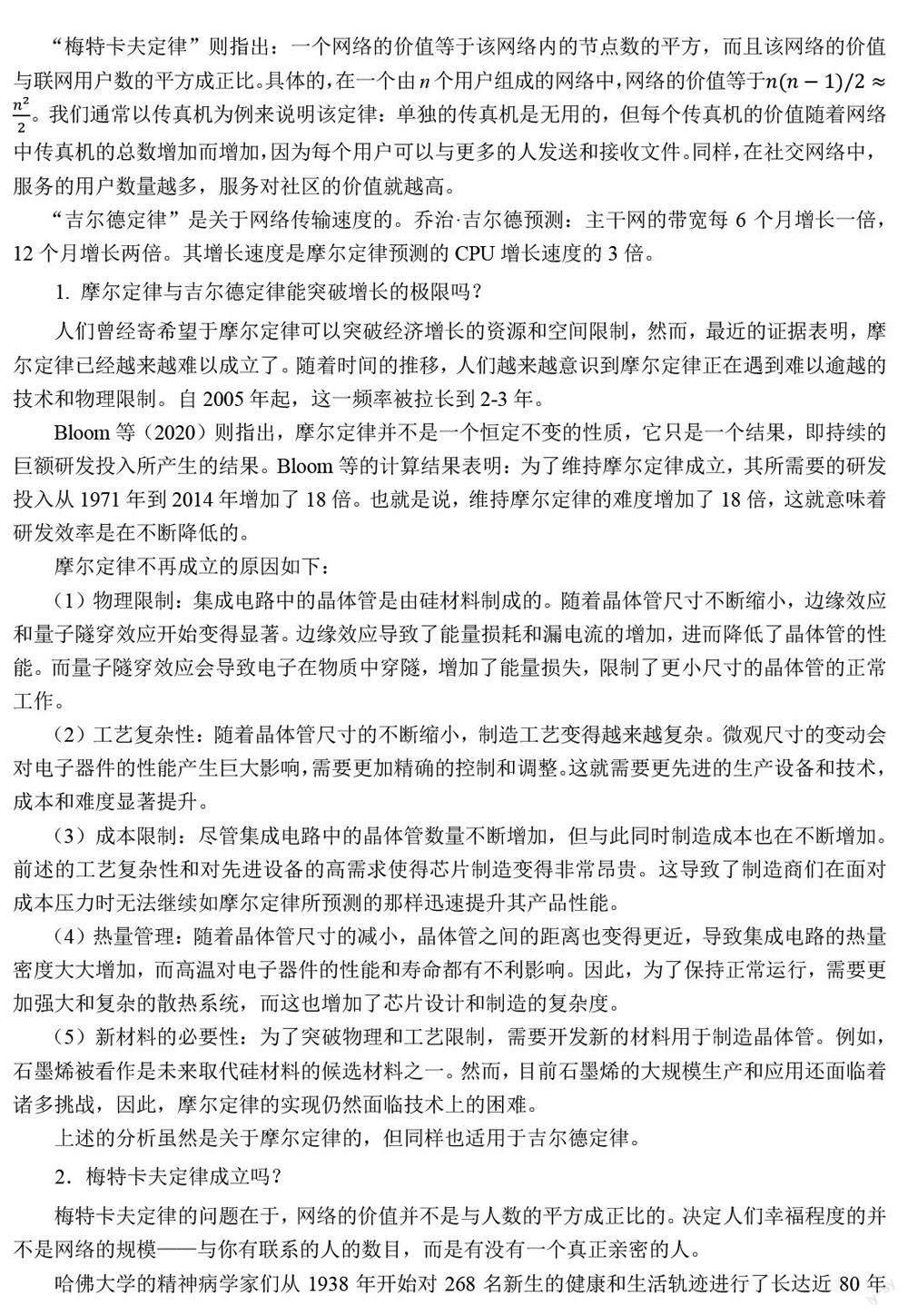
摘 要: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人类是否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数字技术是否可能带来“技术奇点”,从而创造一个不需要人类且产出无限增长的世界?本文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系统梳理关于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限制经济增长的物理因素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重新解读。本文认为:即便数字技术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革命,并且也可能创造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人类经济活动终究不能脱离有用物质有限、空间有限、物质不可无限分割以及地球承载能力有限的约束。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进一步割裂GDP 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为此,从“技术奇点”转向“可持续的福祉增长”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关键任务。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物理约束;技术奇点;可持续的福祉增长
DOI: 10.19313/cnkicn10-1223/f20240312.004
一、引 言
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奥秘。然而,从漫长的历史长河来看,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和连续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 年的《人口论》中指出: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产品产出的增长速度,这就注定了人类无法走出疾病、饥荒、贫困、战争和灾难的陷阱。历史研究表明,从罗马帝国衰落到中世纪这长达8 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经济都没有增长;在1300 年到1700 年的4 个世纪里,英国的人均产出仅增加了一倍。正因如此,经济学也被19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冠以“令人沮丧的学科”(The dismalscience)之名。
工业革命,特别是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并点燃了人类对于无限增长的遐想和渴望。然而,两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似乎并未持久。实际上,自1970 年之后,虽然信息、通讯领域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但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之后再度变得十分缓慢。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话来说,“你可以在各个方面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响,但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却看不到它的影子。”(Solow,1987)。Brynjolfsson等(2019)则指出:尽管计算机性能呈现出巨大的进步,IT 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整个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增长放缓,甚至在许多IT 投资较多的行业内也是如此。尽管美国的计算能力在20 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增加了100 倍,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从上世纪60 年代的3%左右降至上世纪80年代的1%左右(Spencer,2012)。无独有偶,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Dewan and Kraemer,1998)。这个发现被称为“索洛悖论”或“生产率悖论”。
那么,数字时代的到来能否打破“索洛悖论”,并突破经济增长的极限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虽然,数字技术使得语言翻译以及语音、文本和图像识别的精确度有了大幅提升,人工智能也已经在游戏以及体力劳动方面明显超过了人类,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未发现数字技术革命能够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效应。我们不妨把该现象称为“数字版索洛悖论”。概括起来,出现“生产率悖论”的原因如下(Brynjolfsson,1993;Brynjolfsson 等,2019):
其一是“错误的期望”(False hopes),即把数字技术与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相类比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原因。
其二是“度量错误”(Mismeasurement),即数字技术的生产率效应是被低估的。例如,由于线上内容是免费获得的,其虽然能够带来人们效用水平的增加,但并未被统计在GDP 范围内。该观点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数字内容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实物,数字内容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被广告定价了。
其三是“租金再分配”(Rent redistribution),即IT 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只是把社会剩余从消费者转移到企业、从小企业转移到大企业。研究发现,IT 技术并非全部用于生产,而是用于营销和获取消费者信息。明星企业在市场份额和市场势力方面与其他企业的差距是在不断增加的(DeLoecker et al.,2020)。确实,很多的数字技术并不能增加产出。例如,大数据分析技术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一天登上长白山能够看到天池,却不能够增加风景的供给。
其四是“贯彻时滞”(Implementation lags),即IT 为一种通用型技术,其从发明、实施到扩散需要很长(可能是几十年)的时间。Brynjolfsson 等(2019)认为第四种情况是最为可能的,即他们认为数字技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革命,然而,其要在全局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则需要等待一些互补性技术的出现。
其五是“投资扭曲”(Mismanagement),即由于IT 技术的收益是不确定的,企业的管理者可能会用IT 技术来偷懒。也就是说,IT 技术在企业层面的投资是扭曲的。
尽管对于数字技术能否带来显著的生产率增长依然存在很多的质疑声,但是当数字技术的进步累积到一定程度,生产率的爆炸式增长或许真的指日可待了。①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微观上的生产率增长未必能够转化为宏观的经济增长。为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是数字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率,而是落脚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终极目标上。
本文第二节从经济学的角度梳理了支持“技术奇点”的观点;第三节则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反对“技术奇点”的观点;第四节从物理限制的角度讨论了限制经济增长的物理因素。最后是总结。
二、数字技术与“技術奇点”:支持的观点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工智能开启了一扇大门,它将使经济增长率出现爆炸式增长,即所谓的“技术奇点”。“技术奇点”是一种不同于稳态增长的增长模式。所谓的稳态增长,是指长期增长率为常数的情况。一旦出现“技术奇点”,这意味着长期增长率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时间而增长的。约翰·冯·诺依曼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技术奇点即将到来的人。Good(1966)和Vinge(1993)则认为AI 有可能通过不断自我改进,最终超越人类的思维,实现在有限的时间内与无限智能相关的“智能爆炸”。
四、经济增长的物理限制:超越经济学
物质不会凭空产生,而只能相互转化。因此,经济增长不是创造物质,而是把“无用”物质转化为“有用”物质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用产出”不断增长或者说物质的“用处”不断放大的过程。所谓“有用”,是说人们愿意为这种产品付出代价去购买。
实现持续的增长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突破有用物质的资源限制;第二,突破堆放产品的空间限制;第三,突破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
(一)有用物质的资源限制
在原始社会,矿石虽然不能说完全无用,但用处比较有限。冶炼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把藏在矿石中的金属提炼出来,从而把矿石这种不太有用的物质转化为金属这种比较有用的物质。有了金属,人类就可以更有效地耕种、狩猎和编制衣服。特别是铁器的出现,更是极大提高了手工制作和耕种的效率。这不是说铁器就一定优于铜器,而是因为铁的矿藏分布比较广泛和丰富,因此,农具和武器才能大规模生产。
在春秋时期,青铜是一种非常稀缺和珍贵的材料,因此只有少数诸侯和贵族才能使用它来制作武器和饰品。例如,春秋时期的楚国是以青铜制品闻名的,他们的剑、戟、盾等武器大多由青铜制成。楚国君主、将领以及一些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青铜武器,而普通士兵则使用其他材料制作的武器。另外,贵族和达官显贵也常常选择青铜来制作饰品,以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他们可能佩戴青铜制作的项链、手镯、戒指等装饰品,这些物品不仅具有漂亮的外观,还象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然而,由于青铜产量有限,生产工艺复杂,并且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其制造成本也较高,因此,普通人往往无法拥有或使用青铜制品。青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稀缺性和珍贵性使其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铁犁是中国古代农具的重要发明之一,虽然其最早可能出现在商周晚期,但普及推广确是在战国时期。相比于以前的木制犁,铁犁能够更有效地翻耕土地,提高农田的耕作效率,从而增加粮食产量。这对于古代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便意识到农业生产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为了能够保证军粮供给,秦国特地制定了一部名为《田律》的法律,要求所有农户都必须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法。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而使得各个诸侯国组织起更多的军队用于打仗,而且也扩大了人们的空间活动范围,从而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铁器的应用不仅是在古代意义重大,在近代也是。如果没有铁器,近代工业革命也是无法想象的。19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铁路的建设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铁路的兴建使用了大量的铁材料,例如铁轨、桥梁和机车等。铁路的建设加速了产品的流通和交易,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出行速度和方便性。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时期,钢铁产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钢铁广泛应用于建筑、船舶、机械制造等领域,对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产业也是军事装备生产的关键,对战争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冶炼技术的角度来看,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并非是革命性的进步,但生产率之所以发生了巨大进步,主要是因为发现了成本低廉的“有用物质”,所谓成本低廉,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相对“不稀缺”。由此可见,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进步主要是突破了“有用物質”的资源限制。
无独有偶,如果爱迪生没有发现“钨丝”这种低廉的导电物质,那么电气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电灯出现之前,人类生产生活时间受到自然日光光照时间的限制。钨丝灯泡使得人类可以在夜晚拥有明亮而持久的光源,从而大大突破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生活的限制。
首先,电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电灯问世之前,人们的生活受到日出和日落的限制,夜晚光照不足、活动受限。电灯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随时享受到明亮的光线,可以在夜晚读书、工作、娱乐等。这种改变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没有电灯的时代,城市夜晚是一片黑暗,街道上远没有现代城市这样繁华热闹。随着电灯的普及,城市的夜间活动逐渐增加,夜市、夜景观赏等业态开始兴起。例如,中国的成都锦里古街,这条坐落在市区中的古街,晚上灯火辉煌,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成为当地夜间经济的重要一环。
其次,电灯对于工作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电灯出现之前,工人们只能依赖自然光源进行生产活动,工作时间受到昼夜变化的限制,生产效率不高。而有了电灯之后,工作场所的照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不再受到自然光的限制,可以随时保持充足的照明强度。这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也减少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例如,20 世纪30 年代末,福特公司发现,保持充分的照明可以直接影响到各种零部件的有效生产。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引入了更先进的照明系统,使得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更加容易看清零部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奈,2017)。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寻找有用物质的过程。因此,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取决于能否发现新的“可用物质”。由于新的“可用物质”的出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就使得在新的“可用物质”出现之前,经济会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因此,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常态。
(二)空间限制与物质“不可无限分割”
地球上的存储空间是有限制的,因此,产出的增加势必要求存储空间的不断扩大或者产品体积的不断缩小。按照物理学的观点,物质是不可无限分割的。除了理论依据外,实验结果也支持物质的不可无限分割。例如,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可以对物质进行高精度观测。通过TEM 观测样品,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具有特定形状和排列的几何结构,这些结构反映了物质的原子和分子层次的组织。这表明物质在极小的层次上是有一定结构和组织的,并不是无限分割的。
另外,物体并不是越小操作起来越方便。例如,如果手机小到一定程度,那体验感可能就大幅下降。当然,或许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并不需要使用手机,一块芯片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通话、休闲娱乐的所有功能,但是,这就对芯片的信息存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球的信息存储和计算量是否存在上限是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在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人类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信息存储与计算的能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得海量数据能够被高效地存储和处理。同时,云存储和分布式计算技术可以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计算资源,为信息存储和计算提供了更大的扩展能力。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绿色计算和低能耗计算成为了可行的解决途径。
然而,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无限的信息存储和计算量呢?
首先是物理存储介质的容量和速度。根据信息论的基本原理,信息的存储是需要有足够大的物理介质来容纳的。在经典物理学中,物质被认为是有限可划分的,即物质可以分割成有限数量的离散单位。例如,在计算机领域,信息以位(bit)为最小单位进行存储。每一个位可以表示0 或1,即两个可能的状态。因此,一个位信息可以表示2 的次方个不同状态,即具有2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使用所有物质来存储信息,仍然难以达到无限的存储量。目前最常用的存储介质是硬盘和固态硬盘(SSD),其容量和读写速度都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然而,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硬盘容量可能会面临瓶颈。同时,存储介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硬盘或SSD 的故障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给信息存储带来风险。
其次是计算能力的限制。虽然计算机的性能正在以指数级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物理和工程方面的限制。例如,处理器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受到热量和功耗的限制。此外,复杂的计算任务可能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信息存储和计算是需要大量能源支持的。根据热力学的基本原理,能量是有限的,无法无穷地供给信息处理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能耗成为了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如何在提供足够计算能力的同时降低能耗,成为了技术和工程的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地球的信息存储和计算量存在着一定的上限。尽管科技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存储和计算的能力,但我们仍然面临着物理介质容量、能耗和计算能力等方面的限制。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可能会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来突破当前的限制,但是否能够实现无限的信息存储和计算量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寻找更高效的存储和计算方式,以满足人类对信息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三)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经济活动一直伴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从1970 年到2000 年,生活在森林中的物种数量减少了15%,淡水鱼类减少了54%,而海洋生物减少了35%。导致地球承载力超支的原因有二:一是能源足迹,即大量消耗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二是非能源足迹,主要表现为人类使用土地面积的增加。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地球承载能力都濒临警戒线。
人们在努力追求GDP 增长的过程中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活动增加对地球的破坏一旦接近临界点,似乎微小的变化都会激发巨大的反应,从而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21 世纪后半叶很可能遭遇这样的危机:当全球变暖开始消融永久冻土时,冻土层中封存的大量甲烷气体会被释放出来。甲烷是非常强大的温室气体,一旦释放,就会加剧全球变暖。而全球变暖反过来又会加速冻土层融化,直到冻土全部融化、所有甲烷气体被释放殆尽为止。”(Randers,2012)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或许很难感受到2 摄氏度的差别,然而,对于地球而言,如果全球变暖幅度超过2 摄氏度的临界点,那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态环境。最明显的影响包括北极圈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30 厘米、极端天气频发、淡水缺乏等。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要想将全球升温控制在既定的1.5°C 范围内,全球必须在2030 年前将碳排放量迅速降至250 亿吨二氧化碳的量。国际能源署2023 年数据表明,2022 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68 亿吨以上。①因此,“我们正处在悬崖边缘,很可能错失实现1.5°C 温控目标的机会。”②
此外,当超过一定的生存标准化,GDP 和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消失了。一旦人们吃饱、穿暖、安全有保障、生活舒适,大多数人就会渴求更多的“抽象享受”(Abstract satisfaction)。物质消费和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可能会使一些人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但微弱的收益很容易被其负面影响盖过。因此,总有一天,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需要由“化石燃料推动的经济增长”(Fossilfueledeconomic growth)轉向“可持续的福祉增长”(Sustainable well-being growth)。
五、结束语
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能够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来源吗?本文透过心理学、经济学和物理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思索。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不会凭空产生,而只能相互转化。既然如此,经济增长不是创造物质,而是把“无用”物质转化为“有用”物质的过程。而可用资源的数量不仅取决于人类的吸收能力,也取决于地球的承载能力。二者共同决定了可用物质的有限性。这就决定了GDP 增长是有极限的。
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可以发现,技术革命的进程常常是不平衡的。换句话说,总是有一些部门的增长比其他部门滞后。同时,由于劳动力和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技术进步的过程往往会伴随着劳动力从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的转移。这是技术革命不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地球上还存在未曾开发的土地和市场时,先进的工业国可以通过全球化来突破本地资源和市场的限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市场被开发,新的技术革命能够带来全局性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正在从“正和博弈”转向“零和博弈”。此时,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很可能超越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从而引起人类的灾难。
与此同时,伴随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贫困线,GDP规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弱。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人类的幸福感同比例增长,相反,很多人虽然已经摆脱了物质上的限制,但是却依然感到不幸福。如果幸福感没有提高,那追求GDP 增长的意义是什么呢?退一步来讲,即便我们依然希望追求GDP 增长,但是,当GDP 增长不能带来居民幸福感提高时,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最终会葬送掉经济增长。
從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虽然工业革命最终确实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其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经历动荡(如两次世界大战)。因此,从追求单一的GDP 增长转向“可持续的福祉增长”已经变成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创造新的娱乐方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提供让人类幸福的钥匙。
参考文献
[1] 大卫 E. 奈(David E. Nye). 百年流水线:一部工业技术进步史[J].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2] 马特耶·阿本霍斯和戈登·莫雷尔. 万国争先:第一次全球工业化[J].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3] Aghion P., Benjamin F. Jones, and Charles I. Jones,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grawal,Gans, and Goldfarb,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4] Baldwin, R.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 57(3): 415-426.
[6] Brynjolfsson E., D. Rock and C. Syver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 Clash of Expectations and Statistics," NBER Chapters, in: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 2019, pages 23-5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7] Brynjolfsson, E.,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6 ,1993 (12):66–77.
[8] De Loecker J., J. Eeckhout, G. Unger,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2),561–644.
[9] Dewan, S. and Kenneth L.Kraemer,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98 41 (8): 56–62.
[10]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1974.
[11] Good I. J.,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1966, 6(6): 31-88.
[12] Gordon, Robert J.,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REVRevis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 Jones, Spencer S., Paul S. Heaton, Robert S. Rudin, and Eric C. Schneider, M.D., "Unraveling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Lessons for Health Ca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2,366 (24): 2243–2245.
[14] Maslow, Abraham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 (4): 370–396.
[15] Randers J. 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2012.
[16] Solow R. "We'd better watch ou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12, page 36, 1987.
[17] Vinge V.,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 Science Fiction Criticism:An Anthology of Essential Writings,: 352-363,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