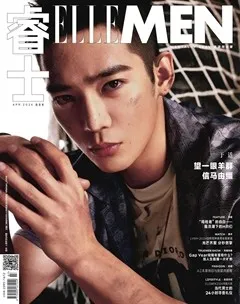韩博:达达:从镜子胡同一号到十四号
2024-04-25韩博
韩博

苏黎世镜子胡同(Spiegelgasse)十四号,列宁故居外墙的铭牌已被粘上一张乌克兰国旗图案的胶纸。
而在一九一六年二月五日,也就是革命导师莅临苏黎世半个月前,德国诗人及理论家雨果·巴尔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宁斯,在数十米开外的镜子胡同一号,开出一家与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同名的酒馆(Cabaret Voltaire)。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轮番上演街头歌谣、“黑人舞蹈”、诗歌朗诵等各式各样体现“现代情感”之娱乐节目,观演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观者经常对演者报之以嘲弄,演者则以噪音相对抗。后者声称,他们部分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心灵动荡,释放出连其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的力量。
出没于斯的诗人、艺术家以及乔装打扮的革命者——列宁声称他从未去过伏尔泰酒馆,散步只朝另一个方向走,不过,当班经理却认为自己曾在一顶假发之下辨认出了导师的脸——其绝大多数,并非瑞士国民,而是被炮弹驱逐至此。德法双籍的诗人、艺术家汉斯/让·阿尔普因而声言:“出于对一九一四年世界战争无谓杀戮的厌恶,我们在苏黎世献身于艺术。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时,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我们在寻求一种基于基本原则的艺术来治疗时代的疯狂,寻找一种可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恢复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
酒馆开业两个月之后,“达达”这一自我命名诞生了。当时,诗人和艺术家们决定出版一份刊物。依据雨果·巴尔的日记叙述,乃是他本人提出了“达达”的概念,创造出这一凸显国际流动性的文化世界语:“达达”在罗马尼亚语中意谓“是的,是的”,在法语中则为“木马”和“竹马”,对德国人来说,它又指向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乐以及对婴儿车的全神贯注的痴迷……不过,德国达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却声称,是他和巴尔一起快速翻阅词典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词,“达达”强调的是破裂与新生的观念:这是孩童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表达了一种原始感,它从零开始,是艺术的新生。
除此之外,关于“达达”的命名,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阐释。2016年,“达达主义”问世百年之际,我重访苏黎世,亲耳听到若干其他说法,比如强调艺术家彼此呼应的“跷跷板说”,以及源自同名品牌的“肥皂广告说”,等等。整饬一新的伏尔泰酒馆,其内部被辟作纪念品商店的部分,则悬挂出“达达”品牌的大幅沐浴用品广告,只不过,那不是一九一六年的原版,而是一九六六年的戏谑版,它套用《哈姆莱特》的著名独白,喊出两行口号:达达还是不达达,这是个问题。
一九一六年来到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者们,就像希腊悲剧诗人笔下的酒神征服忒拜—— 埃斯库罗斯在《报仇神》开场白中,借女祭司之口曰,“我也没有忘记,布洛弥俄斯身为天神,带着他的女信徒们前来,像杀兔子一样把彭透斯弄死了,他从此占据着这个地方”。达达主义者试图以狄俄尼索斯式启蒙精神——自由、平等、快乐—— 使人摆脱毕达哥拉斯式“有序宇宙”(Cosmo)的约束,重回赫西俄德式“混沌”(Chaos)的怀抱。他们做到了吗?的确。达达主义开启的非理性主义表达,迄今仍属当代艺术主流语言之一。2023年10月,当我终于在“疫情”之后回到伏尔泰酒馆,发现其内部再度被改建,地下展厅却有一个纸糊的展览——艺术家伪造了几根或立或倒的“大理石柱”——倒是不折不扣延续了早年的达达主义者青睐廉价纸张或是随处可见的现成品之观念,墙上还有打印在纸上可以被带走的小诗。小小一个展览,知识生产能力似乎远超大型双年展—— 倘使后者尽被权力或资本所操纵且阉割。
不过,对于伏尔泰酒馆,我印象最深的场景,依然是2016年3月8日清晨六点半,我冒雪来到刚刚亮起灯光的这里,等待一场并未准时开始的达达主义朗诵。差不多六点三刻的时候,身着正装的经理艾德里安·诺兹扫视了一下观众,然后转问我:“英文朗诵,怎么样?”当然好。于是,他打开一本书,面向观众介绍今天的诗歌作者,达达主义艺术家奥托·格里贝尔的生平,而后,转过身去,背对著观众朗诵。1916年6月23日,雨果·巴尔在这里朗诵语音诗歌的一张“经典照片”悬在他身前的墙壁上,仿佛一具圣像。雨果的语音诗歌朗诵饱含无意义的噪音—— 他将诗歌拆碎,将基本词汇与生造词汇混杂于一处,成为含混不清的咒语,因为其强调:“在语音诗歌里,我们完全抛弃了已被新闻界滥用的语言……我们必须恢复字词最幽深之处的魔力。”正是在这种魔力之中,我没能听懂一个字。朗诵结束,没有人发出早期达达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嘲笑,唯有一连串礼貌的掌声。艾德里安·诺兹投桃报李,提出请大家喝杯咖啡。但当他钻入吧台,奋力捣鼓了一阵之后,又严肃地走回正厅宣布:咖啡机坏了,没有咖啡了。
雨果发明噪音的时候,镜子胡同十四号的那位作者正在奋笔疾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用不了多久,他的画像就将挂遍一个横跨十一个时区的“新世界”。而无论是他,还是雨果,抑或那个清晨的艾德里安,都让我想起同一句话——《克里托篇》中的苏格拉底说:“我们为什么要顾忌‘大多数人的想法呢?”

伏尔泰酒馆的地下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