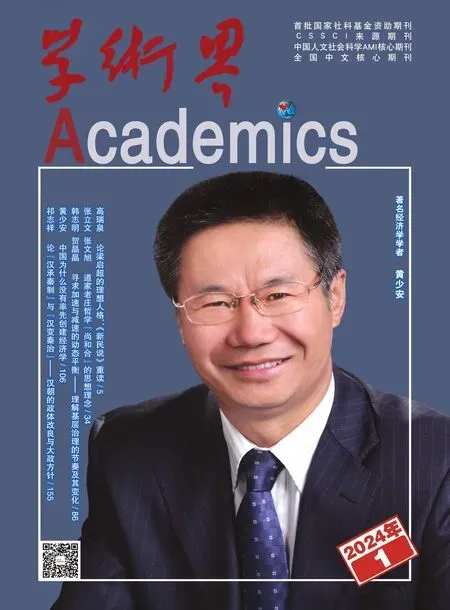道德底气:儒家德性精神论〔*〕
2024-04-13张方玉
张方玉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范畴、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和道德精神,儒家伦理思想是人类伦理文明的璀璨明珠。现代儒家德性论则是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它以推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根本方向,参照会通西方德性伦理学、德性论,尝试建构一种现代性的儒家德性论,进而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性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此意义上,对儒家德性精神的深入考察,既不是粗糙地模仿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一种“对着讲”,也不是肤浅地套用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一种“照着讲”,亦非简单地承接传统“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一种“接着讲”,而是致力于讲出儒家德性的“真精神”和“现代精神”。
一、浩然之气——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
“德性精神”作为伦理学界一个重要的概念,与“道德精神”和“伦理精神”是相互关联又各具丰富内涵的。以“精神”而言,三者均是对其中所谓核心、实质和深层元素的关注,是整体内容的凝练和升华,是指那些可以称之为精华的、灵魂的东西。德性论以品德、行为者——人本身为中心,更加重视“何以成人”,它以相对体系化的德性条目为基础,更加关注个体德性的完善,在一定条件下由个体之善推及社会之善。采用孟子的说法,就是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相比之下,规范伦理学以规则、行为——“应当如何做”为中心,通常依靠外在的他律来实现行为的善。不难发现,德性伦理具有更强的人文精神价值,而规范伦理则更加偏重社会秩序意义。
德性是人的一种品质或品格,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一般是指人的品质的道德特性、形态,常常特指那些优秀的道德品质,比如古希腊的“四德”,再如儒家的仁、智、勇、诚、信等道德条目,又或者现代的自尊、乐观、慷慨、敬业、友善,等等。“相对于个体所处情景的变动性及行为的多样性,德性具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品格,它并不因特定情景的每一变迁而变迁,而是在个体存在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绵延统一。”〔1〕可以说,就伦理学科的类型而言,无论是规范伦理学还是美德伦理学,无论是道义论伦理学还是功利主义伦理学,德性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当然,在美德伦理学或者德性论的体系中,德性的意义与价值更为凸显。“儒家伦理学的美德思想就是突出以心德为主要特色的美德伦理。一个人是好人或者恶人,主要是就其内心、心灵而言的。儒家在看重行动的同时,更看重行动者的心德。”〔2〕突出心德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色,这无疑是一种内在的德性,对内心、心灵的重视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德性精神。如果说康德所谓“内心的道德律”是其道德精神的鲜明表达,那么儒家德性精神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典式呈现?
社会生活的语境中,人们在论及“精神”二字时,常常有“精气神”的表达,于是,在考察德性精神时,径直将儒家德性精神与“气”相关联,实在是一种天然的内在理路。可以发现,这种内在的关联在传统语境中存在已久,当目光投向现代语境,这种内在的关联仿佛是“一以贯之”,越发受到重视。比如,在现代社会谈论改革创新的精神时,可以将这种精神形容为“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是一种“气”,是一种“劲”。唯有凭着这样的“气”和“劲”,才能开拓新的道路、新的事业。又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的奋斗起点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因此而更加自信、自尊、自强,奋发有为的中国青年因此而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在这里,所谓“志气”“骨气”“底气”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回到中国古代哲学的视域中,作为哲学范畴的“气”,既是指物质之气、自然之气,“气”意味着世界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同时,“气”又是指精神状态之气、道德境界之气,比如所谓“圣贤气象”。宋明理学家对此种气象津津乐道,程颢、程颐描述孔子具有“元气”——“天地之气”,颜回呈现“春气”——“和风庆云之气象”,孟子具有“秋气”——“泰山岩岩之气象”。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是相当丰富深刻的,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气涵五理”,〔3〕就是说“气”这一概念涵盖了哲理、物理、生理、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可以视为儒家德性精神的经典表达。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必须指出,作为儒家德性精神的“浩然之气”并非孟子一人的“专利”,而是儒家德性文明的思想、情感、智慧的结晶。不难发现,孔子那里已经有“血气方刚”表述,荀子有所谓“治气养心之术”,朱熹更是对于“浩然之气”作出深入的诠释,比如:神秘之气、刚大之气、先天之气、创生之气,等等。南宋著名词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有大义凛然之《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在这里,天地正气、自然之气、物质之气、浩然之气可谓浑然一体,“气”既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又是主体的道德修养、道德境界和道德精神。搁置“气”范畴实体存在的意义,聚焦“浩然之气”在德性精神层面的意义,可以这样概括:“浩然之气”是儒家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又分别在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等方面具体展开。
二、志气——德性精神的目标之维
“志”与“气”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内涵的两个概念。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尤其是在德性论的视域中。关于志、气相连的表述,孟子有相当体系化的经典名句:“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在孟子看来,既然“志”为“气”之“帅”,那么志、气的地位排序立刻明晰,这就是“志至焉”“气次焉”;既然志、气具有这样的逻辑关联,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持其志,无暴其气”。为此,孟子还作了补充说明:“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应当说,《孟子·公孙丑上》的这段话已经为后世“志气”一词建立起比较充分的思想根基。志气就是由“志”主导之“气”,与孟子“气之帅”完全同理。“志”通常就是指远大的理想、目标、志向,更通俗地说,就是未来的、大的打算;“气”就是指人的精神,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具有某种指向或目标的德性精神。按照孟子的义理,“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志”发挥着主帅作用,“气”对于心、志又具有反作用。可以看到,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紧接着这“志气论”,孟子就阐述了至大至刚、塞于天地、配义于道的浩然之气。以其内在的线索而言,志气可谓浩然之气在目标维度上的呈现。在《孟子·尽心上》篇中,德性精神的“目标之维”表现得更加直接: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论语·泰伯》中有曾子的名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在孟子看来,士的根本职事就是——“尚志”。不难发现,曾子所谓“弘毅”“任重道远”与孟子所谓“尚志”之间,似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以今天的眼光视之,可谓“士之志气”。在这里,孟子还进一步阐述了“尚志”的核心要义,就是“居仁由义”,这与曾子所谓“仁以为己任”,也是意思相通的。需要明确的是,就志气的主体承担者而言,作为德性精神的志气并非“士”所独有;就志气的核心内容而言,“居仁由义”也不是志气的所有指向。作为德性精神在目标指向上的呈现,儒家的志气大体又可以划分出底线目标、中等目标、终极目标的层次结构。
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中,有一种道德结构的设想:社会制度提出的基本规范和个人义务体系形成规范伦理学,是为“底线伦理”;社会公民在“基本价值”上的一致,同置身其中的社会秩序,达成所谓的“共同信念”;而“对于伦理的最终论证”,即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系,乃至宗教信仰,则构成所谓的“终极关怀”。〔4〕这样的结构设想与儒家志气的层次结构非常相似。“底线伦理”是对所有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而底线之维的志气大约就是修身、做人——“人禽之辨”;“共同信念”涉及民主商谈、公共生活,而中等之维的志气大体能涵盖修、齐、治、平的内容;“终极关怀”关乎个体的“安身立命”和对现实的超越,而终极之维的志气,一言以蔽之,就是“志于道”。
以志气的底线之维而言,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是志气极为精炼的表述。匹夫泛指平民百姓,常常带有轻蔑的意味,然而孔子讲“匹夫不可夺志”。正因为对于“匹夫之志”的肯定,志气的底线维度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做人的底气。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匹夫之志”表明儒家思想肯定平民具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展现出人的尊严。〔5〕关于志气的底线维度,孟子还有更加巧妙的表达——“懦夫有立志”(《孟子·尽心下》)。懦夫是软弱无能的人,无疑是个贬义词,然而孟子讲“懦夫有立志”,与孔子“匹夫不可夺志”的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志气的底线提供的是做人的底气,而这样的底气提供了随时提升的可能,或者说这样的底气随时可以上升为更高的层次。“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6〕从懦夫、匹夫之志,到“大做一个人”,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升级。很显然,“大做一个人”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已经相差不远。
以志气的中等之维而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思想可谓响彻千年。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里的每一个语词,仿佛都是儒家成人之道设置的一个个里程碑、标志牌,鲜明地展现了儒家志气的中等目标。志气的中等目标还可以表述为“志于学”“志于仁”“志于义”,或者“内圣外王”等人们熟悉的语词。《论语·公冶长》中有“各言尔志”的经典表述: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路、颜回均为孔门弟子,孔子与二人各自表达志向所在,于是就出现三种志向目标。显然,夫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更为经典,是为儒家志向的典型与榜样,可视为志气的中等之维的具体呈现。在宽泛的意义上,这里的子路和颜回之志,当然也可以视为志气的中等之维。
以志气的终极之维而言,“志于道”可能是最佳的表达。如果说“匹夫之志”“懦夫之志”尚处于志气目标的底线之维,“志于学”“修己安人”尚处于志气目标的中等之维,那么“志于道”就已经触及所谓“性与天道”的终极层面。子夏讲“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的追求构成儒家志气的终极所在。宋明理学推崇“孔颜之乐”,寻孔颜乐处,这种“乐”就常被理解为“乐道”,从而展现出“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乐境”。“志于道”和“乐道”的情形在“曾点之志”中也有呈现,《论语·先进》篇中有著名的四子侍坐、各言其志的故事。子路、冉有、公西华各自表达国家治理、宗庙之事的打算,而曾皙的回答则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此,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从而树立起一种儒者生活中具有终极关怀性的追求。此种“志于道”“乐道”的终极关怀,在孟子那里就是——“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在荀子那里就是——“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荀子·性恶》);在《大学》里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中庸》里就是——“至诚无息……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疆”。
三、义气——德性精神的价值之维
百姓日常话语中常有“讲义气”的说法,有时人们也用“哥们义气”“江湖义气”,这其中既有仁义精神的意思,又多有侠义精神的意味。而作为一种深刻的儒家德性精神,义气的内涵主要定位在道义之气、仁义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对于浩然之气的阐述中,“气”与“义”、“气”与“道”的关联是内在的:“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以说,所谓浩然之气,义与道乃是标准配置。在这个意义上,浩然之气就是义气、道义之气,宽泛地说,因为儒家仁义并联,所以又可以称为仁义之气。
义利之辨是儒家价值观的主题,义气、道义之气所侧重呈现的便是德性精神的价值维度。应当说,儒家重义轻利的主张可谓童叟皆知,人们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于“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对于孟子“鱼与熊掌”的比喻可谓了然于心。然而,儒家的义利之辨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稍作深究,人们便可以看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还可以看到“义者,宜也”(《中庸》),甚至人们还会搬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等等。
就“义”范畴而言,伦理道德的意义当然是基本的,这就是“义德”,由此展开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而后取”“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等道德规范、原则,进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君子的价值追求。延伸到政治领域,“义”的政治伦理色彩凸显,这就是“义政”:例如“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又如“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再如“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这种侧重伦理秩序的“义”,《礼记·礼运》明确地表述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在义、利关系而言,“义”范畴实际上既有道义的意思,也包含着功利的意思。义与利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乃是公利,公利即义;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所排斥的显然不是“富且贵”,“合义之利”可以视为义的外在功利价值。显然,儒家之义的根本乃是内在的精神价值,这是对外在的功利价值的超越。
可以发现,儒家的义利观远远超出义利关系本身,乃是儒学体系中的一个复杂的、深层的核心问题,在这样意义上,“义利之说”可以视为“儒者第一义”。义利之辨蕴含的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学者已多有探讨,有的侧重个体价值选择的层面,强调个体对于道德义务、伦理规则的自觉遵循,要求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有的侧重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价值取向的层面,强调个体主动让渡部分私利成就公义,要求做到义重于利、义先于利;更加深入的,侧重人生理想、人生意义的价值追求的层面,强调道义是人的超越性追求,是人安身立命之本,要求做到“义以为上”“义以为质”。沿着这样的思路前行,考察儒家德性精神的价值维度,义气可以具体展开为人生价值、行为价值和情感价值。
义气的人生价值之维,可以表述为尚义、思义。这一问题,学界在儒家义利观的道德理想主义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价值选择上,观点又有所差异。有学者认为:“先秦儒家是从人禽之分的角度来讨论这种义利关系的”,“人禽之分意义的义利之辨本质上属于价值选择关系”,“牢牢把握人禽之分意义的价值选择关系,是准确理解儒家相关思想的关键”。〔7〕此种观点确认在一般情况下义利不矛盾,既崇尚义,也肯定利;在特殊情况下,义利发生矛盾,这时便要求选择价值更高的义。这种观点貌似合理,但实际上混淆了“人禽之分”与“君子小人之分”。在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理想追求的维度,儒家着眼的并非人与动物之差别,而是君子、小人之别,这是一个价值体系中高层次追求与低层次追求的价值排序问题。倘若在动物性与人性的层面来探讨义利之辨,大约是未能抓住儒家义利观的真谛。以“义”的主体而言,《论语》中出现的“义”常常与“君子”相连,比如“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又如“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再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等等。这表明,义气乃是君子人格、理想人格的德性精神。在孟子、荀子那里,这种“义”的价值选择更为鲜明地体现为“天爵”“人爵”以及“义荣”“势荣”。孟子讲:“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依儒家义利之辨的价值排序,理想主义的价值选择便是“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荀子讲:“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便是“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便是“势荣”(《荀子·正论》)。荀子作出明确的判断:小人可以获得“势荣”,而不可能拥有“义荣”。
义气的行为价值之维,可以表述为重义、行义。人生价值层面的义利选择,关涉人生理想、人生意义的根本性,而行为价值层面的义气,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场景中具体的行为选择。比如,对于隐士与做官的态度,《论语》记录子路之语:“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在此意义上,儒家的出仕乃是行义之事。《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所谓“正路”“人路”,从字面而言就是道路、路径,其实也就是人的行为方式、行为选择,这里的“义”所标明的也就是正确的行为价值。可以看到,孟子对于义利之辨的行为价值探讨是极为深刻和彻底的。比如,一般主张“言必信、行必果”,然而孟子则更加深刻地主张:“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如,在面对“二选一”的选择时,孟子形象地比喻成“舍鱼而取熊掌”;面对生死抉择时,孟子坚决彻底地主张“舍生而取义”。在荀子那里,“义”的行为价值表述清晰:“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在一定意义上说,荀子是义利之辨的调和主义者,荀子常常将“礼”“义”并提,并由此呈现出礼义的功利性价值,比如:“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关于义气的行为价值之维,《中庸》还有一个经典的表达:“义者,宜也。”冯友兰先生对此有精到的解读:“儒家所谓义,有时亦指在某种情形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就功利方面说,在某种情形下,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就道德方面说,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道德成就。”〔8〕
义气的情感价值之维,可以表述为悦义、乐义。相对而言,儒学研究对于义利之辨的人生价值维度的考察最多,对于行为价值维度的探讨就略少一些,而对于情感价值维度的关注则要更少一些。实际上,儒家哲学乃是真、善、美的综合统一体,就以儒家伦理来说,道德知识、道德规范、道德价值都是与情感问题密不可分的。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学说不可忽视的关键性特质,这样的伦理精神具有深刻的感性特征。可以看到,儒家的义利之辨是与人的好恶之情、愉悦之心、乐的体验、羞耻之感紧密关联的。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里清楚地呈现出一种道义之乐,以及“于我如浮云”的心理情感。孔子又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个体价值选择的喜好之情跃然纸上。孟子讲:“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理义之悦”与“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相类比,这种感性特质就很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共情。“理义之悦”“尊德乐义”是正面而言的,情感的反面刺激则是羞耻之心,孟子直接将“羞恶之心”视为“义之端”。《孟子·离娄下》中记载一个齐国人墓地乞食炫耀于妻妾的故事,并提出“富贵利达”与“妻妾不羞”的思考,也正是情感价值维度的深刻呈现。“有情才有义,谓之‘情义’,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内在根据,也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为了活着而牺牲生命的价值,就是‘无义’之人,人而‘无义’,是一种最大的耻辱。”〔9〕
四、和气——德性精神的关系之维
和气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惯用语,家和万事兴、心平气和、和和气气、和气生财的说法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将“和平主义”“老成温厚”“遇事忍耐”视为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也可以视为和气的一种鲜明呈现。在当代儒家思想、文化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和”的研究——中和、太和、和合、和谐乃是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已然获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提出:“贵和谐、尚中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崇尚和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范畴,“普遍和谐”的理念可以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等等。不难发现,这些成果在“和”的含义与内容、本质与价值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新观念。例如,张立文先生提出“融突和合论”,认为“和合融突”是人对于生存、意义和可能世界的反思与创造,它“纵贯”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全过程,它“横摄”不同时代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进而提出:“无论是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还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抑或是自然生态、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情感,都连通着和合,构成一个和合网。”〔10〕
就“和”所关联的概念和范畴而言,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是十分集中的,主要围绕中和、太和、和合、和谐等概念展开,而其他概念就涉及较少,例如“和气”。而“和气”之说,恰是儒家德性精神的一个主要方面,宋明儒学所津津乐道的“圣贤气象”就对“自然之和气”推崇备至: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11〕
这里,孔子所呈现的如同天地之元气,孟子所呈现的如同秋天肃杀之气,而颜回所呈现的则如同春风化雨之生气,极为自然,不言而自化,又似“和风庆云”之气象。由此可见,“和气”所体现的德性精神无疑是儒家道德的重要内容,它和孔子所代表的高明博厚、无所不包之精神,和孟子所代表的刚强挺拔、泰山壁立之精神共同构成敦厚丰满的“圣贤气象”。
就“和”所涵盖的内容和关系而言,学界业已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就是所谓“普遍和谐”的观念。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的“太和”观念就是“普遍和谐”的观念,涵盖了四个方面: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与此相近或相似的表述还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的普遍和谐,这是非常近似的四个层面;身心平衡、人际和谐、天人和谐,这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略去了自然界本身的和谐;和谐家庭、政和国治、协和万邦,这是从儒家“家—国—天下”的理想所概括的三个部分。此外,也有将“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分开而言的,也有强调儒家“政治和谐”的理想、凸显整体主义观念的表述。总体来看,“普遍和谐”观念的四个方面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成中英先生的儒家和谐论:和谐概念划分为太和、义和、中和、人和、协和、共和等六个层次,分别用Primordial Harmony,Harmony by Righteousness, Harmony by Centrality, Harmony in Human Relations, Harmony among States and Nations, Universal Harmony来表达;“和”既被视为一种状态,也被视为一个过程,是一种创造生命、创造新事物的积极力量。〔12〕
从以上内容来看,儒家的“和”具有多维度性、多层次性、多关系性,“和气”所包涵的关系维度仍然可能获得创造性的开展。依据《大学》中“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侧重于儒家德性精神的考察,“和气”所涵盖的多种关系就可以划分为身外关系、身内关系。身外关系涉及天人之和、人伦之和、邦国之和等方面;身内关系则涉及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进一步而言,人身内外关系之和气,并非完全自然、自发地形成,儒家的和气意味着一种“生生”之德性精神,礼乐之和在人身内外关系的调谐中发挥着枢纽之作用。
身外关系之“和气”,具体在天人之和、人伦之和、邦国之和等方面展开。
第一,天人之和可以称为“太和”,蕴含本体论、宇宙论的意义,既涵盖“自然和谐”的内容,也涵盖“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和谐的思想并非儒家之专利,而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例如,《老子》第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下面对涉及天人之和的经典论述作些简要列举: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乾·彖》)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文言》)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普遍和谐的根源在于“天人合一”。在此意义上,人是自然和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思想正是天人之和的深刻呈现。
第二,人伦之和是儒家伦理的主体部分,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亲疏厚薄,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之辨。《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五伦”的经典论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大约是儒家伦理中最为常见的人伦关系,给人以温情脉脉的印象。必须指出,儒家的人伦关系并非是所谓的“一团和气”,而是具有深刻的辩证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强调人和的意义,与此同时,儒家的和气明确反对所谓“好好先生”:“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那些看起来没有过错、貌似老实廉洁的乡愿式好人,实际上是在搞坏道德、混淆是非,其行为并不符合真正的圣人之道。对此,儒家真正推崇的是“君子和而不同”,以及“君子和而不流”。
第三,邦国之和是指国家、天下的和平,“协和万邦”“天下为公”是儒家向往的社会理想状态。许多学者发现,儒家和谐的目标最终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普遍和谐所要追求的是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建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九族”“百姓”“万邦”乃是一种连续的整体。儒家心系天下,和平、大同的理念根深蒂固。《周易·乾·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咸·彖》又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宋代大儒张载有名句曰“为万世开太平”。“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和平”“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句是儒家和谐大义的精彩呈现。
身内关系之“和气”,具体在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展开。
第一,情感之和大约是人们最为熟悉的身心和谐。儒家伦理极为注重人的情感,所谓良心、良知都具有深刻的情感意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可以清楚地看到,喜怒哀乐之情虽然是人的心理情感,但儒家明显提升了情感的意义与价值。所谓“大本”“达道”已经明确将身心关系置于本体论、宇宙论的视域中,当人之常情达成中和之状态,实际上就意味着所谓的普遍和谐。李泽厚先生认为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关键点,指出儒家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从而实现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平衡。蒙培元先生著有《情感与理性》,对儒家情感哲学、情感理性深刻论述,提出儒家哲学是情感型的哲学。陶渊明有诗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不难发现,陶诗所阐发的是“不喜亦不惧”的意境,《中庸》所致力的是“发而皆中节”“致中和”的境界,两者显然是有所差异的。
第二,气质之和是儒家身心和谐的重要内容,学界许多研究往往因为高度重视天人和谐而容易将其忽略或遗漏。实际上,孔子已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可以视为儒家气质之和的一个经典表达。沿着这样的思路,荀子的表述更加详细: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之昭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修身》)
这段话中,可以看到“血气刚强”“知虑渐深”“勇胆猛戾”“狭隘褊小”等一系列不同的典型气质,荀子相应地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调和策略,并称之为“治气养心之术”。
第三,口味之和也是儒家身内关系和谐的组成内容,这也是儒家和谐思想中容易忽略的部分。《诗经》载有“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小雅·宾之初筵》),这里可以看到美酒的醇和口味,还可以发现饮酒在筵席中的谐和作用。《诗经》还载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商颂·烈祖》),这里的“和羹”既是指调和的浓汤,又有和睦、和平的价值意蕴。上文已经列举《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和如羹焉”的表述,所谓“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显然是指调和不同食物的味道。其实还需要特别注意,食物的味道并非只是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口味之调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可以认为,在德性精神的关系之维上,儒家之和气既在身外关系中展开,包括天人之和、人伦之和、邦国之和等方面;也在身内关系中展开,涵盖情感之和、气质之和、口味之和等方面。作为一种深刻的德性精神,和气既具有本体论、宇宙论的意义,又有方法论、价值论的意义。董仲舒讲:“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13〕朱熹讲:“人皆自和气中生。天地生人物,须是和气方生。要生这人,便是气和,然后能生。”〔14〕和气展现出儒家的“圣贤气象”,意味着一种“生生”之道德精神。
五、勇气——德性精神的动力之维
儒家“三达德”——仁、智、勇,其中有勇;古希腊四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勇敢也位居其中。孔子讲“仁者必有勇”,我们便清楚看到一种“仁者之勇”;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统治者尚智,武士尚勇,平民尚节制,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武士之勇”。《说文解字》明确讲:“勇,气也,从力甬声。”然而,《说文解字》接着又讲:“勇或从戈从用,古文勇从心。”于是,仅在字面而言,“勇”便有从力、从戈、从心的三层意思,稍微引申一下,勇气便又可以具有气力、武力、心力等多重意蕴。就讨论儒家德性精神的动力维度而言,这样的勇气必须经过深入的追问、推敲。
当孔子认定“勇者不必有仁”,那么便要追问:勇气可否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精神,抑或必须依傍“仁”与“智”才行?孟子有所谓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的划分,荀子有所谓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的分类,荀子还有所谓上勇、中勇、下勇的界定,宋儒有所谓“颜子大勇”的论说……。显然,不是所有的勇气都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于是很自然地便要追问:何种意义的勇气才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深入一步,还可以追问:作为德性精神的勇气有何功能?勇气作为动力之维的德性精神如何展开?
第一个问题:勇气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抑或必须依傍“仁”与“智”才行?人们发现,仁、智、勇看似三足鼎立,实则不然,其地位实有差异。“仁”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儒家也常常“仁智并提”,比如: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这些儒家仁智并联的表达结构中,“智”的相对独立性得以呈现;而在仁勇并联的表述中,情形却有实质上的不同: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这就意味着,勇德在实际上蕴涵于仁德,构成仁德的必要因素,是为仁德之附属物;与此同时,“不必有仁”之勇也就并不具备独立的道德属性。简而言之,“勇”依附于“仁”。进一步而言,“勇”与其他德行的关联性表述中,儒家往往又是搁置勇的意义而强调其他德行。比如,论及“勇”与“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这里论及“君子有勇”与“小人有勇”,然而就“勇”本身而言,几乎看不出此两种勇有何德性色彩。只有当“勇”与“义”相结合的时候,“勇”才能化身为道德之勇。
可以看到,仁、义、礼、智、信等德行毫无疑问自备道德光环,然而勇是例外的。儒家似乎并不关注抽象或纯粹的勇,而总是将“勇”的评判放置在某个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比如,孟子曾论及世俗之“五不孝”,“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就被认为是一种不孝之行。可以看到,这样的“好勇斗狠”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德行,反而是需要纠正的意识和行为。由此可以判断,勇气不能被视为具有独立形态的德性,勇气作为一种儒家德性精神是有条件的。
第二个问题:何种意义的勇气才可以视为儒家的德性精神?根据上述对第一个问题的解析,勇气不能自成独立形态的德性,要想构成一种德性精神,就必然需要将勇气与德性融为一体。勇气与德性融为一体的路径显然不止一条,当儒家称“三达德”的时候,已然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勇气与德性的连接。抽象、纯粹之勇大体缺乏内在的道德属性,然而仁、智、勇一体化的时候,“勇”即成为“勇德”,成为德性之勇,勇气构成道德之勇气,从而可以视为一种德性精神。尽管在《论语》两处“三达德”的排序中,一处是智、仁、勇(《论语·子罕》),一处是仁、智、勇(《论语·宪问》),总是居于末位,但总算跻身“达德”之列。既然跻身“达德”之列,将这样的勇气视为一种德性精神,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仁、智、勇的并联大体是儒家最为经典的方式,“勇”与其他德行的并联也是非常典型的,比如: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除了这种与诸德行并联的方式,勇气上升为德性精神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分化来实现。如果将“勇”视为一种混合体,那么就是要将那些低级之勇区分出来,提炼出所谓高级之勇,这样就可以得到德性之勇,道德之勇气由此而生。荀子对此有非常精到的论述: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
在这里,荀子明确地区分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并对每一种勇敢都作了形象的描绘。前三种所谓勇敢,或争夺食物,或贪图钱财,或残暴轻生,均非道德之行为。唯有士君子之勇重义轻利,不倾于权,才是真正充满德性精神的勇气。
第三个问题:作为德性精神的勇气有何功能?上文提及,勇气具有武力、气力、心力等多重意蕴,由此便可以引申出相当丰富的意思。在现代语境中,儒家之勇既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偏重精神的意志力。以“勇者无惧”的字面意思而言,包含着无所畏惧的心理品质,勇气具有治惧的功能,这大约是勇气最起码、最基本的功能。而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勇者无惧”意味着面对艰难困苦、障碍险阻方才显示出来的人生毅力、耐力,以及继续前行的人生动力。此种勇气,是道德的底气、骨气,是人生的情感意志力和理性精神力的统一体。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夫子大勇表现为“天生德于予”的底气;在匡地被囚,夫子大勇表现为“天之未丧斯文”的信念。此种勇气,在孟子那里亦有经典的呈现: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勇气清楚地展现出儒家德性精神的动力之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勇气在危难的时刻更显可贵。“勇是冲破障碍克服艰困的能力……在挫折中求生存,固然要有勇气,在挫折中要求实现理想,更需要勇气。任何大小的成就,勇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一遇打击就退缩的人,必一事无成。”〔15〕
人生的历程中,沧海横流只是少数境遇,多数情况大约还是平流无险的普通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勇气可有可无。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勇气作为一种意志力、行动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儒家看来,“智”发挥着“知”的功能,“仁”发挥着“守”的功能,而“勇”则发挥着“行”的功能。为强调“勇”的作用,儒家的勇气常常又被赋予“着力去做”的意义。因此,勇气也应是生活中持续存在的动力。“从心灵哲学的角度说,勇是一种高度凝练、高度升华了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理性化的,也是持久的,不是凭一时意气用事的……。”〔16〕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下所谓“躺平”的生活态度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第四个问题:勇气作为动力之维的德性精神如何展开?上文论及,中性品质的勇气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德性精神,只是具备勇力或者勇气之人并不一定是有德之人。因为勇力、勇气的主体差异,在士君子之勇之外,也可能存在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等等。于是乎,勇气作为德性精神的展开就必然意味着勇气与诸德性的并联,以及勇气自身的凝练、升级。依照儒家的表述,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词很好地体现出勇气的延展:尚勇、好勇、养勇。
关于“尚勇”,子路曾有“君子尚勇乎”之问,孔子的回答则是“君子义以为上”,进而将“勇”与“义”融为一体。可以发现,儒家常常赋予勇气以其他德性或德行的意义。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认为儒家是从引导、规范、补充、提升的视角展开勇德。在此意义上说,所谓尚勇,就是在仁、义、礼、智、好学、知耻、行道理诸方面使勇气展开为一种德性精神。
关于“好勇”,齐宣王有“寡人好勇”之问,孟子的回答是“请无好小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这里孟子提出了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好勇”从“敌一人”的个体之勇转向“安天下之民”的政德之勇。可以认为,王者好勇也是勇气作为德性精神的一种展开方式。
关于“养勇”,公孙丑曾有“不动心有道乎”之问,孟子则以北宫黝、孟施舍之“养勇”作答: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
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可以看到,北宫黝之勇大体为武士之勇、战斗之勇,孟施舍之勇大体为将军之勇、战争之勇,均有“勇者无惧”的英雄色彩。但孟子对于“养勇”的回答并未打住,而是接着论及“夫子之大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勇敢的精神与正义的精神融为一体,勇气在德性精神的动力维度上充分展开。
勇敢是古希腊四德之一,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此有浓墨重彩的论述。倘若将儒家之勇气与亚氏之勇敢稍作扼要的比较,大体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二者均强调对于怯懦、鲁莽的克服。“怯懦的人、鲁莽的人和勇敢的人都是与同样的事物相联系的,不过对待这些事物的方式不同。前两种品质是过度与不及,第三种则是适度的、正确的品质。”〔17〕相比之下,儒家的勇气与仁义礼智紧密关联,似乎更多些情感力、意志力;而亚氏之勇敢与适度、正确、承受能力等紧密相关,似乎就更多些理性力、精神力。这也体现了勇气作为儒家德性精神的内在特质。
六、正气——德性精神的秩序之维
论及正气,人们常常联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诗的开篇便是“天地有正气”,这与孟子“养浩然之气”遥相呼应。古往今来,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塑造,正气二字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广义地看,正气等同于浩然之气,即意味着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正气成为上位概念,包含志气、义气、和气、勇气等诸多方面。狭义地看,正气也可以限定在德性精神的秩序维度上进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指向秩序之维的正气所构成的乃是德性精神的一个方面,从而与指向目标之维的志气、指向价值之维的义气、指向关系之维的和气、指向动力之维的勇气共同构成统一的儒家德性精神。整体意义上的浩然之气,上文已有论述,这里着重在秩序维度上探讨正气作为德性精神的开展。
“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周易》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于是有爻位或爻数,于是有得位失位、得中失中的情况,于是人们期望的状态就是“正位”“中正”,宇宙人生的理想秩序由此确立。张载《正蒙》有言:“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18〕中正可以贯通天下之道,君子居正可以致其用、感而通。《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从天道论及人道,万物性命由此端正。《蒙·彖》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这是一个关于培育德行、涵养正气的经典表达。在《文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刚健中正”“正位居体”等表述,由此可以达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可与《周易》的“正位”相媲美,孔子提出更具儒家标识的正名思想: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
孔子正名思想因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状况而创生,其目的是恢复周礼,就是要重新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广为人知,但“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表达,更为深刻的“正”的理念蕴含其中。不难发现,在儒家正名的思想体系中,不只有正名这一种表述,还有正身、正位、正礼、正乐、正颜色、正衣冠、正人心、正路、正命、正物、正权、正法则等众多意义丰富的指称。进一步细细分析,这些有关“正”的论述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相对集中于个体身心秩序,另外一类则主要集中于群体社会秩序。
第一大类,个体身心秩序:正身、正心、正命、正路。
正身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修身,《荀子·乐论》中有“正身安国”之语,其意即可理解为修身治国。细细推敲,可以发现正身在根本上又凸显端正之意。《论语》中有人们熟悉的名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有:“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两处关于正身的论述均出自《子路》篇,与同篇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相辅相成,正身与正人就突出了“正”的理念,最后同归于为政之道。暂且撇开为政之道,单在个体身心秩序而言,正身也即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德性精神,并在“正衣冠”“正颜色”“正身行”等方面具体展开,凭依礼乐,成为“正身之士”。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
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
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尧问》)
在荀子看来,“正身之士”与“仰禄之士”相对,认为“仰禄之士犹可骄也”,而“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因为“正身之士”的存在,天下之纲纪不息、文章不废。不难体会,一种正气蕴含其中。
正身、修身的路子向内开展很自然就是正心,《大学》有名句:“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是其中重要一条。孟子提出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关于“养心”“尽心”“求其放心”有很多论述,其中还有“观其眸子”判断心正的说法: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
这种说法颇有现在人们所谓“眼睛是心灵窗户”的意思:心正,眼睛就明亮;心不正,眼睛就昏暗。《孟子·离娄上》中,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告子上》中,孟子又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有的人放弃了正路不走,丢失了善良之心却不知寻找,所以真正的学问之道便是“求其放心”。这里可以发现,孟子将正心与正路紧密相连。
以个体身心秩序而言,孟子的“正位”“正命”思想同样可以视为浩然正气的鲜明呈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大丈夫之人格形象影响深远,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立天下之正位”。孔孟都讲天命,但均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孟子讲:“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孔子讲知命,孟子讲“修身以俟之”,实际就是立命、正命,充分彰显儒家德性精神的积极性、主动性。
荀子有关正身、正心、正命、正路亦有诸多精彩之论,这里列举一二:在《荀子·非十二子》篇,论及“古之处士”,荀子提出——“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赫然在目;论及“君子”,荀子提出——“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也是清楚可见。
第二大类,群体社会秩序:正名、正礼、正乐、正物。
孔子的正名思想针对“礼坏乐崩”而创,直接指向恢复周礼、复兴周礼。在字面的意思上,正名是指用名以正实、名实相符;而在具体的层面上,正名就在正礼、正乐、正物中具体展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恢复君臣父子之间的一整套礼节仪式、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这些内容经由孟荀等后世儒家的发展,正名思想实际上形成更为丰富的正礼、正乐、正教、正国、正权、正物的理论。《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讲“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这意味着,正名思想实际上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在现代意义上,孔子的正名思想常常被视为一种公正的原则,正名、致中和表明一种“恰如其分”,是一种“各得其所”“各有所值”。〔19〕与上文中个体身心秩序相对应,这里也选取四个方面——正名、正礼、正乐、正物来讨论蕴含于群体社会秩序中的德性精神。
正名思想在荀子那里有很大的发展,《荀子》三十二篇,其中专有《正名》一篇,对于名实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正名》篇中,荀子提出:“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君主制定名称,可以辨物、可以行道、可以通志、可以率民,制名、正名就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和完善。荀子又讲:
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
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情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
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俯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荀子·正名》)
这些精彩的论述均出自《荀子·正名》篇,可以发现,正名思想中又涵盖了“正利而为”“正义而为”“以正道而辨奸”“正衡”“正权”诸方面的内容。高频出现的“正”字则充分说明,在这样的社会秩序建构中,儒家正气的德性精神深刻蕴含其中。
个体行为符合礼的规范,这是很好的德行:“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尽心下》)从对个体行为的功用而言,“礼者,所以正身也”;而从礼作为社会秩序而言,其本身也有合理设置的问题,于是荀子又提出:“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儒家认为,端正、阐释礼义是教师的职责所在,“正礼”与“正教”相关联——“教者必以正”(《孟子·离娄上》)。礼的功用并不止于正身、正教,还可以继续上升至——正国:“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或者修齐治平的思想轨迹,而当人们留心、注意、发现其中蕴含的正礼、正教、正国等可谓理直气壮的论述时,儒家的正气精神才可能真正映入人们的眼帘。“立于礼”“成于乐”,儒家礼、乐相连,儒家有关正乐的表述有很多,这里也列举一些加以说明: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
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
礼乐政教均是对群体与社会的秩序而言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儒家之正气精神并未止步,而是由人类社会秩序继续上升,进而构成天地宇宙秩序。在这样的意义上,群体社会秩序中的“正己”又可以达成“正物”:“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在此意义上,孟子所谓“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或者文天祥所谓“天地有正气”就显得越发自然。
儒家德性精神的考察与阐释,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在“道德之气”的角度进行概括与提炼,是将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德性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现代儒家德性论的视域中,“浩然之气”意味着一种浑然一体的德性精神,又具体呈现为志气、义气、和气、勇气和正气。所谓志气,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目标维度上的呈现;所谓义气,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价值维度上的呈现;所谓和气,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关系维度上的呈现;所谓勇气,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动力维度上的呈现;所谓正气,可解读为儒家德性精神在秩序维度上的呈现。增强当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儒家德性精神依然可以提供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