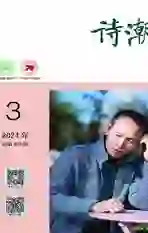山河忽晚
2024-04-08巴音博罗
巴音博罗
落 日
我垂首默立。落日在远方的天际徐徐下沉——始皇和李白都见过的落日!
尘世间总有这磅礴的事业渐行渐远,如果说纪念也不能替代那偉岸的身影,被暮霞染红的翅膀该如何扇动?
哦,河畔那独自洗涮的人要罢手吗?流水已载走他的沉思和默想。设若这时一只归鸟的啼叫是虚幻的,万里云山也仅是戏曲舞台的布景,我还要不要像剧中人那样拔刀自刎并献出沉甸甸的头颅?!
大路、倒影或名叫诗艺的月亮
一个人从一条遥远的大路上走来,后面跟着一群起哄者:一个人从一条偏僻的小路上走来,后面跟着一群乌鸦;一个人从一条傍晚的暗路上走来,踩着细碎的月光(那月光像锋利的玻璃碴,割伤了他的脚趾……)一个人从一条烟一样的往日之路上走来,后面跟着一群破败的亡魂!
假若是在灯下,你挑拣以往使用过的词语——那美丽、细小的尸骸。你将它们埋在月亮般的墓地上,你将用抛光的皮具细细打磨那珠串,为了重获纸页上的光芒——语词的心脏以及语词内部的坚硬,像铁锁,像乡村山野上一枚紧密相扣的核桃,像工厂里齿轮的钢牙。
一个人倾其一生能打开几颗石头一样的语词?
你敲击它直到自己把心敲硬。你敲击它,日夜不停地敲击它,直到词语打开门扉从里面走出另一个自己!
词语的监牢像是罪与爱的禁地。火焰焚烧,梦的翅膀卷曲焦糊。一个人成为火炭,那灰烬的余温就是你苦苦寻找的诗艺吧!
你可以一个人离去,不带走一只鸟儿或烧煳的翅翼。你可以号啕大哭却不忍那颗颗眼泪碎成瓦片。当秋天突然降临到这贫瘠的大地上,早死者纷纷从空中坠落,像黄叶,像山坡上寺庙的钟声——在那战栗的钟声里你终于把自己照亮了。
而睡眠中一条苍凉的河流拖着青烟开进了诗歌史,你的脸更暗了,像一块礁岩。而那海上乘风远航的人是你的兄弟,他叫沉默,也叫夜夜失眠的地鼠!它溜进房间,噬咬着孤独者的梦。你等待突然从船上跌落时溅起的水花……
晚年的你不断地修理你的房子——那生命的避难所。你用回忆擦拭那些器皿、丝绸,以及盛梦的碗。你用泪水将它清洗干净。烛盏熄灭了,电灯开关也失灵了,你的内心一片漆黑。你终于成了黑暗的奴仆。
你老了,老而且瞎。你的身体像块破布,你骨头酸胀手脚痉挛,一根尖锐的长钉扎进你的骨缝并在骨缝之间蜿蜒穿行,那么锋利、专注,像亮晶晶的痛!
你知道那是你期待已久的死,这诗的最后一章!
在地平线绷紧的尽头
世界已飞速退行至地平线的尽头,它拉呀拉,拉长了我的眼线如同拉皮筋。我的眼线越来越细都快绷断了,我担心如果再用力就会啪的一声,我的眼球会像弹弓射出的石子一样飞到地平线的另一头。
而歌声正飞速地消逝在地平线的尽头,那声嘶力竭地拉长声调的人唱呀唱,他的声带如同二胡的丝线拉呀拉的。我担心如果运弓的手臂再用力些,这五千年历史的线头就会拉扯出风雷激荡的一部辉煌大剧,而戏台还在河的对岸。我说过的那句话正如鹰蹲在我祖父肩头。它在等待一声号令。当一只野兔出现在书页里,我祖母的小脚正以马蹄的嗒嗒声叩击大地。族谱即书卷,打字机即梦的犁铧。我说月亮照耀过的乡愁就此珍藏吧,压箱底的珍宝,我要用丝绸包裹!
冬日的北国大地
“只有土地永远不会背叛你。”这句话说得多好啊!这是一位美洲作家在他作品结尾时停下激流般的叙述说出的。对于一个离开儿时的乡村蜗居于城市里这水泥森林里的我来说,听到这话时心里触电似的一动。而我脚下这片被祖先用旧了的北国大地此刻正无声无息地铺展向冬雪皑皑的远方。它上面发生过的战争、硝烟、流血、动荡,以及嘈杂的呐喊如今也早已沉寂了,像被践踏过的斑驳的雪野以及泥路上杂乱的脚印和车辙……
我站在这冬日的广袤无垠的平原上,头顶是深邃得仿佛梦境似的穹天和隆隆转动的仁慈太阳。土地像饱经磨难的农妇裸开被化肥浸淫的胸脯,任收割后的荒草缓慢爬进地头那户户农家的窗棂。土地像我的寡母,早已过完了她山羊的一生,耕牛的一生,艾蒿、晚芸豆花和粗瓷酱缸的一生。我喜欢在暮秋后的地垄间伏下身子,嗅一嗅黑土的味道,汗的味道,腐烂的、清苦的味道,活着或死的味道……
我祖父的坟就在地头的不远处荒芜着,像挂在檐下那盏闲置多年的旧马灯。我父亲的新坟傍在祖父的坟边,像是来年春头地垄间的粪堆。我常常一个人在这儿发呆。我喜欢看这地上的一些印痕,看风把垄沟里一片枯黄的玉米叶抬上垄台,看几只搬家的蚂蚁排着队运走一粒发霉的种子。一群俗名驴粪蛋子的土山雀疯疯地在灰尘里嬉闹追逐,把我平静的心绪吵乱。我不喜欢那些来历不明的风,冷飕飕地吹落我噙在眼眶里的泪水……即使那片耕地从不曾属于过我。
当风雪重新描绘了大地,雁声暗示道路的方向和堤坝的走向。娶妻生子的我似乎过上了一种衣食无忧的日子,一种我不想被什么变故打断和改变的温馨日子。而此刻我像怕谁抢走似的紧紧握住铁锹木柄站在那里。那外国佬说得多好啊,“只有土地永远不会背叛你。”命里的卑贱和屈辱也是!猪啊,羊啊,鸡呀,狗呀……生活从没有背弃过我,荒唐和不公也是。如同那本不断被改版的小学课本。从小我背诵它、牢记它,以为世界是它告诉我的那样,生命也是不可轻易被墨水涂改的,仿佛一台轰鸣着开进春天的拖拉机,钢铁牙齿咬遍这荒凉而辽阔的土地,咬遍我逐渐苍老的肉身。我是和这片家园朝夕相伴慢慢变老的,我的幸福也在这里。我光秃秃的脑袋如今成了空旷的谷仓,我的梦想仅仅是机井里流出的一汪清澈冰凉的泉水。
你瞧,生活就是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的。生活绝不会欺骗你。也许我们苦苦寻觅着并想永远占有的东西并不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并不值得丢家舍命地去护卫。只要口袋里还盛装着粮食,只要胃里还满蓄着胃液,我就有本钱快乐。我就要把这牵牛花一样的日子过到底!
我热爱那一小块荒野
在城郊帽盔山北面有一小块荒凉的原野,一万年前滚落的一块巨石现在成为凝望远方的头颅。它的嘴巴和眼睛早已被丛生的荒草所吞噬和遮盖。当歌谣乘着风儿飞来,树们齐刷刷举起手臂要抬高那天幕,但地平线却抬高了故国的人民——当人民坐上安详的云端……
我想着想着,缓缓躺下,耳朵贴紧大地,一条长河像时间哗哗涌动,使我慢慢成为一个清澈的人,流淌的人!
火车总在午夜时分穿过城市
火车运载着睡眠,运载着月光和幻梦,当然也运载阴影、梦中人的嘟哝——口齿含糊又语焉不详……火车也运来了一只野猫的叫春声……
我翻了个身,继续在床上想象。那一节节黑沉沉的钢铁车厢,沉重的巨轮辗轧着铁轨并发出年代的咣当声,像是一个世纪的伤口,拉链一样拉开:眼泪,口信,恋人温存的气息以及更大的钢铁牲畜在道路上粗重地喘息……
火车总是在午夜时分穿过这座城市的。如果它鸣笛,则是赶牲人在驱赶梦境。那些想安眠的人在抓紧黑夜的缰绳,而我却喜欢独守在这由马匹和石头砌成的古井里,向更深的地底沉落。我该数这永远也过不尽的火车车厢吗?我要把一直亮着的信号灯用温热而咸涩的泪水擦拭干净吗?
这整整一个世纪囤积的苦痛,要在明晨还给朝霞。这衰老却又坚强的火车司机更像我亡父!如果明晨他从大海里归来,带着他的火车,我和母亲将以鲜花铺展这空旷如野的餐桌,以歌和星粒般的鸟鸣,喂食房间!
群 鸦
在有雪的北国荒地上,在松林间,神的手有如一位狂烈的国画师。他啸叫,旋步,挥动狼毫斗笔恣意淋漓地倾洒着夜色和墨团。鸦群在盘旋,又忽地栖落于树冠上,鸦群使树冠的分量陡然加重,使夜色加深,使雪从此有了更加苍茫的意念。一个在此经过的人脚步踉跄,仿佛宣纸上书家写错的汉字,而更多沉默不语者则似枯瘦的寒枝在风中战栗……
突然,一个大声音从远方响起,群鸦似乎受到惊吓,只听呀的一声早已呼啸着腾冲到半空,黑压压遮住了楼群和路灯,真正的夜晚刚刚开始!
林地中央一个人在练拳
他好像凭空在抓取什么,他甩掉了自己的虚空,因此使树林微微颤动。阳光斑斑驳驳,像池塘里的静水。感官晃动,因此能听见树汁流动的声音。他一直在与虚空较劲,而寂静正吞噬着他和整个林地的荒寂。
我感到他已溢出身体之外了。此时,如果一棵树脱离树林单独从阴影中走出来,一块石头抬起灰色眸子好奇地深入人的内部……
我在慢慢生长,树林轻缓地浮上半空又落下来……哦灵魂,我说,就让一声清脆的鸟叫划开我的皮肤吧,我情愿自己是最先受伤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