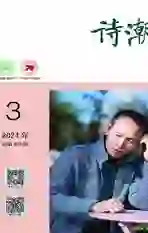何以“反诗”
2024-04-08向卫国
向卫国
本文受命谈一谈诗人阿吾的诗歌创作,但在谈论阿吾之前,似乎需要先谈谈“第三代诗歌”的问题。尽管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员,阿吾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一两首代表作品,如《对一个物体的描述》《相声专场》等也算是广为人知,但总体看,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的诗歌写作多少有些被忽略和轻视。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长期活动在诗歌的圈子里;另一方面,客观地说,阿吾在“第三代诗人”之中,并不属于最突出的那一部分,诗歌作品也偏少。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诗歌批评界对“第三代诗歌”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和深入,甚至有些求全责备式的偏见,加上历史还不够长,所以诗歌批评界尚未来得及对阿吾这样的诗人重新展开考古式的发掘。
近年来,看到和听到不少诗歌批评家要求重评“第三代诗歌”的主张,从他们发表的言论和书写的文章来看,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认为以往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第三代诗歌”的评价过高,需要重新定位。这些批评家中有令人尊敬的师长,也有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在严肃地提出问题,也各有自己的理由,值得倾听和重视。由于本文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讨论这个问题,本人也无意于搞“学术化”的考据和研究,就不一一加以举证和辨析了。个人认为,“第三代诗歌”之于中国诗歌的意义至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一方面,近数十年来的中国诗歌批评,总体看来,带有一个时代鲜明的负面特征,浮华多于诚恳,情绪大于理性,名利重于创造。这些问题在诗歌创作中同样存在,但在批评界的表现尤为突出,远胜于诗歌创作。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远不能胜任对自身诗歌创作经验进行认识和理性总结的重任,流于现象和表面的评述过多,深入的歷史观察和有效的理论总结则极为少见。由于诗歌批评的多数从业者,例如本人,缺乏更深厚的中、西哲学和理论修养,未能养成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理论能力,当代批评几乎未见有相对可靠的诗学理论的建构,而真正杰出的批评家必定是以独创性的诗学思想或观念为支撑的。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文学批评和诗歌批评历来重视的是历史主义的方式和方法,但多数人对“历史”的理解也相当短视和表象化。就对“第三代诗歌”的认识而言,由于普遍缺乏更多的耐心和综合能力,我们在“历史”的意义上,把它“终结”得太早也太快了。不错,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海子之死有如一根诗歌的琴弦突然绷断,演出戛然而止,“第三代诗人”在这一年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但在三十多年之后来看,这不过是又一次大浪淘沙,“第三代诗人”中有不少离开了诗歌(有些后来又重新归来),但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从来没有中断诗歌的写作和探索,且一直坚持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有的甚至还是当下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和杰出代表,比如欧阳江河、西川、李亚伟、杨黎、赵野、于坚、韩东、翟永明等等。
个人看来,“第三代诗歌”之于中国诗歌至少具有如下两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一)“第三代诗人”是唯一的一代“青春诗人”。“朦胧诗人”大多是知青出身,他们的写作起步于完全遭压抑的青春期,诗歌得以面世却到了青春已逝、岁月催老的年纪,整体的诗歌气象多少有些未老先衰。“第三代诗人”却大多是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届大学生,历史在他们身上同时赋予了青春、欲望、自信的生命特征。但由于长达十年的文化停顿,在这一代大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身上,又都表现出一种知识的盲目性,如饥似渴、囫囵吞枣但又漫无目的地阅读是这一代青年的成长方式,他们对未来同时抱有天真的好奇和缺乏方向感的热情。这些洋溢着青春力量又混合着盲目的知识和思想冲动的生命特征,恰恰是诗歌所需要的。想一想盛唐诗歌,正是由青春的初唐成长而来,既不失青春的朝气,又有了中年的沉稳,方能成就诗歌的辉煌。再看“第三代诗人”之后的更年轻一代诗人,“中间代”尚未正式出道便遭遇一个集体沉默的年代,压抑虽然不一定都是坏事,厚积薄发也自有好处,但气质必然已有不同;70后、80后诗人是最早的网络诗人,诗歌写作门槛的突然消失同样带来了好处和坏处,表面上有了发表的自由,同时也是集体潜入了时代文化的水平面之下,等他们醒悟过来冲出水面时,激起的浪花已然不能和“第三代”掀起的诗歌浪潮相比,文化本身已呈明显的历史颓势。几代诗人虽然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却再未出现“第三代诗人”集体那样热腾腾的青春与诗歌的朝气。在我看来,许多“第三代诗人”能够保持长久的创造力至今,与他们青春时代生命力的自然勃发和滋养是有内在关联的。(二)“第三代诗歌”开创了汉语当代诗歌的各种可能性。正是由于“第三代诗人”的青春力量和知识的某种盲目性,使得他们仿佛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开辟出了汉语当代诗歌诸多可能的道路和语言模态。想一想诗坛后来的“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口语诗的”分野等等,无不肇源于“第三代”。即使是今天批判“第三代”诗歌的批判者,他们所持有的立场和方法自身也跟“第三代”脱不了干系,在某种意义上不过仍然是“第三代”中的某一种诗歌立场对另一种或若干种主张的批判和对抗。但是,由于诸种原因,“第三代”开创的诗歌资源并未得到全面的认识、总结和扬弃。
阿吾就是一个以一己独特的声音开创了汉语诗歌某个方向的“第三代诗人”之一员。尽管迄今谈论阿吾诗歌的人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批评家注意到了他诗歌的独创性和诗学上的独特追求。比如著名评论家西渡和陈仲义先生都对阿吾进行过评述,但他们更感兴趣的似乎都是阿吾的“反诗”主张或“不变形”诗学。西渡认为“阿吾的‘反诗主要从两个方向上对世俗的诗歌样式发起攻击:其一是反修辞。……其二是反象征。”“阿吾在两个方面的努力合而言之就是,以一种很客观的、说明的语言达到对事物的‘不变形处理,从而让事物自身在诗中现身,并最终更新我们的眼光。”陈仲义则把阿吾的“不变形”诗学主张与现象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联系起来,认为阿吾从变形到不变形的诗学主张是对普遍认同的“陌生化”理论的反拨,“与韩东‘诗到语言为止,蓝马、周伦佑的反价值、反修辞的‘三还原,于坚的‘拒绝隐喻以及‘及物写作‘废话写作构成相同的谱系。不变形或少变形的谱系依托口语,在后来的口语大潮中也逐渐稳住脚跟。”
从以上诸家论述可以看到,阿吾的“反诗”或“不变形”主张尽管颇受关注,从纯粹的诗学角度看,却并无多少新意。近两年,随着对智利诗人帕拉的译介,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反诗歌”早在1954年就提出来了,他针对“纯诗”和“抒情主义”诗歌的传统,强调“诗人已经从奥林匹斯山走下来了”“诗人不是炼金巫师/诗人是普通人/是砌墙的瓦工/是造门造窗的建筑工”“我们的语言/是日常语言”(尼卡诺尔·帕拉《宣言》),这些主张与阿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但是,不管是“反诗”主义,还是“不变形”的主张,都不可能进行到底,最多只能代表某种倾向和追求,甚至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诗学。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传统诗学的强大,而是诗歌作为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传达,“不变形”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在本质上受限于身体的感知系统,人们对任何对象的认识都局限在这个系统之内,不要讲抽象的意义,即使是单纯的物理属性,声音、颜色、形体等也都经过了由感官刺激到神经信号传递,再到大脑的图像还原和识别过程,这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信息的处理与传播,必定会有信息的丢失、变异和主观的增值,绝不可能是完整的、全息性的处理过程。所谓“不变形”最多只能是在传达个人对事物的感知时,主观上追求尽可能地客观、完整,保持原样,但并不可能做到。语言的能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替代关系,决定了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所指非所言”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感知本身其实早已先行对事物进行了变形,所感知的东西并不是原来的那个客观之物。也许是作为修习哲学出身的阿吾本人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对自己早期的主张进行了修正:“后来我认识到,变形的意象和不变形的白描没有彻底的界线,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变形的世界里。我以为没有变形的词句,其实细究起来,有一些也是变形的。”
我们今天讨论阿吾,究竟是将他主要作为一个诗人来看,还是诗学理论家?我认为当然应该是前者,当我说他是开创了一个诗歌方向的诗人时,指的是他的诗歌而不是他的诗学,他的诗学主张并不能涵括他的诗歌。在我看来,他的诗歌确实可以接受为某种“反詩”倾向的诗,但并不是“不变形”的诗,只要是诗,就不可能不变形。
首先,我们看看阿吾的名作《对一个物体的描述》:“该物体产于四川/八一年起归北京保管/它长1.72/宽0.43/厚0.21//物体为不规则状/暂时称作组合式/有一个椭球体/两个圆柱体/两个圆锥体/五个长方体/表面呈天然光泽”。这首诗所描述的“物体”是阿吾自己,也就是作为“物体”存在的阿吾本人的身体。大概在诗人的意识中,如果将一个人彻底物化,用一种纯粹的物理测量方法,将它的物理数据记录并复述出来,就等于很彻底地客观化或“不变形”了:(1)没有任何使用修辞的嫌疑;(2)没有任何主观性(包括抒情性和认识性)介入。但诗人忽略了,他所描述的对象与此处“物体”的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人”作为一个具有实体对象的概念不管是单称还是全称,都不是单纯指物质性的肉体,还同时指向其生命(包括意识、精神、灵魂等),所以像诗歌这样的“物化”方式,不仅不是“不变形”,恰恰是最大程度的变形处理,即剔除了其生命,只保留物质形式,这是其一。其二,对一个物体的语言描述,是无法穷尽其物理数据的,无论多么详细,都必定要省略更多的细节,也就是说,符合已有数据,但其他数据不同的“物体”依然有无穷多,因此诗歌的语言描写最终没有具体的唯一所指,而是另一种非概念性的概括和抽象。其三,当诗人用一个人体的部分数据或特点、功能等代替一个完整的“人”体,本身就意味着修辞的产生,西方人称之为“提喻”,中国人称之为“借代”。
进一步分析,诗歌为达到绝对客观化的目的而将人“物化”处理的方法,并不只是实现了客体或表现对象的物化,而是反过来,对诗歌的认识主体进行了物化。作为主体的“人”在认识过程中,是不可能将对象的所有细节特征和生物的生命特征完全忽略的,只有当主体被物化为物理工具性的存在,比如照相机,才可能将一个活人简化为一些可测量的数据。换句话说,在阿吾的诗歌中,客体可能依然是一个人,但主体却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测量工具。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其另一名作《相声专场》:诗歌将讲相声的两个人,物化或简化为“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等等,将他们富有个性特征的声音和动作简化为男声和女声、粗和细等等,读者阅读过后,脑海里留下的只是完全物性的剪影或动画,完全去除了人的个性和精神特征。如何做到这一点?阿吾的方法就是将诗歌的认识主体替换为皮影戏的灯光、皮影、幕布,再加一台音频分辨仪一类的东西,读者看到的是这些工具投影出来的影像,听到的声音只有高低粗细,没有个性化的音质。
到此,阿吾诗歌的创造意义,即其“反诗”的价值,才真正被发掘出来:阿吾的创作不是直接对客体进行的,而是通过主体的“变形”实现对客体的客观化呈现。也就是说诗的认识主体不再是“人”,而是某种物理工具。就诗歌写作的历史来看,这显然是一种发明,它将诗歌的写作主体彻底物化,去除了任何主观性的可能。诗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是出于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不信任。人类总是带着自己的一切知识偏见或文化立场看待世界,做出判断,从而扭曲了事物本身。但要在人的一切活动中进行全面的文化祛魅,谈何容易?人都是既有的人,人的历史就是被塑造、被书写的历史,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被其自身之所是规训和限制。无数思想先贤曾经做过努力,企图摆脱这种人性的束缚,比如中国的老子、庄子主张回到纯粹自然状态,禅宗主张弃绝语言;西方也有形形色色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发明了心理直观、现象学还原、知识考古、意义悬置等各种方法,但在具体的写作和行为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做到彻底摆脱知识的偏见和主观的牢笼,所有这些思想者自己首先就是思想的集成器、文化的塑造物,其思考的场域先天地被限制在其认识限度之内。
阿吾的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跳出了纯粹思想的内置框架,而发明了一架外在性的观察装置,也就是彻底摆脱了写作者的主体性特征,用工具代替了人的感知器官,这样“写”出来的诗,称为“反诗”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一方面它没有了创作主体,另一方面客体完全物化,从而完全不同于传统诗歌。
但是,人们仍然要追问的是,当传统文学的“人学”特征彻底丢失,情感、个性以及承载这些内容的丰富细节统统不见了之后,剩下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还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呢?我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呢?阿吾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后期的写作,实际上是适当地恢复了“人气”,或者说是部分选择性地突出了“人”之所思、所要。比如《这两天看见人我就感到孤独》,无论“孤独”意味着什么,它都不属于“物”而是属于“人”的感觉,也是人保持自己生命感的需求之一。还有《向黑暗扔一块石头》,为什么要扔石头?这是一个人的动作和行为,无论扔出去的石头会遇到什么,有没有回声,或者“向黑暗扔一块石头/和向光明扔一块石头/效果竟然完全一样”,或不一样,那又怎样?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扔石头的人感觉到了他的主体性,“扔石头”就是主体性的自我证明和自我生命表达。《我站在海边等那条大鱼出现》中言之凿凿的“那条”大鱼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也不一定“出现”,但“我”还是要“等”,而且要强调那是一条“大”鱼。为什么?没有理由,只能说“人”生来就必定要“等”这样的一条“大鱼”。
从一个“物体”到一个“等”“大鱼”的人,阿吾创立了一种诗学,又修正了它。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