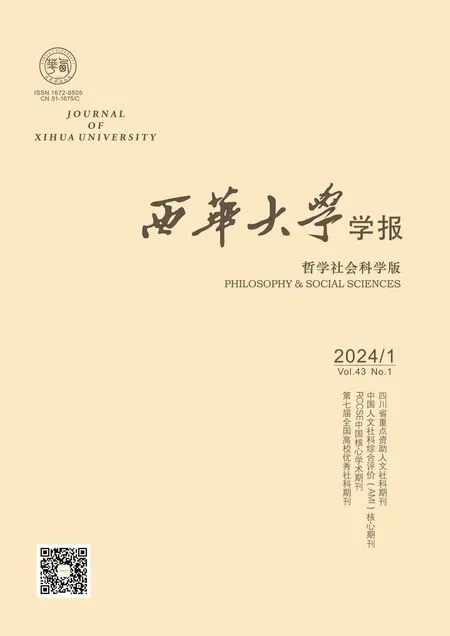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
——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2024-04-06蔡杰
蔡 杰
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济南 250100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从更宏观的学术史角度看,这其实也是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思,最终诱发了以经学解构理学,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晚明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本身作为一位思想精深的理学家,却提出回归经学的主张,在一个人身上深刻地反映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型的特点。以往学者对黄道周思想的刻画,多是从理学方面着力,例如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主要通过分析其论北宋五子、朱陆、王学来展现黄道周的学术倾向,并分析黄道周论性与气质、格致工夫、心性定静、戒惧慎独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黄道周的理学思想面貌[1]87-121。然而,陈来也注意到:“他的思想虽然是明代的一支,但确非理学所能范围。而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包含了他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1]118可以说,黄道周既是一位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经学家,其学术思想具有理学与经学交融、治心与治世并举的特征。
本文先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入手,按照时间的顺序,勾勒其理学著述与经学著述交迭出现的治学历程。其次,研究分析他著名的理学问答录《榕坛问业》,发掘与揭示其中的经学内容,展现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的特征。最后,从工夫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述黄道周试图调和理学与心学,并以此作为基础,与他的经世思想相统一与互补。
一、理学著述与经学著述交迭出现的一生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等,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庶吉士。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参加修纂《神宗实录》,又充任经筵展书官,一反膝行奉书的惯例,平步以进,受到魏忠贤目慑而不惧,天启五年即告归。后闻清兵入关,慨然出山,于崇祯三年(1630)四月抵京,晋升右春坊右中允,八月抵杭州主持浙江乡试,次年十一月乞休。后又闻清兵攻入京畿,又出山勤王,于崇祯十年升少詹事。崇祯十一年因抗辩忤崇祯皇帝,八月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崇祯十二年返乡守墓,十三年五月因江西巡抚解学龙案株连被逮,杖八十下狱;十五年八月复官,十二月又返乡守墓。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任弘光朝礼部尚书。七月在福州与郑芝龙拥护唐王称帝,颁年号隆武,官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十二月募兵在江西与清军血战,最后在婺源被俘,被解至南京,清顺治三年(1646)拒降就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文以品行称其为“一代完人”,道光五年(1825)清廷将黄道周请入孔庙从祀。
黄道周是晚明大儒,著名的理学家、经学家和书法家,时人徐霞客盘数天下名流时,称:“至人唯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2]所谓学问直接周、孔,即指黄道周以六经救世,重拾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尤其是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兼容并跨越汉学宋学,回归六经,直追周、孔。学界将黄道周与刘宗周并称为晚明“二周”,陈来指出:“东林之后,明末大儒公推刘宗周和黄道周。近世以来,学人多重船山、梨洲、亭林诸公,以为明末三大家,然顾、黄、王皆于清初成学名,若论晚明之季,则不得不让于二周。”[1]87“二周”这一称号,与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组成的“清初三大家”,形成了晚明与清初两代人的传承和呼应。
从黄道周的治学历程来看,其一生讲学著述,呈现为理学问业著述和经学著述交迭出现。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的易学著作《三易洞玑》成书之后,在漳浦北山守墓的他听闻清兵入关,毅然出山。随后数年中,黄道周往来于北京与福建之间,政治活动频繁,十分活跃。包括崇祯三年(1630)四月在北京上疏建议断绝清兵退路,八月抵达浙江主考乡试,十一月在北京参加《神宗实录》的修纂庆功宴,十二月上疏营救钱龙锡等。但也因此卷入一系列的政治纷争,遂于崇祯五年(1632)二月离京,年底回到漳浦北山。此后三四年间,黄道周一直在漳州诸地讲学,所集成的《榕坛问业》正是这一期间的问答录。《榕坛问业》是继《三易洞玑》之后,黄道周的又一部重要著述。《榕坛问业》的问答虽然掺杂部分的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典籍真伪等内容,但其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四书”展开的。而即便是涉及经学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辅助于其理学思想的论证的。这一时期的理学问业类著述,除了《榕坛问业》之外,还有《北山问业》等[3]。
崇祯九年(1636)《榕坛问业》编成之后,在漳浦北山墓庐的黄道周又听到清兵攻入京畿的消息,再次出山。随后数年中,黄道周一直在京师朝中,政治活动依旧频繁,也因此陷入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崇祯十年(1637)二月分校会试《诗》一房,进士中有陈子龙、夏允彝等人;六月上疏《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举荐当时被削籍或入狱的刘宗周、倪元璐、张燮、钱谦益、郑鄤等人;七月上疏营救郑鄤。崇祯十一年(1638)曾因杨继昌夺情,三次与崇祯皇帝当庭辩论,场面情势十分紧张激烈。最终,黄道周彻底离开大明崇祯朝。在此期间,黄道周曾掌司经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洪范明义》《月令明义》《儒行集传》《缁衣集传》四本书,正是这一时期由司经局编纂而成的。
明代经学不兴,朝廷的司经局也颓坏不堪。黄道周在掌管司经局期间,苦于书库无存,决意清理库局,钞录宝书。于崇祯十年(1637)十月二十六日上《申明掌故疏》,建议整理编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中一些重要篇章,安排人员给太子讲授。所拟定的重要篇章包括《诗经》的二《南》、《豳风》、正《雅》、《周颂》,《尚书》的“二典”(《尧典》《舜典》)、“三谟”(《大禹谟》《皋陶谟》《益稷》)、《洪范》、《无逸》,《礼记》的《王制》《月令》《儒行》《缁衣》《坊记》《表记》《礼器》《礼运》《学记》《乐记》,《周易》的《乾》《坤》《文言》《系辞》[4]201-204。这些篇目不列于“四书”,从中可以看出,黄道周主张回归周孔之言、周孔之制,亦即回归经学本身。十一月一日即得圣旨云:“东宫(按指太子)讲读,循序渐进。这所奏经书各种,黄道周职在官僚,著同詹坊等官精心讲求,果集成帙,次第进览。”[4]226所以此后的九个月,一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被贬离京,黄道周一直在朝中司经局编纂他的经学著作,他自己曾形容当时的状态:“在长安中,闭门深于幽谷,今复作小书生,再翻传注。”[4]770
可以看到,黄道周编纂经学著作的目的,一方面是苦于经局颓败而急需整理,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太子讲授。他的书单中虽然不列“四书”,但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四书”,因为明代太子的学习安排中,“四书”的讲解篇章已经十分详备,而经学著作却寥寥无几。所以说,黄道周列此书单,是为了补救经学著述的匮乏。在《申明掌故疏》中,黄道周曾说:“择此四经(按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大篇钜章,不过五六十帙,讲官六人,人习十篇,错于‘四书’,以翼《宝训》。”[4]203这就说明黄道周对太子的授课设计是兼顾“四书”和“五经”的,亦即同时看重理学与经学。
也正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秋,黄道周的《孝经集传》开始起草。这一年九月,黄道周离京,十月抵达浙江的大涤书院讲学,与弟子陈子龙等的讲问中就包括《孝经》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当作为《孝经集传》的写作,或者也可以说是为《孝经集传》的最终成书做准备。而《孝经集传》与《易象正》两部经典著作初稿的最终完成,其实是在之后的牢狱之中。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黄道周因崇祯皇帝疑其结党而被捕至京,在狱中被拷问,直至次年年底被释放。在狱中初步完成的《易象正》与《孝经集传》,堪称体现黄道周最高经学成就的两部著作,在《易》学史与《孝经》学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应该说,这两部经学著作不再是纯粹地为太子讲授而作,而是黄道周在牢狱之中由对天德治道的深层思考与探索而成。
在这一时期,虽然黄道周一直身处司经局或牢狱中编纂经学著作,但他实际上并未放弃对理学问题的探讨。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黄道周出狱后再次路过浙江大涤书院讲学。这一次在大涤书院的讲学内容,最后被编成《大涤问业》,所问答内容除了经学之外,主要包括《儒脉》《朱陆刊疑》《子静直指》《格物证》等理学内容,其实就涉及到了道统论、朱陆之辩、格物致知工夫等重要的理学论题。另外,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在漳浦讲学编成《明诚堂问业》,五月与九月在漳州讲学编成《邺山讲义》,尽管二书均已佚,但其中问答的部分内容在《黄道周年谱》中有所记载,前者包括讨论《中庸》的明诚、良知主敬、思诚明善工夫等理学内容,后者包括讨论性命与经世的关系、仁之体用等理学论题,可以看到两本问答录也同样涉及对理学重要问题的探讨[4]122-128。
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底,黄道周在漳州接到三月十九日明亡的消息,率弟子袒发痛哭三日。九月出山北上,历南明弘光、隆武两朝,一直坚决抗清,直至隆武二年(1646)二三月间慷慨就义于南京。黄道周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是在政治动乱与战斗中度过的,这也意味着黄道周在1644 年出山之后,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其学术生涯。
综上可以肯定的是,黄道周在一生的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是兼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理学与经学在黄道周思想中并非是对立或者割裂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成就,共同构成其学术思想的整体。换言之,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具有理学与经学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的统一,正好体现理学与经学在整个儒学系统中,并不是两种对立的学术形态,而是可以交融互补的。
二、理学著述《榕坛问业》中的经学思想
上文已提及黄道周的理学著述《榕坛问业》主要是围绕着“四书”进行问答的,这也是黄道周现存著述中,唯一一部能够集中体现其理学思想的著作。而贯穿《榕坛问业》始终的主题是关于“知至知止”的讨论,其开卷即讲明“以格物致知、物格知至为第一要义”,并且黄道周也提出“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5]272。格致工夫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学问起点,因为其位于《大学》“八条目”之首,是一切学问的根本,黄道周将它与《中庸》的“明诚慎独”与《论语》的“求仁克复”相发明,共同构成了《榕坛问业》的思想主体。
道光五年(1825)二月十六日,清廷拟将黄道周从祀孔庙,礼部奏云:“《榕坛问业》一书考古证今,探微抉奥,发端以格物致知为第一要义。盖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4]11应该说,清人对《榕坛问业》这一部理学著述主旨思想的概括,还是十分到位的。不过作为黄道周理学思想的代表作,《榕坛问业》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理学论题的探讨。四库提要已明确指出:“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窅无归。明人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诮矣。”[5]272可以看到,《榕坛问业》虽然是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但实际上涉及对经史内容的讨论,体现了明末清初时期以经学解构理学,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本文试发掘一部分《榕坛问业》中的经学思想内容,以说明与展现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特征。
首先,经学的复兴需要以儒家经典文本作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必须破除宋儒对经典的质疑,重新确立经典文本的可靠性与权威性。所以对儒家经典文本的辨伪,是明末清初思想家与学问家的一个治学重点。黄道周一生的著述中,除了经学方面的著作(如《儒行集传》《月令明义》等)不可避免地要确立文本的可信度之外,在《榕坛问业》的问答中,也屡屡出现对经典文本的辨伪。
道周弟子曾就《尚书》今古文的问题发问,提出伏生的《今文尚书》并无《大禹谟》和《舜典》,那么这两篇到底是孔子所述,还是后人仿照圣人之言而创作的呢?又借引蔡沈的观点,说伏生记诵的《今文尚书》语言艰涩,孔安国抄写的《古文尚书》语言反而平易,如何是孔子的原意①?第一,黄道周是明确反对《大禹谟》《舜典》等出自模仿(或者说伪造)的观点:“孔壁中五十八篇,与伏生合得其半,只多二十五篇,余漫灭不行耳,宁道中有依傍耶?”[5]466第二,黄道周并不是从文献辨伪考证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立场,而是站在义理思想的层面上去分析,认为:
《书》在孟子已不尽信。刘歆常云:“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今不论敬修是仲尼之述虞《典》,是《禹谟》之依仲尼,然自“危微”垂训以来,只此两字至精至一,吾辈可以无疑矣。[5]466
意思是说,传世文献本身可能不是完全无疑的,但《大禹谟》《舜典》这些经典文献中所蕴含的义理思想却十分精深。也就是说,文献本身可能有真伪问题,不可完全去相信,但是有些文献中所承载的义理思想就是圣人之论,即便文献是经后人伪造的,但里面的义理思想也是可靠的。可以看出,黄道周处理传世经典的真伪问题,并不是像后来的清儒采用文献考据方法,而是承认文本思想的可靠性与权威性。这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理学所注重的义理思想方式,去确立经典文本的可靠性与权威性。
所以当弟子再问司马迁随着孔安国学《尚书》,而《史记》中却没有记载《舜典》《大禹谟》,还有汉儒贾谊、董仲舒等学问至博至深,却都没有涉及《古文尚书》这部分内容,又借引朱熹、蔡沈认为孔《书》出于东晋的观点,对《古文尚书》提出质疑②,黄道周回答:
古二十五篇深旨奥义,岂是后儒之所能及?昔有疑《礼记》诸篇是汉儒杜撰者,晦翁亦谓“汉儒深醇,莫如董、贾”,董、贾如何做得《礼运》《礼器》《郊特牲》许多文字?东晋诸贤既不能作一《书》序,岂能创出许多精微质奥之言?[5]467
意思是后儒的造诣虽然值得肯定,但是造诣再高也无法超越圣人的思想,所以黄道周认为《尚书》《礼记》所承载的义理思想正是出自圣人,而无关文献载体。黄道周在看待宋儒对《周礼》的质疑问题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且如《周礼·大司乐》一章,未经秦火,河间古书,此最先出,玩之长人神智,决非后儒之所能造。”[5]471可以看出,黄道周并非要回到汉代经学的模式,而是试图跨越汉宋,回到圣人的思想本身。这也表明他并不全然信奉汉宋以来的传注,而是主张直接回到经典文献本身,直接处理经典文本的义理思想,由此探寻圣人的意旨。也就是说,经典文本中的圣人思想才是最具权威性的,这也意味着宋儒建构的道统观,在黄道周看来其实意义不大,这在无形中对宋明理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其次,黄道周对汉学宋学的平等看待,也体现在对汉唐与两宋政治的义利王霸之辩上。早在宋代,朱子就曾与陈亮辩论过这一问题,在宋人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三代与汉唐两个阶段,而朱子基本上只推崇三代之治,并批评汉唐霸业云:“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6]而事功学派的陈亮则肯定汉唐王朝的功业,认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说,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7]可以看到,朱子与陈亮争论的焦点在于汉唐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在明人的历史叙事中,除了完美的三代之治以外,还有汉唐与两宋这两个时代,所以很容易就将两个时代的功绩拿来对比。自从晚明实学思潮兴起之后,士人不断地反思与批判两宋的柔退风格,同时就会相应地肯定汉唐之治的事功与霸术。
卢君复问:“士不通经学古,不足致用。宋儒讲论,于斯道极为有功,然如当日经济,视汉唐如何?汉治杂霸,唐治杂术,宋治积衰,日沦日废,议论成功,亘然两辙,毋亦德行文章、经济判然两物,并成两事欤?”
某曰:“今日最喜得贤此问,异日免被天下笑骂。宋家天下自燕山来,半是敌国,赖得元佑诸贤清明洁治,末后衰颓不比五代,自是气运使然。向无诸贤,不知几多豪杰臣辽臣夏,何况金元?且如狄武襄、岳武穆诸贤,经许多危疑,从容问道,岂是河朔节度皮毛所及?陈同甫骋骤天下,作一虞允文不成。但看张邦昌、刘豫做不成天子,亦是周、程诸公手末弩。千万勿说德行文章不成政事。”[5]281
道周弟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两宋所代表的德行与汉唐所代表的事功之间是怎样的联系?或者换一种说法,内圣与外王之间是不是割裂的?这一问题其实是儒学自古以来的难题。然而黄道周并没有认为两宋就只有德行而已,他列举出狄青、岳飞以及陈亮等贤臣,要么具有丰功伟业,要么主张事功思想,均是撑起宋代朝廷的顶梁柱,否则宋朝在辽、夏、金、元的围攻之下恐怕早已覆亡。所以黄道周指出:“宋无诸贤,岂得与汉唐齿?凡天下治道不效,皆是学问不明。书生开口便道‘读书是读书人,做官是做官人’,从此人才日益污下,嘉榖不茂,稂莠日长,灭裂卤莽,取报宜然耳。”③也就是说,黄道周认为两宋也具有和汉唐一样的功绩。那么,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如何?他主张读书与做官不是割裂的,读书人也是做官人,做官人也是读书人,这就意味着内圣与外王是结合统一的。
将内圣与外王相结合,实际上也体现了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上文论述了两宋虽强调内圣,但也有外王的功业;那么反过来说,想要实现外王的功业,也不能忽略内圣工夫。这就表明黄道周虽主张经学救世,但并没有舍弃理学工夫。所以当弟子质疑周子、二程的性命之谈不如胡瑗的实学“当胡海陵(按指胡瑗)时,立经义、治事二斋,修兵农、礼乐、书算诸务,士人皆有实学,数十年间,用之不尽。今书生不过举业,其精微者,又谈性命理道之细,于兵农书算等事,废置不讲。县官宵旰,忧簿书钱榖之务,卒无一人起而荷承者。想周、程之谈性命,不及海陵课实事之最也”[5]407,黄道周作出了批评:
天下事靠簿帐不得,只是寸心去做。心地清者,做事必明净;心地密者,做事必周详;心地了彻,做事必简切。决无虚凭簿帐弄出才谞之理,譬如水利、土工、鼓铸、收纳,这三四事极是琐碎,使小人有才者干办一番,极是报效。然不过数时,法立弊生,旋归破坏,惟有心地清明、不惮劳苦者,从头彻尾一一做去,便成百年之规。[5]407
意思是说,外王事业必须从内心做起。否则若只是在琐碎的事务上用力,让一些有才干的小人去做,似乎也能办好,但是如果小人丛生的话,势必破坏朝纲法度。所以黄道周强调,内心工夫是一切工夫事业的起点,如此一一做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在黄道周看来,治心是治世的根原,治心与治世需要兼顾并举,或者说,理学、心学是经学与实学的前提,前后二者不可偏废。所以说“经世治心,都是要细;明体致用,都是要实。岂有两种道理”[5]449?黄道周这句话可以作为其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特点的概括。
三、互补与统一: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
可以进一步追问: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的具体模式是什么样的?一言以蔽之,是一种互补式与统一型的模式,析言之则是回环互补,浑言之则是交融统一,以此保证“止于至善”的理想状态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在这里,本文以黄道周的工夫论来说明这一点,然后借助具体的案例,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加以探讨与申说。
在黄道周看来,工夫从理论上讲可以分出次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做工夫中,做过一截工夫就可一劳永逸地进入下一段工夫,而撇开上一截工夫不管。换言之,做工夫的目的是追求最终的至善,但如能达到至善,并不是说就可以一劳永逸,而是仍需不断地做工夫,以维持至善的状态。这说明黄道周的工夫模式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型,而是环环相扣、回环往复的一种整体形态。《榕坛问业》记载:
张子京问:“成己先于成物,如何又说知及先于仁守;复礼乃可为仁,如何又说仁守还须动礼?”
某云:“此道无穷,东西相起,切勿粘他字句。”[5]299
玉斧又问:“《大学》经文说诚意先在致知,先儒又说明德工夫专在诚意,岂知至后意尚有未诚,抑致知后另有诚意工夫耶?”
某云:“鸡鸣后尚有日出,日出后尚有鸡鸣。只管读书,不消拆字。”[5]479
从这两个问题来看,道周弟子所问的工夫都是层层递进、节节往上的。前一问涉及的典故较多,是将儒家经典中的诸多言论进行通贯的理解,其中“成己先于成物”一说出自《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8]3544,这就将“仁(成己)”和“知(成物)”联系起来。但是孔子又有“知及先于仁守”的说法,出自《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8]5471。那么这就出现了“先仁后知”与“先知后仁”工夫次序上的差异。同样的道理,“先仁守后动礼”一说,也与“先复礼后为仁”的说法相矛盾,后者出自《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8]5436对此,黄道周批评弟子说,不可纠结于文本上的字句,而要洞彻文本背后的义理思想,并提出做工夫应当是回环往复、前后兼顾的,而不是一蹴而成、一劳永逸,因为道是永恒无尽的,需要以不断做工夫为基础,才能维持道在现实中的持续不衰。
后一问虽涉及典故不多,但却洞察细微,提出在《大学》“八条目”中“致知”工夫排在“诚意”之前,但先儒为什么却强调明德工夫以“诚意”为根本?所谓“先儒”其实是指王阳明,而这一问题也是王阳明与其弟子讨论过的。王阳明弟子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9]王阳明回答:“《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要紧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9]王阳明的工夫论主要突出诚意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以诚意为本,那就必须“添个敬字”④。而黄道周弟子的问题在于,既然诚意是根本工夫,亦即意诚之后再去做致知工夫,为什么知至之后却还要做诚意工夫呢?是因为知至之后意尚有不诚,还是因为致知之后另外有一段诚意工夫呢?
黄道周这位弟子实际上是倾向于认同王阳明的工夫论:以诚意为主,认为意诚之后才能格物致知。可以看到,这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模式,先诚意而后致知,如此可以一劳永逸。对此,黄道周借助一个比喻来回答,说先鸡鸣然后有日出,但是日出之后还会有鸡鸣,就是说诚意之后尚须致知,致知之后尚须诚意,诚意与致知工夫的关系是回环互补的。我们也能看到,黄道周实际上是调和了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工夫论,既没有突出诚意,也没有突出格致,而是使二者互相补充,融为一个整体。对这种互补回环工夫模式的强调,是黄道周工夫论的一大特点。
所以在回答弟子所问“格物”与“致知”孰先孰后的问题时,黄道周说:“知得前后,自然不同。知在斗极下看,得在斗极上坐。既先入关,尚有鸿门一节,马上意思如何便得四百余年。”⑤同样的道理,“格物”与“致知”也是无所谓先后次序的,而是回环往复的,需要不断地做工夫,才能保证至善的状态持久永恒。就像历史上刘邦提前入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能一蹴而就地取得天下,后面仍有许多艰难险阻,只有不断地做工夫事业,才可能维持汉朝四百余年的基业。
黄道周的这一工夫论,不仅能够调和理学与心学在工夫次第上的差异,放在治心与治世的关系上,也能够较为圆融地解释理学工夫与经世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以《论语》中“修己以敬”一节作为具体案例,对此加以论证与申说。《论语·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8]5461黄道周与弟子就此展开讨论:
戴石星问云:“‘君子修己以敬’,只此一句便尽却君子事功、君子学问,如何又说到安人、安百姓上去?”
某云:“俱是君子本体。”
石星云:“于本体上是一节事,是两节事?”
某云:“既是本体,何分节次?”
石星云:“既无节次,何须充拓说来?”
某云:“俱是圣贤就本身上商量无尽。若有尽时,己外便无人,人外便无百姓。若无尽时,人安,己亦是未安;百姓安,己亦是未安。千古圣贤俱就本心为天下立身立命,舍此寸心,天下身命俱无安顿处,圣贤自家亦无处下手。”[5]462
道周弟子戴石星认为只要做足了修己工夫,那么外王事业是自然而然的。显然,这一思路符合宋明理学重视内圣的特征。黄道周则予以提醒,不应过分偏重修己工夫,还要注意到安人、安百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修己与安人、安百姓都是本体工夫,任何一方均不可偏废。于是,戴石星进一步追问,既然修己与安人、安百姓应当兼顾,那么二者是一节工夫,还是两节工夫呢?从《论语》原文来看,孔子是将前后二者分开来说的,岂不是层层递进、节节往上的模式?黄道周认为既然都是本体工夫,那么就不能割裂为两截。在黄道周看来,个人与天下是浑然一体的,修己做到极致就是达到天下安定,亦即立此本心是为天下立命。所以修己与安人、安百姓一样,都是圣贤君子做工夫的下手处,这就意味着内圣与外王两边须同时兼顾。
这里面隐含着一个问题,既然修己与安人、安百姓都是本体工夫,那么这里的本体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是何物将内圣与外王通贯起来的?“敬”在黄道周看来既有工夫的性质,也有本体的意义⑥。所以黄道周对此解释云“静处敬便见天德,动处敬便见王道”“尧舜此心,亦只是无己,无己处亦只是不安。一个敬字,了得百样修己;百样修己,了不得一个敬字也”[5]463。意思是说,“敬”能够贯通修己、安人、安百姓等一切工夫,而如果只在修己工夫上持敬,那是无法真正做到“敬”的,因为在安人、安百姓上面仍须持敬。“敬”能够贯通内圣与外王,是体察天德与王道的根本工夫,这也验证了上文王阳明所提及但没有展开的“添个敬字”,因而可以说,“敬”正是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的内在保证。
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黄道周看来,己身与天下是一体的,治心能够治世,治世也能反过来治心。他并不是只强调治心的一面,而是同时突出治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治心与治世互为工具,互为目的,或者笼统地说,治心就是治世,治世就是治心。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应是阳明心学“万物一体”的观念,黄道周以此作为出发点,就将理学与经学融合统一起来。己身心性与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下有灾难,如同己身有病痛,体现出儒家学说的家国天下关怀,所以黄道周提出:
才说“尧舜犹病”,凡就己身看出天下,痌瘝不获皆是己身罪过;就天下看出己身,营窟为巢皆是己身病痛。尧舜授受之际,无端说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八字便是古今君臣所断舌才知它,看敬字极精,看己字极一。[5]465
这说明修己工夫达到极致形态,如同达到尧舜的圣人境界时,修己与安人、安百姓是统一的,因为天下有一人不安,就意味着修己工夫尚未圆满,这实是将自己与天下万物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至此,反观黄道周关于“止于至善”的说法,就不难理解他对“知至”与“知止”的论断。黄道周在《榕坛问业》开卷即阐明:
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试问“止”字的是何物?……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继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新,不说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时乘。在吾身中,独觉独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对照过,共觉共知,是家国天下。世人只于此处不明,看得吾身内外,有几种事物,著有著无,愈去愈远。圣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极明极亲,无一毫障碍。[5]272
陈来对此解释云:“人身心性,与家国天下,又决不是二物,而是一物,就是说,内(人身心性)与外(家国天下)不是割裂的、无关的不同实体,而是贯通为一的统一体。不仅内与外是统一的,形而下(有声有色)与形而上(无声无臭)也是贯通为一体的。”[1]87也就是说,“至善”既是内圣修养下己身的至善,同时也是经世事业上天下的至善。那么,如何保持这样的理想状态,亦即如何止于至善呢?这就需要不断地做工夫。工夫不是一节一节的间断形态,而是回环往复、圆融统一的。所以“止”是形容一切工夫的完整形态,达到统一;“至”则是己身与天下的融合,达到极致。从这一角度来看,黄道周的理学与经学思想就是融合无间的,并非由理学开显经学,或者由经学融摄理学,而是理学与经学交融一体,不分彼此。
四、余论
从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的特点出发,必然会推出黄道周对陆王心学某些主张的批评。尽管上文提到黄道周对阳明心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是有所吸收的,并且也积极调和理学与心学,但是他身处晚明时期,对阳明后学空疏虚妄的流弊却极为警惕,这集中表现在其对陆王心学的漠视经典与良知现成两个方面的批评。因为重视经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重视经典,或者说经典的教学是经学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不能光靠本心自足而将经典束之高阁,并且,调和理学的格致工夫与心学的诚意工夫,其前提是对工夫践行的重视,这就意味着不能空谈良知现成而整日冥思幻想。对此,黄道周提出批评:
陆文安(按指陆九渊)有言:“汝目自明,汝耳自聪,汝事亲自能孝,事长自能弟,本分自足,何假旁求?”近代王文成(按指王阳明)亦云:“人自知亲长,自知孝弟,见人孝悌,自生敬爱,即是良知。其人不孝不悌,自然畏恶,即是格物。如此则孟子所云不学不虑,全抛思勉之功;仲尼所云教敬教爱,无资问辩之力也。”答曰此是要关,不宜错过。仲尼开口便云:“教所由生。”又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如使学虑不施、问辩无用,则生儿去乳,不别爷娘;怀抱终身,何分菽麦?舜、禹不亲民事,亦为痴儿;曾、闵长于幽闺,亦成骄子。⑦
可以看出,黄道周并不是反对孟子良知良能的观点,而是批判陆王心学过分依赖良知良能。黄道周对陆王心学的本分自足、良知自生的观点十分不以为然,认为一旦依赖于良知本分的自生自足,就可能废弃后天的学习思考与知识问辩。如果一个人信奉这种思想,那么恐怕连基本的生活都会成问题,以至于在伦理上男女不别、父母不辨,在生存上完全倚仗亲人的供养而缺乏自身的实践能力。所以即便如大舜、大禹、曾子、闵子拥有天才资质,如果整日光靠冥想参悟,而不深入到人民事业与伦理实践中,再高超的天才资质也会泯灭于后天的无知与虚妄。然而这种无需学习就能成圣成贤的观点,随着阳明后学的传播,在明代中后期却十分流行,人人幻想良知现成、顿悟成圣。黄道周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有意针对当时这一现象而发,或者说,他对经学的重视也包含着救治人心的目的,即试图挽救阳明后学的流弊。因此,黄道周强调工夫践行与经典学习的重要性:
周公仰受于父师,而犹曰继日待旦;仲尼挺精于天纵,而犹有废寝忘餐。近罗洪先达夫亦云:“世间岂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得也!”江右、岭南俱为良知之学,其超卓跖实有可持循者,达夫而已。象山又言:“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试问《孝经》为谁注脚?故二思六可,当竭毕世之功;显亲扬名,要有立诚之本。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犹闻叱叱之声;卜子夏之读《诗》《书》数载,乃别星辰之义,终身自云不逮,何敢遂比于良能乎?⑧
显然,黄道周对罗洪先的说法表示赞同,即认为良知绝非现成,而是要经过万死工夫才能达到。这也不难理解王阳明只有经历过诸多生死劫难,例如被贬龙场、南赣平叛之后,才能悟出“致良知”的真谛。也就是说,即便是如王阳明之类的贤才也需历经生死之事的磨砺才能真正致良知,那么普通人更应该切实地在工夫上磨。就此而言,读经就是追随圣人步伐的不二途径。陆九渊曾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著名论断,而黄道周则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如果说“六经”是陆九渊的注脚,而“六经”又总会于《孝经》,可作为《孝经》的注脚,那么《孝经》是谁的注脚?难道也是陆九渊的注脚吗?陆九渊这一说法,实是将圣人言论作为其一己思想的注脚,亦即将自己凌驾于圣人之上,这就具有非圣的嫌疑。所以黄道周强调经不可废,这也是在陆王心学逐步走向极端之后,经学获得的反弹式复兴。
总而言之,黄道周以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的独特模式,倡导经世治心的思想主张。无论是在探讨宋明两季遗留下来的理学问题中,还是在其经学著作中,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都是其治学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学与经学思想交融的思路下,陆王心学漠视经典与良知现成的主张,必然会受到黄道周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道周是拒斥陆王心学的。总体来看,他既主张调和理学与心学,又主张宋明理学与汉唐经学的融合。所以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是打开黄道周学术思想的一把金钥匙,同时这也体现了明末清初时期,以经学解构理学的一种思想新动向。
注释:
① 黄道周弟子原问为:“夫子敬修之论,实出于虞廷。然自济南伏生授《书》二十八篇无《禹谟》,《禹谟》出于孔壁,《舜典》得于大航头,前世多疑之者。不知是孔子述《禹谟》,以申其意,抑是《禹谟》依圣论以行其书耶?……蔡九峰(蔡沈)尝言汉儒以伏书为今文,今文语反难读,安国书为古文,古文语反从顺。今古相反者,谓今文出于女子之口,古文已经儒生之笔耳。然伏生背经暗诵,反得其所难;安国摩勘古书,反得其所易。《书》经两人之手口,而文势语意夐然不同,岂得谓仲尼原本乎?”见黄道周:《榕坛问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7 册,第466 页。
② 黄道周弟子原问为:“伏生女子既传四七之篇,河内女子遂献《泰誓》之简,梅赜晋中始上孔壁之书,姚兴齐时乃补《舜典》之阙,岂以前汉而古书难读,迨于末世蝌蚪始明耶?史迁尝从安国授《书》,述《本纪》亦无《舜典》《禹谟》,只以《禹贡》《洪范》继《尧典》之后,如有则史迁亦应见之,史迁不知有危微精一执中敬修之学,乃未尝读,非识不到也。贾谊、董仲舒亦未尝读此书,贾谊称性神明命,仲舒称二中两和,皆极精微,未有及《禹谟》中语者。朱晦庵云先汉文章厚重有力量,孔《书》东晋始出,大传格致极轻,疑是孔丛子等为之。蔡九峰亦以孔安国《书》序绝不类西汉文字,然古今绝学开于是《书》亦是东晋诸贤之力。”见黄道周:《榕坛问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7 册,第466 页。
③ 这段话是回答其弟子所问:“天下大患,治道不效,岂患圣学不明?汉之地节甘露,唐之贞观开元,宋之景祐康定,当时四夷宾服,闾左蕃庶,士大夫辨政莅官,子弟优游庠序,诸贤初无发明,及熙宁、元丰、乾道、淳熙间,始辟门讲论,分曹诵说,天下已自萧然,不复可观,岂如晦翁所云时有穷达,善有独兼,不得持同甫之说,关颜闵之口耶?”见黄道周:《榕坛问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7 册,第406 页。
④ 黄道周的工夫论正是添了这个“敬”字,以“敬”贯穿于全体工夫的始终。
⑤ 这段话是回答其弟子所问:“不知此‘知止’‘知’字,在格物前,抑在格物后?如在格物前,则此至善二字,尚属含糊,如看斗极者,傍指众星,了无的据。如在格物后,则此定静安虑,的是空体,妙慧相生,如看斗极,无一星处,才成不动,才是万轴之毂,如何还有节次等待得来?”见黄道周:《榕坛问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17 册,第479 页。
⑥ 黄道周说“敬以成始,敬以成终”(《孝经集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6 页),“以敬为建极之本,盖万物之生,非敬不聚”(《洪范明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817 页),体现了“敬”所具备的本体意义。
⑦⑧ 见黄道周:《孝经定本》跋,见无名氏:《我川寓赏编》,清代鸣野山房抄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