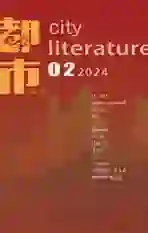裂 缝
2024-03-26子衿
六点一刻。叶菁菁站在厨房窗口喝水,一墙之隔的马路上,汽车尾灯连成一条长线,像一列亮着红灯的火车,正在减速进入站台,停下,等待一场即将开始的远行。吞入喉咙的热水,将暖意一直送到指尖。雨丝嘈杂着纷纷涌入车灯前的小片光亮中。新的一天。
孩子们往书包里塞进面包和牛奶,从门口的鞋柜上拿起各自的雨伞,乒乒乓乓下楼。叶菁菁熄灯、关门,跟在他们身后。车停在楼道出口,苏均的手机在方向盘后面闪烁。他盯着手机,但从不留意时间。叶菁菁努力让自己不催促,不发表意见,安于任何一次等待。沈均在这方面总是很有耐心,每次一起出门,他都是最后一个从候車室椅子上站起来,拎起行李,不紧不慢加入最后几个匆匆赶来的人当中。他说,队伍那么长,何必去挤在一起呢。他们因此错过航班,只能改签,在机场附近过夜。叶菁菁记得在高速公路上,自己始终盯着仪表盘上的时间。“没关系,来得及。”苏均说。他们没能赶上,通道在两分钟前关闭了。失误,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上帝分配给他们俩的时间好像来自不同的宇宙,叶菁菁总是在追赶,另一个却躺在时间里。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能量守恒。
马路湿漉漉的,映着一地的红色车灯。孩子们下车,走进校门,回过头挥手,留给她穿着校服的背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又完全不同的背影。叶菁菁每次都要把他们放在所有的背影中,再从中找出他们,像牧羊人在羊群中一眼认出自己的羊。她经常想大声喊他们回来,告诉他们“妈妈爱你”,再让他们离开。她为自己早晨的急迫感到不安。那种急迫,像校服里子上一道小小的裂缝,需要及时缝补。否则,那个裂缝将跟随她一整天,啮咬她的五脏六腑,直到晚上,孩子们放学回家,她得以拥抱他们,为他们端出精心烹制的食物。阿蛮和阿馋的背影隐没在第一栋教学楼后面,她呼出从起床开始一直提着的一口气,把椅背朝后调整了一些。车窗玻璃上爬满雨水流下的印子,这些蔓延得到处都是的印迹,像鼻涕虫爬过的路径,又像是泪痕,还可以比喻成什么?她虚弱地企图填满脑袋里那道越来越大的裂缝。刚才她替他们关车门的时候,差点儿夹到阿馋的脚——车门已经碰到阿馋的鞋跟了。阿馋一定要在车里先打开伞,不肯沾到一滴雨。她希望他更像一个男子汉,但她用驱赶的方式去实现。真是愚蠢,愚蠢。
高架桥底下两株玉兰开花了,在灰蓝色的天空和黑色的柏油马路之间,洁白、明净、让她脸上发烫。“春天的雨也是明亮的。”她说。她得高兴起来,他们现在去港口吃早茶,她知道苏均眼睛里的光彩和血丝,她不想扫兴。苏均出差凌晨才到家,行李箱放在卧室墙角,生活全部的苟且暂时还锁在那里,他们不着急,甚至有意拖延打开行李箱的时间——还没到时候。三分期待加上七分幻想,再黯淡的日子,别后重逢也还算得上一抹亮色。至少,她得抓住这一点。黎明时分喝下的那杯蜂蜜水,此刻引出一种积极意义的饥饿感,叶菁菁心里热络起来。不管怎样,今天,和昨天不一样。
苏均把车停在巷口对面。隔着落雨的街道,海棠春临街的这面玻璃窗后面,只有一位客人,独自坐在靠窗的桌子旁,面对着一笼包子。入口的自动伞套机坏了,叶菁菁犹豫了一下,收起不太湿的折伞走进去。柜台里的女人说完“欢迎光临”,马上喊人来帮她套伞。
“其实……好吧,谢谢。”她把伞交出去,她总是愿意随遇而安的。
“吃什么?”苏均问。
“嗯……我想喝鱼汤。点一份鱼汤面,你吃面,我喝汤。”
“不,我不想吃面。”他们已经摒弃了那种不够诚实的迁就,但她仍然有些吃惊。
“……嗯,那就不点。”
“可以单点一份鱼汤哦。”老板娘说。
“但是我觉得煮了面的汤更好喝,还是……算了,就来一份鱼汤吧,再加一份烫干丝,谢谢。”
苏均点了包子和豆浆。
他们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子。苏均坐在对面,抽烟,低头看手机。他们来得太早了,早市还没开始。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穿梭着,从厨房一笼一笼搬出冒着热气的蒸笼,店里还是显得冷清,和他们的胃口一样。
“别抽了,在人家店里。”叶菁菁皱眉,避开缭绕的烟雾。
“是的,我们这里禁烟的哦。”给他们送干丝的服务员赔着笑脸说。
“掐了吧。”
“烦不烦啊!”
“一大早就抽烟,到底是谁烦?”
“哎呀,没事,没事啦……”老板娘深谙中庸之道。
叶菁菁不说话了,专心吃早饭。餐桌铺了软胶桌垫,有一两处水迹压在下面。鱼汤有点咸,搭配秧草菌菇包子,总觉得寡淡,安抚不了早春的胃。还是应该点一碗鱼汤面。
小店后窗外面看得到沿江的公园。柳树刚透出一点新绿。前几年的春天,叶菁菁拍过停在梅枝上的喜鹊,喜鹊、梅枝和淡青的天构成了一幅细致淡雅的工笔画,那组照片赢得了很多赞美。那时候,她以为生活就像这组照片,靠着热爱和勤奋,加上一点天赋,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九十分。
“等下,咱们沿着江边走走吧。”叶菁菁对苏均说,这样也许能找回早起的清爽。
“下雨呢……等明天不下雨了再说吧。”
好。她不应该问的。
在经历过那么多次劳心劳力的角逐之后,她终于觉察出自己的执迷不悟。争执毫无意义,现在她更愿意退守。
吃完饭,他们回到车里。雨还在下,暖气开得很足,她陷在座位里,哪儿都不想去,只希望车一直开下去,开下去,没有目的地,只有沿途的风景。生活最好永远和她隔着这道玻璃,留她在倦怠和热爱之间。
结婚前,他们在雨中散步,苏均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最喜欢雨天和你走在一起。那条悠长的梧桐夹道,那片明亮的绿,那场耳热心跳,如今只剩下没有生命的静止画面,植物标本一样留在叶菁菁的回忆里。后来,他们在雨夜发生过争吵,互不相让,她开门冲进雨里,光脚踩在湿冷的水泥路上,那种透骨的寒冷带给她的恐惧曾让她产生怀疑: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事后和俞禾说起,她着意显得轻描淡写,甚至还打了个哈欠:“昨晚和苏均生气,整个晚上都在吵,现在困死了。”俞禾说:“别那么用力,孩子,轻松点儿好吗?”
她是第一次买车的时候认识俞禾的。她对车一无所知,俞禾热情主动,有问必答,她没想到的部分也帮她想到了。头几次上路,叶菁菁肩膀僵硬,紧握方向盘,手心出汗,阿蛮坐在后面,俞禾坐在她右边,身穿黑色套装,散发着“略有辛辣感的木质玫瑰的味道”,适当的时候才开口。当她终于把车停在婴儿游泳馆门口,拉好手刹,转身看俞禾,她们相视而笑的那一刻,叶菁菁想到“奇妙的缘分”这句话。她为自己拥有的友情骄傲。“这是我闺蜜。”俞禾向所有人这样介绍她。她永远记得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背后是下午两点灿烂无比的阳光——露出一口光亮洁白的牙齿。真是个完美无缺的笑。俞禾没有虎牙,后来叶菁菁知道她做过美牙,两侧的虎牙被磨得尖尖的、小小的,套在无可挑剔的烤瓷牙冠下。
俞禾下班约她逛街。她们会坐在街边喝东西,俞禾喝咖啡,叶菁菁喝奶茶。俞禾从来喝不完一杯奶茶,她没办法喜欢那种味道。
“居然有人不爱奶茶?”叶菁菁吸着珍珠,觉得不可思议。而她不敢碰咖啡,会失眠。
“看那个女人。”俞禾把脑袋偏过去,靠着叶菁菁小声说。
叶菁菁看到一个穿着红色开衫、黑色百褶裙的女人正在过马路。吸引俞禾目光的是裙摆下面露出来的半截大红色羊毛打底裤和脚上那双崭新的旅游鞋。
“天呐,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想死。”俞禾拍着自己的脑袋,故意唉声叹气。
叶菁菁摇了摇头,咬着嘴唇笑。还好她们是朋友。她感觉回到了高中时代,大孩子故意做出那些“可恶”的行为——他们坐在教室里,日复一日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位老师,背地里乐此不疲地调侃他们,诸如物理老师“围魏救赵”的发型、英语老师的土味发音,或者只是某位老师走错了教室。他们只是喜欢笑而已。
她们一起发现了几家特别的店铺,成了那儿的忠实客户。那段时间,叶菁菁觉得自己整个人被欲望包裹着,她渴望那些店铺每周的上新,迷恋穿衣镜前全新的自己,偏爱某种材质,但喜欢所有的色彩。她穿着和俞禾一起淘来的衣服,上班、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学习做饭。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幼儿园在大剧院有一场汇报演出,她穿一条黑色镂空曳地长裙——对一场幼儿园内部演出来说,未免过于隆重了些。她没有恰当的场合去匹配这条裙子,也完全没有必要花两千多买一条裙子,但是她买下了它。“腰身收得刚刚好,像为你量身定做的耶。”镜子里俞禾站在她身后说。那时候,苏均给她很多零花钱,他股票投资做得不错,可以说风头正劲,但叶菁菁不是那种乱花钱的女人,远远不是。俞禾买贵重的首饰和包,叶菁菁把钱存进了一张存折。
内衣厚厚的胸垫让她的胸部鼓鼓的,六厘米的鞋跟限制了她走路的速度,她一级一级小心翼翼爬上大剧院的台阶。她记得从她身边走过的其他家长,那些轻快的脚步,也记得她有点骄傲和慌乱的心。她觉得她的自信几乎都源自那些精心搭配的衣服和鞋,有一种暂时性的满足。暂时,这两个字多少藏着她天性里难以逾越的那部分:她不懂得拒絕。她喜欢经常在她耳边响起的赞美声,不管那些赞美有多少来自她的衣服,又有多少来自她本人。赞赏衣服不是也意味着赞赏她的眼光吗?虽然,是她和俞禾的眼光。
有一件丝麻连衣裙,面料像深蓝的湖泊上浮观一轮圆月的影子,清幽、灵动,宛若梦境。“你需要在里面穿一件衬裙。”至少店员是这样理解的。那种薄透,是叶菁菁在卧室穿了被苏均看到也会脸红的薄透。但是俞禾没穿衬裙。走路的时候,宽大的裙身轻轻晃荡,像一种轻柔的舞蹈。俞禾的黑色内衣和凹进去的腰身在那种舞蹈中的大部分时候清晰可见。那天她们在商场,灯火璀璨,人来人往。叶菁菁偶尔走到俞禾的后面,觉得她像一株大丽花,因为害怕错过花期,正在竭力盛放,旁若无人。
苏均找叶菁菁吃饭,遇到她们逛街的日子,当然就三个人一起去。苏均喜欢烤肉,叶菁菁不喜欢,但俞禾喜欢;苏均喜欢吃海鲜,叶菁菁不喜欢,但俞禾也喜欢;叶菁菁想吃路边摊,苏均和俞禾一起摇头。最后,他们还是去吃了烤鱼。坐在夜晚的路边,烧烤摊上刺啦啦冒着白色的烟气。阿蛮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俞禾和苏均的同学郑浩坐在对面。俞禾和苏均分别拿走了最后两串羊肉,苏均开玩笑说,干脆我们俩一起过吧。俞禾大笑,露出好看的白牙。即使在那样的夜晚,她的光芒也没有一点隐藏。叶菁菁羡慕她在各种场合应对自如,换作她是俞禾的话,苏均开玩笑,她也许会不知所措,笑起来也不知道如何收场,她会低头咀嚼那个玩笑,直到它淡而无味,直到她意识到她本人在别人眼中也是一样的淡而无味。俞禾当然不像她一样。俞禾就像她山南水北的另一面,就像苏均,就像被咬掉的那口苹果。叶菁菁乐于看到苏均加入她们,三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紧密快乐的小圈。
阿蛮靠在她怀里睡着了,她得回家放她到小床上睡,可烤鱼刚上桌,她才吃了两口。苏均送她到楼下。他们站在路灯下面,阿蛮长长的睫毛在灯光下轻轻颤动着,叶菁菁不可避免地感到有点委屈。后来,苏均给她重新点了一份烤鱼带回来,郑浩和俞禾也一起上来,他们决定玩扑克牌。
“你家男人居然给你重新点了一份,真是的。”俞禾倚在门框上,眼神迷离,好像喝醉了。虽然他们谁都没有喝酒。
“那你还不赶紧找一个男朋友。”叶菁菁的那点委屈全部消散。
他们今天叫上郑浩的意思,四个人都心知肚明。郑浩一直在跟俞禾说话,俞禾也很配合,两个人看起来很投机。但是俞禾事后说没什么感觉。
“那你们聊得那么欢?”叶菁菁说。
“朋友嘛,多一个朋友不好吗?”
是,多多益善。如果是她,她会少说几句。但俞禾不是她。叶菁菁叹息了一声,不知道是为郑浩,还是为俞禾。
后来,叶菁菁第二次怀孕。这个生命来得计划之外,生活再次将她抛向令人晕眩的半空。她吐得厉害,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最后不得不请假去医院输营养液——那种白色的牛乳一样的液体。阿蛮被暂时送去奶奶家。苏均每天上午来医院看她,按照他平常晚睡晚起的作息,他这些天里起得很早。他常常在值班医生离开之后,护士来输液之前,从医院西边的一个偏门进来,不用经过住院部大厅。他总是很困,倒在叶菁菁病床上,和她挤在一起,几句话之后就睡着了,直到护士推着药品车进来,把他从床上轰走。“睡在妇产科病床上的男人。”叶菁菁把这当作笑话讲给俞禾听,她们一起嘲笑苏均。
那天早晨,苏均没有来。也许他熬了通宵,支撑不住睡着了。叶菁菁输完营养液坐电动三轮车回家(那时候,电动三轮车通常歇在商场、公园和医院门口这些地方“守株待兔”,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她决定给自己和苏均放个假。在医院躺了十几天,她感觉好多了。医生说如果她感觉可以,下周一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她在路边那棵银杏树下下车。俞禾挽着阿蛮的手站在社区出口处的拱形门洞前面。俞禾弯腰和阿蛮说话,风吹动她米黄色的碎花裙,裸露的脖颈在阳光下泛着白光。她们没注意到她。苏均的车从车库出来,在她们身边停下,他摇下车窗,把手臂搁在窗口。他和俞禾都没有说话,有几秒钟,时间仿佛静止了。之后俞禾打开后车门,抱阿蛮坐进去,扣好儿童座椅的安全带,关上车门,绕到前面,打开前排副驾驶的门,身体滑进去。她做着这一切,温柔、平和、坚定,好像她才是阿蛮的妈妈。“她比我做得好。”叶菁菁好像在观摩一堂亲子课程,怀着羞愧。只是她不知道,为什么苏均没有说话?他把手臂搁在那儿的姿势为什么让她感觉心痛?为什么俞禾也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儿?她不太明白他们用什么填满其中的空白。或者,他们也不知道?有一些静止的时刻在你的生命中,永远无法被填满,但你如何安放这些时刻?车朝着医院的方向驶去,他们没有看见她。她转身,手扶着银杏树,呕吐感再次袭来。那个瞬间,她发现她在想念住了十几天的病房,那白色的一切。原来银杏树的树干有那么多粗糙的裂纹,布满整个树身。
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买白色内衣的。她渐渐把抽屉里的内衣全部换成了白色,没有蝴蝶结,没有蕾丝花边,没有一点多余的点缀,只是棉布原本的白。午睡前,她脱掉牛仔裙,只穿白色的内衣,站在卫生间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镜子里的身体。怀孕前三个月,她的小腹还是平的——阿蛮只给她的肚子添了一条浅色的竖线,在肚脐下面,几乎看不出——乳房却开始饱满。怀孕是一种煎熬,却也可能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最好的时候。苏均推门进来,等一下他要出差,他说,过几天就回来。他们的欲望开始得并不相同,结局却前所未有地一致。他们是那么地忘乎所以。年轻的爱几乎等同于占有。不,她不想讲道理,只想要完完全全地拥有。就像现在,她双手环在苏均的腰上,胸口的黏湿让她觉得幸福和羞耻。她选择无视那种羞耻,她在选择。然后,她感觉肚子疼了一下,之后又一下,是某种违背她意志的间歇的疼痛,她爬起来,看见床单染上的颜色。她被吓住了,在夏天的午后,忍不住战栗起来。
苏均搂着她的肩膀站在电梯口,他们唯一能做的是立即去医院。她的牙齿咯咯地响,无法阻止。
孩子没事,谢天谢地。当然,医生告诫了他们,温和地,在她垂落的目光对面。她向公司申请到延长休假,跟着苏均出过几次差。最长的那次,他们坐火车去四川。车窗外接连出现长长的隧道、豁然开朗的绿色山谷、流经山谷的溪流,和溪流中散布的大大小小的巖石。水草丰美,一些她从未见过的鸟停在溪水中间,埋下脑袋啄食它们的猎物,尾羽优美地指向大山深处。她发现她没办法说出心中的疑惑。她要怎么提起呢,问苏均“不说话的时候你们在想什么”吗?说到底,那一切不过是她的直觉,只有她肯相信、她肯承认的直觉而已。令她痛苦的是,它并不明朗。只能让它悬而未决,并在之后她毫无防备的任何时刻,跳出来,摇晃流经她眼前的景致,她对苏均的信任、对俞禾的依赖。
崩塌在崩塌之前就开始了。
鱼汤面和雨中的梅枝,只在她心里叹息了一下。车不可避免地驶向目的地,停在菜市场门前。她不可避免地下车,走进那个喧闹纷繁的世界。苏均为她打起门上的帘子。以前有个刻薄的同事说,苏均看起来像她的司机。是的,那是在她还没学会开车,以及接连怀孕、生子、照顾宝宝的那几年。他总是充当司机,殷勤、机敏、擅长倒车,带她出入各种地方。她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在那种信任中丢失了自我。后来,也许是因为俞禾,她一点一点打捞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喜好,站远一点审视她和苏均的关系,不再害怕离别,亲手打造他们的生活。阿馋比姐姐乖巧,阿姨和他们磨合得很好。他们拥有几乎完美的周末和假期。常常她走在晴朗的天气里,抬头看见蓝天映着绿树,轻风就填满了心间。有时她会感到过于幸福,甚至为自己拥有的幸福感到害怕。就在她以为一切已步入正轨,渐入佳境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那几乎像一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一切。
她甚至不太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她拿出自己的存折交给苏均,像之前一样。他会还给她,连本带利,虽然她不在乎——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共有的,不需要分那么清楚。但这次不一样,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苏均已经一筹莫展了。唯一确定的是,这又是一次可以避免的失误,又一次。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不是在机场附近睡一夜,听着飞机起落的噪声难以入眠就可以过去的。他没有及时收手,在决定他们所有人命运的那个时刻,他彻底忘了他们——她和孩子们。
因为急于出手,他们以一个荒唐的价格卖掉市中心的大房子。夏天下了几场暴雨,她忘记关天窗,在俞禾那儿买的那辆车泡了水,他们也处理掉了。他们几乎告别了原有的一切,搬到汉北镇。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她离开,也许丢下孩子,也许只带走女儿,就像许多和她拥有类似遭遇的女人所做的选择一样。“及时止损”,他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好像婚姻从来就只是一桩交易。她没有离开,虽然她的确看见自己一步一步踏入生活更阴暗潮湿的地底,命运的绳索紧了又紧。她开始记录一些感受,在书中用记号笔勾住一些句子,用这些方式抓住点儿什么,安抚内心的惊讶,承认他们的现状。不管怎样,她就是没有离开。至少暂时没有。
“你会看到极大的痛苦,并且会在这种痛苦中得到幸福。”她把这句话摘录在手机备忘录里,但没有注明出处。
上次见俞禾差不多是一年前。她们再也没有去逛街,她们早已过了那种试探的年纪。她知道俞禾开始收敛心性,计划性地存钱,偶尔出去旅行,不再四处结识朋友,买了第一套房子。她没有透露自己的全部现状,不想求助任何人。“不好不坏,还是那样。”她说,她们都真的长大了,不是吗?
菜市场的鱼今天特别新鲜。一尾鲈鱼从卖鱼女人手中的网兜跳进隔壁鳊鱼的水箱里,哗啦啦溅起一大片水花,鱼档外面的叶菁菁往后退了几步,她从不知道一条鱼奋力跳起来可以那么高,真是条优美的抛物线。卖鱼女人用力呸了一声,吐掉嘴里的泡沫,骂了句“你妈的!”操起网兜重又舀出一条鱼来,扔到东边水迹斑斑的案板上。汉北镇这里杀鱼杀得潦草,身穿黑色皮围裙的鱼贩子手脚麻利得像开了二倍速,开膛破肚,三下五除二处理好叶菁菁要的鱼,装进白色塑料袋,外面再套一个绿色的袋子,递给她。
叶菁菁把装鱼的袋子放在脚下,苏均重新发动汽车。现在是上午九点,她可以下午再去公司,这是她半离职状态下的福利。他们刚转过路口那株盛大的樱花树,叶菁菁还迷离在樱花的粉色云雾中,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动吓了她一跳。响动就在靠近耳膜的地方,看不见,但充斥着不祥的意味,愈来愈强烈。恐惧攫住了她,叶菁菁捂住耳朵尖叫起来。在尖叫的余音里,她渐渐明白了动静来自脚下的鱼袋。她闭上眼睛,叫苏均赶紧挪走袋子,赶紧。片刻安静之后,那条鱼又剧烈挣扎起来,叶菁菁再次紧紧捂住耳朵。她不吃鱼了,再也不吃了。她大声说话,坐直身体,不靠近任何地方,但她无法减弱鱼的垂死挣扎。左边的太阳穴在跳动,疼得厉害。她不能忍受一条鱼大声宣告给她的痛苦,在那种拼尽全力的响动里,她体味到鱼的全部惊恐。
他们的房门关着,像一条封闭的通道。白色的门上应该贴着“此路不通”,但没有指明“请绕道行驶”的方向。她不用推门进去就知道,苏均戴着耳机躺在床上。他在努力工作,与此同时,越来越沉默。干完自己那部分家务,也就是叶菁菁分派给他的那部分,他就回房间,关上房门,用手机填满睡觉之前的时间。经历了那加速崩塌的一切之后,他似乎害怕一切琐碎的事物。她不喜欢命令别人,某种程度上,她乐于在他近旁忙碌,仿佛他的状态对她是一种有益的指示。所以她有做不完的事。距离房间几步之遥,可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进去,躺在床上,看几页书或半部电影,之后沉入对她来说有如故乡的睡眠。她永无止境地忙碌,收获一种如愿前的满足。
叶菁菁端出给阿蛮准备的夜宵。今天周三,是老师发布周练成绩的日子。下午在便利店,老师正好发来消息,付款之前她点开图片看了一眼,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让她不得不用手撑住柜台。她竭力微笑着结完账。在搬家之前,阿蛮的成绩本来很好。她提醒自己:你不可能因为这个就倒下。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不是吗?你经历了那么多,你还要经历更多。现在女儿坐在对面,大口吃着她从饭店打包来的鱼粥,青春期的孩子整天喊着减肥,但从不肯少吃一口。她隐忍不提那个用红色记号笔圈过的分数,嘱咐女儿抓紧吃完去学习。时间,时间,时间,她总是在催促,总是死乞白赖地抓住时间的衣角,试图替她的孩子攥紧,然后眼看着光阴一寸一寸从阿蛮指间溜走,像出逃的鱼。
阿馋穿睡衣光脚从房间跑出来,嚷着要吃卤蛋。姐姐高高端起盘子说:“去去去,你个小屁孩该睡觉去了,不许你吃。”
“妈——妈,你看姐姐。”
叶菁菁在厨房,她不想说话。接阿蛮放学之前,她已经和阿馋费了足够多的口舌。磕磕绊绊写完作业,还有一首古诗需要背诵,她的耐心几乎耗尽。已经这么晚了,水流的声音、阿蛮挑事的笑声、儿子急恼的叫声、房间里隐隐传来的手机外放的声音,在她脑中嗡嗡织成缠绕不去的魔咒。小腹也在隐隐作痛,生理期大概要来了,这次比上次来得早还是晚?她不知道。一切都偏离了轨道。在剥离理智的想象里,她已经用力摔了手中的碗,熄掉了一切声响和光亮。
苏均穿着羊绒衫躺在被子里,手机掉在枕头旁边。叶菁菁摁手机侧键,直播间那种喋喋不休的声音,隔着黑掉的屏幕,更加怪异和刺耳。她扑灭火苗一样连摁了好几下,手机终于闭嘴了。看着丈夫睡熟的样子,那张脸寡淡似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这种时候,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换取他的清醒。她需要他醒着,看着她,和她说话。她那样摇晃他的肩膀,那样急切地在他耳边喊他的名字,像在喊救命一样。苏均蓦地坐起身,睁开眼睛,他说:“那边,还差一个人。”说完又躺倒在枕头上。他只是在说梦话。她喊不醒他。一种荒芜从他闭合的眼睑处弥漫开,漫过站在床头的叶菁菁,淹没整个房间。旋风般的战栗侵袭了她,由皮肤渗入血液,瞬间流过全身,最后在心脏上方收拢。她觉得冷,抱紧胳膊蹲下来。那整个的荒芜再也不能结束。她没有力气站起来,她需要力量,来自拥抱,或者争吵,或者眼泪。她宁愿摆在她眼前的,是苏均和俞禾带给她的那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道裂缝。
她脱掉衣服,钻进被子,贴着苏均躺下。如果什么都得不到,至少她得采集一点体温过夜。髋骨在旧床垫上硌得生疼,她转过身,平躺着。方正的天花板,圆形的吸顶灯,引不起一丝遐想。她想开灯,但夜晚不是太黑,就是太亮。她再次转动身体,弓起背抵着苏均的胸膛,让自己面对着空荡的房间,而不是丈夫的呼吸。去年夏天那次摔跤之后,她的腿伤一直没有好,那个受伤的部位挑剔她每一个侧卧的姿势。苏均咕哝了一句,把他的手臂伸过来,等着叶菁菁抬起头,枕到他的胳膊上,他们曾经习惯这个姿势。但现在不行,叶菁菁用力推开他,在他们中间掖好被子,用被子隔出一条界线。她让自己保持那个姿势,接受那种不适。睡眠也变得陌生。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不确定。在迈进四十岁之前,叶菁菁仿佛已被生活架空了。最先来临的危机是失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十五年之后,被领导叫去办公室。领导的话委婉、诚恳,但毫无转圜,鼓槌在她心里大声落下去。她可以待到找到新工作之前,但不能太久。所有的招聘信息都在说,三十五岁以下。三十五岁,此前她从未想到人们会赋予一个数字如此大的使命。她原本已经不去记自己的年龄了。谁知道,这么快她就不得不承认:她再也不年轻了。
她不知道,一直弄不清楚,是女儿讲话的声音越来越低,还是她的听力出了什么问题;她买的衣服、鞋子,她做的饭菜,全都不对。她好像生活在一个弥天阴谋之中,常常觉得晕头转向。那次他们去看电影,离开场时间只剩几分钟,她和苏均不得不分头行动,苏均领着孩子们进影厅,她去一楼取线上预约的咖啡。队伍很长,店员慢条斯理,她不得不按捺住自己稳稳站在队伍中间。她想着也许要错过的序幕,拎着咖啡踏上自动扶梯。但是她上不去,反复几次还是跟不上扶梯的速度。差点摔倒之后她才发现,她踏上的是下行的扶梯。天呐,她在干什么?她脑袋嗡嗡、满脸涨红。电影院就在二楼,但她像个被时代落下的老太太,在茫茫人海中失去了依傍。序幕是肯定错过了,她想哭。
她现在的哭泣很奇怪,总是发生在大笑之后。她看喜剧电影、看脱口秀或者一些逗趣视频,她喜歡的主题是猫和人类幼崽。笑得肚子疼,笑得直不起腰,扶着桌角,然后,她抬起头,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她想象自己像漫画里大哭的孩子,眼泪飞出眼角,完全忽视地心引力的存在。她为这种哭泣感到抱歉。为了避免尴尬,有时候她不得不克制,克制的时间久了,她渐渐地不会大笑。现在,她虔诚地信仰平和,就像她从前信仰爱。
无动于衷,的确是某种幸福。
在她独自睡去的梦里,她一脚踏进一部破旧不堪的电梯。那部电梯像铁皮火车的车厢,逼仄、昏暗,同时又大而无当。地板上到处看得见裂缝。最大的那道裂缝,可以掉进去人的两只脚,她不得不岔开双腿站在里面。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她跟随电梯跌跌撞撞地上升、下降,抓紧随身携带的几件工具,在黑暗的颠簸中感受手指用力捏紧硬物的疼痛,等待有人在一楼按下按钮。她相信,终会有人需要并且按下这部电梯,在此之前,她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
闹钟响的时候,她感激地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床上,外面是平平无奇的阴天,一切都喑哑无光。她突然开始想念,疯狂地想抓住什么人,对她讲述她的梦。她拿起电话。
“孩子,周末下午,我们在老地方约,巷子口那家咖啡馆。别忘了。”俞禾在电话里说。
责任编辑 申宇君
作者简介:
子衿,本名毛艳艳,现居江苏。自由职业者,发表小说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