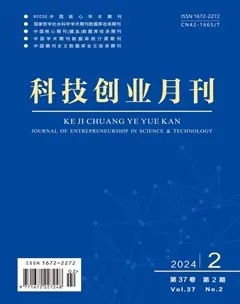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治理路径
2024-03-25李胜利汪靓
李胜利 汪靓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法的新发展”(SK2021ZD0001)
作者简介:李胜利(1972-),男,博士,安徽大学法学院暨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竞争法;汪靓(1998-),女,安徽大学法学院暨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竞争法。
摘 要:大型数字平台为强化市场力量、消除潜在竞争,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频繁进行扼杀式并购活动。“切香肠式”的扼杀式并购短期内不会引起市场结构的显著变化,但从长远来看,对数字市场公平竞争、产品创新以及消费者福利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在我国,反垄断法对扼杀式并购的防范、识别和事后监管均面临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结合数字经济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同时在秉持“包容审慎”理念之下调整监管思路,多措并举,实现对数字平台的长效监管,保障数字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数字平台;初创企业;扼杀式并购;经营者集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08075
The Anti-monopoly Governance Path of Large Digital Platform Strangl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Li Shengli, Wang Liang
(Law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英文摘要Abstract:In order to strengthen market forces and eliminate potential competition, large digital platforms frequently carry out strangl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virtue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other advantages.“Sausage-cutting” strangl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ll not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market structure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run, they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market,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welfare. In China, the anti-monopoly law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he prevention, identification and post-supervision of strangl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view of this,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tifl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adjust the regulatory think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and prudent”,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long-term supervis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ensure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Digital Platform; Start-Up; Killing Acquisition; Concentration
0 引言
互聯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数字平台已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大型数字平台凭借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业务遍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力量不断被强化,跨界竞争愈演愈烈,极易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
回首全球互联网巨头近年来实施的并购交易,1998-2020年,亚马逊和苹果分别收购了104家、120家企业;谷歌在2001-2020年收购了256家企业,脸书在2007-2020年共收购86家企业,其中脸书在并购后关闭了将近一半的企业,亚马逊和谷歌以未能达到预设提质增效为由关停部分企业[1],在脸书实施的并购交易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其行为具有垄断性质,目的是扼杀竞争对手。自2017年起国内也形成了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首的数字巨头,它们在2020-2021年间投资和并购事件高达395起,覆盖多个领域。在对外收购企业方面,阿里巴巴花费273亿美元并购10家公司,腾讯花费137.94亿美元并购10家公司[2],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形成类似托拉斯式组织。时至今日,全球大型数字平台并购势头依旧迅猛,但我国在《“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中提出要完善线上市场监管体系,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加强对新业态市场秩序监管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加强对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监管,防范其可能造成的竞争损害。
1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特征
厘清扼杀式并购特征能够有效规制此类行为,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2018年,制药行业的三位学者柯林·坎宁安(Colleen Cunningham)等在进行实证研究中提出扼杀式并购这一概念[3]。随后该概念被应用到数字经济领域审查并购交易,若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在业务范围内具有互补性,并购方在完成并购后将会通过优质项目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基于潜在竞争对手损害理论,该行为被称为包围型扼杀式并购;如果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在业务范围内存在重叠,并购方在完成并购后冷冻初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此彻底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基于杀手并购损害理论,该行为被称为终止型扼杀式并购。
相较传统企业实施的并购,数字经济领域扼杀式并购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实施扼杀式并购的主体多为财力雄厚、资源丰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第二,被并购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成立时间较短的初创企业,英国里尔报告(Lear Report)曾指出在以GAFA和微软为首的并购交易中,其中有60%被收购企业为初创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4年,具有潜力的年轻型公司更易受到大型数字平台的青睐[4]。第三,因为被并购对象在产品或服务上与大型数字平台往往存在相似或重叠,易产生竞争威胁,故扼杀式并购的目的是消灭现存及潜在竞争对手,从而保持自身优势地位。随着扼杀式并购的不断深入,数字市场极易形成杀伤区(Killing Zone),OECD曾在报告中指出“杀伤区”是大型数字平台控制的产品投放空间,以管理人身份对具有价值的产品大肆复制,引导消费者转向自身相似产品,对原始产品造成极大杀伤力,同时给后续初创企业建立市场进入壁垒[5]。
2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动因
大型数字平台通过扼杀式并购实现跨领域发展,市场力量得到强化,但从长远来看,该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创新发展和消费者福利均带来巨大冲击。
2.1 损害市场竞争
一方面,大型数字平台依托强大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技术,实施扼杀式并购时对目标企业的人才、技术、数据、知识产权进行一系列分析和优势传导,若目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自身业务相同或近似,在并购完成后将会直接终止目标企业;若目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自身业务能够互补,则会在并购完成后将核心技术纳入自身业务范围。主导平台产品或服务输出效率大大提升,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上实现快速发展,对相关市场产生封锁效应,提高市场进入壁垒,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另一方面,大型数字平台的跨领域发展和雄厚的资本,导致一些投资者畏惧初创企业不确定的回报率放弃投资,资金链断裂,构成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最终不得不投靠大型数字平台。纵然如此,大型数字平台也会将自己的并购之手伸向与之不存在竞争关系的初创企业,以防止此类初创企业被自己的竞争对手收购。大型数字平台在实施扼杀式并购时,通过减少相关市场中的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进而实现自身的垄断地位,破坏市场有序竞争格局。
2.2 阻碍创新发展
一方面,大型数字平台通过并购初创企业获得潜在项目的研发控制权,极大降低了大型数字平台自主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大型数字平台因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高端技术人员,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与其费时费力去自主创新,不如对初创企业直接进行“吞噬”或者“攫取”核心技术和产品,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继而主导平台以扼杀式并购为捷径减少创新激励。
另一方面,初创企业一般会选择自己专长为研究方向,谋求在某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囿于有限的研发资金和未来可能被大型数字企业并购的风险,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初创企业往往会去迎合数字巨头的需求,在数字巨头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创新,创新路线逐渐变窄,产品或服务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减少。
2.3 减损消费者福利
反垄断法立法宗旨就是保障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以最优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服务和产品。但大型数字平台实施的扼杀式并购与此背道而驰,直接导致消费者福利受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压缩消费者选择空间。大型数字平台的扼杀式并购多数会将被并购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消灭或永久封存,导致数字市场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降低,消费者选择空间受限。
第二,增加消费者支出成本。主导平台通过扼杀式并购在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上掌握了主动权,通过提高定价或者降低质量使自身利润最大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囿于产品或服务多样性减少,不得不为此支付不合理的价格以享受服务和获得产品,变相提高了消费者的支出成本。
第三,加大消费者隐私泄露风险。大型数字平台通过扼杀式并购获得初创企业的大量用户数据,并且进行数据流量变现保证自身对数据的控制权。通过算法推荐模式分析消费者偏好,进行用户画像,实现精准广告推送及大数据杀熟,攫取消费者利润。尤其在电商行业,用户数据往往涉及到消费者身份信息、支付信息等,并购双方的数据流通可能给一些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若主导平台没有强大的数据防御系统,消费者的隐私将被置于危险境地。
3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反垄断规制面临的困境
誠如前述,扼杀式并购加剧了市场集中度,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然而现行《反垄断法》用于数字经济领域并购交易审查存在不适应性,对扼杀式并购未能进行有效规制,主要表现为审查标准单一、竞争损害分析难有定论、事后干预力度不足。
3.1 营业额标准具有单一性
目前,我国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在《反垄断法》第26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有所提及,主要采取的是达到营业额标准的强制申报和未达到营业额标准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调查两种并购申报审查方式[6]。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传统实体经济中,企业市场力量的衡量标准主要通过营业额来评估。虽然营业额标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审查方式,但是放置在数字经济之下,此标准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固有弊端。
在数字经济领域,对于大多数初创企业而言,前期主要是靠优质产品和服务“引流”积累用户数据,营收很难达到4亿元的申报门槛,而大型数字平台在实施并购时,平台经营者往往会在平台的一边采取免费定价或补贴模式,几乎没有任何营业额。在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时,这些企业会因营业额未达申报标准而免于审查,顺利实现并购。然而低营收并不代表该初创企业不具有市场竞争力,若一味地以营业额为申报标准,极有可能造成“假阴性错误”,从而引发大型数字平台滥用行为。而且在数字市场中,单一的营业额标准掩盖了初创企业所拥有的的巨大市场竞争力以及忽视了大型数字平台实施扼杀式并购的垄断动机,该标准在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失灵。此外,《反垄断法》规定对于未达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若有证据证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求经营者申报,未申报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法主动调查,虽然此举可以作为营业额标准的补救措施,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效果并不显著,仍有一些经营者集中案件游离于监管之外。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应固守原有营业额标准,应有所突破,方能实现数字市场的长足发展。
3.2 竞争效应评估难有定论
审查扼杀式并购的关键在于对竞争损害的评估,即使达到申报标准进入审查程序,最终也会因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而搁置。数字经济之下唯静态因素分析方法失灵和举证责任分配失衡是导致竞争效应评估难有定论的主要原因。
3.2.1 唯静态因素分析方法失灵
一方面,在传统企业中以价格作为竞争损害的考量因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在数字经济领域,初创企业为积累用户流量,往往会牺牲营业额采取免费定价模式,因此价格未能准确评估大型数字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是否造成竞争损害,若仍循规守旧,极有可能造成“假阴性错误”。如在“3Q大战”案件中,主审法官认识到价格不是该经营者竞争的主要手段。是故,扼杀式并购的竞争损害不应唯价格论,否则会造成“假阴性错误”。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之下,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格局呈动态发展。对初创企业而言,若没有大型数字平台的肆意干扰,通过不断创新、技术迭代升级极有可能收获大批投资者的青睐,从而在相关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初创企业的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及合适的契机。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特征、市场份额等皆不确定,很难预测初创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如饱受关注的滴滴并购优步和浙江融信收购恒生电子案,至今没有任何关于该案件调查信息的报道,是否会产生竞争损害无从知晓。因此传统的静态竞争分析方法未能准确预测今天的并购对明天的市场竞争的影响,此类分析方法存在短视风险,难以有效顾及扼杀式并购对数字市场长期的竞争影响。
3.2.2 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集中审查采取效果分析法,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承担并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证明责任,需要搜集与此相关的各种信息资料甚至企业内部文件。由于大型数字平台凭借强大的数据搜集分析能力,构建“情报系统”“预警系统”对潜在竞争者进行追踪和锁定[7],对并购造成竞争损害的资料进行销毁隐匿。基于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时难以获取关键证据,造成信息不对称,很难判定大型数字平台实施并购的目的和动机以及完成并购的企业是否真的不会造成竞争损害。同时在当前执法资源有限的境况下,如何合理分配资源实现动态监管均是规制扼杀式并购应当考虑的问题。
3.2.3 事后干预不足
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单一以及竞争损害评估难有定论导致执法机构未能识别出所有的扼杀式并购,在事前审查缺位的情况下,事后干预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意义重大。然而我国在扼杀式并购事后干预方面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事后干预的范围有限。虽然《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4条和《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9条、第20条,均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享有对未达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事后调查权,但这只是针对那些应申报而未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拥有事后调查权,对于经批准和免于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未赋予此项权能。第二,反垄断执法机构事后干预的主动性不足。如针对某两大集团实施的40多起并购交易均未启动事后调查。此外执法资源匮乏也是导致执法机构迟迟不进行事后调查的原因之一。第三,我国对扼杀式并购事后调查多表现为程序性调查,未能准确评估并购对竞争的影响。
4 我国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治理路径
上述分析表明,数字平台的快速成長和扩张打破了传统的竞争格局和秩序,对于损害市场竞争秩序的扼杀式并购,现行的反垄断法和相关规定难以有效规制。应对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这一挑战,我国应结合域外新发展和本土国情,在“包容审慎”理念之下适当加强对扼杀式并购的监管力度,既能降低执法错误成本,又能深入贯彻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理念,打破市场进入壁垒,防止内幕交易,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4.1 增设交易额标准
申报标准之于行政资源有效利用和防范扼杀式并购具有重大意义。以营业额为申报标准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单一性,容易造成“假阴性错误”,不能有效回应数字平台并购的新变化、新问题。曾有学者指出,在瞬息万变的数字市场,营业额未能适时而变,难以预测特定行业特征和发展趋势[8],也有学者提出将营业额标准降低,但这会导致更多的并购交易落入申报范围,大大增加了执法机构的负担。基于此,增设交易额作为辅助标准,不仅迎合了数字经济的特点还从源头对扼杀式并购行为进行防范。
交易额标准不基于企业现有的实力,而以并购交易背后所产生的潜在价值为着眼点。扼杀式并购具有估值溢价特征,高溢价表明了初创企业的潜在价值,而且交易额还反映出并购后主导平台可获得的未来收益以及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带来的垄断租金。因此,增设交易额这一辅助标准相当于进行了事前申报的二次筛选,可以提前将此纳入重点审查范围,有效防止其逃逸审查程序实现并购交易。其中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九次修订引入若交易对价达到4亿欧元,数字平台就须向有关机构进行并购申报;奥地利在其竞争法修正案中也引入若交易额达到2亿欧元,参与并购的企业负有申报的义务[9]。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实践表明,引入交易阈值并未过度增加执法机构的行政成本及数字平台的合规成本。引入交易额标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修订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我国国情,在确定交易额标准的数额时,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治理市场失灵与不干扰市场机制之间寻求平衡点[10]。
4.2 完善竞争效应评估以识别扼杀式并购
4.2.1 综合分析非价格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平台企业的“心脏”,推动着企业向前发展和保持市场活力。《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明确说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掌握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是评估市场控制力时可以参考的一个因素。欧盟在《数字市场法案》的建议稿中,要求“守门人”对集中后活跃用户数超过一定标准的核心平台服务向欧盟委员会进行报告[11]。因此,在竞争损害效应分析中引入数据与隐私保护这一指标,可以弥补静态因素评估的缺陷,同时提高企业数据合规意识,保障消费者信息安全,及时识别扼杀式并购。在具体适用该标准时,应重点关注并购各方的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用户的注意力、基于数据处理的商业模式和营利情况、隐私保护水平等因素。如谷歌并购Fitbit案,有了脸书并购瓦次普的前车之鉴,欧盟委员会充分考虑了隐私保护问题,要求谷歌承诺将Fitbit用户数据与用于广告的谷歌数据分开存储以及谷歌须确保用户能够有效地选择是否允许其他谷歌服务使用用户存储在谷歌账户或Fitbit账户中的健康数据[12]。由于互联网经济中大多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在竞争损害效应评估中可以引入创新因素,与静态的价格、消费者福利因素并行不悖。根据并购对创新是否有损害进而识别此交易是否存在扼杀性质。因此,在竞争效应分析中引入数据和隐私保护、创新非价格因素能够实现并购双方共赢且消费者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符合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
4.2.2 调整证据规则
如前所述,执法机构在规制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时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取证难等一系列困难,在实践中对证据收集和证明责任分配予以完善,能够有效提高反垄断监管的准确性和效率。
证据收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考虑:一方面,在过往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件中,平台方对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信息资料予以封存或销毁,导致执法机构缺失关键证据。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可以比照域外实践经验,在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特殊情况下实施技术调查与突击检查,防止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执法机构可以借鉴民诉法中的证据开示制度,要求实施并购的平台企业主动披露并购的相关资料,若有拒绝披露或者隐匿销毁行为,将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如果将竞争损害的证明责任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主导平台共同承担,则能减轻执法机构的举证负担。在处理经营者集中案件时,需要去厘清相关市场、进行竞争损害分析、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在此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的证据进行支撑。其中美国在《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中完全免除了执法机构的证明责任,由平台方举证证明并购不会引起市场高度集中和竞争损害。日本《提升特定数字平台透明度和公平性法案》将“特定数字平台”作为规制对象[13]。在此背景之下,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立法思路,对数字平台采取“特别化规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从数据管理、反垄断、公平竞争示范、消费者保护多角度落实互联网主体责任。转移竞争损害证明责任是要求部分头部数字企业承担举证义务,否则会加重所有数字平台企业的合规负担,是故,应当从多维度考虑要求数字平台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实现市场竞争与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站在监管者的角度而言,可以比照民诉法中的举证责任缓和制度,即适当降低一般证明标准的上限,在特定情形下只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竞争损害达到最低证明标准,此项并购行为可能存在反竞争效应,执法机构可以对此作出附条件批准或者禁止批准的决定。
4.3 完善事后调查权
《美国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指出,对大型数字平台实施的扼杀式并购要秉持早监管、长监管、强监管的原则[14],在我国也应当借鉴此原则,不仅要强化事前监管力度,还应当完善事后调查权。完善事后调查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由于数字经济处于动态变化,在并购之时不会产生竞争损害,但是不能确保在并购完成后也不会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故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扩大事后调查权的适用范围。第二,调动反垄断执法机构事后干预的主动性。对已经完成的并购案件进行追溯,发挥反垄断法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使事后调查权应当充分利用有限的执法资源,如互联网平台曾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借鉴此项举措,对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分类分级,即分为严格监管、一般监管、简易监管的案件,实现执法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第三,构建实质性审查机制。实质性审查虽然耗时长,但它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后调查中可以借鉴美国的“潜在竞争损害理论”来评估并购是否破坏了市场竞争格局,若被并购的对象在未来可能成为并购方的强劲竞争者,则该项交易具有扼杀性质。
5 结语
大型数字平台对初创企业的扼杀式并购,损害了数字经济市场的竞争秩序和创新发展。波斯纳曾说过:“反垄断法永远是当代的。”故反垄断法应顺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积极应对。面对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带来的挑战,我国反垄断法应结合数字经济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实体和程序双管齐下,通过增设申报标准以防范扼杀式并购、完善竞争效应评估以识别扼杀式并购、加强事后监管以威慑扼杀式并购。从法治层面优化营商环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实现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数字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标。
参考文献:
[1] 孫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J].新华文摘, 2021(21):5-8.
[2] 王晓晔.浅论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监管[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21(2):10-13.
[3] 方翔.数字市场初创企业并购的竞争隐忧与应对方略[J].法治研究,2021(2):140-143.
[4] 韩伟,高雅洁.英国2019年《数字市场合并控制执法事后评估》报告[J].竞争政策研究, 2019(3):11-14.
[5] 王先林,曹汇.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三个关键问题[J].探索与争鸣,2021(9):54-65.
[6] 仲春.数字经济平台相关市场界定研究[J].法治研究, 2023(2):15-17.
[7] STUCKE M E. Should webe concerned about data-opolies? [J]. 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2018(2):275-324.
[8] 仲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检视与完善[J].法学评论, 2021, 39(4):11-13.
[9] 周万里.《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第九次修订[J].德国研究,2018(4):78-89.
[10] 王伟.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J].中外法学, 2022, 34(1):99-103.
[11] 王煜婷.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经营者集中制度的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2(1):161-165.
[12] 赵丰.欧盟数据驱动型企业扼杀式并购的监管发展及启示[J].电子政务,2022(5):36-38.
[13] 郭传凯.超级平台企业滥用市场力量行为的法律规制——一种专门性规制的路径[J].法商研究, 2022, 39(6):13-18.
[14] 陈兵.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J].法学, 2020(2):26-28.
(责任编辑:吴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