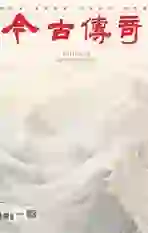大山儿童生活的诗意书写
2024-03-22庄桂成魏亚枫
庄桂成 魏亚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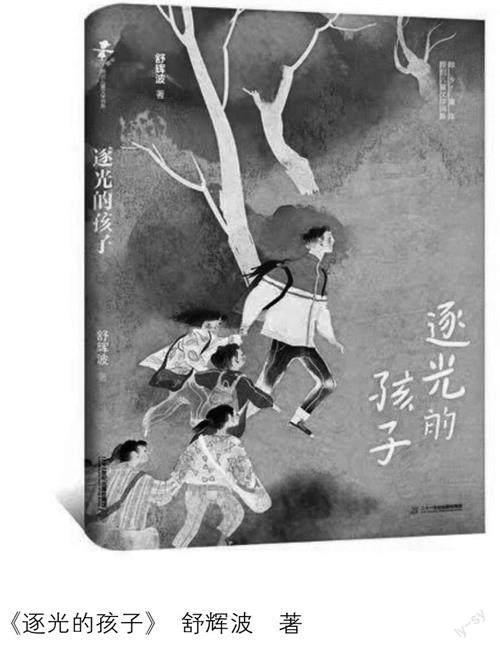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榜单”揭晓,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逐光的孩子》入选。作为一部围绕支教活动展开叙述的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的长篇小说《逐光的孩子》打破了众多读者对这一题材作品的刻板印象,作者以温暖舒缓的笔触将大山深处的自然风光描绘得如诗如画,而充满诗意的语言又将读者从轻松愉悦的阅读中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思考。《逐光的孩子》的出版不仅让更多的人关注山村儿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需求,同时也有助于让各个阶段的读者摒弃浮躁与喧嚣,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寻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一、以“温情”奠定全书主基调
在《逐光的孩子》这部小说中,没有外来文化与山村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没有人际交往中的算计猜疑和利益争夺。通读整部小说,没有一位令人深恶痛绝的人物形象。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也极少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与隔阂。即使是曾经想要拐卖郑天齐的“胖叔”,也是由于一些难以言说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怀着不轨之心将郑天齐带往武汉,但胖叔在途中对他颇为照顾,而且在发财致富之后也不忘回报家乡。而对于郑天齐来说,面对一个差点卖掉自己的人,却始终表示同情他“胖”的遭遇,理解其因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
除此以外,在舒辉波的笔下,蓝溪小学的孩子们之间也相互包容。郑天齐因为偷了齐老师的云南白药气雾剂导致陈高翔在篮球比赛中受伤被送往医院,但是后来他不仅主动承认错误,早起为学校的菜地挑水、施肥,在比赛中赢得的运动服也选择了陈高翔的尺码,陈高翔也并未因为此事而怨恨郑天齐。覃图南因擅自将戚海燕历经辛苦摘来的樱桃分给同学和老师,导致两人产生冲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覃图南、郑天齐、陈高翔三人连夜去采摘野樱桃,回来的时候脸上都带着被荆棘划的伤。最终,他们凭借诚恳的认错态度获得了戚海燕的原谅。
《逐光的孩子》这部小说中的多重人际关系被作者表现得十分美好,无论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感受到故事中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小说中塑造的几位乡村老师不仅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同时也将自己的身影剪入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像中。装上假肢毅然扛起重担的齐老师,身怀六甲依旧不放弃讲台的白老师,为学校建设尽心尽力的“黑”老师……他们始终怀有大爱之心,以极大的包容和宽广的胸怀维护幼小的心灵,同时将这份暖意延续到了文字之外。在舒辉波的笔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并没有扭曲人性。对于戚海燕和郑天齐来说,虽然家里遭遇了种种变故,但他们毅然以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同时还依旧保持童心。在“我”被沙土迷了眼睛时,郑天齐误以为“我”哭了,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又紧张,小声地说道:“老师……不要哭。”在“我”艰难地在吊桥上挪动时,面对狰狞可怖的狂风暴雨,戚海燕的声音迎着风声传过来:“苏老师……不要怕。”良言一句三冬暖,这两句看似简单的话语不仅给“我”带来了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撑,同时也向读者传达了儿童世界的单纯美好和溢出文字的乡土温情。
通读小说,儿童的天真无邪在蓝溪小学的孩子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份天真便是作者极力想要融入人物中的重要品质。在访谈中,舒辉波曾说过:“所有的艺术最高的境界就是天真,人生而就有的天真。”正是由于这份对“天真”的追逐与向往才使得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以“温情”书写作为全书的主基调。除此以外,在《逐光的孩子》这部小说中,老师和学生之间从未爆发过激烈的对立冲突,他们都努力向对方传递着当代社会不可多得的温暖和热爱。通过艺术加工所表现出的温情书写也使得身处冷漠、孤独中的读者倍感温馨,不自觉地将自我融入小说中描绘的那个美好纯粹的山间生活,使人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身临其境,享受内心的片刻宁静。
二、用意象刻画山间美好
多重意象的组合为《逐光的孩子》增添了别样美好,首先书名中提到的“光”便是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之一。书里提到光的地方有很多,包括星光、月光、阳光、火光、灯光、目光等等,这些“光”的存在不仅能照亮乡村黑暗,还能温暖身心。晚上为孩子们照亮蜿蜒曲折的山路的星光和月光,白天象征着温暖与朝气的阳光,经历过吊桥上的风吹雨打后看到树林里闪烁着的手电筒的光,以及照亮老师劝学之路的火把发出的微光……正是因为“光”的出现,蓝溪小学的孩子们才能在直面生活的黑暗与冰冷之时,还能一直保持着内心的纯善。除了以上描述的这些“光”,还有一种照进孩子精神世界的光,那便是齐老师的目光。蓝溪小学对于齐老师来说意义非凡,因此在小说的开头他才会如此渴望新老师的到来,“把眼睛放在路的尽头”仿佛使我们看到了齐老师眼中既紧张又坚定的复杂情绪。齐老师为蓝溪小学呕心沥血,奉献一生,孩子们在齐老师目光的迎接中踏入校园,又在齐老师的目送中离开学校,踏上更广阔的舞台。
以上这些“光”不仅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生活,还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众多“小光”凝聚在一起,使孩子们的理想之光越来越明亮、庞大。
“意象”虽多运用于诗歌领域,但在小说创作中,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也能使其为文本的情节发展、结构脉络以及创作者的情感寄托服务。除了“光”以外,“种子”作为《逐光的孩子》中的另一重要意象,有力促进了作者、读者、主角人物等內心的各类追求在生活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在小说中,“种子”首先作为蓝溪小学师生生存需求的必备之物。其次,齐老师常说蓝溪小学的孩子是读书的“种子”,在老师的引导和知识的浇灌下,他们一定能茁壮成长,走出大山,在更广阔的天地绽放笑颜。苏老师在课堂上曾教给同学们一首由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所写的诗歌,名字叫作《种子商店》。关于苏老师为什么要将这首诗送给同学们,戚海燕认为:“齐老师总说我们是读书的‘种子——由此我想,其实我们都像是一个商店货架上的植物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子像沙,可是我们可以长成百合花,长成草地,长成一片片森林……”齐老师将孩子们比作“种子”,将他们视作承载着希望与未来的种子,期望他们能早日摆脱现有困境,在不同的土壤之上结出绚烂的果实。相比较城市孩子而言,蓝溪小学的孩子就像女诗人笔下那落满了灰尘的种子一样,他们需要一个为他们掸去灰尘的人,需要被埋藏到各自所属的土壤之中,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早日开花结果。
苏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和同学们定下“十年之约”,让他们早日种下自己梦想的种子。对于戚海燕来说,对“诗歌”意蕴的解读能帮助她拓宽思维,让她更加明确地寻找存在的意义;对于覃廷雍来说,他想要做一个掌控时间的人,所以那个隐瞒了同学们多年的手表便是助他实现理想的“种子”;而对于作者来说,创作《逐光的孩子》的整个过程也像是一个种子不断在心里生根发芽。舒辉波在小说的后记里写道:“从一个隐约的想法像眼前一团模糊的光亮开始,我来写一本书,这个过程也多么像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的过程啊……那些文字像是有生命的种子,在我的身后长成一片片草场。”文字的组合构成了小说的具体内容,对文字的斟酌使作者变得更加宽容、真诚。在这里文字既是文学创作的“种子”,同时也是创作者精神的“种子”,它解答了作者生命中的困惑,支撑着其不断追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三、将诗意语言融入故事
舒辉波在《逐光的孩子》中运用温暖柔和的笔触描写大山里令人神往的自然美景。例如对晨景的描述:“我在晨鸟的啾鸣声中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暮春的风送来森林里草木甘润的气息,夹杂着植物的青气、花卉的芬芳和溪水的腥甜。”以及在苏老师第一次踏上前往蓝溪小学的石子路时:“行路的时候,又大口大口呼吸着这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还有这缥缈细雨飞若游丝,氤氲蒙蒙,天地混沌,心胸也顿觉开阔。”还有在前往参加运动会的小火车上,孩子们被车外的景色吸引,纷纷探出头去:“一只苍鹰学着云朵的样子,从云雾迷蒙的谷底升浮起来,姿态就像刚刚飘浮的那朵白云。它平展着巨大的双翼,像一朵云一样随着气流飘浮。”作者刻意将乡村的自然环境描绘得如诗如画,使人心生向往,同时也表达作者内心对蓝溪小学的怀念与热爱。在这样一个充满大爱的极美极善之地,作者不忍让世俗的猜疑争斗渗入其中,将这份美好打破。
除了对自然美景的诗意描写,作者还将诗歌融入故事。《逐光的孩子》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极具特色,虽是小说,语言却像散文和诗歌一样优美;虽是儿童文学,但作者依旧十分重视对作品深度的挖掘。作者通过精炼语言和故事情节的刻意设置来唤醒隐藏在孩子们内心深处的诗性,同时这也引发了读者对小说的深层思考。在小说的开头,齐老师一直在小火车的终点等待着下一个来到蓝溪小学任教的老师。“我”问他:“您的眼睛就是放在这条路的尽头吧?”此处引入诗意的语言,使得读者瞬间感受到了齐老师内心的焦急程度。作者在陈述情节发展时往往擅于将诗歌融入其中,这不仅能增强故事的美感,还能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有人说儿童文学的创作应表现得浅显易懂,但舒辉波并不这样认为,他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作家的格局应该更大,除了说理还可以提供一种审美体验,着笔从细微处入手,给小孩子看的作品应该更注重文学性。”孩子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不一定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因为孩子天性爱玩乐而非思考。所以作者在《逐光的孩子》中引用了许多诗歌和带有诗意的语言来开启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诗性,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开阔思维,把阅读当作一种审美活动。
作为支教老师,苏老师曾经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一起品读斯图亚特的《种子商店》。小说中诗歌也常伴随着故事出现,在“我”回忆三年的支教经历之时,总会想起劝学路上孩子们高高举起的火把,火光映在路边的溪水中宛如一颗颗星星,但再闪烁的星星也没有孩子们澄澈的眼睛让“我”挂怀,就像蒙塔莱诗中所说:
我漫游在星星间,
我深知,
即使它们都黯淡了,
你的双眼仍能亲切地闪烁。
因“樱桃核”而引发的关于戚海燕和覃图南之间的冲突使“我”不禁想到拉丁美洲著名诗人聂鲁达诗中的“樱桃核”:
樱桃核心的甜味
为什么如此坚硬?
是因为它终须一死
还是因为它必须延续下去?
原本轻松愉悦的故事因为这首诗的出现瞬间将书外的读者引入沉思,是否只有冲破生活的苦难才能将光明传递下去?在创作这首诗歌时,已是垂暮之年的聂鲁达仍然童心未泯,对自然的奥秘充满好奇。有学者曾经对他的《疑问集》有过如此评价:“成年人的生活经验和孩童的纯真直觉,两者结合产生了令人惊喜的质地。”也许这也是舒辉波选择用成人的视角讲述儿童世界的原因之一吧。
四、借“他者”视角反观诗意生活
从个体的层面来看,“他者”一般指与自我相对的个体存在,黑格尔和萨特曾强调过“他者”之于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却使自我和他者处于一种对立层面,其实“他者”的存在或者“他者”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从侧面展示“自我”的美。在《逐光的孩子》中,“他者”视角便主要侧重于表现山村生活图景的美好。对于没经历过乡间劳作的山外人来说,他们对于山村所关注的往往是那种贴近大自然的舒畅,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以及在如今快节奏的生存现状下渴望能暂缓脚步,欣赏自然景物的美感追求。
就像近年来火遍全球的李子柒式短视频一样,李子柒在视频中营造的祥和之态正好符合了受众作为“他者”对乡村的想象,或者说是他们凭借主观意愿所构想出的乡村形态。危欢在分析李子柒视频中的他者想象时提到:“对于乡村的想象是这些‘他者为区别自我和自身生存环境之上构建出来的主体想象。视频的受众始终都呈现出‘他者的‘凝视姿态。”“他者”对于在乡间生活的主体的“凝视”可能源于对自我优越感的寻求,也可能源于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与崇拜。对于长期在大山里生活的孩子来说,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强烈需求早已让他们忽视了身边不可多得的美景,相反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才是他们思考的重点。但对于《逐光的孩子》中的“我”来说,山外人的视角反而更善于挖掘山间的美好,体会自然的诗意,在欣赏和感受的过程中达到放松身心、舒缓压力、解答困惑的目的。
既是儿童文学,便要以儿童为中心,表达儿童的心理需求,反映少年心声。对此,儿童文学的创造者通常会选用孩子作为第一视角。但同样作为儿童文学,《逐光的孩子》反其道而行之,作者在讲述蓝溪小学学生的故事时,选择以成人的视角观察这些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同时表现成年人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虽然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是方卫平在阐释儿童文学的创作时认为如此叙事将会导致成人与儿童的二元对立:“叙事者的默认身份大多为成人,而被讲述的对象则往往是儿童。在这样的叙事关系中,成人叙事者常常处于某种居高临下的上位,儿童则相应地处于被观察、被描述、被评价的下位。”显然,这种由于成人在上观念的不自觉流露所造成的二元对立局面既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会对儿童读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逐光的孩子》虽然以“我”也就是一名支教老师为视角來看待蓝溪小学的学生们,但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挖掘童真和良善上,渴望建立一种平等、和谐、互助的师幼关系。在小说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虽然也运用了成人视角,但并没有将成人与儿童设为对立面,也没有用成人的眼光俯视儿童。作者以儿童为中心,将“我”视为“他者”一样的存在,企图通过成人内心的复杂煎熬来反衬童真的美好,同时作者也正因为看遍了成人世界的烦琐无奈才对儿童世界的天真纯粹心生羡慕,并将这种情感通过文字传达到读者心中。
全书以“温情”书写奠定主要基调,用一个个意象勾画出了美好和谐的乡间美景,而充满诗意的语言更在无形之中帮助读者去寻找内心深处被生活的艰辛压抑已久的诗性。在这部小说中,舒辉波用“他者”视角关注大山里的儿童生活,重构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固有印象,没有想象中令人望而却步的磋磨苦难,也没有想象中的利益争夺和文化冲突。乡村与城市、教师与学生、成人与孩子之间存在的隔阂与矛盾在《逐光的孩子》中被尽数打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者完成了对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与超越。
庄桂成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魏亚枫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丁怡15963716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