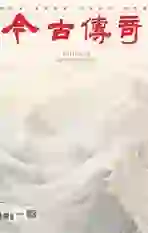出漫水,归家山
2024-03-22沈念
沈念

前方起了薄雾,事先不知道这是一条尚未完全贯通的高速。跟着信号迟钝的导航,在两处收费站之间折返了两个来回,车如同驶入无人之境,不再需要方向的指引,也不知道驶向何处。总感觉前面的道路在缓缓抬升,一起升起的还有“漫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词,也是一个烟火漫卷的小鄉村——作家王跃文的故乡。很多时候,我回想几年前第一次去漫水的经过,似乎它预示着什么,但我还没想得透彻。
真正到了叫漫水的村庄,靠近县城,田野条分块割,建筑高低林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湮没了期待的田园风光。面对时代变迁,谈不上多少遗憾,对“漫水”的心绪早已刻进奇异的旅程之中,或者说将我从高速带离的是对文学的热望。这也许愈加显出一个作家的贡献,把一个村庄建在了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上。
20多年前,《国画》风行,我还是个懵懂的文学爱好者,跑到书店买的是1999年的第一版。这是与跃文老师的第一次相遇。长在扉页照片上的脸,青春刚毅,醒目的痣,浓黑的眉,明澈深邃的眼神,掩饰不了的孤傲。那时正是无数人满怀憧憬和迷茫迎接21世纪到来的前夕,人们期冀发生改变世界或被世界改变的大事件,依然只是不同日历翻转的流水生活。“国画”这个书名迄今有口皆碑,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水墨丹青,在这里被雕刻成一个兼具现实意义和人性深度的文学符号。交织在朱怀镜身上的复杂性格和沉思苦想,拎起周遭人群中的三六九等。这不是某些具体人的故事,而是对一类群体甚至国民隐秘内心世界的洞穿。静寂无声的生活水面下,是澎湃的暗涌,坚硬的冰山。从小山村走出来的跃文老师一个猛子,潜到水底,从水下多层镜面般的光棱里透视岸上“喧哗与骚动”的世界。
纸上相遇,最初种在记忆中关于朱怀镜这个文学人物的人生沉浮,和作者有几分似与不似,倒是惹出不少猜想。他是谁?他的经历,他的性情,他的喜好,他的……
文友交谈中论及跃文老师的过往,从县里、市里到省里,从县长秘书到省政府办公厅的年轻干部,闲时跑到文学原野流连忘返挥洒才情。在公文和文学之间游刃有余,不动声色,他是得了何方神仙的点化,钻通了哪条幽邃小道,来往自如,令人羡慕。但绝大多数人会选择的仕途,最终被他放弃了。他必然是要“出走”的。出走背后那些复杂的现实纠葛已付诸谈笑,多年后的今天回眸,《梅次故事》《大清相国》《苍黄》《爱历元年》等等在文学圈内外被交口称赞的作品一部部诞生。最重要的是,一个很早厮磨官场,谙熟官场规则,却无半点官僚气息的人,找回真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我做过几年时政记者,体会过那种外人察觉不到的孤独。他必定是经历着他的有限和难度,而文学成了他的自我搀扶。这让我想起你刻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自己。
谁不认识自己,谁又真正地认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又是最难践行之事。尼采在《道德的系谱》中如此阐释:“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近或远,并非可以丈量的距离。跃文老师经历和跨越的,告诉每个人,一辈子要做自己的“知者”。
我在基层写作,参加文学活动遇见跃文老师的机会渐渐多了,但仍是隔着距离望着已成名家的他。待人真诚,不摆架子,是他骨子里的自然流露,让很多作家朋友倍感亲切。十来年前我在一家市级媒体干得志得意满,与文学若即若离。负责创研室工作的他搭起了我与省作协之间的桥梁,青年文学奖参评、鲁迅文学院学习,他都会来电话问询。每一次的电话都让以忙碌为借口写得少的我感动和羞愧。我在世俗生活中仿佛要远离文学的时候,又被他这根线扯回来。或者说,他是以行则将至的路,引领湖南很多青年作家和基层作者,重新检视前行的方向。
时光兜转,没想到某一天我们竟成了同事。共事之后,日常往来,那个原以为会一直隔着书页的跃文老师愈见立体。我听说过他不少慷慨的故事,他在电视上看到湘西凤凰某小学偏僻,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送去,还资助了三名留守儿童上学;他去云南旅行偶遇家境艰难的藏族孩子,毫不犹豫地掏钱相助;母校要设立王跃文文学奖,他坚辞不受,提出以学校文学社刊物《涉江》为名设立“涉江文学奖”,并把刚到手的十万元鲁奖奖金悉数捐出。他在省内外文学界尊老携幼,和单位同事融洽和睦,待人接物情真意浓,严于律己低调淡泊,人品文品堪称楷模。有一年省作协机关公推他申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主动让给了老作家。
跃文老师的风趣睿智、超强记忆,为口拙的我暗自羡慕。笔会、出差途中,那些亦庄亦谐的段子,仿佛“信口一吐,就是开怀快乐”,漫长的旅行变成欢声笑语的短途。他爱读书,通古今中外,善以史鉴今,笔下的主人公都缠绵着知识分子的优点和毛病。他与人为善,又坚守正义,对假恶丑的不宽容不妥协,是“心里装得下一个世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我尤其喜欢他微信微博上的只言片语,“我只有爱人亲人友人熟人和陌生人,就是没有仇人”“人才不在于他的才有多高,没有才学可以慢慢弥补,而没有德行的人将无法立足于世”……短小却别有洞天,平实却富有深意,纤细却壮硕凌厉。他的品性情怀无时无刻不在言行中光芒闪烁。有一回,读者在活动现场问他的美好时光是什么,他的回答朴实又诚挚:每天下班回家,饭后与夫人去桃花岭散步。桃花岭是他家附近的小山岭,那条上山的路平缓向上,看得到很多的风景。
到漫水的地界,不得不说跃文老师翻新父母旧宅后命名的“忍冬居”。花开了,谢了,“玉兰断路,紫藤侵屋,蔷薇临窗,椒青枣黄,芜草没了豆角秧”,忍冬居花开花谢,生机蓬勃,他的足迹和朋友圈文字,经常在四季轮回中重返那片山水大地,完全是血脉中对故乡的热爱使然。他眷顾那些乡下的果蔬草树,也想着法子给故园办些实事。漫水村支两委拾掇村部的一间明亮大房,要设立“王跃文工作室”,他婉言回拒,提议改成“漫水书屋”,给村民和孩子们个读书的地方。他人缘好,在作家朋友圈“一呼万应”,大家纷纷寄来各类书籍著作。那时我刚到长沙工作,带来的一箱私人藏书寄存单位一楼传达室,次日去取时书不见了,辗转打听,才知道这些书“混进”捐赠书里去了漫水。这也算是一次无心插柳之举吧。
离中篇小说《漫水》获鲁迅文学奖八年之后,洋洋洒洒五十四万字的《家山》横空出世。还是写的故乡山水,东边山叫齐天界,隔着万溪江,北边山更远,人在沙湾望得见远村的树……在风雨交加的20世纪上半叶,“家山”的乡野大地演绎着岁月流转的日常悲喜、风俗人情以及时代的波澜起伏。兔年春节,不少朋友都在热读《家山》,我读得缓慢,格外珍惜一个作家的记忆与创造。我想象小说中那个宅院里清水自流的娘井儿井,想象天井里油光水亮、日光下冒火星子的青石板,想象田埂上来去的劭夫、贞一、齐峰、扬卿,又为韵味十足的方言会心一笑……他在记忆中将乡土的诗意叙事与时代的苦难叙事融为一体。故乡作为血地,家族血脉在个体身上的绵延,都融入那些看似平常却充满张力、似乎日常却不同寻常的文字中。文学在此有了唤醒之意,唤醒对生命美德的追寻,比如劳作、谦逊、容忍、崇贤向善、明德尚义。
2022年三月起,跃文老师沉浸“家山”世界,写得夜以继日、文思泉涌。有一次同坐高铁出差,他拿出笔记本电脑写作,说起“时常有小说人物附体,同悲欢、同哭歌之感”。他常是以泪洗面,和夫人张战老师叙说今天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谁。当我开启阅读后,才真正体会到这种附体感。每个人物的活着与死去,都是亲人的活着与死去。还有作品中从容的叙述令人羡慕,作家在这个奔跑的时代拥有一颗从容心是多么难得。似乎我也在那山川路上走着、田地里耕作着,那些人物的生死、壮怀与缱绻,令人伤怀落泪。“漫水”的余公公、慧娘娘身上的真善美,延宕到了更广阔的“家山”中。
有理想的人是不孤獨的。《家山》里的陈扬卿把全副才学献给乡村建设,他和妻子史瑞萍夏夜歇凉看挤到天井的星星,他俩谈星空的遥远,星辰的距离和生命,谈如何办好乡村教育。扬卿说的话突然击中我心:“我们活在前人的光芒里,这是宿命,也是福气。”充满诗意哲理的夜晚,是那个动乱时代属于吾乡吾土的安宁一幕。我想,跃文老师定是借着扬卿之口,说出自古往今的一个理:是精神的力量帮我们保留并传承着内心的安宁,“前人的光把我照耀了”。我们循光而行,也成为未来的光。
2022年末的跨年夜,跃文老师坐在北大红楼鲁迅先生教学过的大教室里,在文学中国直播中脱口诵出文学史上著名的《故乡》:“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此刻变得那么迫近。沉淀在他生命中数十年的时光、生活和记忆,对万事万物生命的深深疼惜,成就了跃文老师笔下湖湘大地上的文学山水。它连同钱起的“莲舟同宿浦,柳岸向家山”、汤显祖的“梦醒家山泪下”、龚自珍的“无双毕竟是家山”,交织绘就的是铁干虬枝的壮阔山河与绵延不绝的人间值得。对许多人而言,离开“家山”,一切经由此发生,而写作就是回顾,回顾逝去的生命,也是体味自己的命途。每一个读者,都在《家山》讲述的一个个人物身上,看到他们为自己赢得的荣光。因为这些荣光,他们有尊严地承受起了苦难和灾难。
跃文老师当然不是苦行僧式的写作者,他养花种草,舞文弄墨,常与家人漫步麓山、自驾国外。在京拿到《家山》第一本样书,他题赠夫人张战:“家山无双,琴瑟合一。”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把他从写字桌前拖回到充满烟火气的世间生活中,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就是“关上门,在纸上把世界打开”“有慈悲,有热心肠,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作家与这个世界,原本就该是如此状态。这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意,爱是他的文学底色,文曲人直,为人与为文的相得益彰,如同双子塔的矗立。
走出“漫水”,归来“家山”,跃文老师是天空的飞鸟,也是大地的行者。他的文学与生活,贴身又贴心,走的就是一条前方不断升起的路。
(责任编辑 丁怡15963716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