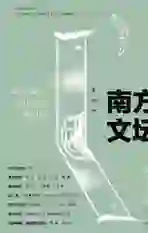写作与批评主体的重建
2024-03-12吴晓东
2019年的深秋时节,我有幸参加了黄子平先生新书《文本及其不满》的发布会,那次发布会的标题也是“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当时就感到子平老师阐述的“同时代人”的观点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话题空间。这次看关于此次座谈会的海报,仔细阅读了一下出自黄子平手笔的内容简介,发现他关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又有了新的拓展。
阿甘本关于同时代人的阐发,最令人欣赏的是黄子平引用的这句:“同时代人深刻地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像蘸着墨水一样蘸着时代晦暗写作。”这个关于“同时代人”的界定其实是很苛刻的,也意味着只有绝少的一部分人才能称得上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不能因为我与黄子平先生都生存在当下的历史时空,我就有资格与他称为同时代人。因为真正的同时代人是要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同时要蘸着时代的晦暗而写作的,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更习惯于蘸着时代之光写作。真正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之光的人,或许才是真正能够揭示时代和历史的危机结构的人,也才能真正做到蘸着时代晦暗而写作。我心目中的这种蘸着时代晦暗而写作的人,看遍天下,也没有几个,而黄子平先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黄子平继续追问的是:“如何携带我们各自的‘古代来进入当代?这关乎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糅合的历史性装置,关乎记忆、期待和对当下的关注。”这意味着同时代人看似处理的是共时性的当下时间结构,但是同时蕴含了历史维度以及未来远景,黄子平恰是把历史以及未来的时间向度带入了关于“同时代人”的思考,也就发展了阿甘本的说法。我当初阅读黄子平的《边缘阅读》这本书,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历史是什么?历史即至今仍然刺痛人心的记忆。”黄子平在他的专著《革命·历史·小说》(内地版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的前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说法:“本书的主要部分即在于试图重新解读这批‘革命历史小说。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这里触及的历史性装置其实就蕴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糅合的三维时间坐标。正如洪子诚先生在《“边缘”阅读和写作——“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这篇文章中关于“历史”的精彩判断:“‘历史深处不仅是实存的‘历史自身,也不仅指叙述历史的文本形态,而是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正是黄子平在这次座谈会的海报中所强调的:“这关乎人文学者的时间哲学。”
那么人文学者的时间哲学有什么特殊性?按照黄子平的理解,比起其他领域的学者,人文学者更需要面对一个如何携带自身历史的问题,以及如何直面历史时间的问题,也就是更关乎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糅合的历史性装置,这个装置对人文学者来说更有一种及物性、及身性或反身性。所谓的及身性指的是人文学者所面对的历史不是与当下以及学者的生存境遇全然无关的客观对象,而是对当下的深刻介入,甚至是对个体生命以及社会现实的深深刺痛。
接下来我更想参与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这个历史性装置背后的所谓同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除了历史性的时间维度,在黄子平对“同时代人”的阐释背后也有个在空间维度中游走的移动的主体性。
我曾经把黄子平先生与鲁迅相比较,如果说鲁迅是一个钱理群、汪晖等学者强调的“历史中间物”,那么黄子平关于同时代人的思考中也表现出一种“地理中间物”的特质,这个“地理中间物”是黄子平从“历史中间物”衍生出来的一个有智慧的概念。我觉得黄子平如果写自传,那么他在梳理自己生命的时间坐标之外,当然还有同样重要的空间坐标,这个坐标中一定有广东梅县(出生的地方)——海南(知青插队的地方)——燕园(求学和工作的地方)——北美(去国后旅居的地方)——香港(教授荣休的地方),然后是荣休之后又辗转于大陆、台湾、港岛。这是非常丰富的跨国度、跨文化、跨语际的越界体验,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子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把批评的位置理解为“游动的、越界的”:
而这位置当然是游动的、越界的,或者用萨义德回忆录的书名来说,是‘无家可归或‘格格不入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真正的位置,不管你是不是具有離乡背井的现实经验。
我觉得黄子平先生离开内地之后的写作整体上说也笼罩着一种批评主体意义上的“地理中间物”意识,这个批评主体是游动的、越界的、“无家可归”的、“格格不入”的,这是一种对批评主体的非稳定性的体认。当然黄子平自己的表达更为精彩,用他在《文本及其不满》的前言中的说法是:“写作者无不身处主体被撕裂的状态之中。”我认为这种对历史中的主体曾经撕裂性的体验和表达,在当今学界,可以说是尤其珍贵。
这就是黄子平对人文学者的某种主体姿态的反思,当他揭示出“写作者无不身处主体被撕裂的状态之中”的时候,如何重建写作与批评主体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前边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游动的、越界的、“无家可归”、“格格不入”,都与历史中的主体曾经撕裂的体验建立了关联性。
我还想说说黄子平写于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早晨,北大》,回顾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在1970年代末编辑的一本校园文学刊物——《早晨》。作为同时代人,恐怕没有哪一届学子比起77级这一代更辉煌了。不妨看看《早晨》中的作者,也就是黄子平的同班同学:张鸣、夏晓虹、陈建功、黄蓓佳、查建英、郭小聪、梁左、岑献青、江锡铨……后来都成为文坛与学界的中坚力量。据黄子平回顾说,《早晨》当时每期只印一百本,“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纯粹好奇用电脑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可以想象身为《早晨》主编的黄子平当时体验到的是一种载入史册的自豪与荣耀感。
但我真正想说的是读到这篇《早晨,北大》的结尾,却发现黄子平试图表达的是一种“挫败”感,他说作为77级的大学生,“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无论之前有过多少磨难,似乎从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起,我们的名字就习惯了与成功之类的字眼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群,常常忽略了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多少年了,午夜梦回,如今时时袭来撞击久已沉寂的灵魂,岂不正是生命中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败,那些未能实现的历史可能性,那些被错过的、擦肩而去的历史瞬间?”
我很为这种“挫败感”感到震撼。当然我们不能信以为真地认为黄子平的这种挫败就是个体生命的失败,我想起的倒是他同班同学黄蓓佳当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名字叫《这一瞬间如此辉煌》。我想,黄子平的这种“挫败感”或许应该理解为经历过无数个辉煌的生命瞬间的一代人对历史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深刻颖悟。
最后我想用钱理群先生来印证一下。前几天去看望钱老师,钱老师开始总结自己的一生,其中有一句自我评价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钱老师形容自己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失败人生。”我一时间对钱老师“失败”的措辞有些困惑和不解。但是印证子平老师的相类似的体悟,我觉得我好像理解了自己导师这一代人,也就似乎理解了他们对“同时代人”这一范畴相似的体认。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