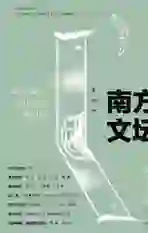文学之所以求真、致善、尽美
2024-03-12高远东
高远东
这个有关时代与文学的话题,没有想到,自觉还年轻的我也要开始谈论了。子平、平原老师是77级,我跟在座计璧瑞是大学同学,是79级。79级比较有意思,比较沾光的一点,是可以归划到“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所谓新三届。在新三届里面,77、78级以外还可以挂一个79级,处于太阳光芒边缘,比较无感。但79级的过渡性也很有限,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大哥大姐们和自己同学,这些大哥大姐的经历、学历甚至所遭受的苦难,和77、78级没有两样——我因此常常产生幻觉,觉得既然和大哥大姐们同学,其实也就是和77、78级同学,因此这个狭义的新三届,就与时代的关系而言,其实属于广义的新一届。我们的经历、学历乃至精神发展,共享着一个时代。
对于“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个主题,我还是要发一下感慨。不管是文学,还是学术,还是文学批评,还是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时代的产品。文学,它是时代的结晶。它不是由作家写,而是时代通过作家之手所做的记录,所做的想象,它是时代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结合的产物。所以在存在的意义上,我们都是时间的产品。子平老师刚才所说的同时代人的经验,决定着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同时代人”这个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同时代人”的经验、遭遇,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光明、黑暗的界限的消失。我们自己的状态是悬置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的意义,只能在相对性的世界里边相对地漂浮着、思考着。这和我们色彩鲜明、界限确定、非常“主体化”的昨天非常不同。所以我在观察和思考,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美好的人事都在不断地失去。王富仁去世后,我在纪念王富仁的文章里就发了很多感慨。王世家去世后,我写的《而已斋忆往》也是想把逝去的美好時光和人事记下来。想起这些,看着日渐衰老的老师们,我总是被浓烈的感伤包裹着。为什么好的东西留不住,为什么坏的东西反而能够不断地、体制性地生产,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里边的凰歌,它在问:“我们年青时代的新鲜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甘美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光华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代的欢爱哪儿去了?”它在那样一个心情下面“集木自焚”,进行浴火重生的努力。所以我就想我们跟时代的关系在哪里?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
我自己,从我的个性来讲,不是那种“大写的人”,虽然坚守理性批判的求真原则,却没有什么宏大的精神气象,我是很随和甚至很愿意依附的人:我的老师们在的时候,我的学长们在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在的时候,我愿意依附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围绕或者跟随在他们的身前背后进行思考,优游自在。他们写出来好的论著,说出我想说的话,我觉得非常高兴;说出我说不出的话,更觉得享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眼看着老师们一个个老了,学长们也慢慢地快要退出学界,退出这个研究、思考、进行学术文化创造的工作,而我这个跟跟派呢,就突然发现:我也快到了这个尽头。因此就更加丧失阅读、思考、积极写作的动力了。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据我的观察,在日本的学界也有类似现象。我知道围绕丸山昇先生有一个“三十年代研究会”,到丸山昇先生去世之后,研究会的不少朋友都进入抑郁状态,有的甚至退出了学术界。我就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好的东西留不住有关。所以,我们留恋这个美好时代、美好时光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心情。我其实跟钱理群老师、黄子平老师、陈平原老师他们这些特别积极地在一线进行学术创造、文化创造的人不一样,我自己没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目的,随波逐流,比较有学术虚无主义的倾向。鲁迅讲道家人物,说他们是“薄周孔,蔑诗礼,贵虚无”,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以后要跳的坑,一步一步地跳:薄周孔,蔑诗礼,贵虚无。当然虚无主义是一方面,另外一面,我觉得我要坚持中和主义。我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两派,左派和右派吵得不可开交,立场和价值观对立和分裂,我就想做和事佬,说你们不要吵了,我和各位进行左右斗争不同,我是想搞左右调和的,是想把鲁迅和胡适搞到一起。我说你们能否想一想,鲁迅和胡适的同是否大于异?如果我们退到鲁迅、胡适文化价值观的原点,再出发思考问题,分歧还会这么大吗?他们只不过在政治选择上有了分歧而已。可政治选择那就是投票的选择嘛,可以就事论事,完全没问题!政治选择不像文化的价值观,这个东西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有什么可吵的,在我眼里,鲁迅就是胡适,胡适就是鲁迅。所以我自己喜欢搞这种中和、息争甚至怀安,不愿意世界有纷争、对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