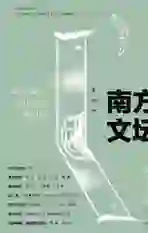引言:断裂时代的文学与批评
2024-03-12黄子平
我的学生去做概念的谱系学搜寻,说我在1983年的时候为赵园的那本《艰难的选择》写过一个很短的小引,在小引里边就已经提到“同时代人”这个词。其实是我年轻的时候读“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读来的。那年头除了读马列文论,就剩下“别车杜”可以读。我听说北大考研究生,问“别车杜”是谁,答得上来的不多,也难怪,年代太久远了。这三位的著作,里头大量出现“同时代人”这样的概念,因为19世纪俄罗斯突然冒出来很多人,提到一个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串,所以这个概念用得很多。到现在我们还是能够读到《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或者《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类似这样的著作。到了我四十年前写小引的时候,时代背景就很类同,也有一些人突然成群结队地冒出来,多多少少意识到我们不是一个人,用那首被广泛引用的诗来说,“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或者“也不是一个人倒下”。那时候顾城会用《一代人》这样的题目来写一首诗,或者舒婷写过《献给我的同代人》,没有人觉得他们用这样题目来写诗是一种愚妄,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集体的(潜)意识。
为什么我在前几年开始重新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来讨论呢?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一个70后的作家,也是一位大学教师,他问我为什么你不再写当代文学批评了?他说的“当代文学”指的就是像他一样的70后。我就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他。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我好像连阅读都只是读到苏童、格非他们为止,后来的作家几乎不太读,更不用说写评论了。最后我找到什么理由呢?想来想去,觉得我跟他们已经不是“同时代人”了,用这个理由来抵挡一阵子。可是“同时代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跟80年代很不一样了。举一个很切身的例子,我的77级的同班同学,陈建功,现在是著名的作家,另外一个同学叫梁左,梁左的妈妈叫谌容。按照规矩,同班同学陈建功应该叫谌容为阿姨,但是陈建功跟谌容是同期出道的北京作家,所以就大大咧咧直接叫谌容。当然77级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但那时候的标尺是以“出道”作为一个时间标准,到了这位70后作家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标准就变成出生证明书了,你是哪一年出生的,这个标准的移动其实蛮说明问题,香港叫出生纸,以出生纸来判断,以公历的十年,这么一个间断的标志来区隔作家之间的“代”。这个当然是比较容易的,查身份证就行了。但是他们之间其实千差万别,他们之间到底是不是“同时代人”,是很可疑的。
后来我就读到了阿甘本的那篇不是太长的文章(《何谓当代人》),结果就把我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彻底地推翻了。大家可以找到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有两种译本,有的译成“当代人”,有人译为“同时代人”,在意大利语里大概是同一个概念,它最主要的论点是当代人或者同时代人,是非常深的镶嵌到时代里边,但同时又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所以他是用了尼采“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概念。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存在,即一个人很深地卷入到时代里头,可是跟时代格格不入,他觉得这是当代人的必须的条件。如果这个人紧贴着时代,在所有的方面都跟时代合拍,他反而不是同时代人,不是当代人。正是这一点,一下子把我对“同时代人”的理解彻底轰毁了。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同时代人、当代人对时代黑暗之光的那种感受、感知,他不是单纯地说这是黑暗或者绝望的深渊,他说的是光,这个光是黑暗,黑暗之光,这种说法就很妙。我们要怎么样去凝视,不能抵达,但是我们能够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他说同时代人像蘸着墨水一样蘸着时代的晦暗来写作。这些比喻性的描述,其实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点,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时代是处于断裂之中,就像哈姆莱特的苦恼:“时代分崩离析,却要我来重整乾坤。”这就跟“别车杜”的概念打通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突然涌现很多人的时候都是因为时代断裂,像欧洲的文艺复兴、19世纪的俄罗斯或者20世纪“文学爆炸”的拉丁美洲,包括我们的五四,都是因为时代发生了断裂。一断裂就会产生两类人,一类人站在断裂的这一边,非常有能量地发出保守主义的光芒,阐释传统价值的观念,站在另一边的一类人要去重新发明全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时代的断裂是一种危机,是连续性的中断或确定性的消散。阿甘本进一步的说法是,由于时代的断裂,使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他说我们进入当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古代”进入的。比如说有人是带着李白的盛唐来进入当代的,有的人带着苏轼的北宋来进入当代的,像老钱(钱理群)他们都是非常固执的,要带着鲁迅的五四來进入当代的。这些人好像在谈论古代的事情,其实都是要带进来跟当代对话。
这三点在他那篇短文里面表达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自己是做文学批评的。做文学批评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就是你跟作者、跟作品一起共享“对未来的无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在后世看来到底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值得批评?批评家的冒险就在这里,你跟作者和作品一起承担了一个对未来的无知。不像做文学史的人,他们是享有一种后见之明,所以做当代批评或者跟同时代人的文学对话,困难重重,承担了很多的风险。“过去、当下、未来”是一种时间的构建:你怎样进入你的当代?你怎样在深深卷入时代的同时保持观察时代的距离?你能不能凝视时代的黑暗之光、感知时代的黑暗之光,蘸着时代的晦暗来写作?这都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