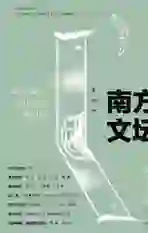文学与民间
2024-03-12王彬彬
最近,西南某大学文学院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民间、民俗与地方文学的当代价值”。朋友圈里,好几位与会者转发了会议信息。我在一位朋友转发的信息下面留言:“‘民间、‘民俗是并列的概念吗?啥叫‘地方文学?”友人回复:“确实不够严谨。”“地方文学的当代价值”这说法的问题姑且不论,只说将“民间”与“民俗”并列,实在不应该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所为。什么是“民俗”,“民俗”就是民间风俗,就是民间社会代代相传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一些婚丧嫁娶的仪式。如果民间社会是大海,民俗就是大海里的一道波浪;如果民间社会是高山,民俗就是高山上的一块石头;如果民间社会是草原,民俗就是草原上的一丛野花。民俗是民间的一部分,民俗是从属于民间的,二者不能是并列關系,正如某所大学的文学院与这所大学不能是并列的关系。这其实是极简单的逻辑,极明白的道理。如此简单的逻辑,如此明白的道理却被堂皇的大学文学院所无视、所践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民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被滥用、乱用到何种程度。
但对“民间”的滥用、乱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真个是久矣夫,几十年来,已非一日矣。
文学与民间是否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但要思考文学与民间的关系,首先要思考“民间”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呢?在任何一个时代,民间都是社会的主体部分,而非民间的宫廷、庙堂,相对于民间来说,必然是微小的部分。如果社会是一棵树,非民间的部分只能是那尖尖的树梢,树梢之下都是民间;如果社会是一座塔,非民间的部分只能是那高耸的塔顶,塔顶之下的部分都是民间;如果社会是汪洋里的冰山,那非民间的部分只能是那露出海面的部分,海水里面的部分都是民间。当然有的时代民间社会更发达些,非民间的社会便更微小些,而有的时代民间社会则比较萎缩,非民间的社会便要膨胀些。但即便在民间社会再萎缩的时代,民间社会也一定远远大于那膨胀着的非民间的社会,否则整个社会就根本存续不下去。既然非民间的部分总是一个社会中非常微小的部分,那在许多时候,“民间”与“社会”之间,就基本可以画等号。如果对“民间”与“社会”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就会发现,“文学”与“民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早已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早已有一门“文学社会学”专门研究这个大问题。既然有了“文学社会学”,应该没有必要再建立一门“文学民间学”。如果有人能够建立一门在基本问题、研究路径、研究方法上都与“文学社会学”有学科性差别的“文学民间学”,我们当然乐见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但我想,这样一门“文学民间学”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在三种意义、三个层面上与“民间”发生关联。第一,是在创作主体创作意图的意义上,是在创作主体思想情感层面上与“民间”发生关联。这时候,创作者是怀着民间化的思想情感在观察世象,在描绘人物,是在以民间化的价值尺度衡鉴世间的一切。至于其表现的对象,不必属于民间,可以是宫廷,是庙堂;而使用的表现手法,也不必是民间文学的“叙事惯例”,不必是通俗文学的常用技巧。第二,是在创作客体的意义上,是在题材的层面上与“民间”发生关联。这时候,创作者着力表现的是民间社会的人和事。至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至于创作主体用以评价表现对象的价值尺度,不必是民间化的东西。创作主体完全可以对笔下的人物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第三,是在创作主体表现手法的意义上,在创作主体所运用的艺术技巧的层面上与“民间”发生关联。这时候,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至于创作者的思想情感、所秉持的价值尺度,不必是民间的,作品的表现对象也可以不是民间社会的人和事。当然,还可以有第四种情况,那就是一部作品在上述三种意义、三个层面上都与“民间”发生关联,即创作主体怀着民间化的思想情感、秉持着民间化的价值尺度,以民间文学的基本手法,表现民间社会的人和事。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作品具体对待,而不应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批判或歌颂。一部作品,可能因为在某种意义、某个层面上与“民间”有关联而值得肯定、歌颂,也可能因为在某种意义、某个层面上与“民间”有关联而必须否定和批判。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社会内部也有着多种层次,是极其复杂的。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民间社会的行为方式、民间社会的生命态度等,都不可能完全美好或完全丑陋,不可能应该彻底肯定、歌颂或彻底否定、批判。
但自从“民间”这个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流行起来后,便成了一个肯定、歌颂性的概念。几十年来,在评说现当代文学作品时,“民间”不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一部作品,只要被认定与“民间”有关联,只要被贴上一张“民间”的标签,就意味着是毋庸置疑的一部好作品。“民间”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文学价值,甚至是最高级的文学价值。批评家们、研究者们,在认定一部作品与“民间”有干系时,在给一部作品贴上“民间”的标签时,通常使用“民间化叙事”这样的话语。但总是把他们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也弄不清他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民间化”这说法的,因而也不明白他们所谓的“民间化叙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一部作品,只要被认作与“民间”有关联,只要被判定为是所谓“民间化叙事”,就意味着是一部值得赞美的作品,就意味着本身的优秀,这实在是很大的荒谬。
这个概念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流行,起源于早已生活在美国的研究者孟悦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孟悦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今天》199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杂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了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收入了孟悦此文,但题目改为《〈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孟悦要说明的,是不能简单地把“延安文学”理解成纯粹是“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因为“这种带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反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上下文”①。孟悦通过对《白毛女》细致分析,指出“这种带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其实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些民间文艺的表现手法,而正是这种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白毛女》这样的作品还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孟悦把这种民间文艺的常用手法概括为“叙事惯例”:“虽说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机制。使《白毛女》从一个区干部的经历变成了一个有叙事性的作品的并不是政治因素,倒是一些非政治的、具有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换言之,从叙事的角度看,歌剧《白毛女》的情节设计中有某种非政治的运作过程。这里,问题涉及的已不仅是政治文学的娱乐性,而是政治文学中的非政治实践。因为,这个非政治运作程序的特点不仅是以娱乐性做政治宣传,而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一个民间日常伦理秩序的道德逻辑作为情节的结局原则。”②
孟悦的逻辑很清晰。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民间”这个概念在孟悦的论文里出现了六十多次,但没有一次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出现的。在孟悦论文里出现的,总是“民间形式”“民间艺术”“民间伦理秩序”“民间伦理逻辑”“民间伦理的道德逻辑”“民间伦理原则”这样的说法。这说明孟悦有着基本的逻辑感。与文学发生关联的,总是民间社会里的那些具体的东西,因而笼统地把“文学”与“民间”绑在一起,在逻辑上便是有点问题的。如果说“文学”是一根细细的螺钉,“民间”却是一只很大的螺帽。把“文学”这根螺钉往“民间”这只螺帽里拧,无论怎样使劲,都是拧不紧的。需要强调的另一点,是孟悦一直是在“延安文学”这个前提下谈论民间文学的“叙事惯例”,一直是在“政治功利性的文学”这个总体语境中肯定民间文学的“叙事惯例”。民间文学的那些“叙事惯例”,毕竟是属于通俗文学惯用的表现手法,不能说是特别高级的文学技巧,更不能说是最为高级的艺术表达方式。打个比方吧。在粮食紧缺只能以瓜菜充饥的“瓜菜代”年月,在一锅瓜菜糊糊中撒上一把麦麸,这麦麸在一锅瓜菜中就是特别珍贵的粮食。但脱离了一锅瓜菜这个整体语境,在粮食充足的时候,麦麸就不能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东西,很多时候只能用来喂猪。
孟悦从民间文学“叙事惯例”的角度解读“政治功利性文学”的研究方法,很快在中国内地有了仿效者。内地的仿效者在转述孟悦的基本观点时,将其大大扭曲。一方面,转述者从孟悦的“民间形式”“民间艺术”“民间伦理秩序”“民间伦理原则”等表述中把“民间”抽离出来,让“民间”单独与“文学”发生关联,这样,“民间”便从孟悦论文中的限制性的语言成分变成了“主词”;这样,便开始了把“文学”这根细细的螺钉往“民间”这只大大的螺帽里拧。另一方面,转述者把孟悦概括的民间文学的“叙事惯例”从“政治功利性文学”这个整体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奉为文学艺术应该遵行的最高原则,甚至把民间文学的“叙事惯例”扩展为民间社会的一切,以至于只要一部作品与“民间”有了关联,就具有了优秀的品质,这正如把一把麦麸从一锅瓜菜糊糊中捞出来,说成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美味最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孟悦的转述者在将“文学”直接与“民间”对接后,就开始了对“民间”的研究,并且给“民间”下了简洁明快的定义。既然如此,我也表达一点对“民间”的看法。
首先要强调的,是不能把“民间”本质化,不能脱离时代、地域而抽象地、笼统地认为“民间”一定具有怎样的性质、面貌。例如,不能认为在任何时代,“民间”都具有“自由自在”的性质。正如在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的前提下,“社会”的性质和面貌迥然有异一样,在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民间”的状态也往往有巨大差别。在中国历史上,一再有过“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时代,有过“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就不能说“民间”是“自由自在”的。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而生长于“民间”的人,实在没有留下什么“自由自在”的童年和少年记忆。关于民间的“时代性”,就说这些。
不能把“民间”本质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國的大部分地区,从古代到民国,民间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都是宗法社会,而宗法观念、宗法力量对人的控制,往往比政治观念、政治力量更严苛。其实,要知道自古代到民国的广大乡村民间的情形是怎样,用不着从事现当代文研究的人再去“研究”,只须读读费孝通那本通俗而经典的小册子《乡土中国》便可以了。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绝对得不出乡土民间是“自由自在”的结论。相反,费孝通告诉我们,在传统的乡土民间,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差序格局”中,而在这个“差序格局”中,“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③。只有每个人都每日每时地“克己”,“差序格局”才能维持下去,民间社会才能延续下去。如果有人胆敢不“克己”,那遭受的惩处可能是极其严厉的。费孝通指出,传统的乡土民间,是一个“礼治社会”,而“礼治”完全可能比“法治”更无情、更凶残。费孝通强调:“礼治社会并不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④如果硬要说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社会,那就未免太荒谬了。
确实有一些特定的地域,与那种“礼治社会”有所不同,人们受到的束缚、管控要松弛些。但这并非正宗、典型、标准的“民间”。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把“民间”的地域性差别表现得很明显。大淖地处城乡结合部。这个“城”,也并非通都大邑,一座小县城而已。那个时代,一个县里,除了县衙不能算“民间”,其他地方大概都属于“民间”的范畴。但“大淖”这小小区域的“民间”,却与县城,与周边的“民间”,都有深刻的差异。《大淖记事》说:“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坐在大淖的水边,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大一样。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又说:“这里人家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与县城里人的行为方式有如此不同,“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生活在大淖的人,可以听见县城里的市声,真可谓近在咫尺。但大淖这小小的地域,却在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伦理标准方面与县城有巨大差别。这小小地域的“大淖”,固然是“民间”,但你不能说那县城里的闾里巷陌不是“民间”,更不能说大淖周边无边无垠的乡村,不是“民间”。实际上,县城里的闾里巷陌,大淖周边无边无垠的乡村,才是正宗的、标准的、典型的“民间”,而“大淖”这小小的区域,倒是特殊形态的“民间”,是非正宗、非标准的“民间”,是非典型性“民间”,也是为正宗的、标准的、典型的“民间”所鄙视甚至敌视的另类“民间”。有人说,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表现和歌颂了“民间情义”。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大淖记事》表现和歌颂了那种非正统、非典型性民间社会的情义。
研究民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给“民间”下的另一个定义,是“藏污纳垢”。评说任何事物,都有两种角度、两种尺度。孤立地不与其他事物比较地评说某个事物时,是一种角度、一种尺度;在与某个具体的事物比较中评说这个事物,又是一种角度、一种尺度。例如,孤立地、不与其他事物比较地评说苦瓜,我们可以说苦瓜的味道是苦的,甚至可以说很苦很苦。但如果在与黄连比较中评说苦瓜,我们就不能强调苦瓜之“苦”,而应该强调比起黄连,苦瓜的味道不那么苦,甚至有点甜。评说“民间”时也是这样。如果孤立地、不与其他社会区域比较地评说“民间”,可以说“民间”是“藏污纳垢”的。但与“民间”相对的区域是宫廷,是庙堂。热衷于谈论“民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是在与宫廷、庙堂相比较的意义上给“民间”下了“藏污纳垢”这样的定义。这时候强调“民间”的“藏污纳垢”就违反常理了。因为任何一个时代,宫廷、庙堂必定比民间“藏”着更多的“污”、“纳”着更多的“垢”。这道理,《红楼梦》中两个人物,焦大和柳湘莲,已说得很明白。《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是侯门,当然不算“民间”。第七回里,资深奴才焦大醉酒后说道:“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里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于是换来马粪塞嘴。第六十六回里,柳湘莲说得委婉些:“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贾府算是庙堂,贾府以外的里弄、胡同,算是民间。如果不把里弄、胡同与贾府对比,说里弄、胡同里“藏污纳垢”,大抵也没错。但如果在与贾府对举时评说那些里弄、胡同,就决不能给里弄、胡同下个“藏污纳垢”的断语。因为贾府中的污垢,必定比那些里弄、胡同多得多,那污垢的状貌、性质,甚至是里弄、胡同中生活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其实,一个文学研究者,离开具体的创作现象而辩说“民间”的时代性、地域性,本身就很是滑稽。退一步说,就算“民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自由自在”和“藏污纳垢”,那与“文学”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难道“文学”的使命就是表现“民间”的“自由自在”和“藏污纳垢”吗?
但既然已经谈开了,就再说一点。我以为,还必须强调,“民间”和“民间性”是两个概念。世界上确乎有些区域,是宫廷,是庙堂,不能算作“民间”,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民间性”。宫廷不是民间。皇帝的卧室就更是离“民间”最远的地方了。但皇帝的卧室里是否有“民间性”呢?当然有。侍候皇帝起居的太監、侍寝的嫔妃,都来自民间,当然也使得皇帝的卧室具有了“民间性”。既然世界上没一处没有“民间性”,那实际上要找到一部完全没有“民间性”的作品,便很有些难。尤其是那种叙事性作品,又尤其是那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作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完全排除“民间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因此,研究者要想找到一部完全没有“民间性”的叙事性作品,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我想,那些热衷于谈论文学作品“民间化叙事”的批评家,那些成天把“民间”挂在嘴上的文学研究者,不会想到把《红楼梦》这部作品也装进那“民间”的篮子。但《红楼梦》有没有“民间性”呢?当然有。不但有,还十分充沛。只说焦大醉后的那一番骂,就十分具有民间色彩,就是一种“民间化叙事”。比焦大醉骂更为民间化的叙述,还有很多。刘姥姥也算是《红楼梦》里一个重要角色。但刘姥姥可是地地道道的民间人物。刘姥姥可真是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民间的馨香”。刘姥姥几进荣国府,都可说是在这侯门里尽情地播撒着那“民间性”。贾宝玉与凤姐一起为秦可卿送殡的途中,在一村庄人家暂歇,宝玉对那人家的女儿二丫头心生爱意,甚至恨不得跟了那村姑去。这可是标准的“民间化叙事”,而且这侯门公子与民间姑娘的情感纠葛,还是特别富有思想内涵的“民间化叙事”。还有,那薛蟠虽是富贵之家的纨绔子弟,却混迹于民间,有着浓烈的民间流氓性、市井无赖气。换言之,薛蟠这个人物身上,也是有着强烈的“民间性”的。《红楼梦》中的“民间化叙事”太多了。如果要以《〈红楼梦〉中的民间化叙事》为题写一篇红学研究的论文,绝对没问题,可以写得很长很充实。就是以《〈红楼梦〉的民间性研究》为名写一部红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可以写得头头是道,自圆其说的。
但是,如果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能从“民间”“民间性”的角度进行评说、研究,“民间”“民间性”这样的概念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吗?
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何“民间”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后,迅速被广泛运用的原因。连《红楼梦》都可以从“民间”的角度进行评说,还有什么作品不能从“民间”的角度进行研究?既然“民间”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评说研究几乎所有的作品,那就是一件写文章、做学问时非常趁手的工具。紧紧抓住“民间”这个工具,可以制造出一篇又一篇科研成果。
“民间”这个概念流行了几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好用。
【注释】
①②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50、55页。
③④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28、50页。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