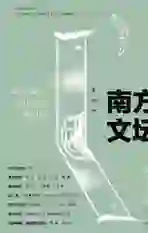反常合道·流水行云:小议当代作家的“晚期风格”
2024-03-12杨辉
一
谪居黄州,闲来无事,除四处寻访胜迹,吟诗作赋,寄托怀抱外,苏轼还有意教导子侄。赵德麟曾在苏辙家亲见苏轼寄给侄子的书札,其中有论少年文与老年文之异同,颇有可观处:
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走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①
少年血气方刚,规矩、法度尚未习得,或得而不精,故下笔为文,多活泼生机,如春如夏,万物竞萌,花开阔绰,气象峥嵘;老年血气渐衰,规矩、法度尽皆精熟,倒是可以随意“破”之,其文可浓可淡,可以雷霆万钧,亦可雨收风住,如冬如秋,可涵纳万象、包罗万有,风格、意趣亦不拘于一途,常得自由挥洒、任意所之之妙。所谓的“衰年变法”或“晚期风格”,落脚点多在此处。如王德威读《晚熟的人》,特意点出莫言作品“向来大开大阖,篇幅越长,越能显现他那种异想天开、兼容并蓄的气魄”。此论可与莫言对长篇之“长”的理解相参看。“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写长篇,要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而所谓的大家手笔,也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皆属“长篇胸怀之内涵也”②。诚哉斯言!《酒国》《生死疲劳》《檀香刑》诸作,汪洋恣肆也可谓泥沙俱下,涵纳万象也是气象万千,乃莫言长篇一大特点。但《晚熟的人》却与此不同,王德威以为莫言或有意摆脱前述特点,“风格转为内敛,时而怀旧,时而嘲讽,显露一种若有所思的节制”。当然,书中所录诸篇,皆为短制,其“形式也不容许过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发展”③。此为莫言“晚期風格”的特点之一。
或属偶然,新世纪后,久已不专意经营短篇的贾平凹写出了《秦岭记》。《秦岭记》“不可说成小说,散文还觉不宜”,“写时浑然不觉,只意识到这如水一样,水分离不了,水终究是水,把水写出来,别人用斗去盛可以是方的,用盆去盛可以是圆的”④。其要在去规矩,破法度,得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之妙。或进而言之,规矩、法度也无需去“破”。文章作法多样,究其本源却并无一定之规。有多少眼光,见多少世界,便有多少文章。明清文可以法唐宋,唐宋文可以法两汉,两汉文可以法先秦,先秦文所法者何?!文章法度,源出于“六经”。“六经”或也无心确立法度,古人仰观俯察,书之竹帛,自然成文。那文中自涵磅礴气象,其“力量在于混沌未开,像一片汪洋”,后之来者只能取其一瓢,格局、气象,自然逊色许多。“先秦那种汪洋恣肆、无所不包,看不出界限的气概,那种未经规训、未经分门别类的磅礴之势”,呈示的乃是“充沛自然的生命状态”⑤。
钟意于多元感通,醉心于聚“精”会“神”,贾平凹对天地、人神、物我,皆有自家理解。他对“山水三层次说”别有所见,将之解作贾平凹感通天地、人神、物理的独特法门也未为不可。其“大实大虚”且相“圆融”,它是“作为‘道的形象的生活本身,是自然万物万象的天意运行”。如一朵花“由种子,由根由茎由叶而自然开花到散发芳香”⑥。如是说明或嫌不够,他参之以《心经》,王阳明的学说,克里希那穆提的灵修之道,来说明上述阐释的要义,在“让现实回到现实,让生活回到生活”,如此,“一切都是本来面目”⑦。
如将《晚熟的人》视为莫言“晚期风格”的表征,王德威以为其间仍有若干疑问,“所谓‘晚熟是饱识时务,是随波逐流,还是从心所欲——‘必逾矩?”⑧此处所言之“逾矩”,莫言并非个例,而是“晚期风格”特征之一种,它“涉及一种不和谐的、非静穆的紧张”,最为紧要的,是它“涉及一种刻意不具建设性的,逆行的创造”⑨。相较于《晚熟的人》之前的莫言,那种常有的“沉默中暴发的愤怒”,“饯于郊衢的狂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既属“强烈的批判”,亦为“热烈的赞歌”,《晚熟的人》则多为“离殇”,闻之教人“手足无措”,“彷徨于无地”⑩。此就书中人物和他们的生命情状,作者蕴藉抒发之情感论,如以章法、笔意观之,则又当何解?!李洱对此亦有洞见,以《晚熟的人》为界,此前作品(限于小说),皆属“虚构”,故而可以天马行空、肆意放旷,《晚熟的人》则属“非虚构”,其中诸作偏向不同,具体人物也异,然一真实的莫言贯穿全书,将之读作莫言“用小说的方式写下的自传式片段”未为不可。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或许在于,“以此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11。
“为活生生的现实赋形立传”,抑或“让现实回到现实,让生活回到生活”,莫言与贾平凹,路径不同,做法也异,但殊途而同归。他们共同,也是重新指向“生活”和“现实”。此“现实”已非彼“现实”,《晚熟的人》不同于《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长篇;《暂坐》《秦岭记》和《河山传》也不似《浮躁》《废都》《秦腔》。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写作者心之不同,则目之色异。一当再度直面现实,而不是如堂吉诃德如艾玛,和世界之间始终有个“欲望介体”(前人文本),眼前障蔽尽去,得现活泼灵机,其境近乎庄书所谓之朝彻、见独之境。何以言之?李敬泽笔下的鲁智深差可比拟。被赶出寺院的鲁智深一曲《寄生草》,唱得慷慨悲凉,也“顿挫出了释然快意,有一种‘破劲”:
鲁智深如果也读书、也写文章,此一去轻身向茫茫,不被归类不入流,鞋破帽破袈裟破,捧一只破钵提一支秃笔放空了随缘化,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认了自己的命,一栖二栖三栖十八栖,随处栖便无所栖,无所栖便随处栖,从此得了自在。12
所“破”者何?如何“自在”?莫言有莫言的路径,贾平凹有贾平凹的道理,其间虽有相通处,却不可强求一律。二人皆可谓高高山上立过,也深深海底行过,待到“随处栖便无所栖,无所栖便随处栖”的大自在之境,如何不生障蔽尽去的脱然顿悟。然欲破“障蔽”,便须反“常”。反常绝非全然逆反,而是合乎“道理”。所谓“反常合道”是也!无论所反者何,所合何“道”,任性自在为其根本。“晚期风格”与作家与文本世界与观念与文体与笔意和笔法之关系,要义便在此处。
二
将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的副标题“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译作“反常合道”,单德兴以为颇为允当。“反常合道”之说,出自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其词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以示书中所讨论的音乐家与文学家的晚期作品,虽不如早、中期作品之技巧精熟,结构完整,圆融和谐,却不拘泥于技巧、结构,反能突破框架,超越规矩,出格反常,‘令那些不知选样尝味之辈涩口、扎嘴而走”,然此另成之风格,“其实符合更高层次之道”13。“晚期风格”的要义,因之不在“术”而在“道”,不在技巧、文字等表层,而在观念、人格、趣味等内部。
若以《晚熟的人》为莫言“晚期风格”的开端,其观念之调适和技法之变化重点究竟何在?可以“奇”“正”之辨大略言之。论者谈莫言《晚熟的人》之前的作品,无论取径、进路有何差别,几乎皆难脱一“奇”字。“《透明的红萝卜》是夺目的,有元气,混沌而通透。《月光斩》戏拟了武侠和官场,而内里的暴力和清冷,令人想到鲁迅乃至蒲松龄(齐文化)的奇思异色”14。“经过大风大浪,作家看尽一切,传奇不奇,他要书写平常里的不堪,也要记录那屈辱里的高洁。”15此两处“奇”字,意义重心并不相同,却可谓是一体两面,用意仍在“奇”与“不奇”的起落、辩证。《红高粱》写奇人奇事,《生死疲劳》更是奇中有奇,同写高密东北乡,《晚熟的人》却是繁华落尽的风景。打铁的老韩,他的徒弟老三,使左镰的田奎,隐于其后不可或缺的“我”,奇乎哉?不奇也。“晚熟”的典型蒋二,早年痴傻,不可理喻,“晚熟”之后,出口成章,舌灿莲花,在东北乡呼风唤雨,弄出许多热闹,叫莫言自叹弗如。此人行径,类如“高参”,虽因时代之变而心理扭曲,却也属一类人物的日常性情。至于柳卫东、马秀美,经历奇也不奇,奇在个人命运攸关之际的出奇选择,不奇则在如此选择背后人心与人性的本然。那个几乎可以认定就是莫言的叙述者“我”对这一对夫妇经历的好奇在某一刻忽然散去,“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16自然风物随时而变,柳卫东和马秀美亦如早已成熟的高粱,悬挂枝头太久,因风雨侵蚀而发霉腐烂。然则发霉腐烂的高粱仍是高粱,枉披人皮行事卑劣的人仍然是人。他们行走在高密东北乡,行走在莫言身在其中的世界,“晚熟”得让人心惊,让人胆寒,让人为之纠结、为之慨叹,也为之齿冷。
何为“晚熟”?“晚熟”究竟能否对应于“晚期”——一种为阿多诺、萨义德所阐发的生命进入老境的观念与风格。通观全书,可知莫言“晚熟”的寓意,重心当不在此。蒋二或蒋天下对“晚熟”二字,自有明确定义:“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开窍,过耳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秃头生毛。”还如他说,“有的人,小时胆小,后来胆越来越大”,“有的人,少时胆大,长大后胆越来越小”,此即“早熟和晚熟的区别”17。这早、晚、生、熟背后当然有时间流逝今日非昨的感慨,必然也难脱时移世易观念变化的叹息,其意并非简单地指向萨义德所述之“晚期”。《晚熟的人》一十二篇,无论讲述何等样人,何种遭际,皆有今昔、物我、正反、变常的参差对照暗含其中。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莫言,境遇与心绪,与贾平凹庶几近之。如他写“高参”的主要阵地,在网络,她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欢喜得如同兔子,因她深知“得网络者得天下,失网络者失天下;得网络者得民心,失网络者失民心”。“网络是天堂,网络也是地狱”,其既可用来“伸张正义”,亦可用之“冤杀好人”18。《河山传》开篇,先述一段网络流言,且生如下感慨:“网络上的流言,多仇官仇富仇名,舆情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常常就演变成了一种暴力:诋毁、诽谤、造谣、谩骂。那可是山崩地裂、洪水猛兽。多少被网暴的人如一棵苗子正蓬勃生长,突然被掐掉尖儿,委顿而不能再分枝散叶,甚或有的从此抑郁,精神崩溃,跳楼自杀,一死了之。”19如是境况,与《红唇绿嘴》中的“高参”之流的种种行径何其相似乃尔!还如《表弟宁赛叶》,通篇虽未涉及网络暴力,但宁赛叶其人其思其想其行,或非“实写”,而是别有怀抱。他与那个金希普表面虽有不同,骨子里却属同类,皆是惯于兴风作浪、颠倒黑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晚熟的人》中皆处于前台,《河山传》中则居多隱于其后。后者开篇与结尾,均以这一则网络流言贯穿,却明显有反讽的意味。书中那个作家文丑良,多年来始终关切现实,有伦理关怀和责任意识,孰料却被呈红利用,落得个声名狼藉的结局。然虽以洗河与罗山身份的“互换”为基本结构,《河山传》却并非将之作为理解时代和人物的“认知图式”。书中没有绝对的“坏人”,但四十年风流云转,人事代谢,成后有败、起中有落,阳光普照之际,树下必有阴凉。罗山事业红红火火,生命却因偶然休止,读来令人感慨万端。但天行有常:四时流转、阴阳交替,死生无定,论暴烈或不输于《山本》所述宏阔历史背景下若干饮食男女的命运遭际。
同为“晚期风格”,《鳄鱼》却是另一番境界和义理。何以言之?且看《鳄鱼》后记莫言所述该作观念、人物及笔法渊源,用语直白,下笔肯定,绝无含混、歧义之处。如他感慨昔年好友,未发迹时人品尚可,一登高位便腐败变质。原因无他,“根源于他们心中失控的欲望”。欲望存在,无可厚非,但须节制,“因为欲望一过度就会成为贪欲,而满足贪欲的行为就会成为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占与夺取”,就会“造成社会不公、人心败坏,乃至引发动乱与灾难”。如古人论“慎独”的难度时所示,缺乏外在的规范,自我持守的工夫并不易得,遏制纵欲之害也不能简单委之个人的精神自觉,“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用法律来控制欲望,比道德教育发挥的效果应该更为明确”。此前同类题材作品,较少写此类人物“犯罪的原因”以及“犯罪后的反思”,莫言有心于此,欲从“人性”上找源头,且以为此属可以“比较深刻地揭示人性的角度”,亦是“能够触及读者(尤其是贪官)灵魂的角度”。在本能满足和德性修养所造就的自我的成就感之间,莫言显然偏于后者:“当一个被百姓爱戴的好官,替人民干了好事、立了功劳,这样的功利欲望的实现与满足,其幸福感、成就感,是庸俗低级的欲望满足无法相提并论的。”20《晚熟的人》中何以有如此众多的如魍魉似魑魅的人物?这一干人物年轻的时候,也曾活在《创业史》《山乡巨变》的世界里,他们锐意进取,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改天换地的雄心创造新的生活。如此气魄,这般雄心,如今安在?!
此属《鳄鱼》题旨与风格的要义所在,在“立”不在“破”,在“正”不在“奇”。何为“正”?依寇效信总括刘勰的意思,是“文章思想内容纯正,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规范”,其中“用‘事翔实可靠”,语言“平正畅达”而风格“典雅端庄”。“奇”则不然,思想“奇突新颖,标新立异”,用事“奇诡怪诞,荒唐不经”,辞采“奇崛瑰丽,振聋发聩”,风格“雄奇恣肆,不坠庸凡”21。如对刘勰此说不作胶柱鼓瑟解,则可知此处所论“奇”“正”,可与莫言早期与晚期风格(以《鳄鱼》为典范)约略对应。莫言、贾平凹数部晚期作品,关切的皆是现实以及现实中普通人的命运,即便书写暗处,怀抱中却有大光明、大悲悯、大坚持。这里面或许还包含着另一层值得点明的意思,无论以何面目描述现实,明暗、正反并非根本。根本在于,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现实的问题性,必然包含着“一种更具现实意味的召唤结构——呼唤自上而下的整体的、制度性的改革,以克服社会内部的‘危机”。如是思虑,近乎布洛赫所论之“希望”义,内蕴着“社会(文学)实践的伦理目的——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形态”22。其理亦如余华作品中人物历经种种困境之后,仍然保持的“一种精神和心灵”及其意义。“他笔下的人物独享自己的孤独”,然在“绝对虚空的存在之荒凉中”,“人的高尚精神与生命一起幸存”23。《文城》亦复如是。林祥福堪称极致的善良彰显的乃是一种人所秉有的内在的“纯洁的力量”。此境亦与其早期作品颇多不同,亦可解作“奇”后之“正”,或“破”后之“立”。因是之故,“破”“立”之间,应非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选择,而是如太极图阴阳两端交替更新、生生不已的状态。一言以蔽之,“破”的目的是“立”,是一种真正的,指向现实实践的深具建设性意义的向上力量。
三
无论以中国古典诗美概念的“老”(境),还是阿多诺、萨义德所论之“晚期风格”讨论莫言、贾平凹晚近十年风格之变及其意义,身体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身体衰弱,其文亦老,或“衰顿”或“老练”,或造境“平淡”,或刻意“绚烂”。其人不同,其境也异,“各各有其所逆之理、所逾之矩、所反之常、所离之经”24,“晚期风格”缘此亦呈纷繁多样之势。然以“自然”之境,最值得注意。朱庭珍《筱园诗话》论之甚详:
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种妙谛,实费功夫。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酝酿之熟,火色具融;涵养之纯,痕迹迸化。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也。此可以渐臻,而不可以强求。学者以为诗之进境,当于熔炼求之,经百炼而渐归自然,庶不至蹈空耳。25
此“自然”之境,源出于“性情”,成就于“熔炼”,非强力可至。今人论文,绝少言及“性情”,然人之品性、个性,诗情、世情、人情,纷繁复杂,杂糅其中,不分彼此,皆是文章所由之出的本源之一26。《晚熟的人》短制居多,汪洋恣肆的莫言显现出少有的节制。书中的莫言行走于高密东北乡,似乎眼前人事、物事、天下事皆为亲历,且有原型。但细细读来,可知此书仍属虚拟,即便其间不乏真实而具体的人事,然一当进入高密东北乡,进入那个文字所持存开显的寓意的世界,他们已不是现实中人,而是一个形象,一个行走的影子,登场片刻便悄然退场,也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麦克白》中此说适足以说明《晚熟的人》中的人事。《左镰》《斗士》《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天下太平》《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中的高密东北乡又不是同一世界。这里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正写,有反写;有实写不尽又虚写,反写不尽又正写,或者干脆正言若反,反言若正,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看似写实,实则写意;貌如嘲讽,实为悲悯。笔法也颇多摇曳,并非一味实写,有空隙,有留白,也沉痛也快意处叫人为之动容,且看首篇《左镰》述及打铁的场景:
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27
这哪里是写铁匠劳作的风景,俨然便是这一部《晚熟的人》的旨趣、章法和笔意形象化描述。时空自由转换,人物随意来去,场景变化无定。线性、循环;善、惡;过去、现在;自我、他者;美、丑等无分轩轾,共同出现在虚拟或实在的高密东北乡。作者所感受的冷热、炎凉、坚硬和温柔,写作时的沉痛和快意均不难得见。如《晚熟的人》先写蒋二;再写常林与蛟河农场的故事,写常林与单雄飞比武,引出那滚地神龙蒋启善;后再写蒋二、单雄飞等,其间虽有关联,但用笔洒脱自由。还如《火把与口哨》,开篇为宋魁故事,由之引出杨结巴;再写三叔和三婶故事;后又述及三叔此前结识的那三位朋友:郑华波、邓然、邱开平,写他们如何与杨结巴义结金兰;三叔去后,又写三婶失去子女,怒杀群狼之后绝食自尽……篇幅虽然不长,故事却丰富复杂,中间转折起伏,真如莫言文中感慨:“情况大概如此,大家看,这哪里像是写小说啊?简直是写交代材料或是记流水账。”这话应属反话正说,《火把与口哨》并非流水账,也不是事事皆记,其中所写未必多于“未写”,实境未必多于虚境。笔法之摇曳自如,脱然快意,前引朱廷珍所论“自然”之境足以说明。
同臻“自然”之境,贾平凹《山本》《暂坐》《秦岭记》及《河山传》诸作取径并不相同。贾平凹有意法古,至今四十余年矣。先取古典意象,再习古人笔法。源流、取径亦有不同。《带灯》之前,或可分明清世情小说传统与两汉史家笔法,前者柔婉而后者刚健;前者偏于写意而后者重在写实;前者如阴如柔,后者则如阳如刚;乾坤有别,笔法有异,虽属同源,流脉却有分别。《山本》之后,可谓浑融。《秦岭记》主体内容五十七篇,皆为短制,旨趣、笔法亦各有不同,如山如水如云如雾如花如草如木,看似写实,实则写意。其文如泰山出云,莫有规矩;如百川汇流,自如来去,看似随意挥洒,骨子里却尽有分数。《河山传》文法亦是。洗河与罗山事业的起落、成败,贯穿全书,时间跨度四十余年,所涉内容之庞杂、繁复自不待言。但作者一气写来,人物、情节皆为文思驱动,断续、开阖、动静、张弛皆如流水行云、任意所之,左右逢源却无不合“道”(核心观念、章法和笔意)。其境如古人论书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通会”二字,乃是根本。天地之间,万象并生,人所能感通发挥之境可谓多矣。文可以如山峦之起伏,亦可如江河之涛涛,所“象”之“形”不同,呈示之心性与才情也异。“晚期风格”所开之不同境界,根源便在此处。
《河山传》后记结尾处,贾平凹言及谪居黄州,躬耕于东坡的苏轼,对照的自然是他的心境。苏轼其时,生命已近“晚期”,常以“老翁”自居,然如思兄弟二人,早年苦读于眉山,声名初起于京师,此后却宦海沉浮,不得已亦不得志,经世济民之心犹热,所成却极为有限,怎不教人心劳神伤。此亦合萨义德所论若干音乐家与文学家身处老境却“未达究竟、未臻完美”,甚或有“冥顽不化、难解,还有未解决的矛盾”。此即阿多诺所言之“灾难”,萨义德所论之“不和谐的、非静穆的紧张”。究其实,萨义德书中所显现之“种种未竟”,更让人“深切领会并如实面对艺术与生命中的衰老、无奈、不圆满与无可如何”。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万象万境,无可无不可,悉皆坦然接受,“将缺憾还诸天地”28。
【注释】
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413页。
②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③⑧15王德威:《晚期风格的开始——莫言〈晚熟的人〉》,《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④贾平凹:《秦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第261页。
⑤舒晋瑜、李敬泽:《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⑥⑦贾平凹:《关于“山水三层次说”的认识——在陕西文学院培训班讲话》,《当代》2020年第5期。
⑨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淮栋译,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0,第85页。
⑩11《〈晚熟的人〉评论小辑》,《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12李敬泽:《何枝可栖,醉打山門》,《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1328单德兴:《导读之一未竟之评论与具现》,载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淮栋译,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0,第23页。
14莫言、木叶:《文学的造反》,《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16171827莫言:《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第132-133、46、238、15页。
19贾平凹:《河山传》,作家出版社,2023,第1页。
20莫言:《鳄鱼》,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第187-197页。
21周振甫:《释刘勰的“风骨”与“奇正”》,《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22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23陈晓明:《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
24彭淮栋:《译者序反常而合道:晚期风格》,载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常合道的音乐与文学》,彭淮栋译,台北麦田出版: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10,第52页。
25蒋寅:《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26关于人格与文风之关系的细致讨论,可参见吴俊:《先生气象:识才与雅量——从王瑶先生说到谢冕先生》,《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张新颖:《陈思和老师的少年回忆——〈1966-1970:暗淡岁月〉读记》,《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杨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