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居间性到艺术的边界本体论
2024-02-23□李洋
□李 洋
【导 读】 近十年来, 艺术史的全球化转向与中国艺术学科的建制争论是艺术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背景, 其实二者在内在是彼此相关的, 艺术史写作方法的变革昭示着新的艺术观念的诞生, 周宪教授的《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 展现了他围绕这两个话题的集中思考。
一、 全球化转向与中国的艺术建制
2000 年以来, 欧美艺术学界出现了艺术史的全球化转向 (global turn)。 从汉斯·贝尔廷 (Hans Belting) 到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 从吉尔·卡西德(Jill Casid)到雅希·埃尔斯纳(Ja Elsner), “全球化” 的提出不仅关涉民族国家之间地理意义上的跨国、 跨文化, 更针对根植于艺术史书写的等级秩序:欧洲中心主义、 男性中心主义、 造型艺术的优越性、 传统媒介的优先性等, 与单一线性历史书写交缠在一起, 构成了艺术史知识生产的中心。[1]巫鸿教授2023 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漫游与偶遇”, 也明确提出探寻一条可以呼应全球化转向的艺术史路径。[2]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 更是把艺术史的去中心化拓展到艺术史学史, 他以冷静而中立的年代作为章节, 突显世界各地的艺术理论的历史平等性。[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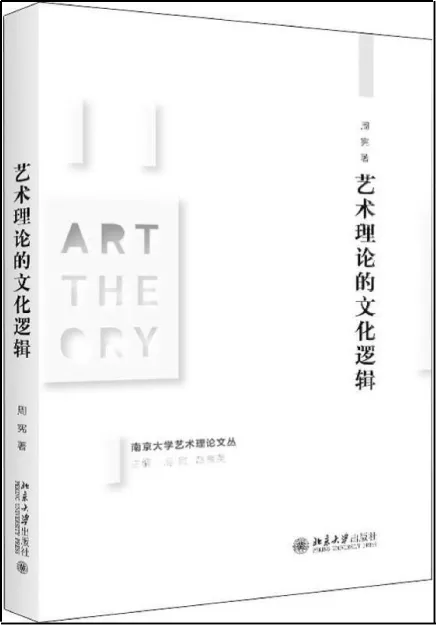
当欧美学界掀动艺术史的全球化时, 中国艺术学界正紧锣密鼓地完成艺术理论的学科建制。 这场对艺术学进行系统性和基础性反思的理论运动, 缘于2011 年国务院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 这是一场似乎没有号角的运动, 艺术学的建制激活了学者们去探讨艺术的定义、 范围与学术体系, 诸如王一川、 彭锋、 周星、 夏燕靖等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对中国艺术学科的知识体系及其合法性展开了深入的阐发与论争, 这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罕见的, 其深远影响或许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去评估。 发生在中国的艺术学科建制争鸣与发生在欧美的艺术史全球化转向, 二者遥相呼应, 成为近十年来艺术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议题。
艺术史转向与艺术理论的建制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们可以把艺术史理解为一种对艺术的定义, 因此全球艺术史的提出, 也是一种对新的艺术观的召唤。 周宪教授的《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 (2018) 正是在这样的双重学术背景下尝试重构艺术理论的著作, 也是他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集中体现。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从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与具体门类艺术的创作现象, 对艺术理论的可能性及其当代特征展开论述。 周宪把当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艺术理论分为三种类型, 即主导型、 古典型和新兴型, 用话语的象征资本理论分析了三者的关系。 “主导地位的理论话语具有较多象征资本, 往往与体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起作用; 传统的甚至较为保守的话语, 特别是有关古典话语的研究, 也具有一定的市场; 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新锐激进的话语, 它们不断挑战已有的理论, 提出新的理论观念。 这三种话语相互角力抵牾, 形成了艺术理论场域的内在张力。”[4]12周宪在保留艺术理论的整体性基础上, 选取了艺术理论建制中的焦点问题, 逐一分析, 逐个击破, 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和坚定的雄辩, 梳理了重建艺术理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假如概括这本书的理论贡献, 那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一种以居间性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
艺术理论当然是一种 “本体论”, 必须关涉本体, 但在强调反本质主义和全球化的今天, 艺术理论仿佛成为一种没有本质的本体论,或者说一种意义的本体论、 一种关系的本体论。 新的艺术理论务必要在与艺术史、 艺术批评、 美学和门类艺术理论的关系中, 确立自己的价值。 周宪最具前瞻性的洞见, 就是通过这些关系的分析, 提出了艺术理论的居间性。
二、 艺术理论的居间性
在这本书的开始, 周宪就开宗明义, 认为中国艺术理论在学术建制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争议, 正是因为居间性。[5]“一方面表明了它(艺术理论) 是一个延展性和关涉性很强的知识系统,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边界是模糊的, 与其他知识系统相互交错。”[4]4因此, 他不否认艺术理论的模糊性、 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 相反, 应该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评估艺术理论的居间性, 挖掘这种特性的优势。 首先, 居间性体现在美学、 门类艺术理论的“之间”:
艺术理论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知识领域。 它介于美学和部门艺术理论之间的居间性, 既是它所短又是它所长。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 居间性使得艺术理论可以上通下达, 对艺术研究起到更加有效的作用。 正是这种居间性, 所以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进入艺术理论的场域, 构成了复杂的学术共同体, 进而形成了一种协商性的合力状态。[4]17
沿着居间性理论, 周宪分析了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关系、 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 艺术家与美学家的关系等。 正是由于居间性,恰恰是这些看上去彼此冲突的关系,为建立艺术的系统知识提供了灵活的自主性和丰富的内涵。 “居间的定位要求艺术理论努力去建构属于自己知识体系的相关概念、 范畴、 方法和原理,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美学理论, 同时有区别于门类艺术的具体理论。”[4]8周宪进一步指出, 居间性的形成在于艺术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是建构边界、 切分价值。 “划清边界, 也就是区分不同的事物、 知识、 对象, 其实这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4]88他借由哈贝马斯的理论, 指出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是对世界“分岔”,把人类活动区分出不同的价值域,把艺术区分为不同的门类。 周宪没有激进地把“居间性” 简单地推给后现代主义, 而是回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对真、 善、 美的分化, 认为这种分化形成的结构化与体制化,让艺术理论不得不处在居间的状态。“艺术是现代性的产物, 现代性的分化使艺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价值领域而出现。 真、 善、 美的区分既为艺术的自主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又为艺术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4]91-92
周宪对艺术理论之 “居间性”的强调,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艺术的方式, 即艺术的问题不在于本质, 而在于边界。
三、 从“居间性” 到“边界”
艺术研究中布满了各种边界。但周宪强调, 这些边界不是不能跨越, 恰恰相反, 艺术理论的居间性、不可定义性, 恰恰是理解艺术本质的关键。 艺术理论开始于对艺术的定义。 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的“艺术终结论” 复兴了对艺术边界的思考, 但在诸多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划界的理论中, 周宪提出:“艺术边界的问题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界定或思辨的问题, 毋宁说, 它是由艺术界内部不同角色——艺术家和美学家——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现代性问题”[4]106。 周宪对艺术边界的历史条件和意涵进行分析, 尝试回应理论界不断重复的艺术与非艺术的定义问题, 即艺术的身份问题,边界成为他厘清这些复杂关系的标尺。 比如, 他提出: “对于艺术家来说, 所谓的艺术边界也许并不存在,恣意妄为天马行空是他们的本性;对于美学家来说, 没有边界的艺术将不再是艺术, 没有边界遂将取消美学家存在的理由, 只要有美学家,就免不了要去界划艺术的边界。 艺术家感性突围和越界, 美学家理智测量与划界, 这一张力关系构成了现代艺术边界亦破亦立的关系”[4]113。在《艺术家与美学家的角色冲突》中, 他明确引入边界理论, 概括了艺术家与美学家这两个至关重要又彼此不同的角色。 他十分明确地把“边界” 这个问题提升到艺术理论的核心, 并富有洞见地提出: 不断划定艺术的边界是一种理论的徒劳,与其不断回到艺术的定义与边界的问题, 不如清醒地意识到: 艺术的本质不是划定边界, 而是突破边界。
周宪把艺术领域边界丛生的现象归因于现代性的出现与资本法则对艺术的入侵, 这体现在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边界在艺术市场上的模糊甚至消失, 尤其是19 世纪下半叶以来, 资本对艺术界进行日益严重的渗透和支配, 让艺术家被资本和市场裹挟。 “艺术的边界再一次被打得粉碎……艺术中商品的特征越是明显, 就将越是迅速地导致艺术的消失, 而艺术的边界也就越发难以存在”[4]98,100。
对边界的关注也体现在对新的艺术史方法的关注上。 在新近关于数字艺术史(Digital Art History) 的研究中, 周宪梳理了主要使用计算、数据挖掘和信息可视化等方法的艺术史研究, 认为信息科学的工具可以帮助艺术史学家把握那些可计算、可分析、 可数据化的内容。 数字艺术史的提出主要在于打破了艺术史的边界, “没有明确边界的领域……很多艺术史相关问题由于通过数字人文视角来审视和解析, 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艺术史研究”[6]。 数据计算的技术优势会在分析艺术史中那些跨地域、 超大空间、 长时段的对象方面凸显出来。
周宪尽管认识到边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但他反对不断为边界立法的行为。 他在几篇文章中反复提到, 不断地设立边界其实是一种理论的内耗, “为艺术划定一个边界实在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费力之举,也许它根本无法得到解决。 但反对这一看法的人仍在孜孜不倦地在为艺术划界, 提出了无数假说。 ……过了好多年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些假说好像都在原地踏步, 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4]103。 中国在艺术理论建制过程中, 关键问题在于面对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艺术的边界问题由现代性而产生, 因此过于沉重, 而艺术的本性是反边界的。[7]他坚持以后现代的策略去面对边界的问题。 “从后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性来看, 艺术无边界。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为什么要给艺术划出一个确定的边界呢?”[4]100后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就是对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分化, 实施“去分化” 的操作, 这意味着对边界的拒绝。
四、 从“艺术的边界”到“边界本体论”
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一条与“批判的边界理论” 不同的道路。 我在一篇关于艺术史方法论的文章中,初步概括了什么是“边界本体论”,可以与周宪的居间性论和边界论形成呼应或补充。[8]所谓“艺术边界的本体论”, 不仅指重新定义艺术的边界(民族国家艺术史、 艺术体制论、 艺术终结论等), 更强调艺术史写作的去中心化, 即强调艺术的本质就包含了不断试探边界、 修正边界和创造边界。 艺术并不是“跨界”, 艺术的本能就是不断挑战和突破边界。
诚如周宪所说, 现代性以来,各种形式的边界在艺术研究中被生产出来, 形形色色的定义、 界限、藩篱和栅栏, 成为艺术研究的障碍。边界有许多接近的术语, 边缘、 交界、 边境等, 这些不同的名称在地理、 数学、 政治等不同领域很难被真正澄清, 工具书对这些术语的解释也是相互参照、 循环替代。 然而,艺术边界的本体论必须澄清“边界”的不同形式及其在艺术中的表现。边界是物质的交界处(物、 艺术品的区分) 或社会流动的交界处(身份、 共同体的区分), 边界在各个语境中的每一层含义及其现实中的对应形式, 都揭示了艺术诸多令人神迷又令人困惑的特征, 也能恰当地阐释艺术形式和质料在风格演化中的流动与交融。 当我们反思艺术作为边界的特性时, 作为居间性的艺术理论自然应运而生。
我认为, 艺术的边界本体论克服艺术史(全球化转向) 与艺术理论(中国艺术学科建制) 共同面临三个问题。
首先, 它克服了民族国家的问题, 即把艺术的“边界现象” 简化为地理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切分,从而忽视了艺术创作在材料和语言上的“接壤”。 同样, 艺术与非艺术之间、 门类艺术之间、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之间、 艺术家与美学家之间,艺术的边界本体论关注它们在“地表” 之下隐含的构成关系和动力过程。 周宪把这种关系阐述为一种尚未被充分理解的 “张力” 与 “协商”。 张力最大、 协商性最强的地方, 就发生在边界。
其次, 艺术作为边界, 不是在分化与差异的运动中被动形成的痕迹, 也不是艺术的媒介、 技法、 语言、 风格、 类型之间对峙的结果,而是一个主动对艺术世界划分类型的知识技术。 它既不能被还原为政治中的权力, 也不能被还原为几何学意义的抽象的线。 边界像一把足够锋利的剪刀, 把看上去连续平滑的表面裁剪成两个部分, 或者在边界内部创造新的边界, 以揭示出艺术世界隐藏的差异与看不见的张力,并以此彰显边界自身的独特性。
最后, 边界是一个流动的领域,不是静态的、 没有质量的边线。 人们之所以把边界设想为稳定的, 是因为被切开的两个世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张力平衡。 用周宪的话说,就是“协商中的平衡”。 边界自身包含着大量的作品, 而且一直在运动和变化, 甚至在不断生成。 作为边界的艺术作品同时具备两个世界的特征, 但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不同的艺术世界需要边界来区分彼此, 但边界作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世界。 边界的运动调节了两个交界的艺术世界的互动与变化, 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提供新的经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