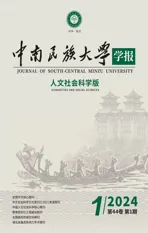全球史视域下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形成
2024-02-23黄达远孔令昊
黄达远 孔令昊
(1.西安外国语大学 丝绸之路与欧亚文明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00;2.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一、“关中-七河”沿线的跨区域交流:城镇带的形成
关中平原是中国西北部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之地。渭河以南是秦岭北麓河川交错地带,植被丰腴。渭河北岸至黄土高原南缘则为一片干燥地带,秦汉时期,该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物资供应的灌溉网络,是最为富饶的谷仓地带。秦岭北麓辽阔的台地,隋唐时是一片绿地,可供长安城贵族们打猎享乐。由此可见,关中平原的土地利用,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其一贯的格局[3]。
关中平原所在的中国西北部,正好处于不同风俗、不同历史区域的交错地带。该地区可以通过河西走廊连接新疆,通往西藏;而由关中平原出发,经黄土高原或山西,则与蒙古相连;经山西陆路与北方相连;翻越秦岭可以到达蜀地;经渭河、汉水可以通往长江中游,具有无与伦比的通达性。冀朝鼎曾提出过“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论证中原王朝统一的经济基础[4]。欧文·拉铁摩尔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区”的概念,即该区域所形成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往往高于经济功能,西北的战略区在经济上对于中原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中原王朝需要举全国之力为其提供必要物资,确保“战略区”能够正常运转[5]。因为“基本经济区”与“战略区”分别位于中原地带与草原、绿洲地带,则这一运转体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枢纽来连结,而这个强有力的枢纽一般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核心区”。关中平原是各种文化的大熔炉。该地区在交通和心态上都比较容易接受外来事物,因而可以作为普遍文化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枢纽地区(即“政治核心区”)。只有当中原王朝呈现出农牧复合的特质时,靠近农牧交错地带的区域才会成为“政治核心区”。
七河地区涵盖了中天山与西天山的部分区域,其绿洲是天山北麓草原绿洲的延伸,这种绿洲形态介于草原与绿洲之间,具有极强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从绿洲性质看,七河地区的草原绿洲无疑是更容易受到游牧政权的控制(2)拉铁摩尔认为,草原绿洲徘徊于各种可能的发展形态之间,绿洲农业与草原游牧交替出现。参见欧文·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因为这种过渡地带既适宜放牧,也适合农耕。七河地区兼具了这两种生产模式。其农业承载力高于草原地区,低于农耕地区,其农业模式属于旱作农业。七河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依托于高山流水而形成绿洲、草场与商道。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将七河地区的楚河流域称为另一个“河西走廊”[6]3。历史上该地区经常作为草原民族统治的核心地带,形成强大的游牧政权,但河西走廊刚好相反。究其原因,七河地区的牧区、绿洲的空间分布格局值得关注。
拜占庭史家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记载,蔡马库斯访问西突厥时,发现室点密可汗(弥南德记作Sizabulus)的牙帐位于一座名为艾克塔的山上,希腊语意为“金山”[7]171。西突厥可汗的冬季驻地位于此山中。七河地区的夏季尤为炎热[8]。因此,西突厥可汗拥有自己的夏日避暑营地,这一地区即是位于碎叶与塔拉斯城之间的千泉。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千泉在哈萨克斯坦梅尔克附近[9]344。不过,玄奘说千泉“地方二百余里”,那么梅尔克可能只是千泉南境。千泉北境也许在西突厥可汗王庭所在地“羯丹山”[10]。不难看出,七河地区的绿洲农耕地带与牧区高度重合,使得定居人群与游牧人群能够形成一种混合经济共同体,这正是其成为草原核心区的关键。
七河地区的游牧政权控制着蒙古高原势力进入河中绿洲的要道,因而容易与其发生冲突。这些游牧政权兼具草原绿洲的特质,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势力作为侧翼牵制北方游牧力量,这是它在汉唐时期与中原政权关系友好的重要因素,也是该地区被称为另一个“河西走廊”的原因之一[6]201。汉朝曾与乌孙和亲,并联合乌孙的力量对抗匈奴[11]。南北朝时期,乌孙由于屡次遭到柔然的袭击而迁徙至葱岭地区[12]2267。取而代之的悦般也曾与柔然敌对,并派遣使者前往北魏,意图与其结盟并一同进攻柔然[12]2269。唐代虽然消灭了七河地区的西突厥汗国并建立了碎叶城,但仍依靠突厥人与粟特人来控制当地。当突骑施兴起时,唐王朝将碎叶城交与突骑施可汗苏禄(3)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七年(719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此处“十姓可汗”指的应是苏禄。参见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30页。。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否认七河游牧势力的“两属”现象。它与蒙古高原游牧势力之间也存在着交往关系。《汉书·西域传》就记载乌孙及其以西的一些国家曾在一段时间内“近匈奴”[13]。悦般在遣使北魏以前,也曾“与蠕蠕结好”[12]2268。
在两大异质性的政权之间,是由河西走廊与天山组成的“过渡地带”,这条“过渡地带”就是内陆亚洲的绿洲地带。由关中平原向西,即可进入内陆绿洲区。欧文·拉铁摩尔发现了绿洲社会的多种形态,他将内陆亚洲地区的绿洲划分为次绿洲、沙漠绿洲与草原绿洲。河西走廊是次绿洲与沙漠绿洲,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是沙漠绿洲,天山北麓则是草原绿洲。荣新江等揭示了绿洲人群对于“历史中国”的影响。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公元前121年以来,如果把散布于天山南北的绿洲相连,再将其与丝绸之路连接的话,这一部分正好是东西交通的枢纽,是一座连接中国与中亚的桥梁。这座桥梁称作“甘肃绿洲桥”[14]。“绿洲桥”作为一种通道,一端是长安、洛阳等中国的腹心城市,另一端是昭武九姓等河中地区的城市,更远的一端则是地中海腹地城市[15]。
绿洲形态中最为特殊的是“次绿洲”。沿着从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及自南部流来的支流,散布着许多可以灌溉的土地,它们叫作“次绿洲”[16]108。从兰州继续往西,则河西走廊的地理景观逐渐从“次绿洲”转变为“沙漠绿洲”,这种“次绿洲-沙漠绿洲”的渐变景观是河西走廊的底色。因为次绿洲与关中农耕区的环境较为接近,因而更容易为中原王朝所控制。因此,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很早就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中原王朝向西方发展的路径主要是经过河西走廊抵达西域的丝绸之路。而打通河西走廊的计划,只有依赖中原王朝强大的国家力量方能实现。此外,河西走廊作为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带,具有一种非常立体的历史区域关系:蒙古草原、中原农耕、西域绿洲与雪域高原都对河西走廊施加影响,使得其历史时空的关系尺度呈现出混合性与复杂性。
由河西走廊的张掖向西,经敦煌可以抵达天山山脉的东部区域。松田寿男指出,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拉铁摩尔也指出,新疆的地理重心是天山[16]100。天山对于内陆亚洲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南北方向来看,天山是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的分界线。天山的地理空间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南边是塔里木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这两大盆地的自然特征有极大差异。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属于沙漠绿洲,适宜旱作农业,而准噶尔盆地属于草原绿洲,农牧业兼具,但更偏向牧业。
从东西方向来看,天山也是多元文化的分界线。天山可以分为东天山(以博格达山、巴里坤山为主体的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以及巴里坤盆地)、中天山(夹在在博罗科努山、哈尔克他乌山等山脉之间的伊犁河谷地带以及南麓的各沙漠绿洲)、西天山(以塔拉斯山、吉尔吉斯山为主体的楚河河谷、塔拉斯河谷,以及依托阿赖山及其支脉而形成的饥饿草原)、南天山(夹杂在费尔干纳山与阿赖山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以及依托阿赖山的两个分支山脉而形成的泽拉夫尚河谷与喜萨尔盆地)等四个板块,这构成了多元文化交流的空间。东天山受到中原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影响。中天山受到蒙古高原游牧文化、沙漠绿洲文化以及西天山游牧文化的影响。西天山以游牧文化为主导,这种游牧文化是与蒙古高原不同的草原绿洲游牧文化,同时它也受到南天山沙漠绿洲文化的影响。南天山是沙漠绿洲文化,但该区域的沙漠绿洲比塔里木盆地的规模要大,这些绿洲受到西天山游牧文化、西方“波斯-希腊”混合文化和南方印度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对方。
由此,“关中-七河”沿线形成了三条主要的城镇带,可被归纳为两种类型:“次绿洲-沙漠绿洲”城镇带与“草原绿洲”城镇带。
从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到中亚河中地区的南北两条城镇带即是“次绿洲-沙漠绿洲”城镇带,这两条城镇带更偏向于农业生产,因而历史上更易被中原王朝所控制。河西走廊的经济核心区无疑是坐落于肥沃扇状地带的甘州(张掖)与凉州(武威)。凉州是连接关中地区与西域的重要枢纽城镇,但由于该地区一开始尚未得到开发,因而河西地区在7世纪末期的中心是甘州[17]68-70,《新唐书》称“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18]。8世纪前半期,凉州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中心[17]163-164。即便如此,河西走廊的文化核心区与交通枢纽是被称作“华戎交所一都会”的敦煌[19],季羡林称之为“世界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汇聚之中心”[20]。中原王朝通过敦煌对伊吾、高昌等地进行持续性的经营,这使得东天山地区与敦煌逐渐形成了一种地缘关联性[21]。
自敦煌向西,可达伊吾、高昌、鄯善,这三个地区都是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个城镇带的枢纽。由伊吾向北,可进入草原城镇带,向西则前往高昌、焉耆、龟兹等处,最终经疏勒可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乃至中亚河中地区,而高昌、焉耆、龟兹又有道路可通往作为草原城镇带核心城市之一的庭州,河中地区的粟特诸城邦可通过石国(即今塔什干地区)与七河地区的碎叶城产生联系,因而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沙漠绿洲城镇带可与天山北麓的草原绿洲城镇带形成相互联动的格局。唐朝以天山廊道为依托至少分布有56屯的大规模屯田,使得天山北麓与天山南麓的两条城镇带被整合为重要的战略核心区[22]。鄯善曾在隋末毁于战乱。据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记载,贞观时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在鄯善故地上重新修筑了典合城(即后来的石城镇,原隋朝鄯善镇),后又修筑了屯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城镇,因而形成了以石城镇(鄯善)为核心的城镇体系[23]61-62。由鄯善向西,可达且末、于阗等地,最终经由渴槃陀与吐火罗斯坦以及印度河上游诸城镇、聚落产生联系。尼古拉·辛姆斯-威廉姆斯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一则粟特文题记,揭示了古印度北部地区与渴槃陀的联系[24]。关中平原通过这两条城镇带与帕米尔高原乃至域外中亚、西亚、南亚等地产生联系。
“草原绿洲”城镇带从东天山开始,一直绵延至七河地区,沿途的庭州、轮台、弓月、碎叶、塔拉斯等城镇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商人聚集之地。这条“草原绿洲”城镇带通过石国可与河中粟特诸城邦产生联系,最终汇入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城镇带,甚至可以通过该城镇带与地中海沿岸诸城市产生联系。2018年至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唐代墩古城遗址(唐代庭州所辖蒲类县),就曾发现唐代至高昌回鹘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景教寺院遗址以及公元10至13世纪的罗马式公共浴场遗址,可见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密切[25-26]。
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能够以天山北麓和七河流域的“草原绿洲”城镇带作为进入域外中亚地区的枢纽。而中原王朝也可以通过这条城镇带与七河地区的游牧政权取得联系。唐代在天山北麓的“草原绿洲”城镇带上构建了以北庭为中心的三条东西向的防线,切实有效地实现了对天山以北的管控[27]。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书残片《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表明,粟特商人往来于弓月、龟兹、长安等地[28],足可证明“草原绿洲”城镇带与“次绿洲-沙漠绿洲”城镇带密切了中原内地与七河地区的联系。
“关中-七河”沿线各区域的地理环境特质,造就了各人群生计模式的差异,这提供了区域经济互补的可能性,进而带来跨区域的交流,并进一步塑造了丝路东段沿线的三条主要的城镇带,连绵不断的绿洲城市网络,奠定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形成的基础。
二、商道开拓与区域整合: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与兴盛
虽然在汉朝时,中原农耕区就与七河地区的乌孙有一定的联系。但新商道的开拓以及各区域的整合,才使得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成为可能。
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离不开新北道的开辟与畅通。所谓的新北道,主要由域内的伊吾道与域外的石国道构成。早在东汉时期,伊吾道就已开辟,即“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29]。但这一通道最初并未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魏书·西域传》所记载的西域四道(其实依然是塔里木盆地两侧的通道)中并无伊吾道(4)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参见魏收著:《魏书》卷一百二十《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1页。。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天山北麓一直处于蒙古高原游牧势力的掌控之下。游牧势力能够南下影响塔里木盆地,阻碍中原政权与七河地区的联系。早在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匈奴军臣单于就认为“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30],并以此为由扣押了张骞与堂邑父。这一态度也被后来的游牧势力所继承。北魏时期的王恩生曾出使西域,被控制东天山的柔然扣留[12]226[31]3212。柔然封唐契为伊吾王[32],从而控制了东汉时期开辟的伊吾道,并能南下敦煌,进而影响从敦煌至高昌的新道(即唐代的“大海道”)(5)该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参见陈寿著:《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59页。。因此,当时的西域主干道依然是以鄯善为枢纽的塔里木盆地南道。
为了疏通北部商道,北魏曾于太安二年(456年)派遣尉眷攻克伊吾,但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柔然依然数次进攻敦煌地区,这使得尉眷之子尉多侯又“上疏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33]。北魏孝文帝由于春耕正在进行,而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在北朝中后期,伊吾道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大海道,原因在于大海道需经过莫贺延碛,旅途十分凶险。根据《北史·西域传》可知:“自敦煌向其国(高昌),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31]3215而5世纪中期粟特人占据伊吾,使得粟特人的商业路线转向伊吾道,这也直接导致了伊吾路的兴起[34]。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献城内服[35],伊吾道得以畅通。
北魏分裂后,中原王朝再次丧失了对伊吾的控制。隋朝于大业四年(608年)在原伊吾城以东修筑了新伊吾城,后在此设郡,并且使高昌王麴伯雅归附隋朝[36],这为唐王朝经略西域打下了基础。隋朝对于西域的经略,使得伊吾道最终成为了丝路要道。在《隋书》中,包括伊吾道的新北道从伊吾(哈密)越过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37]。可见,敦煌、伊吾已然成为河西走廊与七河地区相互连结的核心区域。唐代之后,庭州成为新北道的枢纽,以该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支路。例如:从庭州经回鹘牙帐至长安的回鹘道,从庭州至西州(高昌)的他地道、乌骨道与赤亭道,以及从庭州经轮台至焉耆的焉耆道[38]。此外,从龟兹向西经大石城翻越凌山的“热海道”也可抵达七河地区的碎叶城[39]。
新北道通过这些支路与中道乃至原本的草原道相互连接,构成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道路网络体系,但新北道的开通不应只注意到伊吾道路的畅通,还需要从域外予以进一步地审视。石国道的开辟与使用也是新北道成为丝路干线的重要因素。早在波斯阿契美王朝时期,河中的粟特本土就与锡尔河北岸的塞人产生贸易上的往来,可以推测那时就已经有从索格狄亚那到北方草原的商道。亚历山大的征服,可能迫使一部分粟特人北迁七河地区[40]。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阿布鲁依在布哈拉的专制统治迫使当地的德赫干和富商逃往塔拉斯,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41]。这些粟特居民点是沿着500到1000米的山麓东西排开。粟特聚落向北方的延伸促进了七河地区的城市化以及该地区的农业发展[42]72。在七河地区粟特移民城邦兴起的基础上,石国道被正式开辟。但根据相关汉文史料的记载,石国道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应当还是在北朝中后期。
巴托尔德指出,7世纪费尔干纳盆地(拔汗那,Fergana)地区发生叛乱,使得商路北移。商人从撒马儿罕取路向东北方,经由塔什干和鄂里亚·阿塔进入七河地区,直抵楚河河岸[43]。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宁远国(拔汗那)在贞观年间遭到西突厥的攻击,国王被杀[44]。巴托尔德所说的动乱应是指该事件。沙畹也考证了中原王朝与突厥汗国交战以及平时交往、交流常用的道路[45],与巴托尔德所述通道大体类似。但笔者认为,巴托尔德将石国道的使用归因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隋书》中就已提及新北道(囊括了伊吾道与石国道)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干道的地位[37]。事实上,考虑到七河地区是各异质性社会的交汇地带,同时又是游牧政权(西突厥)的核心区,自然会产生农耕、游牧、绿洲互动的贸易需求,因而石国道的开辟与使用也在情理之中。社会的日常需求使得石国道的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偶然的战争只是使得这条商道愈发重要而已。
伊吾道、石国道的开辟与畅通,使得新北道最终于隋代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条新通道通过敦煌、伊吾(伊州)、西州(高昌)、庭州、碎叶、石国等枢纽地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七河地区乃至中亚的河中地带,从而使得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成为可能。七河地区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上。从中国来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北道还是南道,都能在碎叶城、塔拉斯城交会,因此,玄奘称此二城内“诸国商胡杂居”[46]。顺着楚河河谷西去,丝路从此分成了北方的“草原之路”和南方的“绿洲之路”。当然,如果从此沿着锡尔河北岸往西北走,可以通往饥饿草原及东欧大草原;向南转折,则是进入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绿洲群。而若从这里越过兴都库什山,经阿富汗即可直达印度,或者绕过咸海、里海,西去波斯、阿拉伯、罗马。
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文明交流的作用产生于强大国家行为体政治、军事目标实现的过程中[47]。唐代“长安-天山”跨区域廊道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其长距离贸易离不开权力关系的维系,这种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游牧(如东西突厥、回鹘)、农耕(唐朝)、绿洲(粟特)三个主要政权或群体的地缘合作上。
唐王朝以疆域辽阔、族群成员众多、与外界沟通频繁而载入史册[48],这体现在它与周边诸地缘体的多边互动上。唯有通过全球史的视角进行整体性考察,我们才能揭示这种互动模式,“在考察东方唐帝国内部出现的种种动向的同时,中亚的游牧与绿洲定居社会的活动,波斯帝国与西亚阿拉伯势力扩展之关联,乃至地中海周围东罗马和拉丁基督教社会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交往呈现出何种相貌或状态等等,也同样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2]。陈寅恪所提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49]就具有全球史视野。蔡鸿生认为,这是“一个惠及后学”的卓识,“这种对历史联系的网络式理解,把双边与多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互动的视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0]。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发生的重要地缘空间就是走廊地带,因为它正是各种势力交汇的“过渡地带”。法国学者魏义天敏锐地注意到从中亚的索格狄亚那、吐火罗斯坦到中原北方长城沿线的混合型文化特质,因而在《粟特商人史》一书中使用了“突厥化粟特环境”这一概念予以概括总结。根据他的定义,“突厥化粟特环境”指的是粟特文化与突厥文化相融合的空间。这一空间往往位于农耕势力(包括绿洲势力)与游牧势力相接触的“过渡地带”上。在中亚,这一环境表现为统治阶层的“粟特-突厥”混合文化之生成;在中原北方长城沿线则表现为六胡州的突厥化粟特人聚落以及东北的“粟特-突厥”职业军镇与商业网络。[42]127-140“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在这一环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魏义天的这个判断忽视了唐王朝对外发展的巨大能量。笔者认为,或可将当时过渡地带的相关特质总结为“中原-游牧(各种游牧政权)-绿洲(粟特)”地缘环境。“长安-天山廊道”应是在这种地缘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它的兴衰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在欧亚大陆空间格局上的总体呈现。
索格狄亚那所处的空间位置非常特殊,它处于绿洲世界的边缘并长期与草原游牧部族接触。当时有很多穿过中亚的道路,而索格狄亚那地区则是大部分道路的交汇点,这是粟特商业兴起的地理区位条件。随着萨珊波斯东侵与贵霜王朝的衰落,丝路贸易的主导权出现真空,而嚈哒人的入侵又补充了索格狄亚那的人口,无意间刺激了粟特城市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发展[42]67。作为游牧政权的突厥汗国则为粟特商业网络在欧亚大陆的拓展提供了契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单一性使得游牧政权必须依赖商业与农业补充自身的经济体系,因此,控制绿洲、商道就至关重要[9]17。要想进入中亚的绿洲地带,七河流域就是枢纽。该地区是新北道的枢纽,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可以作为游牧核心区。西突厥正是以此地作为统治的核心地带,以便控制中亚绿洲诸国。粟特人通过充当突厥汗国外交使臣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商业网络[7]167-170。通过这种权力关系,粟特人得以将自己的商业网络延伸至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游牧-绿洲(粟特)”联盟保证了“长安-天山廊道”西段的畅通,但东段依然需要依靠中原地区的唐王朝来开拓。
贞观四年(630年),伊吾的粟特城主石万年率七城来降,唐朝始置伊州[23]65-73。贞观十三年至贞观十四年(639-640年),唐将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置西州[51],这揭开了唐王朝经略西域的序幕。唐朝通过设置羁縻府州的方式,向西域地区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秩序,突厥人与粟特人则作为地方首领加入到这个秩序之中。作为农牧二元结构调和者的绿洲粟特人则承担着连结中原势力与草原势力的功能,发挥着“过渡地带”人群的中介作用。这样一种“中原-游牧-绿洲(粟特)”地缘环境,是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繁荣的前提。而唐王朝对“长安-天山廊道”的控制,也是其经营西域以及统治北方游牧区的战略保障。
游牧(东西突厥、回鹘等)、农耕(唐朝)、绿洲(粟特)三种不同势力的合作,整合了丝路沿线各区域。这是唐代“长安-天山廊道”能够发挥廊道作用的关键。通过这一廊道,唐代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唐朝控制碎叶城,为当地带来了汉地佛教文化,汉地佛教文化的传入深刻改变了七河流域的历史面貌[6]。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则展现了唐朝(西州)与粟特人以及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之间的经济往来[52]。可见,以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为基底,在这一地区构成了事实上的历史命运休戚与共的区域共同体。
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位于不同势力的边界上,是名副其实的“过渡地带”,因而其运转需要仰赖周边诸政权提供的稳定秩序。魏义天认为,粟特人的商业和政治基本上没什么区别[42]145。事实上,这也是“长安-天山廊道”与整个丝绸之路的写照。一旦地缘空间开始重组,“长安-天山廊道”就会受到影响。该走廊的繁荣,本是建立在跨区域的联系之上。阿拉伯征服河中地区以后,西部粟特人融入到穆斯林体系中,粟特人的身份认同遭到破坏并开始重构,跨区域群体的联系中断。中原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出了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中原-游牧-绿洲(粟特)”地缘环境消失,“长安-天山廊道”随之衰落。这一走廊再次发挥廊道作用,则要等到蒙元帝国征服西夏以后。
三、附论: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对于中国与中亚的历史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欧洲在借助制图学、博物学等学科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构建了以欧洲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世界秩序,同时也重构了亚欧大陆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中亚地区都被整合进作为欧洲“镜像”的野蛮、落后的“亚洲”地理概念之中,失去了自身文明的中心性,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自16世纪帖木儿王朝覆灭后,中亚地区诸汗国分裂割据、宗教战争不断,与中国的交往逐渐陷入停滞,“长安-天山廊道”一度阻顿。
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基于“文明-野蛮”二分法的线性史观的摄入,使得“历史中国”话语叙述陷入“农耕-游牧”二元对立的困境之中,游牧被视为农耕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中亚地区也被输入民族主义相关话语。中亚五国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话语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与中国的区隔。“历史中国”的书写被隔断,中国与中亚地区长期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被掩盖,“中亚史”失去了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二重属性,“中国史”也成为孤立于世界的国别史。
为克服这种“舶来”的历史观,笔者以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为例,超越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立足于农牧共生互动的区域视角来理解中国与周边关系,理解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以下对于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研究提出三点认识。
第一,地理环境对于研究唐代“长安-天山廊道”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走廊位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连接处,是大部分商道的交汇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该地区商业的发展。基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区域差异所形成的“关中-七河”沿线跨区域交流,是唐代“长安-天山廊道”兴起的动力机制。当然,新北道的开拓与相关区域的整合也推动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
第二,地缘连环性是理解唐代“长安-天山廊道”贸易兴衰的钥匙。这种地缘环境概括为“中原-游牧(突厥、回鹘)-绿洲(粟特)”模型。事实上,这一模型可以进一步提炼为更具普遍性的模式,即“秩序担纲者-过渡地缘体”环境。只有当“秩序担纲者-过渡地缘体”地缘环境形成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长安-天山廊道”才会贯通并逐渐走向兴盛。所谓的秩序担纲者,必然是兼具农牧特征的复合型政权。否则,它就无法为兼具草原特征与绿洲特征的内陆亚洲地区提供稳定的秩序。这种秩序担纲者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但必定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轴心文明。因为内陆亚洲地理环境的破碎性使得当地不可能产生强大的轴心文明,所以它只能接受周边轴心文明所提供的秩序。轴心文明与内陆亚洲之间的“大陆历史共同体”关系则使得它们必须为内陆亚洲提供秩序,如果轴心文明无法安顿内陆亚洲,它们就无法成就自己。过渡地缘体必须建立起跨区域的文化身份认同,否则就无法发挥其沟通内陆亚洲东部地区与内陆亚洲西部地区的功能。
第三,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发现欧亚大陆各区域之间的共时性关联。影响唐代“长安-天山廊道”有序运行的地缘体,并不局限于唐朝、突厥、粟特,还包括同样作为秩序担纲者的阿拉伯帝国、作为突厥后继者的回鹘以及雪域高原的吐蕃等政权。阿拉伯征服粟特诸城邦、吐蕃与回鹘的西域争霸,也影响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运行。限于篇幅,笔者并未在文中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由此可见,尽管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最远只到达过中亚的呼罗珊等地,但它的“利益边疆”则远至西亚甚至欧洲等地。这启示我们在研究“长安-天山廊道”时,不能“就走廊谈走廊”“就区域谈区域”。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作为历史中国“内、外边疆”(6)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边疆是一种空间,可以被分为“外边疆”与“内边疆”。“内边疆”为已经被帝国治理并控制的地区,“外边疆”则是文化风俗等与“内边疆”相似的区域,帝国的权力无法在这些地区形成直接的统治,因而一般采取外交或者羁縻统治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外边疆”地区的部族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帝国的。参见欧文·拉铁摩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的特质,体现了该区域的“中国性”以及中国的“世界性”的局部重叠。应当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研究视作中国史与世界史重叠的领域,充分发掘其内在多元性与外在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