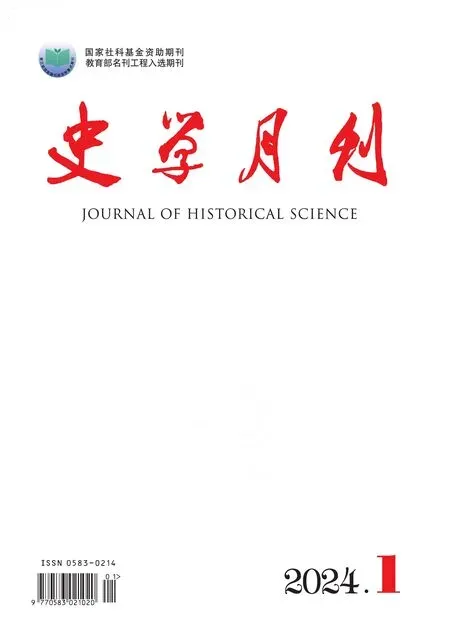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研究*
2024-02-15陈海懿
陈 海 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同意国联组建李顿调查团的阴谋之一,是想通过李顿调查团对包括东北在内的整个中国进行调查,实现日本所扶持的伪满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进而达到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但是,日本的谋划在调查团报告书中遭到否定,即“维持‘满洲国’”不是满意之解决办法。有必要从历史细节处追问,日本在李顿调查团赴东亚调查期间,是如何诱使其接触伪满,是否产生效果,李顿调查团和中国如何应对,伪满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等?
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就九一八事变通过组建李顿调查团的议决案,“决定派遣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中日两国政府各得派参加委员一人襄助该委员会。两国政府对于该委员会应予以一切便利……”(1)张生、陈海懿、杨骏编:《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李顿调查团五大代表和中、日两国任命的参与员顾维钧、吉田伊三郎是法理组成成员,中、日两国有义务为参与员提供便利。1932年3月中旬,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抵达中国,在赶赴东北途中发生的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下文简称“调查团受阻事件”)为探究上述问题提供了案例。该事件指伪满洲国以安全威胁为借口,拒绝顾维钧进入,因顾维钧是调查团的法理成员,导致李顿调查团无法前赴中国东北,遂引发各方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日本满铁附属地展开了多重政治外交博弈。
关于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先行研究,多从属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和顾维钧个人等方面,尚未有专题性的探讨。有学者分析了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的路线问题,指出这是“调查团在日本及其操纵的伪政权的压力下开始妥协的第一步”(2)俞辛焞:《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页。,但没有探究受阻事件的具体解决过程及其多重影响,对该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研究有待扩充。另有学者陈述了顾维钧受阻一事,“几经周折到达东北”(3)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92~295页。,未深究受阻背后外交博弈与政治意涵。顾维钧在个人回忆录中也记载受阻问题,侧重展示其不惧危险的气节,对具体细节回忆不足(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7~429页。。有关李顿调查团的先行研究主要关注国联外交博弈,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因应李顿调查团及各方评价报告书等方面(5)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可参见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22~141页;张生:《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66~83页;樋口真鱼:《国际联盟外交的终结与国联派外交官:对国联关系的摸索与挫折(1933—1937)》(樋口真魚「国際連盟外交の終焉と連盟派外交官:対連盟関係の模索と挫折、1933―1937年」),《国际比较政治研究》2017年第26期,第107~128页;带谷俊辅:《杉村阳太郎和日本的国联外交:国联秘书处内的外交及其归宿》(帶谷俊輔「杉村陽太郎と日本の国際連盟外交:連盟事務局内外交とその帰結」),《涩泽研究》2018年第30期,第25~45页。,对于调查团受阻事件通常以“经过多方交涉”一笔带过(6)高克:《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1页;金光耀:《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民国春秋》2000年第2期,第4~8页。,说明学界对于“多方交涉”的具体过程及其实质存在不明晰之处。本文拟追溯调查团受阻事件之来龙去脉,重点梳理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的具体交涉过程,挖掘交涉背后的冲突、妥协与利益考量,进而分析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和影响,以此呈现日本诱使调查团承认伪满的多重目的,展示由伪满“合法性”引出的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的真实面相。
一 调查团进入东北的路线分歧与多方互动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李顿调查团于3月14日抵达上海。此时中国东北的局势已经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与国联决议成立调查团的1931年12月10日亦大不相同。调查团赶赴东北是迫切的,李顿希望“经由南京、北平,尽快进入中国东北”(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第2卷第1册,东京:日本外务省1979年版,第702~703页。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本文一律称北京。。而吉田伊三郎建议调查团应该先视察广州、武汉等地,再前往中国东北。顾维钧则劝说要尽快前往中国东北,主张“应从山海关开始调查满洲”(8)《驻华公使重光葵致外务大臣芳泽第543号电》(1932年3月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外務省記録『国際連盟支那調査員関係』)第2卷,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本文所引日文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3200。。从调查团计划赶赴东北伊始,各方就出现路线分歧。
与此同时,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外交官们围绕顾维钧出关一事展开行动。4月1日,参赞伊藤述史与伪满外交实际操纵者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进行秘密会谈,伊藤述史建议:“除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以外,‘满洲国’从理论上是可以反对中国参与员进入满洲。”(9)《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499号电》(1932年4月2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3200。大桥忠一表示会在同军方商议的基础上,以伪满政府的名义做出决定。可见,伊藤述史和大桥忠一4月初就决定借伪满的名义,商量阻止顾维钧进入中国东北。4月4日,伪满内阁会议就拒绝顾维钧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等顾维钧抵达北京后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送声明照会(10)《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21号电》(1932年4月6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200。。日本借伪满阻止顾维钧进入中国东北的方案基本成形。
尽管顾维钧及调查团还未抵达北京,但拒绝顾维钧出关的传言已经满天飞,报纸媒体相继报道(11)如《东北叛逆竟欲拒绝顾维钧出关》,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5日,第3版;《东北叛逆电外部,不招待顾维钧》,《申报》,1932年4月6日,第6版。。面对此等传言,顾维钧向记者表示:“余乃系调查团一行所任命,如果叛逆拒绝我,则无异于拒绝调查团前往。”(12)《叛逆竟电外部拒绝顾代表》,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6日,第3版。调查团内部一致认为:“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权质疑他们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可接受性,反对顾维钧将会被视为反对调查团整体,他们将立即报告至日内瓦。”(1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28~729页。4月9日,在调查团抵达北京之际,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发送反对顾维钧进入东北的电报。该电报被罗文干拒收并退回,但仍引起了各方的行动。
顾维钧和南京国民政府坚定前往中国东北,要求日本负全责。顾维钧本人不惧危险,坚决赴“满”,“本团所调查者,乃九一八事变后情形,伪国亦在调查范围内,华代表在任何情形下有偕赴东北责任”(14)屈胜飞、陈志刚、杨骏编:《〈中央日报〉报道与评论(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6页。。罗文干在拒收谢介石电报后,分电驻国联常任代表颜惠庆和驻日公使馆代办江华本。对于颜惠庆,罗文干指示其将信息报告国联,吁请“国联即取有效之方法,使国联决议案得以充分施行”(15)《外交部致日内瓦中国代表团第533号电》(1932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75,第56~57页。。颜惠庆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信息时,李顿也将同样信息送到,颜惠庆就未做过多陈述,向外交部回复:“傀儡提出此事于我方有利,因反对襄助员,即是反对国联也。将来政府讨论关于调查团之东行有最后解决时,国联对一般意见不甚重视之傀儡政府之态度,将见固定。”(16)《照译日内瓦颜代表第310号来电》(1932年4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75,第60~61页。
对于江华本,罗文干要求其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叛逆谢介石竟发出荒谬电文……郑重声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及中国代表赴东行使职务时,遇有障碍或意外之事发生,日本政府应负一切责任”(17)《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致日本外务省的节略》(1932年4月12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外務省記録『満洲国ノ支那側参与顧維均ノ入国拒否問題』),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400。。4月12日,江华本约见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负责人谷正之,谷正之狡辩称伪满拒绝顾维钧一事,属于中国和伪满之间的问题,“日本十分尊重国联决议”(18)《外务省致驻华公使馆第26号电》(1932年4月16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600。,驻日公使馆的交涉无果而终。
李顿视顾维钧为调查团不可分割之一份子,遂求助于国联。4月10日,李顿在记者见面会上表明“顾维钧能否入‘满’等同于调查团能否入‘满’”的强硬态度(19)《顾维钧入满问题,依赖理事会的训令,李顿爵士的意向》(「顧維鈞の入満問題、理事会の訓令を仰ぐ、リットン卿の意向」),《朝日新闻》(「朝日新聞」),1932年4月12日,第2页。。4月11日,调查团内部开会提出三种办法:第一,调查团及中日代表同赴东北;第二,全体不赴东北;第三,中日代表一律退出(20)《招待国联调查团报告》(1932年3月至9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76,第22页。。顾维钧表示对于后二种办法不能承认,如果依据第三种办法,调查团无法获知东北受日军压迫实情,在法理上不符合调查团的构成标准;如果依据第二种办法,调查团则无法完成任务(21)《北平辅佐官致参谋次长第614号电》(1932年4月15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600。。李顿随后发出致国联两电,一电呼吁国联理事会成员国“在必要时向其驻北平的公使馆和驻东北的领事馆发出协助调查团完成任务的指示”(22)《1932年4月9日调查团委员长关于有代表在场的各国政府向调查团提供便利的来函》(Communication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regarding the facilities to be granted to the Commission by the Governments having Representatives on the spot,April 9,1932),《国联公报(特刊)》(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Special Supplement)第101期(1932年),第209页。,另一电叙述调查团受阻一事(23)《1932年4月11日调查团关于中国参与员进入中国东北的函电》(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with regard to the Admission of the Chinese Assessor to Manchuria,April 11,1932),《国联公报(特刊)》第101期(1932年),第209页。。
国联理事会于4月12日举行临时会议,要求各理事国对驻北京及中国东北的本国官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协助调查团(24)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37~738页。。国联秘书长将调查团的要求通报给美国政府,美国驻日内瓦领事吉尔伯特(Prentiss B.Gilbert)表示“美国驻中国和日本的官员已接到国务卿的指示,向调查团提供一切适当的协助”;理事会主席、法国总理塔尔迪厄(Andre Tardieu)则当场表示法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采取必要步骤”(25)《1932年4月12日调查团来电》(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April 12,1932),《国联公报》(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第13卷第5期(1932年),第1020~1021页。,即“愿对于该团工作之完成,予以相同之便利”(26)《调查团定十六日离平》,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14日,第3版。。德国驻国联代表团中有人针对调查团受阻一事质问日本代表泽田节藏,泽田一面答以“日本对李顿调查团提供诚意是不会改变的”,一面通报外务省,希望指示“如何应对该问题”(27)《驻日内瓦事务局局长泽田致外务大臣芳泽第348号电》(1932年4月12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400。。
日本内部进行“协商”,引向海路进入东北方案。针对伪满拒绝顾维钧事件,日本内部各方存在调和过程。以外相芳泽谦吉为代表的外务省主张,在允许顾维钧进入中国东北的前提下予以监视即可,“‘新国家’当局在顾维钧进入满洲后对其行动进行监视,静观其入满后的行动,以便让调查团一行在事实上不存在进入满洲的障碍”(28)《外务大臣芳泽致驻长春领事田代第285号电》(1932年4月9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500。。不过,日本关东军与外务省并不一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伪满“将本事件作为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第一步,颇为重视”,因此应该“控制对他们行动的指摘”(29)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30、741、742~743页。。芳泽谦吉随即同陆军省进行协商,并以陆军省和外务省的名义向关东军指示:“在‘满洲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斡旋,使中国参与员可以进入满洲。”(30)《外务大臣芳泽致驻长春领事田代第36号电》(1932年4月12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700。但是,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亲自向陆军次官小矶国昭发电,指出“关于拒绝顾维钧入‘国’问题,军方大体持旁观主义”,强调国联应该避免对伪满进行施压,“希望国联能够持公正的立场对满洲进行视察”(3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30、741、742~743页。。关东军表面上奉行的“旁观主义”,实际上就是支持伪满。
鉴于关东军的固执立场,日本驻外领事试图劝说调查团和日本外务省。4月13日,伊藤述史会见李顿,指出调查团“全然否认‘满洲国’存在的事实”是“绝非高明之策”(32)《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72号电》(1932年4月1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700。。翌日,吉田伊三郎向李顿表示日本中央和驻地机构之间存在隔阂,劝说“包括顾维钧在内的调查团经由海路,从大连入满,绝对不能经由山海关”(3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30、741、742~743页。。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则致电芳泽谦吉,认为拒绝顾维钧虽然是“满洲国外交部”的提议,但日本驻当地官员对此至今都采取默认态度,即日本间接认可此事,“事到如今……若强迫‘满洲国’变更方针,会极大地丧失日本对‘新国家’的威信”(34)《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583号电》(1932年4月14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800。。于是,外务省和芳泽谦吉改变立场,建议“调查团一行经由大连”,并指示吉田伊三郎以时间紧迫为由迫使调查团接受,“希望不过于延误入满日期的话,倒不如经由大连先进入满铁附属地”(35)《外务大臣芳泽致驻北平参事官矢野第69号电》(1932年4月14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800。。
中国反对经由海路进入东北的路线,原因在于从陆路经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入东北,可以沿路调查日本撤兵情况,“盖此次调查团之主要工作,在视察日本是否依照国联议决案履行撤兵,现山海关以外及锦州等处日本均驻重兵,若取道大连,则适与此主要性违反,故我方无论如何须坚持经山海关入东北之主张”(36)《调查团确定星期四离平》,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18日,第3版。。顾维钧极力主张“调查团乘火车取道山海关至打虎山,继北进通辽,然后由南满路线赴哈尔滨,卒乃南下至沈阳”(37)《顾维钧坚决反对分组出关》,《申报》,1932年4月18日,第6版。,点明“由大连入沈,无异参观日本”,但也意识到“调查团以日本态度坚决,似有软化之意”(38)《北平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2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103-00012-005,第35~37页。。
调查团倾向于妥协,主要是时间紧迫。原定5月1日国联理事会重新开会前需要提交《初步报告》,就必须尽快进入东北,“期限日迫,焦灼异常”(39)《招待国联调查团报告》(1932年3月至9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76,第23页。。在综合考虑中日立场之下,调查团于4月16日向日本提出“希望调查团的一部分代表与中日两国的参与员及随员,通过海路经由大连,调查团其他部分代表及秘书处通过列车经由山海关”(40)《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89号电》(1932年4月16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800。,如此可以“两方兼顾,是亦情理上之可能”(41)《调查团略定星期二出发》,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17日,第3版。。
这样,李顿调查团最终采取分道进入中国东北方案,在秦皇岛分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顾维钧陪同李顿等人在4月21日登陆大连,前往沈阳(42)《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2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57,第11页;《调查团昨晚抵沈》,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22日,第3版。,进入东北。不过,在李顿等人进入东北之际,顾维钧能否走出满铁附属地又成了问题。满铁附属地的主权属于中国,由日本享有行政权,在1935年“撤废”附属地治外法权和归并伪满之前,满铁附属地尚不能等同于伪满(43)参见周颂伦:《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的“撤废”与行政权的归并》,《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第133~142页。,故伪满威胁称,若顾维钧走出满铁附属地,则予以逮捕。调查团受阻事件并未终结。
二 调查团走出满铁附属地与妥协性交涉
顾维钧走出满铁附属地就是进入伪满,若伪满果真逮捕顾维钧,日本就会因需要保护包括顾维钧在内的调查团安全,而面临日“满”对立之困境。因此,推动调查团与伪满直接联系,由双方协商解决受阻事件成为日本的努力方向。
伪满强硬阻止顾维钧走出满铁附属地,以各种方式逼迫调查团正视伪满。4月17日,谢介石致电芳泽谦吉,告知若顾维钧“擅自踏出附属地外一步”,伪满“将采取断然处置,以实力阻止顾维钧”(44)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58~759、776~777页。。次日,驻长春总领事田代重德向吉田伊三郎指出,调查团“无视作为‘新国家’的‘满洲国’拥有事实上的权利”,日本对此表示不满,并威胁称:“如果调查团不向‘新国家’提出任何形式的入‘满’照会,‘新国家’也绝不会考虑同意调查团入‘满’。”(45)《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61号电》(1932年4月1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100。当天下午,吉田伊三郎将田代重德的信息传达给李顿:“调查团如果采取无视的态度,将会产生许多麻烦。”(46)《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204号电》(1932年4月19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100。待到调查团进入沈阳后,田代重德再向调查团表示,由于调查团始终没有联系伪满,伪满“不再履行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警戒职责,‘新政府’要人也不会以官方身份进行任何会面”(47)《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69号电》(1932年4月2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600。。
日本驻外领事以中日参与员都不陪伴调查团出附属地的建议相胁迫。吉田伊三郎于4月16日提出:“关于铁道附属地外的视察,日中双方参与员都不与国际联盟调查团同行也是一个方案。”(48)《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92号电》(1932年4月16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800。森岛守人支持该建议,认为调查团前往附属地外视察时,“中止日中双方参与员及随员同行的方法是高明的”(49)《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579号电》(1932年4月17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000。。操控伪满外交的大桥忠一欣然同意,“如今只能允许排除日中参与员之外的调查团前往附属地以外地区”。针对上述建议,南京国民政府和顾维钧无法接受,顾维钧认为:“北满现状纷乱,华军抗日形势日甚,深盼全体前往调查以明真相。”(50)《北平张学良致罗部长电》(1932年4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103-00012-005,第46~47页。调查由日本控制的东北地区,中国参与员对调查团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日本参与员,罗文干亦电告顾维钧要北上,“近日哈尔滨一带情形正可作为我方对日军及其傀儡组织之明证,调查团自应前往,既往自应由中国代表协助”(51)《南京罗部长俭外九十九号电》(1932年4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57,第27页。。
关东军逼迫调查团接触伪满,并支持驻外领事的建议。4月23日,桥本虎之助会见吉田伊三郎、森岛守人、大桥忠一、田中都吉等人,询问如何解决受阻问题,田中都吉告知可以“让调查团对‘新国家’进行问候,在此基础上由‘满洲国’和调查团协商”,桥本虎之助表示赞同,“希望能够进行内部折冲”,由伪满与调查团进行协商,“在严格限制顾维钧一行人数的基础上,允许顾维钧前往附属地外”,大桥忠一亦同意如此处理(52)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83、773~774、777~778页。。与此同时,抵达沈阳后的李顿专门与本庄繁谈及受阻问题,并提出一种方案,即李顿本人与顾维钧同行,可以“保证顾维钧不发表顾问业务以外之言行,希望‘新政权’惠予理解”(53)《关东军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第836号电》(1932年4月2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外務省記録『国際連盟支那調査員関係』)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600。。李顿此种个人担保提议其实也是由日本提出来的。早在4月12日,日本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长冈春一向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提出,伪满拒绝顾维钧是担心“顾维钧进入东北后,除参与员的任务外,还会从事政治运动”,因此“调查团保证顾维钧不会从事在参与员任务以外的一切行动,或许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54)《驻日内瓦事务局局长泽田致外务大臣芳泽第351号电》(1932年4月13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500。。李顿向本庄繁提出的妥协方案表明,调查团已经准备通过日本建议的担保方式来避免受阻。
英法介入与日本外务省指示都不能改变日本驻地军政人员的行动。李顿之所以会向本庄繁和关东军寻求帮助,跟英法介入和日本内阁指示都不能改变局势有关。4月13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F.Lindley)向日本外务副大臣进行质询,得到的回复是“即使在铁路区外,日本军队也以保护生命和财产为目标,并将被期望执行该任务”(55)W.N.梅德利科特、道格拉斯·戴金、M.E.兰伯特编:《英国外交政策文献(1919—1939)》(W.N.Medlicott,Douglas Dakin,M.E.Lambert,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系列第10卷,伦敦:皇家出版局1969年版,第289、310、339~340页。,4月15日,芳泽谦吉向林德利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说服‘满洲国政府’撤回对顾维钧入境的反对。”(56)W.N.梅德利科特、道格拉斯·戴金、M.E.兰伯特编:《英国外交政策文献(1919—1939)》(W.N.Medlicott,Douglas Dakin,M.E.Lambert,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系列第10卷,伦敦:皇家出版局1969年版,第289、310、339~340页。4月21日,林德利再次拜访芳泽谦吉外相,传达西蒙(John Simon)外相的意见,希望日本给调查团提供充分便利(57)《外务大臣芳泽致驻英代理大使泽田第49号电》(1932年4月21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700。,但是被告知日本政府无法劝说,准备由关东军“为使团提供一切便利和充分保护”(58)W.N.梅德利科特、道格拉斯·戴金、M.E.兰伯特编:《英国外交政策文献(1919—1939)》(W.N.Medlicott,Douglas Dakin,M.E.Lambert,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系列第10卷,伦敦:皇家出版局1969年版,第289、310、339~340页。。林德利当晚会见法国驻日大使,商量共同行动。翌日,法国驻日大使拜访芳泽谦吉,同样要求日本为调查团提供便利,并告知这是史汀生(Henry Stimson)、西蒙、塔尔迪厄的共同建议(59)《外务大臣芳泽致驻日内瓦事务局局长泽田第176号电》(1932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500。。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日本内阁在4月20日经过协议,发出由总理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及陆军次官署名的电报,要求日本关东军、驻外使领馆和伪满解决问题,“关于调查团视察,帝国政府应该提供便利与保护。这样的便利与保护同样要提供给与调查团有不可分的中国参与员”(6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83、773~774、777~778页。。但是,日本关东军和驻外领事依旧没有改变立场。4月22日,关东军答复日本内阁,“鉴于现在中东铁路沿线的状况,执行确保绝对安全的责任是不可能。暂不论附属地外的商埠地带,就是长春以北一带,也无法绝对排除‘满洲国’行使武力”(61)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83、773~774、777~778页。,也就是说日本关东军不会阻止伪满逮捕顾维钧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田中都吉回复外务省,称调查团拘泥于“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无视“满洲国”存在的态度,不会见伪满高层官员,“所带来的感情伤害毫无疑问将会波及日本”,指出“对‘满洲国’表示适当的礼让,对调查团和日本都是很有必要”(62)《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619号电》(1932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500。。
因此,调查团是否同伪满进行接触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德拉蒙德在4月11日就曾建议“与傀儡政府接洽”是解决受阻问题的办法之一,被颜惠庆视为“不甚妥善”(63)《照译颜代表日内瓦来电》(1932年4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010112-0030,第219~220页。。在出关前,顾维钧亦询问李顿“将来抵沈后,日方或托词‘满洲国’反对,拟阻往他处,则调查团将如何”,李顿的答复是“只能离满”(64)《北平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2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80103-00012-005,第35~37页。。但是,肩负重任的李顿调查团不可能就此离开,而身处日本绝对控制之地的调查团和顾维钧亦没有太多选择余地,联系伪满以完成调查任务成为不得已之选择。
4月23日,李顿向吉田伊三郎透露其欲求助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来联系伪满,吉田伊三郎等人一致认为,李顿“给‘新国家’发电是非常紧要的事情”。调查团翌日召开内部会议,草拟以李顿个人身份致谢介石的电报草案(6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4月25日上午,李顿向谢介石发送个人问候电报,内容就是要其为调查团提供便利。这份电报使伪满态度“缓和”,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决定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允许顾维钧进入中国东北(66)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
为了达成所谓的附加条件,伪满不满足于电报联系,进一步提出需要调查团派员前往长春进行直接协商,目的是利用调查团来增加伪满的“合法性”和认可度。4月27日,大桥忠一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达成协议,为解决顾维钧进入中国东北问题,“拟由调查团向长春派遣代表与‘满洲国’进行协商”(67)《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666号电》(1932年4月2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600。。28日,当李顿会见桥本虎之助参谋长时,桥本虎之助透露附加条件主要包括随员人数限制、通过书面形式保证顾维钧及随员不会有调查任务之外的言行等,并提出由调查团“派遣代表前往长春进行交涉”(68)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李顿同意了这些附加条件,但拒绝派遣代表,并于5月1日以电报形式将中国随员名单和书面保证发给了谢介石(69)《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91号电》(1932年5月2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800。。
5月2日,大桥忠一向桥本虎之助指出李顿仅发送5月1日的电报“还不够充分”,必须“由‘满洲国’和调查团之间进行具体的直接交涉”,希望桥本虎之助能够劝说李顿(7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在桥本虎之助的力劝之下,李顿被迫妥协,同意在5月3日前往长春访问谢介石。关于顾维钧问题,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大桥忠一与调查团秘书长哈斯(Robert Haas)进行交涉(71)《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99号电》(1932年5月4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800。。至此,调查团还是不得不直接与伪满打交道,受迫于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双簧戏与得寸进尺,李顿不得不无奈地改变既定方针,这也让伪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被“认可”的目的。
从5月3日至6日,大桥忠一与哈斯进行三轮会谈,各有妥协。调查团同意谢介石派遣私人代表,名义上陪同调查团,实际上“监视”顾维钧,大桥忠一则同意不将“顾维钧取消之前言论的要求”作为必要条件(72)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5月6日,李顿与谢介石之间传递了三封仅具形式意义的往复书信(73)关于这三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832~835页。。调查团受阻事件终于得到解决,5月7日早上,调查团全体出发前往吉林,实施调查工作。
三 受阻事件的多重博弈实质及其影响
1932年4月9日,谢介石致罗文干电文中关于拒绝顾维钧的核心内容是:“……倘顾氏一行入境,难保毋与不逞之徒种种机会,为将来双方亲善之阻碍。应请贵部长妥为设法,勿使顾氏一行东来,免滋意外。”(74)关于1932年4月9日谢介石所发《致中华民国外交部电》中文全文,可参见《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79号电》(1932年4月11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300。伪满表面上是以避免给“不逞之徒”有机可乘为由拒绝顾维钧,而通过梳理因“拒顾”引发的调查团受阻事件全过程,可以发现其中的多重博弈。
第一,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关系伪满对内“合法性”问题。这种“合法性”最具现实性,包含顾维钧在内的李顿调查团赶赴东北,引起伪满的统治危机,并激起东北民众的反抗意志。顾维钧的个人特殊身份引起伪满担忧,他在九一八事变前担任张学良的顾问,二人关系不一般。张学良被伪满和日本视为旧东北政权的象征,而且谢介石认为“张学良心怀叵测……已经派遣了很多便衣队潜入东北”(7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94~795、793、801~802、812、824、758~759页。,对伪满治安造成紊乱,故而竭力阻止顾维钧。同时,马占山“叛逃”进一步加剧了伪满的危机。1932年3月末,鉴于调查团即将前往东北,马占山一面调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准备向调查团举证,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并于4月1日离开日军控制的齐齐哈尔,抵达黑河后通电反正,再举抗日旗帜。伪满担忧存在“其他想借此机会起义的义勇军”,故强力阻止顾维钧进入,断绝东北民众试图反抗的思想,借机向国联和各个国家“展示‘满洲国’的威严,确立在东北的统治权”(76)《拒绝顾维钧进入“满洲国”问题的经过》(1932年5月18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800。。
第二,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关系伪满对外“合法性”问题。伪满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破坏自然不会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轻易得到认可,而李顿调查团主动来到东北,恰好给伪满突破对外“合法性”束缚提供了契机,正如大桥忠一所言:“‘满洲国’利用此次机会,强调独立性,使全世界对此予以认识。”(7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71~773、730~731、766~767页。
从产生伪满拒绝顾维钧传言开始,各方就注意到了这层意义,随着调查团与伪满的接触增多,对外“合法性”问题愈加引人关注。中国媒体认为“拒顾”与“合法性”之间如此明显的联系肯定能为调查团所识破,“调查团诸氏,皆为久经世变、周知情伪之人物,此种鬼蜮之技,适以见其作伪心劳日拙而已”(78)《社评:异哉拒绝顾维钧到东北?》,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6日,第2版。。确实,李顿在4月7日面对记者问询时特意强调“目前调查团只承认日中两国政府”(79)《驻南京代理总领事上村致外务大臣芳泽第316号电》(1932年4月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500。,杜绝伪满试图利用调查团谋求“合法性”认可。日本驻北京参事官矢野真也询问外务省该如何向媒体解释质疑,即拒顾问题“是否跟‘满洲国’的承认问题联结在一起?”(8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71~773、730~731、766~767页。抵达北京后的李顿向日本驻外领事们重申:“至于理事会决议,调查团不与中日以外的政府进行交涉,在东北的安全保障应由日本政府负责。”(81)《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72号电》(1932年4月1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700。
随着关东军与伪满的步步逼迫,李顿向桥本虎之助明确表示调查团无权认可伪满,“调查团在法理上显然没有承认新政权之权能,或者仅承认其一部分为新政权,从而在承认问题上造成误解”(82)《关东军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第836号电》(1932年4月23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600。,在此前提下,李顿才同意联系伪满。对于李顿举措,罗文干认为“如彼以个人名义发电,吾方固不能阻止”,若是“迹近承认伪国,吾方当向国联抗议”,至于李顿以个人名义发送,属于“私电”,因此“询问溥、谢一节,我方固不反对”(83)《南京罗部长感外九十八电》(1932年4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990600-2057,第21页。。
第三,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涉及调查团及国联的能力问题。李顿调查团来到东亚,给中日以及伪满都带来一定的期待,尽管期待的内容和目的迥然不同。调查团受阻事件发生后,日本外务省的最初立场是根据国联理事会的议决案,要求驻外领事和伪满交涉妥善解决,但是关东军的态度截然不同。外务省曾联合陆军省发出指示,也无法改变关东军的立场,有恃无恐的伪满自然坚持强硬立场。日本驻外领事人员也表示:“如果我方强硬要求‘满洲国’同意此事,会使推动‘新国家’成立的要人们产生日本屈服于国联的印象,这对今后‘满洲国’与日本关系的大局会产生不利影响。”(84)《驻沈阳代理总领事森岛致外务大臣芳泽第565号电》(1932年4月12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400。日本中央与驻地机构的对抗态势使调查团受阻事件性质发生了变化,即日本是否需要遵从国联议决案,调查团及国联机制在东亚是否适用。
按照日本外务省的策略,因顾维钧个人导致调查团受阻,造成国联理事会全盘议论伪满问题“不是上策”(85)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71~773、730~731、766~767页。,芳泽谦吉认为此时的伪满未成气候,必须转移国际注意力,因此希望尽快解决调查团受阻问题,以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此,芳泽谦吉向大桥忠一重申日“满”真实关系:“作为日本,表面上需要尊重‘新国家’为独立国家,然而实际情况是,倘若‘新国家’无视我方的利益,且与我方立场冲突时,需要对其进行指导”(86)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67~769、771~773页。。
为回应芳泽谦吉的指示,大桥忠一道出了拒绝顾维钧可以实现的第三层目的。大桥忠一表示“关于早晚都会到来的关于满洲问题的国际性讨论,如果现在强调‘满洲国’的独立性,可以使日本采取立场变得更加容易”,因此这个时候强调独立性,让东北地区民众“认识到自己的愚昧,认识到国联是不可靠的”,打破寄希望于依托国联来恢复原状的想法。大桥忠一认为调查团的各国代表“对撰写报告书的态度,与其说反映中国东北的事实,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代表背后国家的国际政策”,因此“即使同帝国政府的立场相反”,伪满也要坚持,目的是“为了调查团在制作报告书时可以参考”。大桥忠一还指出,日本“不能寄期望于调查团代表的态度和调查报告书”,因为“国联背后的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基调时,都是出于冷静的利害关系,而不是报告书”(8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1册,第767~769、771~773页。。质言之,大桥忠一阐明调查团虽然是由国联派遣的,但其实真正影响调查团和决定九一八事变如何解决的是调查团各个代表背后的国家。
其实,此种观点并非大桥忠一独有。中国媒体在议论调查团受阻事件时,也质疑调查团及国联的能力,认为国际大势更为重要。4月14日,有读者表示对于调查团应该有两个疑问,即“一、国联调查团能不能忠实调查报告?二、假使报告很忠实,但国联能不能以公理裁判?”指出国联理事会处置纷争的弱点在于“理事会是政治的团体,不能用法律方面使永久和平,不过用政治手腕调处而已”(88)张贺君:《对调查团的感想》,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14日,第8版。。鉴于调查团受阻,《大公报》认为:“纵令调查团出关,终不易有所获,势则然也”,所谓的“势”指的是“此次调查团五委员,虽同受国联之委托,而各有本身之背景,具有天然之限制”,调查团报告书“一方须重视日本政府之意旨……一方更须受本国政府之指示”,断言调查结果“与其谓操之日本,又毋宁谓操之日本以外之国际大势也”(89)《社评:国联调查团出关愆期》,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16日,第2版。。如此,调查团受阻和伪满“合法性”的幕后蕴藏着李顿调查团调停结果的因子。
第四,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折射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问题。不论是李顿调查团来到东亚,还是伪满拒绝顾维钧进入东北,这一连串事件都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调查团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事变进行定性。质言之,调查团与其说是调查事变,倒不如说是寻求事变的解决方案,而伪满及其制造的拒绝顾维钧进入东北事件,就变成了九一八事变能否解决的一次试验。于日本而言,伪满的对外“合法性”得到认可,九一八事变就是一场性质合法的行动,故其积极利用“拒顾”以实现侵略行动“正当化”。其实,在调查团受阻过程中,日本就反复强调伪满是在调查团成立后所发生的,是东北民众“自治”的结果,试图以此为借口说服调查团承认伪满的存在。因此,日本外务省在《拒绝顾维钧进入“满洲国”问题的经过》中指出,拒绝顾维钧的另一层意义就是通过拒绝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实现“‘满洲国’完全解除和国民政府的联系,向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表达‘满洲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90)《拒绝顾维钧进入“满洲国”问题的经过》(1932年5月18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800。。总之,因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牵扯出的多方交涉,使得伪满政权的“国家”身份定位关系到九一八事变的定性。
尽管中国与调查团出于完成任务考虑而存在妥协之处,但日本的“拒顾”阴谋以拒绝顾维钧进入伪满而告终,此次受阻事件对中、日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结果是一场没有绝对胜者的零和博弈。就中国而言,最终实现顾维钧陪同调查团一起前往中国东北各地调查,但在受阻事件过程中顾维钧等人受到严密的监视(9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30页;《顾执中谈赴沈经过》,天津《大公报》,1932年5月3日,第3版。、中国报社记者不准随行(92)《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89号电》(1932年4月30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700。,调查团的中国陪同人员数量受到最大程度压缩,直接导致在调查团调查东北期间中国话语权的严重不足。南京国民政府本来计划派遣四十余人陪同顾维钧出关,“在东北的日本人,除参与员、随员外,还有各种机关,必会有很多专家,但中国并没有此等有利条件,因此有必要让相当数量的随员同行”(93)《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201号电》(1932年4月19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5000。。在实际操作中,因分道出关,中国陪同人员被压缩至20余人(94)屈胜飞、陈志刚、杨骏编:《〈中央日报〉报道与评论(上)》,第504~505页。。为走出满铁附属地,调查团答应伪满的要求,再次缩减中国的陪同人员,包括顾维钧在内仅允许6人,而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陪同人员则多达20人(95)《关东军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第970号电》(1932年5月2日),外务省记录:《“满洲国”拒绝中国参与员顾维钧入“国”问题》,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51700。,且该数字不包括关东军与伪满派遣的陪同人员。经过调查团受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对调查团于东北期间的协助作用遭到严重削弱。
调查团进一步认识真实的日“满”关系,亦意识到日本关东军扶持的“满洲国”改变了中国东北状况。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可以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后的实况,“今得欧美五国代表的人物,躬临其地,与日本军阀浪人亲相接触,不特于将来解决东北问题,可有裨益,即于各国人之日本认识,亦可获得实际的参考材料”(96)《社评:国联从此将充分认识日本》,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25日,第2版。。通过实地考察与交涉,伪满作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的本质在调查团受阻事件过程中得到印证,调查团没有为伪满“合法性”进行政治背书。不过,伪满和日本关东军的举措确实影响了调查团的叙述与判断。4月30日,调查团完成《初步报告》,指出中国东北地区产生一种新局势,该局势“为去年九月本案进展中,理事会所未经计及,而为本次调查之目标者,即当地之行政组织业经变更治安维护委员会,由日方协助之,成立于公历一九三一年末数月中。该委员会嗣由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所成立之政权,号称‘满洲国政府’者,替代之”(97)参见《国联调查委员会初步报告》(1932年5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20-010102-0243,第25~33页。,日本所扶植的伪满成为调查团分析中国东北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伪满达到了调查团同其联系之目的,但“国家”认可没有实现,日本扶持的“傀儡”本质没有改变。日本《朝日新闻》指出,伪满拒绝顾维钧可以打破中国基于“领土保全”宣称东北是中国领土(98)《中国的领土?“满洲国”独自的强硬态度,调查团苦恼的问题》(『支那の領土とは?満州国側独自の強硬態度に、調査団悩みの難問題』),《朝日新闻》,1932年4月22日,第2页。,《读卖新闻》则宣传调查团与伪满的直接交涉等同于确认伪满的“国家”身份(99)《确认“满洲国”主权,解决顾维钧同行问题,今天共同前往吉林》(『満州国の主権を確認、顧維鈞同行問題解決、きょう相携えて吉林へ』),《读卖新闻》(『読売新聞』),1932年5月7日,第2页。。但是,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Johnson)于4月21日就向国务院通报,伪满拒绝顾维钧“想必是日本人唆使的”(100)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32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2)第3卷“远东”,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710~711页。。在实际交涉过程中,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指出,调查团代表一致认为:“‘满洲国’乃日本军一手炮制,日本军从满洲撤退的话,‘满洲国’也会被消灭。”(101)《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95号电》(1932年4月1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500。在调查团受阻事件解决后,调查团专家开脱盎葛林诺(Kat Angelino)指出:“从顾维钧入‘满’问题可以看出,长春政权和日本政府及军部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调查团提交报告,指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肯定会被人视为是疯狂的举动。”(102)《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芳泽第226号电》(1932年5月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3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600。调查团专家勃来克斯雷(G.H.Blakeslee)将本庄繁同意顾维钧入“国”、大桥忠一反对顾维钧入“国”、哈斯被迫与大桥忠一进行“为时甚久”的谈判等系列过程,戏谑为“一场技艺精湛的演出”(103)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32年)》(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2)第4卷“远东”,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8年版,第149~165页。。
调查团受阻事件使得调查团、国联对日本的观感下降,且暴露出日本中央与驻地机构之间的矛盾明显,驻地军政人员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1932年3月,关于调查团对日友好程度的评估是“调查团中法国代表持有的态度常常对我方有利,意大利代表不时亦表示出亲日态度……英国代表则努力采取公平的态度”,仅“美国代表在多数场合下批评我方的政策”,但自从调查团受阻事件发生以来,“各位代表对我方甚感不满”(104)《驻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外务大臣芳泽第195号电》(1932年4月18日),外务省记录:《国际联盟中国调查团关系文件》第2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Ref.B02030444500。。在日内瓦,拒绝顾维钧一事引起国联反感,国联对日氛围恶化(105)《日内瓦反感,拒绝入“国”问题》(『寿府では反感、入国拒否問題』),《朝日新闻》,1932年4月13日,第2页。,日媒担忧,如果伪满“坚决拒绝顾维钧入‘国’,满洲问题将再度成为国联的当务之急,引起重大事态”(106)《国联气氛恶化》(『連盟の空気悪化』),《朝日新闻》,1932年4月12日,第2页。。
在调查团受阻事件中,日本内部协调过程也暴露出日本中央与驻地机构的矛盾,日本中央无法对关东军、驻外领事等驻地军政人员形成强制约束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下克上”传统被带到了中国东北地区,驻地军政人员自主性进一步加强。这种自主性的发展趋势非但不是日本中央扭转对驻地人员的控制,反而是日本中央支持驻地人员行动,关东军的对华侵略行径不会因调查团而停歇。在调查团受阻过程中,日本中央包括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驻地军政人员包括外务省驻北京和东北各地的领事、以本庄繁和桥本虎之助为首的关东军、陪同调查团的吉田伊三郎以及实际操控伪满的大桥忠一等人。概观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侵华进程,不断扩大侵略行动和日本中央的故意放纵,推动了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的历史演变,中日危局持续恶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0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在调查团受阻事件中,包括日本驻地各类型军政人员的性格、立场、利益等在内的“偶然性”,在特定历史时期充当了解释历史发展的特定因素。
四 结 语
围绕调查团受阻事件的交涉,可以明显发现日本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和李顿调查团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原因在于中国东北被侵占后的实际管控权变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扶植成立伪满,而南京国民政府与李顿调查团则迫切希望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李顿调查团在受阻事件上的应对空间。回溯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的过程,分析该事件的实质与影响,有三点值得深入阐释。
其一,李顿调查团受阻事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的国际解决策略无法恢复东北原状。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以《国联盟约》为代表的国际条约体系,兼及《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等,试图利用国际解决策略,背靠大国集团和拉拢第三方的形式制衡日本。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积极推进伪满政权的扶植工作,“拒顾”与调查团受阻事件是日本谋求伪满“国家”身份的国际认可,进而实现控制中国东北的策略性手段。在9月底完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李顿调查团认为“恢复原状,并非解决办法”,“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时组织,亦属同样不适当”,故而将两者并列为“不能认为满意之解决办法”(108)张生、陈海懿、杨骏编:《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第421页。,明显是受到日本与伪满的运作影响。
其二,调查团受阻事件反映出国联调停机制难以维系东亚和平秩序。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表面上维系着欧洲及东亚地区的秩序,但秩序之下潜伏着系列危机。由于顾维钧兼具中国官员和国联调查团参与员的双重身份,日本透过伪满实施“拒顾”行动,不仅希望实现伪满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试图诱导李顿调查团对伪满的认可。不过,调查团实际上不仅未认可伪满,反而进一步认清了日本与伪满的真实关系,日本的动机与效果发生异化,其侵略行径没有实现“合法化”。李顿调查团、国联和伪满、日本之间存在的认知与利益沟壑,注定了国联调处方案不会得到日本认可,日本抗拒调处和退出国联的结果隐然可见,深刻反映出国联机制在东亚的尴尬性。
其三,由“拒顾”所引发的调查团受阻事件实际上是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的一个缩影。李顿调查团的背后除了国联外,更重要的是五大代表所属的英、法、美、德、意等国家,这些大国是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制定者与参与者。中、日两国都视调查团是应自己倡议而组建,试图通过调查团向国联与五大国发声,形成有益于己方的情势。身处弱势的中国将九一八事变诉诸国际社会,寄希望于通过调查团实现大国介入,促成“国际解决”东北问题;日本则预谋通过调查团、国联与五大国实现九一八事变后的现状认可,即达到伪满的“国家”认可。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东北,不仅代表国联调查九一八事变与调停中日争端,而且象征五大国对东亚秩序变动的现地视察。中日两国的诉求、内容与目的截然相反,恰好反映九一八事变的复杂性与李顿调查团之行的艰难性,围绕李顿调查团而产生的大国博弈情形在此期间反复出现,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