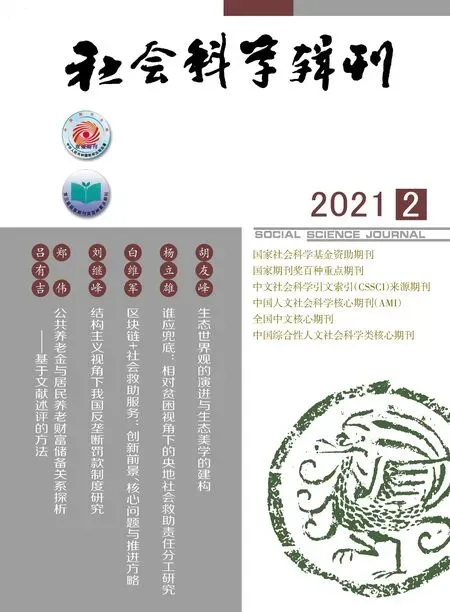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代表选定研究
2021-01-29陈海懿
陈海懿
引言
九一八事变后为人所熟知的国联调查团五位代表分别是:意大利代表马柯迪(Luigi A.Marescotti)、法国代表克劳德(Henri Claudel)、英国代表李顿(Lytton)、美国代表麦考益(Frank McCoy)、德国代表希尼(Heinrich Schnee)。但是,1931年12月14日,国联理事会起草委员会向日本驻日内瓦代表团提出来的代表名单是:意大利代表施恩泽(Carlos Schanzer)、法国代表吉拉马特(Adolphe Guillaumat)、英国代表麦克米伦(Macmillan)、美国代表海因斯(Walker D.Hines)、德国代表希尼。〔1〕对比这两份名单,可以发现只有德国代表是一致的,但日本仅对希尼出任德国代表提出异议,要求换成佐尔夫(Wilhelm Solf),内中缘由饶有趣味。
实际上,尽管国联调查团的五大代表是为人所熟知的史实,却鲜有人发问为何调查团的代表人数是五人,也少有人探究为何是上述五国代表构成调查团,更遑论作为当事国的中日两国如何因应调查团代表选定。目之所及,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没有分析调查团的人数与来源国设定、成员遴选与确定等问题。①既有研究关注国联调查团的调查过程和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关于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调查过程和调查团报告书是构成国联调查团这一历史主体的三个阶段,都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学术界近年的重要研究可参见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崔海波:《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日〕樋口正士:《ARA密約:リットン調査団の陰謀》,東京:カクワークス社,2015年;〔日〕後藤春美:《国際主義との格闘:日本、国際連盟、イギリス帝国》,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6年;〔日〕帶谷俊輔:《杉村陽太郎と日本の国際連盟外交:連盟事務局内外交とその帰結》,《渋沢研究》2018年第30巻;〔日〕石原豪:《国際連盟脱退と日本陸軍の世論対策》,《文学研究論集》2019年第50巻;等等。本文拟利用多元资料,一方面扩充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的史实,具体呈现调查团的人数与来源国设定、具体成员遴选过程,窥探国联调查团蕴含的大国意志;另一方面探析在调查团代表选定过程中的中日因应,阐明中国的急切心态和日本的引导预谋,以跨国史路径反观中国历史,实现从大国意志、中国心态和日本预谋三个层面透视九一八事变的“国际性”、国联调查团的权威性与紧迫性及其远东之行的必然结果。
一、人数设定和来源国构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最早向国联建议派遣调查团的是中国,但日本反对第三方介入,以中日直接谈判为挡箭牌,派遣国联调查团的提议遭搁置。1931年11月中旬,伴随着派遣调查团的舆论不断高涨,国联对日本的抵制立场日趋不满。与此同时,日本需要时间布控中国东北,调查团反而成了日本可利用的策略之一,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的代表、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沃尔特斯(Walters)就指出,“掌握邀请调查团的主动权是日本政府认为最紧要的事”〔2〕。于是日本内部开始酝酿,“建议理事会派遣视察员前往当地是为一策……由我方提议派遣上述视察员,可以取得事态有利于日本的效果”〔3〕,其目的是让调查团按照日本方案组建,从而利用调查团。
在日本的最初方案中,没有明确调查团的人数,对于代表人选则明确表示:“视察员的人选按照我方希望进行设置。”〔4〕日本此时抛出被搁置的调查团提案,得到国联理事会的积极对待,“各国理事最忧虑的事情是不能暴露国联没有实力的事实……解决此难题的一大对策就是派遣由一流人物组成的调查团,表面上可以被认为是国联努力的结果”〔5〕,急于证明自身可以发挥和平效力的国联开始朝组建调查团努力,调查团人数与来源国几经变化。
首先,调查团最初的人数设定是三人,由英、美、法三国代表充当。11月18日,德拉蒙德向日本代表团提出建议:“由英国的一流法学家,美国的一流实业家,法国的一流将军等担任视察员,他们所形成的意见必定可以获得各方面的重视,达到扫除中日之间危机的效果。”〔6〕外务省批示同意:“由英美法有力人士组成”,并建议“由通晓此事件的中日两国派遣代表参加”〔7〕。
外务省还专门针对调查团的构成人数及团长对日本代表团做了批示,“调查团的构成应该充分尊重我方意见……召集英美法重要人物组成调查团非常合适。若以法国将军为团长,更是我方极为欢迎的”〔8〕。芳泽谦吉亦向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表示:“调查团应该在与中国存在最直接利害关系的英法美三国中,选拔地位高且有能力的人组成。”〔9〕从上可见,日本计划调查团人数是三人,分别来自英、美、法的一流人士,并倾向于以法国为首。
其次,调查团人数因时变动,运作加入调查团的国家不断出现。11月20日,德拉蒙德向时任国联副秘书长的杉村阳太郎提出,“在法美两国人士之外”,如何应对“荷兰要求加入,意大利和德国正在运作加入调查团”等问题,而且“英国在客气地谢绝”〔10〕。外务省对此答复:“非常希望英国的一流法学家能够参加调查团,对荷兰与意大利的参加没有异议,鉴于德国的态度,希望能够避免德国参加。”〔11〕
11月26日,国联理事会成立起草委员会,具体商议组建调查团议决案的起草事宜。意大利在起草委员会中继续积极运作,希望能够加入调查团,“小国也有同样的行动”,结果可能会造成“调查团的人数不得已要增加到7名”〔12〕。日本对此表示不满,兼任日本代表团成员的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表示:“由与远东毫无关系的小国担任代表,而不是权威人士,这些代表与英美法等代表具有同样的权限,不仅会对调查团报告的撰写造成消极影响,而且担忧会削弱调查团自身的权威。最初方案仅限于英美法三国,迫不得已可以为意大利增加一个席位,不能再增加。”〔13〕
与此同时,德拉蒙德提出一个新方案,建议:“调查团人数可以用5人来取代7人,在军人、法律家、实业家之外,再增加铁路及金融方面问题的专家。”〔14〕11月29日,外务省批示“对于意大利人加入调查团没有异议”〔15〕,而与意大利同时运作加入调查团的德国却遭到日本拒绝,这引起法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莱热(Alexis Léger)等人的不安,“鉴于德国不能加入调查团,意大利也不能派遣代表,否则会伤害大国的颜面”〔16〕。所谓颜面的实质是大国的意志,大国之间的均衡在当时尤为重要。
再次,随着德国加入调查团问题得到解决,调查团人数和来源国最终敲定。德国驻国联代表于12月2日亲自会见杉村,指出“仅限于英美法三国人士的方案会影响调查团的效率发挥,起草委员会已经将调查团的人数定为5名,因此大国可以派出委员,德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且对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故要求任命德国人士参加调查团。德拉蒙德也询问杉村:“由英美法三国人士的方案变为英美法意各一人及其他国家一人的5人方案,德国要求再加入一人,目前形势是可能进一步变为6人方案。日本政府对此意见如何?”杉村坚定表示人数必须限制在五人,至于赞成哪国人士参加,需要请示外务省。〔17〕日本坚持五人方案和德拉蒙德暗中许可德国派遣代表加入,调查团的代表人数和来源国构成已经基本成型。
关于日本反对德国参加调查团的原因,杉村同德国代表的会谈内容给予了解释,根源在于日本担心德国会认可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行为。杉村提出“德国希望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围绕中国单方面抛弃条约问题上,德国与日、英、法等国存有不同态度,德国在欧洲提倡改订《凡尔赛条约》”,因此日本担忧德国赞成中国修改,乃至废除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故反对德国加入。德国代表予以解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是被《凡尔赛条约》夺走,而不是德国主动放弃,可以断言德国不会有日本所担心的情况”〔18〕,意在向日本表明德国不会支持中国“破坏”中日之间的协定。日德之间的会谈不仅体现德国要求加入调查团的意志诉求,而且反映日本对调查团的构成存在强烈预谋性质,力图排除任何不利于日本的因素。
实际上,日本对强硬拒绝德国参加调查团也存在犹豫,“相比于对待其他四个国家,日本对德国存在差别,将来会成为大国的德国肯定对此表示遗憾”〔19〕。当德国提出派遣驻日大使佐尔夫①佐尔夫(Wilhelm H.Solf,1862年10月5日—1936年2月6日),德国学者、外交官、法学家和政治家,曾担任德属萨摩亚总督(1900—1911)、德国殖民部部长(1911—1918)、德国外交部长(1918.10—1918.12)等职。从1920年到1928年,佐尔夫历任德国驻日本代办和大使,主导恢复德日良好外交关系,并协助谈判达成《德日和约》,被视为亲日派。加入调查团后,日本同意了,转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佐尔夫属于亲日派。芳泽就表示:“如果佐尔夫得到任用,对于我方是利好之事……希望同意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人士担任调查团成员。”〔20〕德国外交部在12月4日向国联秘书处提交了德国的三名候选人名单,以佐尔夫为首,另外两名是塞克特(Seeckt)和希尼。
至此,经过大国之间的较量与妥协,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遣代表构成调查团逐渐达成共识,中国亦不反对。1931年12月10日,组建调查团议决案获得通过,随之开始成员的选定程序,即先由五大国征求本国候选人的意见,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潜在候选人,再由国联理事会向中日两国征求赞成与否的意见,理事会根据意见最终确定正式代表。
二、成员遴选和大国权衡
英、美、法、德、意五国向国联理事会提出候选人的情况不一,费时颇久。由于每个国家遴选代表的步骤和过程都不尽相同,本文将依次介绍五大代表的产生。法国、意大利、英国代表确定较早,且未发生太多纠葛。美国代表确定较慢,涉及具体代表更换。德国的最终代表不是佐尔夫,引起日本不满,争论较大。
第一,法国代表的遴选过程。由于时任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是法国人,日本提议由法国代表担任调查团团长,“鉴于白里安是理事会主席的关系,可以考虑由法国委员担任委员长”〔21〕。按照方案,法国应该派遣“一流将军”参加调查团,故法国提名的候选人都是将军出身。最初建议吉拉马特将军参加,但将军的家人顾及其年龄以及健康状况,并不赞成将军前往远东,吉拉马特遂申请退出。法国又提出里昂军团司令官塞里尼(Serigny)为候选人,但未得到通过,其原因可能是日本认为塞里尼资历不如吉拉马特,“作为调查团的首脑,也必须是如同吉拉马特这样地位的人才能够胜任”〔22〕。法国提出的第三位候选人是克劳德将军,担任殖民地防御委员会议长等职,参与筹备裁军会议,该提议得到克劳德本人、国联和中日双方的认可。
第二,意大利代表的遴选过程。1931年12月15日,根据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吉田茂致外务省电报所示,意大利向国联提出来的候选人有五名,分别是前驻德国大使马柯迪、上议院议员和驻法大使萨尔瓦戈(Marchese Salvagoraggi)、前外交大臣施恩泽、在任大使维托里奥·切瑞蒂(Vittorio Cerruti)、海军大校德尔格雷科(Delgreco)。国联本计划委任施恩泽为意大利代表〔23〕,不过意大利和日本都倾向于马柯迪,“意大利希望选用此人,并已经向国际联盟提出了申请。驻洛桑的日本代表也多次表示同意此人当选”〔24〕,最终确定马柯迪为正式候选人。
第三,英国代表的遴选过程。英国应该派遣“一流法学家”参加,国联理事会最初有意选择常任上诉法官麦克米伦,德拉蒙德则表示:“如果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前外交大臣)本人愿意的话,由他出任会更好。”〔25〕外相西蒙(J.Simon)首先询问麦克米伦“是否同意作为英国代表,加入国际联盟任命的调解中日争端的调查团”〔26〕,麦克米伦回复“鉴于我是两家公司的董事……无法辞去这些董事职位,除非获准休假,否则不能离开9个月之久”〔27〕,变相地回绝了邀请。
西蒙随后致函李顿,一方面晓之以理,以调查团意义重大相劝导,“这项工作的价值对于英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另一方面动之以利,以调查团团长相诱导,“希望你能成为委员长”〔28〕。12月18日,李顿给西蒙回信表示接受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邀请。1932年1月21日,在调查团第一次内部会议中,李顿被推选为团长。
第四,美国代表的遴选过程。国联希望美国派遣“一流实业家”充任代表,海因斯成为德拉蒙德内定的理想人员。他曾于1925年受国联委托,调查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运情况,国联对此比较认可,因此建议美国先试探询问海因斯本人的意见。〔29〕12月17日,副国务卿卡斯托(William Castle)征求海因斯意见:“国联调查团可以……促使持续威胁远东和平的种种争端得到最终解决。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更有意义且完全值得去做。”〔30〕不过,海因斯拒绝出任代表:“深思熟虑后打算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上,现在不能承担如此重大的、突然的调整……无法担此伟任。”〔31〕
在美国推选麦考益出任调查团代表的同时,有诸多人士自荐,或希望成为国联调查团的代表,或希望成为调查团的专家技术人员,其中就有曾担任过美国驻南京领事的厄内斯特·普赖斯(Ernest B.Price)〔34〕、美国对华贸易专家爱德华·莫兰(Edward E.Moran)〔35〕、工程储备部(Engineers Reserve)的顾问级工程师杰尼(L.A.Jenny)〔36〕,以及曾在中国、日本、俄国等地工作的福特汽车公司外交官桑顿(P.B.Thornton)〔37〕。这些来自外交和技术领域的积极自荐者们,希望加入调查团前往远东地区,从而做出一番事业,这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团的重要性。
第五,德国代表的遴选过程。关于前述德国推荐的三人情况,佐尔夫属于亲日派;塞克特在一战中是军团参谋长,战后投入政界;而希尼是国会议员,在一战前曾担任德国殖民地阿弗利加总督,长期在殖民部任职。德国外交部东方司司长曾亲自向德拉蒙德明确表示希望“佐尔夫能够当选”〔38〕。不过,由于中国强烈反对、佐尔夫明显的亲日特质等原因,出现在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初步名单中的是希尼,这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国家间的外交折冲不断上演。
三、中国因应及心态
在大国遴选调查团代表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媒体舆论都及时跟进,中国期待调查团尽早出发和能够遏制局势恶化的心态表露无遗,其对代表的选择基本上以立场中立为标准。
首先,中国对调查团代表产生的艰难性深有认知,希望尽早确定代表并启程。在通过组建调查团议决案后的第二天,媒体就感慨“该委员会之人选,尚未确定一人”〔39〕,并认识到“大约此事非短时所能办,盖于五国各种专家之中,选出工程家、法学家、经济家、军事家与普通商业家各一人,殊非易事,恐须费相当时日”〔40〕。其原因是“惟人选一层,因须得中日及各调查委员本国政府之同意,故进行不能迅速”,因此调查团抵达中国东北的日期“当在明年开岁以后”〔41〕。基于调查团启程日期不定,日本甚至在日内瓦散播谣言,“中国表示如果调查团启程被延迟,将会开启直接谈判”〔42〕。日本散播谣言的实质是其希望调查团延迟赴中国东北,从而迫使中日直接交涉。
鉴于调查团迟迟未定,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成员胡世泽向白里安申述“有尽速将调查团派出需要”〔43〕,后来担任调查团秘书处成员的吴青峰亦向白里安催促从速派出调查团。〔44〕经过大国内部的权衡和成员遴选,到1932年1月上旬,调查团的五大代表才基本确定,当中国代表团向国民政府外交部发送名单电报询问是否同意任命时,外交部在电报上简明回复:同意。〔45〕调查团的“主席未定”〔46〕、“行程未定”〔47〕、“经费未定”等问题都一定程度上牵动着中国政府希望调查团尽早启程的心,其中的经费问题尤能反映出中国在组建调查团事宜上积极主动的态度。
关于调查团经费负担的问题,亚维诺最早提出“应由中日两国分担”,日本代表团认为“既然本次调查团是由国际联盟派遣而来,那么也理应由国际联盟支付其费用”〔48〕,不同意由日本支付费用的提议。相较于日本,国民政府外交部积极筹措经费,国联调查团的预算是100万瑞士币,而前两个月需要预支35万,外交部得知后马上“呈请行政院转饬财政部立即筹拨”〔49〕。1932年1月25日,外交部告知代表团,“调查团川装……正竭力筹汇”〔50〕。中国在支付调查团经费问题上相对果决,目的之一自然是希望调查团可以尽早启程,免因经费问题而延宕。
目前北欧及国内按不同的矿种矿石建造而且作为钼矿资源的主要对象仅有钨钼型矿石建造、单一钼矿石建造、铜钼矿石建造3种类型,而目前就其开发利用水平看,最主要的是大型、超大型网脉状即细脉浸染状亦即目前我国最主要的矿床类型—斑岩型钼矿床,其中包括钨钼、铜钼以及单一的钼矿石建造的矿床在内,矽卡岩型钼矿床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种[5]。
其次,中国反对存有倾向立场的人充任调查团代表。中国从一开始就担心调查团受到日本的误导,12月10日,顾维钧表示:“国联视察团如果来华,在我如何筹划使不受日方包围……关系极为重要。”〔51〕对于何种人员可以出任代表,有媒体提出三项必要条件,“须年富力强,俾能服当地之水土;须有余暇远适;须有相当之声望”〔52〕。顾维钧则表示:“可以同意任命任何人,只要这个人既不亲华亦不亲日即可。”〔53〕
围绕五大代表的遴选,中国基本以赞成为主,仅在德国代表人选问题上反对佐尔夫。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12月5日就明确反对佐尔夫任代表:“由于调查员需要公平无私方可,而佐尔夫最近关于满洲问题发表了一些演说,存在明显的偏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反对任命佐尔夫。”〔54〕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调查团代表的要求是“对于人选须以不反对中国与不偏袒日本者,方可同意”〔55〕。中国媒体还专门报道希尼的立场,12月24日,希尼关于九一八事变向新闻记者说道,“余决定以最客观态度,观察此项事件,而提出报告”,关于调查团,“余参加调查团之工作,对两国将维持完全不偏之态度与同情”〔56〕。
再次,国民政府更为关心东北局势,对调查团的失望和期望共存。在调查团代表的选定过程中,日军没有停止侵略,其借口镇压土匪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代表团备文通知行政院,提请注意,并请设法制止”〔57〕。1931年12月21日,中国代表团指出日本“违反12月10日议决案,仍在谋划扩大对满洲地区的军事占领”〔58〕。12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陈铭枢致函白里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处理这种情况,以使12月10日的议决案可以生效”〔59〕。尽管中国不断申诉,无奈国联没有遏制日军的能力和决心,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军事局势不断恶化和调查团代表选定艰难两相纠葛,中国对调查团形成了双重逆反心态。有媒体失望地表示:“锦州已被暴日占领,国际联盟的中立调查团至今尚未派出。国联之不可恃,已成赤裸裸的事实。”〔60〕当国联理事会第66届会议开幕时,调查团还未出发,媒体指摘道:“当初希望开会期内,对于辽东至少可得一调查团之临时报告,但迄今调查团犹未启程,此种希望迨成泡影”〔61〕,对于“整个满洲问题可搁至国联调查团赴华调查并提出报告后再谈”的无奈事实,媒体嘲讽这是国联的悲哀,国联调查团不过是“旅行团报告”而已。〔62〕
除悲观和失望的心态之外,对调查团抱有期望的舆论亦未消失,遏制军事行动是催促调查团尽早出发的唯一目的。中国对调查团的作用充分体现在“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上①1931年9月3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议决案,规定日本将军队撤入铁道附属地内,同时中日两国政府“为不使事件扩大或事态恶化,将各自采取一切必要之措施”,因此在通过“12·10”议决案的同时,理事会主席白里安发表声明,当调查团到达中国东北后,“如果两当事国尚未履行在9月30日决议中所作之承诺”,调查团“应尽快就其事态向理事会提出报告”,这就是“调查团首先调查事项”。参见赵朗编:《“九·一八”全史》第5卷资料编·下,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820-821、835-838页。,“惟其第一任务,即在将届时日军之曾否撤退,报告理事会”,同时希望调查团能够为国联处理中日冲突提供依据,“至理事会将来对于辽案之行动,则将以此调查团之总报告与建议为根据”〔63〕。尽管调查团迟迟无法启程,但依旧期望调查团赴远东之后,可以“首研究满洲情况,然后再考察中国本部情形”〔64〕。
日本军事行动不断持续,相较于调查团的具体代表产生,国民政府、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媒体舆论都更为关心东北局势,这也是中国对调查团期望的一种折射。
四、日本评估及其预谋
调查团成员选定过程深刻反映了日本的利益诉求和预谋,尤其是德国代表人员的确定。对于拟定希尼出任德国代表,日本起初没有接受,而是经过协商、争论和质询后,才无奈地接受,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步,日本进行内部协商。芳泽于1931年12月15日向外务省汇报:“德国代表当初被指定为佐尔夫,我方也曾预想此人一定会得到任命……但现在推荐希尼代替佐尔夫,我方认为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65〕犬养毅外相回电表示:“关于德国的候补者,我方最初的基本方针是不同意德国加入调查团之中。在推选出佐尔夫之后,我方才认可,因此希望佐尔夫当选。”〔66〕
第二步,日本向国联争取任命佐尔夫。12月16日晚上,芳泽亲自拜访亚维诺,指出“从理事会开始交涉本问题起,日本一直主张接受德国参与调查团的前提条件是由佐尔夫出任。但事到如今却要换人,这让日本感到非常失望”,亚维诺则表示调查团代表需要得到当事国的同意才行,“如果当事国的某一方表示难以接受的话,选定佐尔夫就变得非常困难”〔67〕。
第三步,日本质询德国和德国的解释。12月17日,日本驻德国参赞东乡茂德质询德国外交部东方司副司长,该副司长解释德国确实指定了“以佐尔夫为首”的三人候选名单,“由于最终的决定权在理事会主席、国联联盟秘书长以及日中两国的手中,德国无论做出何种努力都很困难”。中国不仅反对佐尔夫,而且反对军人身份的塞克特以及长期对殖民政策抱有兴趣的希尼,“中国的非难一直存在”〔68〕,德国将佐尔夫未被选任的责任推给国联和中国。
第四步,经过一番争取后,日本内部开始接受希尼,主要背景是若不同意希尼,会引起对日舆论的恶化。12月24日,芳泽向犬养毅汇报,“关于此事,正通过直接委托杉村公使,为选用佐尔夫而努力操作”,不过表示“如果我方仍然固执坚持选用佐尔夫的话,会出现不愉快的结果也未可知……请对此决定表示同意”〔69〕。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向犬养毅劝告:“日本对任命佐尔夫以外的其他人选表示不满,因此拒绝德国派遣代表参加的话,德国肯定会很不愉快。在任命之前便对候选人表示不满,实非良策。”〔70〕在经过对诸位候选人进行评估后,日本最终同意了包括希尼在内的代表人选。为了尽可能有利于日本,最低限度也要避免不利于日本的人士当选,日本对调查团的潜在候选人都进行评估,方式包括直接沟通和间接判断。
关于法国代表,日本对最初可能出任代表的吉拉马特将军的评估是“对日本抱有亲近感”,原因在于吉拉马特曾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受伤,得到日本医生的救治而避免手臂截肢。〔71〕对克劳德将军的评估是“一位风评极佳的将军,在担任大演习总指挥时,特别向日本陆军军官表示善意”〔72〕。驻法代理大使栗山茂还于1932年1月4日同克劳德进行了会谈,栗山认为克劳德“表现出不少对于日本的善意态度”,属于“聪明温和的人,对日本没有任何不利的先入为主印象”〔73〕,判断克劳德不会对日不利。
关于意大利代表,日本驻意大利参赞冈本认为施恩泽“对中日的感情可以说如同白纸一般”,评价其“是一名实干家,一名和蔼可亲的人……选用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对日本来说非常合适”〔74〕。在意大利正式推出马柯迪后,日本驻意使馆评估马柯迪是“纯粹的外交系统出身”,曾在巴黎和会期间担任意大利代表团的秘书长,后供职于阿根廷和德国大使馆,且“对日感情已经得到认可”〔75〕,判断马柯迪的立场不会有损日本。
关于英国代表,松平恒雄表示麦克米伦不属于英国外交部人员,而是“颇有力之政治家,同时也是法律专家”〔76〕。对于最终选定的李顿,日本代表团仅报告李顿曾代理英属印度总督〔77〕,在李顿被推选为调查团团长之后,杉村对李顿的评价不高,称其:“绝非领袖之材……不如说他是才子一样的人物……对东洋人之性格多少有所了解,处理事情较为融通灵活。”〔78〕或许是李顿曾担任过殖民地总督的经历让日本坦然接受,也或许是日本根本无法拒绝英国选定的代表,日本对李顿参加调查团没有异议。
关于美国代表,得知国联有意海因斯,日本就开始搜集有关海因斯的资料,判断他“没有处理过远东事务,理应会做出公正的观察”〔79〕。12月17日,驻美出渊大使还专门拜访史汀生,试探海因斯的立场,再确认“海因斯迄今为止和远东地区没有任何牵扯……可以做出公平的观察”〔80〕。对于最终被选定的麦考益,日本评估就更多了:(1)日本代表团认为麦考益“在日本也广为人知,且是一位对日本持有良好印象和感情的人物”〔81〕;(2)出渊大使汇报与其说麦考益是一名军人,不如说“是一名拥有卓越手腕的政治家”〔82〕;(3)吉田茂汇报麦考益“时常关心国际关系问题……厌恶共产主义,是一名现实主义者,是合适派往视察中国的人选”〔83〕;(4)日本驻厦门三浦领事汇报曾与麦考益共事的美国驻厦门领事傅克林(Lynn W.Franklin)的看法:“麦考益将军的当选,不论是对日本还是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正如满洲之于日本,麦考益恰好被派遣到过有类似关系的尼加拉瓜,体会过辛酸,对于妥善处置困难的局面有经验。”〔84〕经过评估,日本判断麦考益出任美国代表有益于日本。
关于德国代表,日本对希尼的评估结果是最终认可希尼的原因。12月18日,小幡向外务省汇报,认为希尼“性格是官僚的”,鉴于希尼长期从事殖民事业,“对殖民地问题仍保有浓厚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希尼“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未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会出现国家主义衰退的情况”,小幡判断希尼“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理解日本的对华经略”,即“由于人口增殖,日本必然对中国采取帝国主义的方针”〔85〕。1932年1月27日,小幡与希尼举行私人会谈,希尼不仅肯定小幡对九一八事变的解释,而且表示“德国对于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可以保证完全中立的立场”〔86〕。
此外,日本针对调查团的准备工作从1931年11月底就开始了。11月23日,驻华公使重光葵命令驻华各领事馆准备各种材料“向调查团说明日本立场”〔87〕,11月30日,驻沈阳总领事森岛守人围绕“排外状况及排日状况”“中国对国联的报告与事实相违背”等13个项目准备说明材料。〔88〕在初步拟定调查团人选后,日本代表团指出调查团中“通晓中国事情的人非常少。在调查团代表到达中国之前,绝对有必要向他们预先传达正确的信息……应当抓住代表们在日内瓦集合会面之类的机会,分发资料”〔89〕。
1932年1月21日,杉村以国联副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调查团第一次内部会议,而中国代表颜惠庆则被理事会拒绝出席。杉村利用此次机会,对调查团做了诸多劝告工作:(1)向调查团分发“有极高价值”的参考资料,“旅途中预先获得必要之知识,到达现场方能完成充分之视察”;(2)指出中国的情报存在来源不确定问题,“希望代表们每日开会,能仔细分析情报的来源,交换意见以避免观察流于偏颇”;(3)建议调查团先抵达东京,“2月上旬从欧洲出发,3月10日前后抵达东京,希望首先访问日本外相,并按照日本内阁提出的计划进行活动”,到4月下旬再去中国;(4)提议调查团应该“尽可能广泛地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同时会见各个阶层、类别之人士”,并以大连为基地,“每次前往满洲地区考察1个星期或10天左右后就返回大连休养”〔90〕。可见,杉村的言行充满了试图让调查团远离中国而偏向日本的预谋。在调查团初步选择海上航线后,日本极力安排日本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伊藤述史与调查团同行,若共渡大西洋无法做到,“横渡太平洋时一定要让伊藤和代表们同船”〔91〕,目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诱导调查团。
结语
1932年2月3日,国联调查团终于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正式开启远东调查之行。由英、美、法、德、意五大国派代表组成的国联调查团,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可以称得上是豪华阵容,充分反映了中日冲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在国联理事会的外交博弈就显示了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更是进一步体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模式在处理中日冲突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同时预设了各国国家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汇合与角逐。
首先,英、美、法、德、意五大国遴选国联调查团代表的过程,充分反映出五大国对调查团寄予期望。确定调查团代表的来源国的过程,清晰地呈现了这是大国主导的政治运作,集中体现了大国意志。从五大国遴选出的多名候选人中可以发现这些候选人都可以称之为“一流”,从而保证调查团的“权威”。毫无疑问,五大国对调查团代表的遴选是国联调查团具有时局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其次,选定的代表们确保了调查团的工作能力,这是调查团能够完成任务的前提保证。整个国联调查团囊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关键领域的人才。团长李顿曾对调查团进行定性,调查团“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调查机构,它的主要目标是向中国和日本提供服务,以便找到使这两个国家达成长期共识的基础”〔92〕,寻找中日之间恢复和平的解决方案是调查团的重要目标。在赴远东途中,调查团频繁召开内部会议,共同商定的《工作安排备忘录》有关于调查团的行程安排,第一步就是“首先与中日的主要官员和民间人士沟通接洽”〔93〕,前赴远东的调查团进行了一定的合理规划。
再次,国联调查团成员的选定过程蕴含国联和当事国的意志,确保了调查团的合法性。由国联调查团成员的选定程序可知,调查团代表的产生是在综合来源国、国联和当事国三方共通意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受到广泛的认可。由此组成的调查团所主导的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公平与公正。以此反推,日本因调查团报告书退出国联,可谓是摆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蹂躏了国际联盟所代表的和平。
第四,中国在国联调查团代表选定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心态,既决定了中国对代表的要求以立场中立为标准,也反映出中国寄希望于调查团遏制中国东北的恶化局势,体现派出调查团的紧迫性。在确定调查团代表的过程中,一方面相对于日本在代表人数、来源国构成及具体人员上的外交运作,中国的实际话语权不足,以代表不具备明显的政治立场倾向为底线;另一方面中国关心的重点在于东北军事问题,调查团赶赴东北是中国的现实所需,而这并不是日本的努力方向。中日的这种反差是两国国家利益在国联外交层面的体现,日本预谋利用调查团为其服务和背书,中国则是以调查团遏制军事行动、阻止局势恶化为主要目的,调查团的能力和调查效果是最为中国在意的。
最后,日本深谙国际外交手段,其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预谋,对国联调查团造成的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调查团远东之行的必然性结果。在调查团组建过程中,日本代表团就曾向外务省表示“假使调查结果中有不利信息,日本也没有必要受到报告书的束缚”〔94〕,日本从一开始就决心不能受调查团的束缚。在决定组建调查团后,从人数设定、成员选定等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日本的预谋,试图造成调查团及其具体代表倾向日本之结果。日本的预谋亦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调查团不仅迟滞启程赴远东的日期,使日本有更多时间布控中国东北,消化“战果”,而且首先前往日本东京,给予日本进一步误导和影响调查团的绝佳机会,此环节对中国极为不利。
总之,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尤其是人数确定、来源国设定、具体代表选定等环节,深刻证明调查团是国联意志、大国意志以及当事国意志融合的结果,并影响了调查团赴远东之后的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