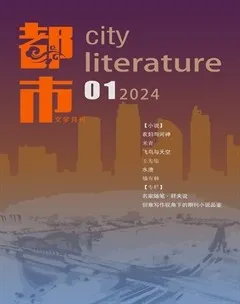平静却流淌着
2024-01-31钟小骏
钟小骏,1978年生,祖籍浙江,长居山西。文创二级。小说、人物传记曾获奖,参与创作影视剧多部,有随笔、杂文等散见于国内各媒体。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兼职教师。
邓一光的这篇小说是《收获》2023年第6期中的短篇头条,全文万字,叙事清晰简洁,描述了一个地铁的安保员“狄二岸”工作的一天,从“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就要被迫起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十二點十八分,狄二岸交完班,走出保安室”结束,其间狄二岸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它们既是“非常的”,但这种“非常”又恰恰是地铁的“常态”,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对“狄二岸”来说是“特别”的,那就是今天是“他在地铁集团服役期间的最后一次”。
这篇小说先打动我的是“语言”,不是指语言风格,那种俏皮的、幽默的、小清晰或者故弄玄虚的,而是言说的“内容”:“他独自穿过岬湾海岸挂满海葵和层孔虫的海蚀崖,从那里折返,通过生物遗骸沉积而成的盐矿,依次去了咸头岭和大黄沙、屋背岭和九祥岭、红花园和铁仔山的地下遗址,它们分别是新石器时期、商代和汉代人类活跃过的地方”。这样的内容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甚至就是在故事刚开始的第一段,不得不说是极为大胆的。霍金说“书里每出现一个公式就会减少一半的读者”,作者建立的进入门槛让我替他捏一把冷汗。
然后就是“形式”,在分段进行了“ABCDE”的标注之外,还进行了“时间标明”:“A 00∶30,深时王国的短暂旅行”“B 05∶30—05∶45,地铁安保员的晨间活动”“C 05∶45,机场、码头、珠江三角洲和地铁1号线”,还是那个问题——难度太高,如果内容方面的说服力不够,这样赤裸裸、明晃晃使用“时间”作为“线索”来进行“叙事”,对早已经被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反转”“再反转”“猎奇”“刻奇”磨炼得心如止水的现代读者来说,就只剩下被放弃了。邓一光自己说“故事的时间标题是红明老师建议我加上的。我推测这对主人公没有太多意义,但对故事有”。
可作品还偏偏没有“人物”——从头到尾“狄二岸”都不负责提供“动力”,而只是提供“视角”,而对建立人物而言的技巧中,外貌描写没有,性格描写没有,心理描写极少,动机描写没有,变化描写没有,只有相对模糊的处境描写和需要仔细观看被作者分隔得很远的行动描写,换句话说,与其说对“行动”的描写是为了建立人物,不如说人物是为了让“行动”更合理。至于其他人物更是如此,众多的“保安同事”,地铁中的“大学生”“长发青年”“中年女工”,只从命名方法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一群“普通市民”,也就是我觉得有些模糊的“处境描写”的一部分,但在之后的叙事中作者又太过克制,并未对“处境”进行更多讨论,又让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偏执影响了我的判断,对某些词汇或者状态太过敏感以至于产生了误读。
那么“事件”或许是叙事的“核心”?却也并非如此,吃早饭、领装备、上车、处理纠纷、吃午饭、巡逻、吃晚饭、巡逻、下班。并不是说在每一个部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而是说叙事并不针对这些事情,作者给“事情”下一个定义,使用着“叙述”的语言完成对“事件”的描述,“长发青年一边小声打电话,有人靠近他他就躲开,这样换了好几个车厢……长发青年出门闯荡了几年,毫无收获,身心疲惫的他想回家,可身上只剩下二十块钱……在车上用微信和家人通话,请他们给自己订一张回家的高铁车票。他打给爸爸、姐姐、舅舅、堂兄……车过世界之窗后,他换成给同学和熟人打电话,一直打到科学馆站,剩下的四站,他绝望地收起电话,靠着车窗发呆。”即使在“故事理论”中天然自带强戏剧性的“死亡”,作者也没有浓墨重彩。“狄二岸看见一个职员模样的中年男子步履迟疑地走下站台,在最后两级台阶上站住……二十分钟后他得知,中年男子被发现倒在地上,脑袋耷拉在台阶下,急救人员赶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只叙述所看到的现象却不进行探讨,或者是作者对世界的尊重。他说:“普通人的世界多半是局促和限制的,至少在人们眼中这是现实,但我怀疑它是全部的真相。”
那么就是“情绪”了。我一直认为“主题”其实只是一部作品被介绍给读者时为了方便解释而被提出的概念,在我看来,其实这是对“作者答案”的一种解读,也就是说最初推动作者进行创作的动力来源,举例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所触动的“场景”——画面、声音、行动、表情甚至是感受、知觉等等——我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值得分享给他人的,但有时这个场景不太容易复述,难度或者来自技巧,或者来自性质,总之那一瞬间是多个因素在起作用因而使得转述时繁杂、琐细又不够准确,最终无法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共情,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一个故事,这样沉浸其中的读者自己推动着心情进入场景中来,掩卷之后恍惚能够体会作者的那个瞬间。这个答案可以宏大也可以微观,可以是某个理念,也可以是某种细微的体会,但无论是哪种,这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最终的目的,也是最初的动力。因此,有评论家认为“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清水河仓储区大爆炸时,狄二岸和胡先生同在现场,那会儿胡先生还是一名记者,是个长发飘逸的年轻人。不同的是,胡先生赶到现场前,狄二岸已经被下午一点二十五分的第一次爆炸掀进一片废墟,身子炸得难以辨识。……狄二岸几天后才知道,胡先生在第二次大爆炸时受了伤,自行车也丢失了,他忍着伤赶回报社,写下一篇新闻稿:《深圳在我眼前爆炸》。胡先生在稿子里写到现场的险情:六个过氧氢罐离大火仅十三米,如果第三次爆炸发生,必将引爆附近八个储量超一千吨的液化气罐、十八节液化气槽罐和加油站,威力将是广岛原子弹的两倍,大半个特区将夷为平地!‘苦心经营十四年的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难道真要毁于一旦?’……他不知道人们是否给那三千多位无名男子塑了纪念碑,如果人们忘记了,应该补上,因为他们救下了这座城市,救下了一个时代。”这段是这部作品的“答案”,并总结道:“邓一光在《在地下》中对当年那场大爆炸的回忆性创伤描述,很大程度上应该被看作是富有良知的作家对深圳既往生命隐痛的一种真切书写。”
其实我是部分同意的,毕竟这部作品我思考了挺久的,却总觉得说不清楚,却又忘不掉,然而邓一光似乎也不太认同,“清水河爆炸后,主人公不可能在原地重建支离破碎的生命和生活,但他可以重塑。若干年后他回来了,我跟着他走了一天,记下他在人类世最后的行程”。“别尔嘉耶夫在《历史的意义》中说,时间在表面上被撕裂,彼此征服和反抗,但终极处却指向永恒,这符合人类世的生活。”
或者每个人的说法都对,邓一光的、评论家的和我的,毕竟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故事结合后生出的答案——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内部激流湍涌。或者完全反过来,自己觉得惊天动地,但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显现也不值一提的“无所谓”。
责任编辑 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