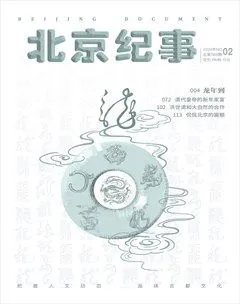童忆过年
2024-01-31刘建民
刘建民

童年的我和四合院里的小伙伴儿们一样,心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能打牙祭、能穿新衣服、能放鞭炮、能跟在大人身后,东家走西家串的磕头拜年,还能得到压岁钱。既热热闹闹,又开心快乐。到了年三十晚上还能点灯笼。
四合院里的小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腊月二十三是民间的小年。小年一过,正月初一的年就进入倒计时了。家家户户都忙碌了起来。二十四扫房子,到了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都忙着归置屋子,打扫卫生,扫房子。
我家居住的屋子不大。原本有一间四合院里的西厢房,也就有十三四平米,后来我家旁边的邻居搬走,那间房给了我家。我们将两间房屋打通,连在一起。房屋进深很浅,呈细长状态,还有两个房门。我戏称我家叫无轨电车,即使这面积狭窄的无轨电车,过年也要有个过年的样儿。父亲上班工作繁忙,不能请假打扫卫生,扫房子的任务就落在了年逾花甲,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母亲身上。母亲换上旧衣服,头上系上一块毛巾,把家里的一把鸡毛掸子绑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高高举起,掸扫着落在墙上厚厚的尘土。
二十七宰公鸡。说到宰公鸡,还有一个小故事呢。有一年腊月二十七一大早儿,我父亲就忙活开了。他先从我家鸡窝里抓出来一只大公鸡,在院子地上放了一个大碗,准备杀了鸡,往碗里滴血用。我父亲天生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做什么事都思前想后,三思而后行。只见他左手掐住大公鸡的两个翅膀根儿,用右手揪住大公鸡脑袋上的鸡冠子往后拉。然后交到左手捏着。这样就把大公鸡的脖子完全暴露出来。用右手把大公鸡脖子上的几根毛拔了下来,然后右手拿起身旁准备好的菜刀,哆哆嗦嗦地照着鸡脖子就剌了一刀,鸡脖子流出了血。我父亲吓得赶紧把大公鸡往地上一扔,可是没一会儿工夫,那只流了血的大公鸡,一扑棱又站起来了。我父亲又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大公鸡,又在鸡脖子上剌了一刀,然后扔在地上。没过几秒钟,这只生命力顽强的大公鸡又动了动身子,还没死。
这时候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邻居里,有我的一个干爹,他曾经在他们单位食堂里做过厨师。他对我父亲说:“刘大哥,没有你这么宰鸡的,太温柔了。照你这个宰法,再来两刀,鸡也死不了呀。你把刀给我,看我怎么宰。”
父亲把菜刀递到我干爹手中,只见我干爹左手把还没死的大公鸡按在地上,右手高高举起手中的菜刀,手起刀落,一下就把大公鸡脑袋砍了下来。这只被砍下脑袋的大公鸡,突然腾空而起,一扑棱飞起一人多高,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再也不动了。当时把在旁边看宰鸡的我吓了一跳,一个大屁股蹲儿就坐在了地上。二十七宰公鸡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一记就是50多年。
难忘的除夕夜
大年三十一早儿,还在被窝里的我,就被传来的鞭炮声震醒了。开始是零星的二踢脚的爆炸声,接着传来的就是整挂鞭炮的拉鞭声,此起彼伏。
大年三十一早起来,母亲就给我和哥哥穿上新衣服和新鞋。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我穿的新棉袄、新棉裤和新棉鞋,是我三姨的闺女——我表姐给我做的。我穿着崭新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甭提多高兴了。穿上就不想脱。穿上新棉鞋,不知怎么迈步了,生怕把新鞋弄脏了。到了晚上睡觉,把衣服脱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炕头儿,生怕压出褶子来。
除夕夜晚上,家家户户都包饺子。那时候不和现在一样,在超市里买现成饺子。而是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剁白菜、调肉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那种和谐的氛围,令人难忘。
大人们包饺子,准备年夜饭。孩子们都跑出家门,在四合院里,在胡同里,打着灯笼,走街串巷地开心玩儿着,乐着。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除夕,我打的是一盏大公鸡造型的纸灯笼。母亲先把大公鸡灯笼底部的小蜡烛点上,然后把灯笼翻过来别好了,又找了一根小棍儿,把灯笼调上。我拿着灯笼和小朋友们院里院外疯跑,玩得别提多高兴了,正赶上那年三十晚上有风。我穿上过年的新衣服,手提着灯笼一个劲儿地摇晃。晃来晃去把小蜡烛晃倒了,顿时大公鸡灯笼着起火来,我赶紧提着着火的灯笼往家跑。还没跑到家,纸灯笼已经烧完了,就剩一个空架子了。我哭着跑回家。母亲安慰我说:“烧了就烧了吧,没烧着你就行了。别再出去了,帮妈包饺子吧。”于是我就脱了新衣服,坐在小饭桌前,帮母亲擀起了饺子皮儿。
大年初一拜大年
每到大年初一大清早,母亲就早早把睡梦中的哥哥和我叫醒。我们起床后,母亲就忙着收拾屋子,父亲拿来一个小方棉垫,放在我家一进门的门口,把花生,瓜子和糖果摆放在盘子里。又拿出牡丹和凤凰牌香烟摆在烟灰缸旁,准备招待前来拜年的街坊邻居。
早晨八点多钟刚过,拜年的就来了。在我们那个四合院里有8户人家,除了我家对门的王大爷王大妈比我父母岁数大以外,其余的街坊邻居都比我父母小。所以其他的邻居都管我父母叫刘大哥、刘大嫂。北屋的庆章大哥、东屋的秉章大哥和玉珍大姐,还有北屋的我干爹、干妈都来给我的父母拜年。一拨接着一拨,本来就狭窄的屋子,更显狭小了。但门庭若市,更显出了过年火热的氛围。庆章大哥往我家屋里的棉垫上一跪,两只脚已经顶在我家门槛上,正赶上我干爹也来给我父母拜年,我干爹往屋里一迈步,一不留意就踩在庆章大哥的脚上。庆章大哥赶紧站起身来,对我爸说:“得嘞,先且让后且。”然后告辞走出我家屋子。紧接着我干爹、许大叔等街坊一个接一个来到我家,给我父母拜年。我父母拿出烟和糖果招待他们,他们也不抽烟,也不吃糖。进屋磕完头就走,也不待着,又到下一家去拜年了。其实过年晚辈儿给长辈儿磕头拜年,就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了弘扬中國的传统文化。
那时候我还上小学,还是一个小豆包。看着院里街坊都来给我父母拜年磕头,就坐在我家土炕边儿上,看着眼前的一幕,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中国传统风俗过春节拜年的情景。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许多老屋老院都拆除了,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不少北京市民都已从低矮潮湿、简陋的平房,搬进了高大敞亮、方便宜居的楼房。但人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老北京平房四合院里过年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那种一家炖肉满院香,其乐融融的过年氛围,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