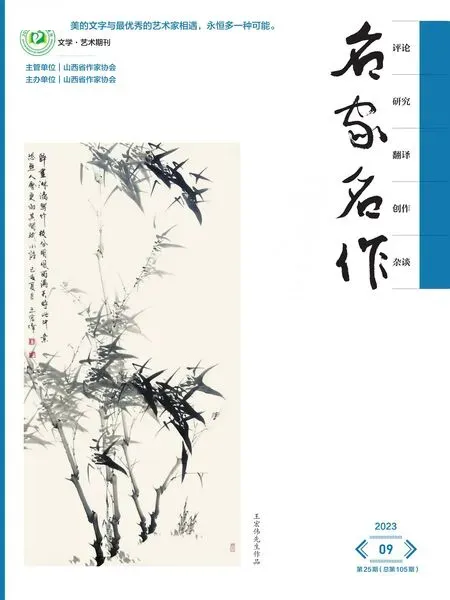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身份困境探析
2024-01-28尹晓琳韩君隺
尹晓琳 韩君隺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展示了进城青年陈金芳失败的奋斗过程,不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城市中。本文尝试从陈金芳身份认同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困境入手,探究石一枫笔下进城青年身份认同困境形成的原因及对当下的意义。
一、腹背受敌——进城青年的困境呈现
进城青年在社会上普遍呈现出一种“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他们不被城市人接纳和认可,城市人认为他们是农村人,对他们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当他们离开家乡奔赴城市时,农村老家的村民却把他们当成了城里人,对他们也赋予了对城里人的期望,尤其是在自身遇到困难或者有其他需要时,就自然而言地向已经成为“城里人”的老乡求助。他们不被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接纳,这种双方都不接纳的处境让进城青年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
(一)回不去的农村
对以陈金芳为代表的进城青年来说,他们的出生地农村对他们的发展完全没有带来正面影响。农村不仅无法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甚至连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依靠也无法提供。一旦离开家乡,在家乡众人眼里,他们就是可以当作“摇钱树”的城里人了。陈金芳的姐夫许福龙留在北京之后,他的家就成了乡亲们的免费据点。对于乡亲们来说,一旦自己家乡的人有了在北京扎根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就是可以依附、索取的对象。他们眼中的许福龙就是北京一个免费旅馆的老板,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住到那里去,谁叫许福龙已经有了两间小平房可住呢?而“许福龙们”的想法和为难之处则不在乡亲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陈金芳在学校受同学排挤,回家还要面对亲人的算计。她想留在北京,姐姐却以“不养闲人”为由将她赶出去,完全忽视这些年她对家里的付出,对她拳脚相加,这也导致了她辍学,使其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对于以陈金芳为代表的进城青年来说,家庭并没有给予她们什么温暖。家庭不仅不是他们的后盾,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他们的对立面,成为另一股对抗他们的力量。
陈金芳住院后,闻讯赶来的“我”,再一次邂逅陈金芳的姐姐和姐夫。这两个典型的小市民先是询问“我”是不是债主,在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后,又开始诉说这些年陈金芳的种种投机行为。陈金芳一直是村里人嘲笑的对象,可是当村里人觉得陈金芳挣了大钱之后,态度又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争先恐后地要求她带村民们发财。在身处困境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对陈金芳伸出援手,甚至连骨肉至亲也没有帮助过她。而陈金芳“功成名就”后,他们又理直气壮地要求分一杯羹。进城青年不仅在社会中面临着劣势局面,甚至在精神上也是孤独的:失败时,身边都是耻笑的声音;而成功时,身边又都是算计的声音。这种精神上的困境也限制了进城青年的生存与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完全是进城青年割离了农村,而是农村“放逐”了进城青年。
(二)进不去的城市
陈金芳在学校一直饱受嘲讽,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出格或不正常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她是行为的发出者。对于陈金芳来说,来自同龄人的恶意往往更为尖锐,她无法融入这个处处对她施以白眼的环境中。比如她决心改变形象时,虽然同学们也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经历,有过分者还软硬兼施地逼迫父母用半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一双球鞋,但同样性质的行为到了陈金芳身上就成为一种原罪。甚至连老师都出言讥讽她:“你们家那么个条件,还穷嘚瑟什么呀?”“我”说出了大家排挤陈金芳的真正原因:“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大院子弟们对陈金芳的鄙夷不是真正因为“虚荣”,而是“凭你也配”。
在学校中的陈金芳需要面对来自同学和老师的蔑视,而走进社会的陈金芳则需要承受来自所有人的恶意。她和痞子们厮混,可痞子们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可以一起玩乐的工具,从情感上并不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她;当她好不容易挤进梦寐以求的艺术圈子后,其他人也总是用怀疑的目光去审视她。陈金芳选择依附男人,用身体和那股闯劲当本钱。她一路向前,先是和小混混合伙做买卖,最后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圈子的名人陈予倩,最终却因为一意孤行,将所有资产都押在一场艺术投资上导致破产并身败名裂,被债主打进医院。陈金芳辍学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过程中,除了像其他进城青年一样要付出很多辛苦,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从“底层”的混混圈子到“上层”的艺术圈子,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她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她在外闯荡的时候,每次投资失败,她都要以身体为代价去还债或积累本钱。在小说中,城市吞蚀了农村的土地,吸纳了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还剥削着陈金芳这样年轻女性的肉体。“陈金芳们”在这个社会腹背受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二、进城青年的身份认同困境溯源
(一)城市追求溯源
身份认同指个体在社会中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深刻影响着群体的身份认同。在阶级社会中,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从一开始,陈金芳就以“农村插班生”的身份出现,加上她土气寒酸的外形,大院子弟们自动与她划清了界限。实际上,陈金芳受同学排挤的原因主要还是她“农村人”的身份,但刚进学校的她并不太能理解这种身份所带来的白眼,而是想要通过改变外形的方式改变自己“土气”的状态,这种对美的尝试给她带来了新的罪状:虚荣。进城之后,虽然陈金芳见识到了繁华世界,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繁华世界就会对她全盘接受。农村人的身份只会为陈金芳带来白眼,因此,陈金芳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她拼命地想贴近城市,变成城里人。对于少女时代的陈金芳来说,外貌和衣着打扮是她可以贴近城里人的唯一途径,通过外貌的改变就可以完成身份的变换。她天资不算聪颖,也没有一技之长,或许在她心里,只要看起来和城里人一样,那就算是半个城里人了。这种急于需要认同的心理状态影响着陈金芳的外部行为,她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得到“城里人”的身份认同。
长大后的陈金芳想用金钱和名声收获城市上层阶级的身份认同,可对于深谙此道的人来说,陈金芳不过是注定入局的被宰割者。她所谓的阶级跃迁,也不过是成为另一个圈子的“外来者”。陈金芳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走南闯北,看似光鲜实则狼狈。在村民眼里,陈金芳手里似乎有了一些钱,她开着轿车回乡,带来了穿着考究、看似专业的合伙人,甚至在母亲去世后为母亲举办了十里八乡最隆重的葬礼。虽然陈金芳已经成为村民们眼中的能人,但她并不满足于成为这一方小天地中的红人,她的追求依然是到大城市去,哪怕大城市的风险更大,人们的内心更险恶,她也毫不畏惧,一心要做成一番大事业。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陈金芳对城市的追求也不难理解——机遇都在城市,农村可以满足陈金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虚荣心,却满足不了她的野心,所以她拒绝“农村人”的身份,一门心思想要转变成“城里人”。她在见识到城市的繁华以后,无法接受自己不是城里人的现实,因此,成为体面的城里人就是她所追求的目标,无论是农村的放逐还是城市的排斥,无疑都加深了她的这种渴求。陈金芳的身份认同困境实际上是外部生存困境在她内心的映射,社会对她的排斥和伤害影响了她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又对她的行为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二)艺术追求溯源
陈金芳的艺术梦是贯穿全文的线索。陈金芳并非粗鄙贪财的进城青年,相反,她对高雅艺术有着狂热的追求。布迪厄认为,文化偏好有划分社会阶层的作用,高雅文化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从某些意义上来说,陈金芳对艺术的渴望实际上来源于她对另一个阶层的渴望。“陈金芳的贫苦出身从根本上便决定了她与音乐无缘, 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我’自小便被迫着在脖子上架上一把昂贵的小提琴,‘小提琴’——或者广言之——‘音乐’,在此处便有了阶层分化的象征意义”。①陈佳任:《石一枫小说中的音乐在场:以〈世间已无陈金芳〉为中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 年第4 期,第49-52、58 页。在陈金芳心中,艺术既不是一种高雅的乐趣,也不是生活的调剂品,而是只有更高阶层才配拥有的奢侈品。“我”这个业余小提琴手用悠扬的琴声向她展示了另一个阶层的生活,这对于陈金芳来说是一个难以触及的高度。对艺术的莫名迷恋严重影响了陈金芳的人生轨迹,青年时代的她为了一架钢琴花掉所有的货款,也因此与她当时的姘头决裂;后来,她更是将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押到艺术投资上,最终一败涂地,血本无归,精神追求随同物质追求一起湮灭。“在工业社会中,身份与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身份源于职业或专业。而在后工业社会中,身份越来越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①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23。正是因为出身让她难以接触到艺术活动,而进城之后的生活经历让她将艺术与体面的城市生活画上了等号,在这种身份认同困境的加持下,才造成了她对艺术的狂热追求。
三、展现进城青年身份认同困境的意义
(一)进城青年的迷茫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二元制度慢慢消解,人口的流动也越来越自由,由此涌现出一批进城务工人员。但是,随着进城农民人数的急速增长,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最开始进城的第一批农民或许吃到了时代红利,借助改革的东风得到了经济利益甚至改变了自己及后代命运。但是,城市的岗位需求和报酬是有限的,而进城农民的人数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进城农民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经济报酬也不断被削减,更多地与“廉价劳动力”画上了等号。进城农民特别是进城青年群体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迷茫。一方面,他们不像父辈对农村更有认同感;另一方面,农村留给他们的机会甚至比城市更少。许多进城青年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始终处于迷茫飘荡的状态,因此他们亟须社会认同。而进城青年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选择不外乎寥寥几种:第一种是像陈金芳的舅舅,彻底选择“农村”的身份回到家乡,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失去了“进城青年”的身份;第二种是像陈金芳一样,削尖了脑门往城市人的圈子里挤,希望自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第三种是像文中“安徽火车票贩子群体”,他们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而是在城市中建立了一个以地域、亲缘等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在此用“城中村”来称呼这个群体。“城中村”群体有极强的抱团意识,他们往往通过老乡的身份迅速聚集成团体,然后垄断当地某区域内某一行业,具有极强的排外性。这就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陈金芳为了成为“城里人”和痞子们混迹于灰色地带,后来参与诈骗活动。这种迷茫的心理状态不仅对他们自身有影响,还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社会阶级的固化
此外,阶级的固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人员的流动在当代已经相对自由,但是户口政策仍未完全放开。对于一些进城青年来说,他们很难得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户口,这样他们在医疗、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像文中陈金芳一样可以借读公立学校的机会也非常难得。随着阶级固化,进城青年越来越难以打破阶级的壁垒,而在信息越来越重要的当今时代,进城青年所能掌握的信息量却不容乐观,也许正是这种信息差才导致了“陈金芳们”的一败涂地。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和现实情况的转变,城乡文学也从对立渐渐转变为融合。进城的过程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于处于迷茫状态的进城青年来说,得不到城市的身份认同,就无法在精神上融入城市,始终是漂泊的外乡人。他们不被家乡接受,主观上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城市也不接纳他们,这种游离于群体之外又渴望认同的心情也会导致社会问题,比如文中陈金芳的不择手段和诈骗行为。展现进城青年身份认同的困境,不仅展示了进城青年的心理状态,还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性价值。新时期的进城青年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如何在文学中体现出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