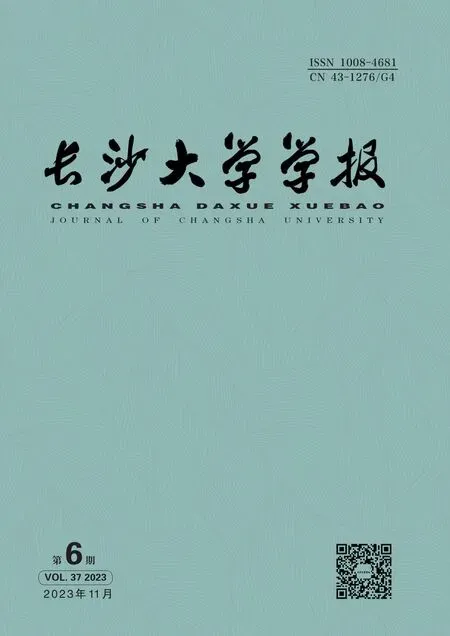缘起与意义:论雷蒙·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
2024-01-23张乾坤
张乾坤
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从二战后重返剑桥撰写第一篇有关易卜生研究的学位论文开始,雷蒙·威廉斯随后出版了《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1952)、《现代悲剧》(1964)、《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1968)、《政治与文学》(1979)等一系列含有易卜生批评的著作。从这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来看,易卜生是威廉斯长期以来最钟情的剧作家,也是他戏剧批评的首要对象与起点。威廉斯为何青睐易卜生批评?这一批评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略作探讨,旨在推动相关研究。
一 易卜生批评的缘起
易卜生是威廉斯早期戏剧批评视域中最为倚重的作家,《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给他“赢得了适当的学术尊重”[1]118。威廉斯如此重视易卜生研究,除了恩格斯、梅林、普列汉诺夫、卢卡奇等思想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向来重视易卜生批评之外,还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易卜生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作家
在威廉斯看来,易卜生戏剧具有足够的分量,值得投入精力。易卜生在他心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外在机缘是易卜生在英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的最早英译者威廉·阿切尔在论及易卜生戏剧的销量时说:“在过去的四年里,英语国家购买了10 万部易卜生的散文剧……在英语出版物中,这样的销售量绝对是空前的。”[2]213除了在书籍市场销售十分火爆之外,威廉·阿切尔还指出,易卜生戏剧“在英国舞台上大放异彩,颇受欢迎”[2]216。此外,易卜生还赢得了同行的高度肯定。另一位易卜生作品的英译者埃德蒙·葛斯提供了一个细节,颇有说服力。在易卜生70 岁寿宴当天,英国文化界的名流亨利·阿瑟·琼斯、托马斯·哈代、阿瑟·温·皮奈罗、萧伯纳等人前往挪威为其祝寿,“易卜生的天才得到英国人‘找上门来’赞赏”[2]115。由于易卜生在英国的巨大影响,威廉斯在中学阶段就已经阅读了其部分剧作,并逐渐认定其是“第一流的悲剧作家”。
(二)面临的两难处境与易卜生所传达的东西最为接近
对于威廉斯而言,易卜生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他所传达的东西最为接近我当时对身边环境的感受”[1]45。二战结束之后,威廉斯从军队复员重回剑桥,发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主要表现是周围的信仰更加多元,学生文化发生了改变,二战前真正意义上自觉的左派已经不复存在。这种环境的彻底变化不仅发生在剑桥大学,而且也发生在校园之外。1945 年大选,工党战胜保守党,威廉斯最初的反应非常积极,以为历史发生了性质上的突变,但事实并非如此。随后上台执政的艾德礼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威廉斯对工党的态度发生了转折。其一,艾德礼政府于1945 年末接受了美国贷款。在这一问题上,左派阵营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威廉斯始终激烈反对,他认为美国贷款以及随后的马歇尔计划,助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货币金融秩序,必然使工党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其二,1946 年至1947 年冬天,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工党政府为了维持能源生产秩序,对工人进行“规训”,反对工人罢工,甚至派出军队镇压工人罢工。透过这一系列镇压行为,威廉斯彻底看清了工党政府的反动面目。其三是工党政府出台的国有化政策与文化政策。作为一名工党成员,威廉斯的父亲在过去一直期待着铁路国有化,然而在国有化政策落地半年之后,他的父亲非常不满,“激烈地反对新体系的官僚性”。就威廉斯的亲身经历来说,他准备与他人合作拍摄一系列表现农业与工业革命的历史纪录片,但政府文化机构“拒绝资助电影纪录片”。针对工党采取“资本主义优先的做法”,即用资本主义话语重建文化领域,拒绝资助大众教育机构与文化机构,威廉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工党在20 世纪50 年代迅速落败的关键因素是在文化上没有资助工人阶级运动。针对战后工党的种种拙劣表现,威廉斯对艾德礼政府上台执政的态度从最初“非常热情”转变为“非常冷淡”,甚至极为不满,以至于直言“打算做工党中的‘左派’”[1]48。
威廉斯不仅不满意战后工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不支持战后英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欧洲范围内快速膨胀,尤其是在《慕尼黑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灾难性国际事件之后,战争的乌云已经在欧洲上空密布。在此背景下,英国国内左翼政治力量搁置了分歧,短暂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组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的孕育与壮大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发挥了引领作用。在论及人民阵线对威廉斯的影响时,德沃金指出:“他是人民阵线的产物。”[3]120从威廉斯早年的经历来看,德沃金的这一判断是有客观依据的。1937 年,威廉斯加入了阿伯加文尼的“左派图书俱乐部”。“与工党相比,‘左派图书俱乐部’的背景与共产党更为接近,其政治文化平台是人民阵线。”[1]141939年11 月,威廉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同年12 月正式加入英国共产党。他利用自身写作方面的特长,在所属的作家小组积极为党组织“赶写宣传资料”。由于以英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政治力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当时的社会主义俱乐部成为“所有校园‘左派’的大联合”,甚至左派学生以“一个非常宽容的阵线”为基础,成功地组织了起来。“在社会主义俱乐部里面,共产党广义的反法西斯团结路线几乎已得到一致支持。其中只有一位重要成员,三一堂学院的塞缪尔·西尔金,支持工党官方立场。他于是成为宝贵的例证,用于彰显社会主义俱乐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4]140威廉斯曾表示:“如果说‘左派’的自信文化曾经衰减过的话,我在1939 年夏天之前并没有观察到,我所能说的是,当我面对它的时候,它是非常强大而又自信的。”[1]25然而,战争的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1941 年6 月,德国入侵苏联,由于“非常清楚战争的政治性质变了”,威廉斯于当年7 月应征入伍,随即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履行党员义务,于是脱离了组织。二战结束后,威廉斯不赞同英国无产阶级政党无视自身实际、亦步亦趋地跟随苏联的步伐。正如德沃金所说:“他认同党的激进主义,但他因为党服从于苏联而感到困扰,并认为这种服从是对战后英国现实的置之不理。”[3]120此外,威廉斯还质疑英国共产党对待工人罢工的态度。由于与战后英国共产党在政治立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威廉斯明确表示不再加入该组织,甚至以“没有来由的自信”表示“自己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宣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见,由于战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彻底变化,“威廉斯发现自己夹在工党与共产主义同事的包含着阴谋和政治迫害的残酷争论之间”[3]120。夹在两极之间的威廉斯从未将自己划归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派别,成为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政治异端分子”。此时威廉斯面临的两难处境与易卜生戏剧“所传达的东西”最接近。在威廉斯看来,易卜生戏剧的内容框架是“个人冲动与绝对障碍之间的张力”[5]79。个人冲动是自发的,也是合理的,绝对障碍是邪恶的,也是无法逾越的,两者冲突的结果是一场无解的僵局。易卜生戏剧的创造性贡献在于对这一僵局进行了多次的诗意呈现。二战后,威廉斯一方面坚信自己选择的立场是正确的,并为之努力,另一方面在根本意义上又无力改变工党政府与英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可以说,威廉斯面临的僵局与易卜生戏剧表现的僵局是高度同构的。
“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6]141,情感结构既是个人的,又具有“新兴性、联结性和主导性等特征”[6]142,是“共同体中的很多人所拥有的”,“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7]57。一个时代的艺术在表达情感结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易卜生戏剧表现的僵局不是一种凝固的沉淀物,而是“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7]57。它不仅是易卜生个人的,也是包括威廉斯在内的“很多人所拥有的”,具有“联结性”以及“沟通和传播”的潜能。二战后的威廉斯“对身边环境的感受”激活了他早年阅读易卜生戏剧的经验,并成功地将一系列文本转换成研究的有机客体。
(三)重建以《政治与文学》杂志为联系网络的共同体遭受挫折
作为“左派利维斯者的杂志”,《政治与文学》尝试将激进的左派政治和利维斯主义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并以此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它标志着威廉斯在二战后夹缝中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开始。作为“一份观点开放的评论刊物”,《政治与文学》的开放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论文章的观点不要求一致,甚至采用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因此,刊物在形式上呈现“对立与矛盾的外貌”。这与当时的《细察》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刊物面向几乎所有的撰稿人,不仅向乔治·奥威尔等人约稿,还向《细察》团队约稿,这与《细察》局限于内部小圈子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政治与文学》在观点上保持开放与包容,但“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好斗”。《政治与文学》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仅仅出版了4 期,由于资金匮乏和编辑之间的矛盾而被迫停刊。它的停刊给威廉斯的打击是很大的,产生的影响长达十年。他说:“这份刊物的失败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危机……这种经验强化了我曾经在易卜生作品中发现的感受模式。”[1]61也就是说,《政治与文学》的失败引发了威廉斯的“个人危机”,与他“曾经在易卜生作品中发现的感受模式”产生了现实的回响。
1979 年,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威廉斯念念不忘自己在20 世纪30 年代“把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行为和普遍的政治斗争融合在一起”[1]45的立场,反复深情地缅怀红色剑桥。国内有研究者指出:“人民阵线所代表的那段艰难但却饱含希望的历史在众多参与者和经历者的心头都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中就包括了许多后来第一代新左翼的代表人物,如汤普森和威廉斯,也包括与他们过从甚密的霍布斯鲍姆等人。”[8]威廉斯等人联手创办《政治与文学》杂志,尝试以评论刊物为纽带构建“联系网络”,“希望读者群能够从共产党员扩展到受利维斯影响的那些人”[1]52。威廉斯说:“我们把刊物看做是某种非常令人鼓舞的联系网络形式,它把工人阶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联系在一起。”[1]521959 年,威廉斯加入了《新左派评论》编委会,与爱德华·汤普森等人设法重新建立联盟。威廉斯回忆说:“我不认为你能理解1950 年代(20 世纪50 年代)晚期新‘左派’的方案,除非你认识到,像爱德华·汤普森和我这样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大家当时都在设法重新建立那种联盟。联盟在那个时期也许不再可得,但是在我们看来,即使联盟难以实现,我们的观点也是合理的。无论如何,那就是《政治与文学》出现的背景。”[1]57-58从历史脉络来看,《政治与文学》这一“联系网络”形式实际上与《新左派评论》这一“联盟”形式相似,它是20 世纪30 年代晚期人民阵线的“大联合”在战后的延续。从人民阵线的“大联合”到《政治与文学》的“联系网络”再到《新左派评论》的 “联盟”,可以看出,以威廉斯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力量致力于构建共同体的努力。
《政治与文学》的停刊不仅是一份杂志运作的失败,也是威廉斯等人努力重建共同体遭受的重大挫折,还是战后左翼激进力量遭遇的重大挫折。但威廉斯未曾放弃,他始终坚信自己冲动的合法性。他认为,自己的处境与易卜生戏剧表达的主题相似。威廉斯认为,易卜生戏剧的写作重心不是萧伯纳等人强调的个人解放,而是个人冲动导致的挫折。屡遭挫折不是对个人冲动的否定,而是对邪恶的否定。易卜生戏剧一次又一次创造性地表现了“挫折的经验并不减损斗争的价值”[1]45这一情感结构。威廉斯在易卜生戏剧中找到了情感知音,并与之产生了持久共鸣。他说:“易卜生的作品反映了我早期的处境,它们保护我不至于从1930 年代(20 世纪30 年代)的立场迅速退却。”[1]45如果没有易卜生戏剧反复表达的“挫折并没有使它丧失合法性”对威廉斯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很有可能像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那样激情“迅速退却”,甚至认为“过去的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1]45,从而丧失了构建共同体的信心,消弭了左翼激进力量的斗志。
二 易卜生批评的意义
易卜生批评是威廉斯戏剧批评与学术研究的最初起点,也是其思想形成的萌发之地,影响深远。威廉斯主要从戏剧形式与主题意蕴两个角度切入,前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易卜生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自然主义戏剧形式再现人类的具体经验,后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易卜生戏剧表达的自由主义悲剧内涵及其实质。从英语文学研究的历史与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来看,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十分重要,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威廉斯首次以易卜生戏剧文本为研究对象,拓宽了实用批评的适用范围,检验了它的有效性,推动了英国文学研究。在20 世纪50 年代之前,除了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的莎士比亚批评之外,戏剧几乎被排斥在实用批评的对象之外。威廉斯的开拓性贡献在于首次将实用批评方法尝试性地运用于19 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戏剧作品,尤其是易卜生的戏剧,这在当时可谓史无前例,开了风气之先。威廉斯自称他的易卜生批评是探索性质的,但取得了成功,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学术声誉。这表明,将实用批评运用于包括易卜生等人在内的戏剧批评,不仅在方法上切实可行,而且在对象上也具有可行性。
威廉斯将实用批评方法运用于戏剧批评,不仅是一种跨越体裁的尝试,还辨明与确证了戏剧的文学身份。在威廉斯之前,实用批评局限于诗歌、小说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批评界对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戏剧充满着误解与偏见。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戏剧商业化步伐的加快导致戏剧与文学分裂。批评界普遍认为,戏剧与文学是两回事,戏剧是一种“实用艺术”,“是一种与文学截然不同的东西”[9]12;文学是一种创造性艺术,没有实用性。因此,戏剧批评的方法与理念不适用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方法与理念也不适用于戏剧批评。威廉斯致力于弥合戏剧与文学之间的裂痕。他不仅从性格和行动两个角度论证了戏剧的文学性,还冲破阻力、打破惯例,将诗歌和小说领域惯用的实用批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易卜生等人的戏剧批评,用实际行动回击文学领域的批评方法不适用于戏剧领域的谬论。
第二,威廉斯首次实现了个人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为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孕育之地。细读相关文本不难发现,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运用实用批评方法解读易卜生戏剧的悲剧意蕴。瑞恰兹、利维斯等人认为,实用批评是反意识形态的。威廉斯改造了这一批评方法,首次将实用批评与意识形态进行结合。通过对易卜生戏剧文本的解读,威廉斯深刻揭示了易卜生戏剧的自由主义悲剧性质。对易卜生在戏剧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诸种障碍的创造性再现,威廉斯不仅没有批判易卜生,反而给予其积极评价。但他也指出,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实质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是一种内在抗议。此外,威廉斯认为,自由主义悲剧框架是一个僵局。这是因为,易卜生强调个人抗争而不是集体抗争,不可能获得突破,也没有前途。威廉斯强调,面对自由主义悲剧的僵局,唯有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才能否定悲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由此可见,威廉斯通过易卜生戏剧文本的解读,批判了个体反抗,最终指向否定无序社会的集体革命行动,巧妙地契合了他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威廉斯运用实用批评方法解读易卜生戏剧文本中的形式问题。威廉斯一贯重视戏剧形式问题的研究,但他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立足文本,着眼于形式传达的具体经验问题。从戏剧批评实践来看,威廉斯非常重视易卜生运用戏剧语言与手法将具体经验有效传达给读者或观众的问题。这一问题视域与早期威廉斯非常重视戏剧、小说、电影、电视等文化形式在作者与读者或观众之间的交流问题是高度吻合的,内在指向个体与社会分裂时代共同文化的建构。可以说,威廉斯聚焦易卜生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戏剧形式传达具体经验的问题,强调作者与读者或观众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他毕生从事文化研究,并努力促成共同体形成的目标是一致的。
三 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的缘起较为复杂,易卜生戏剧被英国读者与观众广泛接受是其外在机缘与文化语境。易卜生戏剧传达的个人冲动对抗绝对障碍后反复遭遇挫折、反复陷入僵局的情感结构契合与激活了战后威廉斯的深层感受,这是他选择从事易卜生批评的内在动力。此外,易卜生戏剧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机制提出严肃的抗议,也客观地迎合了威廉斯的革命诉求。以上这些因素纵横交错与共生互动,共同促成了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凭借易卜生批评,威廉斯不仅汲取了正视挫折的力量,还消除了业内对易卜生作品解读的误解与诋毁,在学术重估之中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声誉。反过来说,易卜生戏剧也借助威廉斯的批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将威廉斯的易卜生批评置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与易卜生批评史之中进行检视,它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威廉斯强调回归文本,坚持从文本语言出发,其易卜生批评纠正了长期以来庸俗的社会历史批评重内容轻形式的做法,助推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性别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诸多易卜生批评先在范式中,威廉斯借鉴与改造实用批评模式,首次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易卜生批评中,丰富了易卜生批评,拓宽了实用批评的适用范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活力与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