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2024-01-22曾枣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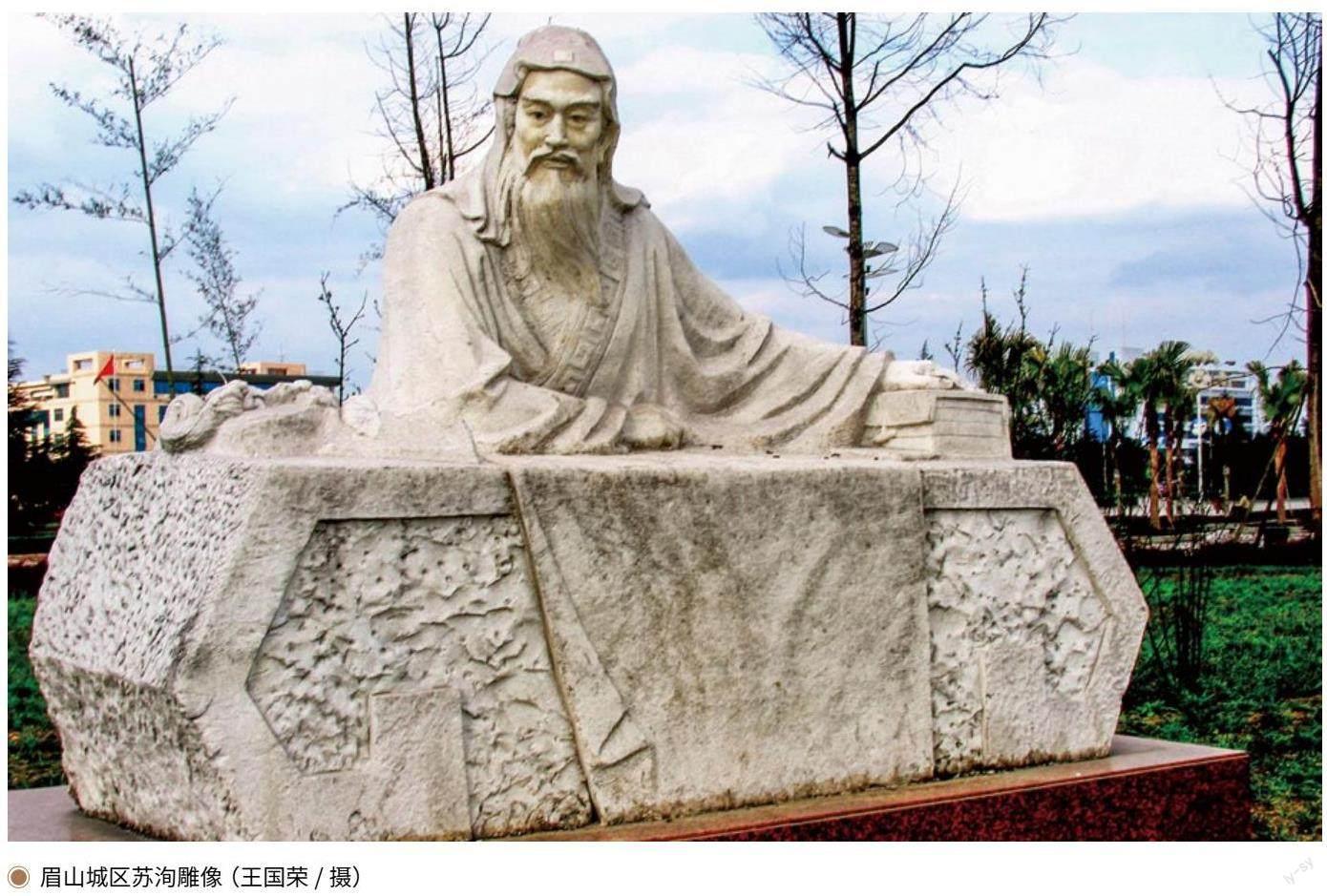


苏洵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力主革新的政论家、“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培养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更是一个“得史迁笔”的史学家、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博辩宏伟”的散文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继韩(愈)欧(阳修),下开苏轼兄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得史迁笔”的史学家
苏洵在“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的期间,除撰成《衡论》《权书》等政治、军事著述外,还写了《史论》上中下三篇。晚年任试校书郎后,主要与姚辟合撰《太常因革礼》100 卷。这既是一部礼书,又是一部史书。
《史论上》论经、史之异同。认为其同有二:其义(写作目的)同,“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用(作文的具体要求)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其别有三:经、史都离不开事、词、道、法,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靠史证实其褒贬,史靠经斟酌其轻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为用;经为“适于教”的需要,或从“伪赴(讣)”,或“隐讳而不书”,故经非实录;史是“实录”,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传统观点是把经奉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苏洵却经史并重,认为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在《史论中》中甚至说“史虽以事、词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认为史兼经之长。
《史论中》提出了修史的四种方法。“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主张把史书的真实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统一起来。
《史论下》为著名史籍点评。专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之失,主张治史需成“一家”之言,反对因袭剽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称其“评骘诸家如酷吏断狱”。
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
苏洵的文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与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是合拍的,他是北宋古文革新的有力推动者。他的文论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把他这些散见的观点集中起来,仍是相当系统、相当深刻的。
反对时文,不肯“区区符合有司之尺度”。真宗朝和仁宗朝曾多次明诏天下,申戒浮文,但是,余风未灭,新弊复作,很多人的文章求深务奇,写得怪僻而不可读。苏洵经常指责那些“浅狭可笑”“虚浮不实”“好奇而务深”的文章,就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的。
苏洵的多次应试“不中”,除因他“少不喜学”外,还可能与他“博辩宏伟”的文风,不符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浮艳怪涩的文章为美的那些考官的胃口有关。而苏洵父子的“不学时文”,正符合欧阳修古文革新的要求,因此得到他的特别赏识。
学习古文。苏洵“陋今而高古”(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他既不满时文,就转而深入研究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他在《上田枢密书》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历评先秦的《诗经》《离骚》《孙子兵法》《吴子》《孟子》,两汉贾谊、董仲舒、晁错、司马迁、班固的文章,唐代韩愈、陆贽、李翱的文章以及本朝欧阳修的文章。从其归纳之准确,评价之公允,可看出他用功之深。他虽然“高古”,但并不迷信古人;很强调各家的独特风格,强调“自为一家之文”。
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反对因袭前人。他在《太玄论上》中说:“言无有善恶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词不索而获。”历代正统文人都把宣扬孔孟之道作为评价文章好坏的最高标准,苏洵却把“得乎吾心”,即文章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作为论文的首要标准。
根据这一标准,他称赞了孔子著述,认为《易经》系辞是经过深思而写出的,因此写得很深邃;《春秋》是有感于历史而写的,因此写得很剀切;《论语》是在接触现实过程中的言行记录,因此讲得很平易。“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也。书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圣人以为自欺。”写在书中的就是口头所讲的,口头所讲的就是心中所想的,如果所说所写不是所想的,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根据同一标准,苏洵批评扬雄的文章说:“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其言而为书,吾于扬雄见之矣。”他说扬雄的《法言》是“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即无话找话说;指责扬雄的《太玄》是“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即因袭孔子而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没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无论苏洵对扬雄的批评是否完全合理,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则是完全正确的。
强调文章内容要符合客观实际。朝廷命他修纂《礼书》,有人认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苏洵反驳说,他修的《礼书》属史书性质,“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书体也”。因此他反对“掩恶讳过”(《议修礼书状》),书其善而不书其不善的做法。
有人托他为其父作碑铭,并向他提供了行状。苏洵说他既“不获知子之先君”,而据以作铭的行状“又不可信”,“行状之所云,皆虚浮不实之事”。苏洵虽然“惜其先君无站于后”而勉强作铭,但却坚持“不取于行状”(《与扬推节书》)。
作墓志碑铭往往有这样的矛盾,请托者希望以一些“虚浮不实”之词使其亲人永垂不朽,而稍微严肃的作者很难满足请托者的所有要求。苏轼也正是有鉴于此,才“平生不为行状墓碑”的(《陈公弼传》)。
反对为文而文,强调文贵自然。苏洵说他的《权书》是“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权书叙》)。所谓“不得已而言”,就是指心中有很多话非说不可,不吐不快;而不是为文而文,无话找话说。
他在描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读书“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也”(《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欧阳修在论述苏洵的写作经验时也说:“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文,以考質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笼统强调“闭户读书”,当然是不对的。苏洵的“闭户读书”对其创作产生了奇效,是因为他从小喜欢游历,去过不少名山大川,又结交了一些有志之士,已有比较丰富的阅历。在此基础上,针对自己的少不喜学,辅之以苦读,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读书也不一定非要“绝笔”不可,一面读书,一面练笔,往往更有效。但这里强调的基本观点是,不要没有什么心得就敷衍成文,而是要“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时,才能写出好文章。好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涌出来的。
苏洵的《仲史字文甫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贵自然的思想。他以风水相激而然成文作喻说:“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相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苏洵还以这样的思想教育苏轼兄弟。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风水相激而成文,山川之云,草木之花实,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非有意为之,故具有自然美。文章也是这样,为文而文是不会有好文章的,要不能不为之文,不能自已之作,才是好文章。“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是苏洵父子共同遵守的重要的写作原则。
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
他说:“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太玄论上》)读书人写文章像工人做器具一样,要有用。
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记载了苏洵一段精彩的文论:“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苏洵反对慕远忽近,贵华贱实,反对以游谈为高,以枝词为观美;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主张文章应像谷可疗饥,药可治病那样解决实际问题。
苏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著书是以“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为着眼点的。欧阳修称赞他的文章“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文”(《荐布衣苏洵状》);雷简夫称赞他的文章“讥时之弊”“惶惶有忧天下心”(邵博《闻见后录》),这都说明他的文章都是“有为而作”的。
苏洵之所以能提出对当时来说可算比较进步的古文革新主张,这首先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到了宋代中叶,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革新政治的呼声已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要求以散文为武器来反映社会现实,为革新朝政服务。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就提出了“敦谕词臣,复兴古道”的要求。同时,也与西蜀的文化传统有关。在晚唐五代,西蜀在词上受浮艳文风的影响较大,《花间》词派出于西蜀就是突出的表现。但在散文方面,正如苏轼所说:“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西蜀士人比较重视西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苏洵本人性格豪迈,不愿受“章句、名数、声律之学”的束缚,他长期沉沦在下层而又注目时局,他的特殊经历也是他能够提出比较进步的文论主张的重要原因。
“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
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韩琦)席间赋诗,明允有‘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如《读易》诗(应为《送蜀僧去尘》)云:‘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这段话颇重要,指出了苏洵诗的特点:在数量上,“明允诗不多见”;从内容上看,“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从风格上看,“婉而不迫,哀而不伤”。
苏洵作诗不多。今存多数版本的苏洵集存诗仅27 首;加上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多出20 首及其他一些佚诗,共存诗50首。在这50 首诗中,以古体诗,特别是五言古诗为多,四言5 首,五言古诗20 首,七言古诗8 首,共35 首。近体以七律为多,也有七绝、五律、五绝,但较少。可见,苏洵虽作诗不多,但却诸体皆备,而且各体都写得不错。
四言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形式。其后,作四言诗的人不多,仅曹操、嵇康、陶潜作过一些好的四言诗。唐宋作四言诗的人更少,而苏洵所存的四言诗占其诗歌总数十分之一。《诗经》的四言诗常以首句名篇,苏洵的5 首四言诗也都以首句名篇。
“四言简直”(胡应麟《诗薮》),苏洵的四言诗也具有古朴简直的特点。如《有触者犊》。
大意是说,牛天生有角,有角必然有触;既然恶牛之角,何不“索之笠”?如前所述,韩琦、富弼对苏洵比较激进的革新主张不感兴趣,对其尖锐的批评更不喜欢,《有触者犊》一诗,正反映了当局者对其触角之厌恶,以及他对当局者的愤愤不平。诗中多用反诘句,简劲有力,强烈地表现了苏洵坚持其主张的精神。
苏洵诗以古体写得最多最好。时人多推崇他的古诗,《答陈公美》诗有“新句辱先赠,古诗许见推”句,可见陈公美就很推崇他的古诗。
古诗中又以五言古诗突出,如《欧阳永叔白兔》诗,是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与欧阳修交游时写的。前8 句写白兔被擒和笼养的经过:“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禽兽乱衰草”的“乱”字,活画出了在“飞鹰”搏击下,飞禽走兽拼命奔逃的景象;“颠倒”二字写出了禽兽被擒被杀的痛苦挣扎之状。在这种背景下,白兔未被杀而被笼养起来,当然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被长期拘留,野性被矫正得来驯顺可抱,对白兔来说也是可悲的。中间6 句云:“贵人织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動槁叶,群窜迹如扫。”此写白兔的本性,好山林穴处,成群奔窜,在平野上形成一片白色。现在身处贵人筠笼,这一切都不可得了。最后4 句借猎夫之口,笑白兔不自匿而被长拘,没有月中白兔骑着蟾蜍捣药自由:“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于手自捣。”“异质不自藏”“自匿苦不早”,就是全诗主题。全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算得一篇佳作。
苏洵的七言古诗也写得不错,如《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记)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就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可分三层,第一层写他想迁离四川:“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在这里,苏洵一方面肯定了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又指出四川山水局促,四周险要,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难以有为。第二层写他看中了嵩洛之地,这里平原辽阔,嵩岳秀丽,人才济济:“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缓无夭扎,衣冠堂堂伟丈夫。吾今隐居未有所,更后十载不可无。”最后一层盛赞陈景回弃官移居上蔡,表示自己也决心移居嵩洛:“闻君厌蜀乐上蔡,占地百顷无边隅。草深野阔足狐兔,水种陆取身不劬。谁知李斯顾秦宠,不获牵犬追黄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当吾庐。”李斯(?—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入秦,佐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官至丞相。秦二世时被赵高所谗杀,临死时感叹欲牵黄犬,逐狐兔于上蔡东门而不可得。上蔡人李斯贪恋官禄而不得重返上蔡与蜀人陈景回弃官归隐上蔡,构成鲜明对比,而以“行看嵩少当吾庐”作结,对陈景回的仰慕之情溢于言外。全诗曲折多姿,方说西蜀民殷物阜,又说“厌倦思移居”;方说嵩山之可爱,又说陈景回的“厌蜀”;方说陈景回“乐上蔡”,又说李斯的后悔之词。全诗波澜起伏,若断若续,活泼跳荡,情致委折。
在近体诗中,苏洵以七律作得最多,其中以《九日和韩魏公》最有名。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的重阳节,苏洵参加了韩琦的家宴,回来后写了这首诗:“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诗的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礼院编纂,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七八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潇潇,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全诗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苏洵诗不仅诸体粗备,而且题材丰富。有论书法的诗,如《颜书》;有题画诗如《水官诗》;有记游诗,如《忆山送人》;有抒怀诗,如《答二任》。从风格上看,苏洵的诗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意气风发,豪情满怀。“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欧阳永叔白兔》)——充满了雄鹰搏击的气氛;“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少年苏洵云游天下的豪迈之情跃然纸上;“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颜书》)——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而他的《上田待制诗》,更表现了击败西夏侵扰的必胜信念。即使在他极不得意时,也能写出“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这类豪情难抑的名句,“意气尤不少衰”。
另一类作品以含蓄蕴借为特征。如《老翁井》:“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团水生花。翁今与世两何与,无事纷纷惊牧竖。改颜易服与世同,勿使世人知有翁。”这首诗描述了老翁井的传说,有位“苍颜白发”的老翁以泉为家,来无踪,去无迹,与世无争。此诗可能与《老翁井铭》作于同时,即作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时苏洵葬妻于老翁井上,因自己入京求仁不遂,也有老于泉旁之念。“改颜易服与世同,勿使世人知有翁”,和光同尘,不求有闻于世,正反映了他当时的抑郁心情。但表达得比较含蓄,正如朱熹所谓“其意怨而不怒,用意亦矣”(《晦庵诗话》)。
“博辩宏伟”的散文家
盛赞苏洵的欧阳修认为:他的文章具有荀子的文风(“目为孙卿子”)。对苏洵“独不嘉之”并“屡诋于众”(叶梦得《避暑录话》)的王安石则说:“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博《闻见后录》)苏洵也公开承认自己对纵横家的爱好。战国纵横家朝秦暮楚,没有自己的固定主张,苏洵是不赞成的;但他很欣赏他们因势利导的雄辩之术。他说:“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谏论上》)
后世也几乎公认苏洵散文深受战国诸子,特别是纵横家的影响。茅坤说:“苏文公崛起蜀徼,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唐宋八大家文钞》)
战国散文,包括纵横家的说辞,往往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纵横恣肆,酣畅淋漓,滔滔不绝,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苏洵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欧阳修说苏洵的文章“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说他的文章“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苏明允哀词》);张方平说他的文章“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文安先生墓表》),都是指的这一特点。
他的《项籍论》劈头就写道:“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而无成焉。”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要论证“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认为项籍没有直捣咸阳为失策,但却以曹操、刘备作衬托,一开头就造成强大的声势。接着根据“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的作战原则,指出项羽不乘胜直捣咸阳,“而区区与秦将(章邯)争一旦之命”,使刘邦先入关中,这就决定了“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百战百胜尚何益哉”。以上是讲项羽直捣咸阳的必要性,有无这种可能性呢?项羽“必能入秦”吗?苏洵又从章邯轻敌,亡秦守关不如刘邦守关,刘邦攻关不如项羽攻关等三个方面作了肯定的回答。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苏洵以虎方捕鹿,罴搏虎子,虎必回救的比喻和围魏救赵的战例,证明直捣咸阳,必能解赵之围。文章通过层层深入分析,已充分证明没有直捣咸阳之失策,文章至此本可结束,但苏洵突然妙筆生花,提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的问题,从侧面再次证明项羽没有直捣咸阳之失策,作者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分析问题,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句,造成磅礴的雄辩气势,读之令人折服。
苏洵的多数文章都具有这一特点,如他的《六经论》,尽管正统文人不赞成其观点,说它是“不根之谈”;但也不得不承认它“行文雄放,有俯仰一世之概”“出入起伏,纵横如志,甚雄而畅”“风驰雨骤,极挥斥之致”(《古文辞类纂》)。苏洵的文章还以委婉曲折见长。《与欧阳内翰第一书》《送石昌言使北引》《上张侍郎(方平)第二书》都足以说明这点。
《送石昌言使北引》是一篇仅400 来字的短文。文章的前一部分写他同石昌言的关系:苏洵儿时为戏,昌言以枣栗给他吃,两家相近,加之又是亲戚,故“甚狎”;后苏洵读书,未成而废,昌言闻之,“甚恨”;10 余年后,苏洵“摧折复学”,昌言又“甚喜”。甚狎、甚恨、甚喜六字,不仅使文章脉络清楚,而且使文章波澜起伏、曲折多姿。文章后一部分才写送石昌言使北,苏洵先发感慨:“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接着写往年出使的人,一见敌方炫耀武力,往往“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接着写敌人不足惧,因为词卑者攻,词强者退,敌方如此耀武扬威,“吾知其无能为也”。最后引孟子关于“说大人而藐之”(对大人物说话应藐视他),以“况于夷狄”四字作结,表面看,苏洵似乎没有一句直接规讽石昌言的话,但实际上作者希望石昌言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折冲口舌之间,敢于藐视敌人,以夺取外交上的胜利。行文婉转曲折,意在言外,言者并未伤人,闻者足为鉴戒。苏洵称赞孟子:“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这篇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
其文往往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其《谏论》下篇,为了说明需要“立赏以劝之”,“制刑以威之”来“使臣必谏”,作了如下的比喻:“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 前两条用以比喻赏(一是精神方面的嘉奖,一是物质方面的奖赏)对“使人必谏”的作用;后一条用以比喻罚(虎要吃人)对“使人必谏”的作用。这种生动的比喻,比说一大堆空道理有说服力得多。
类似的比喻在苏洵散文中比比皆是。如以“酒有鸩,肉有堇(均有剧毒),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医活将死的人),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来比喻礼虽烦但可使人与人免于残杀(《易论》);以“若水之走下”,来比喻“民之苦劳而乐逸”(《易论》);以“欲移江河而行之山”,来比喻风俗之不可复返(《书论》);以“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六国论》),来比喻不可赂秦。
苏洵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练,而内涵丰富,能给人以回味的余地。苏洵用貂裘从一溪叟那里换来木山三峰,置于堂前,并写了《木假山记》。这是一篇借物寓慨之作,抒发了他郁郁不得志而又不愿与世浮沉,力图自立的感情。他说,树木所经历了种种不幸遭遇,或夭殇,或砍伐,或漂没,或破折,或腐滥,在“激射齧食之余”,作为木假山而留于人间,很不容易。人生经历了无数的升降浮沉,得留名于青史,那就更不容易了。
很显然,这里也包含了他求仕不遂的隐痛,是苏洵对自己的写照。他本是“田野匹夫,名姓不登于州闾”;虽曾“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辄以摈落”(《上皇帝书》);他虽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但如果没有欧阳修等人的荐拔,也很难名闻于朝廷。木假山能不能为“好事者取去”而供于堂上,一个人能不能出头而名留青史,确实有很多偶然因素。“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苏洵这些话是充满感慨的。文章后一部分讲到他家所蓄的木假山三峰:“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有人说苏洵在以中峰喻己,而以二峰喻其二子。这未必符合苏洵的原意。看来苏洵主要在以三峰的峭拔象征一种巍然自立,而不与世浮沉(所谓“无阿附意”)的精神,即“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的精神。
苏洵之所以被时人看重也正是他这种“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精神。欧阳修喜欢荐拔人才,当然是苏洵得以名震京师的重要原因。但首先也要苏洵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欧阳修才可能推荐他,苏洵的名震京师并非偶然。苏洵说,木假山三峰得以置于他家堂上,“其理似不偶然也”。可见,苏洵虽然对沦落者“何可胜数”深有感慨,但他却并不屈从这种命运。
苏轼兄弟在后来的政治斗争风浪中屡遭打击,也始终“无阿附意”,继承了苏洵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木假山三峰的峭拔挺立,意气端重,正是苏洵父子三人的象征。
苏洵的《名二子说》也是语言凝冻而内涵丰富的代表作。“轼”是用作车上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一生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既无车之功,但也无翻车之祸,因此说处于“祸福之间”。苏辙一生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当时激烈的党争中虽遭贬斥而终能脱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这篇仅80 余字的短文,说明了苏轼兄弟命名轼、辙的原因,表现了苏轼兄弟的不同性格以及苏洵对二子的提醒和希望。这篇短文确实言简意赅,在极其精练的文字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在《嘉祐集》中,既有相互联贯的成组论文,如《权书》《衡论》均多达10 篇;又有洋洋洒洒,长达四五千言的大块文章,如《上皇帝书》。曾巩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词》)。这可算是对苏洵散文的定评。
(节选自曾枣庄《苏洵的历史贡献》,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