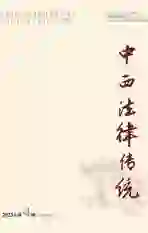儒家道统与礼法秩序
2024-01-22伍卓航
伍卓航
摘 要|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神宗试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礼法之上,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坚决反对,双方僵持数十年,最终以神宗的妥协让步落下帷幕。通过这次争斗,文官集团将礼法的话语权与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关乎皇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控了朝局。文官集团坚决争斗的背后,反映的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与限制皇权的强烈愿望,而他们的最终胜利,也意味着道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政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道统本身其实存在着自我崩解的内在张力,异变出文官所具有的阴阳两面的“怪象”,与之伴生的,是万历“两个身体”的裂变。
关键词|国本之争;儒家道统;礼法秩序;文官集团
公元1586年,是为万历十四年。这一年,是张居正抱憾离去,留下一个“后继无人”的改革大业后的第四年;这一年,本无大事发生,但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却不容忽视,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末端小节,实质上正是明帝国走向分崩离析的症结,也是在日后将要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1]
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这对于一个已受数千年宗法制度影响的国家来说,本无关宏旨,无非是又多了一个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给民众盘剥层层加码的王爷。不过,这是立足于当下的视角来回看历史,倘若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么过早地下定论,难免有失公允,至少在神宗朱翊钧看来恰是如此:他不甘心让朱常洵日后只能做一个王爺,这一点从神宗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准备大加庆贺,特地传谕户部:‘朕生子喜庆,宫中有赏赉,内库缺乏,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1]而驱使着这一切的原始冲动也十分简单:因为爱情。
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十六岁,在母亲李太后的主持以及司礼监太监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张罗下,进行大婚,立了一位王姓姑娘为皇后[2]。皇后王氏秉性端谨,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李太后),颇得其欢心。但由于皇后多年没有身孕,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因无子嗣,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向皇帝建言,不如参照嘉靖九年选九嫔事例,上请皇太后恩准。[3]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一天,皇帝住慈宁宫探望母后,索水洗手,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皇帝见了甚为欢悦,于是就有了所谓“私幸”[4]。后来,宫女王氏有了身孕,但他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私幸了宫女。文书房的宦官记载了这件事情(《内起居注》),直到太后发现王宫女怀孕,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在太后的干预下,皇帝在万历十年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册封两个月之后,恭妃王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皇长子朱常洛。[5]
后来的事实证明,万历对这名宫女根本就没有感情,更谈不上喜欢。也许那时的万历还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郑贵妃。仅凭姿色,她是不会成为万历一生的挚爱。她与万历情投意合,是可以一起阅读作品、讨论人生、有着诸多共同语言无话不说的红颜知己,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她看透了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可以说,只有她是唯一一个把皇帝当作“人”来看的女人。[6]
现在可以回答前述的问题,为何皇三子的降生会让万历如此高兴。在中国古代社会,“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郑贵妃与皇三子朱常洵,正是这一相辅相成的紧密共同体。皇长子朱常洛无疑是不幸的,连同她的母亲。他的降生,不过是其父临时起意、任性所为的偶然。但朱翊钧毕竟是皇帝,历史的选择不容许个人的任性凌驾于其之上,他终将要搭上整个帝国的命运,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当然,彼时的万历并不会看得那么长远,对于他来说,他爱的是郑贵妃,此刻的他,似乎并没有留意到这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背后即将要牵扯出的政治角力早已暗流涌动。他只知道日后立朱常洛为太子以及立王氏为后,实乃迫不得已。没有情投意合,只有接踵而至的繁文缛节,一个又一个的束缚与牢笼。他贵为天子,足以号令天下,此刻却深感无能为力。压在他心头的,是母亲的训斥,是祖训的箴言。也许在他看来,这只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宗法桎梏,也许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单纯凭着年轻时的叛逆与血性,要挣脱无形的枷锁。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冲破桎梏,挑战秩序,斗争到底。这一争,就是数十年。
一、“国本之争”与万历朝局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继承人选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安危、政权的存亡,是国家稳定、延续的根本,故继承人被称为“国本”[1]。明太祖朱元璋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元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是皇位继承混乱,元朝仍然保留着草原部落首领推选继承人的传统,这不可避免地带来纷争与流血,朱元璋恢复了嫡长子继承制[2]。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册封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宣布“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3]“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4],确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嗣原则。其通俗的理解即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称为嫡长子,是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嫡长子早年去世,有嫡孙的则立嫡孙,无嫡孙的,再由嫡次子顺位继承,如皇后没有儿子,则册立庶出的皇长子为太子[5]。为了解决皇帝无子时帝位的继承问题,朱元璋在其亲制的《皇明祖训》中又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6]《皇明祖训》作为朱氏皇族训谕,在历任皇帝在位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遵循,尤其是明前期诸帝,大多重视祖训条规,皇帝常依祖训处理事务[7]。
如前所述,明神宗无嫡子,宫人王氏生庶长子朱常洛,宠妃郑氏生庶三子朱常洵,神宗因偏爱郑贵妃,并不愿遵从祖制立皇长子为太子,反而倾向于皇三子。士大夫群体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接连上疏发动攻势:首先由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尽快册立太子,“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惟国家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8]。申时行毕竟不是张居正,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寥寥数语搪塞了事,采取拖延战术,借口朱常洛年幼,“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9]。与此同时,皇帝正打着他的小算盘:他决定先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进封为皇贵妃,此议一出,举朝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劝阻,后被贬。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更加汹涌。其后,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吏科给事中杨廷相、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相继上疏。最后,由于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10]。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大夫群体就此作罢,其后,关于请求进封恭妃为皇贵妃以及早定国本的奏疏接连不断,诤谏从未停止。在“国本”之争初起时,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都对“国本”一事的走势,有过相当积极的估量。然而神宗屡屡拒谏,士大夫群体望之甚切,却十余年求之不得。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初一,礼部奏请为皇长子举行冠婚礼,二十六年五月,万历传谕内阁:待新宫落成,举行皇长子冠婚礼[11]。人们引颈盼望,一年又一年,仍不见动静,多次被耍弄,忍无可忍,二十八年新年刚过,便连珠炮似的向皇帝发动攻势。最终,迫于舆论压力,才于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12],至此,“国本之争”才算勉强告一段落。[13]
二、国本之争背后:道统与政统的较量
(一)儒家道統的演变与发展
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但问题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士大夫群体为何要坚持立庶长子而不做任何妥协呢其实,从理论层面而言,神宗的这一倾向并无不妥,至少从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来看,找不到任何漏洞,但这却是被当时由道德伦理所建构的礼法秩序所无法容忍的。神宗的“反常行为”令朝堂上的士大夫深感不安,同时也为他们团结一致限制皇权提供了契机,这是阶级利益与道统影响下的共同选择:作为儒家道统的卫道者,他们坚决不允许皇帝肆意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礼法之上。
所谓道统,是指一种儒家一以贯之的,以天道与圣王之道为核心内容,围绕明道传道载道的文化使命而建构、发展与演变的思想传授系统,至明朝已臻于完善。“道统”的表述则首先由朱熹提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中庸章句·序》)。道统的精神内核,可以追溯至孔孟时期。孔子所谓之“道”,并非道家“道法自然”之虚无缥缈,而是立足人伦之“人道”、国家治理之大道,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
与之一脉相承的,是由道统所孕育的士大夫精神,核心标准就是建立在儒家伦理基础上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表现为一种担当精神,家国情怀,国士无双,士以天下为己任,其理想就是先秦儒家倡导的“修齐治平”,实现“出将入相”“内圣外王”。这些饱读诗书的理想主义者们,从读书识字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并彻底信仰他们在书中所学到的圣人之道,一切成功的标准都是单一的、既定的,但现实终究和四书五经所构建的社会是不同的,况且他们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中,皇帝的种种行为往往会偏离这个理想,因此,这种士大夫精神所表现出来的“道统”对于“政统”——现实的政制——的偏离就有一种纠正的力量,并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驯服政统,并最终实现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终极目标。这种士大夫精神,或者说是压在每个人身上无形的道德的负担,把他们推到了卫道者的风口浪尖。
(二)道统的驯政机理:礼法秩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统以君王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如果说政统代表的是政权,那么,道统所代表的则是话语权。韩愈认为:士人所代表的道统要比君王所代表的政统更尊贵,因为道统是儒家的“内圣之学”,政统则为“外王之学”,是先有“内圣”,方能“外王”。社会的发展也应该循着理想的道德和天理来运行,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不可改变的,而政权则是可以世代更替的。话虽如此,实际情况总不尽然,士大夫阶层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古以来,道统与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皇权,官僚和士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3]。只要是在一个世界上,道统和政统在实际上是无法各行其是的。道统不争政统,政统却可以压迫甚至消灭道统。那么,道统有没有可能驯服政统呢?事实上,透过国本之争,看待万历朝的众多政治现象,似乎就蕴藏着这种可能性。历代文官集团都几乎很少从纯粹的政治制度的层面来对皇权加以限制,而是运用自身独特的政治智慧,将限制皇权的愿望诉诸礼法规范层面。
礼法秩序何以“以小驭大”,能够在皇权不断集中强化的明朝对君主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层层剥离之后,似乎能初见端倪:皇权表面上不受限制,但皇权的合法性需要通过对皇权正当性的论证得以实现,这不仅是事实层面上的问题,而且需要在规范性层面上得到论证,也即皇权的所有者需要设法为自己获得和维持皇权寻求到足够的规范性支撑。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正如儒家道统中关于“王霸”和“德力”的讨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支撑在一开始也许可以通过掌控暴力机器而获得,但帝国的长期平稳运行则要诉诸“受命于天”、自然的血缘关系、良好的道德品格、对礼法的遵守等许多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的具体原则,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礼。
礼法秩序为稳固的政治秩序所必需。对于明朝而言,明初的统治者或许可以通过自身的征战直接掌控暴力机器,自下而上地推翻旧有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从而自然而然的实现皇权的正当化。但随着皇位的不断更迭,“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国家迫切需要通过设立文官来解决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文官身为道统的实际践行者,通过不断建构与强化礼法秩序,来维持政治的规范性。当一个朝代步入中期,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时候,礼法秩序遂即逐渐定格为皇权正当性的来源。皇帝作为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不仅要展现出自然血缘关系的连续性(嫡长子继承制)来论证得位的正当性,而且,其本身作为礼法秩序下的选择,就更要遵从这一规则从而不断强化自身合法性的论证,以加强对朝堂的控制力。皇权正当性的论证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礼法框架下的道德规范,并且要成为标杆与表率。这些道德术语似乎成为了某种政治规范,而规范的解释权系于士大夫之手,这样由士大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就可以间接发挥作用,对皇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礼法秩序其实构成了中国古代皇室宗法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点。每当出现礼法秩序失序的时候,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自然就会产生冲突,文官集团就 可以对此大做文章了。当然皇帝也会利用礼法秩序去攻击文官集团,或者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相互攻击时也会围绕礼法秩序的解释而产生“君子”和“小人”之分。特别是宋代以后,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与官员高度重合,使得文官集团认为自己可以掌握礼法秩序上的解释权,并以此参与到与皇帝的互动博弈之中。皇帝需要文官集团在礼法秩序上的支持,同时也忌惮文官集团在礼法秩序上的反对[1]。
国本之争问题的实质就是礼法秩序的争议。神宗试图突破无嫡立长的传统礼法秩序,从文官集团手中夺回礼法的解释权。文官集团的不断争斗,既是为了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也是为了防止皇权的进一步扩张。换言之,皇权只能染指世俗领域,对于礼法领域而言,则不允许出现皇权干预甚至突破的可能(这种说法仅仅是从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得出的结论,不宜扩大,因为礼法总是充斥着模糊的中间地带,后人如何解释前人的文本,以及何人掌控着解释的权力,恰为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文官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提供了对抗与角力的场所。事实上,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皇权就成功染指并干预了礼法,嘉靖皇帝通过自身的“优异表现”、技术手段把礼法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结果就是对朝堂的进一步控制与皇权的进一步扩张)。
三、道统催生的异变?——文官的阴阳两面
道统孕育下的士大夫精神,构成了礼法秩序得以建构的内在基础。从对皇权的限制角度来看,这是道统对政统的胜利,是一种良性的发展。但道统本身其实存在着自我崩解的内在张力,异变出文官所具有的阴阳两面的“怪象”。何谓文官的阴阳两面,文官为何会有阴阳两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按照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的说法,“他(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成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如此看来所谓阳面,无外乎人伦道德,忠义两全,而这正是儒家道统所传承与倡导的,道统塑造了文官的阳;而所谓阴,就是阳的对立面,代表着人性的阴暗面,自私贪婪与腐败。阳就是把道德的一面竭力表现出来,阴则是隐藏自己的丑恶。而人本就是这样一个兼具阴阳两面的复合体。倘若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这个话题似乎在讨论人性,那么,为什么要单独讨论文官这一群体?他们的阴阳两面与抽象的人的阴阳两面相比有何特殊性?
其特殊之处在于,文官与一般的人不同,尤其是明朝的文官,道统的发展至明朝已蔚为大观,明朝又十分强调道德和礼仪的作用,这与洪武皇帝有关,他想要的是一个道德的王朝,要的是大明政治的清廉,官僚的自觉,所以酷刑和颇低的俸禄就成为大明的惯例变得理所当然。同时,科举制也相当成熟,这些文官们都是熟读四书五经、从小受道德熏陶在圣人之道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他们的阳面被无限放大了。他们也许不曾发现原来自己也有阴面,尽管经历宦海沉浮,他们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阴面。一方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承认阴面等于离经叛道,意味着自己还不够心正意诚,解决的办法不在于正视私欲,而是要在每天的内省中正心诚意,修身养性,早日立德。另一方面,国家的纽带、政治的稳定离不开这些原则与信念,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偌大的帝国,其行事、断案,没有成宪可援引,其所依赖的是道德。“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这种路径依赖已经不允许出现轻易的变革,任何离经叛道的异端都是对这个庞大帝国的无形威胁。
阳面的无限放大,与之相对应的,也是阴面的愈发强烈,这无关道德,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高度繁荣,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早期启蒙思潮出现萌芽,典型代表如李贽,对孔孟的传统儒学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明中后期市民阶层的扩大,文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与多元化,使得文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私欲问题。如果是明朝初年,久经战乱,社会生产力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凋敝的情形下,大力弘扬阳面,抑制阴面,还不至于失衡。而到了万历朝,这种割裂已经难以弥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迷惘中丢失了自我,不再将经书的内容奉为圭臬,不再把道德准则真正付诸于实践。他们着眼于自身利益与集团利益,当皇权威胁到这些利益时,他们便“大义凛然”地手持经书,毅然决然站立在君主的对立面。仁义道德是他们的武器,把皇帝逼得无处遁形,只得消极罢工。他们不需要励精图治充满个性的皇帝,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牌子”,上面写着至高无上。规范早已定好,皇帝只需要照葫芦画瓢,通过道统构建起的秩序与稳定不允许被打破。
四、裂变:万历的“两个身体”
被誉为德国历史法学派最后一位重要人物的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对中世纪英国王权制度有过深入的研究。“国王的两个身体”是指国王这个职位同时兼具事实性與规范性两个维度。通俗来讲,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同时兼具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在英国,国王的两个身体被引入到了宪法体制中,得到了法学家的论证(《王权至尊法案》)。康托洛维茨在书中论述了“国王政治身体不死”的观点,和此后的英国革命中国王被推上断头台作类比,国王的自然身体虽然死了,但是作为“人民的头号管制者,国王是不断存续的名号”。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延伸至几乎同时期世界的东方,依然可以架接起二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万历朝中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关系。
至明中后期,皇帝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代表着万历的政治身体:在文官集团眼中,万历只是一个“牌位”,一个帝国存在且平稳运行的象征。万历本人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也曾向往过无拘无束与自由。他想修宫殿,工部不同意,他想走出紫禁城不到百十里,礼部都会将其视作一个严重问题,除了两年之内四次谒陵以后再视察过定陵一次,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他换了首辅,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下圣旨,内阁给他驳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剩下的只是他和这些文官们无休无止的争吵。由于(道德)制度的存在,他的一言一行都被限制在规范中,一套由儒家的圣王之道所主导的规范中,他的任何“异端”,都有可能在这套既成的礼法制度中冲出一个缺口,进而导致整个秩序的失衡。文官绝不会允许,无论是出于纯粹的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还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万历任由自然身体的生长,最终只会将其置身于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由于万历个人能力和性格的缺陷,既没有其祖父嘉靖的权术智谋、难以深谙制衡之道,也没有武宗放荡不羁、无所顾忌的率性,这场与文官集团的较量,他找不到出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与文官争斗,于是只能被迫选择做一个失败者,黯然离场。他的最后一搏,大概是想告诉文官集团:我输了,但你也没赢,于是以消极怠工、躺平摆烂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最后的观点,最终,他的自然身体已经被文官的阳面慢慢消耗殆尽,不复存在了,他成了一个活着的祖宗[1]。他的童年是在严厉的张师父的教导和曾经差点废黜他的母亲的管束下度过的,不能耽于逸乐,做事安分守己,成功的做好了一个皇帝的“牌位”角色,让自己的政治身体茁壮成长。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的背离与裂变,为万历本人染上了悲情色彩,也加速了明帝国被埋葬的步伐。
五、结语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又该如何定义二者之间
的关系,一直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自宋以后,平民百姓中的精英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不仅进入了帝国统治的基层毛细血管之中,而且也进入了帝国统治的心脏,逐步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官集团[2]。道统为文官集团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其能凝聚成一股足以对抗皇权的势力。在皇权与文官集团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文官自认为和被认为掌握着对礼法秩序的解释权,并希望以此来制衡或约束皇权。国本之争中所折射出的政治角力,背后也埋藏着晚明的巨大危机,对勘“国王的两个身体”,许多问题都变得清晰明朗。一边,文官用自己的阳面促成了万历政治身体的蓬勃发展,而这仅仅是树大中空;另一边,文官又用自己愈发膨胀的阴面腐蚀着庞大的帝国,也难怪“明之亡,实亡于神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