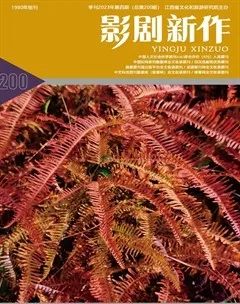金地文人与磁州窑瓷绘的山水趣味之变
2024-01-20陈燕华



瓷上山水作为一种独特的陶瓷绘画装饰类型,在中国陶瓷史上由来已久。站在宏观的陶瓷史发展来看,在金末元初、明末清初及清末等几个官窑相对衰落而民窑相对兴旺的阶段,是瓷绘山水这一题材相对盛行的时期。在这种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官窑往往失去了强有力的资金与人才支持而陷入困顿和停滞,民窑则反而因各类限制的放松而得以发展。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则金元时期是瓷上山水的初步发展阶段,以北方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山水为其代表;明末清初是瓷上山水的全面创新时期,以景德镇青花山水为盛;清末则进入陶瓷业的近代发展阶段,以浅绛山水为其主流。瓷绘山水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陶瓷烧造技术这一决定性的前提外,亦受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整体制约,也与山水画本身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息息相关。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山水瓷是瓷上山水的早期实践,在陶瓷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其不仅是金代在士人文化和世俗文化得到相当程度发展的特殊时期,绘画潮流在陶瓷器上的一种投射;同时亦表现了在社会动荡时期,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及努力自我保存的特质。
一、长沙窑的早期瓷上山水图像
在器物的表面进行图绘表现是人类在陶瓷器发展的历史中衍生出的一种本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等即发现有丰富的低温彩绘陶器,这些器物图绘除少量象生类的动植物纹饰外,多以规律性的几何图案为主。在接下来的商周直至唐代的漫长时期里,陶瓷经历了由低温陶器至高温瓷器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首先将创造力与兴趣集中于釉色与造型方面的创新与改进,形成了“南青北白”以及陶瓷雕塑相对发展的局面。直至唐代在长沙窑才诞生了最早的高温釉下彩绘瓷,将绘画、书法与陶瓷装饰技法结合起来,初开瓷面绘画之先河。长沙窑在瓷面上表现绘画与书法,具有突出的民窑特点,这些题于瓷壶上的书法见有古诗、格言及题记等,内容多反映中下层社会人们的情感与生活,质朴、真挚而强烈;其瓷画题材数量最多的是花草、鸟雁及各类动物,多由窑工信手画成,风格虽稚拙随意,但却充满了活泼的写生意味,陶瓷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类程式化特点在此时还尚未出现。就瓷绘中人物和山水的比例而言,则山水远远少于人物,这也基本是与唐代绘画的发展同步的。
长沙窑早期瓷面绘画中的山水图像数量极少,如图唐代中期青釉山水纹瓷罐上呈现的是少有的以山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画面,图中一侧以线条一层层作简率勾勒以形成一个个独立山体的基本轮廓,山峰最外圈以淡墨晕染以表现树木积翠,山峦似两个“山”字象形符号 的层叠倒退。山峦左部以线条勾勒出一海上佛塔,佛塔与山体之间画有飞鸟以表现画面纵深之感。绘画史上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独立的山水画还处于孕育之中,如现存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的经变图中的山水,多以背景的形式用于表现佛教史迹,大体是以线条勾出个别山峦的大致轮廓,再沿山顶轮廓描绘树木,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其与唐代釉下彩绘山水在构图与表现方式方面有相通之处,同样反映了这一阶段民间画匠对于山水的理解和表达。
唐代長沙窑青釉山水纹瓷罐,见《中国陶瓷全集》唐、五代卷。
二、金地文人与磁州窑瓷枕山水图像的出现
继承了唐代长沙窑在釉下彩绘及在器表题写诗句传统的是宋金元时期北方的磁州窑系。至此时瓷绘山水已有了更为丰富成熟的表现,就风格而言,其与同时期偏重色釉与刻花的景德镇窑大异其趣,但又为元青花和明代以后重新崛起的景德镇民窑瓷绘在风格与主题上奠定了基础与传统,成为明清景德镇窑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多元性格中的一元。磁州窑在宋金时期陶瓷业的发展中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亦是一个民窑特征较为集中和明显的窑口,与官窑受官方意志制约有一定的差别,有着鲜明的民间性和相对自由的艺术表现。在其时各大官窑追逐青釉、白釉等色釉含蓄而蕴藉的表现的时候,磁州窑则于白地黑花彩绘瓷方面有着开拓性的发展。特别是在白地黑花的瓷枕上,白地瓷枕平展似白纸,在其上施以黑彩,其表现近似于白纸黑墨,虽因技术的局限无法作层次丰富的晕染及多色釉方面的表现,但于白描图像方面却有天然优势。这是磁州窑成为最早在瓷器上线描图绘山水、戏曲和小说故事并热衷于在器物上作书法表现的窑口的重要因素。
以磁州窑为代表的民窑服务于民间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人群,这决定了其庞杂而广博的性格,而因面对消费群体的不同,民窑内部亦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进一步分别。但有一点勿庸置疑的是,其装饰内容与风格特征一定是特定时代与社会流行风尚与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投射。民窑瓷绘的内容不仅包括绘画中的图像,也包括织锦、漆器、金属器等其他工艺美术品上面的图案。这一特点基本也为后来的元明瓷绘所继承,这也说明瓷绘图像发展从来都不是一种基于其自身的完全自足的过程,它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图像世界的一个折射面。今日能从瓷面上的图像与诗文中读到当时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无论这种情感来自市井还是知识阶层。总体而言,以宋代汝官哥均等窑生产的官窑色釉瓷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审美,具有典雅、平淡而蕴藉的特质,而以磁州窑系为代表的民窑大体则是直率的、市井的。磁州窑釉下彩绘自北宋中期创烧之时起就有着大量的风俗性、民间性的内容,如婴戏、马戏、熊戏、花鸟、瑞兽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从金代开始瓷面上的山水、历史故事、文人名士的活动等图像以及诗文、曲文以及图文相配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尤其这一时期瓷枕上的山水图像第一次呈规模的出现,显示体现上层知识阶层文化修养的士大夫审美的逐渐下行,且有向城市文化和市井文化中渗透的趋向,为中国陶瓷装饰史带来全新的变化。
在金代此类图像的大量增加,固然是因为自北宋以来山水画之勃兴借助城市生活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已达至民间社会,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时的开封,“时行纸画”已在各街巷的商铺、夜市出售,在相国寺东门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1],可知对山水图像的消费与欣赏,已进入城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金代基本继承了北宋这一社会经济基础,同时被金国所继承的,还有北宋的科举制度与士人阶层。金国为快速掌控华北社会,几乎全盘接受和向化于中原文化,“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2]。十二世纪末的金代中期,科举、学校得到普及,士人阶层不断扩大,士人传统得到保留以至深化,“为华北社会带来了社会、文化规范的均一化”。[3] 而对于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民间社会来说,知识阶层企图表现和保存中原文化正统的意图亦十分强烈。金代文化的这个特点渗透到其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金代文人山水相比南宋更倾向于保存与延续北宋的李成、范宽传统,金代山水中盛行之“怀古”主题,“尤其突出地透露出这个金朝士人社群对其文化传统的高度意识”[4]。就民窑瓷器的装饰主题而言,对北宋及唐代文化的追慕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强烈,相比唐代长沙窑多在瓷器上题写通俗诗句与民谚,在金代的瓷枕上尤为热衷于题写北宋苏轼、秦观等文人的诗词与唐诗名句;而对于南宋的流行文化,也有可能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在金地被追随与效仿。
要谈到金代瓷枕上何以大量出现山水图像,还需看到宋金时期文人与瓷枕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动乱时期底层文人的遭际等等多种社会因素。瓷枕在宋金时代是民间夏日纳凉度夏十分常见的实用生活寝具,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所喜爱,文人诗文对其记述十分多见,如北宋张耒的《谢黄师是惠碧瓷枕》有“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北宋末李纲的《吴亲寄瓷枕香炉颇佳以诗答之瓷枕》有“远投瓦枕比琼瑜,方暑清凉惬慢肤”等等。瓷枕因其纳凉醒脑的功用,还是夏日文人书房必不可少的物品,一件刻有《枕赋》铭的磁州窑诗文枕就记述了书房中文人与磁枕的亲密关系:
有枕于斯,制大庭之形,含太古之素,产相州之地,中陶人之度,分元之全,名混沌之故。润琼瑶之光辉,屏刺绣之文具,泥其钧而土其质,方其样枵其腹。出虞舜河滨之窑,绝不苦窳,灭伯益文武之火,候以迟速。既入诗家之手,欣置读书之屋,鄙珊瑚富贵之器,陋琥珀华靡之属。远观者凝神,狎玩者夺目,来尺璧而不易,贾万金而不鬻。囊以蜀川之锦,椟以豫章之木,藏之若授圭,出之如执玉。是时也,火炽九天,时惟三伏,开北轩下陈蕃之塌,仆南薰蕈春之竹,睡快诗人,凉透仙骨。游黑甜之乡而神清,梦黄粱之境而兴足,恍惚广寒之宫,依稀冰雪之窟。凛然皂发之爽,翛然炎蒸之萧。思圆木警学之勤,乐仲尼曲肱之趣。庶不负大庭太古之物,又岂特不困于烦暑之酷而已也。[5]
在炎热的夏日书房,一件爽人心神的磁枕须臾不可离身,这是什么富贵华靡之物都比不上的,其珍贵就连“尺璧”“万金”都不换。文人对瓷枕的这种喜爱珍视的态度使得瓷枕从寻常日用器物成为可品鉴把玩之物。既入诗家之手,置于读书之屋,对于瓷枕的装饰要求自然要符合诗家的审美。因此瓷枕消费者中的文士、贵族甚至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于枕面装饰趣味方面的要求有可能推动诗文、山水在瓷枕上的流行。甚至有材料显示在金初的动荡年代,有文人直接参与了瓷枕的烧造,一件收藏于日本的底部有“赵家造”戳记的磁州窑绿釉划花长方形枕,其枕面刻划诗文云:
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颖川,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中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闲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共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河望日也。[6]
磁枕上的长诗不仅记载了北地受金兵侵扰的史实,更反映处于战乱年代的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绍兴三年为1133年,時北境处于金太宗完颜晟统治之下的天会十一年,而修枕人却书以南宋年号,遥望故国之情不尽言表。修枕之人著诗撰文,战乱前可能为下层文人,闲居窑场修枕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避祸之举。《金文最》卷六五收《创建文庙学校碑》一文,为纪念天会八年(1130)冀州节度使贾霆为当地重建州学而作,其中提到其作为地方官员的治绩,有“发仓廪减价以赈贫者,兴庐舍给居以厚民生……饥民转徙脱身奴婢者以千计,士夫乱离复籍缙绅者殆万数”[7] 之语,可见在那样一个年代,士大夫失去缙绅的地位而沦为庶民实是一种常态。然而从陶瓷装饰这一方面来看,也正是知识阶层的下沉与介入,才有可能带来陶瓷审美的趣味之变。
三、金代磁州窑瓷上山水的两类图式
狭义的磁州窑,一般是指北宋初至元代河南彰德府(今安阳)磁州及邻近的河北邯郸磁县所属窑场,以章河流域的观台、冶子,滏河上游的彭城、临水等地为中心;而磁州窑系则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包括了北方广大地域的许多民间窑场,其生产的瓷器整体风貌与磁州窑相近,同时又各具特点。如绘有山水的白地黑花瓷枕是磁州窑特色品种之一,但各地瓷绘作风又不尽相同。在山西长治一带的窑场所生产的瓷枕,其上所绘山水图像为北宋北派山水至金代武元直一路作风;而在河南河北一带窑场所产瓷枕,其所绘山水则受南宋院体山水影响较大。这些图像一并进入瓷器画面,并形成瓷绘的新传统,为后来元明时期的景德镇瓷绘所继承。
(一)山西窑场的两件山水瓷枕
山西地区长治一带窑场为广义磁州窑系范围,亦烧造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当地出土的两件山水瓷——一为金代纪年墓中的山水瓷枕残片,一为金元窑场出土瓷枕,在现存的磁州窑山水枕中是十分独特的存在,与磁州窑主窑场烧制的其它山水瓷枕风格迥异。两者风格一脉相承,都绘有全景山水图画,体现了北宋李成、范宽至金代武元直一路画风,且有着一种超越时代的完整与纯熟之感。
其中金代纪年的白地黑花山水纹椭圆形枕残片来自山西长治市崔晸墓。[8] 此墓曾出土一方皇统三年(1143)纪年的墓志铭,明确了这件瓷片的年代。皇统三年为金熙宗统治后期,这一时期金朝逐步恢复了北宋建立起来的官僚与科举制度,社会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就磁州窑系的发展而言,这一时期是其开始突破日用品的范围,开始烧造艺术性陈设瓷的阶段,白地黑花的装饰技法亦出现不久。此件山水瓷枕残片上图像,虽然山水形象较为简洁,但其笔法构图较为老练,不似一般陶瓷工匠处理这类画面的程式化意味和生拙之感。画面为典型的北宋构图,近、中、远景交待清晰,近景为一水两岸的布局,中景为一片淡泊的水域,远景则为高耸的高大主峰,山头以墨点交待着树丛,线条简练而不乏张力。此类图式似来源于北宋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体现了这一时期绘画所追求的“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的审美趣味。
山西东南窑场出土的另一件瓷枕年代略晚一些,可能为金末元初时期所烧制。其上所绘山水图相比崔晸墓残片更为细致、丰富,画面视线拉长以获得更多复杂的元素如小桥、楼阁、小舟等,其构图的完善与皴法的老练,远非普通工匠所能措手,而像是某位画师在瓷枕上直接创作而成。瓷枕画面虽小巧,但全景式构图仍不乏气势壮阔之感,在山体耸立的形态、山顶树木积翠的表现上,同前一件瓷枕一样,接近北宋诸家以至金代武元直的风格,对于了解金代山水画发展的形态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
金代白地黑花山水纹椭圆形枕,山西省长治市崔晸墓出土。
金代白地黑花山水纹椭圆形枕,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山门出土。
(二)磁州窑瓷绘中的高士诗意山水
磁州窑瓷枕上还有更多的山水图像,使用的是有别于以上北宋模式的另一类图式和趣味。这部分图像大量见于河南磁州及河北邯郸等地主要窑场所生产的瓷枕上,年代多在金代中后期及金末元初。这类山水瓷枕大都来自一些特定的制瓷作坊,带有“张家造”“古相张家造”“王氏寿明”“漳滨逸人制”“李家造”等戳记,它们所具有的相似的瓷绘作风,是金元时期磁州窑山水瓷绘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作风:即多以如意开光的形式呈现,两侧有花草纹以为装饰,线条与造型较为简率,且带有一些陶瓷业中常见的程式化特征。最重要的是,这些瓷绘山水表现的内容、使用的图式多是一种带有南宋院体风格的、有高士悠游其中的诗意山水。其中部分瓷画是以诗或文配图的形式来表现,在实用之外,已寓文人清玩之意,其画面虽有高士活动其中,但亦有别于叙事性的图像,而带有明显的抒情性特质。
如前所述,眷恋唐诗的风气弥漫于北地的金国知识阶层,而在南宋的杭州地区,反思北宋诗之好说理议论而返归唐诗之抒情传统的潮流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基于感性认识的抒情倾向,当然是唐诗最得意的长处。从此以后,对于唐诗的向往成为南宋诗的一股潜流”[9]。自北宋末徽宗至南宋的皇家画院,以唐诗为题材来营造画面是一项重要的能力,“院画家及其追随者为他们的观众(从皇帝到有教养的城市居民)而创作,并且完成得格外出色,不断召唤、再造和重新想像一个失去的诗意世界”[10]。南宋院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语言,充满怀旧情感的自然形象、高度提炼的景物以及沉浸其中的理想化的高士形象等等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可以想见,在繁华的都市杭州,这类新颖的带有精巧构思的新图式在宫廷画院一经形成,就会被临摹复制成无数个副本,成为商业书画定件、扇面、或酒楼茶肆中的招贴画,被广泛地进行传播,其所到之处也包括北方的金国。瓷枕作为一种商品和扇面、书画一样是当时的人们互相馈赠的礼物,而市场的需求才能决定图绘其上的主题,这也许解释了磁州窑瓷枕此类图像的出现和流行。
以马远为代表的院画家所完成的融合了高士和山水的人物山水画是南宋院体画的一种典型表现手法,这类图式在金元磁州窑瓷枕上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不同于北宋山水的全景式构图,这类图式通过小幅画面的裁剪来暗示人物视线所至之处的幽深旷远。通常在幽谷之一侧伸出的岩石上,高士或坐或卧,或凝视或回眸景物深处,其身旁树干呈挺立之姿。这正符合自马远以来建立的传统,只不过画工所处理的画面更为简率随意。在远景处有时仍会有高大山体的出现,但一般是一种极为程式化的方式:通常是并列的三座山体,以等线作简单的勾勒,是整个画面的背景而非视觉主体。
金代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椭圆形枕,1962年河北省磁县冶子村出土。
金代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枕,磁县观台镇出土。
金代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枕,磁县城北孟庄村南口金代墓葬出土。
四、结语
金元时期磁州窑瓷枕上的瓷绘山水的兴起是中国陶瓷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颇令人瞩目的现象。从陶瓷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国陶瓷装饰山水题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起步阶段,也是民窑陶瓷装饰技法不断进步、瓷绘题材得到极大扩展的一个表现;而在文化史上,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既是从北宋至金代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居民对文化图像的消费需求大大增长的一种表现;也是金地文人在社会动荡时期,将自身的情感与对文化传统的保存意识投射于瓷枕之上所致。总之,金元磁州窑瓷枕山水是其自身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丰富和拓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并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本文为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十七世纪景德镇瓷绘中的“书斋园林山水”图式研究”(项目编号:YG2021 040)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01.
[2]脱脱等.金史:卷六十三[M].清乾隆武英殿本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3]饭山知保.金代科举制度变迁与地方士人[J].科举学论丛,2010(01).
[4]石守謙.1200年前后的中国北方山水画——兼论其与金代士人文化之互动[G]//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特辑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83.
[5]张子英.磁州窑瓷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67.
[6]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观台磁州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563.
[7]张亿.创建文庙学校碑[M]//张金吾. 金文最:卷三十三.清光绪刻本.
[8]商彤流、杨林中、李永杰.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J].文物世界, 2003(01).
[9]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M].郑清茂, 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196.
[10]高居翰.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2:40.
陈燕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谢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