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空间与霓虹美学:《子弹列车》的超惯性叙事模式建构
2024-01-20何珊
何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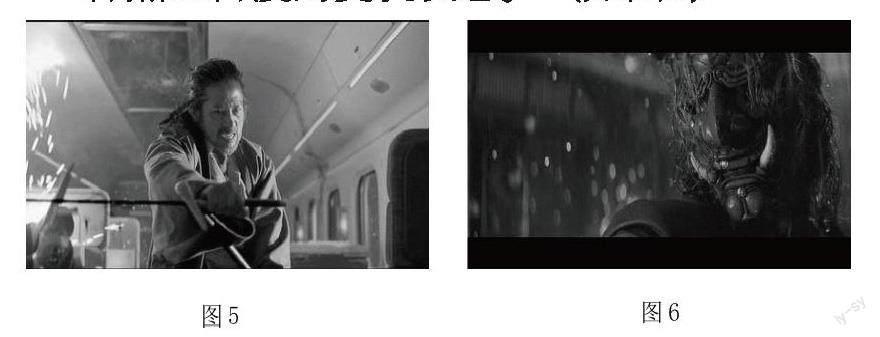
摘 要:《子弹列车》是一部在暴力和幽默之间达到平衡状态的动作电影,极具风格化的动作场面和喜剧元素巧妙结合,展现了商业电影旺盛的活力。兼具封闭性和时空性的列车成为影片的主要叙事载体,“赛博朋克”①风格的视觉效果加上流行文化的杂糅与黑色幽默,捕捉荒诞和滑稽中忧伤的同时,佐证了宿命论的主题。影片中喜剧风格与混乱和失序的细节相结合,将不合常理合理化,覆在深层惯性表达之上的是看似纯粹的消费性质。影片在受限的空间中逐层表现冲突的人物关系,一个人物一个独立的故事,拼凑构建了整个故事,表现出Cult电影②中超惯性叙事③的属性。片中喜剧元素的轻松感、紧凑的节奏与流畅的镜头调度,都为观众带来愉悦精神的舒适感。
关键词:超惯性叙事 受限空间 霓虹美学④ 杂糅文化
电影《子弹列车》(Bullet Train,2022)改编自伊坂幸太郎的小说《瓢虫》(2021),故事发生在一辆从东京向盛冈疾驰的列车上,五组杀手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踏上了这趟列车,从每个杀手的任务展开,拼凑式地讲述了整个故事。五组杀手在各自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发现彼此之间任务的隐秘联系,结合漫画风的动作场面呈现杀手间激烈的生死角逐,在多次反转中,诉出所有人都逃不过的代价——宿命。人物间的关系在层层展开中逐渐清晰,运气与宿命的设置打破惯常情节设定,增强趣味性。
惯性叙事通常为好莱坞电影模式中常规性的电影制片手段,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漫威电影和一些传统的预告片电影,在固有的电影结构中创新。而超惯性叙事作为影像表达与叙事模式的路径,早在一些观众并不看好的复合文本、恶搞影片的格式中就有出现。但随着流媒体的发展,超惯性叙事以新姿态进入主流影像的视野,对惯性叙事有意回避的同时也保持了对其的继承与创新,展现出较为纯粹的消费性质,保留了基本的商业叙事逻辑,看似打破了惯常叙事的模式,却也遵循着“游戏规则”。
电影《子弹列车》打破早期以列车为主体的影片创作,赋予列车叙事超越转场与装置感的特殊意义——电影文本同一性与特异性的对抗表达,列车作为叙事空间既能链接整合叙事整体,也为每个独立个体留有反抗主文本的空间。从影片的叙事逻辑、影像风格与角色塑造等方面的突破与隐喻,深入探析超惯性叙事模式的建构及其深层哲思。
一、受限的“夺宝”战场与黑童话隐喻
列车作为一种在电影中的叙事载体,已经屡见不鲜,如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釜山行》(2016)、《雪国列车》(2013)、《天下无贼》(2004),喜剧动作电影《子弹列车》(2022)也选择了以列车为主的叙事空间,但其叙事逻辑突破了惯常的模式,用看似脱离主文本的独立故事给列车文本带来全新的阐释。
(一)密闭车厢的叙事空间与“夺宝”故事
列车兼具封闭性与时空性成为诸多影片的叙事载体,经典电影《东方快車谋杀案》通过火车的时空场景展开缜密悬疑的推理;电影《釜山行》讲述了在逼仄的空间中人们求生的惊悚;软科幻电影《雪国列车》借列车讲述社会等级秩序,影射人类阶级社会。电影《子弹列车》中的列车已经不仅仅是符号化的意象,通过片名可以得知电影讲的是各路杀手汇聚列车的故事,电影的改编从故事叙事的层面来看,也基本上遵循了好莱坞改编的基本要素:对故事内容的压缩整合、对视听语言的包装升级及对叙事逻辑起承转合的设定。
影片《子弹列车》讲述了一个在杀手组织拒绝杀人工作只承接抢夺任务的打工人,顶替同事踏上这趟暗藏杀机的子弹列车,与其他杀手展开激烈生死角逐,阴差阳错中解决掉其他杀手,最终幸运地下车的故事。布拉德·皮特饰演这位打工人,在这次任务中的代号是预示着好运气的“瓢虫”,在列车上与诸多杀手的相遇和争抢虽有荒诞,但他也“幸运”地在阴差阳错与手忙脚乱中成为列车上杀人最多的杀手。一辆列车与五组杀手,抢夺一只手提箱,复杂的关系绕不开“白死神”这位神秘的雇主。在影片的前30分钟,跳跃式的叙事节奏加上闪回与倒叙为几位杀手的登车及相遇做出初步的解释,影片在受限的车厢空间内用黑帮和杀手与黑色幽默的融合,去对抗时间的宿命。
《子弹列车》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在车厢内,人物在不同的车厢间走动,展开人物间的关系发展,当人物在车站短暂下车与影片后半部分人物突破车厢这个密闭相对独立的空间时,遇到了雇主“白死神”的威胁与空间打破带来的伤害。当封闭独立的空间被打破时,叙事空间就变成了密闭与外部开放的空间相结合的场域,《雪国列车》中也有着如此叙事场域的呈现。封闭独立的场域空间极具限制性,但也推动电影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对主题也有更集中的表现。车厢兼具封闭性与隔离性,也会对视听语言做出一定的限制,人物在此空间中对外部信息的沟通也相对闭塞:影片中“瓢虫”成功穿梭在列车车厢中,是借助了电话中的交流与指示;在《雪国列车》中末端车厢的人开始也不知道列车内全部的状况。影片剧情的推进过程也是人物在寻求生存与救赎的过程,人们萌生打破所在的受限空间的想法,可以看出受限空间对人物的行为也有一定限制影响。[1]
受限时空的叙事载体在电影中也要承担对剧情进行密集集中的设置,密闭的空间会给故事内容带来危机性,在保证叙事完整的同时,也发挥着揭露真相、隐喻现实社会的功能。《子弹列车》中列车车厢的内部与外部如停靠的车站,都带有“白死神”的危险,这种危险性不仅推动着电影情节的演进,也强化了人物间的对立与冲突,以此来凸显人物角色的个性深化电影的主题,使电影的叙事逻辑更加合理化。
(二)“个性”杀手与“巧合”的逻辑建构
影片在列车这个受限的空间中对人物间的冲突关系也做出了建构,列车成为电影叙事的载体,不仅限制构建了物理层面的封闭空间,也在意识形态层面给人以精神状态中的封闭感与受限感,五组杀手在车厢的封闭空间中发生冲突后,也推动着人物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车厢内的不同杀手的相遇与冲突也引发了影片人物之间直接的矛盾与对立,更能凸显出五组杀手不同的人物性格,彰显个性。“瓢虫”是一位有些中庸、神经质的话痨杀手,在执行任务中主张以沟通作为先导武器,但无法避免的打斗发生时会选择速战速决,这些对角色的设定限制了角色的行为,也决定了他所呈现出的是戏谑与不稳定的状态。影片同时也塑造了对“托马斯小火车”有不同见解的双胞胎杀手“蜜桔”与“柠檬”;擅长伪装以毒蛇作为杀人武器过分自信的杀手“黄蜂”;装作柔弱中学生的杀手“王子”;为妻子复仇的杀手“野狼”以及同为复仇上车的木村。车厢作为封闭的空间为观众集中展示了人物关系的矛盾,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在电影叙事中进行穿插叙事,展开多线叙事,沿着多个人物线索进行展开,对人物做出的限定性的行为更能凸显出人物的个性特点。
影片中列车行驶到最后一站的时候,才出现了明显打破车厢密封式空间的叙事,关于杀手间的所有冲突和戏剧性都指向了在最后一站等待踏上列车的“白死神”,子弹列车在影片中沿着站点驶向所有冲突的根源。列车作为一个受限制的时空场域,不断放大人物间的冲突,强化人物的个性,对每个人物的生命旅程也做出了清晰的表述,拼凑呈现出完整的情节内容。对“白死神”的江湖传说在影片前半部分一直被提及,神秘凶狠的他在幕后操控着他人的命运,甚至是列车上五组杀手的出现与抢夺杀戮。这场在列车上的“巧合”厮杀,也为观众提供了几组明确的矛盾冲突,跨种族有深厚兄弟情谊的双胞胎杀手蜜桔和柠檬、亲子关系矛盾却擅长装无辜的杀手王子、复仇心切却意外死于蛇毒的杀手野蜂以及精心布局却未能如愿的白死神。激烈的矛盾冲突与目标明确的杀手以匪夷所思的荒诞死法结束生命,让影片的整体叙事逻辑极具“反逻辑”之感。电影所表现出的荒诞感与戏谑化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严密的逻辑,如同玩笑闹剧般的人物结局为影片构建了“巧合”的逻辑,也将电影的娱乐性强化,甚至在杀戮中营造出了关于杀手的“合家欢”的气氛。
(三)动画角色与玩偶公仔的黑童话隐喻
《子弹列车》中关于特殊角色进行了设定。影片在叙事中将托马斯小火车的儿童动画故事与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列车玩偶公仔的形象结合,串联在影片的多个场景与叙事中,托马斯小火车中的角色成了对列车上杀手们命运的隐喻,用对命运的掌握与失控的过程,去展露人性的弱点。(如图1)
影片中有一位对“托马斯小火车”故事熟悉的杀手柠檬,在整个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借用托马斯小火车中的反派角色来暗喻猜测他们的对手,表达他对人性的看法,但最终面对真实的列车时,却发现烂熟于心的故事不能让他立刻启动驾驶这辆疾驰的列车。影片提及的托马斯小火车里各种角色,以此来隐喻强调影片中人物的角色个性,以安于现状的乐观小火车珀西来比喻白死神的儿子,双胞胎杀手要保护的重要人物;以小火车中能力强且善良宽容、乐于助人的高登来比喻他的兄弟蜜桔杀手;也用油腔滑调、诡计多端的黑色狄塞尔来比喻对他们人物造成破坏的杀手。杀手柠檬不断在对话中用从托马斯小火车中学来的道理来诠释自己的行为与观念,最后将狄塞尔作为线索指向来给双胞胎杀手蜜桔传达信息。列车其实是对个体生活的隐喻,看似完全掌控,实则是面对变故时随意做出的选择,同样托马斯小火车也是对人生的隐喻,不是实际的驾驶指南。
在《子弹列车》中充斥着大量的日本文化元素,在以日本文化为主基调的基础之上,强化了日本动画、漫画和日式风格景物。(如图2)在车站中与列车上多次出现、为杀手野蜂提供藏身之处的玩偶,是对日本的手办文化做出了强化表现;列车途中电视机上的动画片对日本的动画文化做出宣传;放置药粉的瓶装水与结尾部分的橘子不仅是对广告做了植入、增強商业气息,旨在宣传日本的农业文化;列车行进的旅程中,对日本的建筑从老式的房屋到高新科技的动车的表现,是几十年间完成的日本现代化的表征,展示宣传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童话在影片中成了成年人的预言,柠檬用小火车的角色划分列车上的人,而杀手们的命运也验证了他的预言。影片中托马斯小火车的卡通形象与日本卡通玩偶形象的加入,频繁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枪火斗争中渗透出一种诡异的成人黑童话,暗示了列车上人物的命运,为电影增强了幽默成分的同时,也将背后所代表的美式与日本文化元素强调突出,让电影的叙事更加荒诞脱离现实,成为其娱乐性的有力支撑。
二、霓虹色彩与影像表达
在近些年的电影工业与电影文化中,“霓虹美学”已经成为现象级的风潮,霓虹美学以高饱和的霓虹光与高度刺激的视听风格为表征,是赛博朋克类型的作品中较为常见的影像风格,在电影中与黑帮、悬疑、科幻等元素进行融合强化表达主题。
(一)霓虹美学的表征与视觉先锋性的都市构建
许多科幻电影都对赛博朋克世界做出了设定,尝试在影片中打造极具特点的霓虹城市,如电影《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2017)对赛博朋克世界的呈现中,打造了充满着后工业赛博朋克风格的洛杉矶,成为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未来城市景观,荒凉的自然环境与高科技组建的城市对立。对于空旷巨型的体量空间感的表达,更具粗野主义与废墟美学,电影中2049 年的洛杉矶警察局总部的场景构建,让人联想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图书馆的造型,影片中巨大的残破的头部与废墟感让时空呈现凝固的感觉。
电影《子弹列车》的故事是在日本东京这个都市展开的,在1920年初,东京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发展霓虹灯的城市,电影对一个部分场景做出了赛博朋克风格的设定,高饱和度的迷幻色彩、霓虹氤氲,让电影中场景的视觉风格带有复古未来主义的元素。
影片中高速行驶的列车科技感十足,车内部的空间基本采用高饱和度卡通风格的粉蓝色调车厢与常规明亮的车厢,为影片增加了神秘与朦胧感。(如图3)列车外部的场景也多采用了霓虹色光,首先构建了一个极具视觉先锋性的现代都市,在高度刺激的视觉光效中,杀手们的犯罪行为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野性。[2] 影片中对文字如人物名字等信息的漫画式的展示效果,加强了影片的日式娱乐化的风格。列车内外不同的灯光氛围与动画片段的穿插出现,不仅在电影场景上增加了日式漫画感,也在叙事的荒诞与快节奏中突出强调了动漫效果。(如图4)
赛博朋克风格中的霓虹美学所代表的反乌托邦气质与悲观主义色彩的城市景观都与《子弹列车》中所表达的无序与失控之感相吻合,高度刺激的视听效果构建了影片的光怪陆离的场景,也为影片的“荒诞”增效,霓虹美学也与影片中暴力美学相融合。
(二)赛博朋克风格元素的杂糅与个性化的视觉调度
《子弹列车》中直观视觉可以感受到对日本的概念化呈现,霓虹色光构建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武士刀、日式服装与富士山,以及在影片中不断强调的礼节,列车的行进路线上也充斥着面具、人偶与高级马桶等一些标签化的物象。但影片对元素的融合不止日本元素,从个性十足的视觉调度到极具创意的动作场面,电影融合了多种元素,将流行文化杂糅在一部影片当中。导演在电影《极寒之城》中,对动作场面的表现更偏向于现实主义的风格,观众甚至可以通过银幕感受到打斗中的痛感,《疾速追杀》系列中更偏向于展示行云流水的杀人技巧,而《死侍》中因为有着超能力的设定,动作场面更加癫狂、夸张与血腥暴力。
在《子弹列车》中,动作场面在三者间,更具调和后的效果,虽未能表现出真实痛感的打斗,但加入了动漫的镜头表现元素,佐之非线性剪辑,影片的动作场面中表现出荒诞而不荒谬的诙谐之感。杀手瓢虫的“先礼后兵”让他与其他人的动作场面充满了戏谑和不确定的元素,在列车车厢这个受限制的空间内,借用日常用品来进行肉搏,在受限的时空中利用场景和道具出奇制胜,有着成龙式动作戏的意味。在影片最后长老与白死神的决斗中,呈现了关于日式剑道文化与机械武器的对峙场面,两种不同形式的暴力美学相互碰撞,佐之日漫热血式的背景音乐,在列车行驶到曙光射入车厢破除黑暗时,交织相映的是左轮手枪带来的命运赌盘,最后子弹列车脱轨撞击飞射而出,在充斥着血腥与暴力美学的列车故事中增加了一种热血日漫的复仇快感。(如图5)
旋转镜头、慢动作与升格镜头和快速非线性剪辑加以调和,影片中张扬的日式娱乐化风格场景的构建与动漫感动作表现元素,突出影片的日本文化表征,赛博朋克风格霓虹光效、日本黑帮元素、美国绅士与小混混以及墨西哥毒枭等文化元素杂糅,最终都蕴含于玄学的“东方哲思”中。
三、“杂糅”与“反转”的超惯性叙事模式搭建
导演大卫·雷奇一直在动作电影中延续的暴力与幽默,并在二者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子弹列车》这部影片用看似荒诞的故事讨论宿命这一论题。杂糅的流行文化与黑帮元素,加上结构上的前后呼应,使得角色的各自命运与这场“夺宝”之战的结果都颇有因果闭环的宿命轮回之感。
(一)杂糅流行文化与黑帮元素
《子弹列车》呈现出了对列车景观设置的特殊性与超惯性叙事意识表征,围绕子弹列车的叙事表现出叙事个体一致性与个体独立反抗主文本相结合的特征。早期以火車为主的影像文本虽然利用了列车叙事的装置感和高效的转场递进能力,《子弹列车》不仅意识到了列车的装置与叙事递进能力,也利用超惯性叙事的模式在与文本强烈的对立分离感与张狂的消费性表达之间找到观众可以接受的点,文本间强烈的对立感与张狂过度的消费性质所形成的张力,使观众明确消费惯性自身和影像本身之间的隔阂。[3]
影片中对于运气和宿命论表达十分突出,如杀手野狼这个人物的旅程,对于这个人物的过往经历与极端复仇情绪的塑造充分,给予他与重要反派角色相同的重视程度,但在他踏上列车后短时间内就被主角瓢虫的“运气”所秒杀,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电影对超惯性叙事表达的敏感性。影片打破了黑道手下西装革履的刻板印象,白死神的手下们携带冷热兵器,佩戴鬼武士的面具,将白死神及其领导的黑道塑造成鬼魅冷峻且危险的黑帮、直观让观众感受到杀气血腥的黑帮。(如图6)
电影中的拼贴感从美学风格到叙事手法都有体现,新人物的登场与重要的回忆插叙画面介入时,电影就会脱离主线将他的个体故事整体表达,将每个角色的魅力都汇聚到主线中。宿命论作为本部电影中主文本和惯性叙事与运气所代表的超惯性叙事间的对立与根本矛盾,为观众呈现出了超惯性叙事在表达上的魅力。
(二)黑色幽默与宿命哲思
《子弹列车》把列车作为空间载体完成了封闭叙事与非线性叙事的结合,让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关系通过命运的小转折点联系起来,在列车行进杀手们展开任务的同时,对回忆与真相进行插叙,杀手们的过往经历与现实情境形成了黑色幽默的对比,在对比中也将叙事递进推动。影片中不仅充斥着黑色幽默,采用多线叙事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离奇的反转,从叙事的结构来看,有明、暗、支三条故事线,搭建起影片超惯性的叙事模式。明线为瓢虫偷取钱箱的任务、双胞胎杀手对白死神儿子与钱箱的保护押运以及木村父子的私人复仇行动;暗线为杀手王子解决亲子矛盾杀父夺爱与白死神布局为爱妻复仇;支线则为杀手野狼错认凶手为妻复仇和杀手黄蜂为夺财下毒。电影主要围绕着明、暗的故事线推进展开,并未集中探讨杀戮伦理学,而是聚焦于“缘分”或者说“命运”,在诸多的离奇反转中讨论宿命论。杀手们踏上列车相遇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存在关联的,他们都与白死神的妻子的死亡有关系。
影片中对离奇的反转也做出精心的设计,杀手们用最炫的方法杀人,用最愚蠢的方法死去。对于反转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影片中的那瓶极富广告意味的苏打水,一个软广承担了电影中多次重要的叙事转折点,除此之外影片对于反转的设定都很特别,意料之外但也会在下文做出回应。《子弹列车》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的清算,人物间看似无关又相互关联的叙事处理让电影的叙事逻辑趋于稳定,为杀手们的行为赋予复杂的动机,围绕着“命运”的主题完成这场超惯性叙事,通过人物角色的言说,反复强调也佐证了电影关于宿命论的主题。
《子弹列车》完成在超惯性叙事的过程中,瓢虫的衰运也发展演变为了一种意外的好运,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在反转中保住生命,相反白死神在精心布局中死于非命。电影所表现出的黑色喜剧意味也同样是对命运的解读,命运的安排或许本身也是一场黑色喜剧。电影中的宿命论议题已不再新颖,最后都会引向对因果关系与人性善恶的沉思中,以此来彰显人生所追求的自由意志与面对命运之恶的崇高价值,呈现出自毁式的悲剧美学意味。[4]
影片采用揶揄的方式对命运的不可预知性进行消解与再表现,没有过多地强调人的贪念执着、血海深仇,也没有深入挖掘人物背后价值观念的纠葛矛盾,对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引向对命运的解读,导演对影片所传达出来的哲学意味的尺度进行把控,观众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超脱意味。影片中所选用的“瓢虫”这一概念,象征着东方哲学中禅宗意味的处世观,顺其自然而非精心布局,以此来应对不可预知的命运。影片片尾彩蛋的设计,充满了娱乐性,让观众在电影所讨论福祸相依和宿命论之外,获得一丝治愈。
《子弹列车》是一场用暴力和幽默对抗时空宿命的火车乱斗。对于宿命的讨论置于日式文化的背景中,是契合的,导演大卫·雷奇也将在疾驰列车上发生的杀手乱斗变成了一场关于对抗命运的闯关游戏。平衡暴力和幽默,将风格化的动作场面与黑色喜剧相结合,利用夸张的喜剧风格和叙事逻辑的混乱与失序,为主流动作电影遇到的叙事逻辑的困扰和限制,提供了合理化的可能性。[5] 电影在黑色喜剧的包装之下,加之暴力美学,并杂糅流行文化,使观众能在荒诞但不荒谬的现实情境中,感受瓢虫在宿命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徘徊,最终精准地捕捉荒谬与滑稽之间的忧伤,促成电影商业娱乐性与命运主题的融合,为动作片的表现形式做出良好补充。
作为一部融合黑色喜剧与动作类型的电影,《子弹列车》无论是从影片风格还是叙事模式上都做出了创新,影片没有只局限于列车装置性、对叙事递进能力,也利用超惯性叙事的模式在与文本强烈的对立分离感与张狂的消费性表达之间找到观众可以接受的点,用荒诞的列车杀手乱斗形式讨论宿命论,就像导演大卫·雷奇一直在动作电影中延续的暴力与幽默。[6] 电影的片头与结尾呼应,同一辆货车再次出现,颇有因果闭环的宿命轮回之感。
四、结语
电影《子弹列车》作为超惯性叙事评判标准下的典范性作品,呈现出了对目前主流文本超惯性叙事的高度敏锐意识,突破惯常以列车为主的影视作品的表达,赋予列车叙事以电影文本同一性与特异性的对抗表达的突破性意义。列车驶向固定的终点,影片的故事也被设定为一场“夺宝”之战,影片中的每个“乘客”都形成了对列车的疏远,影片快速华丽的展示也看似脱离主文本,但影片过载的对消费性质张狂的表达又使得观众聚焦消费惯性与影像本身间的隔阂,疏远与被拉回消费意图转盘的牵引力曲线,构成了超惯性叙事的经典表达模式。赛博朋克风格的视觉效果、流行文化的杂糅与黑色幽默相结合极具趣味性与夸张的华丽感,影片中个体与主文本间的对立分离感与关于宿命论的哲思,正对应着主文本和惯性叙事与超惯性叙事的隐喻、突破。
注 释:
①赛博朋克,是“控制论”与“朋克”的合成词。字面意思,就是对“高度机械文明”的反思。该背景大多描绘在未来,建立于“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结合”的基础上,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再以一定程度崩坏的社会结构做对比。
②Cult film/Cult Movie,是指某种在小圈子内被支持者喜爱及推崇的电影,指拍摄手法独特、题材诡异、剑走偏锋、风格异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富有争议性,通常是低成本制作,不以市场为主导的影片。简而言之,就是属于非主流领域却能在特定的年轻族群中大受欢迎的电影作品。
③超惯性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惯性的反叛,它保留了行为的惯性意味,但是它拒绝对惯性做出解读——即利用惯性熟悉度。它只是单纯的行为发生,保持它在情景下的原貌,即使我们相信这一行为是情景下的必然发生,动作是情景的惯性。
④霓虹美学(Neon Aesthetics),指在都市夜色中勾勒出的光影、色彩和线条,成为一种诉诸视觉的风格,發展出一系列的通俗娱乐文艺形式,例如小说绘画、电视和电影。
参考文献
[1]聂晶.密闭空间电影的叙事研究[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8.
[2]王玮莎.霓虹下的阴影:当代电影中霓虹黑色美学的兴起与数字时代的精神困境[J].当代电影,2022(01):58-65.
[3]斯宾诺莎画板.列车叙事的新可能--弹丸列车作为一部典范的超惯性叙事作品[EB/OL].(2022-08-06)[2023-11-22].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4559375/.
[4]董秋荣.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的悲剧美学意蕴[J].电影文学,2018(06): 150-151.
[5]谢爽.《奇爱博士》:黑色喜剧的荒诞与反讽[J].电影文学,2020(12):138-140.
[6]永乐.列车叙事的新可能——弹丸列车作为一部典范的超惯性叙事作品[EB/ OL].(2022-11-05)[2023-11-22].https:// zhuanlan.zhihu.com/p/576517730.
何 珊:上海戏剧学院电影文化研究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