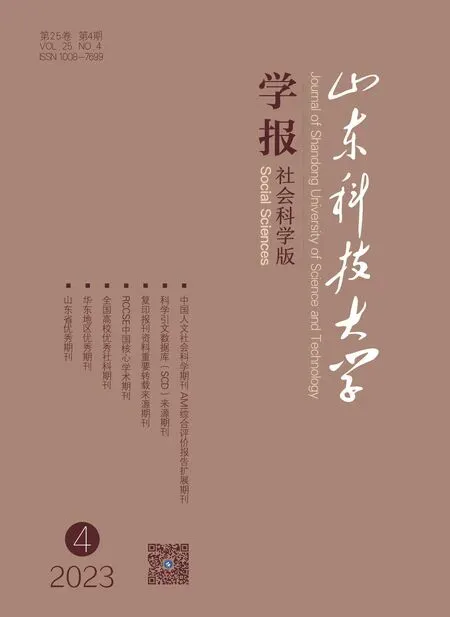“液态监控”下数字游牧民的“灵工”研究
——以手游公会劳动监控模式为例
2024-01-18李杭洋
杨 馨,李杭洋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12年,日本手游“扩散性百万亚瑟王”开始运营,开启了“二次元手游”的新纪元。十一年过去,中国的手游市场业已成熟,腾讯、网易等几大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手游市场,行业竞争日渐白热化。伴随着玩家群体的壮大,游戏充值也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成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玩手游成为娱乐化的消费行为,但笔者在日常游戏实践中发现,许多玩家并未在游戏中获得快乐与满足,反而萌生了“玩游戏如上班”的倦怠感。基于这一困惑,笔者于2020年起针对诸多玩家社群展开了线上民族志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对游戏“公会”这一特定的组织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游戏的劳动化趋势、公会无孔不入的“液态监视”促成了游戏玩家的准职业化,也让玩家在游戏中付出的情感劳动逐渐走向了异化。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
现阶段,围绕着游戏中的劳动问题,国内外均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尤以“玩工”“数字灵工”等议题与本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游戏与劳动控制相关研究亦对本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玩工”相关研究
自库克里奇(Julian Kucklich)提出“玩工”(playbor)的概念后,[1]游戏领域涌现了大量有关游戏劳动的研究。科尔曼(Sarah Coleman)、[2]约瑟夫(Daniel James Joseph)[3]等学者关注游戏公司对玩家开放源代码,鼓励玩家对代码进行修改、创新、开发,发布自己的“模组”,但公司与steam平台享有游戏版权与独占经营权,玩家无权通过游戏营利;或是关注游戏公司鼓励玩家深度互动与参与,发现游戏中的漏洞,提升游戏的质量与玩家体验。[4]而在国内学界,“玩工”的范畴更大、内涵更丰富,还包括游戏代练工作室、“私服”管理员等“技术劳动者”[5]69-70及游戏主播、陪玩等“情感劳动者”。现阶段,游戏劳动中存在着“游戏劳动化”[6]和“劳动游戏化”[7]两个维度的双向发展,游戏玩家被视为“产消合一者”[8]和“数据劳动者”[9],游戏公司可以攫取玩家私人信息,将玩家转化为执行无偿营销工作的“你媒体”[10]。其中,意大利自治主义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许多学者将之与霍奇斯柴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的社会学概念“emotional labor”相结合[11],将“以情感为驱动和成果”的劳动与“与情感为手段和工具”的劳动结合起来,研究游戏主播[12]、陪玩[13]这样的职业和半职业劳动者,他们产出的“成果”除了情感层面的成就感、荣誉感、满足感之外,还包括直接的经济收入和报酬,其代价则是强制性的情感输出导致的自我景观化,造成“主我”和“客我”分离和异化。[14]
(二)数字“灵工”相关研究
近年来,“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国外研究往往将“零工”(gig worker)视为随叫随到的“偶然”从业者,他们使用自备的工具和设备在平台上从事生产性劳动、提供各种附加服务,逐渐消解了传统的职业概念与雇佣标准[15];国内研究则更倾向于使用“灵工”这一翻译,强调其灵活性与创意性[16],董志强认为“互联网+”零工的规模与效率极度依赖数字平台发展,而“互联网×”灵工则源自数字媒体发展带来的打破物理空间限制[17],若照此思路,灵工研究可以包含数字化社会中的“斜杠青年”[18]和依靠平台流量获益的内容生产者[19]。尤其是对于“游戏灵工”来说,平台能让他们摆脱办公室、工位等“工作场所”的限制,在个人房间中随时心无旁骛地通过电脑、手机等电子介质连接至虚拟空间中,自身的生理、安全需求也能得到满足。[20]
(三)游戏劳动中的“控制”相关研究
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起,劳动控制就一直是工业生产的核心问题。进入数字时代后,各种新型劳动相继涌现,韩文龙将数字劳动分为数字化专业技术劳动、非技术数字化常规劳动、数字化众包劳动、数字化产消劳动四种类型,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同意控制、时间控制、算法控制、娱乐化控制四种控制策略。[21]游戏本身就蕴含着劳动控制的可能性,布洛维(Michael Buroway)将计件工作制称作“赶工游戏”,它“通过将劳动过程的‘游戏化处理’,掩盖工作中的劳动控制,营造出一种工人积极主动、努力工作的和谐氛围”[22],从而制造了工人的劳动同意。眼下,这种“赶工游戏”借助算法与平台的力量,扩展到了外卖骑手[23]、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24]与自由撰稿人、网络文学写手等“创意劳动者”[25]群体中。游戏化、娱乐化、精细化的控制形式让资本对劳动者的监控更加无孔不入,这种弥散的权力遭遇了游戏玩家这个特殊的社群之后,形成了一种“网络平台劳动者的自组织”。[26]
总的来说,在现阶段关于“玩工”或“数字灵工”的劳动控制的研究中,国外研究者通常侧重于平台通过版权协议等前置性制度对“玩工”进行的约束,批判往往重结构、轻个体;而国内研究者更关注专业游戏代练机构对从业者的管理与绩效考评,更强调“职业性”,而并未着眼于个体玩家的劳动如何被监控和整合,进而为游戏公司创造剩余价值,也尚未意识到游戏产业与平台经济之间密切的关联性。不过,得益于当代劳动控制领域中存在的“游戏化”倾向,还是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游戏实践与劳动控制之间潜在的同构性,这种隐含于游戏过程中的控制潜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聚焦个体的游戏实践、个体玩家与结构性的经济模式之间的互动过程。从2020年10月起,笔者加入了多个手游社群、线上交流平台、QQ群、微信群,以研究者与玩家的双重身份展开参与式观察,并向30位“深度玩家”(19位男性、11位女性,年龄在19—31岁之间)发出了访谈邀请,访谈以电话、微信语音的方式展开,每次持续90—120分钟,访谈结束后立刻对录音进行整理、编码、存储,访谈对象以主玩游戏首字母+访谈顺序的方式进行编号。这30位玩家全部加入了游戏公会,其中14位玩家在公会内担任会长或管理员,对公会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有着深入的认知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亦能代表玩家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模式。第一轮访谈结束后,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联系到了10位未成年玩家、5位游戏主播、15位游戏同人创作者,展开了第二轮访谈,多角度地了解手游玩家的情感劳动。
二、数字游牧民的组织化及其无酬劳动的异化
不同于传统电子游戏,手游对各网络平台有着极强的依附性,对平台经济存在着强烈的依存关系。因此,商业资本也能利用大数据和算法优势支配平台后端的游戏消费者,将其身份转化为“产消合一”的“玩工”,通过结交网络“同好”、分享游戏“攻略”知识、进行同人创作等方式参与平台建设的同时[27]136,亦通过直接的消费活动为游戏公司创造剩余价值。此时,玩家不仅是游曳于灰色地带的“文本盗猎者”,亦是与平台互惠共生的“游牧民”,其零星、灵活的劳动亦在平台这个双边(two-sided market)或多边市场(multiple-sided market)[28]中遭到游戏公司的收集、整合、量化,最终走向商品化与异化。
(一)游牧民如何走向组织?
“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的概念最早由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曼纳斯(David Manners)提出,他们认为智能技术能够将人们从标准化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作场所中解放出来,使之拥有更多闲暇时间,甚至能在旅行中远距离完成工作任务,实现休闲和生产、工作和娱乐的一体化。[29]而随着媒介环境愈发复杂,“数字游牧民”不仅能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同样亦可摇摆、穿梭在各个平台间[30],从事着多样化的情感劳动。以游戏玩家的同人创作为例,创作同人文、同人图、剪辑“二创”视频、制作游戏攻略解说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情感,这些实践都属于哈特、奈格里意义上的情感劳动。作为“游牧民”的玩家在不同的平台、“圈子”中“放牧”其情感,生产着快乐、激情、安宁等情感体验和共同体中的认同、归属感、自豪感。但玩家缺乏将劳动“变现”的正当性,与文本生产者即游戏公司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版权纠纷,玩家必须依赖平台为其提供庇护所。一方面,平台与游戏公司之间的产业集群或战略联盟关系使得游戏公司对平台上的同人创作格外包容,甚至付费购买优质同人作品以供游戏宣发和推广;另一方面,平台拥有远胜于个体的法务团队和避险能力,玩家相信只要服从平台规则与审查,就能“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们至少有阿B(Bilibili)罩着,阿B和游戏公司穿一条裤子的,版权啥的不是问题。”(Y2)
除了借助平台“收编”玩家之外,游戏公司还能借助“公会”对玩家施加直接、具体的控制。本文研究的“公会”并非组织化、职业化的代练机构或MCN机构,而是依托游戏内的“创建/加入公会”功能,由玩家自行建立、自行加入的“自组织”。创建公会的玩家即为“会长”,他可以任命多名“副会长/管理员”协助管理公会,公会成员皆为游戏玩家,会长、管理员与普通玩家之间为扁平式关系,彼此间可以形成直接的双边/多边互动关系。这种看似平等、包容、互动性强的公会关系在手游“氪金”文化[31]的驱动下,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异化,为游戏公司执行着整合玩家、塑造认同感的功能。具体来说,玩家信奉“又肝又氪”,即在游戏中付出劳动与付出金钱同等重要,这种付出从个人的美德演化成为组织的行为准则。因此,会长、管理员不仅拥有开启团队挑战、发布集体任务、发放任务奖励与“公会福利”的权利,也肩负着督促成员上线、监督成员完成集体任务,甚至是引导玩家充值消费的责任;玩家同样有义务配合公会的管理,每天上线完成日常任务、积极参与团队挑战、完成团队任务等。在日复一日的游戏实践中,玩家对游戏的认同度、忠诚度与社群归属感不断提升,被“肝氪”文化塑造为潜在的消费者,甚至有部分玩家是迫于公会内的群体压力而消费:
“我玩原神到现在没氪过金,就等钟离复刻了,岩王帝君我一定要拥有。”(Y7)
“水电(角色昵称)就是‘本地文件’,不抽(买)没人权。”(G1)
“会长今晚查Box,没抽NNK(角色昵称)的自觉退群哈!”(G4)
(二)从无酬劳动走向“产消合一”
在公会的组织下,玩家零散、灵活的情感劳动得以被整合起来,游走于不同平台的“游牧民”转化为一个集体,从“同好”社群中汲取意义与情感,再以无酬劳动和“产消合一”的“氪金”反哺了游戏与平台的商业价值再生产。无酬劳动(unpaid labor)或称免费劳动(free labor)的概念源自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泰拉诺瓦(Terranova)等学者对全职主妇家务劳动的研究,进入数字时代后,它拓展到了各个互联网领域与数字活动中,泛指一切创造了剩余价值却未获得报酬的劳动实践[32]。“产消合一”(prosumption)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在数字时代产生了异化,“产消合一者”(prosumer)同时扮演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在网络自由主义(cyber-libertarianism)的幌子下自愿地、愉悦地从事种种无酬劳动,以消费的方式创造剩余价值,服务于协同式双重剥削(synergistically doubly exploitative)[33]——玩家付费抽卡、分享游戏攻略、进行同人创作、自费制作并分发“无料”(免费的同人周边)等都是互联网平台中的“产消合一”行为。
除了直接的付费外,玩家也在为游戏与平台执行着免费的营销任务,例如,许多手游都会在各网络平台展开“UP主激励计划”,即鼓励主播、UP主直播游戏和制作游戏实况、攻略、同人视频等,并依据作品“热度”给予作者奖励,“奖品”多为游戏内的“稀有资源”。此类资源在游戏内通常需要付费购买或完成任务获取,因此,平台能够在“内容创作”与“获取游戏内资源”之间建立起并不牢靠的经济联系——“你本该付费购买它们,现在可以通过视频创作获取”——进而掩盖了这种“兑换率”中隐藏的剥削本质。而玩家亦满足于这种“互惠”关系,积极充当游戏“自来水”:
“我们‘用爱发电’,他们(游戏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大家心照不宣。”(G7)
“只要他们赚的钱能转化为我的游戏体验,我不介意给他们多送点钱……我甚至感觉很自豪,正是因为我氪了金,他才能做出这么好的游戏来。”(Y6)
这种“无酬劳动”正是斯迈兹(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在网络时代的延伸,玩家与平台、游戏公司之间的“游牧”关系更接近于弗里曼(Audrey Freedman)所描述的“非典型雇佣”(Atypical-employment),他们既非有身份保障的“单位人”,也非市场经济中的劳务派遣劳工,既不属于“企业-员工”模式,也不属于“派出单位-劳务输出”模式[34],而是更接近灵活工作、创意劳动的“灵工”。一方面,玩家不仅需要在游戏中充值,还得发挥聪明才智、提升游戏技巧、采取多种策略才能获得较佳的游戏体验;另一方面,玩家看似分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中,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登陆、登出游戏,就像一群“网络吉普赛人”一样游走于“产消合一”不同的平台与游戏之间,与游戏公司、网络平台也不存在经济依附关系,这就有别于“工作室”“代练”“陪玩”等组织化劳动的群体。但事实上,游戏公司借助“又肝又氪”文化与公会这一无孔不入的监控手段对玩家进行广泛的、液态的、无所不在的劳动控制,能够更加高效地动员玩家从事游戏实践,将玩家的情感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
三、公会——无处不在的液态监视
公会的运作模式在于,游戏公司设置了“联机战斗”“团队战斗”“集体活动”等方式将玩家组织起来,公会则借助玩家的自组织进行调度、施加监控,通过发布“限时任务”、制定梯度式“奖励”等方式鼓励玩家竞争,并引导玩家将公会关系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登陆游戏、参加“群聊”,加深玩家的情感连结,并借此将玩家的情感劳动置于普遍的液态监控之下。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公主连结”手游的公会会长(G3),他组织成员参加“公会战”的经历便生动地体现了公会对玩家的劳动控制。
(一)监控的液态化——作为“超级全景敞视监狱”的游戏公会
“公会战”是“公主连结”每月一次的核心玩法,每次活动持续6天,公会成员依次挑战5个Boss,所有Boss均被击败后进入下一轮挑战,每名玩家每日有3次挑战机会(“出刀”),每次耗时1分30秒,所有成员对Boss的伤害共同构成公会积分,并计入下月排名。每个Boss需要玩家配置不同角色阵容进行挑战,每个角色每天只可上场一次。玩家必须时刻关注整体挑战进度、“蹲守”适合自己挑战的Boss,以追求高伤害;会长等“管理层”则要通过QQ群或微信群协调、监督玩家“出刀”,避免“掉刀”(忘记挑战、浪费次数)。当然,G3要做的远不止这些:
“公会战开始前,我就得找好攻略,在群里通知所有人,给他们排好刀……晚上11点准时‘催刀’,Boss进下一面了也要在群里通知,不然就会有人抄错作业,然后‘挂树’(在挑战过程中点击暂停,等待队友救援)。”
“有人想出春黑刀的时候,我就得在群里盯着……Boss只剩层血皮的时候,还要找人合刀。有人挂树了我也得找人救,否则整个公会一起‘坐牢’。”
在每月为期6天的“公会战”时段内,G3的“管理”几乎时时刻刻弥散在公会成员之间,这种监控迥异于传统的劳动过程监控,几乎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办公场所-休闲娱乐场所之间的界线,形成了一种“超时空”的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35]“液态”即“流动性”(liquidity),意味着现代性带来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36],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数据库的普及,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逐渐转向了“后敞视”(post-panoptic),即罗格·克拉克(Roger Clarke)提出的“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或“精算监控”(actuarial surveillance)模式[37],构造了戴纳·戈登(Diana Gordon)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电子圆形监狱”和“超级圆形监狱”。流动的数据让监控蔓延到了无边界的动态空间之中,此时,权力动力机制不再是福柯提出的“规训”或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出的“控制”,而是通过消费、休闲、娱乐等“日常实践”的形式展开;不再是自上而下地控制某一主体,而是塑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化的“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38]。
同时,玩家也将“公会战”的规则和条件内化于心,自觉、自愿地配合公会监控,甚至彼此监控。基于微信、QQ等社交媒体,所有公会成员都处在数据宰制之下,他们的肉身体验被重新分解、提取为数据身体,重塑为规范化的游戏身体与数据身体,时刻处在后台“大他者”的监控之中。公会构成了内森·于尔根松(Nathan Jurgenson)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opticon),即“许多人监视许多人”[39],玩家不仅时刻自我审查与自我量化,还会积极督促、“敲打”公会内其他成员;作为“他者”的游戏公司与平台反而隐身了,能够以个性化、商品化、娱乐化的方式驯化玩家,甚至将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也转嫁到了公会身上:
“游戏里发‘工资’(奖励)的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发工资……看排名给大家发红包。上个月我们进了前2000,我在群里发了200红包,这个月能进前1500就再多发点……”(G3)
在公会无孔不入的监控之下,玩家从自由自在的“游牧民”转变为被放牧的“羊群”,被置于游戏公司与平台的数字牧领之下。事实上,劳动监控作为资本剥削劳动者的必要手段,必将导致工人阶级疏远于其生产工具、劳动成果,成为生产线上驯服的“螺丝钉”,最终疏远于其“类本质”,走向商品化与异化。而依托数字技术带来的液态监控,异化的过程被简化和加速了,玩家只要接入互联网,其游戏实践立刻被转化为数据,接受公开的量化管理。换言之,数据化的指标取代了玩家鲜活的游戏体验、乐趣与满足感,成为了一种“绩效考核”的手段,亦将玩家转化为了“数字工厂”中永无休止的劳工。
(二)数字牧领与权力的毛细血管化
权力已经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的弥散状态,尤其是在游戏公会这种高度圈群化、封闭化、组织化的亚文化社群中,“毛细血管”式的权力极易形成一种“数字牧领”关系。[40]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原本是一个宗教概念,它被认为是整个西方近代治理术的原型和母题[41],在福柯看来,这种“向善”和“个人化”(individualisation)的治理技术在近代化之后被异化为“屈从化”(subjectivation)[42],分解了个体身份,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臣服。而随着数字技术对个体生活的“深度浸入”,数字技术成为新的“牧羊人”,亦成为了分配个体化与主体权力的新途径。“数字牧领”不仅意味着借由数字技术与网络实践分配权力,更重要的是个体被数字技术渗透,毛细血管式的权力产生了再度中心化的可能性,以一种超越性和象征性的形式集中于“代理者”手中。
在游戏公会中,牧领关系的宗教隐喻被包装为一种自由、自主、自愿的竞争与合作,会长与管理员如同牧羊人,承担着“上传下达”的职责。在福柯看来,牧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日常行为的指导,这种指导的本质是在日常实践中不断“调整”个体以达成对个体的“教化”——会长对公会成员(尤其是新手)负有指导“义务”。以G3为例,他为玩家提供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层面的指导,例如,手把手地教玩家如何操作、为玩家提供“参考作业”、提醒玩家卡等级与“Rank”(部分角色保持低等级、低品级能获得更高收益);他还需要向玩家提供“情感按摩”,维系公会内的友好氛围、纾解玩家的焦虑与压力、动员玩家积极参与活动:
“平时也要干活,不能扔着公会不管,要是平时人心散了,公会也就没法管了。平时就……给大家找找攻略……一起吹吹水(聊天)。”(G3)
而普通玩家如同被放牧的“羊群”,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游玩时间与游戏知识,只能跟随会长日复一日地进行游戏实践。数字牧领的“普遍原则”在玩家之中树立了一种服从的典范,甚至在公会中形成了一种类似“新教伦理”的职业精神:以服从、勤奋、克制为美德。这种精神与“又肝又氪”文化的结合,将数字牧领关系包装为一种基于兴趣的“合作”,“牧羊人”与“羊群”之间形成了一种轻松的、友好的依赖关系,流动的监视也被包裹上温情脉脉的外衣,合理化为一种“互助”与“共享”。扁平的公会结构逐渐演变为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衍生出一种高度控制的“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 Taylorism)[43]。
(三)手游玩家的准职业化
在牧领关系中,“羊群”对“牧羊人”的依赖源于寻求“救赎”的可能性。电子游戏长期被视为“电子海洛因”,玩家也常常被指责“不务正业”“玩物丧志”[44],很难从“玩家”身份中获取职业认同与尊严的“救赎”。因此,不少玩家会选择成为代练、陪玩、全职主播,将游戏行为转化为职业劳动,以“技术”赚取经济收益,赢得他人对这份“职业”的理解、支持或尊敬;更多的玩家则会通过提升技术、投入金钱、构建同好群体等方式塑造群体认同[5]62-67:
“在游戏里还有人喊我一声大哥,退出游戏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YY4)
正基于此,玩家的“产消合一”压力与日俱增,甚至面临着“准职业化”的身份焦虑。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玩家都面临着“打游戏如上班”的烦恼,他们不仅需要每天打卡、完成每日任务,还要应对公会制定的“绩效”;另一方面,玩家从平台获得的“创作激励”与会长提供的“工资”都非常微薄,与他们的“付出”并不相称,反而需要在游戏中付费购买增值服务与游戏体验。换言之,玩家根本无法通过经济收入获取尊严与满足,追求的“救赎”就变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他们越是按照“职业化”标准来规训自身的游戏实践,按时登陆游戏“打卡上班”、积极完成游戏内“KPI”、服从“领导”考核、维护好“同事”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就越是陷在这种不公平的经济模式中难以脱身。
四、张力的多重生产——劳动异化、劳资矛盾与权力结构
尽管不少玩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不公平的“产消合一”模式,却仍囿于与游戏、其他玩家的情感连结,无法从复杂的牧领关系中脱身。事实上,玩家与游戏公司、网络平台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的多重张力,这种张力模式贯穿了文化、经济模式与权力结构,由玩家的游戏实践再生产构建了一套复杂的亚文化体系。
(一)第一重张力——情感劳动的“异化”与“解放”悖论
根据哈特、奈格里的观点,情感劳动本质上属于“非物质劳动”的范畴,劳动的驱动力是非物质的情感与创意,劳动的产品也是情感层面的满足感、认同感,包括劳动者的主体性、社会网络关系与生命权利。[45]而在笔者接触的玩家群体中,确实有不少玩家通过情感劳动获得了认同感、话语权,他们通过“氪金”“冲榜”成为了游戏内备受尊敬的“大佬”,或是通过同人创作成为了玩家社群中拥有话语权的“大触”(指优秀的画师或同人作者),或是通过制作游戏攻略、分享通关技巧成为了游戏圈的“赛博保姆”。他们获得的“救赎”——认同、尊严、话语权对于玩家来说属于“稀缺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弱权乃至失权状态的青年玩家在“游戏圈”内反而拥有“一技之长”,能够凭借劳动获取尊重,这种意义的生产在青年玩家眼中的价值远胜过经济报酬。因此,许多玩家即使意识到了情感劳动的异化,仍然心甘情愿地继续着“又肝又氪”的游戏实践:
“氪金就能变强,别人就会崇拜我……为这种感觉花钱是值得的,你们可能会觉得游戏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我能买到快乐的体验,这个是真的。”(G1)
笔者提倡跳出“异化—解放”的二元结构,以一种更加辩证、包容的眼光看待玩家的游戏实践。玩家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话语权的缺失、尊严感与满足感的匮乏,不得不在虚拟场域中寻求替代性满足。在游戏中,玩家尚有“氪金改命”的权利,而在现实中,面对不断内卷的社会与学业、事业、生活中激增的压力,青年人往往无可奈何,他们的真实感受应当得到正视与尊重,抛开个体真实的感受空谈“异化”或“解放”并不能产生有效的批判意义。
(二)第二重张力——劳资矛盾的具象化
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产品,游戏的本质是数字化的代码和数值,它提供给玩家的商品和服务本就是数据性的,在游戏策划与程序员编写代码、设定数值之后,游戏产品可以被无数次重复传播和使用,游戏的剩余价值就能够无限复制。游戏公司生产数据商品的“成本”主要是购买技术劳动力(雇佣员工)和生产资料(购置设备)的支出[46],数据产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复制与增加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能够实现“零投入”增长。但对玩家而言,这些数据并非“免费午餐”,游戏中的娱乐、消遣、增值服务都需要付费购买,“产消合一”的经济模式与“又肝又氪”文化形成同构,将玩家置于复杂的劳资关系中:
“别的消费者是上帝,我们玩家花了钱还得给游戏公司当牛做马……”(Y4)
通常来说,平台经济中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方式主要有三种[27]138:传统的“雇佣劳动者”未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半雇佣劳动者”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处于雇佣结构中的“中层”,但关键性生产资料仍掌握在平台、资本手中;“劳资共享型劳动者”则处于雇佣结构中的“上层”,拥有重要知识型生产资料。游戏玩家群体杂糅了上述三种劳动者,玩家的情感劳动与游戏公司雇佣的策划、美工、程序员、工程师的数字劳动,以及“代练”“陪玩”等参与的平台零工劳动交织在一起,构筑了一种颇为复杂的劳动关系,使得“玩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一个极其复杂、难以衡量的问题。
若从版权、著作权的角度来看,游戏内的一切数据信息属于游戏公司,玩家只拥有账号的使用权,根据用户协议、隐私协议,他们在游戏内生产的一切信息的所有权也被让渡给游戏公司。当制作游戏攻略或二次创作同人作品需要对游戏内图像、音乐素材进行编辑加工时,玩家反而要得到游戏公司的授权许可,这就为玩家的情感劳动施加了“缰绳”,在要求玩家遵守版权规约的同时,也合理化了游戏与平台审查玩家作品、征用“二创”展开营销活动等行为:
“官方现在天天转发同人作品,拿太太(创作者)们当免费的宣传工具人。”(YY1)
“天天就知道找UP主买推广,为什么就不能干脆给咱们多发点原石(原神中的抽卡货币)呢?”(Y4)
换言之,除了极少数自主创作的个体(如外包画师)之外,绝大多数玩家只是向游戏公司“租借”了游戏账号及其内容,包括游戏内数据、同人作品在内的劳动成果皆归属于游戏公司,若无版权方的授权,玩家并没有将这些成果“变现”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普通“游牧民”玩家更加依赖平台提供的“庇护”,有变现能力的创作者也渐渐与平台、游戏公司形成经济依附关系,许多全职画手、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游戏公司支付的报酬,这份由游戏公司约稿主导的收入极不稳定,且劳动者无法与公司签订长期有效的劳动合同,短期或单次的劳务关系也很难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畴,劳动者客观上成为了斯坦丁(Guy Standing)所谓的“朝不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47]。
(三)第三重张力——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在扁平的公会关系转向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后,牧领关系逐渐从公会内部辐射到了整个游戏产业中,游戏公司与公会、成员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金字塔,会长作为权力具象化的“代行者”受游戏公司的委托对玩家进行管理,他们手中原本并无实权,同样缺乏将自己的“管理”劳动变现的合法性。但在日复一日的游戏实践中,毛细血管式的微观权力不断向会长和管理员手中汇集,最终形成了科层式的集中权力——会长管理副会长/管理员,副会长/管理员管理普通玩家。在田野研究过程中,许多玩家向笔者抱怨,他们的会长态度苛刻、独断专行,甚至在对玩家进行绩效考核时恶语伤人:
“催我可以理解,直接‘问候’我父母家人是不是就过分了?”(YY2)
“我又不是故意掉刀的,毕业季事情多,偶尔忘记一两次也是正常的吧?动不动就威胁要把我踢出公会,拜托,这只是游戏而已啊!”(G6)
与之相应地,玩家也与管理者玩起了“猫鼠游戏”,以种种“技巧”逃避管理,例如:假装掉线、在QQ群中保持沉默甚至直接“玩失踪”、找其他成员“代刀”等。笔者还见证过一位拥有技术的玩家(G2)在日常游戏实践中逐渐积累起话语权,笼络了一批“亲信”,共同向会长施压,最终率领“亲信”出走,将原公会“掏空”: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也不知道他(会长)狂什么,我走了谁给他打轴?等下个月排名掉了,他自然会来求我回来的。”(G2)
事实上,“制衡”会长也是公会赋予玩家的一种微观权利,玩家能够监督会长、管理员,可以选择退出公会、转投其他公会,部分游戏甚至为玩家提供了投票“罢免”会长的选项,这一功能宛如悬在会长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促使其兢兢业业地履行职责:
“我没空的时间就让我老婆登我的号,帮我开道馆和麒麟……如果我老婆也没空,我就得在群里找副会帮忙……真就跟上班一样。”(YY1)
可见,金字塔式的数字牧领关系是动态的、生成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公会结构可能会分裂和解体,“牧羊人”也会失权甚至被罢免,但新的数字牧领结构始终不断地生成着——“出走”的玩家组建了新公会后,仍复制原有的权力结构,玩家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场所继续从事着情感劳动,其劳动成果也继续被游戏公司与平台征用,转化为剩余价值。换言之,亚文化圈层同样复制着主流社会的权力结构,且这种权力结构始终处在持续不断的再生产中。正因如此,这种权力关系能够持久、稳固地存在于游戏产业与玩家群体之中。
五、路在何方?——非异化的情感劳动将何去何从
在无孔不入的“液态监控”与数字牧领关系下,游戏玩家的情感劳动已经脱离了哈特、奈格里所设想的“主体性劳动”的轨道,而出现了集中化、商品化的趋势,强化了“数字游牧民”对平台与公司的依附性,让玩家的情感劳动逐渐走向异化。
不过,在以往关于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中,批判的矛头往往对准了作为“大他者”的商业资本,将劳动者视为“沉默的羔羊”,处在任人宰割的被动位置上。这种宏观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的鲜活经验,将“人”置于僵化的阐释框架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研究初衷与现实关切。事实上,玩家的游戏实践有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即便是“退坑”“弃游”等“消极”举动亦可折射出青年人的情感空间与生活态度,因此,研究宜聚焦个体,以包容、动态的眼光看待玩家的游戏实践。
相较而言,更令人担忧的是遗落于批判视野之外的“小”与“老”。一方面,手游玩家群体中存在着不少未成年玩家,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若缺乏引导,极易在“又肝又氪”的社群文化的诱导下产生不恰当的消费行为。近期,“未成年人盗用父母账户充值游戏”“贷款玩原神”等新闻不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动态的数字牧领权力结构中,玩家毫无疑问属于弱势的一方,游戏公司与平台本该承担起更多的引导责任,但一味逐利的市场加剧了这种不公平的经济模式,玩家看似可以在不同的游戏、平台之间选择,实际上却囿于同样的剥削逻辑中,不断倾注时间、精力、金钱。如此一来,玩家的情感劳动是否还存在着摆脱异化、回归主体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老年手游市场同样发展蓬勃。中老年人同样属于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权”的群体,同样有着复杂、饱满的情感需求,且据笔者观察,中老年玩家更依赖游戏内的“同好”社群,与游戏内好友、公会成员的互动更为密切,但他们的情感诉求、劳动形态、消费模式显然有别于青少年玩家,仍有待学界同仁展开更为详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