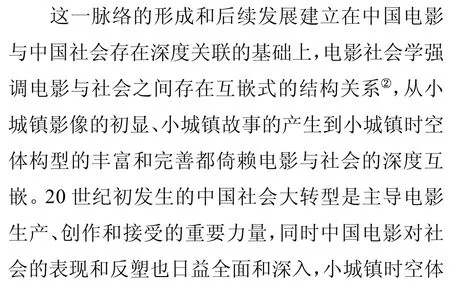《张欣生》与中国小城镇电影的发生
2024-01-16孟君
孟君
(武汉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以卢米埃尔兄弟著名的放映活动为标志,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 年的巴黎,电影的原初事件指向一个独特的社会时空体:一方面,自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电影摄影、洗印和放映术的发明是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作为彼时最重要的现代大都市,巴黎充斥着流行文化的神话,电影的崛起正是都市消费社会中一个日趋显著的神话。中国电影诞生时的情形有所不同,中国电影发轫于1905 年的北京,其时空体的构型更为复杂,中国电影的发生是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和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中国电影最初的拍摄对象、观众反应和社会影响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原因。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文明为主导的乡土社会,鸦片战争后五口开埠,促使19 世纪中期开始中国被迫从内向型经济逐渐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城市文明也逐渐在上海、广州、厦门、宁波、福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发端并繁盛起来,至20 世纪初乡村和城市成为中国主要的两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因而乡村和城市在中国电影发生期得以反复描述。然而,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存在作为“第三种社会”的小城镇,如同小城镇在社会形态上被忽视一样,早期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图廓清早期中国电影中藏匿在城市故事和乡村故事里的小城镇,探究隐约、斑驳的小城镇影像如何展露彼时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并逐渐形成独立和丰富的小城镇电影时空体。
电影是社会的历史镜像,不同时期的电影技术、电影创作、电影传播和电影接受与其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社会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作用于电影,同时电影的制作和放映也反作用于社会,20 世纪初中国电影与社会现实的深度互嵌是探究中国电影发生期诸种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可将电影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要全面考察中国电影何以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应将电影放置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场域中加以分析。同样,要理解小城镇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被如何叙述以及为何如此叙述,也应厘清彼时的社会语境对电影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将电影视为富有价值的历史证据,正如英国学者彼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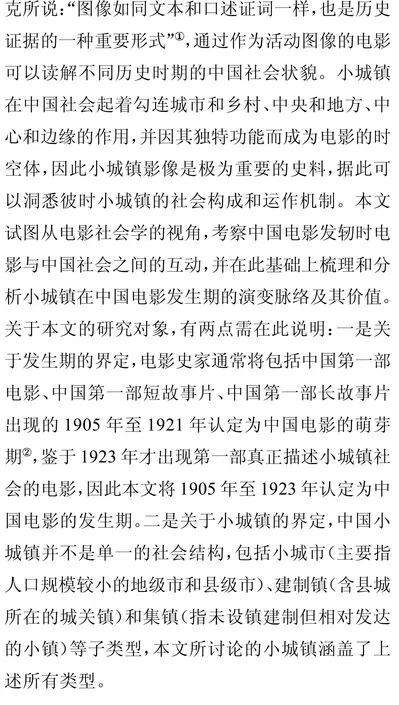
一、小城镇影像的初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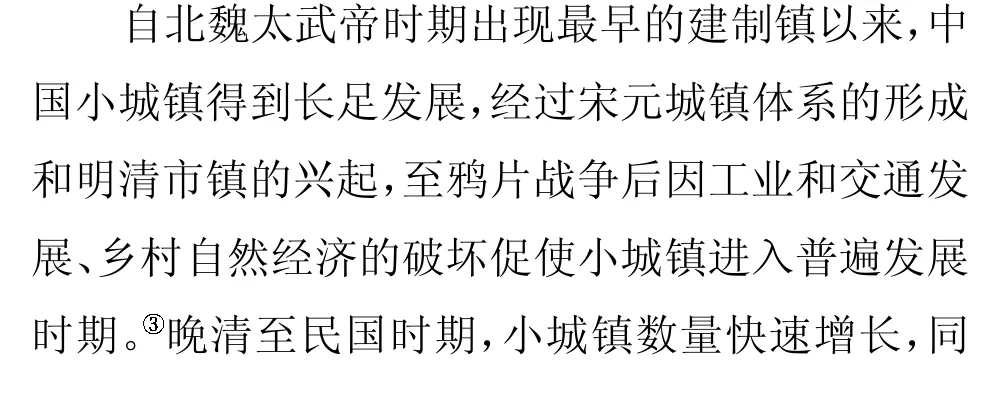
媒婆也是一个别有意味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婚姻为纽带而成为地方社会关系的枢纽。因此,媒婆的社会影响力也不限于乡村,而是辐射至更为广泛的市镇区域,在地方社会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起着建构和维护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郑正秋所批判的包办婚姻习俗就会发现,《难夫难妻》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故事,而是通过婚姻悲剧来审视乡土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影片的创作时间1913 年而言,这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夕在电影中出现的“个人的觉醒”,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城市。由于富绅和媒婆活动的区域无法将乡村与城镇完全剥离开,因此将其叙事空间视为与城市相对立、以乡村为主体涵盖城镇的地方区域更为恰当。借此本文认为,可以将《难夫难妻》视为小城镇影像的萌芽,它以乡村为主体映射城镇,通过富绅家族的婚姻故事展现了乡村与城镇的社会状况。
与《难夫难妻》从乡村辐射小城镇的乡村故事相反,任彭年分别于1920 年和1921 年导演的《车中盗》和《阎瑞生》讲述了以城市为主体辐射城镇的都市故事。
以上对《难夫难妻》和《车中盗》《阎瑞生》的分析显示,从1913 年至1922 年小城镇影像在中国电影中已经初现端倪,尽管这些影像尚显模糊和边缘化,但已经准确地表现了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镇所具有的中间性。《难夫难妻》中小城镇是乡村的辅助视点,《车中盗》和《阎瑞生》中小城镇是城市的外延投射,它们揭示了小城镇作为外部参照和缓冲中介的独特性质。小城镇在电影中的显影具有重要意义,其价值在于发生期的中国电影从乡村和城市的外部视点对小城镇的社会属性进行了界定和描述,但这种表述显然较为简单和粗糙,小城镇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时空体是在《张欣生》中才得以全面建构。
二、小城镇故事的产生与小镇中心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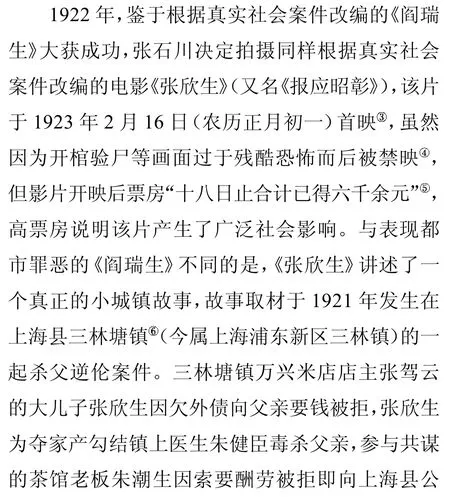
署告发张欣生,县公署当日便“备文饬采”派遣警察缉拿张欣生归案,后经开棺验尸取证判处张欣生、朱健臣、朱潮生三人死刑。
《阎瑞生》和《张欣生》有起意谋财、杀人逃逸、缉拿判处的相同故事主线,表达了欲望与罪恶的现代主题,但是仔细堪比便可发现两部影片存在诸多差异。《张欣生》的空间叙事图谱与《阎瑞生》相反,凶杀案件发生在小镇,主人公从小镇逃亡上海。从上海市区到郊区小镇并非仅是叙事空间的简单挪移,而是反映了中国电影与社会变迁的趋近与同步,影片首次正视了小城镇在城乡之外的独立构成和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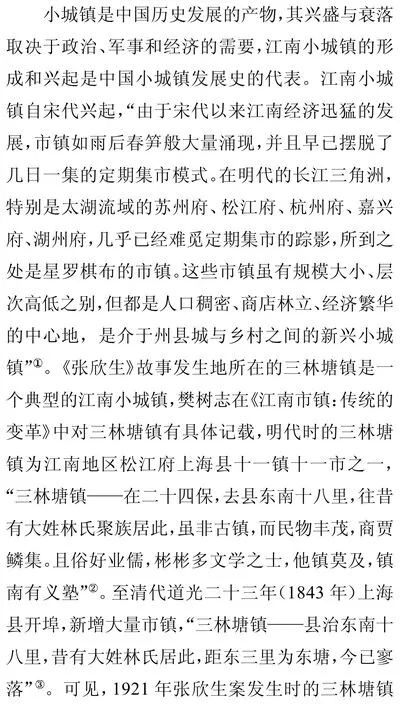
米店、茶馆、当铺等店铺的兴旺说明三林塘镇“民物丰茂,商贾鳞集”,发达的经济活动体现了小镇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作用,但小镇的功能并不止于此。影片中有两处赎田单的次要情节,王阿大向张驾云赎田单被拒、朱潮生向张驾云赎田单亦被拒,两次出现赎田单情节说明张驾云还从事乡村土地租赁和买卖。张驾云这样的地主或富绅来自乡村,但在经济上并未脱离乡村,赎田单情节表明小镇和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小镇存在多样化的贸易活动,影片充分体现了民国初期江南小镇复杂的经济状况和相应的社会交往。
经济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关系,《张欣生》弑父故事揭示了小镇兴旺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对传统伦理的破坏。《张欣生》与《阎瑞生》都通过谋财害命案件来阐释欲望与谋杀主题,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呈现小镇社会传统家庭伦理困境的“显微镜”,后者是揭示都市社会“陌生人”危险性的“万花筒”。与都市社会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契约关系不同,小镇社会由熟人构成的传统伦理关系植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阎瑞生杀害的是都市“陌生人”,揭示了契约关系在维持社会伦理和规范上的局限,张欣生杀害的是自己的父亲,破坏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层,即标志社会伦理底线的父子伦理关系。小镇是弥补乡村贸易不足的经济结构,它既在经济上发展现代商品贸易又在文化上恪守乡土社会传统,经济的繁荣趋向和文化的保守趋向在有限的空间里时常发生冲突,这正是《张欣生》弑父故事指出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小城镇面临的巨大障碍,即在现代经济的刺激下家庭伦理与金钱欲望冲突的爆发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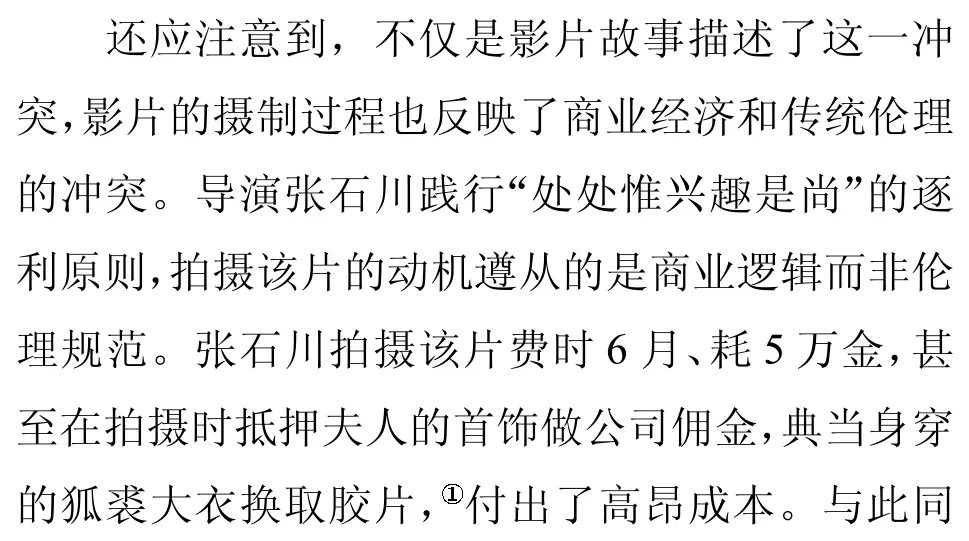
因此,影片的内容和摄制都指出了商业逻辑的胜利和局限,一方面商业经济破坏了传统伦理的规训,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伦理也抵抗着商业经济的冲击。《张欣生》深刻地洞悉了20 世纪初中国小镇社会的吊诡之处,即经济的繁荣对小镇的乡土社会基础产生挑战和破坏,同时嵌入中国社会肌理的传统伦理对这种破坏进行着抵抗和修复,这是基于传统伦理秩序的乡村文明和基于现代社会秩序的城市文明在小镇发生的较量。
电影是现代社会的神话。《阎瑞生》讲述了都市上海的光怪陆离、千变万化,问题丛生的都市的出路是小镇和旷野,与之相反,《张欣生》讲述了张欣生弑父后从三林塘镇逃往上海等地的小镇故事,这是一个以小镇为中心视点向都市辐射的中国故事,因其视点的转换、小镇生活的描绘和小镇社会的分析而具有重要的电影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价值。如果说以《定军山》为标志的第一批戏曲短片是对中国传统的复古,以《难夫难妻》《阎瑞生》为标志的早期故事片表现了20 世纪初期现代性观念影响下的乡村和城市,那么《张欣生》则是对彼时中国小镇社会的深度描摹,影片展现了现代与传统、经济与文化、小镇与城乡之间交融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欣生》是最早完整描摹小城镇社会的中国电影,这个小城镇故事为中国电影建构了一个最早的具有独立构型和叙事功能的小城镇时空体。
三、小城镇时空体的雏形与复杂构型

在《难夫难妻》和《车中盗》《阎瑞生》中,小城镇是以乡村和城市为中心视点的外部参照,具有次要的叙事功能。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小城镇是乡村富绅和地主的聚集地,在经济贸易、行政管理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对乡村产生影响,《难夫难妻》表现了象征着传统社会制度的包办婚姻习俗对乡村社会和作为外部参照的城镇的作用。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小城镇也和城市产生关联,《车中盗》《阎瑞生》中虚构和真实的故事在电影中被时空化,远方的城镇是都市收缩和内卷的释放途径。无论是乡村故事还是城市故事,小城镇在这些影片中都只是辅助性的外部参照物,直到《张欣生》中小城镇才真正成为电影的中心和枢纽。
作为一个独立的时空体,《张欣生》中的小镇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构型,这一构型突出小镇在影片中的主导和支配性地位,体现为它赋予时空体所特有的情节意义和描绘意义。与《阎瑞生》情节上贯穿始终的空间流动性相比,小城镇空间是张欣生弑父的故事驱动力,同时也使得故事在情节上具备时空浓缩、矛盾集中、冲突激烈的特征。影片中1913 年的三林塘镇是一个封闭的时空体,与弑父案相关的人物和情节围绕经济因素形成紧张的关系,张欣生父子间索要和被拒的情节反复递增产生向外的扩张力量,而封闭的小城镇时空体形成向内的约束力量,两种力量的对峙最终激发出欲望与罪恶的爆发。与此同时,《张欣生》对中国小镇的社会生活加以细致生动的描绘,应和了早期中国电影逐步趋近社会现实的发展趋势。1905 年到1908 年京剧短片时期的电影内容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出脱节状态,自1913 年开始《难夫难妻》《打城隍》《黑籍冤魂》等第一批短故事片中的空间场景具有静态、抽象的舞台化特征,即使是1920 年的《车中盗》和1922 年的《劳工之爱情》中空间场景仍然是颇为粗陋的,到1921 年的《阎瑞生》和1923 年的《张欣生》中社会生活场景已能再现现实并具有修辞功能。《张欣生》中的小城镇生活真实而生动,米店、茶馆、当铺等店铺活跃的商品贸易反映了小镇社会最为根本的经济属性,以张欣生为中心的人物关系构成了小镇社会的熟人网络,张欣生父子、兄弟、夫妻的家庭关系和冲突展现了小镇社会的伦理危机,被详细描绘的小镇在影片中具有主导性的修辞功能,它驱动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并阐释故事的归因和结果。
《张欣生》已初步生产了一个小城镇时空体的雏形,但小城镇是一个远非某个具体时刻的小镇可以涵盖的复杂构型。从空间上来说,中国小城镇包括小城市、县城、市镇和集镇等多种类别,它们各自的历史发展和实际功能并不相同。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行政机构上至京城下至地方各府州县,县是行政机构和权力的末端,包括县城在内的“城”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政治构型。市镇则由从事贸易活动的集市发展而来,“镇”主要是作为贸易中心而存在的经济构型。中国的小城镇根据其性质和功能可以区分为上述多元构成,《张欣生》的小镇时空体显然不能涵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和不同地域的小城镇。从时间上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与“镇”各自的政治和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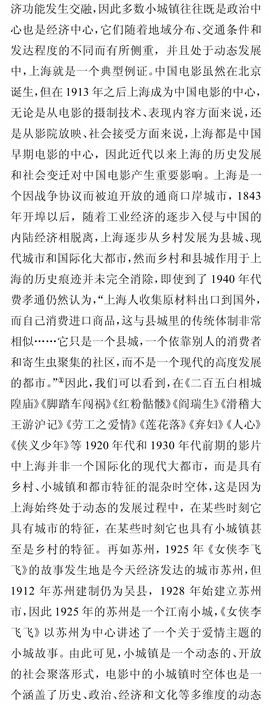
复杂构型。
毫无疑问,《张欣生》建构了一个具有重要电影史价值、社会史价值和文化史价值的小城镇时空体,真实再现了1920 年代初期的江南小镇社会,但就历史发展的纵向层面、地域社会的横向层面而言这一构型还远不充分,小城镇时空体随着小城镇的社会变迁处于一个不断建构和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譬如,1925 年的《小朋友》、1926 年的《芦花余恨》和1927 年的《真假千金》均以乡绅和富商阶层为主要人物,又分别以情节剧的形式解析家庭、婚姻、教育等种种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张欣生》之后的小城镇电影始终围绕小城镇作为经济中心这一根本,从不同角度对小城镇时空体进行丰富和完善。此后,不同时期电影中的小城镇卷入中国波云诡谲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巨变,经济属性逐渐让位于战争、民族、政治和现代化等属性,产生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小城镇时空体构型。
结语
自1913 年中国电影转向现实社会开始,作为社会重要构成的小城镇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电影的叙事空间。考察发生期的中国电影可以发现,从《难夫难妻》《车中盗》《阎瑞生》到《张欣生》再到《女侠李飞飞》《小朋友》《芦花余恨》《真假千金》,中国电影中的小城镇逐步形成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中心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