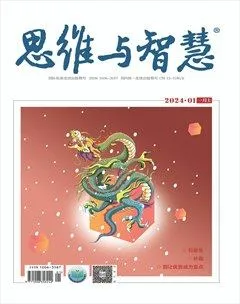炊烟蔽野
2024-01-15卢海娟
卢海娟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说来可笑,年少时,一边读书一边帮父母干农活,只觉得日子清苦、忙乱。记忆之中既没见过火红的枫叶,更不曾站在渐来的薄暮里看晚风中的袅袅炊烟。
“咱家烟囱冒烟了。”这话肯定说过无数次,带着食物近在眼前的兴奋。炊烟是怎样慢慢升起,又是怎样诗意地变成乡村的吐纳——我一概不知,只知道,烟囱冒烟了,母亲已经做晚饭了,狼奔豕突的一天,饥饿的肚皮,疲惫的身体,让我们的眼神自动过滤一切繁文缛节,我看不见炊烟,只想冲破呛人的烟雾,找到可以疗饥的简单食物。
贫困窘迫的岁月,不容许滋长来自天籁的诗意情怀。
但我却看过早晨的炊烟。
读初中时,我是走读生,要走十二里山路去乡政府所在的较大村庄上学。
夏末秋初,爬过山岗,穿过稻田,走过玉米的青纱帐,再一路向上,攀上一个高坡,我们称之为大营坎上——那个名叫碱厂的村庄便出现在眼前。
居高临下,满眼都是灰瓦的屋顶,和屋顶上白练一样的炊烟。我的学校在村庄的西侧,连着一片碧绿的稻田。
炊烟像涨潮的洪水,丝丝缕缕,覆盖了整个村庄,连同我的校园,连同庄稼地和远方的青龙山。那炊烟并不把根扎在烟囱上,它们横卧在村庄的上空,跟晨雾纠缠在一起,雾中有烟,烟中有雾,彼此绞扭着,搂抱着,这儿一缕,那儿一片,它们被雾编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云,像仙女织成的素锦,悬垂在村庄上空,却爬不到浅蓝色的天幕。
炊烟在村庄上空游动,像鱼儿游在山坳的水里,那些错落的灰瓦的屋顶全都成了水里垫底的碎石。
烟雾萦绕到林间,给翠绿赭红系上白罗裙,山峦翩翩,舞得直向云端。
“田舍炊烟常蔽野,居民安堵不离乡。”每一天,匆匆走到坎上,望见村庄,望见炊烟,望见我的校园,我都会无端激动起来。独走山路的恐惧与焦慮烟消云散,勾起嘴角,一路飞奔到教室,开启年少岁月最美好的一天。
早上看炊烟,肚子不饿,时间充裕,有足够的从容享受这短暂的清闲。
冬天,炊烟无处藏身,它们簌簌地从披霜戴雪的烟囱里爬出来,只露个胖乎乎的脑袋,把烟囱当成保暖的冬衣。偶尔被谁推出细小的一缕,像是出来打探的小童,怯怯地,抄着手,随时准备逃回烟囱。
也会有那么一缕,大概被烟囱里的谁踢了一脚,“噌”地蹿出来,旁逸而去。那么冷,那么湿,又那么热气腾腾。
等到零下三十摄氏度时,炊烟冷得连腰也弯不下了,它们直通通从烟囱里升出来,笔直地奔向泼了釉彩的景泰蓝的天空。
白雪覆盖了屋顶,白的炊烟直冲云霄,架起人间天上的通途。
冬天的炊烟最纯粹,也最有趣。
“炊烟一点孤村迥,娇云敛尽天容净。”炊烟纯净了村庄,收纳了乡愁。诗人说,炊烟是村庄升起来的云朵,一如白云出岫;是柴草灶火化成的幽魂,牵着游子无尽的相思;是村庄的声息和呼吸,滋养生命的根脉……
多想再走一走那苍苔盈阶、落花满径的村路,再看一看坎下的袅袅炊烟。多想回到父母的屋檐下,他们不老不病,而我们,也不曾长大……
炊烟蔽野,往事如风。最难忘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编辑 兔咪/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