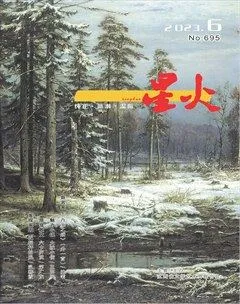长在别人嘴上的名字
2024-01-15范雪明
范雪明,江西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小说月刊》《星火》《安徽文学》《南方文学》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桃花流水》。
名字是别人叫的。对叔曾经对一个叫严二哥的同事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严二哥真名叫严春雷,当过剧团乐队队长,剧团剧院分家后,他被安排在剧院经理的位置上。遇上有名角担纲的大戏来罗城演出,前来求票者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地位高低,有意撇开他实名和官衔,无一例外地称他严二哥。一声严二哥拉近了彼此间距离。如果叫他严老二,差别那就大了。严二哥心里明白,是别人对他的态度决定了这个称呼,他想拒绝都找不出理由。对叔却没有严二哥这么好的福气,他无法左右别人的态度,每个名字的由来总是身不由己。
对叔第一个名字叫狗伢,学名皮金狗。其实对叔对这个名字比较反感,一度不愿接受。瞎子爸说,名字里带牛啊狗的能避灾躲难,一生波折少。决定权不在他那里,有什么办法,他只能认了。依照对叔本人的猜想,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名字应该不是皮金狗,更不会姓皮。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他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多年来,对叔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还是前几天从皮坑口一位叫炳坤的老人口中,才打听到一鳞半爪。他来自一个陌生得叫不出名字的外乡,那地方紧挨着一片肉眼望不到边的湖泊,湖水没完没了地流进永远喝不饱的长江。炳坤提供了一个带着自然特征的地域,却没有指明具体方位。对叔追问,晓得那地方叫哪个省哪个县什么的么?炳坤年逾九旬,耳聋眼花,脑子看来不糊涂,涉及敏感话题总是吞吞吐吐,似乎在刻意隐瞒什么。他说那地方很远,估计几天几夜也走不到,村里从来没有人去过,都不晓得那个地方。那天是我陪对叔去皮坑口的。初见面时,炳坤完全像对待陌生人样打量对叔。一晃五十多年,对叔离开皮坑口时还是个小孩,如今站在跟前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炳坤似乎在记忆深处搜寻许久,始终找不出曾经熟悉的面孔与眼前的人画上等号。对叔探身过去把嘴贴近老人的耳旁,大声喊,我是金狗!老人说,我只认得狗伢。对叔又喊,我就是狗伢,金狗是我学名!老人点头笑了,是狗伢呵,就是当年皮瞎子托人在外面买来的那个狗伢,我认得,当然认得。小时候我还带他去橫冲水库划水(游泳),你狗伢水性好,一口气可以划(游)到对岸山脚下,一看就晓得是水边出生的人。随后他叹了口气,说皮瞎子给人算了一辈子命,就是没算准自家会落到水库做了个水鬼。老人口直心快,应该是藏不住话的人,可是关键时刻他又语焉不详,干脆掐断对叔的念想。我想炳坤或许根本不清楚那个地方在哪里,只是道听途说罢了。离开皮坑口时,日头快要落山。车到乌石河岸,对叔突然叫我停下车。我踩住刹车,回过头莫名其妙地问他,不打算回去了?去橫冲水库看一下。对叔的话没有半点商量的口吻,没等我提出异议,他已经按下车窗,指着西边坡地上一块有两个门楼高的广告牌说,旁边有条小路,一直往南能走到水库。我本想提醒他天快黑了,不如另选日子再来一趟,见他不达目的心不甘的架势,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我只好把车停靠在路边,跟着对叔往水库方向走去。
这座名叫橫冲的水库大得有点像湖,无论置身何处,都无法看清全貌。几座毗邻的小岛,驮着一团秋色,从东南方向逶迤而来,有如一群泅水的野牛,给孤寂的水库平添许多生机。
水库西北角一块空地上,垒起一间矮小的土屋。一扇木门被风雨侵蚀得不成样子,拼凑起来的门板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对叔默不作声地坐在屋前的草坪上,目光投向前面几步开外的那片半月形的水湾。倒映的天空让水底变得辽阔而绚丽,对叔一脸凝重,瞪大眼睛四处寻觅,无果而终。瞎子爸就是从这里走向生命的尽头,像这水中不起眼的小小云朵,一个浪花飞过,消失得无影无踪。
自从有了狗伢,皮瞎子仿佛重新见到一丝光明和希望,走村串户的日子比过去明显增多。无论走到哪里,跟着他的不再只是一把二胡一根拐杖,而是多了一个狗伢。狗伢稍大些,出门时总是很懂事地走在前面,攥紧拐杖,把拐杖另一端交给瞎子爸,像是用一根又粗又牢的绳子拴住瞎子爸并牵引他在坑洼的村路平安行走。到了狗伢上学的年龄,皮瞎子只能独自出门。等天黑回家时,进门就闻到饭菜飘出的香味,一种家的温暖让皮瞎子脸上挂满了笑容,仿佛年轻了许多。狗伢从小听话乖顺,五岁时就学会了烧火煮饭。每次做好饭,他习惯搬张凳子坐在门边望着屋前一点一点黑下的稻场,等着瞎子爸回家。有年夏天,皮瞎子连续三天没回家,狗伢着急忙慌地哭着要去找他的瞎子爸。村里人闻讯后陆续往狗伢家里赶。不久,几个光屁股男孩火烧房子似的跑过来,领头的那个小孩手里拿着一把二胡,边喘边喊,皮瞎子死了,皮瞎子死了,皮瞎子在橫冲水库淹死了!后面跟着的两个小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边说边比划,皮瞎子肚子都鼓起来……鼓得像……像……刮了毛的肥猪一样大。时任队长皮炳坤立马安排人去仓库卸下一块宽门板,找来几根竹篙,领着一群人手忙脚乱地朝水库奔去。
天完全黑下来,我和对叔才离开橫冲水库。
皮坑口距离罗城约摸四十分钟车程。上车后,对叔没说一句话,我以为他在睡觉,从后视镜瞥了他一眼,他头枕在坐椅靠背上,仰面看着天窗,心事重重的。他保持这种坐姿已经很久了,我担心他长时间不改变姿势,肢体会变僵硬,有意跟他说几句闲话,他心不在焉地应付几声,没有继续接话的意思,我就没再跟他多聊。
回到罗城,我把车停在明德街南面入口处。等对叔下车后,我问他要不要在旁边小吃店吃点东西。对叔说,不用,回家随便吃点什么比在外面吃舒服。见我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他朝我挥挥手,回去吧,辛苦你半天,太晚了,胡老师会惦着的。说完,对叔埋头向小街深处走去。
明德街是罗城最老的一条街,房东大多搬到铁路以东的新城區,空下的房子留给一些租房客。对叔年前才搬到明德街,离开翠园小区时,他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一只脱了漆的朱红色樟木箱。箱子虽然旧了点,他还是不舍得丢弃,毕竟是养父吴仁杰留下的东西,算得上是一种念想。母亲说,老对,这个家有一半是你的,除了房子,看中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走。对叔想现在哪有什么值得他带走,真让他牵挂的东西都没了。如果当初胡老师怀上他的孩子没被她做掉,或许不是今天的结局。对叔说,都用不上,谢谢胡老师。虽然母亲伤害了对叔和他未出生的孩子,最终对叔还是原谅了母亲。对叔对母亲还是那么客气,从最初认识到在一起生活,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称母亲胡老师。
对叔第一次来家里,我才六岁多一点。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中教师宿舍。两层楼的房子,我家住一楼。清一色的木板门,敲一下左邻右舍都能听得见。母亲开门时听见隔壁一家人也打开了门,来客个子很高,眉粗面阔,蓄着一脸跟他年龄不相符的络腮胡。母亲叫了声老对。老对没应声,向前走几步,把手里拎着的一塑料袋水果连同自己的屁股干脆利落地撂在沙发上。他们之间看起来很默契,应该认识有些时日。我问母亲,还有人姓对?客人咧着嘴吃吃地笑了起来,拜你妈胡老师所赐。母亲没作何解释,说,小伟,叫对叔。父亲离开后,家里第一次来了陌生男人,我不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觉得应该是好朋友吧。我不想驳母亲面子,有口无心地冲他叫了声对叔。
对叔给我的见面礼是两本少儿版图书,一本是《格林童话》,另一本是《伊索寓言》。书里的文字很多都不认识,每页配的像动画片一样的彩图一下把我吸引住。后来我喜欢美术,毕业后又考进文化馆,以美术为职业,这两本书一直是我绕不开的话题。我的择业是否与它有因果关系,谁也说不清楚。每次提起这件事,母亲总是后悔伤心,把责任全推到对叔身上,一口咬定是他使我误入歧途。对叔平时看起来高大威武,可在弱小的母亲跟前像一名做了错事的小学生,对对对,胡老师,你说得对,是我当初考虑不周。母亲说,在你看来别人都是对的,你就不能说出一件自己做对的事?对叔没料到母亲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大概要证明自己什么,他补充道,那不是美术书,是童话寓言,对孩子成长是有帮助的,属文学类书籍。母亲说,你的意思是我错了是小伟錯了。胡老师是对的小伟也是对的……对叔发现自己话又跑调了,立马闭嘴起身往阳台走去。每次两人起争执,最终都是对叔率先缴械投降。
母亲反对我干美术这一行,缘于伤风败俗的父亲在她心里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父亲是罗城一中美术教师,在同事心目中他属于那种以校为家用心教学的好老师,口碑不错。在母亲眼里他是个傻里巴叽的工作狂,最不称职的男人。他每天早出晚归,连星期天和寒暑假都很少有完整的休息时间。他带的是毕业班,学生累,教师忙,同为人师的母亲能理解。可我这个不知深浅的父亲,把母亲的宅心仁厚视为是对他的放任骄纵,利用外出写生的机会,竟然不知廉耻地跟女学生开房。纸终究包不住火,等女生肚子大了起来,混蛋父亲只能和母亲分手,带着女生离开学校去海口开了间画廊。
我试着拨了对叔的电话,真的如徐美珍说的那样,他关机了。
徐美珍是“俏夕阳”艺术团的团长,她带着一群老姐妹聚集在星空广场,为参加市里举办的“百姓大舞台,大家一起来”比赛活动排练节目。她们左等右盼,一个个像躁动的鹅,脖子伸得长长的,艺导始终没来,确切地说,是艺导失联了。徐美珍团长急得上蹿下跳,电话打不通,她立马派人去了明德街。回来的人告诉她,门上一把锁,艺导不在家。走投无路的徐美珍忽然想到我,急忙打来电话询问艺导的下落。徐美珍所称的艺导是对叔。对叔第二个名字叫吴艺。两年前,对叔从剧团退休后,徐美珍通过严二哥这层关系说动了对叔,把他当宝贝似的请来当导演。徐美珍和她的一班姐妹们活泼阳光,浪漫新潮,面对一个意气风发开明开放的新时代,自认为不落后年轻人。可是她们没有完全脱俗,还是有老思想,认为导演的姓“吴”跟“无”同音,称吴导等同于“无导”,称吴艺导演初听起来没啥毛病,仔细一想也觉得不妥。还是徐美珍团长脑子好使,她说,干脆就叫他艺导。艺导艺导,说具体点就是艺术指导。大家听徐美珍团长这么一解释,一致拍手叫好。
从见面第一天开始,对叔就有了“艺导”这个新的称呼。老姐妹一个个叫得心甘情愿热情爽快,对叔想不接受都不行,她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总不能因为一个称呼扫了大家的兴致影响安定团结。更名换姓的事发生在对叔身上也不是一次两次,见多不怪。
当初把皮金狗改成吴艺,对叔一时很不适应。听见有人叫他吴艺,他脑子是懵的,老觉得那是别人的名字,跟他没一毛钱关系。不过对叔还是认可吴艺这个名字,洋气,叫起来顺溜。吴爸爸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起的名字一定错不了,想拒绝还真的不那么容易。对叔想起第一次叫吴爸爸,岂止是不乐意,完全是开不了口。那时都叫他狗伢,他眼里只认皮瞎子是爸,想赶也赶不走。他经常一个人悄悄溜到橫冲水库,瞅着一眼望不见底的水库,一坐就是大半天。他觉得瞎子爸还活着,可能躲在水底的某个角落,跟他玩捉迷藏,冷不防会跃出水面,绕到身后突然把他高高举起。瞎子爸高兴的时候喜欢把狗伢当个玩偶搂在胸前,一会儿高高举起一会儿快快放下,让狗伢既开心又害怕。有年村里在仓库稻场上放电影,狗伢看不见挂在墙上的银幕,瞎子爸丢下拐杖,双手把狗伢举过头顶,让他骑在脖子上。狗伢立马喜笑颜开,觉得自己是全村最牛气最幸福的观众。
瞎子爸死后不到两个月,爱唱戏的松爷爷突然要狗伢对仅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叫爸爸。狗伢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叫他怎么开口。狗伢忐忑不安地站在松爷爷和那个被称作吴老师的人中间,耷拉着脑袋没吭声。刚才松爷爷托人带口信给狗伢,说县剧团一个叫吴仁杰的老师要见他。狗伢想,我又不会唱戏,吴老师找我做啥。一个小时前,狗伢跟这位吴老师见过面。吴老师进村时打听松爷爷住处,是他做的向导。带信人见狗伢迟迟不肯动身,说,你不去,松爷爷会不高兴的。队长炳坤都得听松爷爷的,在皮坑口,不听松爷爷的话就是不听队长的话。狗伢不想为这事被松爷爷怪罪,随后跟着带信人一起出了门。
没想到松爷爷和吴老师给他合演了一场“认父”的戏。
松爷爷说,吴老师是省城下来的干部,学问高,老伴前年病逝,没有儿女,你跟他走,他会像对亲儿子一样疼你的。
狗伢低头不语。
你跟吴老师是去吃商品粮,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着这个好事。
狗伢哩,这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
别人想去吴老师还不认哩。
旁边站着的几位长辈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松爷爷帮腔。
狗伢一只手在后脑勺来回摸索着。
松爷爷忽然站起身,向前跨出小半步,伸手在狗伢脑壳上重重拍了一下,连嗔带笑地说,傻狗伢,你是从糠箩里跳进了米箩里,过了这个村就怕没那个店,还不赶快跪下叫吴老师爸爸!
狗伢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迟疑片刻,扑通一声跪在吴仁杰跟前,头始终没有抬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吴……吴、吴爸爸。
对叔果真有什么差池,难辞其咎的首先是我。从皮坑口返回的路上,对叔的沉默、郁闷让我心里有些不踏实。但回城之后,我很快把这事置之脑后,按理起码应该去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样的举手之劳我都忽略了,确实不应该。对叔毕竟有恩于我,我们家能住进当时在罗城称得上高大上的翠园小区,对叔功不可没。购房之初,他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己全部积蓄,让母亲感激了大半年时间。从不习惯说漂亮话的母亲,不失时机地恭维对叔:吃水不忘挖井人,一生记住对哥哥;房子最好,对哥最亲;没有对哥,岂有明天。
对叔心眼儿实,听不惯那些没边没沿的漂亮话。起初母亲说什么他没拦着,等母亲说够了,他才接话,胡老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小伟就要上中学了,总不能让他一直在饭桌上看书学习吧。后来类似的话重复多了,对叔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有次实在听不下去,看见我在一旁,故意岔开话题,说他答应我今天要去公园放风筝,像找到救星似的一把拉住我的手趁机开溜。
我与对叔的关系慢慢走近,主要原因是母亲的强势。对叔仁厚、豁达又善解人意,让我心里温暖、踏实,觉得值得依赖。母亲的清高和狭隘,助长了她的霸道,总是以家庭的主宰者自居,我和对叔只能对她唯命是从。但在我个人兴趣爱好方面,对叔是我的坚定支持者,明面上附和母亲,背地里与我暗通款曲。他经常对我说,人的一生能够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小伟,你说是吗?我说,听对叔的。有年暑假,对叔私下帮我报了个美术培训班,为了迷惑母亲,他竟然买通一个课外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直接给我圆谎。直到高考结束,母亲得知我被一所美术类院校录取,悔之晚矣,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悲哀的母亲。随之而来的委曲、怨恨和挫败感让她终于明白,挑战母权的不光是儿子,躺在身边的男人才是始作俑者。从此,母亲对这个同床异梦的男人再没有一句好话。母亲和对叔的婚姻最后走到尽头,除开中间有个徐美珍,我想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对叔是一个纯粹透明的人,像一只白色玻璃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审视,都干净通透,找不到一丁点儿色差。尽管如此,他还是避免不了在我心底留下一个疑团。不知为何,他从来不带我也不允许我去剧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总不让我去剧团?对叔说,不让你去总有不让你去的理由,以后你会明白的。他的避实就虚,让我一头雾水。
有次我跟对叔出门理发,遇见一位认识对叔的人。那人是个秃头,脑壳油光锃亮的。看见对叔,他先是一怔,随后喊道,匪兵甲!
对叔没搭理他,一副很生气的样子,仰着脸继续朝前走。
秃头不识趣,继续穷追不舍,难道你不是匪兵甲?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要不我跟你回忆回忆?
对叔突然停下脚步,面色铁青地瞪着秃头,腮帮上的胡须像刺猬身上的利刺一根一根支棱起来。
滚开!他冲着秃头吼道。
见对叔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秃头像真的遇到一个蛮横无理的匪兵似的,胆怯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第一次听说对叔还有这么一个难听的外号,也是第一次发现他盛怒之下所迸发的威严与气势有如此超强的震慑力,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感到毛骨悚然。我忽然意识到,平时温润憨厚的对叔也有生猛和不为人知的一面。等秃头离开后,我问对叔,才知道匪兵甲是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无名无姓的小角色,对叔当不了杨子荣、少剑波、座山雕,演了个无名小卒匪兵甲。排练时,导演这么叫,其他演员也跟着这么叫,后来戏不演了,大家还没忘记把这个名号安在对叔身上。
我说,戏都不演了还叫你匪兵甲,那是有意笑话你。
对叔说,我们的名字是长在别人嘴里的,别人怎么叫,有他们的道理和目的,我们不去管也管不着。
对叔话虽说得坦诚,听来似乎也合理,可我总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对叔还是隐瞒了什么,不然他不会对秃头叫他匪兵甲反应那么强烈,像是有深仇大恨。我猜想这事跟他不让我去剧团一定有关系。有次对叔不在家,我问母亲,对叔还有个名字叫匪兵甲你晓得吗?母亲阴着脸,很不情愿地回了一句,大人的事小孩瞎操什么心。母亲很明显也在回避这个话题,看来母親和对叔关键时刻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会心照不宣地守住对方的秘密,这让我好长一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
周六早上,母亲先跟老闺蜜们大声哇叫地通了几个电话,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准备去公园健步走。她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软底助力鞋,前几天才到的货,是电视剧《渴望》刘慧芳的扮演者张凯丽做的广告。母亲现在选择商品很迷信明星推荐和媒体推介,所购物品,一般都跟着广告走,这或许跟她的职业有关。母亲离开教师岗位已经二十多年了。父亲的伤风败俗对她打击太大,继续留校任教让她无地自容,无法去面对学生,后来就通过关系调到了电视台。如今电视台更名融媒体中心,母亲所在的广告部,每天都会接待一些做产品宣传的经销商。她的收入有部分跟这些客商挂钩,凡是来打广告的客户,都是她的上帝,可能是爱屋及乌吧,她对广告产品总是情有独钟。
我打算把对叔失联的消息告诉母亲。昨天因为回家晚,见母亲睡了就没去打扰她。他们曾经夫妻一场,尽管不在一起生活,可毕竟共同度过一段幸福时光,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
母亲哼着自来腔精神倍爽地打开门。我说,对叔失踪了。
母亲没回头,他会失踪?像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否定我反问我,一点也不吃惊。没等我把话再说下去,她便迈开双腿跨出了家门。
对叔目前杳无音讯生死未卜,没想到母亲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让我很失望。
我追到门边,打算数落母亲几句,她突然停下脚步,像是想起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转过身来,说,你去找一下徐美珍。
徐美珍是戳在母亲心中的一根刺,她与对叔离婚,真的如外界所传是因为徐美珍插足?看来,我真的要去会会这个徐美珍。对叔突然失联,让我方寸大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他平时交好的朋友当中,首先想到严二哥。严二哥退休后在电影院旁边开了家台球室,平时来玩的客人也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娱自乐消磨时光。进门时他正埋头看手机,我叫了声叔,他愣了半天才认出我,嘿嘿,是小伟呀。小时候,他曾随对叔来过我家几回,还送给过我一个变形金刚玩具,让我高兴了好几个星期。我问他这两天见过对叔没有。严二哥告诉我,吴艺昨晚来找过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说想去寻找自己的出生地,要他帮忙。严二哥说这是大海捞针,中国这么大,他想帮也不晓得怎么帮。他说吴艺立马提供了线索,说是在湖边,湖还连接着江。严二哥说江湖相连的地方多,上有洞庭湖下有鄱阳湖,湖面方圆几百公里,恐怕十天半月也找不到。严二哥说他见吴艺情绪十分低落,赶忙宽慰他,这事急不得,一旦打听到眉目,会第一时间通知他的。他说吴艺还是心神不定,心里好像想别的事情去了,没把他的话听进去,急急忙忙地走了。
现在可以断定,对叔的不辞而别,不是逃离,是寻根问祖去了。严二哥跟我的看法基本相同,他说吴艺始终有个心结。他到底来自哪里?姓甚名谁?人老孤独了思乡之情无法阻拦,解开身世之谜的愿望会越发强烈。可我还有一事不明:对叔为何关机,像是要一走了之永不回头,彻底断绝与罗城所有联系?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他再留恋,一切都跟他毫无瓜葛?对叔对“匪兵甲”的介怀和一直不让我去剧团这两个疑问,忽然汇聚一处像一个巨大的云团在我眼前飘浮。
对叔在罗城还有比你更了解他的人吗?话一出口我立马有些后悔,这明显是对严二哥不信任。
原来有,现在有没有我不清楚。严二哥没有计较我的失礼。
原来那个人是谁?我追问道。
严二哥犹豫了一下,眼球来回转了几圈,看看门,看看窗,看看球桌,又看看空荡荡的球室,最后才把目光停在我身上。唉,他叹了口气说,一个是他爸爸吴仁杰,另一个是他师傅徐美丽,不过他们都联系不上了。
吴仁杰我是知道的,对叔的养父,一个有学问的编剧。对叔曾跟我提起过他,说罗城这个地方太小了,留不住人,迟早他都会离开的,而徐美丽的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经我死缠硬磨,严二哥答应把徐美丽和吴仁杰的故事讲给我听。
徐美丽既唱花旦又演小生,是剧团的台柱子。人又长得好看。长得好看的美人往往傲慢清高拒人千里之外,徐美丽跟她们可不一样,待人热情真诚,不端一点架子,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没找对象的青年人都想方设法接近她,巴不得立时三刻把她娶回家,晚一步就可能后悔终生;成了家的男人不能明目张胆地追求她,只能日思夜想,希望梦里跟她发生点什么值得回味的故事。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剧团和社会上排队追她的男人,她一个没中意,偏偏看上比她母亲小三岁的吴仁杰。这下可坏了徐美丽父母的好事,他们选定的女婿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大公子,那还了得,一气之下把徐美丽锁进房里。但徐美丽心里只装着温文儒雅满肚子文章的吴老师,吴老师才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滴水不进粒米未沾,以绝食进行抗议。到了第三天,不是徐美丽没扛住,是她母亲妥协了。
我忍不住打断严二哥,徐美丽怎么成了我对叔的师傅?
严二哥说,吴艺高中毕业后赶上剧团招学员,吴仁杰私下找了团长,顺利把吴艺弄到团里。起初吴仁杰认为吴艺人高马大不适合当演员,让他进乐队学门乐器。谁知吴艺对什么二胡、京胡、小提琴、大提琴一概不感兴趣,觉得乐器枯燥乏味,一心想上台演戏。吴仁杰又厚着脸皮去找团长,把吴艺调到演员队,交给了徐美丽。后来发生的事,吴仁杰没想到,大家都没想到,徐美丽跟吴艺好上了。
他俩搞起了师徒恋?我十分震惊。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的,你想不信还不行,说这事还是吴仁杰首先发现的。严二哥说,我问过吴艺,他说这是造谣诽谤。我说师傅对你好是公认的吧。他说师傅关心徒弟是天经地义的有什么大惊小怪。我问他师傅怎么关心他,他说给他洗衣做饭帮他织毛衣送他钢笔算不算。我说可算可不算,关键是她对其他人有没有这样做。吴艺有点不耐烦了,说他不清楚,叫我去问徐美丽自己好了。严二哥说我哪敢去问徐美丽,那纯粹是讨骂。我也不好去问吴仁杰,听说他为这事气得躺了几天没起床。
我问严二哥,你真的相信了?
严二哥说,不管是真是假,人言可畏,三人成虎呵。这件事彻底打乱了吴仁杰和徐美丽的正常生活,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匆匆离开了罗城,从此杳无音讯。
我瞪大眼睛盯着严二哥,脑子一片空白,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我现在终于明白对叔为什么不让我去剧团,为什么一直摆脱不掉“匪兵甲”的恶名。身为人子的他公然去抢占父亲的恋人,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只有土匪才干得出来。败坏了名誉的对叔,哪里还有姑娘愿意嫁给她,如果不是后来遇见母亲,他可能会光棍一辈子。
外面忽然闹哄哄的,随后进来几个来打球的。他们是常客,一见面严二哥严二哥叫得亲热,有个挂单的人邀请严二哥跟他配对儿玩。
严二哥开始忙活起来。我起身往门外走,他赶忙过来送我几步。我說叔你去招呼客人,我就不打扰你了。严二哥把嘴凑到我的耳根,细声细气地说,吴艺和徐美丽那些事,你还可以去问问徐美丽的妹妹徐美珍,她是知情人,可能比我更清楚。
知道徐美珍是徐美丽的妹妹这层关系后,我一时难以平静。估计母亲早有耳闻,可她一直守口如瓶,从未提起过此事。母亲怀疑对叔跟徐美珍有私情,看来不是空穴来风,说不定他们早就勾搭成奸,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徐美珍徐美丽同气连枝,可能有很多地方相似,这也是对叔和徐美珍相互走近的内在诱因吧。不管真相如何,对叔在我心里的形象突然大打折扣。我想,如今母亲跟他已经分开,他和徐美珍有什么事与我何干?原打算去会会这个徐美珍,顺便了解对叔的近况,现在看来多此一举,也没必要,起码暂时没有这个必要。
事情过去了两周,有关对叔的行踪得不到星点消息。我正对接省馆举办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精品联展”活动,脱不开身,于是把对叔的事搁置一边。
有天早上,我打开手机,在《头条新闻》无意看到一条消息,大致内容如下: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在一辆行驶的中巴车上,与一名持刀劫匪英勇搏斗,身负重伤,最终将劫匪擒住。事后,他没留下姓名,称自己行走江湖,无名无姓。后面还附了一则《寻人启事》:
江湖无名侠,男,大约六十岁,操南方口音,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浓眉,国字脸,络腮胡。知情者请与江右市湖滨县公安局见义勇为办公室联系。电话×××××××××××
这位江湖无名侠跟对叔的特征刚好吻合,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对叔。我立马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你对叔这个人嘛有时我真是看不懂,说他有情无义无情有义,也不错,说他无情无义有情有义,也在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上最难的事是识人。小伟呀,你说那个江湖无名侠是对叔,我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不过我不相信是他。
母亲的态度让我很迷茫。我寄希望电话向对叔求证,无奈对叔还是处在关机状态。这时,我发现微信里有人邀请我添加好友。我点开“新的朋友”,进来的人名叫“江湖无名侠”。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验证添加。对方的头像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朋友圈里晒出三张照片,第一张是河。弯急滩险,水坦流深,从画面上看,恰似长江的缩小版。仔细看才知是与橫冲水库擦身而过的乌石河。第二张是橫冲水库。晨光初露,水平如镜,岛在水中行,水在画中流,不似湖泊胜似湖泊。第三张是小屋。门黑洞一样张开口,吐出一块乌漆抹黑的船形石。石头临水的一端,坐着一位昂首挺胸戴了口罩的男人,打了夹板的左腕被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绷带系住,成直角悬靠胸前,像个归来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