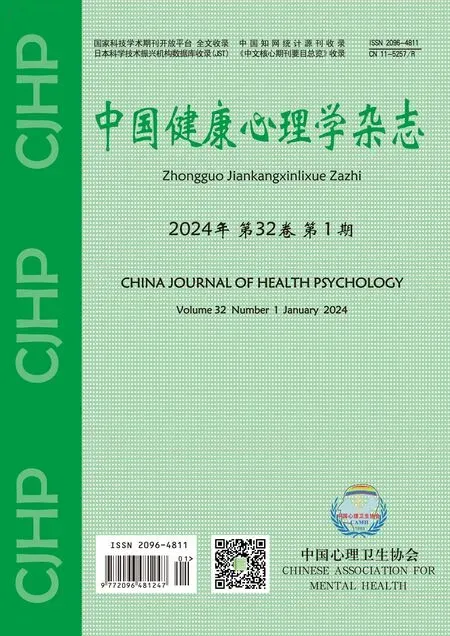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新生社交焦虑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
2024-01-12武春霞薛朝霞闫丹凤
武春霞 薛朝霞 李 静 闫丹凤
①吕梁学院教育系 033001 E-mail:llxywcx@163.com ②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③吕梁学院学生处 ④山西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
社交焦虑主要表现为对人际情境的过分紧张与害怕,在公共场合或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持续而强烈的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1]。大学生正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这一特殊的心理发展时期,不仅承担学习压力,还要考虑就业问题,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是社交焦虑的易感人群[2]。研究发现,45.7%的大学生存在社交焦虑[3],16%的大学生有严重的社交焦虑[4],大一新生的社交焦虑问题尤为多见[5]。社交焦虑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6]、主观满意度[7],而且容易诱发网络成瘾[8-11]、酒精依赖[12]等问题行为。因此,探讨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成因和机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微系统环境因素[13],父母教养方式是众多家庭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14]。心理控制作为一种常见的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以爱之名,控制子女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以符合父母的期望,这种教养方式限制了子女的自主权、忽视了子女情感与心理需求[15]。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是社交焦虑的风险因子之一,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子女的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16-17],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能够预测后期子女的社交焦虑水平[18]。然而,父母心理控制是如何影响子女社交焦虑的,以往有关其内在心理机制的研究鲜少报道。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外在环境因素,可能通过对子女的内在因素间接影响其社交焦虑。为了更好地完善内在机制,本研究试图从认知因素(核心自我评价)和情绪因素(负面评价恐惧)两个方面来深入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影响的作用机制。
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结论或底线评价,是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神经质4种人格特质背后的一个更为基本的结构[19]。社交焦虑认知模型认为,消极的自我认知和评价是社交焦虑产生和发展的风险因素[20-21]。多项实证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能够预测社交焦虑,核心自我评价越低,社交焦虑水平越高[22-23]。此外,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与子女的自我认知密切相关[15]。感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高的子女容易缺乏自尊自信[24],自我效能感较低[25]。心理控制水平高的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支持较少,不利于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自主自控和成就体验感,从而削弱了子女的核心自我评价[26-27]。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社交焦虑。
负面评价恐惧是指个体对他人可能的负面评价的担忧与恐惧[28],是社交焦虑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29-30]。以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31-33],负面评价恐惧能预测个体未来的社交焦虑水平[34]。临床心理研究结果也显示,通过干预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35]。以往研究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个体感知到的父母控制水平越高,对自我的能力认可度越低,对他人的负面评价恐惧越敏感[36]。反之,如果父母给予子女适度的关怀和鼓励,让子女通过家人对自己的接纳与认可,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可以有效降低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恐惧[37]。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负面评价恐惧间接影响社交焦虑。
核心自我评价侧重于个体对自身整体的、深层次的评价。作为最基准的评价,核心自我评价是其他所有评价的基础,影响着各种具体环境下相关的评价[38]。负面评价恐惧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因担心自己的行为表现达不到他人标准而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恐惧。情绪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是个体情绪产生的关键因素。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可能影响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情绪,即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在具体情境对自我的行为表现及后果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进而惧怕他人的负面评价。自尊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均与负面评价恐惧显著负相关[39-40],神经质与负面评价恐惧存在显著正相关[41]。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神经质均是核心自我评价的组成要素。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核心自我评价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且二者在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某高校的大一新生进行施测,共980人参与问卷作答,其中92份问卷因作答时间太短或明显作答不认真而被剔除,最后获得有效问卷888份(90.61%)。其中男生251人(28.27%),女生637人(71.73%)。城镇学生259人(29.17%),农村学生629人(70.83%)。独生子女150人(16.89%),非独生子女738人(83.11%)。大学新生平均年龄18.84±1.27岁。
1.2 方法
1.2.1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选用Wang等人编制的父母控制量表中的心理控制分量表[15]。该量表共18个题项,包括引发内疚、收回关爱、坚持权威3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0.95。
1.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Judge编制、杜建政等翻译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42],该量表共10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核心自我评价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3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陈祉妍修订的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28],该量表共12个题项,单一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1.2.4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Leary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43],共15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是0.86。
1.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施测,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使用AMOS 26.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数的Bootstrap法对结构方程模型中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周浩等人的建议[44],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4个变量的所有项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有7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总变异的60.36%。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9.04%,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可以接受数据。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相关分析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r)
2.3 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潜变量间的关系,对社交焦虑量表进行项目打包。以往研究表明因子法中的平衡法这种缩小组间差异的打包策略模型拟合较好,且打包成3个指标时拟合度最好[45]。因此本研究采用平衡法,依据因子负荷将社交焦虑的15个题目打包成3个项目包。
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的直接影响。模型拟合度指标为χ2/df=2.59,CFI=0.99,TLI=0.99,GFI=0.99,AGFI=0.98,RMSEA=0.04,模型拟合良好。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β=0.24,P<0.001)。
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模型检验(见图1)。模型拟合度指标为χ2/df=3.09,CFI=0.99,TLI=0.98,GFI=0.98,AGFI=0.97,RMSEA=0.05,模型拟合良好。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36,P<0.001),显著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0.20,P<0.001),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6,P>0.05);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β=-0.50,P<0.001),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β=-0.37,P<0.001);负面评价恐惧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β=0.46,P<0.001)。

图1 父母心理控制影响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模型
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直接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0.12,0.01)包含0,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完全通过中介路径实现。具体包括3条中介路径:第一条路径为“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社交焦虑”,其中介效应值为0.133=(-0.36)*(-0.37);第二条路径为“父母心理控制→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其中介效应值0.092=0.20*0.46;第三条路径为“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其中介效应值为0.083=(-0.36)*(-0.50)*0.46。上述3条路径中介效应值的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影响的总效应等于3条中介效应之和,见表2。

表2 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4]。父母心理控制对大学新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父母过度心理控制导致其人际交往能力不足,无法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遭到排斥,进而引发社交焦虑[46]。另一方面,父母长期心理控制会让子女缺乏安全依恋感[47],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稳定关系[48]。亲密感的匮乏与缺失更容易引发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的焦虑情绪。
研究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交焦虑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作为消极的教养方式,通过对子女日积月累的影响,使其逐渐内化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消极的自我概念[49]。父母心理控制导致子女基本心理需求受阻[50],自我价值感受抑[51],也会降低子女的核心自我评价。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负向预测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2]。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更容易注意到关于自我的消极信息,出现信息加工和理解偏差,进而强化自我的消极认知和评价,影响其后续的情绪体验和行为表现[53],因而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情绪。
研究结果还发现,负面评价恐惧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交焦虑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6]。父母心理控制限制了子女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导致他们面对问题缺乏解决应对能力[54],表现出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另一方面,负面评价恐惧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33]。负面评价恐惧高的个体,对威胁性和不确定环境的警觉性高。当面对可能被评价的社交情境时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往往高估消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体验到更多的焦虑情绪[32]。
研究结果还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负面评价恐惧”构成的链式中介也是父母心理控制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途径,占总效应的26.95%,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更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认可,对他人的评价更敏感,总是担心他人的负面评价会对其地位和价值造成威胁[39-40]。核心自我评价低的个体,缺乏自我效能感,在接收到负面评价等消极信号时,不是建设性的积极应对[55],而是陷入对负面评价恐惧的消极情绪中。
总之,父母心理控制既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焦虑,也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焦虑,以上结果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交焦虑影响的完全中介心理机制。本次研究结果对今后改善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