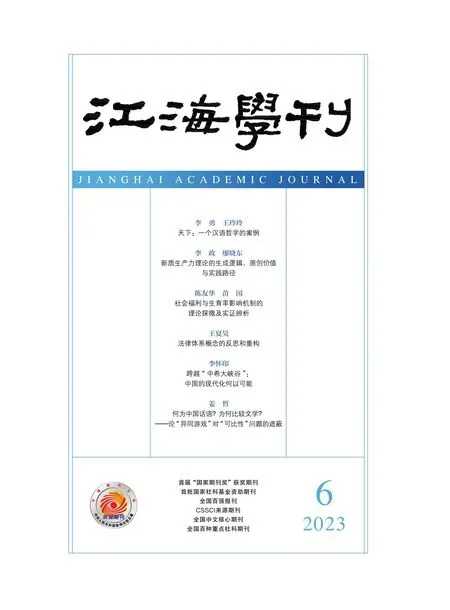生死之间: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衰病叙事与生命意识
2024-01-10诸雨辰
诸雨辰
善写老境是宋代文学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在诗歌中,宋人将身体与疾病转化为审美对象,在写实基础上运以巧似的修辞艺术、轻松的戏谑笔法,淡化了忧惧衰病的情绪底色,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形态。(1)参见庞明启:《“剥落”的“老丑”:宋诗衰病书写与身体审美转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孙宗英:《论欧阳修的衰病书写》,《国学学刊》2018年第4期。然而,文人在札子、表启等文章中,却又将其症状、病程等描述得极为沉重,如欧阳修《辞开封府札子》《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等,其生命底色未必如诗歌所呈现的那样轻松潇洒。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疾病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生命中的沉重与悲凉。(2)陈湘琳、汪超等运用尺牍、行状等资料考察了欧阳修的衰病、苏轼的疮病等。参见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汪超:《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文献》2018年第5期。那么,从消极的衰病体验到积极的文学书写,他们是如何完成心境转换的?这既事关宋人生死观的形成,也最能彰显文学之于人生的抚慰价值。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或许需要借助尺牍这一颇具宋人特色的文体。毕竟除了诗歌与表启外,最为频繁出现衰病书写的文体便是尺牍。“尺牍”即宋代士人交往中私密性的、非正式的书信,往往施于亲友之间,多谈日常琐事,篇幅短小,内容和语言都较为随意,(3)参见李贵、张灵慧:《论宋代书信体类的消长与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并与具有公共属性的书启区别开来。(4)参见[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宋代的信息传递能力大大提升:邮递与馆驿系统开始分离,形成了专门的邮递系统,长江与运河航线也便利了交通往来。宋太宗还下诏允许官员将家信交驿附递,(5)参见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330页。由此,尺牍也就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联络工具,黄庭坚在《宜州家乘》中就记录了他几乎每隔三五日便有收件或寄件。而相对于功能性的表启(通过细致描述症状、病程获得朝廷垂怜)与抒情性的诗歌(通过戏谑衰病完成诗人的人格塑造),私人性更强的尺牍因为不需故作姿态而更近于真实。由此正可以了解北宋文人患病的感受,进而审视其疾病观、生死观以及心态转换的历程。
尺牍中的衰病叙事
北宋时期重要文人的尺牍中,几乎都有对身体与疾病的描述,而且大多会提到病情的前因后果,描述症状也很细致,与诗歌中抽象而选择性的呈现迥然有别。
范仲淹常苦于肺病,他在与石延年、孙沔的信中备述“朋来相欢,积饮伤肺”,(6)范仲淹:《交游·石曼卿》,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05页。“肺疾未愈,赖此幽栖”的肺病之苦。(7)范仲淹:《交游·孙元规》,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第606页。而为了治疗,有时还因为服药而伤及其他内脏,他在家书中就曾提到庆历五年(1045)“到忻、代病嗽,医药过凉,伤及下脏”,结果“淋痔并作,日夜苦楚”,(8)范仲淹:《家书·朱氏》,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第584页。引发更多病痛。
最苦于疾病缠身的可能是欧阳修与苏轼。欧阳修尺牍中不断出现对眼病、腰脚病、眩晕、臂痛、手指抽搐、咽喉肿痛、牙痛等的叙写,几乎全身都被病痛长期折磨着:如庆历八年(1048)“双眼注痛如割”;(9)欧阳修:《与王文恪公》其一,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01页。皇祐四年(1052)“忽患腰脚,医者云脾元冷气下攻”;(10)欧阳修:《与杜正献公》其七,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56页。嘉祐二年(1057)“以客多饥疲,风眩发作,卧不能起”;(11)欧阳修:《与焦殿丞》其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478页。嘉祐四年(1059)“几案之劳,气血极滞,左臂疼痛,强不能举”;(12)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88—2389页。嘉祐五年(1060)“以尝患两手中指挛搐,为医者俾服四生丸,手指虽不搐,而药毒为孽,攻注颐颔间结核,咽喉肿塞,盛暑中殆不聊生”;(13)欧阳修:《答张学士》其一,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493页。治平年间“齿牙摇动,饮食艰难”。(14)欧阳修:《与焦殿丞》其十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480页。苏轼叙述疾病的频率稍低,但其患病的类型与次数也不遑多让。如元丰六年(1083)“春夏多苦疮疖、赤目”(15)苏轼:《与李公择》其八,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9页。“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16)苏轼:《与蔡景繁》其二,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661页。元祐四年(1089)“腰脚蹒跚”,(17)苏轼:《与钱穆父》其十,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466页。绍圣二年(1095)“数日来苦痔疾,百药不效”。(18)苏轼:《答黄鲁直》其四,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33页。也分别提到自己的疮病、眼病、腰脚病、痔疮等病,而这还不算更常见的腹泻、疖子、咳嗽等小症状。
王安石与黄庭坚的情况稍好,所叙多为咳喘、头晕、脚气、臂痛、心痛等症。如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言“脚气已渐平复,殊以为慰”,(19)王安石:《与王逢原书》其八,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807页。元丰三年(1080)“痞喘稍瘳,即苦瞀眩”,(20)王安石:《与章参政书》,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355页。元丰四年(1081)“头眴多痰,动辄复剧”。(21)王安石:《与沈道原书》其一,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800页。黄庭坚亦尝言其“痈方溃,臂作劳辄痛”,(22)黄庭坚:《与胡逸老书》其六,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600页。“某比苦脚气时作,头眩,胫中痛,虽不妨寝饭,亦是老态渐出”,(23)黄庭坚:《与王泸州书》其六,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1645页。“某春来啖苦笋多,乃苦心痛,殊恶,虽进极温燥药得无恙,然遂不能多饮茗,亦殊损减人光彩”,(24)黄庭坚:《与王泸州书》其八,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1646—1647页。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
相较于宋诗,尺牍中对疾病的书写更加真实、也更加沉重。尤其是把时间拉长,观察整个病程时,尺牍所呈现的衰病叙事更会细致到令人心痛。早在嘉祐、治平年间,欧阳修就开始牙痛,可是其病齿“虽浮动,医者云取未得,须候根脱取之省力”,(25)欧阳修:《与陈比部》其五,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513页。连拔牙都做不到。此后,欧阳修的尺牍中就经常见到与人倾诉“齿牙摇脱,饮食艰难”,(26)欧阳修:《与吴正献公》其四,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70页。这对他不啻为巨大的变故。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与杜植交心:“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齿牙,饮食艰难,则向所谓于身所得者,无复有尔。”(27)欧阳修:《答杜植》,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501页。牙痛的切身感受让欧阳修意识到人在衰病面前一无所有,即便得来荣华富贵,身体也无从享受。次年,欧阳修于枢密副使任上,依然“近以口齿淹延,遂作孽,两颊俱肿,饮食言语皆不能。呼四医工并来,未有纤效”,(28)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十三,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91页。因而特别拜托王素求取山豆根为药。就在同年,欧阳修还向王拱辰推荐过张瑰提供的治牙良方,可是他自己却感慨:“中年以后人皆有之,患者医方亦多难得效。”(29)欧阳修:《与王懿恪公书》其七,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96页。一面是求方问药,一面却又困于无效的医疗,言语之间流露出深深的绝望。直到欧阳修去世的熙宁五年(1072),才终于“令医工脱去病齿,遂免痛苦”。但经过近十年的折磨,他已是“情悰索然,但觉一岁衰如一岁尔”。(30)欧阳修:《与薛少卿》其二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511页。相较于嘉祐五年(1060)诗中“颔须已白齿根浮,子年加我貌则不”(31)欧阳修:《哭圣俞》,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133页。与嘉祐六年(1061)诗中“自惭窃食万钱厨,满口飘浮嗟病齿”(32)欧阳修:《初食鸡头有感》,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141页。等句,尺牍的病情叙述显然更真切、也更痛苦。
把尺牍当作长期病历,不仅能看到病程发展,更可以观察作为患者的文人的心态变化,其中尤以苏轼的记述最令人感慨。苏轼向来以乐观著称,元祐三年(1088)他与黄庭坚说自己“坐处苦一疮极痛,至今未穴”,这是坐骨三叉神经处长了疖子,需要令其溃破出脓才能痊愈,非常痛苦。可是苏轼接着就开玩笑,说料想“疮两日当穴,又数日可无苦。诸公自可准法来问疾”,(33)苏轼:《答黄鲁直》其三,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33页。足见病痛下的乐观。甚至贬谪海南,都还开玩笑说:“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34)苏轼:《答王敏仲》其十六,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695页。仍不失豪气。可是到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北归途中,他致书参寥子道:“见知识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果若有应,其他不恤也。”(35)苏轼:《与参寥子》其二十一,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868页。竟迷信提前致仕即可得活,可见其晚年对生命强烈的渴望。对比苏轼病中绝笔诗笑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36)苏轼:《答径山琳长老》,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59页。的诗意洒脱,尺牍中则是对生命的强烈渴望。看似矛盾的观念,却同样是苏轼内心的声音。阅读这些衰病书写,便可了解文人于日常随笔间流露出的面对疾痛时真切而又深沉的心理反应。
衰病叙事与尺牍的文体属性
相较于诗歌,文人于尺牍中的衰病叙事更为具体、细致,身体与情感体验也更为深沉,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相。那么,尺牍何以更适于承载衰病叙事的内容呢?
从文体功能上说,尺牍的核心属性是沟通交往,所谓“反覆读之,如对谈笑也”。(37)黄庭坚:《与王庠周彦书》,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418页。作为信息传递者之间实体性的沟通载体,尺牍的交往属性对其内容也产生了影响。首先,尺牍的沟通是非即时性的,收信人在得到来书后未必能即刻回复,常常需要等待合适的传递者。出于礼貌的考虑,回书时就难免要写一些解释性话语,身体欠佳正是最不失礼节的解释,所以经常出现在行文开头或结尾处,例如:
承惠佳篇,甚释病思,和得纳上。目痛甚,书不得,勿讶。(38)欧阳修:《与吴正肃公》其五,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74页。
数日适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报,灭裂。死罪!死罪!(39)苏轼:《答毛泽民》其七,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73页。
多病,稍劳即头眩,书不伦次。某白。(40)黄庭坚:《与洪甥驹父》其四,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1773页。
某以暑中苦疮痏而苛痒不可耐,爬搔次骨,久乃作痛,意绪无憀,坐此不时具问。(41)孙觌:《与胡枢密》,《孙仲益内简尺牍》卷二,乾隆十二年刻本,第9b页。
这些文字都不无歉意地表示回书潦草或不及时是自己目痛、壅嗽、头眩等疾病缠身所致。这正是尺牍常见的叙事模式之一。
其次,尺牍交往的私密性特点又确保了衰病叙事的坦诚。在宋人观念中,诗文一般要收入别集,公之于世;而尺牍则未必入集,多是后人辑佚的产物。(42)参见[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苏轼在黄州时写给李之仪的尺牍中就明确表示:“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43)苏轼:《答李端叔书》,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433页。欧阳修给梅圣俞的信中也提到希望将“此小简立焚”。(44)欧阳修:《与梅圣俞》其二十三,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456页。在高度私密性的文本中,文人能较少顾忌地谈及一些敏感话题,而疾病亦是敏感话题之一,因为疾病会带来精神上的耻感。孙觌叙述其“入夏苦疮疡,苛痒不能耐”,于是他用硫磺治病,“敝衣破履,拥鼻而坐,不敢对一客”,(45)孙觌:《与孙宣教》,《孙仲益内简尺牍》卷一○,第12b页。即道出这种自惭形秽的病耻感。
病耻感源于疾病令人由身体而精神地“示弱”,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推崇的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坚韧,所以患者往往不愿公开谈及疾病与身体。元丰四年(1081),王安石与蔡肇游土山,就刻画了自己“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46)王安石:《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22页。的老当益壮形象。可是同年他与吴豪的尺牍中却自述:“平生未尝畏暑,年老气衰,复值此非常气候,殊为惫顿。”(47)王安石:《与吴特起书》,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300页。仅因为暑热就感到惫顿,这番告白与诗中的形象大不相同,显然也不符合主流观念的期待。而这正是公之于众与藏之于私的区别:宋人在诗歌中将衰病视为一种高级审美对象来刻画;而在私密性强的尺牍中,则不妨从容地说出一些丧气但却真心的话。
私密状态下的真情流露,甚至让文人们敢于自述违礼行为。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为母守丧时患了腰脚病,医者告知是“脾元冷气下攻”所致,于是欧阳修遵医嘱而开始食肉。居丧食肉有悖儒家礼仪,这令欧阳修深感“自犯名教”,(48)欧阳修:《与杜正献公》其七,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56页。但他依然愿意在尺牍中向杜衍坦陈此事,后来又以这段经历劝吴育“间食少荤味,以养助真气”。(49)欧阳修:《与吴正肃公》其十二,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76页。类似地,王安石劝说妹婿让正在斋戒的四妹“且时时肉食,恐久而成疾也”,虽然有悖礼仪,但经过一番“头眴多痰,动辄复剧”,“槁骸残息,待尽朝夕”(50)王安石:《与沈道原书》其一、其二,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800页。的衰病感叹后,王安石显然认为身体比礼节重要得多。而这些有悖礼仪的真心话恐怕只有在私密性的尺牍中才能自然说出。
最后,与私密性相伴的是语体上的随意性。尺牍一般篇幅短小,即使讲道理也很少长篇大论;语体上则在不失尊重的前提下,保持着轻松、随意的风格。黄庭坚与王云兄弟的书信中就希望“他日惠书,愿悉去表襮,但作家书数行”,(51)黄庭坚:《与王子飞兄弟书》其一,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1673页。追求朴素而真诚、如作家书的风格。这种语体风格有利于保持相对轻松的语境,是交流衰病所必要的。因为一旦交流时的距离感拿捏不当,就有可能把安抚变成说教。比如同样论疾病养生,司马光在《答范景仁论养生及乐书》《与范景仁论中和书》等书中与范镇的交流就颇为失败。这些文章入集时被归入书启类,与短小随意的尺牍并不相同。司马光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在阴阳寒热之间保持平和、节制用药与饮食。可他一定要从六经说起,引经据典,颇有盛气逼人之感,结果引起范镇的抵触。与病人谈养生治病,可以赠予对方药品,或者提供必要的共情与安慰,唯独不需要说服,过于正式、精心组织的语言与论据反而疏远了与对方的距离。而在诸多文体中,唯独信笔而书的尺牍最能弥合作者与读者间的隔阂。王安石与王令的一封尺牍就很得体,他和王令谈起脚气病,首先表示:“然书所传道,岂可以尽意乎?”谦称自己是随便说说,言不尽意,然后再分享其“取唾以手大指摩脚心”(52)王安石:《与王逢原书》其八,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807页。的偏方。这种偏方可能未必奏效,但是王安石对距离感的把握还是比较令人舒服的。在轻松随意的语境中,衰病叙事才能更顺畅地展开。
后人阅读尺牍,读到的往往是作者的独白。但不同于其他文体,尺牍有着明确的接受者,有特殊的语境和意图,因而单方面的独白又指涉着文人之间的互动。而无论是出于关心性的探问、礼节性的解释,还是在疾病与生死之间的真情流露,一旦谈及身体,往往就会引起回信时话题向身体与疾病聚焦。在欧阳修与韩琦的书信往还中,就不断可见二人关于疾病的交流。熙宁二年(1069),欧阳修知亳州,当时韩琦正为“脏腹多不调”所苦,因而欧阳修劝韩琦“更乞节慎饮食,酒能少戒尤佳”,并顺便说起自己病后戒酒,以及“近秋冬以来,目病尤苦,遂不复近笔砚”(53)欧阳修:《与韩忠献王》其三十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45—2346页。的近况。很明显,欧阳修与韩琦共同的交流语境促使了尺牍中疾病叙事的细致展开。苏轼与钱勰也多有谈药问病的书信往来。元祐四年(1089),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致信正在越州的钱勰,半开玩笑地说道:“惟腰脚蹒跚,略不相让,可以一笑也。”显然是得知钱勰腿脚不好,而以自我调侃的方式让对方开心。在此语境下,苏轼开过玩笑便认真地与钱勰分享药理,提出自己逐渐平复是因为“惟用温补药”,并力劝钱勰不要“每用朴消、大黄,昼夜洞下”。(54)苏轼:《与钱穆父》其十,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466页。朴硝与大黄都是性寒之药,苏轼认为钱勰服此治病是有害的。从后来的书信中,又可见钱勰再向苏轼索取紫雪丹,此亦治热病之药,于是苏轼再劝“中年岂宜数进此药乎”。(55)苏轼:《与钱穆父》其十一,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466页。尺牍中很多时候写到疾病、药理、养生等身体相关的内容时,都是因为文人在书信往还之间创造了一个高度互动性的对话语境,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疾病与身体而展开叙述。而在不断的书信往来之间,关于疾病与养生的交流也渐渐深入,这就使衰病叙事成为尺牍文本中一类常见的话题。
作为疗愈的衰病叙事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疾病那样让人专注于自身感受,同时改变对生活世界的认知。疾病销磨着人的肉体,却也可以让人的精神成长。宋诗中对衰病的戏谑,即可视为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在经历病痛后精神成长的产物。相比于中晚唐诗中的衰病书写,宋诗中对衰病与死亡的态度显得更为成熟。即便如韩愈的《落齿》最后用道家的潇洒翻出新意,但由落齿而惧死还是萦绕在诗中的主基调,更不用提孟郊、李贺那些涉病之作。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帮助了北宋文人走出疾病与死亡的阴霾呢?
当衰病降临时,人们会不接受、迁怒于命运、不甘心甚至会抑郁,最终才走向接受。(56)Elisabeth Kübler-Ross, On Death and Dying: What the Dying Have to Teach Doctors, Nurses, Clergy and Their Own Families, New York: Scribner Book, 2014.这一过程无疑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尤其是因为疾病造成的失能而产生的孤立感、无意义感往往更令人痛苦。不少文人尺牍中都流露出这些感受。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已患有眼病、牙病、臂痛等诸多疾病,这使其改变了生活习惯,他对王素说:“呵呵。酒绝吃不得,闻仲仪日饮十数杯,既健羡,又不能奉信。”(57)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五,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88页。流露出对健康人的羡慕。两年后再度致信王素时,欧阳修的心态似乎更加沉重。他不再使用“呵呵”这样的玩笑之辞,并且感慨:“富贵浮名,何可久恃?至于妻、子,亦不能保。”这种感慨很可能源于数年病痛带来的身体上的缺失体验,演绎为世间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而消逝,所谓“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为之悲也?”(58)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十,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90页。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经历病痛后的旷达,但对欧阳修来说却是一种“认命”,同年他与王拱辰的书信中,已经深刻意识到对于他的牙病,无论是“道家修养”还是“患者医方”,(59)欧阳修:《与王懿恪公》其七,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96页。都已无力改变什么了。

面对不可逆的疾病与衰老,医者并非只有药物和手术,更可以去倾听与抚慰。现代叙事医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开创的。叙事不仅是最常见的文学表达,也是一种心理疗愈方式。通过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亲友倾诉病情,患者首先获得了情感宣泄与交流;收到来自他人的安慰或者治疗方法;进而还会实现对自己身体的凝视与体验,获得哲学思考与心理疗愈。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重新体悟生命的意义,获得坦荡、豁达的心态。而尺牍正好为北宋文人提供了心理治疗的可能。
文人对于衰病的倾诉首先体现在尺牍的重复书写中。尺牍本就篇幅短小,便于书写、传递,可以实现类似“群发短信”一般与多人的交流。而最常被群发的就是关于衰病的内容。欧阳修于皇祐年间患眼病,他分别与杜衍叙及“目疾无悰”“眼目昏暗”(62)欧阳修:《与杜正献公》其五,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55页。的情绪,与孙沔叙及“迩来目昏,略辨黑白,耳复加重”(63)欧阳修:《与孙威敏公》其一,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62页。的症状,与苏颂叙及“病目眊然,无以度日”(64)欧阳修:《与苏丞相》其三,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64页。的烦闷;嘉祐年间患臂痛,又与吴育叙及对生活的影响,“左臂疼痛,系衣、搢笏皆不得”,(65)欧阳修:《与吴正肃公》其三,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73页。与赵槩和王素叙及导致疾病的原因,“以几案之劳,凭损左臂,积气留滞,疼痛不可忍”,(66)欧阳修:《与赵康靖公》其三,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79页。“几案之劳,气血极滞,左臂疼痛,强不能举”。(67)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88—2389页。这些病痛叙述的内容都很相近,甚至写给赵槩与王素的文字几乎完全一致。编入全集后,它们可能是重复乏味的。但对于欧阳修本人而言,却可以获得多位友人的关怀,同时又在反复的书写中不断观察自身病体、体验病患,是其最终接受衰病的必要过程。
类似情况在黄庭坚、苏轼、孙觌等人那里也如此。在与胡逸老、俞澹、王云兄弟、宋子茂等多人的尺牍中,黄庭坚都在倾诉臂痛之苦,有时是谈治疗方法,更多则是诉说自己的精神状态。孙觌也不断与人诉说疮痏之苦。更典型的是苏轼。绍圣二年(1095),苏轼在惠州患痔疾,他也分别致书黄庭坚、程之才、王庠、邓守安等,谓:“数日来苦痔疾,百药不效,遂断肉菜五味,日食淡面两碗,胡麻、茯苓麨数杯。”(68)苏轼:《答黄鲁直》其四,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33页。“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断酒断肉,断盐酢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粳米饭,惟食淡面一味。其间更食胡麻、伏苓麨少许取饱。”(69)苏轼:《与程正辅》其五十三,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612—1613页。“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几百日,缘此断荤血盐酪,日食淡面一斤而已。”(70)苏轼:《与王庠》其一,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820页。“痔疾至今未除,亦且放任,不复服药,但却荤血、薄滋味而已。”(71)苏轼:《与邓安道》其四,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855页。几封信说的都是痔疾后断荤食素之事。可是在一次次的疾病叙述中,苏轼有了不同层次的体认:与程之才讲到胡麻、茯苓的药性、烹饪方法,停留在抵抗疾病的卫生层面;与黄庭坚、王庠谈此事则引申到戒严与枯槁之味,已经上升到修身养性,但仍有自我与外物的界限;至与邓守安的信中则上升到“达观久,一喧静”的哲学思考,看惯了喧闹与清静无别,当然也就理解了生死之间的自然连贯。通过在群发的尺牍中反复咀嚼病体、审视疾病与治疗的过程,北宋文人形成了从饮食、药理知识到修身、悟道的多重思考。这让他们有可能在精神上跳出病体,以超我之心观察自我,从而在他者的关怀之外找到自主的解脱之道,驱散衰疾的阴影。
尺牍的核心属性是交流,文人通过尺牍相互存问、倾诉病痛。此时,尺牍中的衰病叙事就成为一场漫长的告别。突然传来的噩耗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甚至产生恐惧。但在长时间的交流中,文人们不断获得他人身体状况的消息,同时又不断审视自己的身体与疾病。孙觌在回复李擢的慰问时,就先描述自己“老境衰残,夏秋感疾在肤革间,虽不至卧病,而块然危坐一榻之上,奄奄弥时”,(72)孙觌:《与宫使李尚书》,《孙仲益内简尺牍》卷二,第5a页。接着又平静地叙说女弟新寡与胡松年之死,整封信都像是一场告别。在这一过程中,死亡并不因为突然降临而带来恐惧。相反,它有条不紊地到来,留给文人足够的时间去理解生命;它在友朋的陪伴中到来,让文人来得及与他人、与自己和解。苏轼重病之际说:“庄生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73)苏轼:《与钱济明》其十六,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56页。这种心境既是与世界的和解,亦是在生死面前放下执着,找回谦卑之心。而尺牍这一文体本身就蕴含着谦敬的体性,不仅体现在开头、结尾的那些敬语之中,更显现在其叙事之中。
充实生命的意义
尺牍往还中的衰病叙事缓解了文人的心理焦虑。在他们重新审视了身体与生命后,再度追问什么是死亡,也就对生之意义有了新认识。
对疾病的思考首先让文人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在重新审视自身后,他们发现追求身心的自适才是切身之事。范仲淹在与其三哥的家书中就如此开导他:
今既病深,又忧家及顾儿女,转更生气,何由得安?但请思之,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将息。(74)范仲淹:《家书·中舍》,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第571—572页。
如果畏惧生死,那么人将无时无刻不陷入深刻的恐惧之中。唯有意识到“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将死亡视为自然的过程,才能“放心逍遥”,从外物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这是为了更好地恢复身体,也是在给生命做减法。而在减去不必要的束缚后,文人心中真正的追求便可以显示出来。
文人最重视立言不朽,在涉及衰病的尺牍中,也最常见到相关的执着。嘉祐三年(1058),欧阳修致信王安石:“某自新春来,目益昏,耳亦不听,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毕,遂恐为庸人以死尔。”(75)欧阳修:《与王文公》其一,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67页。担心因衰病而影响写作,失去生命的价值。当时他与赵槩、王素、张方平等人的尺牍中,也频频提及对《新唐书》的牵挂。王安石也是如此。在其晚年与吕惠卿的书信中,他已参悟了人世的如梦似幻,体验着自己“虽无大病,然年弥高矣,衰亦滋极,稍似劳动,便不支持”的身体状态。而此时最令他挂念的是《字说》尚“未得致左右”。(76)王安石:《再答吕吉甫书》其二,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1804页。一旦正视衰病与死亡的阴影,文人们反而更激发起文章学术的毅力与热情,追问究竟怎样才算活着,怎样活才有意义?
北宋文人又以趣味充实生命,玩物赏美成为文人趣味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素有收集碑刻拓片的爱好。嘉祐四年(1059),病中百无聊赖的他致信王素,请其代为拓打蜀中碑刻:“如今只见此等物,粗有心情,馀皆不入眼也。”(77)欧阳修:《与王懿敏公》其五,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88页。以此作为病中的乐事,或者按《集古录目序》的说法:“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78)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600页。欧阳修在收藏中获得愉悦,也在其中看到生命脆弱的痕迹,就好像他在《唐韩覃幽林思》中所列一连串故去的友人之名。铭文是脆弱的,生命亦然;可是欧阳修却迷恋于此,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在为金石拓片撰写跋尾,这同样也是对生命的迷恋。类似地,在黄庭坚、苏轼、孙觌等人的生命中,也不乏对石刻、书画、古籍的收藏、品鉴,更不乏对生的迷恋。黄庭坚雅好书法,即便在晚年眼病严重到“目前已有墨花飞坠矣”(79)黄庭坚:《跋为王圣予作字》,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609页。之时,仍热衷与人在文字间交流书法行笔之意。而他也把交流书法的热情保持到生命最后阶段,在宜州时仍与张熙载交流用笔作字之道、分享《兰亭禊饮诗叙》的摹本。建中靖国元年(1101),晚年的黄庭坚回顾自己的书法作品,忽然想到星家预言:“六十二不死,当寿八十余。”(80)黄庭坚:《跋旧书诗卷》,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第614页。可见在他心中,对书法的迷恋正与对生命的迷恋等同。而北宋士大夫这些兼具学术性、艺术性的玩物活动,也由此得以在“玩物丧志”的传统质疑下,发展出独特的兼具生命意识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在正视了衰病与死亡,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后,北宋文人找到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安详地与衰病共存。在诸多文人中,黄庭坚似乎是最接近儒医身份的文人,(81)关于宋代儒医阶层的兴起与医学知识的传播,参见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93—205页。他乐于给别人开药方、谈养生:如与王云讲气体饮食的调养之道,又给他开调养腑臓之药;给郑仅开河鱼丸、桃红丸等来治疗痢疾;教王直方艾炙法治疗病疽,用托里散、追风散、云母膏治疗疮毒;建议逢兴文用犀角丸和竹沥法治疗儿子的痈肿等等。可是作为儒医的黄庭坚最终也不得不与疾病和解,在宜州的岁月里,他似乎终于意识到已不知如何用药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在两次向子泽判局问药后,便不见他执着于治疗。在他去世那一年的《宜州家乘》中,只见他与友人对弈、游览,与远方亲友密切书信往来,甚至还开了肉戒,品尝鱼、羊、海鲜等美食,愉快而安详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直到最后几日的日记中只剩下一个“晴”字。
黄庭坚将生命的安详留在了他的日记中,欧阳修则带着对生命的安详完成了他的旷世名作。熙宁三年(1070),衰病中的欧阳修写作了名篇《泷冈阡表》。这篇为父母所写的墓志铭突出了“有待”这个关键词,“待”其一生功业来告慰先人在天之灵。此时的欧阳修已经接近生命的尾声,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等。这篇告慰文字何尝不是他在生命尽头,平静地回忆父母之教与爱的产物呢?接受了衰病反而让他可以平静地回忆人生,正式地与故去的父母告别。在《泷冈阡表》中,欧阳修对父母的追忆止于郑氏“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句话,(82)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394页。虽然这是母亲在欧阳修被贬夷陵时对他的安慰。但是放在文章写作的当下,这个“安之”又恰好是欧阳修此刻的心境。从他这一时期与人的交流看,他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衰病如昨,目、足尤苦”的病体,将其视为“老年常态”。(83)欧阳修:《与赵康靖公》其九,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2381页。因而在欧阳修生命的尽头,后人看到的不是背对衰亡的恐惧,而是在安详于人生后,与衰亡的共舞。
在持续不断的交往中,北宋文人通过衰病叙事完成了对自己身体的重审,进而在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之后,理解生命,保持对生命的谦卑之心。也是不断经历着这种心灵的治愈,让他们能够更为安详、坦率地面对疾病、衰老与死亡。如此,便不难理解宋人何以能够开创一种新的文学抒情传统,何以能将令人恐惧的疾病与衰老重塑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
余论:北宋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疾病和衰老总会令人不悦,可也正是痛苦让人类、也让文明得以成长。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文人对生命的思考逐渐细腻、深入。作为早期书信文章的典范之作,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就流露出“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8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之下对生命、身体与友朋的细腻温情,并汇入魏晋时期文人生命意识觉醒的细流之中。而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衰病叙事,又未尝不可视为中国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所谓生命意识,其实就是如何面对生命的枯荣。儒家往往回避这一问题,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85)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先进第十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3页。其实是逃避对生死问题的讨论。而在北宋理学观念下,人们把心性论与宇宙论统合起来,司马光孜孜不倦地说教:“夫人之有疾也,必自于过与不及而得之。”“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也。”“内和则疾疹不生,外顺则灾患不至。”(86)司马光:《答范景仁论养生及乐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五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9、61页。可是内圣式的修养并不能改变生老病死的节奏,“某某则某某”的因果逻辑链条,只会让人在面对衰病时更加不甘、更难于接受。苏轼在接到秦观的死讯时,就反复哀叹不已。因为在他看来,秦观明明“谪居甚自得”、(87)苏轼:《答黄鲁直》其四,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533页。“饮酒赋诗如平常”,(88)苏轼:《与欧阳元老》,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756页。不改平和中正的修身之道,可是却英年早逝。生死之间没有因果可言,传统哲学并没有完整地告诉人们该如何认识生死。
而日常往来的尺牍以及其中的衰病叙事,却让文人们一次次真实地置身于生死之间的语境中,并促使他们思考。在尺牍中交流病患就像一场漫长的告别:文人们看到他人的患病、康复、失能、衰老,最后收到讣告;在叙事话语间,又伴随着馈赠、建议、玩笑、抚慰与倾诉。在这场漫长的告别中,文人渐渐意识到老病如时序一般不可逆转,他们唯一能做的是让生命之花在漫长的四季中更好地绽放。艾朗诺总结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发现了“美的焦虑”,即“以前被认为离经叛道的娱乐和各种对美的追求得以见容,而且可诉诸文字”。(89)[美]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不错,北宋文人是在正视了生命的脆弱后,依然以有情的执着去充实生命。在石刻、花卉、艺术等赏玩中,既留下美的享受,亦凝固为《集古录》《洛阳牡丹记》等为代表的“不朽之作”。从绽放生命的意义上,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何以在离经叛道的“焦虑”中,北宋士大夫依然能够如此追求美的享受。
如果说魏晋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开始意识到生命的短暂;那么北宋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则是开始懂得如何让短暂的生命绽放得更美丽。他们的生命态度可以反过来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在漫长的衰病叙述与交流中,文人理解了死亡,同时更加执着地迷恋生命。这形成了中国式的生命观与宗教观:即在认定生命的悲剧性前提下,还能执着于人生;在立足于红尘的、入世的立场上,去理解出世与解脱。于是,当人们追问什么是死亡的时候,北宋文人用其“不朽的生命”回答了到底怎样才算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