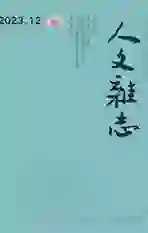苏门反性命之学发覆
2024-01-09乐进进
乐进进
内容提要 性命之学伴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而风靡于世,其特质是对以往儒学系统的哲理性深化。但其兴起之初,便因圣人不论的名义受到以欧阳修为首的官方话语机制的排抑。王安石借由秉政契机将自家性命道德理论定型为国家意识形态,招致以苏门为代表的士人奋起抗争。苏门将外则误国、内则自误作为立论依据,构筑反性命之学的阐发框架,进而将矛头直指性命学说的理论渊源,既抨击释氏心性学说背离原初教义,又对四书体系中的性命资源另作诠解,由此完成性命之学的理论解构。同时,苏门以老庄学说为根柢构建超脱先验道德意识的性命体系,摒弃以善恶范畴为标准的人性探讨,其本质亦为反性命之学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性命之学 反性命之学 欧阳修 苏轼 苏门士人
〔中图分类号〕I206.2;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12-0029-09
宋代性命之学的兴起实质是对汉唐经学的疏离与改造,从章句注疏到义理之学乃至性命之学的转向,无疑是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全新阐释与体系重建。佛学义理的渗入与四书学经典系统的塑造促成了北宋儒学复兴思潮,但历史进程并非单行道,勢必存在着话语争夺的激荡与波折。其间,反性命之学的思想逆流并不意味着对于汉唐注疏的复归,而是呈现出相互歧异的理论抗争。对于性命之学的反抗本身也被裹挟在历史潮流中,展露出时反时论、论而实反的时代风貌,苏门的学术面相堪称典型。杨治宜指明苏轼的心性观点经历过阶段式变迁,即从早期斥而不谈的矛盾犹豫过渡到晚年明确化的人性论,但内在理路又存在着一致性。①虽未以反性命之学为线索,但其将苏轼看似矛盾的思想主旨融贯为相反相成的学术理念,为归纳苏门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思路。朱刚提出苏辙“把禅宗的实践功夫全面地导入儒学”,也隐约透露出苏门反性命之学的辩争策略。②叶平《苏轼、苏辙的性命之学》与金生杨《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均从儒学复兴潮流中抉发出反性命之学的历史图景,可谓慧眼如炬。③ 但此论述多流于现象揭橥,对于北宋反性命之学的演进脉络、体系建构,不免浅尝辄止。尤其是苏门作为时代逆流中的翘楚,如何铺设理论框架、呈现辩证逻辑与内在旨趣,尚未获得充分的诠述。本文以反性命之学的时代演变为逻辑顺序,探究苏门反性命之学的学理依据、言说策略以及别有所指的性命之学,由此揭示宋学所笼括的多元化趋向。
一、排抑太学体与反性命之学的先声
儒家的性命之学本由佛学心性理论借鉴而来,此前的儒释理论仍呈现出内外修养领域相互隔绝的态势。宋初儒者沿袭李翱的理论框架着手发掘性命领域,但其声势微弱尚不足以触发儒家阵营的自我分裂。直至庆历年间,以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为首倡,社会始掀起性命之学探讨的热潮。曾巩虽向欧阳修极力举荐王安石的学术文章,作为文坛宗主的欧阳修却一眼看破王安石性命学说的理论渊源,试图针砭其弊:“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①换言之,这一事件正可视作对当时性命之学的隐晦式对抗。
至和间,欧阳修始就性命之学的推演明确表述自己的反对意见,其论证依据可归纳为两方面。首先,儒家圣人对此问题避而不谈,由此推导出“性非学者之所急”,欧阳修所据以阐论的是六经系统中的学术趣向:“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②其次,人性为贤愚所共有,善恶与否在欧阳修眼中并不妨碍道义的施行教化:“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恶,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者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③相较人性善恶的确认,欧阳修更注重后天教养习得的决定性作用:“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④无论是圣人不谈抑或是性说的无关紧要,欧阳修始终呈露出将其存而不论的搁置态度,尚未做出言辞愤激的抗争姿态。作为引领性命潮流的先驱人物王安石对此终究意存不惬,先是借由道义传承身份的自我认定来反抗欧阳修以文学能手视之的表层界定,⑤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反过来对欧阳修生平学术文章的评骘:“介甫对裕陵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惟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⑥所谓道理者,在神宗、王安石的谈话语境中实即指向道德性命之理。
除却教诫士子慎毋执着于性命学说的探讨外,欧阳修仍有付诸实践的排抑举措。嘉二年(1057),欧阳修受命主持科举取士,有效遏止了风靡一时的太学体文风。但嘉太学体的特征却存在争议,以往多将其定义为奇险僻涩的古文风貌,土田健次郎率先提出“现存的孙复、石介的文章,不但并不晦涩,毋宁说是极为平易明白的,所以仍有重新检讨的必要”,⑦朱刚进而将嘉太学体视为性命之学探讨的文字书写,⑧可谓振聋发聩。而恰在意图扭转太学习气的欧阳修主持贡举时,擅论性命道德的程颐折戟失利,其缘由亦指向欧阳修反性命之学的选录标准。职此之由,程颐不免对考官欧阳修心存芥蒂,语录中几乎不论及欧阳修。程门高弟杨时则有意驳斥欧阳修之说:“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尽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⑨杨时借由排诋考官不晓性命的学术趣向,透露出为其师惨遭黜落而作翻案辩护的隐含意蕴。
王安石与程颐皆属北宋性命之学得以兴盛的关键性人物,其思想学术在对先秦儒家经典做重新发掘、阐释与体系建构后,实质上促进了儒学深化与宋学特质的定型。但在其发声初期,仍属于冲破旧有束缚的尝试阶段,欧阳修敏锐觉察到这股潮流对儒家经世致用之学可能产生的冲击,他以文坛领袖与官方权威的双重身份试图扼制其势头的壮盛,无论是言语的针砭或贡举的排抑,均对性命之学的推演产生了延缓的功效。然而时代潮流不因个人而停滞,新学与洛学均在嘉之后声势日盛。欧阳修作为反对权威无形中成为此后学术主流的批判对象,但其反性命之学观念已然深入门生苏轼等人的学术根柢中。在性命之学升格为官方权威后,苏门群体便对主流话语发起挑战。
二、性命之学的双重缺陷与修养路径的重建
儒家士大夫的性命之学由历史的潜流腾涌为风靡于世的时代思潮,与原先的私人学术话语抬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王安石熙宁年间执掌政柄,尤与神宗君臣相得。其企图借由自身的性命学说“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从而扭转“家异道,人殊德”①的社会紊乱局面。伴随《三经新义》《字说》成为经义取士的官方教科书,王氏性命之学嬗变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定于一尊。士子为求得谋生之阶不免对之亦步亦趋,并演化为非性命道德之学不谈的社会境况。性命理论掌控政局及社会的强制性、延续性,可就陈馞之语管窥一斑:
“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不习性命之理者谓之曲学,不随性命之理者谓之流俗。②
科举新法所造就的性命之学探讨习尚,日益招致苏门士人的奋起反抗。试回顾欧阳修主盟文坛时的状况,其反对性命之学属于官方权威对私人学术的压制,所用托辞无非圣人不论以及谈性与否无关紧要,均可被视为模棱两可的抵抗姿态。相较于此,苏门士人所面对的是席卷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其试图对此现状作出反拨,必然只能借由文字辩论的正当性予以抨击,从而对知识阶层起到劝诫之用。其论证逻辑在于批判性命之学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中包含误国与自误两类。
性命之学注重向内工夫,非有外在事功、形式规范等具体指标得以衡量,其理论探索往往泛滥而无所归,此即黄庭坚所谓“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③苏轼亦云“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④ 因此,置于科举考察人才的科场,以性命之学为研讨对象的学术机制更容易滑入虚无的深渊,由此选拔出来的空谈型官僚反而会阻碍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魏晋时期雅好玄谈以及大历之际崇佛尚教的社会风尚,首先被苏轼引入类比范畴:
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致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世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⑤
此论以历史故实为鉴戒之资,巧妙处在于选取说玄辩道、空谈误国的王衍、王缙之徒,其人物姓氏恰与王安石暗合,锋芒所指可谓溢于言表。苏轼从正反两面分别攻讦性命之学的探讨对于政事操持毫无裨益,抉露其实质为能者无用、用者无能的二律背反困局。苏轼的引史为证策略为时人所广泛汲取,而试图以性命道德同化社会风俗的王安石,也逐渐在众人的文字叙述中化身为大而无当、亡国灭身的王衍形象。以科举选拔、治国理政作为驳斥视角,采取的是性命之学的内省工夫与经世致用的外在事功相互背离的推演结构。一言以蔽之,即苏轼所云“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①
除了通过历史演绎推导出空谈贻害于政权的长治久安,苏门士人反性命之学的辩说特质还在于发掘性命之学对于个体修养的无所裨益。其立论远溯性命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就性与天道无法诉诸言语的特征一笔抹杀高谈阔论的演绎根基。苏轼借用譬喻巧妙地将道不可捉摸、难以言说的性质形诸笔端:“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与烛也。……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②与苏轼的论证异曲同工的是,苏门弟子晁補之也以寓言形式将“道无言,凡言之类妄”的玄妙属性悉数道出,“燕人之晋,问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饮者,燕人也。若乃夫晋人之朝夕饮者,则未始问燕人。故学道犹饮,问而告之,燕、晋之类也”,③借由辞不达意的必然限制,杜绝旁人企图将性命道德学说转相授受的野心。苏轼关于性之难于显见的述演框架,与转相譬喻而终究不得其真的道论逻辑机杼全同:“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④换言之,苏门士人是将《论语》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⑤的语义指向落实到宋儒性命道德理论的空口无凭。
苏门群体从授受传递的角度否决性理学说探讨的可能性,进而指出沉溺于语言游戏的危害便是妨碍个体修养。苏辙抬出《论语》中逐渐被历史湮没的子夏,作为孔门学术大力阐发,以日常洒扫乃至渐进于道的个体修养法对抗虚幻无根的性命言论: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而不急于道,使其来者自尽于学,日引月长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今世之教者闻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虽礼乐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于洒扫应对进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学未必信,务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伪,自是而起。此子贡所谓诬也。⑥
在苏辙语境中,纯然以性命道德为主体的今世教者被视作孔门教法的对立面,由此勾勒出教人学道而终究与道相失的修养困境。因此,苏辙以为道不可教,而借此生发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自至法更是苏门论辩的共通策略。苏轼以“致”为途径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自述理论渊源及内在含义云:“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⑦为证明其事,苏轼虚设南人日与水居,不学而能没的寓言,批判终日学没而不能的北人,借以指代终日空谈道德性命而一无所获的儒家士大夫。黄庭坚面对旁人求教性命之学,也以“诬”字视之,并明示从学路径:“‘君子之道,焉可诬也?吾子欲有学,则自俎豆钟鼓宫室而学之,洒扫应对进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学经乎?曰:‘吾子强学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玺之文可印也。”⑧同样取径于日常琐事的修习,黄庭坚的叙述话语也来源于子夏教学法。所谓“强学力行”,正是追求渐趋升华而自至道德境界的修养方式。此类避免谈道论性而注重现实行事的论说逻辑,无疑是苏门群体的理论特质。
综上所述,苏门群体将性命之学的现实危害归纳为两类:外则误国,内则自误。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给士子阶层的王氏性命之学,其所掀起的社会风潮被苏门士人视作空谈误国的历史重演,这是从国家治理视角发论。同时,性命之学无法言说授受的内在特质决定其风行本身便是对个体修养的戕害,所以苏门转而提倡渐进于道的子夏修身路径。
三、佛学性论的解构与四书文本的再阐释
宋代儒家性命之学的兴起,其内核的理论框架本自佛学假借而来。且不论王安石自道其学术体系融合诸子百家与佛道思想,理学家虽竭力攻击释氏之本领归处不正借以撇清彼我关系,但南宋事功学派领袖叶适却一针见血地阐明“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① 同时,北宋儒家为寻求性命理论的自我正当性,从原始的儒家文献中发掘乃至建构起与五经系统相颉颃的四书学经典体系,并借由性命化视角予以全新阐释,可说是性命之学的合法伪装外衣。因此,佛学性论的儒家化与四书诠解的性命化合力构筑了北宋性命之学的基石,苏门士人的反抗策略便就其学说发轫处解构其理论体系。
六朝以降,儒者治国、佛老治心的二元结构始终是佛学得以横行无阻的生存凭据。然而,心性义理之学的探讨并非佛教思想的全貌,原始佛教的内在自省实则更倾心于日常修持的渐悟式工夫。伴随南宗禅的风靡于世与儒家性理之学的反向刺激,宋代佛学呈现为机锋百出的文字禅,佛教以朴素自持的禅林修行方式逐渐衰落。苏轼的佛教建筑类记文常涌现出追踪原始佛教的怀古情结,实质是就佛学的宋代转型予以针砭: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熏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②
其想象中的佛教徒形象均附着苦行僧的典型特征,而求得佛道的艰难程度远非含混其间者所能忍受。同时,苏轼点明禅门的教义精华尽皆荟萃在佛教传来之初,内核可综括为行善以自持的修行路径:“袁宏《汉记》曰:‘浮屠,佛也。……贵行善修道,炼精养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国始知有佛时语也。虽若浅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尔煮食之尔。其后卖与市人,遂入公庖中,馔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③在苏轼看来,尽管后世对于释氏义理有所扩充,但其之所以为佛教的立足根基始终无法超脱于此。往时记忆的大肆渲染,意味着对于当下境况的心存不惬与抗争意识。那么,苏轼如何看待现下的佛教现象?试观其文:“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④原始佛教自苦以利人的行善自修教义,一变而为安坐宴居、高谈虚论的享乐者形象。更有甚者,苏轼将其心性义理之学斥为荒唐之说,推究其本质不过是语言的把戏。儒家的性命理论内核既从佛教借鉴得来,那么,苏轼对佛学的批判正是从渊源上否决北宋性命之学的合理性。
苏轼用意将释氏的谈玄说性症结推衍为整个社会知识阶层的共通病灶,由此借助圣人言行的权威性规讽其弊病:“近世学者以玄相高,习其径庭,了其度数,问答纷然,应诺无穷。至于死生之际一大事因缘,鲜有不败绩者。孔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世无孔子,莫或叩之,故使鄙夫得挟其空空以欺世取名,此可笑也。”文本旨趣原是彰显荆溪居士所作释教《传灯传》“扶奖义学,以救玄之弊”①的理论功绩,苏轼扩充此举的适用范围,矛头直指儒家士人空谈性命的欺世盗名现状。因此,苏轼以佛教初传时的原始朴素作风为释氏的行动典范,抨击现下佛教徒捕风捉影的禅学机锋与玄谈习尚,而袭用佛学心性框架借以建构自身体系的儒家学者更属等而下之的序列。朱熹就此攻击苏轼不明儒家性命之学,所以诋斥禅学未得其要:“夫其始之辟禅学也,岂能明天人之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阁》、《中和院记》之属,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据彼之外以攻其内。”②此论以心性义理为禅学精要,恰能见出苏轼反性命之学的应对策略正是要跃出性命之学探讨的圈子之外,一并扫除其时儒、释所共同青睐的话语展开框架。
黄庭坚的哲学体系虽主张儒释道融通,其本位却趋向于原始儒家的修养工夫。因此,在选取释氏理论证明己说时,其往往呈现出对于佛学心性论的摒弃,唯独汲取苦学力行的原初佛教义旨,对于士子的教诫尤为如此:“物材、美火齐得,然后成鉴,鉴明则尘垢不止。明虽鉴之本性,不以药石磨砻,则不能见其面目矣,况于下照重渊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学者之心似鉴,求师取友似药石。得师友,则心鉴明矣;求天下之师,取天下之友,则弥明矣。”③心镜的磨拭与否本属禅宗五祖衣钵授受的著名话头,慧能以无心无尘之论获得首肯,而神秀所书之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④虽被弘忍视为未能登堂入室之作,但却演化为北宗禅的肇端与宗旨所在。相较于南宗直指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理论,黄庭坚以弥明之义搭配磨砻之鉴,无疑是对神秀偈语的效法与演绎。所以,黄庭坚反抗时下性命之学的社会风潮,亦是就儒、释理论一道驳斥:“深根固蒂然后枝叶茂,导源去塞然后川流长。浮图书云:‘无有一善从懒惰懈怠中得,无有一法从骄慢自恣中得。此佳语也,愿少垂意。不加功而谈命,犹不凿井而俟泉也,此乃齐智之所知。”⑤引佛教语以排诋性命之学的探讨习气,可谓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与苏轼的辩说策略一脉相承。
宋代四书体系的建构、定型与经典化亦可概括为四书的性命化阐释历程,《中庸》《孟子》以其性命话语的丰富而格外受到重视。苏门群体的反性命之学试图解构宋代四书学的话语诠解体系从而揭穿空谈风气的表面伪装,苏轼总其大要为:“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⑥有鉴于此,苏门士人欲图扭转四书诠释的性命化倾向,但其阐论本身并非汉唐经学的复归,而是独具苏门理论特色的新型注解。
《中庸》在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经典地位的升格,其兴起之由缘于儒释两家或明或暗地均以之作为性命义理具备原初正当性的权威资源。为纠其弊,苏轼开篇明义地指出:“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⑦诚在《中庸》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属于核心范畴,唐宋儒家士人亦借之建构起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性理学说,其演绎路径可从程颐话语中蠡测其貌:“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⑧以诚等同于天道或是天理,意味着将其抬升为先验道德本体,借以作为沟通宇宙规律与圣人境界的桥梁。苏轼径直揭开理学家赋予“诚”的玄虚不定面目,基于个体行动的情感导向予以切实可感的界定:“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①苏轼诠解的“诚”并不具备本体论的意蕴,而是圣人据之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苏轼援引孔子厄于陈蔡的历史典故,阐明处于忧患而不改所学所知之乐即为圣人之诚,其理论构想直指现实处境,丝毫不夹杂神秘色彩,无疑是对天道性命诠释框架的反拨。
孟子由传入经的唐宋升格属于多方面因素的叠加,若以理学家的阐释话语为考量中心,孟子身份的定型则可归因于其人性论思想为儒学性命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核心价值的判断:“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②程颐此论几乎是理学家的共识,虽说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分立的二元结构为宋儒新创,但从孟子性善角度推演而出的先验道德本体却是天命之性的立论根基。因此,苏门群体对于孟子人性论思想的驳斥正是其反性命之学的重要环节。苏轼率先就孟子辨别人性善恶的行为发难:“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③苏轼从孔子—子思—孟子的孔门学术传承脉络出发,指出性善论为孟子对于先圣学术的误读,其抗争策略在于搬用圣人不言性的至高权威压制宋儒所不断抬升的孟子地位。苏辙对于孟子性论的解读与其兄长别无二致:“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则指善以為性。”④与此同时,苏门群体试图从个体践行层面重新定义孟子思想的精华,黄庭坚教导后学治心养性的途径即为“强学自重,读《论语》《孟子》,取其切于人事者,求诸己躬,改过迁善,勿令小过在己,则善矣”,⑤实际上是直截了当地忽略被宋儒视作性命之学原始资源的核心部分。苏轼进而阐论孟子学说的旨趣所在:“唯其不为穿窬也,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此其所以为孟子欤!后之观孟子者,无观之他,亦观诸此而已矣。”⑥苏轼所重出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正是借由日常修养循序渐进而自致于道的别样表述,隐约透露出“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⑦的规避空谈以至回归现实的践行指向。概而言之,苏门士人的反性命之学不仅就时下性命之学盛行的危害针砭讽喻,其应对逻辑也尝试从根源上抹杀其思想内核的合理性与经典诠释的正确性。
四、作为反抗策略的苏门性命之学
苏门以群体力量反抗着主流价值体系性命之学的风起云涌,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亦被迫就此问题作出解答,正如苏轼自述探讨性命的缘由云:“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⑧所以在朱熹看来:“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⑨然而,苏轼的性命之学仍是反抗时代潮流的延续,因此在当时理学士人的议论中,苏轼终究“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是故见于行事者,多非理义之中;发为文章者,多出法度之外”,①虽不无政党攻伐的一偏之见,但也折射出苏轼的性命学术并不拘守儒家藩篱。就性命之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宏观性与完整性而言,理学家在宋儒当中首屈一指,其理论内核的塑造源于孟子性善论,进而推演出先验道德准则。苏轼试图在此话语体系中另辟蹊径,理论资源亦须转而别求,朱熹排诋苏门学术即言其“性命诸说多出私意,杂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说尤可笑”。② 换言之,苏轼的宇宙生成论取资于以无为始的道家学说,试看其对道的阐释:“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③生生正是由无入有的演变历程,所谓“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夫大始岂复有作哉”,④余敦康将其描述为“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莫或使之,无主宰,无目的,也没有启示什么先验的道德准则,但却有一种神妙的自然之理在起着支配的作用”。⑤ 亦即是说,苏轼的道纯粹是自然规律的生成、变化过程,不附加社会道德的倾向性,所谓“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⑥与《韩非子》所作老子之道的诠解“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⑦如出一辙。实际上,苏轼汲取道家宇宙观,正是对理学家将道德境界与宇宙规律等量齐观的理论框架予以反拨。
与宇宙万物的自然生成一脉相通,苏轼人性论也是从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万物所共有的生命本能:“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⑧饮食男女的生物性并不为人类所独具,理学家探讨的性命之理径直越过此类本能,试图发掘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先验社会性价值。但是在苏轼看来,恰恰只有将善恶对立的道德思维消除之后,才是人性本质所在:“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⑨苏轼意图通过消除有关善恶的价值判断,烘托出人类本性非由善恶所能界定。从反向视角着眼,可见出人类既有为善的可能性,亦不排除作恶的可能性,因此,苏轼以为圣人与小人的行动轨迹均由是而发。
理学家奉《孟子》性善论为圭臬,苏轼为驳斥其论点,更向前选取《易传》作为权威佐证,并借之建构起儒道交融的性命体系:
夫仁智,圣人之所谓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⑩
苏轼运用火能熟物的譬喻验证“继之者善也”的逻辑严密性,苏辙更进一步阐明火亦具备为恶的倾向:“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恶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谓之水火,能上、能焚者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哉!”①焚物、熟物均是火的燃烧本质所招致的结果,或以为善,或以为恶,苏辙以为正是众人基于自我的好恶利害所后起的价值判定。因此,苏轼界定善恶原非人类本性所固有,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交往寻求共同利益的契约性表现:“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②从后起的、不固定标准的视角来看待善恶范畴,亦是将人性先天本质的探讨超脱于社会道德价值之外,可谓就先验意识的存在釜底抽薪。
苏轼对人所共有的生命本能的强调,正是“通过划定可能取得共同认识或不可能取得共同认识的领域,而使议论更容易走向一致”,③由此驱散性命之学探索、争辩的热潮。也就是说,当时争论不休的性善论、性恶论乃至性善恶混论,在苏轼的理论体系中都被视为后起的社会道德评判,均非人类原初的自然本性。那么,所谓的人性争论也就失去了探讨的价值。总而言之,苏门的性命之学自其肇端便站在先验道德意识的反面,在宇宙论、人性论、情性论诸层面皆与理学家的性命道德学说判然两途。苏轼着重解构了以善恶为讨论范畴的理论体系,就当时聚讼纷纭的人性论问题予以消解,其理论本身奠基于老庄自然学说,而实质是对以理学家为主体的儒家性命之学的反抗。
五、结语
性命之学作为宋代儒学区别于汉唐经学的重要特质,其兴起、演变、定型的发展历程并非一蹴而就。欧阳修作为庆历士大夫经世致用学术的文坛表率,性命之学甫一兴起便被他视作高谈虚论,由此受到官方话语机制的有意压抑。王安石的新法改革与理学家的群聚授徒,将性命之学推向时代主流。苏门群体便以文字辩驳为抗争武器,反对甚嚣尘上的性命道德理论。而苏门反性命之学在时代思潮的激荡中,也不断受到理学家门徒的反向攻讦,杨时的《杂说》、朱熹的《杂学辨》均属其列。但苏门群体的抗争言论也被納入性命之学的考量范围,理学家群体通过性命学说重新阐释苏门的话语旨趣,进而将其整合为自身的学术资源,从对抗走向消融。试观朱子对苏轼《中庸论》的遗神取貌:“苏氏此言,最近于理。前章所谓性之所似,殆谓是耶?夫谓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本然之至善矣;谓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为性之所在,则似矣。而苏氏不知性之所自来,善之所从立,则其意似不谓是也。”④朱熹从本然至善的视角诠释苏轼的性说,无异于郢书燕说。同时因为苏轼否决先验道德本体,朱熹又将其学说斥责为无根之木,可说是摭拾其文字表述而摒弃其思想本质。因此,在理学家的话语体系中,欧、苏等人逐渐定型为纯粹的文人角色,其反性命之学伴随着思想家身份的丢失,也逐渐淹没在后世主流儒家价值体系中,这恰是需要抹去历史的浓妆才能见到的真面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翼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