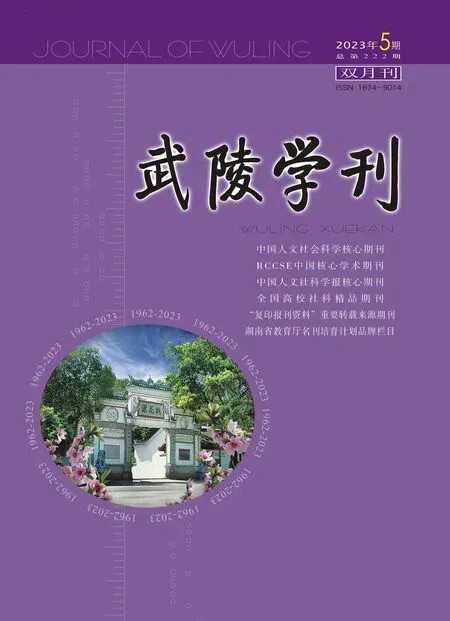曲笔与隐喻
——《白藤花》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苦难书写
2024-01-09桑东辉
桑东辉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自古及今,专制统治者意识里始终抱有“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的成见,并以文字狱来压制不同声音。在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亦深谙此道,一方面在满洲国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则极力压制反满抗日言论。文化专制熄灭不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爱国保种的信念,只能激起有良知的爱国人士更激烈的反抗。当然,作为文化人,爱国作家们并非都直接拿枪上战场与侵略者拼杀,他们利用手中的笔,以笔为枪,以字为弹,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抗争。支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以笔为枪的文化勇士,他也因此成为哈尔滨市唯一一位被中国作协授予“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勋章的抗战作家。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白藤花》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哈尔滨沦陷时期抗战文学的一朵最亮丽、最耀眼的奇葩,与其他优秀抗战作品一道共同点缀烘托起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百花园。围绕《白藤花》与沦陷区文学的书写方式,笔者重点从三个方面做简要的释读和阐析。
一、笔曲而义直
曲笔最早是古代史家的发明。后来,在曲笔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影射文学。到了民国时期,受当权者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文人们也往往采取曲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所有专制统治者一样,日本人在伪满洲国也实行严苛的新闻舆论控制。据支援先生回忆,当时敌伪专门成立了“弘报处”,控制新闻出版,把持舆论宣传,施行法西斯统治,规定不许写黑暗面,不许表现悲观情绪等等。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爱国作家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依然以曲折、隐晦、象征的手法,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1200。
言论不自由就会激发出新的表达路径,在民国时期,一些文人用曲笔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有研究者指出:“三十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高压直接作用于出版,使出版商‘为保血本’不敢再出版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刊物和书籍,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被大大缩小。为了让作品面世,左翼作家不得不改变直接宣泄政治激情的创作方式,转而采用各种‘暗示’、‘曲笔’的形式技巧来寄托政治理想,左翼文学表达的隐晦化和含蓄化不仅增加了文体的美感,也推动了文体形式的丰富和发展。”[2]左翼文学这种曲笔风格也被东北沦陷区的进步作家所继承和广泛使用,这在关沫南、陈隄、支援等作家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支援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曲笔的写作风格,比如不能提及高尔基就用“戈里”来代替,“塞北”字样犯禁,就以“寒冷的地方”来暗示“日伪政府”[1]1372。
对于东北作家曲笔写作的斗争形式,支援先生晚年曾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他指出,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界中,鼓吹法西斯、为日伪歌功颂德的汉奸文学、粉饰文学无疑是存在的,但以宣扬抵抗斗争为宗旨的反满抗日文学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总的说来,大多数作家在民族感情的感召下,以多种文艺形式,隐晦曲折地表达热爱乡土、仇恨侵略的爱国情绪[1]1199。
在日伪时期,支援先生坚持文学创作,用笔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如,《逃亡妇》通过一个在战乱中逃亡的妇人揭露了侵略者发动战争,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残酷现实。又比如,《群犯》歌颂了那些不愿做亡国奴的反抗者,虽然诗中描写的场景切换到了罗马尼亚,但实际上作者是采用“以借古喻今,以外说里的隐晦手法,暴露了一个最触及人心的罪恶残酷的故事”[1]1557。但总的来说,在不允许描写社会黑暗面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伪满洲国,文学作品是不可以直白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更不能触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支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在斗争策略上却显得十分成熟,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更多地运用曲笔,以达到笔曲而意直的效果。比如《极乐之村》中,他以“野孩子”冲进极乐之村行破坏践踏之能事,来抨击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蛮残暴。又比如,在《采野花的姑娘》一诗中,诗人通过抨击那不知羞耻的姑娘,曲折地暗讽了那些忘记国恨家仇、数典忘祖的伪满洲国的“顺民们”。
在支援先生曲笔表达的文学作品中,《白藤花》是最成功的。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在文网细密的伪满洲国,既然不能写日本人压迫中国人民,作者就巧妙地选取了俄侨房东这一对异国没落贵族为主人公,通过写俄侨在哈尔滨的艰难生活,间接揭露了日本统治下东北人民的苦难境地。《白藤花》创作于1941 年“12·31 事件”后,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巩固大后方而疯狂抓捕左翼作家、杀戮抗日反满作家的白色恐怖下创作的,这不仅需要非常大的创作勇气,同时,为了斗争的有效性和作品能够公开发表,更需要斗争艺术和创作智慧。这种斗争艺术和创作智慧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就是曲笔表达的文学技巧。有研究者指出:“那些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们,在血腥的镇压面前没有屈服,他们以更曲折、隐晦的方式与敌人周旋,继续战斗。他们是暗夜的萤火,那微弱的光亮虽不比上太阳、月亮,但它毕竟在暗夜中给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心灵里点燃了一盏明灯。”[1]1529而且正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曲笔等表现手法,使得《白藤花》“才蒙过那些有眼无珠的检查官老爷们的眼睛,得以在报刊上发表。他们在技巧高超的文学作品面前是睁眼瞎!”[1]1530所以说,《白藤花》虽然用的是曲笔的表达方式,但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则是非常明确的,是一种民族大义下的反抗意识,是借给俄侨玛达姆夫妇唱了一曲悲凉忧悒的挽歌,而深刻揭露了伪满时期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抒发了不平则鸣、不争必亡的民族情感。
尽管作者采用了曲笔的艺术表现形式,但《白藤花》这篇看似不涉政治的小说还是被日本人窥破其反满抗日的潜在意蕴,被判定有“不良思想”,作者也因此被秘密逮捕。
二、语隐而喻显
与曲笔一样,隐喻也是一种常见的文学表现手法。在“为尊者讳”的中国古代社会,隐喻更是以俳谑谐的形式出现。《文心雕龙》“谐篇”有言:“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则比较了隐与秀这两种风格各异的表现手法。在充分肯定“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指出:“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煅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畜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尽管现当代文学中的隐喻与《文心雕龙》“谐篇”“隐秀篇”中所说的、隐并非完全等同,但《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譬喻、谐谑、含蓄等表现手法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现代文学中隐喻的色彩。应该说,隐喻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手法和表现形式,并为古今中外文学巨匠所巧妙使用。
在支援先生的《白藤花》中,作者也大量使用了“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藏颖词间”“露锋文外”等隐喻手法,来表现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爱国志士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反抗精神。讨论支援《白藤花》的隐喻特点,首先就要弄清文中反复出现的白藤花的隐喻意义到底是什么?
据百度百科介绍,白藤是棕榈科,省藤属攀援藤本植物,属攀援藤本,丛生,茎细长,雌雄花序异型。白藤生长需要具有一定郁闭度的森林环境,成藤后又能忍耐全光照条件。白藤喜温而不耐寒,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年均气温21—25℃,最冷月平均气温大于14℃,极端最低气温在0℃以上。从地域分布上看,白藤主要生长在福建、两广、海南岛、越南等地。因此,笔者颇疑支援先生笔下的白藤花并非植物学上的白藤花,而是一种生长在北方地区的植物。
为了弄清白藤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刘树声先生当年曾查遍手头几本专门研究花的书,但都没有找到白藤花。后来他亲自向支援先生本人求证。支援先生回忆说:“当年,我就租住在一家俄国女人的房子,现在就在马家沟哈工大院内的遗址。那个俄国人的房子的门口有几个楼梯凳,房子边上有木架,黑篱笆上横着并排开放着一串串小花。”刘树声问:“是不是像喇叭花似的?”支援说:“有点像。”刘树声先生回忆说:“他说得很浪漫。支援本来是挺古板、不太浪漫的人,说得很动感情。”刘树声先生不由得感叹道:“啊!我明白了,白藤花是美丽的,白藤花也是我喜欢的文学作品之花。”[3]35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读者不必再纠结具象的白藤花到底是什么花,而只要明白白藤花是一种象征寓意就行了。也就是说,白藤花在植物学上到底是什么科什么属并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是一种隐喻的表现手法。那么,白藤花究竟象征什么呢?对此,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读视角。
在刘树声先生看来,白藤花象征着美丽和浪漫,而且他这个结论是从作者那里直接得到证明的,可信度较高。杜玉娟则认为白藤花是被人格化了的,象征“身处逆境中的作家”[1]1530-1531。作者在《白藤花》①中曾写道:“许是因那黝黑的篱笆和凋落的白藤的形态,得以象征我衰弱的生命,或是因我病中的心情,适合于这凄淡的情景作表征,我开始竟感到它的可爱,以至对它的生存的珍惜。”然而,在笔者看来,白藤花的隐喻还远不止于此。
无论白藤花是指南方那种藤科的白藤,还是指北方的爬山虎、牵牛花(即喇叭花),小说中的“白藤花”无疑是具有缠绕、攀附的特点。这既可理解成在伪满洲国日伪统治下,压迫、贫穷、灾难、疾病、饥馑等苦难如影相随地缠绕住苦难的人民,正如“我”的房东玛达姆艰难维持着生计一样;也可理解为一些听天由命、放弃反抗的民众被牢牢地束缚在象征黑暗统治的“黑篱笆”上。苦难就如同一种看不见的藤蔓一样紧紧地缠绕、束缚着沦陷区的人民,“我”租住玛达姆房子的“八杂市”就是都市肮脏的一角,这里泥泞,街道狭窄,到处是尘土、垃圾和屎尿,充斥着私售白粉者、乞丐和贫民,还夹杂着裸露“银针客”尸骨的墓地。这些尽管与“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格格不入,与玛达姆昔日风光无限的贵族生活也判若霄壤,但这就是现实,是残酷的现实,是苦难的现实,一如那无法摆脱的、紧紧缠缚住苦难人民的白藤。而在藤条缠绕之下,初时,或许被缠绕和束缚的人们也曾想到过反抗,但由于缺乏强烈的抗争意识,慢慢地在心理上产生了对束缚自己的藤条及“黑篱笆”的依赖和顺从。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了“我在想,习惯成为自然,无论劳累、肮脏以及一切乖舛待遇,生命总会逐渐与之相契合的”。这些话以隐喻的形式道出了东北沦陷区的一些民众的奴顺和麻木。
但藤蔓上开放的白藤花则给这种隐喻赋予了新的、更深刻的、具有生命力的寓意。藤蔓虽缠绕、束缚着苦难的人民,但即便在这样的植物身上也一样是有希望的,那就是藤蔓上开出的白藤花。一方面,白藤花给被束缚的沦陷区“顺民”在苦难生活中投入了一丝希望之光。即便是那“对什么都没有决心,对什么都能忍受”、生活如死水一潭的玛达姆,白藤花也给了她一丝希望。她移栽白藤花固然是因为新房客的到来,但又何尝不是给自己生活点缀的一抹亮色,点亮的一盏心灯呢。当然,在日伪统治的铁幕之下,无边的黑暗和越来越凛冽的秋风和马上到来的寒冬(喻指日本对沦陷区不断强化残酷统治和高压政策),必然加速白藤花的凋谢。正因为“我”读懂了白藤花给玛达姆带来希望的这一花语,因此,“我总也没有告诉她,篱笆上的白藤枯萎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如要真实地对她说,那犹如揭穿一个大的恐怖和祸害一样,我的勇气,像一直被一种惊骇的预想压制着”。另一方面,白藤花也激起了“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抗意识的升腾。既然连被束缚在黑篱笆上的藤蔓都能开出绚烂美丽的花朵,为什么身处沦陷区的苦难人民就不能奋起反抗,摆脱苦难呢?白藤花反抗的先声就是在风中不停地哀叫和哭喊,就是把痛苦大声地表现出来,而不是像玛达姆那样麻木地适应痛苦,或者像她丈夫特莫利克夫那样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掩耳盗铃地使自己看不到眼前的痛苦和悲凉。
作者在小说中几次提到白藤花的哀叫、挣扎。比如,在病中的深夜,“我”不仅听到自己脉搏怦怦地跳动,也听到玛达姆的梦中叹息,更听到了窗外飒飒的西风吹着白藤的哀叫。在这段描写中,玛达姆是悲观的,只知道叹息,“我”则能感觉到自己不屈的生命即便是在病中仍勃勃跃动,而那白藤在西风中的哀叫,正寓意着苦难人民的痛苦。虽然在字里行间还看不出实质性的反抗,至少已经不再是麻木不仁的,至少还知道哀叫。进而,作者用“我”之口喊出了:“我讨厌到屋子里的黑暗和窒塞,我烦腻起窗外景色的忧悒和凄凉,我觉得宇宙一切,都悲伤地承受着一种灰色的重压,低低的,我隐约听到那篱笆上白藤的哭泣。”在小说中,哀叫也好,哭泣也罢,实际上都代表的是白藤渴望摆脱黑篱笆的束缚。在小说中,黑篱笆无疑指代的是日伪的黑暗统治,屋子里的黑暗和窒塞则指代东北沦陷区的凄惨和压抑。如果说白藤花给予玛达姆的是一种活下去的希望,那么,给予“我”的则是唤起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的呼号,这种呼号或以哀叫或以哭泣的形式出现在病中“我”的思想中,促使我一旦走出病魇就立刻要搬离“八杂市”玛达姆的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不被苦难的生活所麻痹,不被奴顺的思想所同化。
有研究者统计,小说中一共出现了十次白藤花,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九次。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和丰富的寓意,特别是按照出现的次第,白藤花渐次枯萎,直至彻底萎败。从第一次出现在作者病中的视线中,白藤花就注定要走向凋零萎落的命运。当然,白藤花也曾经有过欣欣向荣的时候,比如当“我”刚搬来时,房东玛达姆特意在黑篱笆那里为“我”的到来而种上了白藤花。这株特意为新房客而移栽的白藤花实际代表了玛达姆对生活的希冀。但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生活,对远在异乡的丈夫、儿子的无尽思念,以及丈夫归来竟然憔悴苦楚且为逃犯的残酷现实,一步步将玛达姆逼向绝望的境地。伴随着玛达姆和她的丈夫特莫利克夫的被捕,那白藤花也彻底凋谢了。
王滋源在评价《白藤花》这部作品时,曾用“阴柔之美”进行概括[1]1491,其主要是从这篇小说的总格调、文风和语言风格来说的,若从白藤花的隐喻角度看,也能得出阴柔之美的结论。说到“阴”,白藤是生长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的植物,在生长期中是畏光喜阴的,因此,白藤本身就象征着阴。从“柔”的角度看,藤科是柔软缠绕的,其本性就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攀援依附的。因此,用“阴柔之美”来概括《白藤花》的艺术美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但中国古代智慧讲求的是阴阳和谐,独阴或独阳都不可能成岁,必须阴阳和谐,而且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理,阴极则生阳。同样,阴柔之至的白藤花在其阴柔之下本身也孕育着不屈的生命力和勃勃的生机,体现了阴中有阳、外柔内刚的精神特质。这也是尽管小说一开始就是“我”在病中与窗外黑篱笆上的白藤花做着情感上的交流与互动,看似悲观而无奈,但最终“我”还是摆脱了黑暗的束缚和温水煮青蛙的困境,勇敢地走出了阴霾和病郁,走出了黑暗的病屋子,走到了阳光底下,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
白藤花的隐喻还表现在小说的深层立意上。很多评论者都喜欢拿《白藤花》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做对比,认为二者在风格上很相似。我认为从隐喻的角度讲,与其说支援先生的《白藤花》与契科夫短篇小说的风格接近,毋宁说《白藤花》与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白藤花》和《最后一片叶子》一个说的是花,一个说的是树叶,但二者都是植物器官,而植物又都代表着生机和活力。人在失望病苦的时候,常常把自然界的花开花落、四季更迭与个体的生老病死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有些罹患重病的宿命论者更是对植物的荣枯看得很重。在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若不是老画家将那叶子画在墙上,恐怕那受心理暗示影响的病人早就一命归西了。
在《白藤花》中,春天“我”去玛达姆家租房子时,玛达姆特意为我栽下白藤花,想必当初也曾生机勃勃。但小说的一开始就是“我”病恹恹地望着窗外有些枯萎的白藤花,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白藤花也越来越丧失生机,直至“我”准备搬离这里时,玛达姆说:“这花再经不起严霜了,明天拔去罢!”但对这代表希望的白藤花,玛达姆并没有真的舍得拔掉。最后,当“我”重访故园,得知老俄侨夫妇被抓走后,“待我再低头去看那篱笆上的白藤花,枯体依在,然而叶子已完全凋落了”。
尽管白藤花的日渐枯萎曾给予“我”灰颓压抑的心情以消极的心理暗示,但最终“我”走出了精神阴霾,决定要做点什么,而不能像白藤花那样任其萎落。相反,玛达姆和丈夫的精神则随着白藤花的衰败而消磨殆尽。本来,玛达姆作为一个曾经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跌落到与贫民杂处的窘迫生活,已经慢慢习惯了这一切。她随遇而安,对苦难悲惨的生活逆来顺受,麻木绝望。除了在回忆过去中能得到快乐外,丈夫特莫利克夫的即将归来曾一度让她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但备受折磨、偷着逃回来的丈夫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快乐和希望。当“我”问她:“你丈夫的归来不像你所期待那样吗?”玛达姆点点头,眼里含泪说出她的丈夫为了爱她而坚忍地在苦役中艰难地活了下来,现在又以一个逃犯的身份逃回了家里。在作者的笔下,玛达姆的丈夫——特莫利克夫——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担任北铁督办时的无限风光和贵族绅士气质,他已经被生活和苦役折磨得成为一个颓废消沉、彻头彻尾的酒鬼。“一个枯瘦贫血的老人,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旧西服,疲倦的,侧卧在玛达姆的床上。”“消瘦的,肌肤灰黑,左须有一块伤疤,样子像有五十岁,举止颇似吃力,一团蓬乱的黄发,像一个久病的囚徒。”即便是回家将养多日,他的脸色仍然“像坚持寒霜的一个灰白的菜叶”。应该说,作为没落贵族的玛达姆夫妇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和反抗意识,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和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尽管他们希望就这么混下去,但最终还是被抓走了。
说到隐喻,除了白藤花本身的寓意外,描写主人公情绪的一些词汇也体现了隐喻的功用,比如,“悒闷”“忧悒”就带有这样的隐喻意蕴。就像白藤花出现了九次、十次一样,“悒闷”“忧悒”在作品也出现了很多次。“悒闷”“忧悒”等词汇构成了《白藤花》小说的基本色调。这色调是阴郁的,给人一种烦闷和迷惘,一种挣扎的无力和痛苦的绝望。
从字面上看,无论是“悒闷”还是“忧悒”,都有个“悒”字。作者这个“悒”字用得绝佳。“悒”的本义是忧愁不安。《说文解字》解释“悒”为“不安也”。《苍颉篇》亦言:“悒悒,不舒之貌也。”也就是说,“悒”表现的是人因心里忧惧而不安,是压抑而烦闷的。在《白藤花》中,作者用“忧悒”“悒闷”表达了沦陷区人民苦难不安的生活和压抑烦闷的心境。因此,在《白藤花》中,隐喻无处不在,不仅隐藏在频繁出现的白藤和白藤花上,而且弥漫在“悒闷”“忧悒”的气氛中。
为了营造压抑悒闷的基调,作者甚至不惜将绝美的秋日景致也极力笼罩上浓重的郁气。比如,在即将搬离“八杂市”玛达姆家的前一天,“我”与房东夫妇曾一起到大自然中去散步,但这没有带来一丝一毫的快乐。本来那是一个万里无云、艳阳高照、气爽神清的秋日,偏偏作者把那色调调成了极度的抑郁。常规而言,如此美艳的秋日,不是赏五花山,就是看红叶,可作者却写道:“秋阳无力地吻着枯草,……风低低地在我们脚下唏嘘,时而,我们之中,会有一声寂寞的叹息。每个人,都怀一缕不同的思绪,每人都为自己的思绪缠绕,默然地,慵倦地拖着荒径上的步伐。……有一行大雁,远远地啼叫着,飞在高空。……日暮后,寒气立刻使人痉挛。我们回到家门篱笆旁,看见白藤的叶子已凋落不少了。”从上面这段秋日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中不难看出,本来是秋高气爽、万木霜天竞自由的好天气,却因为日伪的铁幕统治而毫无自由可言,自然人们也就没有了秋游的好心情,即便是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心情也仍不免是压抑而悒闷的。
隐喻的作用不在于隐,而在于喻。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说的,“隐喻重要的是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要让读者或是听众把隐喻当隐喻看的效果”[4]。《白藤花》的隐喻技巧就达到了博尔赫斯所说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支援先生的《白藤花》发表在日本大阪的《华文每日》后,就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其中暗含的进步思想,认定作者“对社会表现极度不满,诅咒现实,叙述民族颠沛流离,生活充满凄凉恐怖,刻意描绘了民族没落的悲哀,思想不良,意在推翻满洲帝国”[1]1369-1370。这也是作者在1945 年春天被日本人密捕的原因所在。
其实,早在作者创作《白藤花》时,就想到“为了避免触犯当时所严禁的揭露,全篇都不曾对日本的淫威作任何正面描写,企图暗示时代所给予各个被压迫民族的灾难”,但作者也清楚,尽管自己做了诸多曲笔和隐晦的处理,但隐喻的意象始终非常明确,指向也非常明晰。“明眼人一看便知,尤其在当时,日本人也很敏感。”[1]1097应该说,从日本宪兵密捕作者又释放这件事来看,《白藤花》的隐喻手法是非常成功的。通篇看起来没有一句反满抗日的言论,日本人虽然从中嗅到了反满抗日气息,但最后还是查无实据而释放了作者。有研究者指出,《白藤花》“采取隐晦、含蓄、曲折、迂回、影射、借古讽今等表现手法揭露敌人,唤醒民众”[3]75。不能不说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隐喻性的小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左翼文学的代表作,是哈尔滨沦陷时期文学的抗日精品力作。刘树声评价其为“经典之作”“精品”“珍品”是完全名副其实的,而毫无溢美和夸大之词。
三、压抑而抗争
关于《白藤花》这部小说的总体色调,很多评论者都有所提及。如李汉平认为《白藤花》的基调是“带着淡淡的感伤,淡淡的忧郁”[1]1540,同时也让人“感到一种清新、淡雅的美,感到那种淡淡的忧郁”[1]1469。王滋源认为《白藤花》的基调是缠绵忧郁的,“那种缠绵、忧郁的感情很生动,很感人”[1]1491。杜玉娟则指出:“《白藤花》全篇是以灰蒙蒙的凄楚、哀伤作为基调,读后令人感到压抑。”[1]1532王丽华对评论家以“忧伤”来界定《白藤花》的基调是持不同意见的,她从忧患意识的角度指出:“那淡淡的忧伤情调,衬托着感人的悲剧美,折射出的更是作家的愤怒与无奈。窃以为,与其说《白藤花》的情调有淡淡的忧伤,不如肯定地说,那是作家忧国忧民的意识,是作家仇恨日军的入侵,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散发出的民族忧患意识。”[3]143陈昊虽然也认为《白藤花》基调是忧郁的,但他在忧郁中看到了希望。他盛赞《白藤花》是“现实主义渗透着浪漫主义”,而且“那种忧郁的调子,也可以说是乐观的对生活的追求的另一种反映”[1]1492。杜玉娟在指出《白藤花》那凄楚、哀伤基调所带来的压抑感后,笔锋一转,也指出:“(‘我’)如果不尽快地摆脱这种处境,就会窒息而亡。”[1]1532
笔者赞同陈昊和杜玉娟的观点,陈昊所谓忧郁的调子中的乐观追求,正是笔者对《白藤花》主题的解读,即压抑而抗争,这也是杜玉娟所说的要摆脱的压抑处境和李汉平所谓“那种清丽的笔调,那种淡淡的忧伤,那种被压抑的愤怒如地下的暗火,寻找这可以夯实的隅口”[3]67。从白藤花的象征意蕴和俄侨房东一家的遭遇来看,《白藤花》这篇小说总基调无疑是悲凉而压抑的,抑或说是阴郁而悒闷的。
支援先生在《白藤花》中表现出的基调看似是无尽的悲苦、无边的苦难、无力的哭泣,然而,面对白藤花的凋谢,“我”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惋惜和悲戚,尽管病中的“我”曾一度“爱念起篱笆上的白藤”,但当“我”看到甘受命运摆布的玛达姆沉溺于悲观认命情绪时,“我”反而在病中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讨厌起屋子里的黑暗和窒塞,烦腻起窗外景色的忧悒和凄凉。“我”又想到乡老的衰迈、田园的荒瘠、颓坍破陋的家门与腐朽沉寂的气态,想到几年来的流浪生活中的追求、幻灭和一身的疲弱与疾病,以及一无所得的悲惨境遇。在病中,“我”想到自己如何在污泥中辗转,在深渊里号泣,……在经过一夜的胡思乱想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屋里已淡淡地撒满了阳光”。不仅如此,“我”觉得病体也有些减轻了。
在这里,“我”通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走出了“篱笆上白藤的哭泣”的阴影和消极的心理暗示,身体也逐渐康复,代表着“我”要迎来新生了。促使“我”最终走出白藤花哭泣、凋零阴影的,除了“我”观照白藤花凋谢而实现了自我觉醒外,玛达姆和她丈夫特莫利克夫的颓废也反过来激起了“我”的斗志。
应该说,某种程度上讲,颓废的特莫利克夫和玛达姆夫妇那听天由命、放任自流的堕落和颓唐,反而激起了“我”想要“搬开这沉郁的环境,或者再到远点地方去,另找一个新的生活”的强烈愿望。那么,特莫利克夫夫妇是怎样反作用地激发起“我”的斗志和新生的呢?
首先,是他们的悲观。玛达姆的悲观不消说了,此前她就满足于每天领一斤面包的勉强维持。为了每日一斤面包的基本生存,她自称丢弃了耻辱,葬送掉祖先的光荣,“我觉得人类之中再没有像我这样龌龊的存在,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痛苦的灵魂”。这里的龌龊和耻辱或许暗示玛达姆为了维持艰难的生活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作者几次委婉地提到“一向我不曾问过她自身是否有着职业,有时看她早出晚归,甚或有整夜不归的时候,我不好过问”。当玛达姆在一次酒后自怨自艾地哭泣忏悔时,“我想,不用推测,也不用猜疑,她自然别有衷曲。而且许多人,都有生活的一部内心的秘密”。毋庸置疑,玛达姆的生活是悲观绝望的,也是自甘堕落的,但这一切都是为生活所迫。在悲观绝望方面,特莫利克夫比起玛达姆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归来更加剧了玛达姆的悲观失望,本来他已经穷愁潦倒,而且恶疾缠身,但没想到他还是一个从苦役场里跑出来的逃犯。如果说玛达姆的悲观绝望是表象化的,那么,特莫利克夫的悲观绝望则上升到理论层面。特莫利克夫认为:“许多人反对这向往颓废的生活理论,可是,如把他们的话,仔细地推敲一番,考虑一番,思想却穷得很……”在他看来,“从另一方面观察,尽是黑暗的苦恼生活,费尽劳力,得不着一顿快乐的面包”。且不说特莫利克夫的思想认识是否正确,但他却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个现实世界是悲苦无望的。
其次,是他们的逃避。面对悲苦无望的凄惨生活,特莫利克夫夫妇不去改变现实,而是选择了逃避。玛达姆先是通过追忆往昔贵族生活来寻求逃避,靠回忆过去奢靡惬意的生活来麻痹自己现实中痛苦的神经。继而,她靠着宗教信仰的力量勉强支撑自己活下去。她为了每天那少得可怜的面包而“感谢仁慈的上帝”。即便是生活再困苦,玛达姆仍每晚到教堂祈祷。最后,玛达姆又把希望寄托在丈夫的归来上,但当看到意志消沉、一身伤病的丈夫时,玛达姆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她选择了继续逃避,“现实告诉她:无拘你怎样痛苦地生活下来,如今,还要你再怎样痛苦地生活下去”,因为,“希冀和祈祷,上帝不能在你如何耻辱的生活上,施点怜悯”。同样,特莫利克夫再次将他的逃避上升到理论高度。当“我”表示自己很“忧悒”时,特莫利克夫表现出了共情。他说:“忧悒什么呢?为生活吗?唔!一个人,和我一样。”继而,他以饱经沧桑的过来人口吻,阐释了他的逃避理论。“在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想生活,因为你愈想生活,它愈使你不高兴生活。”简而言之,特莫利克夫用酒来麻痹自己,面对生活的艰辛和莫名的恐惧,他让自己逃避在酒里。用他的话说,“酒可以使你没有生活的痛苦,酒也可以使你没有生活的耻辱”。他承认他是依靠酒来生存的,“没有酒,就没有我的生命”。
最后,是他们的懦弱。作为漂泊异乡的俄侨,原本在中东铁路还掌握在俄国人手里时,他们曾经过着人上人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洋房、别墅和游艇,是典型的“皤耶尔”(指上层社会人士)。但到了日伪统治时期,中东铁路被日本人接管,变成了满洲铁路,特莫利克夫夫妇自然跌落神坛,乃至于从高档奢华住宅中搬到肮脏、龌龊的“八杂市”艰难过活。“我”曾经想激起玛达姆的斗志,但玛达姆恐惧反抗会失败,而宁愿过那种“露宿枵腹”的生活。特莫利克夫的懦弱要比玛达姆更甚,他已经被苦役折磨得彻底丧失了斗志,懦弱得像寒冬风霜里的一片灰白的菜叶,即将彻底枯槁。当“我”打算搬出去,寻找新生活时,特莫利克夫又讲出一大套颓废懦弱的理论来。他对“我”“像背书一样地”说道:“到哪去呢?无论到哪里,都有不幸在,无论到哪里,都有疾病在,无论到哪里去看,都有死亡在。”此处作者形容特莫利克夫说这番话时用了“像背书一样”,这说明他已经彻底麻木,放弃了一切的努力和斗志。在特莫利克夫看来,这个悲惨的世界是“没有法子想”的,唯一能做的是“抱着悲苦的心,无声地活下去”。末了,他照例以过来人的口吻,从理论的层面循循善诱道:“近几年,我觉醒了生活的原则,上帝需要世界有各种人的点缀,你要认识生的宿命,你当顺从着上帝的命令。好一点,你稳健地去悟实际的生活,再乖巧一点,尝一点酒,得一点快乐”。无疑,在懦弱心理的左右下,特莫利克夫和玛达姆夫妇已经成为毫无斗志的行尸走肉,只是在这悲惨世界里苟延残喘。
面对房东夫妇的悲观绝望和懦弱逃避,“我”愈发开始警醒,并从那死水一潭的暗夜中奋力挣扎和努力挣脱出来。与“我”的警醒、挣脱相对的是玛达姆和特莫利克夫的更加懦弱、奴顺、麻木、迷惘和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的温水里青蛙心态。
尽管白藤和白藤花是依附的,纠缠的,它缺乏松树般挺拔、顶风冒雪战严寒的斗争精神,在日渐凛冽的寒风中,白藤花必然枯萎凋落,但白藤毕竟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植物,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根在,来年春天就又会复生。虽然《白藤花》的总基调是压抑而忧悒的,但其主题是压抑而抗争的。那么,《白藤花》的抗争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从小说的字面乍一看是看不到抗争意思的,但仔细品读《白藤花》则不难发现,其抗争主要在于“我”病后搬离玛达姆的房子,下定了开始新生活的决心。正如前面所说,白藤花毕竟是一种植物,虽然随着秋冬的到来,它会渐渐地枯萎凋落,但只要熬过寒冬,春风普度,白藤花就会再度绽放。白藤花的萎落虽然让人失望,但它的生命力却给人以希望。
玛达姆和她丈夫的悲剧就在于看不到白藤花生生不息的精神,而只是感到秋冬到来白藤花的日渐凋零,他们对自己是否能熬过寒冬没有把握,只想随遇而安地活一天算一天。在日本统治者面前,昔日的白俄已经彻底丧失了斗志。作者以这对白俄夫妇来影射沦陷区的国人,揭露他们对残暴侵略者的逆来顺受、奴顺卑屈、唾面自干的劣根性。作家通过描写白俄夫妇放弃反抗却仍被抓走,表达了对沦陷区中那些甘做顺民、良民的亡国奴的鄙视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我”对玛达姆夫妇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这种情感得益于白藤花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的反抗精神。比如,在“我”患病期间,玛达姆为了给“我”解闷,为“我”读《安娜小史》,其中有一段代表她的思想和生活写照,即:“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迄今,四十来年的生活,生活,使我看到生活原是空幻,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我觉得生活。但是,醉意一经消灭,我看见生活是如何欺诈,如何虚妄。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之外,一无所有……”面对玛达姆思想的灰颓,身处病中的“我”保持着清醒和警觉,而没有被玛达姆带节奏。听完玛达姆的诵读和剖析,“我的听觉已被我另种思想掠夺,无故的,我又爱念起篱笆上的白藤了”。在这里,作者为什么说“我又爱念起篱笆上的白藤了”,这与玛达姆在《安娜小史》中所表达的基调有何不同?为什么是“另种思想”?我想这里就有着深深的隐喻在其中。这段话暗示着白藤花骨子里具有一种不自甘堕落、不受命运摆布的反抗精神。“我”正是爱念白藤花的这种精神,才没有像玛达姆那样悲观绝望,而是极力跳出“骸骨”“虫蛆”“一无所有”的命运怪圈,努力寻找“另种思想”,寻觅新生活的路径。
总而言之,《白藤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曲笔和隐喻等表现手法,含蓄地揭露了日伪统治下沦陷时期哈尔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苦难境遇,种下了反满抗日的种子。今年正值《白藤花》发表80 周年,谨以此文重温红色经典,致敬抗战作家支援。
注 释:
①支援著《白藤花》,原载《华文大阪每日》第10 卷101 号,1943年第1 期第29—38 页,收在《白藤花——支援文集》第3—1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本文以下引用《白藤花》的文字皆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