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治理视角的纽约时代广场城市更新研究
2024-01-05周鸣浩卢叶炅许月丽伍江
周鸣浩 卢叶炅 许月丽 伍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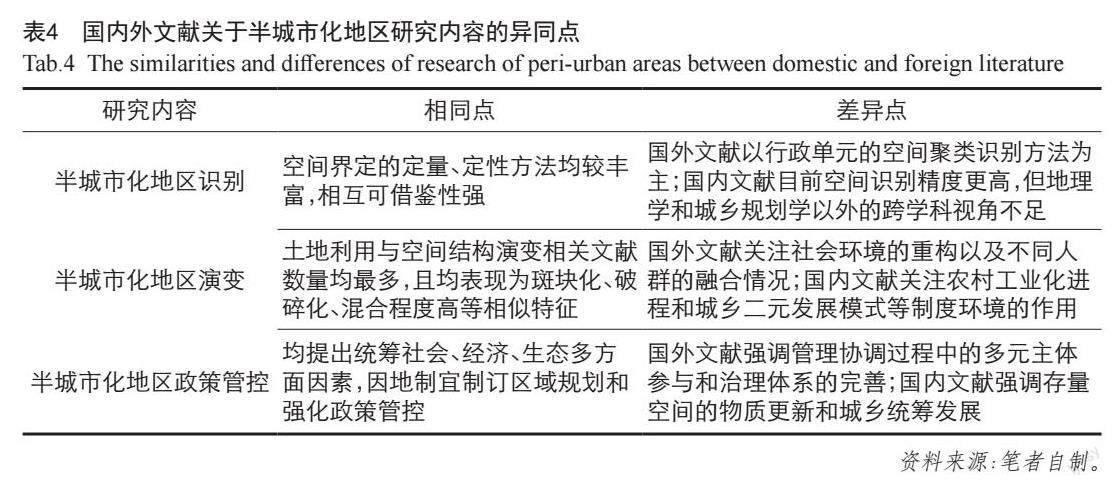


摘 要从1980年代至今,纽约市在时代广场区域先后推动并完成了两次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不仅重塑其产业结构,全面激发区域活力,也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以两次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差异为研究对象,重点聚焦更新过程中的治理问题,剖析与厘清城市更新目标与方向的转变如何影响治理的参与主体、权力关系、合作方式和治理工具的相关变化,旨在为我国当下处于经济转型和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商业街区的城市更新及其治理逻辑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关 键 词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城市商业街区复兴;纽约时代广场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3)03-0128-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30318
0 引言
举世闻名的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are NYC)享有“世界十字路口”(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的美誉,不仅因其优越的城市区位——汇聚了世界上最好的娱乐设施、美食酒店和令人眼花缭乱的LED广告牌的曼哈顿中城百老汇大道中心,也因其在纽约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迎接新年和欢度庆典的重要场所。但40年前这一城市核心商业街区曾一度陷入低谷。剖析时代广场的两轮更新,不仅能探视美国城市更新模式的发展,还能解读西方城市更新发展脉络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合作的机制内核[1]45。
城市治理强调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通过采取持续的、合作的行动来协商管理共同事务的方式总和(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方式) [2],为探讨如何构建城市存量更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这一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转型推动政府在不同空间与尺度上重塑与社会和市场的基本关系[3]。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中国的城市更新正面临市场化与私有化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变迁,推动社会空间涌现出基于特殊利益联结形成的社区力量和非政府组织[4]。由此,运用治理理论解释与指导当下中国城市更新行动就有更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对治理視角下的国际城市更新案例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更新理论和政策演变[1]44-45,[5]、协同治理的条件与过程[6]、城市空间治理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的转型[7]、绅士化及相关的增长机器和城市政体理论[8]、公众参与制度和参与方式[9]等。虽然有研究涉及中心城区更新的动力机制[10],但是,借助治理理论解读城市商业街区在不同更新模式下的机制研究依然不足。因此,本文借助治理视角对纽约时代广场两个阶段的更新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深入剖析影响更新模式的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结构等具体维度,为我国都市核心区的城市更新所面临的多元治理问题提供借鉴。
1 “魔鬼的乐园”——时代广场的更新背景
1.1 纽约市城市更新的政策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城市贫民窟清理计划。1949年联邦政府新修的《住房法》(Housing Act)赋予了各城市将联邦资金用于荒废区域的拆除和重建的权力;1966年国会颁布的《模范城市与大都市发展法》(Demonstration Cities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Act)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将贫民窟认定为阻碍城市生活质量提升的根源[11]。时任纽约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员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坚信:“当街区破败到一定程度时,推翻重建是唯一选择[12]。”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以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为主要特征,由政府负责统筹规划、征收土地,开发商负责承建,以暴力手段驱离城市的底层住民,加上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运动,导致纽约中心城区居住人口下降。
粗暴的开发模式虽然为纽约市贡献了史无前例的建设量,但并未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1974年国会通过的《住房和住区发展法》(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是纽约城市更新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转折点,政府开始重视与开发商的合作,通过行使公权力保障项目实施,以优惠政策引导私人投资,在谋取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倡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复。
1990年代末,因经济复苏与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导致的纽约城市人口回流引发新一轮房地产投资热潮,联邦政府也注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振兴老旧街区,重建中央商务区。这次浪潮看似重返了1950年代的地产开发盛况,但城市更新的模式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经过长期发展已不局限于单纯的政商合作,利益主体更加多样;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开始呈现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势态。从整体上看,纽约的城市更新呈现出从大拆大建的重建更新到渐进式的保护更新、从单一的政商合作到多主体协同、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到重视社会评价的转变。
1.2 时代广场的历史困境
1811年的曼哈顿规划(Commissioners' Plan of 1811)不仅建立了曼哈顿岛的方格网系统,同时也在42街至47街之间的第七大道与百老汇大街相交处形成了不规则的“领结”状区域(见图1)。最早的欧洲移民将此地命名为朗埃克广场(Longacre Square),20世纪初已是纽约市著名的马匹交易与马车行业的中心[13]。1904年,两条新规划的地铁线交汇于广场南侧,时任《纽约时报》CEO的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S. Ochs)买下位于42街与43街之间的三角地块,用于建造新的总部大楼。1904年4月8日,这块领结状的区域正式改名为“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到1929年,时代广场已成为纽约最重要的商业街区,也是城市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和新闻播报的窗口。1930年的大萧条是时代广场发展的历史拐点。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商店关闭,剧院为了生存不得不提供色情表演,性产业开始迅速在时代广场南侧的西42街蔓延。先是成人书店、窥视秀与风俗店取代了传统酒吧,随后出现了站街女郎、非法卖淫与毒品交易(见图2)。非法产业的蔓延增加了街区的犯罪率;合法产业被排挤减少了街区的公共服务和税收,进而陷入恶性循环。1960年一篇题为《42街的糜烂生活》的报道将时代广场评为“纽约市最肮脏的地方[14]”。当地学者詹姆斯·特拉布(James Traub)也在其著作《魔鬼的乐园:时代广场追名逐利的一百年》中感叹:“时代广场的自由、活力和娱乐曾被几代纽约人所追捧,如今这些特征反倒沦为滋生混乱和犯罪的温床[15]。”
面对不断恶化的街区环境,城市更新迫在眉睫。时代广场的问题可以归纳为:(1)既有形象与发展定位不符。曾作为城市核心娱乐与庆典场所的时代广场却沦为臭名昭著的红灯区。(2)非法产业盘根错节,整治难度大。毒贩、妓女、黑帮势力隐藏在影剧院、酒吧和旅馆的内部且均有各自的地盘。(3)业主和商户对城市更新的意愿低下。时代广场的业主和商户作为色情产业的既得利益者,与政府的改造意愿背道而驰。(4)基础设施破旧,历史建筑年久失修。非法产业滋生了大量逃税人群,税收低下使得街区无力支撑公共服务的开支与历史建筑的修缮。
2 第一次更新:从政商联盟到社会介入(1980—2001年)
2.1 政商联盟: 42街开发计划
1980年,时代广场拉开了重建的序幕,改造重点是性产业最集中的西42街。纽约市政府与纽约州城市发展公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UDC”)共同制定了“42街开发计划”(42nd Street Development Project),试图建立政府—大开发商的合作联盟,通过税收减免与容积率转移的政策吸引私人开发商投资。更新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要将时代广场打造成类似洛克菲勒中心的高端商务区,1984年出台的具体方案包括修缮42街内的9栋历史剧院和地铁站,建造4栋规模庞大的办公楼、1个百货商场和1个高档酒店(见图3)[16]。
此次更新计划的参与主体是由纽约市政府、UDC、大型私人开发商公园大厦地产(Park Tower Realty)与保诚保险(Prudential Insurance)组成的政商联盟(见图4)。纽约市政府通过制定开发计划及相关规范文件,统筹把控整个更新计划。市规划局于1981年6月出版的《中城发展规划》(Midtown Development)将中城西侧第六大道至第八大道间的区域列为下一阶段的开发重点,同时规定了42街的开发须以保护历史剧院为前提(见图5)[17]。同年,纽约市政府还委托库博-艾克图特(Cooper-Ecktut)建筑事务所编制《42街设计导则》(42nd Street Development Project Design Guidelines)对街景、建筑风格、天际线等要素做了进一步控制,并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分期减免开发商共计2.4亿美元的税收。
UDC的介入反映出纽约州政府对重建时代广场的重視。UDC是一家半独立性质的国有企业,具有“强制征收权”,可以不受城市管理部门的约束征收私人土地。UDC负责对34栋建筑进行强制征收,涉及236家商铺和企业,并将地块清理整合后转交给私人开发商[18]。
通过招投标,公园大厦地产与保诚保险被市长爱德华·科赫(Ed Koch)选中进入开发计划。在政商联盟框架下,这两家开发商并不参与开发计划的制定,而是承担具体的办公楼开发以及后续的招商使用。他们通过购买历史剧院出让的额外“空间权”(air right)①,换取新建办公楼更高的容积率;通过承担翻修老剧院和地铁站的资金以及为政府垫付部分土地征收费用以换取长期税收减免[19]129。知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及其合伙人约翰·伯吉(John Burgee)被委托负责4栋办公楼的设计。两大开发商也分工明确:公园大厦地产是地产开发公司,负责具体的开发事项和后续招商;保诚保险则负责融资和提供资金。
1984年开发计划的实施并不顺畅。一方面,UDC在征地过程中遭到所涉区域内的业主和商户的强烈抵抗,产生了大量的法律诉讼案件,土地征收沦为一场拉锯战。另一方面,由于二元合作模式一开始就缺少社会力量的制衡,最终导致治理目标的偏离。更新开发的重心倒向总面积高达38万m?的办公楼宇,整个开发计划都过于追求经济效应而忽视社会效益,对历史剧院的保护也沦为支持办公楼建设的一种噱头。一些控制手段相继失灵,如约翰逊的办公楼设计方案就完全忽视了事先制定的设计导则,4栋写字楼体量巨大、形式笨重、色调单一,无论从体量还是风格上都与时代广场的基调格格不入(见图6)[20]。受制于对开发商资金的依赖,市规划局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饱受争议的设计方案。然而,当UDC直到1992年艰难完成征收工作时,纽约市的办公楼市场却已接近饱和,此时动工将面临巨额亏损,政商联盟在艰难协商后不得不暂时将开发计划搁置。
2.2 社会力量介入: “今天的第42街!”临时计划
1992年,市政府与UDC发布临时计划“今天的第42街!”(42nd Street Now!),试图取代原先搁置的开发计划。该计划更强调“复兴”(renaissance)而非“重建”(renewal),不再热衷于写字楼等商业设施的开发建设,而是基于时代广场的历史背景、在地文化和社区需求,意图将42街打造为以休闲娱乐为主体功能的街区[21]。
作为计划的统筹者和主要推手,纽约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并由行政执法配合推动更新计划实施。新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上任后,联合警察局对时代广场性产业残余势力施行大规模整治,有效降低了时代广场的犯罪率[19]336。1992年,时任开发计划负责人的丽贝卡·罗伯逊(Rebecca Robertson)委托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和设计师波蒂·卡尔曼(Tibor Kalman)编制了新的设计导则,强调新时代广场的设计基调应突显活力、惊喜与视觉冲击力。斯特恩在导则中绘制了带有迪士尼风格的想象图,呈现了一个充斥着波普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广场(见图7)。政府也继续给予开发商减税政策来撬动投资,但不再过多干涉具体的开发和运营。
临时计划在组织和实施机制上最大的变革是打破了政府和开发商的二元关系,将创新时间(Creative Time)、新42街(The New 42nd Street)等社会非营利组织纳入开发计划(见图8)。“新42街”是市政府与州政府共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不仅接手了42街内所有历史剧院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协助老剧院实现转型,例如创造性地提出将修缮后的剧院改造成儿童剧院或新式影院。另一个非营利设计机构“创新时间”则负责在街道和空置店铺内策划和举办意图激发街道活力的公共艺术展览[22]。临时计划发布的同年,时代广场的业主和租户成立了“商业促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简称“BID”)②,自发组织清理街区卫生并协助当地警方维护街道治安。社会组织的介入不仅有效促进了历史剧院的活化转型,也推动了对社区在地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注。在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下,规划与导则得以有效落实,建筑设计也受到合理的引导、控制和规范。此外,政府不再依赖指定的开发商来完成城市更新的所有事项,而是基于每个地块的具体需求针对性地招商引资,开发商也不再被要求承担诸如翻修剧院或地铁站等额外项目。1993年,迪士尼公司入驻新阿姆斯特丹剧院,成功将其改造成动画电影舞台剧的表演场所。迪士尼的成功促使更多投资者重新审视时代广场区域潜在的商业价值,有效带动了诸如杜莎夫人蜡像馆、美国连锁影院(AMC)等知名企业的入驻[23]。1995年以后,随着纽约办公楼市场的回暖和时代广场整体环境的改善,经历长期亏损的原开发商保诚保险将原先用于建设写字楼的4个地块的开发权分别转让给3家企业:道格拉斯德斯特、鲁丁集团和波士顿地产。最终被开发建设成为今天的康泰纳仕大厦、路透社大厦、时代大厦和安永大厦。
到21世纪初,西42街内的7家历史剧院已经完成修复和转型,以儿童剧院、歌剧院或电影院的形式重新向社会开放;新媒体公司、律师事务所和金融企业入驻新的写字楼;迪士尼商店、酒吧、高档餐厅等文化娱乐产业置换了原来的性产业;游客和白领取代了毒贩、妓女和皮条客重新成为城市空间的使用者[24-25]。2001年5月,纽约州长帕塔基(George Pataki)参观新的西42街,将时代广场的“重生”描述为纽约城市更新的典范(见图9)[26]。
3 第二次更新:从多方协同到公众参与(1998—2016年)
3.1 社会实验: 多方协同下的联合探索
20世纪末,随着游客人数的激增,时代广场开始面临新的空间治理问题,如街道基础设施破旧、步行空间狭窄、人流交通混杂等。尽管第一次更新成功重塑了时代广场的主体功能和产业结构,但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依然与时代广场的品牌和地位并不相称。“时代广场已经被重新激活,但如何使它更好”成为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更新对象从建筑物构成的实体空间转变为由街道和广场构成的虚体空间,更新目标也从地块内的重建和容积率的提高转变为城市空间综合环境品质的提升。
新一轮城市更新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包括由纽约市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以BID和百老汇剧院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专业力量(见图10)。2000年,市交通局与市规划局联合编制的《曼哈顿中城步行网络发展计划》意图通过拓宽步行道、翻修街道设施以及规范摊贩和车辆对街道空间的占用等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城市步行环境,并将时代广场划入步行化改造的实验区[27]。2001年,在该计划的指导下,市交通局与BID合作完成第一轮时代广场步行空间的扩建,通过替换老旧基础设施、修整路面、拆除或置换老旧的城市家具,使领结状交叉口两侧的步行空间扩大15%。
以BID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则早在1998年就开始探索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的可能性。先是委托菲利普—哈比卜事务所(Philip Habib & Associates)对步行环境和车流量进行预研究,又在2003年与公共空间设计基金会(Design Trust for Public Space)合作举办两次研讨会,邀请来自社会各界不同领域的25名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重建中央交通岛、增加53%步行面积的新方案以及对交叉口处交通组织的新设想(见图11-图12)[28]。2006年的研讨会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街道应根据不同时段的使用需求灵活调整车行道与人行道边界,提升街道功能多样性的新设想[29]。此外,BID还与剧院发展基金会(Theater Development Fund)合作发起了对广场北侧交通岛及中央TKTS售票厅的改造计划。经由国际竞赛,最终选择了澳大利亚建筑师约翰·崔(John Choi)和戴·罗皮哈(Tai Ropiha)的设计方案,新售票厅被设计成红色的梯形看台,在满足售票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了500座看台空间[30]。
在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探索与实践中,街区的业主、企业与居民取代地产开发商,成为新一轮更新的市场需求者和资金提供者,并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更新过程。政府与社会组织缔结成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政府依然是计划的统筹者,而以BID为首的社会组织则成为城市更新的探索者与先行者。需强调的是,由社会力量推动的前期研究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对后续的更新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例如2006年10月,由市交通局策划的“时代广场交通整治”(Times Square Shuffle)③基本上借鉴了2004年BID年度报告中的研究成果,而在研讨会上对于将车行空间转换为步行空间的研究更是为下一阶段的步行化实验奠定了基础。
3.2 公众参与: 从“绿灯计划”到永久“步行化”
2007年,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发布了雄心勃勃的《纽约城市规划:更绿色更美好的纽约》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简称“PlaNYC”),为时代广场的新一轮步行化改造创造了可能。规划在开放空间(open space)的部分提出“确保每一个纽约人步行至身边的公共空间的时长不超过10分钟”的核心目标,计划将现存的一些使用不合理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街道转化为公共活动空间[31]。
这一阶段的治理主体包括市政府及下属部门、以BID为首的社会组织和纽约市民(見图13)。作为PlaNYC战略框架下的进一步行动,2008年市交通局颁布的“纽约市可持续街道战略计划”不仅提出建设更安全、更清洁、更便于生活的城市街道的总目标,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纽约市街道设计导则》加强了对后续街道空间设计的管控和引导,并委托杨·盖尔(Jan Gehl)负责与之相配套的研究课题《世界级的街道:重塑纽约的公共场所》[32]。在对百老汇大街、布鲁克林大街等主要街道的空间使用状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后,这位著名的丹麦建筑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街道的首要任务应是为行人服务,然而当前的时代广场区域却找不到一个可用于举办公共活动的空间,步行道仅占街道总面积的11%,很多行人因步行道过度拥挤不得不在车行道上行走。[33]”他提议政府应借鉴世界著名街道的发展成果,重新评估将百老汇大街车行道“步行化”(pedestrianization)④的可能性。
通过社会实验的方式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是此轮更新的创新之处。2009年,市交通局和BID共同策划“中城绿灯计划”(Green Light in Midtown Project)。这项全新的社会实验于2月27日正式宣布,5月24日实施,8月底结束,实验期间只保留第七大道的车行道,将百老汇大街的车行道改为步行广场,用于店铺外摆或公共活动(见图14)[34-35]。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者将对实验区内新步行空间体验的满意度作为下一步是否永久步行化的关键评判标准。实验吸引了大量纽约市民参与到此次街道空间更新的实践中,也从侧面反映出纽约城市更新价值取向从偏重经济效益到偏重社会效益的转变。2010年1月,由市交通局发布的评价报告显示:在为期3个月的实验中时代广场的交通事故减少了63%,因步行道拥挤而被迫在车行道上行走的行人数量下降了80%,在广场上停留活动的人数增加了84%,超过74%的受访者认为时代广场的步行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36]。基于社会层面的大量正面评价,市长布隆伯格于同年宣布将绿灯计划永久化,这意味着西42街至47街之间的百老汇大街将正式转变成步行广场。
在后续的街道设计、建设和运维阶段,政府与BID等社会组织也一直保持合作,通过招投标选择了挪威斯诺赫塔(Sn?hetta)建筑事务所的设计方案。新方案不仅创造了统一协调的地面层,同时对路面上原本杂乱无章的城市家具做了整合与再设计(见图15)。在BID与市交通局的统筹下,斯诺赫塔于2012年递交了最终方案,2013年12月起分3期施工,最终于2016年12月完成改造并重新开放[37]。至此,时代广场才实现了由愿景到细部、由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重生”。
4 时代广场城市更新的治理模式演进及其启示
我国的城市更新浪潮方兴未艾。尽管与西方相比,这一过程所面对的社会—历史语境、挑战和问题并不完全相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溯时代广场总共两轮、四阶段的改造更新发展历程,尽管也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但总体上是渐进连续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可以说,今天这个高度繁华的“世界的十字路口”是纽约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政策背景与治理目标,不断创新城市治理机制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结果(见表1)。如果说,1980年代对于非法产业的整治、历史剧院的活化和写字楼的开发建设是基础性的“刮骨疗伤”,那么21世纪初开始为了改善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街区活力所做的探索与实践则是更精细化的“改头换面”。 这一过程展现了两方面启示。
一方面,城市更新必须尽可能培育和引入多元的治理主体,建立更加包容性的治理结构。在时代广场更新的早期阶段,市政府既是城市更新的发起者、策划者也是推动者,几乎主导了全部公共事务的决策。在接近一元化和单向度的管理框架下,政府和大开发商结成精英联盟,建立增长机器,推动形成以追求经济效率与土地增值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模式。但由于这种模式对社区意见和社区文化的天然忽视,引起在地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强烈反弹,导致开发成本大幅增加,加上对市场需求的错估,暴露出这一治理模式的高脆弱性。通过对失败的反省,政府开始调整发展策略,转变治理架构,更加关注城市更新的在地性,逐步纳入和借助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与市场主体,不仅调动了各类非政府力量的积极性,也激发了更多的创意,并催生了更为多元丰富的业态,顺利推动第一轮更新的成功完成。在此基础上,随着更多治理机制的创新和治理工具的应用,第二轮城市更新参与主体的类型更多样、层次更丰富,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显著上升,空间实际使用者的个体意见也得到尊重,居民拥有了表达意见的渠道,至此形成一个强调互动、协同与合作的高度包容性的治理框架,为街区整体的可持续更新发展与优化提升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
另一方面,以“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为基础,城市更新必须实现多样灵活的治理工具组合与配置,特别通过社会性工具的导入实现各种利益的统筹与平衡。区分社会性治理工具的主动或被动的引入方式,不仅可以清晰地解读治理主体的不同行动动因,而且便于分析治理主体在治理行动中的行动逻辑。如果参与主体是基于履行社会责任或获得相关利益的自愿主动,那么在面对更新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牵涉主体的多样性问题时,可以更好地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统筹和不同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在时代广场更新的早期,增长联盟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性工具、管理性工具(设计导则)與经济性工具(土地出让和容积率转移)进行组合。治理主体大多被动参与更新改造的过程,伴随其中的是治理工具的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滞后、信息不对称、搭便车等问题。政商二元合作模式正是由于缺乏社会力量的制衡,导致偏离了最初治理目标。但是在第二次更新过程中,不仅政商关系发生了转变(开发商不再与政府强行捆绑),而且社会性工具被主动引入治理过程中,从而通过自下而上的激励性治理工具的实施,实现了高执行效率、有偿性和引导性,并通过征税、收费、补贴、支付转移等方式来调动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合作协调的积极性,激发出自上而下政策制定中难以实现的创造性。由此,不同治理主体可以在更主动的社会性工具的引导下取长补短、协调合作和统筹资源,为实现街区的更新和治理建立有弹性和创造性的激励协同机制。
在存量更新时代,城市更新是一个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过程,我国当下的城市更新在大部分情况下仍过于依赖政府的力量,传统“全能政府”思维框架下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诸领域,无论是在价值体系、知识架构还是实施路径方面都已无法很好地适应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如果要达到存量发展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真正落实“人民城市”理念,那么在城市更新中高度关注治理议题,通过全面推动治理模式的变革来激发全社会对城市更新的参与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趋势。如何在城市更新领域推进多元合作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如何理解城市更新中合作机制的重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如何解释在全球城市更新的模式演化和机制转型等复杂环境中城市更新所反映出的城市治理问题,以及如何推动更加多元、包容的城市核心区城市更新及其相对应的治理模式等,是本文试图以时代广场为例所探讨的核心议题,也是学界和业界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董玛力,陈田,王丽艳.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J]. 人文地理,2009,109(5):42-46.
DONG Mali, CHEN Tian, WANG Liyan. Development course and policy evolu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ities[J]. Human Geography, 2009, 109(5): 42-46.
KEARNS A, PADDISON R. New challenges for urban governance[J]. Urban Studies, 2000, 37(5-6): 845-850.
XU J. Governing city-regions in China: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for regional strategic planning[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8, 79(2-3): 158-185.
阳建强,陈月. 1949—2019年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与回顾[J]. 城市规划,2020(2):9-19.
YANG Jianqiang, CHEN Yue.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2): 9-19.
张更立. 走向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西方城市更新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城市发展研究,2004,11(4):26-32.
ZHANG Gengli. Towards three-way partnership in urban regenerati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to Chinese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04, 11(4): 26-32.
胡燕,孙弈,陈振光. 中国城市与区域管治研究十年回顾与前瞻[J]. 人文地理,2013,28(2):74-78.
HU Yan, SUN Yi, CHEN Zhenguang,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74-78.
葛天任,李强. 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J]. 城市规划学刊,2022(1):81-88.
GE Tianren, LI Qiang. From growth coalition to equity governance: a political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1): 81-88.
何深静,刘玉亭. 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J]. 人文地理,2008(4):6-11.
HE Shenjing, LIU Yuting.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the pattern of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transition[J]. Human Geography, 2008(4): 6-11.
罗小龙,张京祥. 管治理念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J]. 城市规划汇刊,2001(2):59-62,80.
LUO Xiaolong, ZHANG Jingxiang. Governa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1(2): 59-62, 80.
耿慧志. 论我国城市中心区更新的动力机制[J]. 城市規划汇刊,1999(3):27-31.
GENG Huizhi. On the dynamics of urban center renewal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9(3): 27-31.
VON HOFFMAN A. The lost history of urban renewal[J]. Journal of Urbanis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lacemaking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 2008, 1(3): 281-301.
MOSES R. Slums and city planning[J/OL]. The Atlantic, 1945, 1 [2022-07-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45/01/slums-and-city-planning/306544/.
CHRONOPOULOS T. Morality, social disord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Times Square, 1892–1954[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1, 30(1): 1-19.
BRACKER M. Life on W.42d St. A study in decay[N]. The New York Times, 1960-03-14(001).
TRAUB J. The devil's playground: a century of pleasure and profit in Times Square[M]. New York City: Random House, 2005.
REICHL A J.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mes Square[D].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niversity, 1999.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Midtown development[R]. 1981.
STERN W. The unexpected lessons of Times Square's Comeback[EB/OL]. [2022-07-14]. https://www.city-journal.org/article/the-unexpected-lessons-of-times-squares-comeback#s.
SAGALYN L B. Times Square roulette: remaking the city ic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FAINSTEIN S S. The city builders: property, politics, and planning in London and New York[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SAGALYN L B. Mediating change: symbolic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s Square[C]//Conference on New York City History, 2001.10
KAPLAN S. The 42nd Street art project, West 42nd Street between Broadway and Eighth Avenue[J]. ETC, 1993, 11(24): 56-58.
BELL J. Times Square: public space Disneyfield[J]. The Drama Review, 1998, 42(1): 24-25.
BAGLI C. Times Square at 100; and now, for the next act[N]. The New York Times, 2004-06-13.
BAGLI C. After 30 years, Times Square rebirth is complete[N]. The New York Times, 2010-12-03.
MILLER K. Condemning the public: design and New York's new 42nd Street[J]. GeoJournal, 2002, 58(2-3): 139-148.
GIULIANI R W, ROSE J B, CHAPMAN W L. Midtown Manhattan pedestrian network development project[R]. 2000.
The Times Square Allianc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re-imagining the pedestrian environment in Times Square[R]. 2004.
Starr Whitehouse Landscape Architects and Planners PLLC. Times Square: the second century workshop brief: re-imagining the bowtie[R]. 2004.
STEAD N. TKTS: Choi Ropiha, Perkins Eastman and PKSB remake the experience of Times Square[J]. Architecture Australia, 2009: 71-75.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PlaNYC: 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Z]. 2007.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Sustainable streets: strategic plan for the New York City[R]. 2008.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World class streets: remaking New York City's public realm[R]. 2008.
TAYLOR A. Lawn chairs in Times Square: an analysis of the Pilot Streets Program and the provisional project approach for New York City's Green Light in Midtown project[D].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1.
The Times Square Alliance.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0[R]. 2010.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Green Light for Midtown evaluation report[R]. 2010.
中島直人,関谷進吾. ニューヨーク市タイムズ·スクエアの広場化プロセス——BID設立以降の取り組みに著目して[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2016,81(725):1549-1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