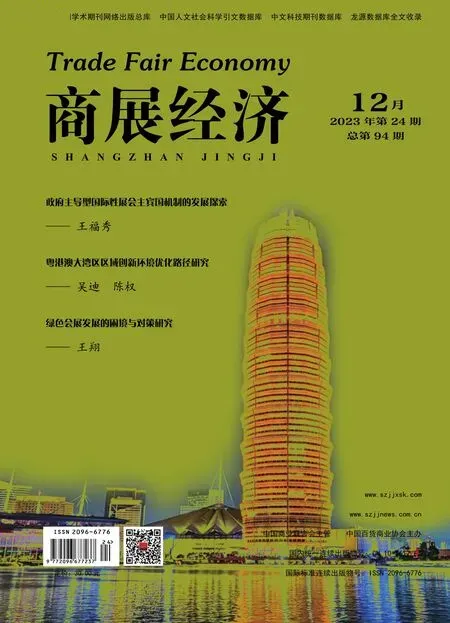新生代员工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
2024-01-04杨启迪
杨启迪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2022年8月25日,人力资源网站前程无忧发布了一份名为《2022新生代员工职场现状》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80后个体的首份工作通常持续3年半,90后为19个月,95后则缩减为7个月。由此可见,新生代员工的首份工作时长呈现出显著递减的趋势。如今,新生代员工已逐渐成长为各行各业中的主干力量。相较60后和70后员工而言,新生代员工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多元化的职业观念,不再把工作仅当成谋生的手段,金钱等外在奖励很难再对他们产生持久的激励作用。因此,管理者需要找到一种稳定的内部动机,以激发年轻个体的工作积极性。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发现,那些体验到自身工作意义,并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员工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将所从事的工作视为自身的使命,通过寻找工作带给自己的意义和自己带给组织的贡献,呈现出持久而稳定的积极工作态度,最终产生良好的工作绩效,即具备职业召唤。由此,职业召唤成为一个深受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目前,关于职业召唤结果变量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态度层面,如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等(裴宇晶、赵曙明,2017),关于职业召唤与个体行为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
进入21世纪,企业要想保持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对所拥有的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知识共享作为知识管理中的重要环节,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帮助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然而,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与否很大程度上受自身内部动机的影响。为了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发生,管理者需要找到一个持久的因素来激励员工,而职业召唤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内在动机,正好满足这一条件。综合上述背景,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新生代员工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间的作用机制,丰富职业召唤的本土化研究内容,为企业在新生代员工的激励上提供相应的启示。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
职业召唤(Career Calling)起源于西方神学领域,指神父与牧师在上帝的引导下,建立起普度众生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职业理想。十六七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期间,Luther将召唤从宗教霸权中解放出来,从此“召唤”一词不再特指神职人员,普通人也能感受到来自上帝的召唤。20世纪80年代,Bellah等社会学家把劳动者的工作价值观划分为谋生、职业和召唤三种导向,之后召唤逐渐发展为职业召唤(林纯洁,2010)。
进入21世纪,学者对职业召唤的研究转移到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在心理学领域,学者主要研究职业召唤的来源;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则主要研究职业召唤对个体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的影响(田喜洲、左晓燕,201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本文将职业召唤定义为:个体将工作视作自身使命的一种强烈的内部动机,具有认可工作的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意义的特点。近年来,学者愈发重视职业召唤对员工建言行为等角色外行为的研究(胡利利等,2017),但有关职业召唤结果变量的研究依然匮乏,无法涵盖多元化的员工行为。
知识共享行为(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是指个体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与组织中其他成员进行互相交换,并创造出新知识的行为。自我决定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职业召唤水平高的个体,工作时可以遵从自身意愿,满足了自主需求;可选择自己能够从容对待的工作,满足了胜任需求;和组织中其他成员保持和谐的关系,满足了关系需求。因此,他们的自主性工作动机较高,自觉将自己归为组织内部的一员,积极参与到利于组织发展的知识共享行为中。此外,职业召唤具有很强的亲社会性,知识共享行为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亲社会性的员工期望自己能为他人的福祉做出贡献,所以他们乐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分享知识。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工作意义对知识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工作意义对知识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亲社会性对知识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亲社会性对知识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
H1e:超然的召唤对知识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
H1f:超然的召唤对知识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职业召唤与组织承诺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职业召唤水平较高的员工会在工作中表现出更高的职业认同感,其自主性需要和胜任需要能够得到更好地满足,因此组织承诺水平更高。国外学者认为,职业召唤对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职业召唤和工作满意度呈现出双高状态时,个体的组织承诺达到最高水平,意味着即使对所从事的工作不太满意,但存在职业召唤的员工也会产生较高的组织承诺(Neubert,2015)。国内学者也认为,职业召唤对组织承诺存在正向影响,如果缺少职业召唤的内在驱动,就会增加员工跳槽的概率(赵小云、王静,201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职业召唤对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工作意义对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亲社会性对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超然的召唤对组织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组织承诺与知识共享行为
知识共享行为是一个互动过程,既需要知识贡献者提供知识,又需要知识需求方愿意接受知识,组织承诺对知识贡献和知识获取都有积极的影响(杨齐,2014)。
一方面,组织承诺代表了个体与组织间的情感联结,当这种情感联结越强时,个体就越愿意为组织做出额外的贡献,比如主动将自己掌握的宝贵知识分享给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以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产生组织承诺的原因是留在组织中能获得物质和情感两方面的满足感,为了持续获得这种满足感,个体愿意主动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请教,获取知识,提高自身价值,避免被组织淘汰,进而表现出主动接受知识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组织承诺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组织承诺对知识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组织承诺对知识获取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认知行为主义理论表明,个体在刺激和行动之间需要有一个心理认知层面的中介变量进行解释,组织承诺属于认知层面,在研究员工动机、组织氛围等因素对个体的行为影响过程中具有很好的中介解释作用。所以,选择组织承诺作为研究职业召唤和知识共享行为作用关系的中介变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组织承诺在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H4a:组织承诺在工作意义与知识贡献间起中介作用;
H4b:组织承诺在亲社会性与知识贡献间起中介作用;
H4c:组织承诺在超然的召唤与知识贡献间起中介作用;
H4d:组织承诺在工作意义与知识获取间起中介作用;
H4e:组织承诺在亲社会性与知识获取间起中介作用;
H4f:组织承诺在超然的召唤与知识获取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湖南、广东10余家企业,涉及的行业主要有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共获得有效问卷302份。调查对象中,性别方面,男性占比45.6%、女性占比54.4%;年龄方面,25岁以下员工占比11.5%、25~30岁占比40%、30~35岁占比38%、35岁以上占比10.5%;学历方面,专科及以下占比4.3%、本科占比71.1%、硕士及以上占比24.6%。
2.2 测量工具
本文采取较为成熟的国内外量表设计问卷,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职业召唤的测量采用Dik等(2012)开发的CVQ量表,共12个题项、3个维度。该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843,信度良好。组织承诺的测量参考陈永霞等(2006)开发的量表,共选用6个题项进行测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信度较高。知识共享行为采用Hooff&Ridder(2004)开发的二维量表,共10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9,信度较高。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Amos21.0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效度,各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职业召唤的三因子模型、组织承诺的单因子模型和知识共享行为的二因子模型均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工作意义、亲社会性和超然的召唤均与组织承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394、0.453和0.430,显著性水平均为p<0.01。组织承诺与知识共享行为的两个维度显著正相关:知识贡献(r=0.547)、知识获取(r=0.570)显著性水平均为p<0.01。工作意义、亲社会性和超然的召唤均与知识贡献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398、0.414和0.418,显著性水平均为p<0.01。工作意义、亲社会性和超然的召唤均与知识获取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依次为0.381、0.415和0.419,显著性水平均为p<0.01。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
3.3 假设检验
本文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参照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检验组织承诺是否在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3.3.1 检验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主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x2=280.596,df=200,x2/df=1.403,RMSEA=0.037,CFI=0.977,TLI=0.974)。由图1可知,在该模型中,工作意义(β=0.27,p<0.001)、亲社会性(β=0.28,p<0.001)和超然的召唤(β=0.30,p<0.001)均对知识贡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a、H1c、H1e得到支持。工作意义(β=0.24,p<0.001)、亲社会性(β=0.31,p<0.001)和超然的召唤(β=0.30,p<0.001)均对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b、H1d、H1f得到支持。

图1 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主效应验证模型
3.3.2 检验组织承诺在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x2=457.785,df=336,x2/df=1.362,RMSEA=0.035,CFI=0.974,TLI=0.971)。由图2可知,在该模型中,工作意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24,p<0.001),H2a得到验证;组织承诺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贡献(β=0.35,p<0.001)和知识获取(β=0.37,p<0.001),H3a和H3b得到验证。此外,工作意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贡献(β=0.19,p<0.01)和知识获取(β=0.15,p<0.05),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第3步,H4a和H4b得到部分验证,即组织承诺在工作意义与知识贡献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承诺在工作意义与知识获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图2 组织承诺在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验证模型
亲社会性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34,p<0.001),H2b得到验证。此外,亲社会性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贡献(β=0.15,p<0.05)和知识获取(β=0.18,p<0.01),H4c和H4d得到部分验证,即组织承诺在亲社会性与知识贡献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承诺在亲社会性与知识获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超然的召唤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承诺(β=0.29,p<0.001),H2c得到验证。此外,超然的召唤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贡献(β=0.19,p<0.01)和知识获取(β=0.19,p<0.01),H4e和H4f得到部分验证,组织承诺在超然的召唤与知识贡献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承诺在超然的召唤与知识获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2)。
4 结语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职业召唤、组织承诺和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新生代员工的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各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组织承诺在职业召唤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4.1 理论意义
拓展了职业召唤结果变量的研究。目前,有关职业召唤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的态度层面,如工作满意度、离职意愿等,缺少进一步探究职业召唤对个体行为和工作的深入影响,以及对组织未来发展影响的文献。本文通过探究职业召唤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拓展了职业召唤结果变量的研究范围。
4.2 实践意义
开拓管理实践新视角,引导管理者从内在动机出发,激发新生代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相比传统的金钱等外在激励举措,企业从内在激励员工更为持久和经济。研究职业召唤和知识共享行为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改善管理模式,促使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来增强员工的职业召唤,提高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促使员工通过知识共享行为把其宝贵的工作经验转化成组织财富,推动知识流动,提高知识的价值,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组织与员工自身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