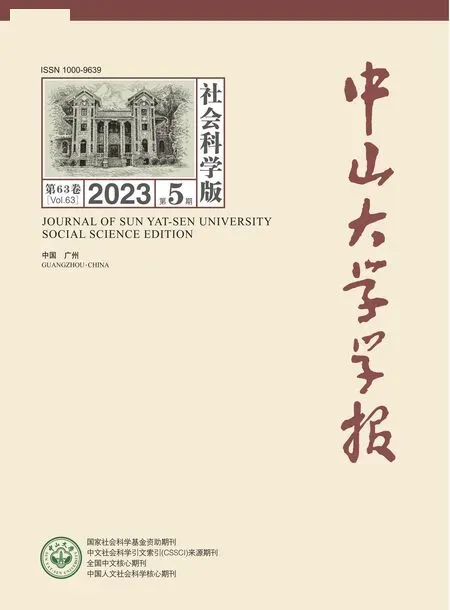论鲁滨孙的枪手形象*
2024-01-03陈建洪
陈建洪
笛福所创造的鲁滨孙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形象。这个经典形象的影响力不仅停留在文学领域,而且扩散到哲学和经济学等等领域。在各种研究中,鲁滨孙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对鲁滨孙的喜爱,也讨论了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的“孤岛上的鲁滨孙”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96、101页。。盖尔纳指出:“马克思已经注意到鲁滨孙是深得经济学家喜爱的角色,但是他在哲学家们的心底出现得更多,尽管他们并不经常提到他的名字。”②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104.哲学领域关于鲁滨孙最有影响的讨论无疑出自卢梭。在《爱弥儿》中,卢梭把《鲁滨孙飘流记》明确为爱弥儿的首要读物③[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44页。,并强行把鲁滨孙看作是未受社会污染的典型。瓦特认为,鲁滨孙是在清教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中体现了英国个人主义特征的文学形象④Ian Watt,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Faust,Don Quixote,Don Juan,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1-171.。韦伯认为,有别于之前的朝圣者形象,鲁滨孙是反映清教精神、注重现世奋斗的“经济人”⑤[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72页。。萨义德则指出,鲁滨孙故事是奠定殖民帝国基础的文学叙事⑥[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86、95页。。鲁滨孙的所有这些形象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被大部分研究文献所忽略的身份,那就是他的枪手身份。面对海盗、野兽、野人和欧洲对手,鲁滨孙作为枪手的身份都具有无比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鲁滨孙年少时便一心要遨游四海,命运却将他的大段光阴锁在荒岛。在岛上,鲁滨孙不得不成为猎人、农夫、牧人、匠人、面包师,一度还想成为酿酒师。鲁滨孙无所不能的形象正是笛福所塑造的“普通人的全能”特征⑦Virginia La Grand,A Spectacular Failure:Robinson Crusoe I,II,III,Amsterdam:Rodopi B.V.,2012,p.153.。鲁滨孙曾经对自己的荒岛形象有一个比较细致的描述。在这个描述中,鲁滨孙强调了两样东西是他“最不可少的”。一是他的枪,二是“又丑又笨的大羊皮伞”①[英]笛福著,徐霞村译:《鲁滨孙飘流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3页。后皆随文注出。。就重要性而言,枪无疑排在伞的前面。枪对于荒岛鲁滨孙的重要性,胜过一切。枪的出镜率远非伞的出镜率可以比拟。如果没有对枪支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那么鲁滨孙就不可能成为鲁滨孙。鲁滨孙的冒险和生活历程也是他成长为一位枪手的过程。从枪手角度来看待鲁滨孙,可以更好地理解鲁滨孙这个形象及其象征的殖民征服故事。
枪对于鲁滨孙故事的意义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布列维特(David Blewett)考察了小说不同版本和不同译本的插图。在绝大部分插图中,枪都是醒目可见的物件。可惜布列维特对醒目的枪支几乎视而不见,主要根据不同的插图来解说不同的文化视角。比如说,在英国人的插图中,鲁滨孙只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在法国人的插图中,鲁滨孙则升格为一种英雄形象②David Blewett,“The Iconic Crusoe:Illustrations and Images of Robinson Crusoe”,in John Richetti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59-190,at 163.。刘禾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了枪对于理解鲁滨孙和星期五之间依附关系的指义功能。鲁滨孙的枪传递给星期五的信息是“要么服从,要么被杀死”。枪指明了殖民统治者所凭借的就是“无法匹敌的军事技术”。所以,“鲁滨孙手中那杆枪的威力,还不在于它是一种夺人性命的物质力量,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实现恐怖和人的意图的符号所具有的那种指义功能”③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7页。。
洛尔(Christopher F.Loar)从暴力和军事技术的角度富有洞见地集中分析了枪支对于鲁滨孙确立主权统治地位和英国自由主义修辞的根本作用。洛尔指出,笛福把暴力看作是欧洲文明与主权征服其他民族的奠基因素,但小说本身或者鲁滨孙这个角色则没有直接肯定这种暴力奠基因素,而是为这种暴力因素披上一层温和的文明修辞外衣④Christopher F.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Vol.19(Fall 2006)No.1&2:pp.1-20,at p.5,at p.5,at p.7,p.9.。殖民主权者拥有具有惊悚暴力效果的枪支,被殖民者对杀人于无形的枪支莫名其妙而惊为神力。洛尔指出,枪支的这种神秘莫测性也遮掩了它所代表的暴力⑤Christopher F.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Vol.19(Fall 2006)No.1&2:pp.1-20,at p.5,at p.5,at p.7,p.9.。洛尔强调指出,鲁滨孙更愿意把殖民关系描写为一种自愿、同意和友谊的关系,他认为,殖民的暴力基础在星期五那里比在鲁滨孙那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体现。星期五惧于枪支的致命威胁而不得不接受鲁滨孙的主权地位和文明要求。鲁滨孙自认为他对于星期五以及其他野人的统治是出于他是一个文明的基督徒,然而从星期五对枪支的态度来看,他的顺从在根本上建立在枪支的暴力之上⑥Christopher F.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Vol.19(Fall 2006)No.1&2:pp.1-20,at p.5,at p.5,at p.7,p.9.。
洛尔的文章颇具慧眼地看到了枪支对于理解鲁滨孙与星期五——也就是殖民关系——的根本意义。不过,洛尔的分析区分了笛福、鲁滨孙和星期五三者对暴力的不同态度,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洛尔的分析包含了两组对照。其中,一组对照是作者笛福与主人公鲁滨孙的对照。他认为,笛福深知而鲁滨孙不知道政治殖民秩序和英国意识形态背后的暴力基础。另一组对照则是鲁滨孙与星期五的对照。星期五知道而鲁滨孙不知道英国秩序的暴力起源。换句话说,鲁滨孙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自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而星期五则表明了自己的顺从是出于对枪支也即死亡的恐惧。因此,洛尔开篇就说:“星期五可能比克鲁索更好地理解鲁滨孙·克鲁索的枪。”⑦Christopher 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19,nos.1-2(2006):pp.1-20,at p.1.我同意洛尔以及刘禾认为暴力和军事技术作为英国殖民秩序基础的观点,但不同意洛尔的一个论证倾向:鲁滨孙否定暴力是出于他纯真无辜的文明信念。换句话说,鲁滨孙和笛福、鲁滨孙和星期五在暴力作为殖民秩序基础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形成那么强的对照。鲁滨孙的枪手身份实际上是他立志成为水手的必经之路。他清楚知道,有枪在手他才能出逃摩洛哥,才能猎杀动物,才能枪杀登岛“野人”,才能击退敌手。
一、水手鲁滨孙
鲁滨孙立志要成为水手,但并没有立志要成为枪手。鲁滨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位枪手,就好像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位水手。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开始就是枪手。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枪手,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枪手。鲁滨孙愿意成为水手,也可以成为枪手。鲁滨孙清晰地描述了他怎样成为一名水手,但并没有清晰地描述他怎样成为一名枪手。成为水手和成为枪手,都需要后天学习。鲁滨孙明确表明,第二次出海也就是第一次非洲之旅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水手和商人。由于自小并不在水上生活,鲁滨孙经过船主的点拨和教导之后才成为一名水手。但是,枪手鲁滨孙似乎是横空出世。鲁滨孙没有描述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了一名枪手,也没有描述究竟谁教会了他用枪。不过,在鲁滨孙的生活时代,水手生涯自然伴随着枪声。也就是说,17 世纪的航海船只常备枪支甚至火炮和弹药。总体来看,船只配备枪支弹药,主要是为了在自然遇险的时候可以发出示警和求救的信号,在面临人为危险的时候可以用来自卫和战斗。成为一名枪手是水手鲁滨孙的必由之路。
第一次航行的时候,鲁滨孙还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水手”(9)。从第一次航行开始,鲁滨孙就体验了航海生涯中的枪声。这一次航行接二连三遭遇风暴。当面临着即将沉船危险的时候,船主看见有其他船只经过的时候,便下令“放一响枪,作为求救的讯号”(9)。鲁滨孙自承,那时候他并不懂得放枪的意思,误以为要么船破了要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因为枪声而大吃一惊,还吓晕在甲板上。等他醒来的时候,船马上就要沉了。船主继续鸣枪求救。途经的另一船只听到枪声,放了一只小艇冒着极大风险前来搭救,最终才幸免于难(10)。从这个经历来看,第一次航行的鲁滨孙完全缺乏对船只上的枪支及其功能的认知。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鲁滨孙此时不会开枪,但是可以断定他还完全不知道船只遇险时鸣枪就是求救的意思。
在第二次航行中,鲁滨孙在船主的指导下学会了一些“数学知识和航海的规程”,学会了“记录航程”和“观测天文”的方法。由此,鲁滨孙说他“懂得了一个航员所应懂的一切”。这个结论的前提都指向科学知识。我们无从知晓,“一个航员所应懂的一切”是否包括枪支及其使用的知识。不管怎么说,这次航行是一次没有枪声的行程。鲁滨孙因为这次航行而成功地跻身“海员”和“商人”之列。这次航行如此成功,以致鲁滨孙变得更加野心勃勃。这次成功之旅的唯一的缺点是鲁滨孙在炽热的气候之下得了热病,因此经常生病。有研究指出,小说用热病与痛风两种疾病来说明鲁滨孙和父亲克鲁索生活态度的差异:患热病的状态是“极端”和“不安分”,患痛风的人则追求一种“适度与平衡的生活方式”①王旭峰:《论〈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疾病》,《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若果真如此,鲁滨孙最为成功的航行之旅也始终伴随着父亲的咒语。
不同于第二次航行,鲁滨孙的第三次航行也是第二次几内亚之旅伴随着隆隆的枪炮声。鲁滨孙把这次航行称为他“有史以来最不幸的航行”。这次航行之所以不幸,是因为船只碰到了从摩洛哥来的土耳其海盗船。鲁滨孙表述了两艘船只的火力对比:他们的船上有十二尊炮,海盗船则有十八尊炮。也就是说,海盗拥有的炮比他们多出三分之一,也就是多六尊炮。炮火交锋之后,两艘船还经过了“枪弹、刺刀、火药和其他武器”的攻守战斗。虽然两次击退海盗船,但鲁滨孙所搭的船最终还是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他们这一方死三人伤八人,全部被掳到了摩耳人的口岸萨利。就鲁滨孙个人而言,这次航行之所以最为不幸,是因为他因此从一名“商人”成了海盗船船长的战利品,沦落为“可怜的奴隶”(15)。鲁滨孙描述了两艘船之间的追逐、战斗和战果,但没有明确描述他自己是否参与以及怎样参与战斗过程。所以,依然无法据此知道,鲁滨孙是否懂得开枪以及是否在这次战斗中开了枪。
被掳为奴的时光里,鲁滨孙特别提到了很少被提到的一个特殊才能。这个特殊才能就是他那高明的“捕鱼技术”(16)。因为他很会替主人捕鱼,所以主人出海打鱼的时候“没有一次不带”鲁滨孙去(17)。鲁滨孙没有明确,是否在被掳那段时间里练就他的捕鱼技术。不管怎样,鲁滨孙是一个不错的渔夫,因此得主人欢心。在最为醒目的荒岛生涯中,渔夫这个身份基本上隐而不显。鲁滨孙曾经不经意地记录他在岛上钓鱼的时刻,但表示没有钓到一条他敢吃的鱼(73)。跟农夫、牧人、匠人这些身份相比,渔夫鲁滨孙在孤岛几乎隐而不显,除了常常捉鳖(75)。
鲁滨孙在萨利为奴近两年时光。一次,因为准备与本地有地位的摩耳人出海闲游打鱼,需要运送大量食品上船,主人还吩咐鲁滨孙预备好“三支短枪和火药”(17)。当鲁滨孙准备妥帖之时,却因客人临时有事而改期出海。但因客人还是要来晚餐,主人命令鲁滨孙和同伴照样出去打点鱼回来。不忘出逃的鲁滨孙此时突然闪现“争取解放的老念头”(18)。于是,鲁滨孙先找了借口让摩耳人同伴伊斯玛(又名摩雷)弄来了一大筐饼干和三罐淡水,同时悄悄地把主人装酒瓶的箱子搬到船上去,还搬了蜜蜡和日用工具。然后,他又以打水鸟的名义让摩雷弄了不少的火药和子弹,同时又自己悄悄地装了一大瓶火药。于是,鲁滨孙、摩雷和小孩佐立跟平常一样出港打鱼。途中每逢有鱼上钩的时候,鲁滨孙总是故意不把鱼钓起来。如此,他就以打不到鱼的借口走得更远一些。在出港二海里的位置,鲁滨孙趁摩雷不注意时瞬间把他扔到海里。摩雷浮出水面,求鲁滨孙让他上船,并表示愿意跟随他走到天涯海角。在这个时候,鲁滨孙到船舱取了一支鸟枪,对准水里的摩雷,表示自己不想害他,只是决心要恢复自由;他要求摩雷不要靠拢船只,可以自己游到岸上去;不然,就要打穿摩雷的脑袋(19)。
整个文本中,这是鲁滨孙第一次用枪对准一个人。当然,这次瞄准的目的只是警告威胁,而不是蓄意杀人。这个场景清晰地展示了鲁滨孙可以熟练使用枪支,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学会使用枪支。水手鲁滨孙似乎瞬间就成为了枪手,枪手鲁滨孙就此横空出世。从文本脉络来看,如果说熟练使用枪支本是一个水手的应有本领,那么鲁滨孙很可能是在第一次去往几内亚的航行中学会了这个本领。至少,从萨利逃脱之旅开始,水手鲁滨孙就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枪手。熟练使用枪支的本领帮助鲁滨孙摆脱了摩耳人同伴摩雷,枪支成功保障了鲁滨孙出逃计划的成功。
为了躲避主人的追赶,鲁滨孙一反常态不向北行驶,而是向着黑人部族的蛮荒海岸开去。从这个时候开始,鲁滨孙就一直担心会被“野兽或是更无情的野人”(20)吃掉。不过,在逃离萨利的航行中,枪支起着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它避免了他们落入野兽之口或野人之手。一路上,鲁滨孙和佐立至少开枪打跑了来袭的一只巨兽——据佐立说是狮子(21),打死了一头狮子(23—24)和一只奇特的豹子(26)。枪支不仅使他们避免野兽的袭击,而且也吓倒了岸上黑人并赢得他们的钦佩。岸上黑人听见枪声见到火光的时候,惊慌失措甚至吓得跌倒在地,完全不知道鲁滨孙用什么东西打死水里的豹子。这个描述也为后来登岛的“野人”听见枪声看见火光的类似反应埋下了伏笔。这种惊吓的原因并不在于隔空杀人的能力,而是对于枪支运作原理的无知①Christopher F.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Eighteenth Century Fiction,Vol.19(Fall 2006)No.1&2:pp.1-20,at pp.11-12.。枪支杀生就好像闪电那样,带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可怕速度。
枪声和火光代表着技术和杀戮的压倒性优势。这个枪声和火光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那片世界。枪支所发出的声音和火光震慑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世界和大西洋西边的加勒比世界。黑人和加勒比“野人”所生活的世界,都被鲁滨孙同等地称为野蛮世界。鲁滨孙“坚信所有与他相貌有异的人都是野蛮人(比如食人族,比如黑人),信心满满地肩负起在帝国之外的荒芜世界传播文明的任务(即使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一片光秃秃的岩石群)”①[加]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著,徐楠译:《迷人的怪物:德古拉、爱丽丝、超人等文学友人》(Fabulous Monsters:Dracula,Alice,Superman,and Other Literary Friend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5,106页。。不过,鲁滨孙没有将摩耳人称作野蛮人。在落难萨利的两年生涯当中,鲁滨孙没有提到他用什么语言跟主人和其他人进行交流。那个时候,他应该并不懂得除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在出逃之旅中,他们遇到葡萄牙船只,当对方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来向他问询的时候,鲁滨孙表示自己“通通不懂”(28)。除了枪声和火光,用什么语言进行交流体现了对话者的地位优劣。关于被掳生涯的语言使用,鲁滨孙保持了沉默。这跟他后来碰到星期五的情况截然不同。鲁滨孙对于教星期五学习英语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信心,但是完全没有兴趣了解星期五本来说什么语言。如曼古埃尔指出,鲁滨孙“不会学习星期五的语言,也永远无法了解星期五的信仰世界”②[加]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著,徐楠译:《迷人的怪物:德古拉、爱丽丝、超人等文学友人》(Fabulous Monsters:Dracula,Alice,Superman,and Other Literary Friend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5,106页。。其实,如瓦特指出,鲁滨孙完全没有兴趣尝试去理解星期五或者与他进行对话③Ian Watt,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Faust,Don Quixote,Don Juan,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8.。在这一点上,鲁滨孙跟哥伦布没有什么区别,他“不去理解别人,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④[法]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著,卢苏燕等译:《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在遇到葡萄牙船只的时候,鲁滨孙用旗帜向对方发出危急信号,又鸣枪求救。枪支保障出逃的顺利和出逃途中的安全,也发出了示警和求救的信号。因此,鲁滨孙得以摆脱奴隶身份,从而被葡萄牙商船带到巴西,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巴西四年的种植园生涯中,鲁滨孙的叙述完全没有提到枪的事情。和在英国一样,枪不是鲁滨孙在巴西生活的关键物品。只有出门在外,枪支才是鲁滨孙随身必备物品。鲁滨孙虽然也把荒岛居所看作家,但那是迫于命运的逗留。落难荒岛的生涯中,比起其他任何物品包括圣经在内,枪支为鲁滨孙带来了最为重要的成就感和安全感。枪支是鲁滨孙在荒岛的生活必需品。只要出门,必定带枪。在岛上的生涯,枪支的功能因为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岛第15 年偶然发现沙滩的不明足迹是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枪支的主要作用是猎杀动物。在那之后,枪口主要针对或者潜在针对到访岛屿的陌生人,尤其是“野人”。所以,在荒岛生涯的前一半,鲁滨孙可以说是一个猎手。后半生涯,则主要是琢磨怎么与人斗的枪手。在与人斗争的过程中,对面的敌手是用冷兵器还是同等使用热兵器,意义也不相同。枪支奠定了鲁滨孙自己的地位,也塑造了他与动物、与野人以及与同样来自“文明”世界的他人之间的关系。
二、猎手鲁滨孙
在萨利的时候,鲁滨孙是渔夫;在巴西的时候,是种植园主;在荒岛,他首先是一位猎人。当然,猎人未必都必然是带枪猎人,比如星期五。在从里斯本回英国的陆路行程中,星期五请求鲁滨孙允许他与熊嬉戏,将它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用匕首将其杀死。鲁滨孙没有星期五这种近身猎杀凶猛动物的技艺。他是带枪猎手。作为带枪猎手,枪支和弹药就显得无比重要。
刚刚落难荒岛之时,鲁滨孙的随身物品仅有一把“刀”、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鲁滨孙没有说明为什么在这生死攸关之际随身带上这几样物品。有一种可能是,这几样物品是鲁滨孙在行船途中的日常用品。当发现身上仅有这几样物品的时候,鲁滨孙感到特别伤心甚至“忧心如焚”,因为他没有枪支在手。缺乏枪支,鲁滨孙就是野兽的猎物。一个缺乏枪支的带枪猎人,一则不能防御野兽捕食,二则不能猎取野兽过活。在这种情况下,鲁滨孙认为自己在岛上将要么“活活饿死”,要么“被野兽吃掉”(40)。从这一点来看,鲁滨孙的自我意识首先还是猎人而不是农夫。在岛上的第一个夜晚,鲁滨孙以烟叶充饥,在树上过了一宿。第二天醒来,惊喜地发现搁浅的大船并没有沉没,于是他设法登船寻找可以“度日的东西”(41)。这一天,他从船只上搬运上岛的首先是粮食、酒、衣物和土木工具,其次是弹药和枪械。具体而言,鲁滨孙搬上岸的枪支弹药包括两支鸟枪和两支手枪,还有装火药的角筒、子弹和旧刀剑,以及两桶干燥的火药(42—44)。
把船上的有用物品运到岸边之后,鲁滨孙开始勘查地势。他带了一支鸟枪、一把手枪和火药,来到附近小山的山顶。通过观察,他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自己落难在一座四面环海的孤岛。第二,岛屿非常荒瘠,估计只有野兽没有人烟。下山的路上,鲁滨孙向栖在树上的一只大鸟(可能是鹰)开枪并打死了它。鲁滨孙相信,这是岛上的第一响枪声(45)。托德(Dennis Todd)专门引用了鲁滨孙岛上第一枪的段落,并强调这意味着殖民主义者对于陆地的评估、占取和明确控制。不过,托德更多地强调殖民者在新世界的幸存,而不是“虚幻”的控制感觉①Dennis Todd,“Robinson Crusoe and Colonialism”,in John Richetti ed.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Robinson Cruso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42-156.。
之后一天,鲁滨孙又登船寻找有用的东西。回来之后,发现有一只野猫一样的动物站在他的一只箱子之上。鲁滨孙走近的时候,也非常镇定自若。鲁滨孙向野猫比了比枪,就好像他曾用枪对着摩雷一样,意在吓唬它。可是那野猫并不懂得枪的奥秘,所以并不在乎,也没有跑开的意思。鲁滨孙分了一块饼干给它,还想要的时候,鲁滨孙拒绝了它。然后,它就走开了。
从落难孤岛的那一刻起,鲁滨孙始终非常担心自己要么被野兽吞食,要么被野人所杀(40,47,50,60—61,117)。对这两种危险的双重忧虑,在鲁滨孙靠岸黑非洲寻找淡水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20—21)。鲁滨孙虽然在岛上一直表达这种双重忧虑,但由于在心底相信这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孤岛,所以实际上对于野兽袭击的忧虑要更重一些。鲁滨孙将野人与野兽相提并论。野人这个词,鲁滨孙没有用来指他曾为之所掳的摩耳人。他所说的野人,一指黑非洲部族,二指美洲部族。鲁滨孙也曾将自己与黑人以及印第安人进行优势对比(111)。对于鲁滨孙来说,黑人与印第安人不仅非我族类,而且是一定意义上的非人类。说鲁滨孙视黑人部族与美洲土著为非人,并非夸张。他的确后来通过描述“吃人”场景来指责“野人”为“非人”(146,207)。这两个部族都完全不知枪为何物,视枪为神物。王旭峰指出,笛福对海外岛屿进行“荒野化”和“原始化”描述,意图在于将这些土地“去文明化”,从而“为鲁滨孙殖民所有权的形成提供了自然权利论层面的前提条件”②王旭峰:《〈鲁滨孙漂流记〉、殖民所有权与主权政治体》,《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荒野化和原始化主要指海外土地,鲁滨孙实际上对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进行野蛮化、非人化。换句话说,鲁滨孙兽化了加勒比人,所以之后怒骂其为畜生。决定文明与野蛮的背后,枪支起着实质支撑的作用。
经过12 次登船寻找物品之后,那艘船在一阵暴风之后消失了。于是,鲁滨孙开始了在岛上的日常生活。他每天都要带枪出门一次,一来为了散心,二来为了猎食。第一次常规带枪出行的时候,鲁滨孙发现岛上有很多山羊。他叙述了第一次向山羊开枪的情形。那次,他打中了一只正在哺小羊的母羊。母羊被打死之后,小羊仍旧站在母羊身边不动。鲁滨孙把母羊提起来,小羊还是站着不动。当他把母羊背在肩上带走的时候,小羊便跟着他。到达住处之后,鲁滨孙放下母羊,把小羊抱进木栅,想要驯养小羊。不料,小羊无论如何都不肯进食。于是,鲁滨孙只好把小羊也杀了吃掉(53)。这个情况,鲁滨孙在日记里也简要记了一笔(62)。这一次应该算是鲁滨孙在岛上生涯的第一次打猎。之前虽然开枪击落过一只鹰,但那只是取乐,并不是捕猎。第一次捕猎山羊之后,鲁滨孙经常带枪出巡。除了山羊之外,鲁滨孙猎过“野鸭似的飞禽”“野猫”(62;62),也打过海鸟——可能是雁鹅(84)。总之,猎人鲁滨孙要比农人鲁滨孙和牧人鲁滨孙更早地出现在孤岛之上。
除了为觅食而猎杀动物以外,猎人鲁滨孙的枪也起着驱赶作用。一是为了驱赶繁殖力旺盛的猫,二是为了驱赶啄食他庄稼的鸟。从搁浅的船上,鲁滨孙曾经带回两只欧洲母猫,并将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其中一只曾经失踪一段时间,后来却带着三只小猫回来了。然后,这三只小猫越生越多,鲁滨孙不胜其烦,于是便把这些猫当作“害虫、野兽”一样加以扑杀,并且将它们赶出家门(90—91,131)。岛上生活的第三年,鲁滨孙开始种植“大麦和稻子”。在庄稼的成长过程中,鲁滨孙得防范两类破坏者。第一类是山羊和野兔之类,会吃掉禾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鲁滨孙把庄稼地用篱笆圈了起来,并且派了他的狗去看守。但是,篱笆和狗防得了温和的走兽,防不了飞鸟。抽穗的庄稼被飞鸟团团围住的时候,鲁滨孙立刻开枪。枪声惊动一大群飞禽从庄稼地里腾空而起。鲁滨孙不想失去他的收成,又无法整日整夜守着庄稼。每当他守在庄稼地的时候,鸟儿就停在树上。当他走开,鸟儿就降落到庄稼地。于是,他生气地开枪打死三只偷吃庄稼的鸟儿。然后,他借鉴了英国惩治窃贼的办法,把那这三只鸟儿用锁链吊起来示众,以儆效尤。这个方法取得了意外效果,那些飞禽之后再也不见了踪影(102—103)。
当鲁滨孙发现自己的火药大为减少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在火药耗光之后怎样猎取山羊的问题。于是,在岛第11年的时候,他开始研究用“陷阱和捕机”(128)。几经尝试,鲁滨孙认为,要想在弹药耗光之后能够吃到羊肉,驯羊是“唯一的办法”(129)。由于担心未来弹药不足而无法打猎,猎人鲁滨孙开始考虑转为牧人鲁滨孙。于是,鲁滨孙开始经营他的驯羊圈地,用篱笆和木栅把自己的驯羊跟野羊隔离。鲁滨孙通过自己的勤劳不断扩充圈地。三年半之后,他已经圈了五六块地,有了四十多只羊。鲁滨孙不光喝上了牛奶,还做出了奶油和酪干(129—130)。不光如此,鲁滨孙一身行头都是羊皮所制。除了肩上扛枪,鲁滨孙头戴山羊皮帽,身穿山羊皮外衣,腰束小羊皮宽皮带,头撑大羊皮伞(132—133)。
在岛上前15年,鲁滨孙除了打猎和采集葡萄之外,他开始种植庄稼、培植葡萄、圈地驯羊,从一名猎人成功地转变为农人和牧人。在这15年的时光里,鲁滨孙表示自己“没有偷懒”,凡是可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事情,他都不辞辛劳(135)。除了食物无忧,鲁滨孙还有一狗二猫一鹦鹉作陪。这一狗二猫一鹦鹉,鲁滨孙实际上有三个定位:一个是家庭成员,二是侍从,三是大臣。鹦鹉波尔仿佛“宠臣”,因为只有它能跟鲁滨孙说话(131)。这只鹦鹉是本岛原住民,但是鲁滨孙教它学会了说英语。鲁滨孙没有提他之前跟佐立用什么语言交流,也没有提他是否教佐立说英语。他只明确了,他教波尔和星期五说英语。鹦鹉与鲁滨孙的对话,有研究者认为是一种提醒,一种自我召唤。鹦鹉的对话提醒鲁滨孙记得自己是“有名有姓、有自我身份的社会人,而不是无差别、无个性的自然人,当然更不是一般的动物”①张德明:《笛福/克罗索的鹦鹉》,《书城》2016年第10期。。在岛生活15年里,鲁滨孙勤勤恳恳经营孤岛生活,食物供给富裕,日子无忧。他跟自己交流——祷告也是跟自己交流的一种方式,跟动物交流,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交流。在岛15年,鲁滨孙经常担心野兽或者野人来袭的危险。实际上,他既没有碰到黑非洲那样的凶猛野兽,也没有碰到凶残野人。他在岛上面对的都是攻击性不强的野兽。既没有黑非洲遇到的狮子和豹子,也没有从葡萄牙返回英国的陆路之旅所遇到的巨熊和狼群。
在岛前15 年生涯中,鲁滨孙可以说是一个轻奢猎人,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人际交往。虽然他有时候觉得命运已经眷顾够多,对人际交往也不奢求,但是鲁滨孙内心对于人的渴望从未停歇过。毕竟,只有人才是人的同伴。当然,也只有人才是人的敌人。
三、枪手鲁滨孙
在孤岛独自一人生活的时候,鲁滨孙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有人陪伴和说话,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害怕有人来袭。对于有人到访岛屿的可能性,鲁滨孙是既希望又害怕。鲁滨孙希望来客是朋友,害怕来客是敌人。所谓敌友,都只能从鲁滨孙的角度来划分,因为来访者并不知道鲁滨孙这个人在岛上的存在。无论是友是敌,来访者对鲁滨孙来说都是陌生人。对于陌生人的到访,鲁滨孙的恐惧与希望并存。两种情绪此消彼长,相互混杂。在敌友不明的情况下,恐惧通常占据优先地位。鲁滨孙曾经认为自己最大的痛苦是被人类社会所摒弃,与人世隔绝,因此盼望回到人群之中;但当直接面对可能的陌生来客之时,他又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
第15年的一天正午,鲁滨孙在岛屿另一头的沙滩上发现了一个人的陌生脚印。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看到赤脚脚印之后,鲁滨孙形容自己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或者“活见了鬼”,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其惊慌程度甚于因为受惊而逃进草窝的兔子或逃进地穴的狐狸(136)。总之,鲁滨孙因为发现陌生脚印而方寸大乱、恐怖至极。因此,鲁滨孙产生了各种幻觉,一夜无眠。他曾幻想,这个脚印可能是魔鬼作祟的结果,之后他又放弃了关于魔鬼的疑惧,并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一些更危险的生物,也就是对面大陆上的野人,乘船到海上闲游,或因急流或因逆风,偶然光临这个孤岛,然后又回到海上去了(137)。鲁滨孙这个结论既平常又惊人。惊人之处在于他把“野人”看作是比“魔鬼”更危险的生物。但这也是17 世纪末期欧洲殖民者把美洲部落看作是无可救药的“野蛮他者”的普遍看法①Dennis Todd,“Robinson Crusoe and Colonialism”,pp.142-156,at p.147.。这意味着,在鲁滨孙眼里,“野人”从来就不享有人的地位,他们只是危险的“非人”。
关于“野人”的危险性,鲁滨孙其实在发现陌生脚印之前就有所表达。在岛的时候,鲁滨孙始终希望回到大陆,回到有人烟的地方去。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这个“妄念”和“幻想”(109)。在如此幻想的时候,他完全忽略了可能落入野人之手的危险,也完全没有恐惧之心。鲁滨孙表示,这些野人“可能比非洲的狮子和老虎还要恶劣得多”。如果落入野人之手,要么被杀死,要么被吃掉。当然,这不是鲁滨孙第一次提到野人吃人的可能性。逃离萨利的过程中,鲁滨孙提到过,如果在黑人部族的海岸登岸,“必然会给野兽或是更无情的野人吃掉”(20)。那时,鲁滨孙也提到过,如果落入野人之手,“与落入狮子和老虎手里一样糟”(21)。那里,已经将“野人”——也就是黑人——与狮子和老虎相比拟。现在,鲁滨孙更进一步,认为“野人”的危险和恶劣程度要更甚于非洲的狮子和老虎。
鲁滨孙之所以认为野人比猛兽更恶劣,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野人吃人。当然,他也明确,关于加勒比海岸的人吃人,他是“听说”的。鲁滨孙进一步表示,即便加勒比人不是吃人的部族,不会把他吃掉,但也会把他杀死,“正如他们对付其他落到他们手里的欧洲人一样”(109—110)。这里,不知道鲁滨孙只是在传递一个时代现象,还是在表达一种个人信念。如果是前者,鲁滨孙传递了印第安人杀死欧洲人的可怕,却没有相应表达欧洲人杀死印第安人的可怕。如果是后者,星期五后来传达的信息表明,落入野人之手的欧洲人并不是必然会被杀死,至少落入星期五部族之手的17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并没有被杀死。而且,据鲁滨孙搭救的西班牙人说,他们和野人“相处得很好”(218)。但是,鲁滨孙完全无视这个信息并始终强调,落入野人之手如果不是比落入猛兽之手更为糟糕,至少是同样糟糕。更为明确地说,落入黑人部族之手跟落入狮子和老虎之口一样悲惨,落入加勒比部族之手则较此更为糟糕。鲁滨孙甚至将落入(加勒比)野人之手等同于“最残酷的死亡”(174)。在鲁滨孙的描述中,一般的“野人”被类比于野兽,甚至被看作是比猛兽以及魔鬼更为危险的生物。鲁滨孙的故事开启了恐惧被吞食的叙事传统,建构了“文本化的食人主义”,从而将“被殖民者归为与动物同类的野蛮人”,也确立了驯服食人他者的正当性①朱峰:《解构岛屿天堂神话——〈福〉对〈鲁滨孙漂流记〉的后殖民重写》,《文学理论前沿》2018年第1期。。
发现脚印的恐惧,主要是对陌生人的恐惧,尤其是对野人的恐惧,最终归为对残酷死亡的恐惧。经过了两个不眠之夜,鲁滨孙才冷静下来,推定这个岛屿虽然人迹罕至,但不是完全没有人迹(142)。鲁滨孙后来认识到,命运让他漂流到岛的一头,而临时登岸的野人通常到访岛的另一头。鲁滨孙这里首次点出了吃人部落的习惯:在打胜仗之后,把俘虏杀死吃掉(145,198)。由于在此登岸的人绝少在岸上过夜,鲁滨孙认为“安全“的办法是:一旦发现有野人登岸,他就躲起来(142)。从此,安全成了鲁滨孙的首要问题。如果前15年的孤岛生活主要是解决食物和生存问题,那么第15年之后的孤岛生活主要是解决安全问题。前者涉及鲁滨孙和岛上生物的关系问题,后者涉及鲁滨孙和其他陌生访客尤其是“野人”的关系问题。
在鲁滨孙的思想中,其他来访者首先被定位为“敌人”而不是朋友。为了确保安全,他加固住所外墙,架好枪支,已便在必要之时“在两分钟之内可以连开七枪”(142)。同时,鲁滨孙又在墙外空地上插了两万多棵杨柳树枝,因此可有足够的空间“看到敌人”(143)。对鲁滨孙来说,陌生到访者就是敌人。在孤岛生活15年之后,鲁滨孙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敌人”的到来做好各种防范准备。枪手鲁滨孙的枪口主要针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敌人”。
面对未知的野蛮敌人,鲁滨孙一直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应该隐蔽自己躲避敌人还是应该挺身而出对敌厮杀?有一些时候,他恨不得杀死那些可恨的野人,并且救出被俘的野人受害者;另一些时候,他又认为这些敌人并没有先来加害他,所以不应该去介入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其实,鲁滨孙犹豫的关键还在于,只要他没有把握全歼敌人,那么主动迎敌可能会让他走上毁灭之路(152)。鲁滨孙一方面加强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对于开枪更为小心谨慎,生怕被“敌人”听见枪声而陷入危险境地。鲁滨孙还是像以前一样,凡出门必带枪。但是,此后两年,他表示“没有开过一次枪”(147),甚至不敢钉钉子,不敢劈木头,不敢生火(155)。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以免被“敌人”发现。
“敌人”的具体形象就是加勒比海岸的吃人部族。鲁滨孙对这个“敌人”既恨又怕。恨是恨他们吃人,怕是怕自己被吃掉。鲁滨孙四次描述了“野人”的吃人场景,也展示了他的深恶痛绝。第一次,鲁滨孙已经在岛18 年。在岛的西南角见到人肉宴会之后的场景,鲁滨孙表示不忍再看“这种人性堕落的可怕景象”。面对吃人宴席的残骸,鲁滨孙的身体表现了强烈的恶心感,几乎晕倒。从心理影响来说,鲁滨孙在之后两年的时光里都因这“极端非人的、地狱般的残暴行为”而整天闷闷不乐(146)。通过展现野人的人肉宴席惨状,鲁滨孙将加勒比海岸的“野人”描述为“非人”,是“堕落的人”(146),是“野蛮的畜生”(147)。鲁滨孙庆幸自己降生在不同的世界里。鲁滨孙的敌人因此被刻画为“非人”,“堕落的人”和“野蛮的畜生”。第二次,鲁滨孙在岛第23 年。这一次,他远远看见“野蛮的人肉宴席”现场,并目送吃人的野人上船离去。随后,鲁滨孙携带枪支和大刀,来到海边现场。跟第一次不太一样,鲁滨孙这一次的当下反应是“立时怒不可遏”(162)。如果说第一次是不忍、恶心和郁闷,那么第二次的反应主要是愤怒。第一次是看见遗迹,第二次是远距离看见现场。第三次,则是近距离靠近现场并解救俘虏。这次是鲁滨孙在岛25 年,场景再现则是在解救星期五之后。击退野人之后一天,鲁滨孙和星期五来到人肉宴席的遗迹现场,目睹“惨绝人寰的景象”。此刻,鲁滨孙形容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冷了,心脏都停止了跳动”(183)。根据星期五的描述,这次一共有四个俘虏,包括星期五。被吃掉的是其他三个俘虏。这一次,鲁滨孙再次用“畜生”(183)来描述“野人”。由于星期五也有“吃人的天性”,鲁滨孙向他表明,如果胆敢再吃一口人肉,他就杀死星期五(184)。所以,星期五顺从鲁滨孙与“西方标准”的基础是死亡威胁①Christopher Loar,“How to Say Things with Gun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obinson Crusoe”,pp.1-20,p.15.。第四次,是鲁滨孙在岛第27年的时候。这一次,解救了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父亲。这一次,23个野人押着3个俘虏登岸开胜利宴会。鲁滨孙虽然从心里憎恶“这班畜生所要从事的残暴不仁的勾当”,但他也不是没有犹豫,是不是非要介入。这群野人并没有加害于他,也没有意图加害于他。鲁滨孙犹豫,觉得自己并没有理由去杀人流血。其实,鲁滨孙之所以会犹豫,主要还在于对人数多寡和实力对比的考虑。在这一点上,鲁滨孙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大屠杀保持了一定距离。西班牙人愤慨于吃人的现象,活活烧死很多人。通过杀人以禁止屠杀,西班牙人认为自己在与野蛮人作斗争②[法]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著,卢苏燕等译:《征服美洲:他人的问题》,第128 页。关于英国殖民者与葡西殖民者建构殖民所有权的不同道路,参见王旭峰:《〈鲁滨孙漂流记〉、殖民所有权与主权政治体》,《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
在解救星期五的过程中,鲁滨孙先用枪杆子打倒一个野人,又开枪结果了追赶星期五的另一个野人。野人的武器是刀剑和弓箭,是冷兵器。鲁滨孙的武器是枪,是热兵器。鲁滨孙知道弓箭是什么,野人则不知道枪支是什么。星期五也是一名野人,所以也全然不知道枪支的秘密。看到追赶自己的两个敌人都倒在地上,星期五被鲁滨孙的“枪声和火光”吓呆了,完全不明所以。星期五浑身发抖,不知道是不是也像他的两个敌人一样会被杀掉。翻查了敌人的尸体之后,星期五也还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这时,鲁滨孙还不想向星期五透露枪支的秘密。当鲁滨孙之后带着星期五去打山羊的时候,他再次被鲁滨孙的枪声吓得浑身发抖,差一点瘫在地上。星期五吓得查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受了伤,以为鲁滨孙要杀他,所以跪下来请求鲁滨孙不要杀他(186—187)。然后,鲁滨孙又当着他的面打死一只鹦鹉。刘禾认为,鲁滨孙射杀鹦鹉既是“对杀死星期五的模仿”,也是预示如果不服从同样会像鹦鹉那样被杀死的结果③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第17页。。星期五无法理解鹦鹉是怎么被打死的,惊愕地以为枪里面藏着“奇妙的东西,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死亡和毁灭”。的确,如鲁滨孙所说,他和他的枪对于星期五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之后几天,星期五不仅不敢触碰鲁滨孙的枪,而且经常唠唠叨叨地对着枪说话,祈求这枪“不要杀害他”(187)。那时,鲁滨孙刻意趁星期五不在身边的时候装上弹药,保留着枪支的神秘性。等到星期五和鲁滨孙进一步熟悉,并且可以用英语交流的时候,鲁滨孙才向星期五透露了“火药和子弹”的秘密,并且教他怎样开枪(197)。
在解救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父亲的过程中,枪支也起到了神一样的作用。鲁滨孙一直在摇摆和犹豫,是否要出手营救。在鲁滨孙得知俘虏之中有欧洲白人的时候,他才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枪。在交战过程中,鲁滨孙对星期五下达指令:“凭上帝的名义,开枪!”只有在解救欧洲白人的时候,鲁滨孙才以上帝的名义发出开枪的命令。这次战斗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一边是鲁滨孙和星期五,中间加上他们搭救的西班牙人;另一边是21名野人。最后的战果是,鲁滨孙一方没有伤亡,野人一方则被杀死17名,逃走4名。在追赶逃兵的过程中,鲁滨孙发现独木舟里还躺着一个没死的俘虏,这名俘虏竟然是星期五的父亲(211—212)。
稍作安顿之后,鲁滨孙叫星期五问他父亲,那四个坐独木船逃跑的野人会不会带着大队人马卷土重来。星期五的父亲给出了两种可能结果。第一种结果,那艘小船逃不过晚上的大风,所以要么被海水淹死,要么吹到其他海岸而被当地野人吃掉。第二种结果,假设他们平安回到自己的海岸,由于被“枪声和火光”吓得半死,他们会告诉同族人,其他人不是被人打死的,而是被“霹雳和闪电”殛死的;他们会把鲁滨孙和星期五当作“天神或复仇之神”,因为他俩通过“射火”和“放雷”就能远距离杀人。根据鲁滨孙的讲述,那四个野人从风浪里逃出生天,但的确再也不敢到这个“魔岛”上来,因为害怕会“被天神用火烧死”(217)。
鲁滨孙的枪,星期五曾奉若神明,星期五的敌族也视枪声和火光为天神在打雷和射火。在信仰方面,鲁滨孙并不能完全解开星期五的疑惑。但是,鲁滨孙的枪直接让星期五拜服在地、完全顺从。正如鲁滨孙所说,他降生于另外一个世界。决定两个世界位置的是武器而不是信仰。枪火和枪声决定了鲁滨孙在摩洛哥的奴隶地位,也决定了鲁滨孙和星期五的主仆地位。
四、对手鲁滨孙
鲁滨孙落难荒岛的时候,他称之为绝望岛。遭遇鲁滨孙和星期五枪声与火光的部族视此岛屿为魔岛。不过,英国船只的叛变水手也认为他们来到了一个“魔岛”(240)。星期五的敌族认为魔岛是因为岛上有隔空杀人的“天神”。英国水手认为,这岛上要么有人居住要么有妖怪。他们不信神,但信邪。鲁滨孙派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父亲回部族之后第八天,一艘英国船出乎意料地抵岸。在岛28 个年头,鲁滨孙之前从未见过一艘英国船靠岸,因为这一带并不是英国人的贸易要道(224)。忽然间看到一艘英国船,鲁滨孙心情复杂,既衷心喜悦又不免疑虑。鲁滨孙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还是因为不知道来客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224)。一个人越期待什么,就越要保持警惕。福克斯认为,鲁滨孙突然看到陌生脚印的恐惧与慌乱其实是“一个殖民者的警惕”。面对一艘英国船只的突然出现,鲁滨孙的犹疑和忐忑无疑也是这种警惕的表现。这种警惕一方面表现了一个孤独者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成就了欧洲人对广袤土地的征服①[英]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著,李小均译:《英雄、情人、势利鬼、恶人:28 个英国小说人物的秘密生活》,(Faulks on Fiction),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荒岛生涯中,鲁滨孙一共两次见过欧洲的船只。在岛第24 年的5 月16 日夜里,鲁滨孙曾经与一艘遇险的西班牙船有过信号交流。那一次,鲁滨孙无比渴望那艘船能有人逃出生天,即便只有一个人。这种心态完全不同于他对待野人独木舟登岸的防范心理,也不同于后来他见到英国船只的疑惧心理。见到西班牙船之时,鲁滨孙正处在两次见到野人人肉宴席之后的“疑虑与焦急”之中(162)。那天夜里,鲁滨孙正在阅读圣经,忽然听到海上一声枪响。鲁滨孙迅速跑到山顶,然后又见火光一闪,并在半分钟后听见第二声枪响。鲁滨孙马上做出判断,认为一定是船只遇险而鸣枪求救。虽然鲁滨孙并不能判断是哪里来的船只,但是他从鸣枪求救的信号里察觉到不是来自野蛮敌人而是来自朋友。这个时候,鲁滨孙没有任何疑虑。鲁滨孙收集干柴,堆成一大堆,并且点燃柴堆。风很大,火很旺。只要海上有船,绝对能看得见火光。在他烧火之后,接着又传来几声枪响。鲁滨孙的火烧了一整夜,一直到天亮(163—164)。鲁滨孙烧火,是希望船上的人能看见,能靠近。即便鲁滨孙并没有办法帮到船上的人,也许船上的人可以因此帮助鲁滨孙离开荒岛。
天亮之后,鲁滨孙远远望见一艘下了锚的大船一直停在远处不动。跑到岛的南部之后,鲁滨孙就看到那条在昨夜触礁失事的大船(164)。鲁滨孙猜测,大船上的人触礁之后,必然设法放小船往岸上逃,尤其是看见山上的火光之后。但是风浪太大,也可能把他们卷走了。看到失事船只的景象,鲁滨孙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嘤嘤求友的强烈要求”,口中呼唤着哪怕只有一个人逃出性命;此时此刻,鲁滨孙满怀渴望能有“一个伴侣”“一个同类的人”可以说话交谈。船只失事的景象触碰到鲁滨孙的多年孤寂之心。他表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有人往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165—166)。这一次,鲁滨孙从来没有表达过一丁点疑虑,船上的人会不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鲁滨孙所说的伴侣和同类的人,显然不是野人,而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基督徒。无论黑人和印第安人,都不是鲁滨孙眼中的同类。星期五的到来虽然帮助鲁滨孙摆脱了孤独,但星期五从来都不是朋友。在鲁滨孙眼里,星期五只是一个可人的同伴,一个忠实的仆人。如福克斯指出,鲁滨孙“总是把‘星期五’当成仆人,当成达到目的之手段”①[英]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著,李小均译:《英雄、情人、势利鬼、恶人:28 个英国小说人物的秘密生活》,第19页。。来自欧洲的白人,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才是鲁滨孙所期待“哪怕只有一个”的朋友。在这种强烈渴望中,鲁滨孙实际上非常明确地表达:“如果有一位基督徒和我交谈交谈,实在是一种无上的安慰。”(166)可惜这次船只失事,鲁滨孙只在海边见到一具青年人的尸体,在船上见到两个淹死的人。根据船只构造,鲁滨孙确认那是一条西班牙船,并且推测那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里约拉巴拉他出发开往哈瓦那而后再往西班牙。除了一条狗,鲁滨孙在船上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生物”(168—169)。鲁滨孙对于“朋友”到访的期待落空,重归孤寂。
西班牙船的意外失事之时,鲁滨孙强烈期待“朋友”的到来;英国船的意外靠岸之时,鲁滨孙则心生警惕,不确定是友是敌。一只小船靠岸之后,鲁滨孙看出来者共有十一人,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其中三人被绑押送。显然,英国人押解着英国人。因此,星期五说,你们英国人也吃俘虏。鲁滨孙也不明就里,但明确俘虏可能会被杀掉,但一定不会被吃掉(225—226)。由于是同胞相残,鲁滨孙的心情类于看到“野人”人肉宴席的心情。眼看着“三个可怜人”可能被杀,他的内心凌乱乃至“发抖”,甚至“浑身的血都冷了”(226)。鲁滨孙之前见到野人杀人吃人的场景,他也表示过发抖和血冷。但是,相同的身体反应不一定来自相同的心理理由。之前对“野人”的愤怒是因为他们吃人,现在对英国人的愤怒则是出于同胞相残。鲁滨孙没有把同胞相残的英国人称作非人的“畜生”,他一直很冷静地观察变化,等待时机。这个时候,鲁滨孙明确表示,他的作战准备比以前更加小心,因为他要应付的是“一种和从前不同的敌人”(228)。鲁滨孙没有详细解释这种敌人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简要推理一下两点不同之处。第一,眼前的敌人不是他一直担忧的两种危险存在:野兽或野人。这次是他的英国同胞。第二,既然是英国水手,他们也一定拥有枪支和使用枪支的能力。就鲁滨孙而言,既然对手是英国人,鲁滨孙可以在暗处偷听,不需要猜测就可以直接获取情报,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断。鲁滨孙这次碰到的是真正平等的对手,是同样持有枪支的对手。
水手“顾前不顾后”(227)的特征和英国人的任性随意给了鲁滨孙悄悄接近三个俘虏的机会。三个“可怜人”一开始也跟“野人”一样惊惶地认为鲁滨孙是从天上来的使者(228—229)。在这个方面,鲁滨孙的态度跟之前不一样。对于野人部族,鲁滨孙宁可他们认为他和星期五是神一样的存在。对于三个英国人,他并不愿意也没有必要装神弄鬼,而是直接挑明自己也是英国人,并且表示愿意带着仆人、武器和军火搭救他们。当然,搭救的根本前提是要带他离开绝望岛。经过简单交流,鲁滨孙得知,这三个可怜人是遭到反叛的船长、大副和一名旅客。鲁滨孙称那些反叛的英国人为三个可怜人的“敌人”和“暴徒”(229)。在这一点上,鲁滨孙的态度也和之前对待野人的态度不同。野人杀人吃人,鲁滨孙直斥为畜生,是非人与人的区分;水手暴动杀人,鲁滨孙视之为暴徒,是非法与合法的差别。一个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另一个则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一个是文明标准,也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另一个则是法律标准,也就是文明世界内部的法律事务。面对野蛮人,鲁滨孙自认为是文明人,要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教化。面对同样来自文明世界的英国同胞,鲁滨孙只需要击败并收服暴徒,甚至最终将恶贯满盈的暴徒留在岛上,以免受到法律制裁。鲁滨孙一边以基督教道德严厉谴责“野人”的“非人”行径,另一边则以法外开恩的手段宽恕触犯法律的英国暴徒。在鲁滨孙眼中,野人需要征服,暴徒需要击败。
鲁滨孙出手搭救被掳的船长,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岛期间不能侵犯他的主权,必须完全接受他的管制;二是收复大船之后,需将他和他的人免费带回英国(230)。被俘船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鲁滨孙的条件。为了迷惑敌人,鲁滨孙以“总督”和“司令”身份分配武器火药,统筹指挥队伍,决定战斗方式。经过一番虚虚实实,斗智斗勇,鲁滨孙率队战胜小船的反叛者,又令船长带队夺取大船。船长按照和鲁滨孙的约定鸣枪七响,表明成功夺船。岸上的鲁滨孙司令才安心睡去。等鲁滨孙再度被枪声唤醒的时候,船长已经出现在眼前。船长搂着鲁滨孙,除了称呼他为“总督”之外,紧接着更为亲切地称呼他为“亲爱的朋友”和“救命恩人”(246)。鲁滨孙在惊喜中昏厥过去,待他再度醒来,也主动拥抱了船长,并称船长是救他出险的“救命恩人”,但是鲁滨孙并没有像船长称呼他那样还以“亲爱的朋友”。
西班牙船遇险之时,鲁滨孙尚未解救任何人,只希望自己得到解救。英国船靠岸之时,鲁滨孙已经解救了三个人。每一次解救都能为他带来助益。第一次行动解救了星期五,作为自己的仆人。作为一个野人,经过枪支立威、语言教育和宗教灌输,星期五学会了说英语,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鲁滨孙的仆人和帮手。作为儿子,星期五不得不告别父亲,告别家乡,跟随主人鲁滨孙浪迹天涯。鲁滨孙的第二次解救行动,首要目标其实是落入野人之手的西班牙人,但同时也意外解救了星期五的父亲。解救星期五是为了自己逃出孤岛找到帮手;解救西班牙人一方面是出于作为欧洲白人和基督徒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也因此增加了离开绝望岛的希望。星期五父亲得救只是解救西班牙人行动的附加结果。这两次解救行动,枪声和火光都起着神力效果和压倒作用。解救英国船长,枪支只是人的武器,关键在于以少胜多的谋划。对野人来说,带枪的鲁滨孙是神,杀人于无形之中。对英国水手来说,鲁滨孙是总督和司令官,战斗胜负定输赢。鲁滨孙与英国叛变水手之间的战斗,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是平等对手之间的战斗:水手对水手,英国人对英国人,基督徒对基督徒。
结 语
英国青年鲁滨孙主动逃离父母,立志出海浪游。从伦敦到几内亚的航行,鲁滨孙如愿成为水手,也同时成为商人。成为水手的同时,鲁滨孙也成为一名枪手。从伦敦到几内亚的再次航行,船只被土耳其海盗所劫,鲁滨孙沦为奴隶。在萨利的被掳时光里,鲁滨孙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渔夫。去西非的贸易生涯和在北非的为奴时光,鲁滨孙没有提到任何文明与野蛮的矛盾问题。鲁滨孙完全忽略英国与摩洛哥之间的信仰差异和优劣问题,只是叙述了炮火强弱和斗争胜负决定了主仆地位。从北非逃离南下黑非洲,鲁滨孙开始表达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开始担忧丧生于野兽或者野人之手。落难荒岛之后,鲁滨孙在前15 年的生活中,主要是考虑在岛上孤身一人怎样存活。这时,他是一个枪手猎人,也同时成为一位农夫、牧人和匠人。在岛上第15年之后,猎人鲁滨孙转变为枪手鲁滨孙,最为主要的担心野人来袭的安全问题。因此,生活的重心便是如何防范和击退野人的意外到来。鲁滨孙其实可以采取完全的自我隐蔽策略。但是,离开荒岛回归大陆的强烈渴望使得鲁滨孙三次主动出击,一次放火暴露。前两次主动出击所面对的敌人都是野人。从野人手里解救出来的,有野人,也有西班牙人。解救野人是为了给自己找帮手。解救西班牙人是给了自己找希望。其实,目标都是为了逃离孤岛。第三次主动出击所面对的是不一样的敌人。这个敌人与之前遭遇海盗的战斗模式类似,是一次身份对等的战斗。不同之处在于,几内亚航行的海盗遭遇战纯粹由火炮和武力决定。出击英国叛变水手则需要以少胜多的筹划和算计。出击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出逃孤岛、回归英国。这一次战斗是鲁滨孙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战斗。
成为枪手是水手鲁滨孙的自我养成之路;猎手鲁滨孙与飞禽走兽战斗,是人与兽的斗争关系;枪手鲁滨孙与野人战斗,是人与“非人”之间的斗争关系;对手鲁滨孙与非法同胞战斗,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斗争。每一场战斗,鲁滨孙都能心想事成,取得胜利。有枪在手,鲁滨孙可以战胜野兽、战胜野人、战胜同为基督徒的欧洲白人。因此,他几乎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①[英]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著,李小均译:《英雄、情人、势利鬼、恶人:28 个英国小说人物的秘密生活》,第4页。,而且从英雄变成了神话②Ian Watt,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Faust,Don Quixote,Don Juan,Robinson Crusoe,p.170ff',p.171.。战无不胜的鲁滨孙似乎是笛福送给18世纪英国的一个希望和隐喻。鲁滨孙的隐喻也说明,英国人征服野兽统治自然,征服野人建立殖民地,征服叛乱恢复秩序。瓦特总结,笛福创造的鲁滨孙形象不仅贡献了个人主义的基础,而且反映了英国特性的德行与恶行。瓦特还直接引用了乔伊斯(James Joyce)在1912年关于笛福的演讲内容来说明英国特征的德性与恶行。乔伊斯认为,“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就在鲁滨孙这个形象之中:“男子汉的独立、无意识的残酷、锲而不舍、迟缓但有效的智力、性冷淡、实际而巧妙平衡的宗教感、工于算计的缄默。”③Ian Watt,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Faust,Don Quixote,Don Juan,Robinson Crusoe,p.170ff',p.171.其实,所有这些特征背后都站着手持枪支的鲁滨孙。洛尔和刘禾都看到了这个枪手身份对于奠定殖民主权的根本作用。洛尔的论证存在着分离鲁滨孙和他的枪支的倾向。洛尔倾向于认为,鲁滨孙这个角色自身否定暴力,其内心通过文明教化和建立友谊来达成殖民主权。其实,鲁滨孙对于野蛮暴力的否定只是一种口头上的修辞。水手鲁滨孙完全具有枪手的自觉性,也对枪支的奠基作用具有明确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塑造了水手鲁滨孙的自我,也确立了他和动物、野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
卡尔维诺指出,《鲁滨孙飘流记》被认为是“一部颂扬商业和工业品德的圣经,一部赞美自食其力的史诗”④[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其实,它更是一部通过枪支占有土地、征服异族和道德驯化的作品。应对自然,鲁滨孙要有伞;应对生物,鲁滨孙要有枪。没有枪支,鲁滨孙无法击杀野兽;没有枪支,鲁滨孙成不了野人心中的神灵;没有枪支,鲁滨孙无以对付叛乱的英国水手。鲁滨孙的故事是一个英国人的奋斗故事,是一个欧洲白人的殖民故事,是一个基督徒的教诲故事。所有这些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正在未雨绸缪或者暗中瞄准的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