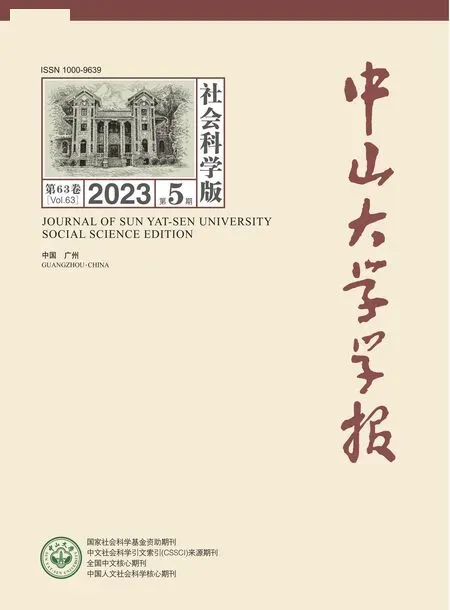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
2024-01-03刘增光
刘增光
圣人观念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侧重对于玄学、理学圣人观念的讨论,对于汉代经学内部圣人观的丰富性多所忽视,而作为两汉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在这方面的贡献更是罕少为人关注。但深受公羊学影响的郑玄在其《论语注》及相关著述中对于孔子形象的塑造颇富创造性:第一,郑玄强调孔子的圣性乃是天授,不能通过学习达到,体现出圣凡绝异的圣人观;第二,孔子谦卑以教人,必须隐藏圣性,隐圣同凡也就成为圣人在世的生活方式;第三,凡人不知圣人,唯有圣人乃能知圣人,孔子乐尧舜之道正是圣圣相知的体现。而这三个方面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孔子形象:圣性天授意味着只有圣人方能制礼作乐,谦卑以教人是说圣人才是礼法、秩序的开端者、奠基者,唯圣知圣则是一种重在外王制度的道统观念。本文所发掘的这三方面都尚未被学界所谈及。
综合言之,在郑玄看来,孔子晚年制作《春秋》是效法周公制礼作乐的行为,而他通过孔子形象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便是圣人制法与王者行道的呼应与统一。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郑玄《论语注》及其对孔子圣人形象的塑造在魏晋六朝时期有重要影响,但整体来看,从汉代关于圣人制法的讨论,到魏晋玄学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辩,再到宋明理学关于学以至圣的不断肯定,《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呈现出政治化色彩不断被稀释和消解的趋势,《论语》也就从侧重呈现孔子之政治境遇与制法行为的典籍演变为宋明时期用于修身成德的教化之书。郑玄第一次将作为制法者的孔子形象灌注进对于《论语》的解释中,只有细究其《论语注》的思想世界,方能明晰《论语》文本以及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对中国哲学史脉络中的圣人观念才能有完整的把握。
一、谦卑以诱人的教化者
《论语·子罕》篇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吾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焉。”郑玄注:“言我无知者,诱人也……有鄙诞之人,问事于我,空空如,我语之……诱人者,必卑之,渐以进之也。”①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5,104,105,106页。与“卑以诱人”相应,郑玄一再提示我们,《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个以谦德自处的人。同篇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郑注:“闻人美之,承之以谦……执御者,欲名六艺之亵事。”②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5,104,105,106页。孔子之博大与谦卑恰为一体。此处“亵事”一语为郑注所常用,如同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章,郑注亦云:“问夫子圣人得大道,于亵事何其多能,多能者则必不圣……言天纵大圣人之心,既使之圣,又使之多所能……鄙事,家人之亵事……试,用也。艺,伎艺也。言我少不见用,故多伎艺也。”③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5,104,105,106页。在郑玄看来,孔子本人即是“圣性”与“多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注文“多能者则必不圣”寓意着圣性和技能是相反的,因为圣性是天授或天纵的,而技能是人为或通过后天习得的④这一点,在后世即发展为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圣人观念的分歧,究竟是通过格物致知成为圣人,还是发明本心。。也就是说,孔子之为圣并非由鄙事而圣人,由伎艺而道德。他所持的正是“圣不可学而至”的观念。就圣凡之别而言,凡人能此则不能彼,多能则非圣,而孔子恰恰是既多能伎艺又为得大道之圣人。《礼记·学记》言“大道不器”,郑玄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⑤基本可以断定,这也正是郑玄对《论语》“君子不器”的理解。比如邢昺《孝经注疏》在注解《广扬名章》时就说:“此依郑注也,《论语》云:‘君子不器。’言无所不施。”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页。孔颖达申之,认为其意是说“圣人之道弘大,无所不施”,也即是《论语》“君子不器”所蕴之意⑥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1页。。郑玄对于孔子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区分“才艺”与“大道”、“器”与“道”而实现的,而这一区分,在《论语》中则是通过构造或阐释孔子与弟子之差别而实现。相对于圣人来说,其他人都是受教者,而圣人之弟子无疑正是受教者的典范。故以圣人之弟子来衬托圣人,比如《子罕》篇的另外一章: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郑注:忽,谓如恍之惚之惚。诱,进也。颜渊初学于孔子,其道若卑,将可及,若濡,将可入;其后日高而坚,瞻之堂堂在我目前,忽焉复在我后,言其广大而近。夫子之容貌,循循然,善于教进人,一则博我以文章,一则约我以礼法,乃使我蹔欲罢倦,而心不能。竭,尽也。立,谓立言也。此言圣人不可及。卓尔,绝望之辞也。既,已也。我学才力已尽矣,虽欲复进,犹登天之无阶。⑦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5,104,105,106页。
这一章的意涵极为丰富。第一,“恍之惚之”⑧王素认为此处“恍之惚之”的第一个“之”字为衍文。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12页。本《老子》形容道之词语,“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以“恍惚”作解正可烘托孔子与凡人之异。以“恍惚”说明天或者天道,乃是汉人旧说,并非郑玄所创,如《淮南子·原道训》言“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惚兮恍兮,不可为象”。而汉代今文经学家解释《尚书》中的“禋于六宗”也说:“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时,居中央,恍惚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页。东汉王充便在批判西汉经学时提到当时流行的“神恍惚无形”“天地之间,恍惚无形,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⑩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3、285页。等观念。可见郑玄沿循了这一传统而以恍惚无形无象来说明孔子之如天如神。毕竟郑玄注文“圣人不可及”正是出自《论语·子张》篇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后来的何晏注解《子罕》此章便云:“言忽怳不可为形像也。”①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7,388页。显然即是承郑玄而来。而上文所引郑玄以道、器差异说明“君子不器”正与此“无形”之说相应,其背后显露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影响。观皇侃《论语义疏》可推知魏晋时人以《易传》解《论语》来说明孔子之圣,当受郑玄影响。第二,郑玄以孔子之道为可入而又高坚,广大而又卑近,此并非无意之言,而是本于《中庸》子思对孔子形象的描述“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正如前文所述孔子博大而又多能。而《中庸》在郑玄看来,是“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22,1001,1460页。。易言之,《中庸》是更早的关于孔子的“传记”,远早于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且既然是由孔子之孙所作,那么也更为可靠,因此郑玄以《中庸》参释《论语》。第三,“博我以文章”与“约我以礼法”二语互文见义,“文章”指六艺,也即六经;实则礼亦是文,对六经的学习要以礼法为归宿,以“周文”为核心。郑注《礼记·大传》即云:“文章,礼法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22,1001,1460页。礼法为文章中最重要者。第四,依郑注,“所立卓尔”是说颜渊无法用言语描述圣人之道,据此,“夫子之容貌,循循然,善于教进人”和“圣人不可及”恰构成了孔子圣人形象之一体两面。《述而》篇的另外两章:“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郑注:“圣人知道广大,弟子学之不能及,以为有所怀挟要术。”④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80,78,106、59,78页。“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郑注:“吾岂敢者,不敢自比方古之仁贤也……孔子之行正尔,弟子不学及,况于圣人乎?”⑤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80,78,106、59,78页。“孔子之行正尔”正是对孔子“无隐”的印证。可见,不论是颜渊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还是公西华之“不能学”(《述而》),都汇归于子贡的那句话——“圣人不可及”(《子张》)。正因圣人不可及,才会遭到弟子、时人的不理解甚至误解。第五,“才力已尽”而“登天无阶”,意味着才力和大道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所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公冶长》),并不是因为孔子有所隐,而是在于弟子才力之限。
既然说“学之不能及”,那么,孔子之好学本身即是卑以诱人的表征。《述而》“五十以学《易》”章郑注谓:“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⑥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80,78,106、59,78页。这也正是在以同篇孔子自道的“学而不厌”“为之不厌”(《述而》)作解。故而孔子赞赏“蹔欲罢倦,而心不能”的颜渊,而批评“豫止不前”的冉有⑦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80,78,106、59,78页。。但是,好学仅仅是圣人的一面,是圣人劝进弟子和他人的表征,很可能并非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根本。作为圣人之本质的“圣性”是天生的,故《述而》“天生德于予”郑注:“天生德于予者,谓授我以圣性,欲使我制作法度。”⑧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80,78,106、59,78页。这一点继承了董仲舒以来的圣人受命说。郑玄《中庸》注亦云:“圣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非得其时不出政教。”此天生之德也即《中庸》与天道合一的“至诚”,故郑注谓:“性至诚,谓孔子也。”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22,1001,1460页。这也意味着,在郑玄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天生之德必然关联着政教层面的制作礼法,“圣人以立法度为大事”⑩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36页。这样作解是郑玄注经的一个特点,如《大雅·既醉》“君子万年,景命有仆”,郑注:“成王女既有万年之寿,天之大命又附着于女,谓使为政教也。”细绎郑意,他必赋予“天生德”“大命”具体的内涵,非如此,则无法解释为何是天生德于“予”而非他人,以及附着于成王的命为何是“大”。见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80页。。循此以进,郑玄对圣凡异同的认识,便与礼直接相关。此点正如深受郑玄影响的皇侃所道:“孔子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1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7,388页。
二、“隐圣同凡”的在世者与“乐尧舜之道”的制作者
皇侃在《论语义疏》中也与郑玄类似,通过说明颜回与孔子之差别来凸显孔子之圣,这与后世理学的孔颜并称差异显著,《论语义疏》对“隐圣同凡”①皇侃:《论语义疏》,第25页。的孔子形象的塑造也正是源于郑玄。孔子谦卑以教化,圣人之道的“恍之惚之”必然要落实在具体的德行、礼仪之“文”上来表现,但圣人教化并不仅仅限于师徒之间,更重要的是教化世人,用郑玄的话说,是“凡人”,惟此方可呈现教化的普遍性。而圣人也是人,只不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圣人必然要在凡世中出现与生活,必然要即凡而圣。在凡世中生活,必然不能采取退隐——远离凡民遁入山林的方式,故而无非两种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要么出仕从政,要么以教导民。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虽周游不息,却不见用于世,因此圣人在凡世中生活的方式便主要是行教。由此,圣与教就达成了必然而又无奈的统一,即“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的无奈。
《论语》中对孔子凡世生活的描述最为细致入微的便是《乡党》篇,此篇开首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下略)”,所述正是孔子日常生活中与人交接的言行举止。而这些言行举止,并不能显示孔子与他人的截然不同,最多体现孔子知礼,或言行举止较他人更符合礼仪,这正是孔子对生活世界的介入。人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礼仪世界,与邻里乡党之人交接,与君交接,与朝廷之人交接等。《乡党》篇所显示的正是凡世生活中的孔子,披着礼仪外衣的孔子。对于开篇文字郑玄注云:“恂恂,恭顺貌也。似不能言者,所以接凡人。”②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18,105页。这句话显得非常突兀,如平地惊雷,恰似子贡所言“天纵之将圣也”。天纵圣人,降临凡世,走入人间。而并非巧合的是,此处对“恂恂如也”的解释正如他对《子罕》篇“夫子循循然”的解释一样,皆是就夫子之容貌而言,“循循然”是夫子善于诱进凡人,而“恂恂如也”是夫子善于接凡人,不论何者,都是圣与凡的交接③不妨比较朱熹的解释:“恂恂,信实之貌。似不能言者,谦卑逊顺。不以贤知先人也。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辞气如此。”孔子之所以谦逊,是因为在乡党中孔子之交接者基本都是自己的父兄辈,而不是与“凡人”交接。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页。。“恂恂如也”又如同《子罕》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的描述,郑注谓“言我无知者,诱人也”④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18,105页。。孔子“不能言”,又“无知”,皆是隐其圣性,以凡人之面貌示人,故郑玄指出,恂恂如、循循然是夫子之容貌,而非夫子之内心,夫子之内心是圣人心性。郑意已经暗含了后世关于孔子形象的一种理解——圣凡合一意味着其内为圣、外为凡。孔子博学,并非无知,并非不能言,为政即需要贤知,教化则需要能言。而《乡党》篇开首就奠定了这一篇的解释基调:《乡党》全篇的主旨即是圣人如何接引凡人。《乡党》所述除却最后的“翔而后集”一章,其余皆为孔子行礼守礼之事,是一个礼仪生活的世界。一个守礼行礼的世界就是凡人的生活世界,故孔子之守礼行礼,即是圣人以礼仪接引世人。礼仪即是教,孔子之守礼行礼正是对世人之教。但是,即使这样,世人亦多有不守礼行礼者,此即“礼坏乐崩”⑤这样的例证在《论语》中很多,比如对于他人之“事君尽礼”反以为“谄也”(《八佾》);又如孔子对子贡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依此,礼仪虽是圣人交接凡人之道,亦是凡人生活必然要遵循之道,但是凡人仍不能遵循,这就又凸显了圣人的不合时宜、不容于世。
这一隐圣同凡的形象,正是《中庸》所言“素位而行”,此正是标以“子曰”的夫子自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人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以父子、君臣、长幼、朋友等人伦关系为经纬的世界。郑注谓:“圣人而曰我未能,明人当勉之无已。”“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圣人之行,实过于人,‘有余不敢尽’,常为人法,从礼也。”孔疏申发郑意,明确指出:“(夫子)恐人未能行之。夫子,圣人,圣人犹曰我未能行,凡人当勉之无己。”“己之才行有余,于人常持谦退,不敢尽其才行以过于人。”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30—1432页。《中庸》这段话恰似《论语·宪问》之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虽然此章郑注已佚,但是“夫子自道”岂不正是郑玄“圣人而曰我未能,明人当勉之无已”及“圣人之行,实过于人”的佐证?无怪乎皇侃疏云:“孔子云无,而实有也。”②皇侃:《论语义疏》,第375页。而“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正是《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另一种表达。圣人超越凡人,但是圣人却“常持谦退”“庸德庸言”,正是隐圣同凡,降格以处。“常为人法,从礼也”正意味着,礼就是圣人的外衣,遵从人人皆遵从的礼,则圣人便与凡人处在同一个礼仪共同体中,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可见,郑玄对圣人的认识与玄学不同,何晏认为圣人无情,王弼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③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0页。,而郑玄对圣凡同异的辨析,则是从教化维度强调圣凡同遵礼仪,共在于礼仪共同体中。
圣凡之别,在郑玄这里已然成为极重要的显题。郑玄对弟子“学之不能及”的强调突出了圣凡之间的巨大差别,圣人不可能通过学来达到。据此,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以及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学以至圣的理念,并非郑玄所能认同。据郑意,“圣性”是“天授”的④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页。,或者如《论语·述而》和《中庸》中一再出现的“生而知之”。《乡党》“首”章郑注所言“接引凡人”云云,其实已明示:圣人并非经过学习或践履凡人的那些礼仪行为“后”才成为圣人,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圣人——从《乡党》的开端处就是圣人。换言之,圣人之接引凡人,就意味着凡人生活所依循的礼仪秩序恰恰是出自圣人,礼乐文明即发端自圣人。因此,毫无疑问,《述而》所载孔子自道的“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只是孔子的谦词,是孔子对圣性的隐藏。
而圣人之隐却可从两重角度分析:一是圣人要卑以诱人,以劝进世人向善,这是发自圣人的主动的隐。更重要的则是第二重原因,即凡人不能识圣人。圣人既然要诱人接人,便须与凡人同处此人伦礼仪的共同体中,以庸常平凡之形象示人,在此意义上,圣人和凡人并无不同,故当凡人见到孔子时,其实并不知与自己同处的孔子就是“圣人”;即使见到了,也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圣人,甚至会认为守礼的圣人是迂腐的“异类”,圣人的出现和在场很可能是对凡人生活的一种“打扰”。此实为圣人在世必然会遭遇的吊诡处境。子思《五行篇》引《诗经·召南·草虫》载:“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不仁不圣,‘未见君子,忧心不能忡忡;既见君子,心不能降’。”⑤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01 页。这样的叙述亦见于被后世认为子思所作的《礼记·缁衣》中,可见子思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圣人问题有深入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注解《缁衣》“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时道及人们在亲近有德者时的一种常态:“言水,人所沐浴自洁清者,至于深渊、洪波,所当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亵慢而无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时学其近者、小者以从人事,自以为可,则侮狎之,至于先王大道,性与天命,则遂扦格不入,迷惑无闻,如溺于大水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511页)人一方面亲近有德者,另一方面又往往生发亵慢之心,不能怀有敬畏之心,因此也就半途而废,不能学以至道。这段话所描述的正是凡人不能知君子或圣人。最令人担忧的是,很可能凡人根本就没有想要见到君子或圣人的意图和动力。此即凡人的怠惰和凡世的沉沦,就连孔子弟子都会心生懈怠或疑惑,又何况未曾与孔子觌面的人呢!《学而》开首言“人不知而不愠”,孔子深知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理解的常态,尤其是在礼崩乐坏的无道之世!
但是,圣人之觉世牖民,正是要“与人为善”①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与人为善之要,则在于见诸行事,与人共行之。天与万物共事,圣人与凡民亦共事,共事则共同在世。此“与”即《微子》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之“与”。道家的至人、神人是“无待”的、“无与”的,而儒家的圣人不会那样地“无待”“绝缘”,抑或是“独化”。“与”就是有待、有缘,就是要与人俱化。
但在郑玄思想中,与圣人不被凡人所知相应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是:只有圣人方能知圣人。这一点,郑玄在注《中庸》时有明确表达: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郑注: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传》曰:“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郑注:“至诚”,性至诚,谓孔子也。“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郑注:言唯圣人乃能知圣人也。《春秋传》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459—1461页。按,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一般认为,自董仲舒开始,先儒将《春秋》视为孔子素王制作之典。郑玄继承了公羊学的这一义理,并以《春秋公羊传》末尾文字发明《中庸》,复调式地强调了“乐乎尧舜之知君子”这一主旨;且依照郑玄的理解,子思《中庸》实为公羊学这一义理的源头,子思本人就是在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中庸》这段文字与《论语·宪问》所载孔子自言“莫我知也夫……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相呼应,“莫我知也夫”即是“凡人不知”,凡人不知圣人,也就不可能效法圣人以成为圣人。依郑意,孔子圣性天授,天之知孔子有着必然性。“唯圣人乃能知圣人”,尧舜知君子,作为君子的孔子知尧舜,其中蕴含着强烈的道统论色彩,但与理学不同,这是从制作立法角度而言的道统。孔子制作的正当性根据有二:一是“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此为法天而制的天道维度;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为历史性维度。孔子“述尧舜之道”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正意味着孔子对先王之道的继承和损益。《论语·述而》就记载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章郑注残缺,然皇侃便径直以《中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解③皇侃:《论语义疏》,第154页。,而郑玄之意在对《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解释中体现得至为显著:“(孔子)乐尧舜之道,思六艺之文章,忽然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也。”④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8页。此与上引《中庸注》意义正同。跳出理学关于孔颜之乐的话语体系,可以看到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儒关于孔子之乐的理解,并不在于如程朱所强调的偏重内圣的“乐道”,而是在于孔子能够获知尧舜以来圣王制作立法之道,并循此而作《春秋》,以待后来之王者取法。
三、孔子“山梁叹雉”的政治意蕴
“唯圣人乃能知圣人”指示的是孔子之“乐”,而“凡人不知”则说明在礼坏乐崩时代孔子之不遇,指示的是孔子之“伤”。如前所论,玄学家王弼认为圣人“不能无哀乐以应物”,“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①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640页。,皇侃《论语义疏》中也一再强调圣人无情,而宋明理学基本接受王弼的观点,如程颢“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②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页。。简言之,魏晋以来思想的主调是要化解圣人之“情”,然而郑玄却特别突出孔子本人的“伤”,如以下二条注文: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郑注:“有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者,伤不得见用也。”③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05,107,122页。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郑注:“言人年往如水之流行,伤有道而不见用也。”④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05,107,122页。
这两条可归纳为一句话:孔子见道之不行,感而自伤。显然,这一深切关怀世道而忧伤的孔子形象洋溢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与玄学、理学的孔子形象都迥然有异。而正如上节所述,《乡党》开篇最能体现孔子“隐圣同凡”的在世方式,而《乡党》末章则最能说明孔子之“伤”,此章郑注尤显精微与新奇: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郑注:“见君之异志,见于颜色,则去。回翔审观,而后下止也。孔子山行,见雌雉食其梁粟,无有惊害之志,故曰:时哉时哉!感而自伤之言也。子路失其意,谓可捕也,乃捕而煞之,烹而进之。三嗅之者,不以微见人之过。既嗅之而起,不食之。”⑤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105,107,122页。
乍一看,会觉得郑注非常突兀,也让人充满疑惑:子路捕杀雌雉而烹饪之,这一画面未免显得子路太无仁爱之心。在解答此疑惑之前,须疏通郑注文意。首先,据敦煌《论语郑注》文本来看,“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与之后的文字似是分为二章。故而我们可以看到郑注中从“见君”到“下止也”,其主语皆是孔子,并非雌雉。皇侃亦认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的主语都是孔子⑥皇侃:《论语义疏》,第261页。当然,郑玄、皇侃以孔子为主语,本就是在以雌雉喻指孔子。。其次,换个角度看,郑玄注《论语》往往将数章视为一个上下贯通的意义整体⑦乔秀岩:《北京读经说记》,台北:万卷楼,2013年,第183页。,此处亦当这样看待,“见君之异志”和“无有惊害之志”恰构成了对应。后来的朱熹正是将二者视为一章,并解释“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后下止。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22页。“色斯”的主语也就从郑注中的孔子变成了鸟。事实上,汉魏六朝间人也多将此二段文字视为一体,甚至将其与“色斯举矣”之上的“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一段文字统观以作解。故皇侃云:“谓孔子在处睹人颜色而举动也。”⑨皇侃:《论语义疏》,第261,261页。但是这样一来,就将“色斯举矣”所指涉的对象普泛化了,不再是特指孔子见君之颜色,而是见他人之颜色,失却了郑注所含强烈的君臣不相遇的政治色彩。相应地,他们的解释也就将“翔而后集”以及“山梁雌雉”的意义普泛化了,何晏《集解》载:“周生烈曰:‘回翔审观而后下止也。’言山梁雌雉得其时,而人不得其时,故叹之。”⑩皇侃:《论语义疏》,第261,261页。皇侃《义疏》言:“雉逍遥得时也。所以有叹者,言人遭乱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时矣。”皇侃所引虞赞之说亦谓:“譬人在乱世,去危就安,当如雉也。”①皇侃:《论语义疏》,第262、263,262页。显然,他们都将孔子之“叹”视为孔子叹“人”在乱世之不得时。但郑玄明确是在说孔子,认为是孔子在“感而自伤”。皇侃等人所描述的是一种无差别的乱世生活状态,而郑玄所看到的则是作为圣贤的孔子所身临的政治境遇。如果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细节,汉魏六朝间的解释没有一人像郑玄那样,将“山梁雌雉”解释为“雌雉食其梁粟”,而是解释为“山梁间之雉”②皇侃:《论语义疏》,第262、263,262页。。“梁”究竟是“山梁”还是“梁粟”,差异甚大,因为梁粟可喻指禄位,雌雉之食梁粟,恰恰是从反面象征孔子之不得其位,故孔子“感而自伤”,这便是此处郑注所包蕴之政治意义。
我们知道,据《论语》中孔子与子路的一些对话来看,子路往往代表了不能理解孔子之道的形象。置此勿论,郑玄这里还有更深广的意义世界,可与《春秋》“西狩获麟”并列而观。《春秋公羊传》记载:“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③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187—1192 页。郑玄深受何休《公羊》学影响,其解《中庸》即受其启发。“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何休注云:“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④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195页。麒麟之死象征夫子之没,麒麟作为仁兽而不为人所知,正如孔子作为圣人却周游而不遇。麒麟为王者或圣人而至,却为人狩杀,无“王者”出则孔子将不得见用;同理,“雌雉无有惊害之志”,为孔子而至,却为子路捕杀,孔子自伤不得见用。二者呈现出意义的同构⑤钱穆认为《论语》之编辑不成于一时,前十篇为第一次结集,《乡党》为末篇,而“山梁叹雉”则为末篇之篇末,“见孔子一生之行止久速”,“更见深义”,“得此一章,画龙点睛,竟体灵活,真可谓神而化之也”。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依郑玄之意,《子罕》篇“凤鸟不至”也正是说无王者出。
在《礼记·礼运》中,麒麟、凤凰俱属四灵。而《诗经·大雅·卷阿》言成王任贤之事,其中也出现了凤凰,以其作为太平的象征。为了便于分析,先将诗文与毛传、郑笺并置于下:
凤皇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传:凤皇,灵鸟,仁瑞也……翙翙,众多也。蔼蔼,犹济济也。
郑笺:凤皇往飞,翙翙然,亦与众鸟集于止。众鸟慕凤皇而来,喻贤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时凤皇至,故以喻焉。⑥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644,1646页。
凤皇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毛传:梧桐不生山冈,太平而后生朝阳。梧桐盛也,凤皇鸣也。臣竭其力,则地极其化,天下和洽,则凤皇乐德。
郑笺:凤皇鸣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视下,观可集止。喻贤者待礼乃行,翔而后集。梧桐生者,犹明君出也。生于朝阳者,被温仁之气亦君德也。凤皇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菶蓁萋萋,喻君德盛也。雍雍喈喈,喻民臣和协。⑦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644,1646页。
首先,“亦集爰止”之“集”也即《乡党》篇末“翔而后集”之“集”。故郑玄在诗笺中再次使用了“翔而后集”,这足以激发出强烈的隐喻关联。其次,郑玄以成王、周公时为周之太平世,凤凰出现于《卷阿》诗中正是指涉太平。再次,在郑玄看来,凤凰喻贤者,而非王者,梧桐才是王者。但是从西汉的毛传来看,并不以梧桐指涉王者,反推之,毛传也并不以凤凰指涉贤者。简言之,毛传仅仅是以凤凰和梧桐为太平的象征,所以才会说:梧桐太平而后生朝阳、天下和洽则凤凰来。由此可见,对此二章的理解,毛、郑差异甚大,绝非如清人陈奂所言“此笺申传也”①陈奂:《诗毛氏传疏》,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900页。。郑玄实则对毛传之说予以扭转。依郑意,此“贤者”正是此诗《小序》所言“召公”或“周公”,考虑到周公与成王共成太平,则此贤者即是指周公。由此,“众鸟慕凤皇而来,喻贤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就是说众多的德才之士看到周公在朝,故而来仕,他们所慕从者乃是贤者,而非在位的王者。众鸟之所以群飞的原因在于慕凤凰,而凤凰之所以居止于此的原因则在于有梧桐,这就象征着有王者出方能有贤者来辅佐,贤者之出仕是有选择的,正如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此即郑玄所言“贤者待礼乃行”。故而郑玄解释《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就说:“喻王当屈体以待贤者,贤者则猥来就之。”②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636,1647页。孔颖达深体郑意,谓:“兴贤者之将仕也,则相时待礼,择可归就。见其明君出矣,于彼仁圣之治世,乃往仕之。”③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第1636,1647页。“相时待礼”也即《乡党》“山梁叹雉”章的“时哉,时哉”。雌雉食梁粟,得其时;贤者出仕行道,居其位,食其禄,亦须得其时。雌雉之食梁粟即是贤者得禄位之象征,难怪郑玄要在诗笺中特别说明“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哪怕这句话源出《庄子·秋水》。
由此即可看到郑玄对四灵的解释有着一贯性,四灵为太平世而来,但是四灵的出现,却主要是因为有贤者圣人,如周公、孔子等。郑玄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四灵与王者的关联,转而着力构建四灵与有德且当居其位的贤者圣人之间的关联。周公、召公之得其位而有凤凰出现,相应地,凤鸟不至、麒麟至而被杀,则是孔子伤有道而不见用的象征。在圣王分离、德位不一的时代,实现太平之治,可行的路径是寻求明王与贤辅的共治,故孟子以辅正太甲的伊尹为志,而在郑玄看来,孔子则是以辅相成王的周公为志。成王与周公共治,恰构成了王与圣的合一,且周公所代表的贤者的存在恰是对成王所代表的天子之权力的辅正与限制,此亦为郑玄屡屡言孔子伤有道而不见用的真实用意。而周公制礼作乐以致太平,言外之意也即是,孔子亦制礼作乐,故郑玄《六艺论》直言:“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④此条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郑注:“孔子昔时,庶几于周公之道……末年以来,圣道既备,不复梦见之。”⑤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第75、82页。程朱将“衰”视为孔子不再具有“行周公之道”的心志,“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4页。,与郑玄截然相反,此说实源于皇侃《论语义疏》中所载孔安国注⑦皇侃:《论语义疏》,第156页。,而郑玄则将“衰”视为指称孔子晚年的中性话语,之所以说“圣道既备”,正是因为孔子晚年作《春秋》的制法之举。就此而论,圣人仍是制度、秩序的开端。可见在郑玄思想中,孔子制作《春秋》是上承周公制礼作乐的行为,周公是儒家士人进入政治场域的典范形象。周孔并称,制法在于周孔,而行道则有待王者,既然当其世而不遇明王,则修订六经以待后世。由此,孔子的“伤”方转化为仁者对于尧舜之道的“乐”;制作《春秋》,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也就从早年的梦周公归于晚年的“不复梦”。
余 论
郑玄通常并不在冠以中国哲学史名称的书籍中出现,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以范畴、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哲学命题为核心,这无疑是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和限囿的结果,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非常丰富的经典、经典注疏及其作者的思想也往往不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学界已对此加以反思,认为在肯定传统哲学史学科意义的前提下,应“尝试对经典做不以范畴研究为中心的哲学性探究”,这“不是排斥对古典思想做概念的研究,而是要直接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经验,把观念置于具体的背景中去理解”,或者更进一步,“从古典的生活经验中,发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进行有深度的哲学反思”①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本文所关注的“圣人”并非概念或范畴,却是中国哲学中至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凤凰”“麒麟”也不是概念,而是“物”,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意象或观念。郑玄《论语注》对《乡党》篇的重视,正是从孔子的生活世界出发,体贴孔子的内心以建构《论语》的意义世界。通过对此篇首末两章微言隐义的发掘,他将孔子塑造为秩序的发端者与法度的制作者,并在经传文本的注释中建构起了“山梁叹雉”与《春秋》篇末“西狩获麟”以及《诗经·卷阿》“凤凰于飞”相呼应的意义世界,对象征太平世的麒麟、凤凰形象加以新的理解,将二者与周公、孔子的形象直接对应起来,从而揭示出了《论语》所隐含的明王与圣贤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而孔子所身处的礼崩乐坏的生活世界与郑玄所身处的汉末乱世相互映照,郑玄对孔子制法形象的强调也就从侧面显露出了郑玄思想的意义世界,他遍注群经,尤重三礼,也正体现出了制法的思想抱负。
当我们将郑玄《论语注》纳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便能生发出很有意义的哲学比较:在郑玄这里,圣性天授,凡人不知圣人,故圣人谦卑或圣性隐藏不仅仅是孔子作为圣人的教化方式,本身就是孔子在世生活的必然态势;而在理学尤其是朱熹对孔子形象的认识中,则强调圣人的谦卑是出于内在修养而自然流露出的德性,这一德性是凡人通过学习修养可以达到的。类似地,郑玄对孔子感而自伤的突显,揭示了孔子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忧思,故孔子于晚年法天承圣以制作法度,这完全不同于后世玄学、理学对于圣人之情的讨论,其显著区别在于,玄学与理学对于圣人性情的讨论已基本脱离了孔子所身处的时代境遇,变成了对于什么是完满的性情进行讨论的哲学概念,孔子也成了“抽象”的圣人。也因此,郑玄对孔子德性的思考,更近于“政治德性”,即作为制法者的德性,而非就人能否学以成圣而言的“美德德性”。理学对圣人心性精神的推崇,重在道统心传,可以激发士人践履道德的内在动力,而郑玄以礼法制度为文明传承的核心要素,则体现出鲜明的“宪章”意识。思考中华文明的演变与传承,这两个维度无疑都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