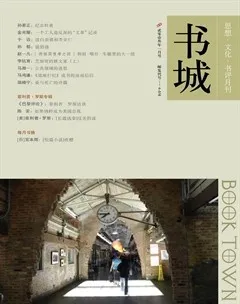走向综合
2024-01-03袁永苹
袁永苹
女性诗歌往往给人以一种单薄、脆、尖利的印象。这里所归纳的诗歌并不是特指某一个诗人的创作,而是总体上来说女性诗歌呈现出的一种倾向性。这种诗歌传统类似于狄金森,短小、精悍、凝练,呈现出一种自我化的精神样态,这种诗歌自然有自身的魅力,而且在创作上也更加容易进入,许多人刚开始写诗基本上都是从这种诗歌开始的。我把这样的诗歌称为“内爆性诗歌”,即这种诗歌的诗意依靠的是一种诗歌小容器内部的张力、语言弹性与断裂引爆诗意,这是一种诗歌的生成机制。如狄金森的这首诗歌《剖开这只云雀》:
剖开这只云雀,你将发现音乐
一卷卷,缠绕着如银丝
还未曾唱给夏日的早晨听
只留给你,当鲁特齐琴已变旧。
奔流,这热潮,你将看见
一波波,只为着你;
血红的试验!多疑的托马斯!
现在,你是否还怀疑这鸟儿的心意?(江枫译)
诗人通过语言的跳跃和语义的切分,实现了一种诗意的婉转,如鸟鸣,构造出一种精致的诗意,同时又将诗歌创作主体诗人的心意(有关爱恋)藏在跳跃的语句之间,最后通过一个设问句,向对话的“对象”发问,由此,鸟儿的心意与诗人的心意合二为一,完成了一首诗歌的整体构造。
纵观美国诗坛,狄金森的诗作为一种诗学传统已经内化为诗歌的血液。长久以来,许许多多试图与之呼应或者竞争的诗作,都是向内指向的,企图内爆出一种更大范围的诗意,以完成诗歌作品的诗意建构。我们从许许多多的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类创作的影子,比如文森特·米莱、玛丽安·摩尔、伊丽莎白·毕晓普、西尔维娅·普拉斯……包括二○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2023),众多女性诗人都是在这一传统中写作。有人说美国诗坛一个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传统,一个就是艾米丽·狄金森的传统,两位大师一阳一阴,一雄一雌,一个诗风庞杂澎湃,一个诗风内敛敏锐,这两大传统滋润着美国诗歌的发展。在我看来,露易丝·格丽克就是狄金森传统的继承人。她的诗歌拥有鲜明的女性诗歌风格,阴柔当中带有着刚毅与素美,接续了一种古典主义的诗歌美学,肃穆端庄,诗意悠远尖锐。然而与格丽克并称为“战后美国最杰出的女性诗人”(海伦·文德勒语)的另一位诗人,在中国却不像前者那样受到推崇,原因之一是这位诗人更为驳杂、更加智性,她一改女性诗歌的狄金森传统,从写作之初就进入了一种综合性的特质,这位诗人就是曾经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华莱士·史蒂文斯奖、被称为美国战后最杰出诗人之一的乔丽·格雷厄姆(Jorie Graham)。
格雷厄姆的诗歌中文译本只有一个,就是由金雯翻译的《众多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也许是由于格雷厄姆的诗歌过于艰涩难懂,难于模仿,也许是少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助推,她的诗歌在汉语诗歌中的影响力远不及露易丝·格丽克。这不但体现在对格雷厄姆诗歌整体的译介上,也体现在读者和诗歌从业者对诗人诗作的关注度上。可以说,网络上关于格雷厄姆的介绍只有几篇,而且大多都集中在图书推广的前后,在书籍出版之后就鲜有人问津。而对于格雷厄姆的阅读,除了她那首传播很广的代表作《鲑鱼》之外,也很少有其他诗作被广泛认知。
诚然,这样的遭遇与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不无关系。格雷厄姆的诗歌与格丽克的不同,格丽克早期作品受到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白倾向,这类诗歌以《头生子》为代表,描写了格丽克青年时代的一些私人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语言比较浅白,好读,容易进入,也容易共情。格丽克的自白与普拉斯的自白、安妮·塞克斯顿的自白有很大区别,更多地呈现出内省和隽永的特征,少有一代自白派二位主将的精神展演和自身分裂的语言特征。而后期,格丽克的诗歌风格则走向了隽永的诗风,并结合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等,创作了许多具有当代特征的另类精神内化的诗歌。与她截然不同的是,乔丽·格雷厄姆从创作初始就走上了一种在我看来带有她日后诗歌创作雏形的“综合复杂诗学”。
格雷厄姆一九五○年生于美国纽约,比格丽克小七岁,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视觉艺术家,父亲也是知识分子,良好的家庭出身让格雷厄姆拥有了知识分子的底蕴。成年以后接受的教育也是精英路线。她曾经在法国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学习哲学,后又到纽约大学学习电影研究,这两项学术背景给格雷厄姆的诗歌创作打下了思维底色,我们可以在她的一些主要诗歌中看到哲学和电影的思维是如何渗透进诗人的创作的。
格雷厄姆的诗歌写作生涯开始较晚,一九七八年,诗人在艾奥瓦创意写作班获得寫作硕士学位,这个时间诗人的年龄已到三十岁左右,可以说是人格各个方面比较成熟的时期。令我们比较吃惊的是格雷厄姆几乎没有很多诗人的那种比较稚嫩的习作阶段,我们也很难看到她未成熟的少作,可以说,她一登上诗坛就给人一种成熟诗人感觉。她最早的一部诗集《植物与鬼魂的混血儿》中的很多诗歌都是二十行以上,她几乎没有短于二十行的诗歌作品。像《鹅群》这样的诗歌,已经出现了格雷厄姆后期发展壮大的“长行诗体”,拥有了一种强悍的特征。她的第二本诗集《蚀》诗行继续拉长,诗歌的题材继续深入,诗歌朝着哲理、思辨、感性等各个方向综合发展。到了《美的意义》(另有翻译为“美的终结”)这本诗集中诗行呈现出一种长短句的交杂状态,研究者金雯指出,正是从这本诗集,格雷厄姆试图与早期的两本诗集中的短诗和抒情诗告别,这里格雷厄姆进行了自我的形式革命和反抗,企图构建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诗学。到了后面的几本诗集如《非相似性之域》《物质主义》中,诗歌的风格再一次被她推向极致,基本上呈现出一种长行的风格。而在她后几本诗集如《地点》《新诗》当中,则呈现出鲜明的实验性诗风,在这些诗集当中格雷厄姆企图利用自身的思维特征建构一种复杂的综合性诗学,这种诗学的一大形式上的探索就是她的长行诗的写作,这种写作被著名批评家海伦·文德勒称为“打破风格”(《打破风格》,李博婷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文德勒说:“当一个诗人不再写短行而开始写长行时,这种变化叫作打破风格,其含义比其他任何打破风格的含义都几乎更加重大。”文德勒是格雷厄姆诗歌的长久的观察者,她敏锐地指出了格雷厄姆诗歌创作的特征,以及这一特征在风格上的意义。可以说,长行诗比短行诗更加难写的地方就在于长行诗需要更多的“钉子”挂住诗体,同时,长行诗的句子需要更大的张力、弹性和柔韧性。诗行一旦拉长,就需要足够的支撑点。格雷厄姆的诗歌创作,从长行开始,必然走向一种综合性诗学。这里所谓的综合性诗学就是在诗歌中综合运用了叙事、抒情、抽象思辨等众多的表达形式,并运用声音、视觉语言(包括绘画、电影、雕塑)等综合性手法的一种形体上足够庞大的诗体。请注意,这里需要辨析的是这种诗体与史诗、诗剧本、叙事长诗的区别,这种被我称为“综合性诗歌”的诗体在整体上还是一种诗歌,只是手法和结构上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元化的综合性特征。
纵观国际诗坛,有这样能力的诗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虽然,近些年也有一些硬朗诗风的女性诗人出现,譬如英国诗人安·达菲,加拿大诗人、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但是,拥有像格雷厄姆这样的能力和强力,将诗体推进到如此庞大复杂的诗人并不多见。而在我看来,这种诗体正是未来诗歌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之前的那种短小、薄、脆,依靠着诗歌语言跳跃、意象挪移嫁接而成的诗歌已经无法涵盖如此复杂多元的当代图景,诗歌在手段和形式上都在呼唤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呼应时代的综合性诗学。可以说,格雷厄姆提供了一个方向。
格雷厄姆擅长从各个角度对世界的本质问题形成追问。这一追问的结果就是她的这些复杂诗体。我想将这些诗歌定义为“织体”。因为,这些诗歌就像是从各个角度织就而成的巨毯,悬挂在天与地之间一张巨大的需要书写的空白纸页上,而诗人的工作就是在其上写出她的无限诗行。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格氏诗歌的综合性。
我们先以她广为传读的一首诗《鲑鱼》开始。这首诗收录在她创作开始期的诗集《蚀》当中。诗歌开始于诗人对于鲑鱼的观察:
我曾经观察过鲑鱼,黄昏时分,电视上,在播放,
在我们的旅店房间里,去往
内布拉斯加的途中,身形迅疾、光芒闪烁,超越了美,超越了
美的重要性,样貌复古,
并不饥饿,甚至没有濒临灭绝,扎进更深的地方
遁入虚空。
它们跃至瀑布顶端,如登上阶梯,
或攀上岩石,腾挪飞舞,如一条金色的河流
与蓝色的河流背道而驰……(金雯译;下同)
诗人从对于电视上鲑鱼的描写开始,用精细的笔调刻画了鲑鱼群在岩石的衬托下飞跃金色河流的场景,将鲑鱼的壮烈和鱼群与周围岩石、瀑布之间的动态张力进行勾勒,呈现出一幅神奇景观。接下来诗人将意识拉入到自我的回忆,提到了“尝试自尽的母亲”“飞蛾”“蚂蚁”等意念中的細节,接着诗人的主体出现,叹息道:
我多么无助
这个静止的池塘
在上游的地方,
等待这金色刀锋
飞快地到来。
这是这首诗歌的上半部分,长达二十多行,可以说,有很多诗人在此处就可以结束这首诗歌了。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格雷厄姆用“无缝衔接”的方式“嵌入”另外一个完全可以独立成诗的“诗歌片”—
有一次,在室内,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曾在午间透过木质百叶窗张望
一个男人和女人,赤裸身体,眼睛闭着,
爬到彼此身上,
倒向露台地板,
飞驰—如两道金色水流
团团围住彼此,拥紧,
松开……
这个诗歌片很长,有三十行。这一诗歌片描写的是菲利普·拉金《高窗》式的“震惊”场景,但是与《高窗》不同,格雷厄姆出人意料地用“鲑鱼”统摄全诗,将两个看似独立的诗歌片拼接到一块,并用相互映衬的语言线索,逐个互相提醒和映衬,形成了一首更为复杂的诗歌织体。这样的操作令人不解,但是在读者勾连全部的诗歌线索,将鲑鱼的动作与男女的动作相互之间的牵扯关系加以构造,就能够理解该诗的意图:在一种自然的、难解的、秘密的强力驱使下,鲑鱼的无畏运动与人类的动作,都指向着一种对于抵达极限的渴望,对于自身本能的神秘顺从,以这一思维观念为内部思想,诗人将两首完全可以独立成诗的作品相互拼贴,构成了一个更为复杂、拥有角斗之力的新作品。
但是像《鲑鱼》这样的作品还只是格雷厄姆复杂诗体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她的真正能力是将诗歌建构在一个多重空间当中进行推演。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举一例,就是在她二○一二年罹患癌症之后的诗集《地点》当中的一首诗歌《阿马教堂消息,2011》。这是一首两百行左右的长诗。这首诗歌形体十分复杂,杂糅了电影叙事、微镜头、抽象思辨、主体抒情等诸多手法。
诗歌开始以一个设问开头:“这将会被如何/诉说,这个证据,我们的生命,所有的线索都已不见踪影?”从这个设问开始,接下来诗人陷入对于时间的思辨:“所有的时间一股脑压在上面,没办法向前,因此/原地打转……”在接下来的地方,诗人进入对阿马教堂一个石面上的雕塑的书写,关于这个雕塑,她在诗歌的注释当中给予了解释,雕塑是凯尔特神话中的战神努阿达,他是一位失去一只手臂的独臂英雄,后来一位医生为他安装了银质假肢,他夺回了王权。结合这一故事,诗人对于这位战神给予了怀恋般的刻画和互动性的抒情。诗人先是交代了战神的故事,然后进入了主体显现的抒情阶段:“此刻你再一次完整。几乎完整。我垂下手触摸那一处。三只手,同样/大小,我握住你的手,盖住它,我和你一起握住你身上的/臂膀。”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格雷厄姆通过教堂当中正在举行婚礼场面的跳接,完成了从玄思回到“现实”。在这之后,诗人单刀直入切到了对于阿马曾经发生过的暴力事件的回顾,她还原了爆炸一瞬间,被炸者的状态、精神内部的图景,包括动作、对于家人的思念等细节,动用了电影中的慢镜头效果。在这一场面之后,诗人又切回到了婚礼场面,“新娘走出去暴露在阳光里。我感觉有些什么我必须告诉她。祝愿你的梦想成真,我说,/手里握着导游书……”
诗歌通过一个旅行者的视角,勾连了婚礼和暴力镜头的场景,又将之与艾略特《荒原》中的“圣杯”般的形象依托,即用战神缺失的手臂来指出当代战争的残酷性与人类文明的衰落。可以说,在这首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企图与《荒原》进行文明重建对话的希望,即诗人企图通过“阿马教堂的消息”这一主题,完成的是对于人类文明、暴力、战争、和平等多种方面的综合思考,既是一种对于暴力以及暴力所建立的文明的担忧,同时也是对于纯净世界(以婚礼为依托)的一种向往和探究。值得注意的是,格雷厄姆利用自己强大的嫁接能力,几乎是不留痕迹地在叙事、抒情、玄思等多个维度来回切换,以构建她极为复杂的诗歌织体。
可以说,格雷厄姆的综合性诗歌写作虽然面临一种可能被指为非诗意化、散文化的危险,但是对于汉语诗歌的整体单薄、纵向、缺乏强有力作品的状况而言,仍给我们一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