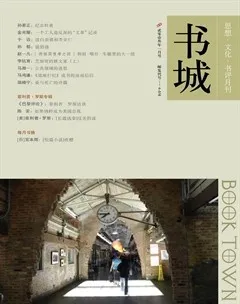回归万物有灵的世界
2024-01-03毛竹
他在寻找一个值得分有宇宙的灵魂。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圆形废墟》
在《塞斯的弟子》(Die Lehrlinge zu Sais)中,十九世纪德国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如此描绘“来临中的社会”(Kommende Gesellschaft):“他很快便察觉在所有东西中的联系、相遇、巧合。他看到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他的感官所察觉的东西涌进一幅幅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画面:他听、视、触、思同时进行。他很喜欢搜集异样的东西。对于他,时而星是人,时而人是星;石头是动物,云是植物。”(Novalis, Die Lehrlinge zu Sais, in Novalis, Schriften, hrsg. von P. Kluckhohn und R. Samuel, Stuttgart, 1960)这位狂飙突进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心谙自古希腊以来人与自然“大全一体”(Hen Kai Pan)的唯灵论传统,人只不过是“生命体共和国”(Republik der Lebendigen)的公民之一,与植物、动物、石头和星云无异。
万物整全一体的理念是德国浪漫派运动的核心观念之一,人与自然合而为一是哲人们关于未来世界的统一愿景。在歌德的《亲和力》中,万物莫不具有某种类似“亲和力”的化学磁场,自然对于男女主人公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每对男女主人公情感的推进都在与自然的曲折遭遇之中,这个自然既包括诸如山川庭园的外在周遭世界,也包括每个人对其内在本性(自然)的理解。这是自从十七世纪笛卡儿主义对世界祛魅化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精神试图企及自然的最后一次融合与反动,亲和力意味着人既以科学的眼光拆解自然,同时又保持与自然高度切近的意愿。
几个世纪后,当代世界呈现出了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现代人被裹挟着卷入了一个丧失了奇迹与魔法的“未来世界”,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机械世界闪耀的“灵韵”是来自赛博网络的字节跳动,自我压榨式的自由追求绩效将血肉之躯肢解成了困顿在格子间与算法之内的无差别“社畜”。现代性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异,所有异质性的古老文明传统变得整齐划一—现代人轻易就能乘坐飞机穿行到另一片散发异域风情的想象中的热土,却只会发现跟我们一样身着T恤牛仔裤喝着可乐吃沙拉的外邦人—无论是在金字塔、波斯波利斯还是在玛雅,现代旅人无须历经班扬笔下艰苦卓绝的朝圣者之旅,也丧失了卡尔维诺脑海中寒冬夜行人的朦胧意向,人们只需掏出手机按下快门,然后传输到社交网站接收点赞,所有旅行都变得朴实无华且枯燥。
在这个全无奇迹的祛魅世界,发掘葆有其自身文化传统的土著的生活習性、风俗、语言和世界观念的人类学研究,似乎成了亚里士多德式“拯救现象”的可能性之一。在其饱受赞誉的著作《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How Forest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2013)中,爱德华多·科恩直言:“我们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区别:森林在思考;当‘土著’(或诸如此类的其他人)想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被‘有一个正在思考的森林’这样的想法占据。”(《森林如何思考》,毛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 227页)“土著思考一个正在思考的森林”涉及一种试图超越二元论的人类学方法论视角转变,它意味着承认存在诸多正在思维着的自我(无论是细菌、花卉、真菌还是动物),这些自我与我们一道在世生存,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就不能仅仅将自身局限在只探索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表征其自身—与其他存在者的相互遭遇使我们被迫认识到,诸如看、表象、认识和思考等活动,不是专属于人类的事物,只是那些非人类存在者表征世界的方式与视角,与我们表征世界的方式与视角不同。
“思考一个正在思考的森林”意味着我们需要转换人的视角,参与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之中。在爱德华多·科恩看来,考察以鲁纳人为代表的厄瓜多尔阿维拉地区原住民与他们周遭世界的诸多存在者之间打交道的过程,能够作为人类学转换视角的“拐杖”(walking sticks,《森林如何思考》中频繁出现的双关语,字面义指亚马孙地区的一种具有保护色的竹节虫,隐喻义指帮助我们进行视角转换以解决人类学斯芬克斯之谜的思维工具)。采用森林之思的视角,放大了各种活生生的存在者之间相互遭遇的过程,呈现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超越人类自身“太过于人性”的既软弱又自负的人类中心主义。借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家安南·潘迪安(Anand Pandian)的评论,“科恩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境进入清醒、清醒进入梦境,两者交织在一起的空间”(Anand Pandian,“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2], 2014)。为了进入这个超越人类之上的领域,我们需要效仿漫游奇境的爱丽丝—“我会高兴地喝下死藤水,吃下红色药丸,跳进兔子洞”(同上)。
一、灵域、梦境与等级秩序
厄瓜多尔亚马孙河上游的阿维拉地区(Avila)是鲁纳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充盈着森林主人、灵、恶魔,灵师、生者与死者,以及周遭诸多“自我”的世界—爱德华多·科恩称之为“诸多自我的生态系统”(ecology of selves)。这些“自我”之间的沟通,形成了一种跨物种的混杂语言。在阿维拉地区,不同等级秩序的存在者之间有着视角转换的盲区:处于同一等级的存在者之间的交流,例如若一个人可以接受另一个人的观点,那么文字交流就可以起作用;但是不同等级之间存在者的交流,则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交流工具。按照鲁纳人的理解,亚马孙森林是属于森林主人的家园,灵师(萨满)是沟通森林主人与鲁纳人的桥梁,通常“高阶”存在者可以更为容易地理解“低阶”存在者,例如人类能够理解狗的语言,或者“灵”和森林主人能够听到鲁纳人的恳求,这种理解是直接而当下的;反之,低阶存在者要想获得高阶存在者的视角,则需要借助工具或者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实现,例如为了进入灵师的领域,灵师需要喝下死藤水或是吸入烟草等致幻物作为辅助。(《森林如何思考》,第208页)
这种施行萨满的技艺贯穿鲁纳人生活的整个视角,例如对于普通鲁纳人来说,喝可乐、穿白色兽皮,或者拿属于白人的物品,也是通过将高阶存在者的力量转移到其自身并增强其自身力量的一种方式(《森林如何思考》,第295-296页)。在诸多跨物种的沟通方式之中,梦境是一种有效的隐喻性语言方式,有时鲁纳人会在梦境中与森林主人直接沟通。通过梦境,鲁纳人认识到了自己与森林主人之间的差距,借以瞥见“灵”所看到的东西—动物是森林主人的家禽,植被是森林主人的花園。当做梦者进入所访问的强大事物的视角时,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关于梦的隐喻性解释,来纠正这种视角,并使其为自己所用。在爱德华多·科恩看来,亚马孙自我的精髓就在于,所有自我都被认为是萨满,并且所有自我都像森林一样思考(《森林如何思考》,第141页)。
与之相对,鲁纳人也尝试劝导他们的狗分享人类的视角,就像成年人教导孩子如何正确生活一样,将狗带入人类自我的主观领域,爱德华多·科恩称之为“犬之命令”(canine imperative)。如果想让狗理解人,就必须把狗的鼻子绑住,给这些狗服用致幻药物,也就是要将狗变成萨满。如果狗回嘴了,那么人就会进入狗的主体性质中,从而失去人之为人的优先地位。犬之命令意味着要让犬之自我暂时被淹没,让它的人类自我涌出。然而这样的治疗往往非常危险,许多狗根本无法在这场磨难中幸存,这些例子更加突显证明,狗必须依赖于其展示的人类品质才能生存—作为动物的狗在鲁纳社会之中没有立足之地(《森林如何思考》,第198-201页)。
人对狗的命令意味着人对于狗的权力关系,鲁纳人置身于一个等级秩序的世界关系网络之中,这种关系在狩猎的行为中得到了放大。鲁纳人认为,“灵”是使这种跨物种的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的东西。动物“意识到”其他种类的存在者,因此它们被认为拥有灵魂(《森林如何思考》,第150页)。例如刺鼠和狗都拥有灵魂,因为它们有能力“意识到”那些与它们有关系的捕食者或猎物。当一只狗吞下一只刺豚鼠的胸骨,一个人喝下美洲虎的胆汁或者吃下鹿胃中未能消化的牛黄石(鲁纳人认为这会提高它们探测猎物的捕食能力)时,灵魂转移就发生了,这表明某些跨物种交流的尝试模糊了生物学的界限。换言之,人吃掉动物并不只是为了摄取肉类,而且是将其作为自我吃掉,以便获得该动物的自我(《森林如何思考》,第151页)。
在与非人类的自我的接触中,动物如何表象我们的方式非常重要。在阿维拉地区,人必须敢于回应美洲豹的凝视。如果你凝视它,它会认为你也是一个能够回头看身后的存在者、一个与它相同的自我;如果你背对着它,它就会认为你是一坨可以吃掉的死肉(《森林如何思考》,第132页)。鲁纳人认为,美洲豹和人类享有某种平等,基丘亚语中“runa”的意思是人,“puma”的意思是捕食者或美洲豹;鲁纳人死后会变成美洲豹,或者遭受美洲豹的捕食后幸存下来的鲁纳人就是“美洲豹人”(《森林如何思考》,第3页、第132页)。为了不被美洲豹吃掉,鲁纳人需要学习美洲豹看待事物的视角,而灵魂作为超越肉体界限的东西,是“主体之间符号诠释的结果”(《森林如何思考》,第151页)。捕猎活动带来的伦理困境恰恰在于,它使人认识到了“生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人类的食物完全由灵魂组成的这个事实”,其他存在者同样也是自我(Eduardo Kohn,“Toward an Ethical Practice in the Anthropocene”,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1])。如若某个自我无法意识到其他存在者的灵魂或者与其他具有灵魂的自我相联系,爱德华多·科恩称之为“灵魂失明”(soul blindness),这会使其落入被捕食者的视角,从而变成“死肉”(《森林如何思考》,第165页)。
二、白、殖民与成为AMO
在爱德华多·科恩笔下,“繁茂且困难”(但丁语)的亚马孙森林并不是一座西方文明眼光审视下蛮荒的野蛮森林;万物有灵,世界是充满魔力(enchanted)并且具有灵性的(ethereal),这是《森林如何思考》一书试图还原出的鲁纳人的周遭世界。但是,视角主义并不完全是对等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在一次访谈中爱德华多·科恩提到,很多年前他试图跟一位土著联盟的领导人解释自己关于视角主义的见解,这位领导人问了他一个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当爱德华多·科恩向其展示,一只美洲豹会把猎物的血液看成木薯啤酒时,这位土著领袖回答说:“是的,可是当一个白人男子喝可乐的时候,他会把它看成什么?”(Eduardo Kohn, “A Conversation with Philippe Descola”, in Tipití: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Vol. 7: Issue 2, Article 1, 2009)
在阿维拉地区,“白”(whiteness)是可乐的对应物,就像土著对应于木薯啤酒、美洲豹对应于血液一般。“白”并不意味着肤色意义上的白人,而是代表鲁纳人关于自己作为文明的基督徒印第安人、身披白色皮毛的鲁纳美洲豹人(yura runa puma)、穿着白色衣服戴满美洲豹犬齿的赏金猎人,以及白的森林灵师的视角—“白”意味着占据主人地位的存在者的优势视角。鲁纳人与白之间关系的视角主义,概括了亚马孙地区的一段殖民与征服的历史。白人已经成为“万物”的“los amos”—主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鲁纳人参与其中的动态权力机制,却并不简单。(《森林如何思考》,第261-262页)
事实上,阿维拉人并没有为自己的民族命名。他们从不称自己为“Runa”(或 “Ávila Runa”),也没有使用“Kichwa”一词(这是当今国家土著政治运动中使用的民族名称)。在基丘亚语中,“runa”的意思就是“人”(《森林如何思考》,第270-272页);然而在西班牙语中,白人殖民者将缺乏文明状态,或者品种不可识别的杂种狗称为“runa”。在阿维拉地区,狗、鲁纳人、美洲豹、森林灵师和白人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总是具有彼此相对应的视角。在殖民历史中,白人曾在橡胶业繁荣时期用猎狗猎杀鲁纳人的祖先并奴役他们,鲁纳人长期作为白人和未经征服的非基督徒野蛮人(Auca,尤其指瓦奥拉尼人[Huaorani],鲁纳人长期以来的敌人)之间的桥梁,鲁纳赏金猎人曾经是帮助白人追踪瓦奥拉尼人定居点的猎手(《森林如何思考》,第193-194页),鲁纳人也充当着背扛着白人进入基多的挑夫角色(《森林如何思考》,第233页)。正如鲁纳人与狗和美洲豹之间的权力纠缠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鲁纳人也是森林灵师和白人殖民者视角中的“狗”。然而如果想要将自身视为一个“自我”,鲁纳人必须同样也占据那个占优势地位的捕食者的位置,对此唯一的选择就是,鲁纳人生而为鲁纳人、美洲豹、“白”人,以及“AMO”(主人,《森林如何思考》,第276页)。
在《森林如何思考》中,爱德华多·科恩描述了历经殖民和传教双重洗礼的鲁纳人关于自身之文明的肯定信念。鲁纳人的大洪水神话笃定地认为,鲁纳人才是应当上升天堂的圣徒,鲁纳人生而为“白”人,生而为基督徒,地狱是属于其他人(尤其是白人和黑人)受苦的地方。这则神话无比真实地揭示出了鲁纳人的民族理性,是保存和维系鲁纳人作为一个饱受侵略和奴役的弱小民族的自身存在和生命信念的核心观念。只有从这个视角上看,我们才能恰切把捉到爱德华多·科恩反复论及尼采的“太人性的”视角主义的良苦用心—鲁纳人世世代代以对其民族生命的保存和延续最为有利的方式流传这样一则大洪水神话,这个事实恰恰印证了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经典判断:越是热爱命运(amor fati),便越是有利于自我保存。这既是权力意志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鲁纳人在亚马孙热带森林的诸多自我的生态系统之中孕育出的、无比符合权力意志的生存论视角以及“形式毫不费力的有效性”(参看《森林如何思考》,“译后记”)。
三、回归万物有灵的世界
回归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曾经是十九世纪以来德国浪漫派哲人的终极梦想,也是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古已有之的信念,繁星闪耀的天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在云层和黑暗,唯在那一片洁莹澄澈之宇宙的最幽深处。在二○○九年与法兰西学院和巴黎社会科学高阶研究院的人类学教授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一次对谈中,爱德华多·科恩曾谈到,在给公众演讲亚马孙森林的万物有灵的世界时,人们对这种信念反而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可爱的小老太太们完全会赞同说,“动物有灵魂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玫瑰花丛也有灵魂”(“A Conversation with Philippe Descola”)。
对于爱德华多·科恩而言,“森林思考”绝不是隐喻意义上的,“森林之思贯穿鲁纳人和其他人的生命,他们以充盈的生命之独特的逻辑方式,密切地与森林之中活生生的存在者接触。那些活生生的存在者为森林赋予了魔力,使其有灵”(《森林如何思考》,第307页)。万物有灵论迫使我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并不是唯一了解世界的人,任何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都必须得到修正,诸多存在者与人类一样都是活生生的“自我”,与我们一道享有看待世界的眼光与倾听世界的耳朵。
在当今世界既有的形而上学框架中,“灵魂”曾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语,关于“灵魂”的研究早已被清扫入信仰的领域,或者经过形而上学提纯之后变成古典学研究中的问题标本。作为科学家的人类学家又如何能够在不被贴上“迷信”标签的情况下,将“万物有灵”的信念重新带回到概念工作和理论的对话之中呢?(Cf. Eduardo Kohn, “Anthropology as Cosmic Diplomacy: Toward an Ecological Ethics for Times of Environmental Fragmentation”, in Living Earth Community: Multiple Ways of Being and Knowing, Sam Mickey; Mary Evelyn Tucker; John Grim eds., 2020)
实际上,人类学家的尝试从不是个例,回归万物有灵世界的这个光荣与伟大的梦想,一直回响在哲学与文学作品之中,试图召唤出另一个与现代性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一九四三年,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赫尔曼·黑塞构思长达十二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虚构了一个未来世界,其中黑塞试图以尼采式超善恶的目光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意识,透过无区分的眼光考察各种极端对立的事物。这部晦涩之作既是一段柏拉图式的永恒梦境,也是自我和世界遭遇的另一种可能性,黑塞借助卡斯塔里的玻璃球大师之口教导说:“真理是有的,我的孩子。但是你所渴望的‘学说’,那种绝对的、完善的、让人充满智慧的学说却是没有的。我的朋友,你也不应该去渴求一种完善的学说,而应该渴求讓你自己完美无瑕。神性在你自己心中,而不在任何概念和书本里。真理是体验而得,真理无法传授。”(《玻璃球游戏》,张佩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这重梦境就像一面聚焦于想象之中的未来之镜,有时会与世界中不断涌出的真实相互回应。对于爱德华多·科恩而言,严格科学的人类学需要学术化的理论奠基,重新训练我们看待其他存在的视角,以及倾听其他自我的耳朵,这种工作意味着人类学需要一种存在论转向。然而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除了相信我们的玫瑰花丛也具有灵魂的信念之外,我们又如何才能发展出看的眼光和听的耳朵?二○二三年六月,哥伦比亚四名乌托托族(Huitoto)原住民儿童从飞机失事中幸运逃生,在亚马孙雨林的中心地带度过了四十天。这片名为亚拉拉库阿拉(Araracuara)的地区是属于美洲豹、巨蟒、鳄鱼、蚊子和其他肉食动物与有毒植物的世界,也是曾经哥伦比亚最危险罪犯的流放地,以及当前毒品走私团伙和反政府武装人员铤而走险的法外之境。被找到时,孩子们除了有些脱水、营养不良和蚊虫叮咬,并无大碍。孩子失踪后,当地原住民举行了传统的对雨林喊话的仪式,请求雨林放过这些孩子;每次进入雨林,原住民也会征得大自然的允许。对他们而言,森林是具有理性与意志的生命体,蕴含古老的能量,例如孩子们的祖母就坚定地认为,大自然会阻止这些孩子逝去,孩子们的母亲变成了“灵”守护孩子们。这篇报道是对森林之思的有力印证。据说军方发现幸存孩子的联络代码叫作“奇迹”,每重复一次,意味着有一名孩子幸存。当地时间六月九日下午四点左右,军队收到的广播是:“奇迹,奇迹,奇迹,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