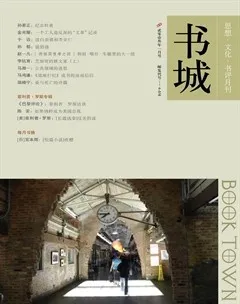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四时之外》:超越的存在与艺术
2024-01-03重木
重木
从《诗经·曹风·蜉蝣》中“朝菌不知晦朔”的微小蜉蝣,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不安,中国的古人们不断地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和存在,可能只是不断流逝的时间之河中转瞬即逝的匆匆一瞥,因此抵抗不断的消逝以及存在的崩溃就成为他们念兹在兹的创造与想象的动力。“诗是关于人生困境以及怎样从这困境解脱的咏叹”,除此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往往承担着相似的功能,即作为寄托、创造和展现古人永无止境地对抗存在焦虑的存在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关于存在本身的显现。朱良志在《四时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中,便通过对传统中国艺术的研究与探索,重现作为古人存在意识以及形式的艺术作品中的深邃与超越。
在《四时之外》中,作者认为中国艺术的灵魂正是清代画家恽格(号南田)所谓的“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四时之外”不仅暗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来龙去脉,也直指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时间。而恰恰是对于时间的敏感,导致古人对于自身的存在产生了最为清晰与亲密的感知。从这一不断流逝的时间中,他们所窥探到的存在真相便是,人类个体的有死性以及万事万物的荣枯循环。古人发现,时空作为人类存在的先验条件,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存在的基本框架,但同时也限制和界定了人类的存在形式,在《四时之外》的作者看来:“在时空二者之间,重视超越的中国艺术更注意时间性因素。”因此中国思想也大都展现出“时空结合、以时统空”的传统,而如何突破这一时间性对于存在的限制,以及为其所赋予的特定且秩序化的形式,便成为中国艺术不断探究和希望破解的难题。
古人对于时间性的关注,与他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和思考息息有关。中国古人早早地就意识到,自己生活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一基础性的心理时间结构或许从先秦诸子思考“何谓美好的生活”或是“如何重建和谐的天下”时便已经深藏其中。先秦诸子虽然思想各异,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想象或预设曾经存在着一个完满的时代,上古三代的黄金时期成为整个时间启动的源头,而也恰恰是因为三代的没落才导致时间开始流动,而在它奔流的方向中潜藏着衰败。古人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这一不断变化的时间之流中的沧海一粟,面对其汹涌往往除了兴叹,别无他法……或许正是为了抵抗这一无能为力感以及试图重新构建黄金时代,古人便想要成为“控制时间的‘英雄’”,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挣脱不断被形式化与知识化的历史之流,发现或是创造另一种新的存在—时间形式。
朱良志在《四时之外》中认为在中国古代艺术家心中,实际存在三种不同的对于历史的认知:一是“在时间流动中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这是历史现象”;二是“被书写的历史……具有知识属性,多受权威控制”;三是“作为‘真性’的历史,它既不同于被书写的历史,又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是人在体验中发现的、依生命逻辑展开的存在本身”。前两种历史都存在于时间之中,前者始终是混乱杂多的现象,后者则是形式化的知识,这两者最终不仅无法对抗时间的侵蚀,而且因其企图对时间的知识性切割、认知和书写而僵化了时间,从而导致其无时间性;唯有第三种“历史”,它与生命与存在共同生成,不断地流动、变化与创造,是一种“生命时间”,与存在紧密相连,而与知识和权威无关。这样的“历史”被古人看作是“生命真性”,它“不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普遍规律,而是人朴素本真的存在状态”。
因此,“四时之外”指的便是“超越时间和历史”,不作时史,仅仅依赖于“个体生命感觉”,好似一尾透网金鳞,从时间、历史、知识、欲望等密密织就的罗网中脱出,到生命的海洋中自由游弋。在这样一颗净明心体(或曰“古意”)中,存在不再受困于时间,身体虽然依旧会在其中不斷地衰败,但生命却已经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与天为徒”,而这才是存在本来的、真性的面目。因此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在中国艺术观念中,不断地出现关于“相”“真”与“幻”的讨论,“幻”与“真”的关系都被置于时间之中,是从“荣枯过眼、倏忽万变的角度来理解的”。对于那些无法在时间流逝中自我持存的东西,它们都是“幻”而非“真”,诸多向我们显现的“相”不过是暂时的、因缘际会的幻觉,因此只有“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人的身体、形象以及其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与荣誉,最终也不过是注定会毁灭的“诸相”,因此对其的沉湎只会造成不断的痛苦和焦虑,唯有穿透这些被时间所束缚的诸相,发现存在于这一切杂多之后的“真性”,生命才能真正变得灵活生动。
因此,“文人艺术所推崇的创造方式,不是再现或表现,而是‘示现’”,它是“两面历史镜”:“一面照出如幻的人生,映现出历史书写(第二种历史)的喧嚣和魅惑;一面照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本相,那种洞穿历史现象、脱略知识书写的第三种历史的本色。”对于古人而言,虚幻的“诸相”背后存在着一种顽璞的真性,它不仅是存在的本质,也是生命解脱之道。而艺术的位置正在于此,它具有“示现”的能力,以及对生命真性的直观。
区别于形式化与规范性的“知识时间”,存在的真性,即“生命时间”,有着自身的节奏,它是“天之时”,体现着天地本然的节奏(“天趣”),因此不需要人的巧心经营。“人作”在艺术创作中属于下层,只有“宛自天开”才是上品。这一中国艺术创造纲领恰恰体现了对于“生命时间”的追求,而非一种矫饰,因为“人”的知识及其能力始终是有限的、短暂且困于具体时间段中,因此只不过是暂时的“相”,是“幻”,脱离了生命时间的整全性,而只有把这一时间段(瞬间)置于“天”(永恒)之中,其才能获得生机,否则只是僵死的形式。因此,“瞬间永恒”这一于知识中的悖论在此被完美融合,如庄子所谓的“齐物”,无论是瞬间还是永恒都只不过是知识性的认知建构,实则二者都不过是时间性的展现,“它不是一种认识方式,而是对人朴素本真存在状态的描述”。
就如《四时之外》中所指出的,自唐宋以来的艺林中人所追求的永恒,实则是非时间的,而总是在“四时之外”徘徊,它也不是一种由外在赋予因此能够被规定和形式化的,而是“在当下即成心灵体验中实现的”,今生今世的此时此刻就是永恒,它是一种“永恒感”,而非庸俗所理解的对于物质的永远占有或是精神的不朽。对于中国艺术的精神追求而言,它不执不迷,由此才得自在,才能够不断地接续,生生才是可能的。朱良志在《四时之外》中通过对诸多艺术意境的考察来重现古人于艺术中的追求,如“杖藜行歌”“一朝风月下”与“茶熟香温时”,它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此刻的永恒感。因此,唐宋以来的文人艺术创造的核心精神被总结为“以简易的方式,超越变易的表相,表现不易的生命真性”,其目的依旧在于超越时间的秩序化束缚,而能够在“四时之外”开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存在。
中国古代艺术虽然同样注重各类技巧以及拥有一套完整且复杂的知识系统,但其根本精神或目的则始终脱离了对于特定时间点或时间段中存在的描摹,而往往是关切着在所有时间中的生命本身,穿过所有时间,才能抵抗时间之“短”“暂”,以及由此产生的“老”“幻”和“坏”的身体感受。这是关于生命存在的根本问题的追问,“目对脆弱易变的人生,到艺术中寻找底定的力量;深处污秽生存环境,欲在艺术中觅得清净之所;为喧嚣世相包围,欲到艺术中营造一方宁静天地;为种种‘大叙事’所眩惑的人,要在当下直接感悟中,重新获得生命平衡”……对于古人而言,这是关于自身存在最真实的问题,即使于当下,它也依旧咄咄逼人,因为“知识时间”在现代社会已经彻底宰制着人的生活、生命与存在,“真性”成为虚无缥缈的幻觉,可计量、可被知识化,成为判断生命重量与价值的总纲领,“生命时间”彻底哑然,时间依旧流逝但却不再穿过生命,它变成了荒漠。
《四时之外》通过探索古代中国艺术的精神、风格与其对于存在之“真性”的示现而企图重新激活这一渐渐被遗忘的古老感知和心灵能力,对于处在当下世界的我们而言或许尤为珍贵。作为一种始终处于不断流动、生成和差异化的生命(living),“知识时间”自始至终都企图通过对其的形式化和客体化而实现对其的管控,不断涌出的生命之流被切割成一段段可以计量的单位而能够在商品与生命的市场中被交换与流通,存在不再是生生不息,而成了僵死的物。就如朱良志在《四时之外》中所说的,“中国艺术家所在意的,是人们不明白时间的实质,心被表象世界掠去,被知识的叙述掠去,脱离了时间的本义,脱离了生生的逻辑,从而成了时间的奴隶”,而作为中国艺术的超然时间之思所渴望发现的“匝地清风”,是否还能够重新激活生命的动力,在此时此刻突破浮游的困局,则依旧有待我们不断地去省思、感知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