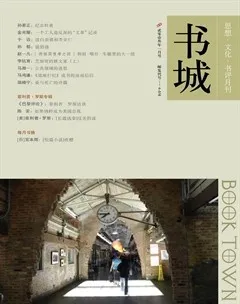风姿花传:宋朝人的园艺生活
2024-01-03周朝晖
周朝晖
宋代是中国历史文化一个关键发展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调整、变革和定型体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方面,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平民,日常生活都极富审美色彩,这是宋代较之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历史性进步,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对此,史学家钱穆曾用形象的描述展现了一幅宋代人日常审美生活的场景:
宋以后的文学艺术,都已经平民化了,每一个平民家庭的厅堂墙壁上,总会挂有几幅字画,上面写着几句诗或画上几根竹子、几只小鸟之类,幽雅淡泊。……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壶,一边总有几笔画,另一边总有几句诗。甚至你晚上卧床的枕头上,也往往会绣有诗画。……只要经济上稍微过得去的家庭,他们在院子里,往往留有一块空地,栽几根竹子,凿一个小池,池里栽几株荷花,或者养几条金鱼。……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面所说,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国史新论》)
这种变化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们追求美的生活的热情。宋代在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乱世局面后,致力于社会稳定以及生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劳动的价值,使得从事劳动的庶民阶层对当下和将来的生活有了憧憬和信心,心有余裕,才会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审美投以关注和兴趣。
其次则是在技术层面,农业科技的进步,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园艺的普及。在前代农业生产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宋代的种植技术出现了突破,扦插、压条、嫁接、保鲜等普遍运用于园艺之中。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专门的花圃市场和从事园艺的专业户。园艺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各种观赏性花卉的资源同时,也为社会园艺风气的形成提供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园艺成为两宋时期,人们普遍热衷的一项雅好,进一步成为全民审美的时代特色。
花花草草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城市发展时期。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汴河两岸繁荣的都市景象,细腻地展现了市民多彩的社会生活,各种情状跃然纸上;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则以亲身见闻经历的角度,追忆北宋帝都东京汴梁的盛世繁华。市民阶层前所未有的扩大,是两宋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城市中的居民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赏花成了当时的重要娱乐方式。而城市的赏花胜地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呼应了这种需求。
在宋代,据说皇家禁苑和私家园林都会定期对外开放,供市民观赏游乐。此外,寺庙里的花园庭院,也是两宋时期的公共园林场所。比如北宋开封太平兴国寺的牡丹绝艳天下,欧阳修记载“淳化三年冬十月,红紫盛开,不逾春月,盖冠云集,僧舍填骈”。在寺僧园丁的精心培育下,开发出玉板白等精品。扬州的龙兴寺的山子、观音、罗汉和弥陀四个僧院培植出四种各不相同的品种,被称为扬州芍药四绝,名冠江南,远近争相观赏(王观《扬州芍药谱》)。
据孟元老记载,宋都皇城汴京内外,花木成荫,到处是葱茏锦绣的园林:“大抵都城左右,皆是园圃,百里之地并无闲地。”与汴京相比,西京的古都洛阳的园林盛况更胜一筹。洛阳是汉唐名都,在历代皇家苦心经营之下,这里的园林文化底蕴深厚,名园佳苑驰名海内,有“天下名园重洛阳”之盛誉。据北宋学者邵伯温所见,当时的名园有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归仁园等。这些私园讲究花木的配置,如《记归仁园》中写道:“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千亩,南有桃李弥望。”值得注意的是,所记天王院花园子,则更像是一个公共花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以极其写实的手笔记录了他身临其境观览游历过的十九所洛阳名園,这些园林大多数是在汉唐池苑旧址的基础上兴建的,其中大多数是私家园林,书中对所记录的各个名园,从整体布局、假山、水池、建筑到各种花木都有极为翔实的记载,代表北宋时期园艺的最高成就。
到了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平江(今苏州)则代表了南方园林的另一种格调和气派。江南园林以苏州为盛,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录的园艺名所和园林建筑有三十多处。临安紧邻西湖,周围群山环绕,到处是绿树成荫,花卉争艳。南宋朝廷在吴越国建都杭州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杭州西湖园林。周密《武林旧事》卷四、卷五里记载了大量当日临安的亭台园池,如皇家的聚景园、清河邵王张俊的真珠园、平原郡王韩侘胃的南园、太师贾似道的集芳园,等等。俗话所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根基便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
此外太湖之滨的吴兴(今湖州市),同样是士大夫聚居的地区,文人士大夫的私家园林成了一大亮色。《吴兴园林记》中涉笔的吴兴园林达三十四处,恰与《洛阳名园记》所记成南北呼应。所记园有以花木造景取胜的,如莲花庄,四面环水,莲花盛开如锦云万顷;又如赵氏菊坡园,前为水溪,溪流之上修筑了堤与桥,夹岸密植芙蓉、垂柳,有数百株之多,溪中沙洲植名菊百种以上。《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原是中原华族,祖上为官已历五代,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之人。北宋灭亡后随赵宋政权南迁,定居于山柔水媚的吴兴,后半生以游历名园,写诗读书为乐,他说:“尝评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
除此之外,在西蜀成都、闽南泉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里都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园林。这些园林,除了山石、泉池、台榭之外,花草树木的种植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且每个地方,根据本地气候风土特点,都有代表本地特色的植物品种,如洛阳的牡丹,成都的芍药,杭州的梅花,福建漳州、泉州的兰花,及扶桑、刺桐之类的异国花卉,各地名花嘉卉争奇斗艳,共同构成了两宋繁花似锦的园林锦绣风光。
宋朝的文士阶层,对居住环境的审美要求很高。所谓环境要求,未必追求豪华奢侈的居所宅邸,而是对居住环境的诗情画意追求一种美的尺度,诚如苏东坡所说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肉与竹,分别代表生理嗜好与清雅脱俗的品位。在这种时代风气下,文人间私人造园的风气很盛。司马光晚年退官后,在洛阳构筑私人别墅“独乐园”,读书著述,安度晚年。关于独乐园,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有记录: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逾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抄者,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独乐园”虽小,却远近闻名,乃至成为被欣赏钦羡的对象,并不在于园子本身,而是这个私家园林反映了主人的某种高雅脱俗,洁身自好的儒家修养。
南宋洪适,官至右丞相,晚年退休后回到故乡饶州鄱阳。他利用故居依山面水的地形,建造的私人园林“盘洲”,占地约有百亩,在两溪之间,水源充足。园内有“洗心阁”“有竹轩”“双溪堂”“涧柳桥”“一咏溪”“索笑亭”“野绿堂”“隐雾轩”等多处景观。引人注目的是,洪适从各地引进珍稀花木品种,栽入盘洲中,分别以颜色来划分,非常丰富,比如白的有广陵芍药末利(茉莉)、水栀、安石榴等;红的有扶桑、杜鹃、丹桂、木槿、山茶、海棠等;黄的有菊花、木樨、棣棠、蔷薇、蜀葵、秋菊等;紫色的有含笑、玫瑰、木兰、瑞香等。真是万紫千红满园锦绣,一年四季,次第开放。
在宋代,未必人人有条件营造自己的私家园林。但对诗意安居的审美已经深入人心,文人会根据自己的条件处境,为自己营造优雅诗情的环境。宋代散文中书写私家雅居之乐的篇什不少,可能和这一时代风气有关。
宋初诗人、散文家王禹偁,历任右拾遗、翰林学士等职。他秉性刚正,敢于直谏,屡屡触犯权贵,晚年被贬谪湖北黄州,论才情抱负、仕途际遇,与后来的苏轼很相近。贬谪黄州期间,他写了一篇《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的散文,记述他在城西一隅倾颓的荒地中,用当地盛产的竹子盖了两间小楼。小楼的建材因地制宜全部采用本地盛产的黄冈大竹,屋顶用粗大的竹子剖开平铺屋顶为瓦,墙体均用竹竿,室内也都全用竹子做成。别看小楼简陋,住竹楼里风光无限,遥对远山,近瞰河洲,是一幅天然山水画。最妙的是竹楼里的音响:夏日急雨声如瀑布,寒冬密雪声比碎玉,而平日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王禹偁左迁的黄州,在北宋时期是一个穷乡僻壤,只要读苏轼在这里写的诗文就知道了。但王禹偁在有限的条件中美化自己的环境,营造了一个诗意安居之所,一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苦中求乐的达观士人形象跃然纸上。
含英咀华
花草与宋人日常生活的密切,还体现在花卉成为食材进入食事中。花卉入馔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除了少数有毒,或者有刺激性气味的花卉之外,大多数草本、木本花卉都可以食用,有的本身就被归入蔬菜之列,如萱草、百合等。屈原的诗中,既用鲜花供奉神灵、祖先、逝者,用香花熏染衣冠,也以花瓣为食。荆楚一地,气候潮湿温暖,草木葳蕤、花卉繁多,“含英咀华”是楚地自古沿袭的风俗。
后来,食用花卉与道家医食同源的观念相结合,还包含了医疗养生的目的。《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着合欢花、木兰、杜若、菖蒲、芍药、菊花等多种花卉的药用和食疗功效。也许是这个原因,记录饮食之道的书在古代中国目录文献学中,被归入道家范畴的医方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说:“医方者,所以除疾病、保性命之术者也。”所谓保性命,除了尊生、养生之外,还包含繁衍生命的意义。魏晋时期,花被认为是植物之精华,随着炼丹求道风气在士人中的盛行,逐渐被作为丹药食用。但除此之外,有意识将鲜花入馔在宋代之前实属少见。
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鲜花入馔的做法一下子多了起来,甚至成为一种饮食风尚。当时出现的各种花卉谱录书,都对记载的花卉有关于可食性的介绍,比如范成大所著《菊谱》中,记载着甘菊、黄菊和白菊三种可以入药的菊花,其中甘菊可以入馔;陈景沂《全芳備祖》中写了用茉莉花熏制花茶的方法,被认为是福建茉莉花茶的最初源头。淳熙年间(1174-1189),南宋朝廷在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者,老诗人陆游应邀参席,并记下了国宴菜单:
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炙、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公式子、髓饼、白胡饼、环饼……
从菜单可以看出,宴会的菜肴充分照顾了招待对象的饮食习俗,大都是按照塞外游牧民族的口味嗜好制作的。不过个中也有体现南宋饮食饮馔新风的菜肴,比如“莲花肉油饼骨头”这道主食,就是用莲花瓣和面做成的肉煎饼。还有将柰花捣成泥,和入面粉,再切成面条。这种花瓣入馔的味道如何不得而知,但形色的优雅则不难想象。花瓣不但可以做成食品,也可以制成佳酿,也就是用花瓣来泡制酒。这方面,陆游也留下了文字记录,在《新酿熟小饮二首》有“篱菊犹堪采落英,一尊玉瀣酿初成”之句,写的正以菊花落英来浸泡初酿的米酒。
宋代以花卉入馔的食尚,最集中体现在南宋的食谱著作《山家清供》中。此书作者林洪(1137-1162),是福建泉州晋江安仁乡永宁里可山(今石狮市蚶江镇古山村)人,绍兴年间进士。《山家清供》是我国一部重要的烹饪著作。据书中序言说,书名源自杜甫“山家蒸栗暖,野饭射麋新”的诗意,“山家”指的是山居人家,与官宦商贾之家相对,“野饭”者,蔬食淡饭之谓,与豪门上等饮馔相对。全书分上、下两卷,收录了当时流传的菜点、饮料制法约百来种。上卷记载了青粳饭、碧润羹、苜蓿盘等四十七种,下卷记载了蜜渍梅花、持螯供、汤绽梅等五十七种。与前代的食谱相比,《山家清供》所记的菜肴大多数是用花卉、水果、野菜等制作而成的,尤其是鲜花入馔。书中记录了十多种花卉料理的食单,如“莲房鱼包”“梅花汤饼”“菊苗煎”“牡丹生菜”“梅花粥”“蜜渍梅花”等,虽然食材普通、烹饪简要,但菜品形色素雅、滋味清淡中余韵悠长,极富于艺术审美。这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转变。
群芳谱志
时代热点在哪里,出版就在哪里。宋代园艺风气之盛,还可以从当时与园艺有关的谱录的出版表现出来。
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农书问世。汉代后农书渐多,但失传、散失的不少。相比之下,中国利用并栽培花卉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古农书中的反映却更晚。唐代以前的农书中,基本没有花卉的内容。汉代《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书,虽记有园艺作物,也只限于果树、蔬菜。这一现象,除了花卉生产发展远较其他作物迟缓之外,还有认识上的原因。如贾思勰就在《齐民要术》序中称:“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故而,古代早期的农书中很少出现对观赏性植物的介绍,或许与早期农学家的这种以农为本的价值观有关。不过,唐宋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这种现象大为改观,各种园艺研究专著层出不穷。据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所载,中国古代有关花卉的书籍达一百五十种以上,现存的约九十种,其中宋代出版的占了很大一个比重。
地域性、专業性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花卉园艺著作的一大特色,所记花卉从种类、品种到栽培技术,都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因此此类著作大都冠以地名,如《洛阳牡丹记》《天彭牡丹谱》《桂海虞衡志》《金漳兰谱》等。在近世以前,栽培技术一向被精英阶层视为“鄙事”,尽管也有人从儒家价值观出发,提倡学稼、课耕,但真正愿意脱下长衫、躬耕园圃的士大夫并不多见。因此,著书论花卉,往往成为古代文人雅事,书中的生产经营意识比较淡薄,甚至有的根本不涉及栽培技术,只是欣赏、品评,或辑录掌故、逸闻等的趣味性著作。但其中也有写作比较严谨的书,在辑录前人所述外,加上亲身实践的经验,细细道来,已有某种科普的成分在其中,十分可贵。更有偏重辑录前人有关诗文的,算是文艺型的科普文章的前身。尽管受历史局限,但历代花卉著作仍然在研究中国观赏植物的起源、引种、品种演化与改良、栽培与繁殖、应用与欣赏等方面,为后代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形成并发展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花卉文化等方面,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出版成就可以说处于世界先导地位。
通谱类植物书是收录多种花卉资料于一书的一种综合性著作,如《洛阳花木记》《花史左编》《花镜》和《群芳谱》等。现存最早通谱类著作是唐代后期宰相李德裕撰写的《平泉山居草木记》,书中记述他所搜罗的珍奇花卉种类和产地,颇为可观。虽然更早的花木著作还有后魏元欣的《魏王花木志》、隋代诸葛颖的《种植法》和唐代贾耽的《百花谱》等,惜乎都已失传。随着专谱类的花卉著作,在宋代的大量出现,通谱类植物书也随之兴起,其中以周师厚《洛阳花木记》(1082)最早,也最具代表性。该书列举牡丹品种一百零九个、芍药品种四十一个、杂花八十二种、果子花一百四十七种、刺花三十七种、草花八十九种、水花十九种、蔓花六种;花品之后,继以四时变接法、接花法、栽花法等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1175),志花部分只记广西独有的花卉十六种,文字简练,翔实可靠。与上述两书不同,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所记植物虽多,但重点在辑录赋咏花卉的辞藻,其广收博采,诗词尤多,虽于植物学而言乏善可陈,却也开了中国古代花卉类书重文采之先河,故也占有一定地位,至今我们从周瘦鹃、贾祖璋等名家的花卉小品中依然能感受到这种源远流长的风雅气质的留存。
二○二二年十月八日初稿
二○二三年七月五日修订